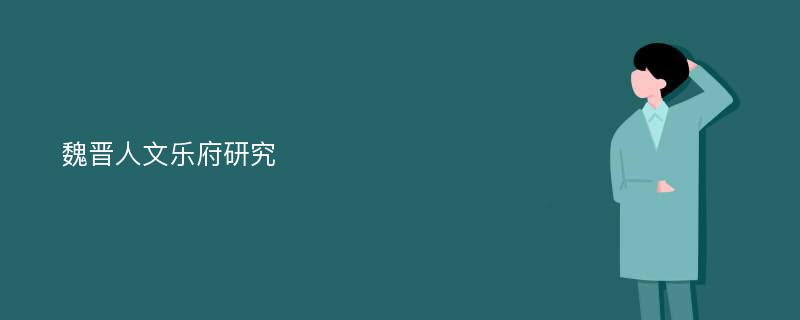
邹晓艳[1]2001年在《魏晋人文乐府研究》文中提出魏晋文人乐府是中国文学诗歌发展史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乐府诗体的重要转型期。汉魏之际的诗歌振兴是从乐府创作开始的,曹氏父子积极创作,使乐府得到文人的重视,转入文人手中,并且抒情性加强。魏晋乐府在题材、形式等方面实现了文人化的转变。 本文在提出了论述的问题后,第二章从生产基础、社会风气、音乐变化以及文学自身的传递规律等方面探讨了乐府成为魏晋文人创作的一种诗体的原因。而所谓乐府文人化,实质即文人对传统主题、题材和语言选择、创变的过程。本文第叁章对魏晋乐府的重要题材多有叙及,目在勾勒乐府题材的变化。魏晋乐府继承了汉乐府的传统题材又有所拓展。现实主义传统、男女情思、宴游行乐、生命意识等题材继续发扬,却呈现出新的面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乐府是一方面它仍保持着歌谣的抒情性,却失去了民间歌谣的活泼性和多变性,另一方面则融合了文人的精神。可以说,魏晋乐府是歌与文人精神的结合,在保持乐府歌形式的同时,加强了文人抒情言志。 魏晋文人对汉乐府古题作了总结,而更为重要的是开创“篇”题。魏晋乐府在表现手法、篇章结构、语言形式等方面自成特色。篇章复沓、铺陈的特点之形成,是魏晋文人表现技巧加强以及乐曲曲制发展的结果。而随着诗人对表现技巧的自觉追求加强,以及艺术素养的提高,乐府素朴的形式变得复杂,丽藻和徘偶成为乐府诗语言发展的新趋势。这是第四章主要论述的内容。最后简单提及了乐府五言与徒诗五言的关系。
吴相洲[2]2015年在《现代乐府学史概述》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成立至今百余年间,乐府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宫廷乐府活动宣告结束,相关记录研究已无从谈起;受西学观念和方法影响,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故本文从文献、音乐、文学叁个层面进行总结。因受社会总体环境影响,大体呈现前30年相对冷清,中间30年论题单一,后30年丰富转型,近十几年走向自觉的格局,时间上与1912~1949年、1950~1976年、1977~2000年、2001年至今四个时期基本相当。
陈岸汀[3]2015年在《“华化”与分型:汉唐琵琶的类型特征、演奏方式及其人文存在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首次在中国音乐史论域中,就中国古代琵琶的历史发展提出乐器类型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从乐器类型和人文类型两方面进行了概念界定,并就类型特征、演奏方式、类型的分型以及人文存在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建构。类型分类方面,琵琶之共鸣箱体、琴柄(琴颈)、共鸣箱体和琴柄(琴颈)的关系、琴项依次是为辨识形制结构特征及其演变的重要依据,弦数变化是文献叙述体系中对具体下级类别作区分的重要概念,本身不作为一级分类的依据。对类型特征的复杂性,提出宽、窄,长、短,曲、直,大、小四组变量并界定。按逻辑关系讲:圆形共鸣箱-直柄琴体类琵琶和梨形琴体类琵琶是中国汉-唐琵琶类型的一级分类。圆形共鸣箱-直柄琴体类琵琶以下,二级分类可见长柄、短柄类琵琶。结合地域音乐文化因素,长柄类琵琶下分Ⅰ式和Ⅱ式,Ⅰ式之下还发展有圆形共鸣箱-梯形长柄曲项琵琶。Ⅱ式在文献的概念叙述中成为唐代阮咸琵琶的前身。梨形琴体类琵琶的二级分类中,有短颈、长颈类琵琶,二者之下均有直项、曲项之分。短颈直项类琵琶以下还有五弦和非五弦两种,受人文因素的影响,五弦琵琶与上一级的短颈曲项类琵琶,在共鸣箱体的变化上都可分见宽体、窄体和小梨形之别。事实上,中国琵琶的演进决非是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其类型的传播和演变夹杂在时间和空间坐标中,受民族-文化-历史-地域四个因素的影响,呈现多向复杂的发展态势。因此,文章都是在时间和空间变化中梳理类型与分型。在对应文物、文献名实及其所指方面,考虑形制与人文因素的关系,另提出有“西域琵琶”和“汉式琵琶”、龟兹制琵琶和“唐制琵琶”两组两相对应的关键词。关于起源:典型符合傅玄《琵琶赋》描述的圆形共鸣箱-长柄Ⅱ式琵琶,即阮咸类琵琶的前身,是汉魏两晋时期中国琵琶的主流样式。其创制和定型发生在河西地域。河西地有能够影响琵琶定型与发展的非单一性的多元文化条件,有能产生娱乐性琵琶音乐文化的社会经济环境,特殊的汉文化土壤使这一地域很快创制产生出既借鉴有更西地域的琵琶形制特点,又扎根在汉文化思维基础上的阮咸类琵琶。魏晋名士是这一时期这一琵琶类型的主要使用者和鉴赏者。关于传播:结合地域音乐文化,汉魏至南北朝时期形成有四大系别琵琶:龟兹地的琵琶、河西地的琵琶、东胡琵琶及南朝南方地区的琵琶;形成明显可见的叁条流布主线:一是出现在汉魏时期的龟兹和凉州之间,二是两晋南北朝时期自凉州到中原北方多地的延伸,叁是汉音乐文化的南迁。隋唐中心社会的琵琶及琵琶音乐文化,总体上承自北朝琵琶音乐文化。其构成一是有西域龟兹琵琶的渊源,二是有凉州地琵琶音乐的传统,叁是有北朝北方诸胡音乐风俗之因素的影响,四是来自南朝南方清商乐文化的延续。关于演奏方式:从文献文物互证的角度梳理有拨弹、指弹、运拨、搊弹、摘阮演奏手法,就唐代叁种典型琵琶音乐风格及其与传统拨弹、运拨演奏和搊弹手法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华化与分型方面:中国古代琵琶之圆形共鸣箱-直柄琴体类琵琶和梨形琴体类琵琶,经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代沉淀为阮咸和琵琶,二者都涉及华化问题。前者华化的系列工程,从结果上展现为:乐器名实皆具、有文人参与定名;渊源上与“弦鼗说”直接相连、突出了传统汉乐所出的意图;竖抱摘阮的演奏方式就此与横抱运拨相别,形成“摘阮”与“搊弹”二分的提法;强调了上承魏晋名士之风的文人音乐属性,逐渐淡出了宫廷享乐音乐文化氛围,保留了作为华夏正声“清商乐”重要参与者的声誉,此后主要用在文人雅集的活动中,成就了“雅声发兰室,远思含竹林”的文化定位。总览其华化过程,可谓“脱胎换骨”。后者来看,唐社会完成了对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胡乐文化的沉淀,在全面吸纳的过程中建立起了新的琵琶音乐中心文化,并以此在空间上向其它地域辐射,时间上纵深影响了后世中国琵琶的发展,华化过程实有“洋为中用”的特点。
柳卓娅[4]2017年在《出土文物与汉代乐府诗歌表演研究》文中认为汉代乐府是一种涵盖诗歌、声乐、舞蹈、器乐等多种形式的综合性表演艺术,流传了两千多年之后,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些乐府歌辞以及一些简单的配乐和表演的文字记录。在今天的学科分类中,汉乐府已经进入了文学的范围,属于汉代诗歌的范畴,在文学范围内,经常采用的提法是"乐府诗"。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汉乐府曾经是一个综合的表演性的存在,这种存在方式对它的语言表达和文学特性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要追溯它曾经拥有的表演性存在方式,尽量求得对乐府歌辞和艺术更加准确的和综合的理解。本论文把汉乐府歌辞放在表演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充分利用出土文物对汉代乐府诗歌的表演性特点进行系统研究,虽然不可能完全展现汉代乐府诗歌表演的原形和全貌,但是希望能在此方面取得一定的突破和进展。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组成。首先是绪论部分,主要对本文涉及到的重要概念如出土文物、乐府、表演等做出界定,然后对目前学术界已经取得的关于汉乐府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特别是对在汉乐府表演以及出土文物与汉乐府表演结合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重点介绍。在此基础上,介绍本文的研究空间、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接下来是正文部分,主要由五章构成。第一章是汉画汉简与汉乐府叙事诗情节性表演研究。汉代乐府的叙事性情节性很强,汉代画像石中有很多同题材的故事画像,人物故事、乐府歌曲与故事图画的流传往往是互相照应的,这些图画和故事有助于推进我们对汉乐府叙事诗的把握和研究。汉乐府相和歌清调六曲中的第六曲《秋胡行》,古辞早已流失。汉代流传的"秋胡戏妻"故事以及汉代画像石"秋胡戏妻"画像等一系列文物的出土使我们考察《秋胡行》古辞的本来面目成为可能。1993年江苏东海尹湾汉墓编号为13号的木牍上记载的书目《列女傅》应该是刘向编撰《列女传》的重要取材之一,其中"鲁秋洁妇"故事,应是《秋胡行》演唱的记录。由此古辞《秋胡行》的歌辞考察对汉乐府歌辞留存研究就有了重要启示。①沿着这条思路下去,我们发现汉代乐府借咏鸟来歌颂爱情,汉代辞赋故事多以咏鸟来升华爱情,乐府和叙事辞赋又大都是可以表演的。近年来一系列出土文物,特别是敦煌汉简关于韩朋的材料、尹湾汉墓《神乌赋》的出土,表明咏鸟歌和爱情辞赋除部分题材相同并可以演唱以外,还有更深层的关系,即二者可能是同一部说唱作品的不同部分,咏鸟歌本身不一定讲故事,却可以是在爱情赋讲故事之前或之后演唱的。据此也可以推断,一部分民间乐府和俗赋应该是同源关系。第二章是出土文物与汉代乐府仪式歌曲表演研究。汉代社会对前代礼乐文化有很多的继承和发展,在汉代乐府中有大量的仪式歌曲。大量的金石乐器的出土特别是刻有"嘉至"、"安世"等文字的编磬的出土证明汉高祖《登歌》、唐山夫人作的《房中祠乐》有很高的演出规格,《房中祠乐》为祭祀宗庙之乐,有时也用于宴飨。汉代金石乐器出土很多,丝竹乐器也很多,而且制作精巧,说明金石乐器在汉代郊庙乐府演奏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丝竹乐器也取得了越来越高的地位,汉代雅乐并没有随着俗乐的兴盛而衰亡,而是形成了新的雅乐体系。这一雅乐体系虽然备受一些朝臣的非议,其发展趋势却是不可阻挡的,而且最终形成一代乐府强音。汉武帝将《天马歌》用于郊庙演奏也是备受争议,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篇以及长沙马王堆叁号汉墓着名帛画"神祇图"中"太一"神的重要性说明"太一"在汉代人思想意识中极高的地位,汉武帝明写天马,实则在写对宾服四夷一统天下、遨游天界实现长生的愿望和祈求,这和汉武帝本人的诗性气质有很大关系,也是其礼乐教化的一种手段。汉代宫廷驱傩仪式非常隆重,其中也有歌曲演唱,汉代画像石中的驱傩图展示了驱傩歌词中的傩形象;驱傩歌选择儿童合唱是汉代人认为儿童能够驱妖除魔的心理反映,汉墓镇墓形象设计中的儿童塑像可以为此提供佐证。汉代丧葬画像石的出土展示了《薤露》、《蒿里》等歌曲的应用表演情况,山东苍山东汉墓画像石题记石柱、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渭水桥"的榜题说明鼓吹铙歌《战城南》歌曲应该也应用于丧葬仪式。徐州"亲迎图"画像石展示了汉代婚恋歌舞表演的情形,汉乐府中很多歌曲可以在嫁娶时歌唱。出土文物中的踏歌图案展示了戚夫人歌唱《赤凤凰来》时"连臂踏歌"的表演形式。第叁章是出土文物与汉乐府表演形式研究。首先结合汉画像石歌乐俑中的乐舞形象分析汉代乐府相和歌表演时的演唱形式,主要有歌歌相和、歌乐相和、两曲相和等形式,歌曲的舞蹈表演主要有自歌自舞、歌舞分离、歌乐舞综合等多种形式。俳优说唱也是汉乐府表演的一种形式,内容以滑稽调笑为主。《俳歌辞》其实是汉代俳优说唱表演的歌辞,说唱俑的出土具体地展示了这类表演可能有的一人自歌自舞和四人配合表演两种形式。第四章是出土文物与汉乐府表演场所研究。汉代乐府作品非常丰富,表演形式多种多样,规模有大有小,适应不同表演需求和不同的演出场地,出土文物展示了汉代歌曲的居室、殿庭、广场、楼台等表演场地。表演场地所带来的娱人性特点对汉乐府有重要影响,直接影响了其文本内容和艺术特质。第五章是出土文物与汉乐府表演的服饰和道具研究。服饰是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长袖舞的运用对于汉乐府的特质展现有重要作用。"象人"表演是汉乐府的重要表演形式,画像石中《总会仙倡》的图象证明这是一场很有规模、综合性很强的歌曲演唱和化妆模仿表演。诸城"象首人身"画像石可以给汉代与大象有关的歌曲表演提供形象展示。汉代画像石中的缚虎图和汉简中关于禹步、"粤祝"的记录为我们了解《东海黄公》表演中的老虎面具的使用以及禹步、"粤祝"等表演情景提供了材料。最后是结语。借助出土文物,本文对于汉乐府诗歌表演研究有很多重要收获。因为对表演的关注,我们对汉乐府诗歌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对很多汉乐府诗歌的表演形式有了直观的了解,对一些歌曲和个别没有记录歌词的曲目进行了推测,对一些汉乐府诗歌表演表素要素背后的内在文化意义进行了考察。但是因为对声乐、器乐、表演等专业知识的不足和文物出土的偶然性,一些汉代乐府诗歌表演研究还有待深入。
周仕慧[5]2005年在《《乐府诗集·琴曲歌辞》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琴曲歌辞是乐府诗集中独具特色的一类,郭茂倩在《乐府诗集》“琴曲歌辞”总题序中说:“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自是已后,作者相继,而其义与其所起,略可考而知。”可见,在乐府歌诗中一直存在琴乐琴歌的传统。然而学界对琴曲歌辞的研究一直很不充分,有多问题都没有弄清。有鉴于此,本文对琴曲歌辞展开专门研究。基本上是以时间为线索,分四个时段,每个时段集中谈一个问题,以求对琴曲歌辞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第一章,论上古琴歌。说明早期琴歌的传播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传统琴乐和歌诗的渊源,其基本特征和艺术精神在乐府琴歌中的很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章对作品本身明显的入乐痕迹和其所反映的音乐文化精神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第二章,着重论述汉代骚体琴歌兴起的音乐背景以及骚体琴歌体式与《楚辞》的关系。在汉代楚声艺术高度发展的音乐背景下,琴乐受到汉代楚声音乐的影响,于是出现了区别于《诗经》四言雅颂体的楚骚体杂言琴歌,进而成为琴曲歌辞中最具特色的诗歌体式并对后世骚体诗的创作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第叁章,论述魏晋南北朝琴歌的新变。一方面,由艺人琴到文人琴的转变,琴歌创作主体发生变化,从而带来了琴乐功能的变化和艺术审美观念的革新。与此同时,随着隐逸风尚下文士对山水审美的普遍认同,琴歌中加入了山水因素,南朝琴歌极力地展现新音乐中的音乐意象和物色绮丽的自然情调。另一方面,南北朝琴曲和当时流行的清商乐关系密切,清商乐中的部分曲目通过琴乐、琴歌的形式在社会中流传和保存下来。南朝琴歌在诗式上也借鉴了吴歌西曲等乐歌中流行五言诗体以及“送、和声”形式,显现出音韵婉转的新鲜风貌。这些都对后世文人琴乐琴歌创作和欣赏的艺术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四章,通过对唐人《白雪》《宛转歌》两个琴曲的分析论唐代琴歌的复与变。在隋唐时期大量外来音乐风行的时候,古琴音乐犹保留了一些具有华夏历史传统的作品,《通典》卷一百四十六,称“唯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琴乐、琴歌直接成为唐旧题乐府创作的一种重要凭借和依据。唐人在乐府琴歌旧题创作中十分注重于重申汉魏乐府本事大义或者秉承乐府写实的传统,复古中寓革新之意。
李敦庆[6]2012年在《魏晋南北朝礼仪用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礼仪用乐的研究是建立在这一时期所施行的五礼制度之上的,以此为框架对每一大类的用乐进行考察,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以仪式与中国古代乐舞的关系为出发点,从礼乐文化建立之前与之后两个角度来进行考察,论述乐舞在仪式中功能的发展与变化,并讨论在礼乐制度建立之后乐舞新功能的确立及其对后世礼仪用乐的创作、使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二章重点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学发展及在礼学发展影响下五礼制度的实施对礼仪用乐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所举行的五礼制度已经超过了两汉时期的士礼体系,并且在礼学的规范下日益将儒家经典作为制定礼制的依据。与这种变化相对应,国家礼仪中所采用的音乐也随着礼制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本章内容主要论述五礼制度的施行,并与之前国家礼制中所施行的制度作对比,体现出这一时期礼制的新变:魏晋时期,尤其是从西晋开始,对传统礼典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表现为将传统礼典作为制礼的依据,体现出向传统复归的倾向,但这种复归并不是对礼典的照搬,而是根据现实做出调整,以利于其统治;其次讨论影响这一时期礼仪用乐创作的内外因素,对在各种因素制约下礼仪用乐创作所表现出的特点我们也有所涉及。第叁章主要论述这一时期的吉礼用乐。吉礼在历代都备受重视,其用乐涉及郊祀、宗庙、藉田、社稷以及山川等祭祀形式,这些礼仪中的用乐作为礼仪的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本章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吉礼仪式的主要程式有哪些,在这些程式中哪些环节需要音乐的配合,其作用是什么。其次讨论这一时期吉礼中用乐的内容、特点及其在维护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第叁讨论这一时期吉礼用乐的沿革与变化。第四是针对礼仪用乐中歌辞的论述,讨论这一时期吉礼歌辞创作模式的来源,即从句式、风格上继承了《诗经》中整饬典雅的特征。同时也对这一时期吉礼歌辞的句式、韵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这一时期吉礼歌辞的风格及艺术特征。第四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宾礼、嘉礼用乐研究。第一节主要论述这一时期嘉礼、宾礼内容的改变。随着西周分封制的结束及专制集权国家的建立,在周代施行的乡饮酒、乡射、大射、燕诸礼都发生了较大改变,有的甚至不再举行,所存留的主要是体现封建统治权威的正旦元会礼,表现在用乐上即为这一时期历代都有所创制的元会乐。第二节主要从功能上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嘉礼、宾礼乐歌与先秦时期礼典用乐的差异及元会乐在这一时期的创制与使用情况。第叁节讨论这一时期的嘉礼、宾礼用乐歌辞创作上的特点,即随着这一时期仪式中嘉宾地位的变化,其歌辞在内容上由先秦时期歌颂赞扬嘉宾转向对统治者的歌颂,在句式上以四言为主,风格上典雅庄重,与《诗经》的宴饮诗风格有所不同。第五章主要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乐。首先对军礼所包含的内容、军礼用乐的起源及其功能进行论述;其次讨论在各种军礼及军事活动中音乐的使用情况,分析并指出军乐在仪式中发挥的作用;第叁,主要针对这一时期普遍施行的鼓吹乐进行讨论,指出鼓吹作为军乐,其作用已经不仅仅是在军事活动中鼓舞士气、壮大军威,其赏赐军功和表明军事将领地位的作用日益明显。第六章论述魏晋南北朝凶礼中的禁乐与用乐。在经典中,凶礼是禁止用乐的,但在具体礼仪实践中却存在用乐。因此本章从凶礼禁乐与用乐两个角度展开,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凶礼中发生禁乐与用乐的具体礼仪形式、原因及作用。
阎福玲[7]2004年在《汉唐边塞诗主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在汉唐文化背景下对汉唐边塞诗的苦寒、尚武、思乡、征战与风俗等五大主题及其创作模式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研究。 第一章引论,通过分析“边”与“塞”的具体内涵,比较边塞诗与征戍诗、本土诗、边疆诗的差异,为边塞诗做出较为合理的定义,进而概括边塞诗的叁大特征:政治性、地域性和特殊的时代性。之后分古代、近现代和新时期叁阶段概述边塞诗研究史,对不同时期的研究成就与贡献、不足与缺憾作出简要的评介。最后介绍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成果的得与失。 第二章,先从边疆自然地理特征、边疆开发迟滞和写景抒情需要叁方面探讨了边塞诗苦寒特色的成因。之后从共时性上探讨苦寒主题的具体内涵,分析诗中表现的征行、思乡、失意和生死抉择四种苦寒体验,再从历时性上解析《苦寒行》、《雨雪曲》、《从军行》等典型苦寒模式,梳理苦寒主题的演进历程。最后探讨《陇头水》乐府模式的特征与发展规律。 第叁章,通过分析尚武内涵,认为受农耕生活和传统教化的影响,汉民族文化有任侠精神而无尚武精神。先秦和东晋南北朝两次民族融合为秦汉文明和隋唐文明融入了尚武精神,在边塞诗中表现为爱国精神、功业歌唱和任侠精神的高涨。最后通过解析《白马篇》和《少年行》乐府系列,探讨边塞诗尚武精神,认为其中的自马少年形象不仅为唐诗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形象,而且也成了民族朝气、锐气与义气的象征与载体。 第四章,讨论征战主题,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具体分析了汉唐边塞诗对民族征战的表现,唐代边塞诗对边塞战争的思考,进而概括蕴含在边塞诗中的深沉哀婉的悲剧精神,最后解析《出塞》、《入塞》、《塞上》、《塞下》等典型乐府模式。 第五章,讨论思乡主题,认为思乡恋家是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农耕文化背景与传统教化强化了这种情感。第二节梳理汉唐征戍制度的演进历程,认为征戍的广泛性、恒久性及艰苦性构成汉唐征戍制的总特征,是思乡主题产生的现实土壤。第叁节从征夫乡恋、战士乡恋与军幕文士乡恋的差异方面,分析了边塞诗思乡主题的嬗变及特征。最后具体解析《关山月》、《度关山》、《梅花落》等思乡模式的发展变化。 第六章,从写景与风俗两方面纵向勾勒古代边塞诗自然写景的基本格局和时代特色,描述汉唐边塞风俗诗的创作状况,概括了风俗诗的写作模式,进而阐释边塞诗风俗主题的价值与意义。 结语,从文学与文化对汉唐边塞诗作简要归纳总结。
向蒙[8]2016年在《六朝涉乐诗审美风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六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六朝文学和音乐在这个时代也经历了大变革、大发展。六朝是文学觉醒的时代、人性的自觉时代,也是钟情于艺术的时代,时人普遍有着很高的音乐素养,爱以音乐入诗,六朝音乐诗种类众多,异彩纷呈,展现出独特的审美风尚。以竹林七贤、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人不仅精通音乐、思想深邃,还能将二者融会贯通,从音乐中体悟哲学道理,进入一种高深的境界。他们弹琴长啸,风度潇洒,因而他们喜爱的琴、啸等音乐形式也成为了魏晋风度的标志,成为后世人心慕手追的精神偶像。到了南朝,士风相对比较颓靡,音乐对于士人而言几可等同于声色享乐,他们欣赏歌舞表演,远观近查并方方面面、细致入微地摹写歌姬舞妓,音乐诗展现出体物性和艳情色彩。总观六朝音乐诗,审美取向可用叁个字概括:悲、清、和。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士人的生命浸透着伤感与悲凉,悲音引起了他们心中的共鸣;南朝人自觉“大事已不可问,我辈且看春光”,沉溺于对女性的审美,体现出浓厚的男权意识。六朝的山水欣赏和人物品评都尚“清”,与音乐审美中的尚“清”互相影响,“清”成了音乐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无论是受儒家还是道家思想影响下的音乐诗,都追求“以和为美”,这是由各家的世界观、政治观决定的。单从艺术层面来说“和”也是举足轻重的,音乐中的各种元素要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才会优美动听。六朝音乐诗中展现出的审美风尚基本上延续了从先秦到两汉美学中传承已久的尚悲、尚清、尚和的特征,同时也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各个时代展现出了有别于从前的不同的特色,这些美学观成为了华夏美学的组成部分,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后世。
王国瑛[9]2010年在《叁曹乐府诗歌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汉代设立乐府机关后,乐府文学便蓬勃发展起来。从建安时期的曹操、曹丕、曹植叁父子首开文人拟作乐府诗歌的先河之后,后代文人紧随其后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创作了大量的文人拟乐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乐府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曹氏父子的开创之功实不可没。他们以积极的态度创作了大量乐府诗,从而改变了汉乐府中以民歌为主导、汉代文人不作、不屑作乐府诗、文人乐府荒芜的状况,也改变了汉乐府重音不重义的现实,使乐府由用于表演的歌辞发展成为诗人抒发理想怀抱,表达思想情趣的有效手段。乐府诗歌自此开始了它的另外一种生命样式,是其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转变。本文主要由叁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在整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叁曹乐府诗歌转型的论题,并证明这一论题的合理性。第二章是文章的主体,主要分析了叁曹乐府诗歌创作中的新特点,他们的诗歌与汉乐府在性质功用方面的差异以及他们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和对后代文人乐府诗发展产生的影响。第叁章则是从当时的外界环境及作家主体的特殊性两个方面,分析了这种转变产生的原因。
李鸿雁[10]2010年在《唐前叙事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前叙事诗是中国诗歌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本文试图对唐前叙事诗进行系统的梳理。确定叙事诗的内涵,分析叙事诗产生的原因以及《诗经》、《楚辞》、汉代、魏晋南北朝等不同阶段的唐前叙事诗的基本情况。在历时上,顺着历史的足迹,围绕不同时期叙事诗发展的内在理路,以及唐前叙事诗所共同关注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展开研究,通过对唐前叙事诗及其历史背景公正、全面的考察,将中国唐前叙事诗的内在理路细致而真切地还原在一个以时间为轴的历史线索之上,并使这种历史阐释的描述,有一个吻合历史内在理路的清晰脉络,来描述与把握唐前叙事诗的演进轨迹。在共时上,借鉴西方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模式上总结中国唐前叙事诗。全文共分叁部分,即导言、正文和结语。导言部分。首先阐释唐前叙事诗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然后介绍唐前叙事诗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最后回顾唐前叙事诗研究的历史并展望未来。正文部分共六章。第一章研究叙事诗的两个基本问题。唐前叙事诗研究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是叙事诗,叙事诗的起源与叙事诗的基本特征。本章通过金文、《周易·卦爻》以及后世的一些典籍,探究叙事诗的起源,进而界定叙事诗,并对叙事诗的特征作出理性的阐释。第二章重点阐释《诗经》与叙事史诗,剖析《诗经》的史诗与叙事短篇。首先是对《诗经》史诗论争的研究,认为中国存在史诗,并探究周人史诗与先周历史的关系,总结史诗的叙事模式;然后对《诗经》叙事短篇进行研究;最后总结《诗经》的叙事模式。第叁章阐释《楚辞》与神话叙事诗。探究神话叙事诗的起源,《楚辞》与神话叙事诗,神话叙事诗的意义与价值。第四章主要考察汉代乐府叙事诗与民间叙事诗。首先综论汉代叙事诗;然后从汉乐府的确立与演进、题材内容与叙事模式等方面对汉乐府诗进行研究;最后对以《故事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叙事诗从题材类型和叙事模式方面进行研究。第五章对魏晋南北朝叙事诗进行研究。首先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综论,并对两种重要的叙事诗类型,即咏史诗和纪传类叙事诗进行研究。第六章借鉴西方理论,介绍西方叙事理论的中国化演进过程,掌握叙事理论为我们提供的方法论指导,然后从叙事内容与叙事语言方面研究唐前叙事诗。结语部分,总结全文,突出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创见。
参考文献:
[1]. 魏晋人文乐府研究[D]. 邹晓艳. 首都师范大学. 2001
[2]. 现代乐府学史概述[J]. 吴相洲. 乐府学. 2015
[3]. “华化”与分型:汉唐琵琶的类型特征、演奏方式及其人文存在研究[D]. 陈岸汀. 中国音乐学院. 2015
[4]. 出土文物与汉代乐府诗歌表演研究[D]. 柳卓娅. 山东大学. 2017
[5]. 《乐府诗集·琴曲歌辞》研究[D]. 周仕慧. 首都师范大学. 2005
[6]. 魏晋南北朝礼仪用乐研究[D]. 李敦庆.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7]. 汉唐边塞诗主题研究[D]. 阎福玲.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8]. 六朝涉乐诗审美风尚研究[D]. 向蒙. 湖南大学. 2016
[9]. 叁曹乐府诗歌转型研究[D]. 王国瑛. 四川师范大学. 2010
[10]. 唐前叙事诗研究[D]. 李鸿雁.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琴歌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琴曲歌辞论文; 魏晋论文; 文化论文; 古代礼仪论文; 诗经论文; 礼仪规范论文; 汉乐府论文; 楚辞论文; 秋胡行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诗歌论文; 汉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