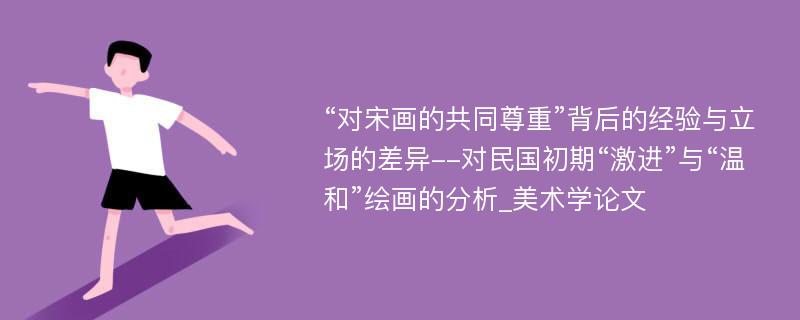
“共尊宋画”背后的经验、立场之差异——民初画学“激进”与“温和”之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激进论文,温和论文,差异论文,立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独秀在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上,为呼应吕澂的《美术革命》发表了同名通信体文章。他在文中以几近谩骂的方式痛斥了文人画传统,认为“这种风气,一倡于元末的倪黄,再倡于明代的文沈,到了清朝的三王更是变本加厉。人家说王石谷的画是中国画的集大成,我说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并呼吁“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①。此文之“激进”言论,在后世论述中多与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一文并置,成为20世纪中国画“革命派”的理论起点,并通常与陈师曾、金城为代表的“温和改良派”相对,构成很多研究者主观想象的所谓“新”、“旧”两大阵营简单对立之历史描述②。
然而,历史却绝非如此“二元对立”的简单逻辑所能厘清,它往往表现为一种混融的相互关联。比如,在论及这两派画学思想时,一个现象就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温和改良派”中,以陈师曾为中心的传统派强调文人画价值,与否定文人画的激进思想有着较为直接的矛盾点,但强调宋画严谨刻画风格的金城一派,却与康、陈激进派对宋画的“推崇”有着一定的重合、相似之处。诸如陈独秀在《美术革命》中曾言“中国画在南北宋及元初时代,那描摹刻画人物禽兽楼台花木的功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③,陈氏对“专重写意,不尚肖物”之倪黄文沈的批评,并不影响他对宋画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与推崇。而这,在康有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画至五代,有唐之朴厚而新开精深华妙之体;至宋人出而集其成,无体不备,无美不臻,且其时院体争奇竞新,甚且以之试士,此则今欧美之重物质尚未之及。”④那么,面对这种“共尊宋画”的相似性,我们又该如何理解?
这个问题难于简单回答。首先,我们所理解的“激进派”在其表面的相似性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比如康有为、陈独秀二人,其观点的细节便出入甚多。对此,李伟铭曾有论述:“表面上看来,《万木草堂藏画目》指出的近世画学衰败的原因与陈氏所攻击的目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尤其是陈氏认定两宋元初院画‘功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很容易被认为与康氏之尊院体为‘正宗’一鼻孔出气。但是,我们不会忘记,当康、陈的文章发表之时,康氏作为背气的晚清遗老正在重弹虚君共和的老调,不遗余力地倡言捧孔教为国教;陈氏作为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则把打倒孔家店,宣扬德、赛两先生的盖世勋业视为责无旁贷的头等大事。如同在意识形态上把科学、民主看作与孔教的传统无法相容的现代意识一样,陈氏的美术革命论无疑具有强烈的文化整体论色彩。康氏正好相反,他不但把写实画法看作中国绘画一种已然存在的伟大传统,从而将‘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这一理想纳入其‘以复古为更新’的思想框架,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器用之学’的角度,把调和中西的写实画法看作一种可以直接丰富日常器用生产的物质力量,由此呼应其几乎根深蒂固的‘物质救国’的主张。”⑤李伟铭于文中指出康、陈之间的区别,相对今日学界人云亦云的关于20世纪初画学之变的论调,显得细腻而深刻,颇具参鉴价值。而对陈独秀推崇“写实”,他则认为“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的绝对必要性的潜在理由中,还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假设:‘写实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地观察世界和再现世界的方法,对于盲目崇拜古人和辗转模仿古人之病具有天然的免疫力,艺术家一旦离开习惯于案头临仿的封闭的书斋,将局限于专注过往名家名作的眼光瞄准正在发生变化的外部世界,他就能够获得真正的活生生的创作灵感,并主动、有目的地学到古人有用的艺术语言技巧,进而才能自由地展现自己的思想情感。不言而喻,在陈独秀这里,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并非‘美术革命’的最终目的。作为一个画学变革的提案,它仅仅是消除科学、民主的障碍的手段;关注个性解放、关注个人价值和尊重、发展个人的创造性潜能——用陈氏自己的话来说,‘发挥自己的天才’,‘做自己的文章’,才是‘美术革命’理想的栖着点”⑥。李伟铭指出陈独秀的“美术革命”是为了消除“科学、民主的障碍的手段”,较为合理地解释了陈独秀关于“美术革命”的论述与他一贯的文化主张之间的关联性。然而,李伟铭显然也忽略了一个问题——康、陈对中国画本体审美经验的缺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认识上的共同误区。
在陈氏逻辑中,中国画的模仿即意味着不创造,故而需要打倒。因为纯艺术作品,需要“创作的天才和描写的技能”⑦,然而中国画作为特殊的视觉符号性审美体系,它的临摹一方面是体会、学习前人经验的方式,同时也是延伸新的语言组合与表现的重要方式,也即一种创造。比如沈周,集古人形式经验而取得的绘画语言表现上的转化即为一例⑧。对此,陈独秀显然难以理解。而正是因为这种审美经验的缺失,陈独秀才会出现“因临摹而需打倒”的简单逻辑。其次,陈独秀关于“描写的技能”,虽没有详细论述,但通读其文,这一概念是被等同于“再现”的。但是,中国画具有平面化、意象化的表达特征,明清文人画如此,宋元亦如此,所以“描写”在传统绘画中是渗透主观体验的表达,而非外物的直接呈现,与西画之“再现”有着本质区别。显然,陈独秀并非如此认知的,就其论述而言,他对中国画自身描写方式在解读上是有所欠缺的,并进而导致了他将“再现”程度当作“描写能力”的判断标准。所谓“说起描写的技能来,王派画不但远不及宋元,并赶不上同时的吴墨井(吴是天主教徒,他画法的布景写物颇受了洋画的影响)”⑨。也即王画不如吴画,在于吴画中呈现的洋画再现性——布景写物,而其不如宋元亦如此。由此可知,陈氏肯定宋元画风是因为宋元画风在“再现”上较之文人画要强,所谓“那描摹刻画人物禽兽楼台花木的功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那么,沿着这一逻辑继续推导,将宋画的“再现”比较西画之“再现”,则一定前者不如后者。故而,陈独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宋画,但他却不会选择宋画,而一定将论调最终落实在“引入写实主义”之上。
由此可见,因为陈氏于中国画传统审美、鉴赏能力方面的薄弱,他对宋画的肯定,并不是对宋元画风之独特审美价值的肯定,而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西画的“再现精神”,相对后来的文人画要强。同样现象,在康有为身上也有所体现。虽然,康氏的文化出发点不同于陈氏。他以“复古更新”的理论为基础与出发点,按照一般逻辑推理,他的结论应该是将中国画前进的方向定位于“复古”——对古代自身体系内某种画风的回归上。然而,康氏之论最终却没有落到“复古更新”上,而是落在了传教士郎世宁的身上。原因何在?考康氏之文,虽未如陈氏明确提出“写实主义”,但却借用了传统理论中另一个“写形”概念。他认为“近世画学之衰盖由画论之谬”,而画论之谬谬在对古代画论“写形”观的背离上。“今见善足以劝,见恶足以戒也。若夫传神阿堵象形之迫肖之尔,非取神即可弃形,更非写意即可弃形也。……夫大夫作画安能专精体物,势必自写逸气以鸣高。故只写山川,或间写花竹。皆简率荒略,而以气韵自矜……中国既摒画匠,此中国近世画所以衰败也”。就此逻辑,他继而推导“以形神为主而不取写意,以着色界画为正,而以墨笔粗简者为别派;士气固可贵,而以院体为画正法。庶救五百年来偏谬之画论,而中国之画乃可医而有进取也”⑩。应该说,至此,康氏还是沿着“复古更新”的逻辑前进,他的画学改革仍落实在中国画内部的画学传统上。那么,他为何会在结论上出现“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所谓“墨井寡传、郎世宁乃出画法;它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讲之,当以郎世宁为太祖矣”(11)又言出何处?解答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他对“写形”的认识上——中国画传统于其早期确实曾强调“写形”,但这种“写形”绝非西画客观再现的“写形”,而是有着自身形神相济的、对客体进行平面而主观化描述的视觉呈现。正如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虽然也重视“写形”,但考察顾氏前后文“凡生人而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对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也”(12),他所谓之形是无法孤立于“神”的,绝非西画之再现。很显然,康氏并没有理解这一点。在他看来,传统之“写形”与西画之“写实”是相通的。因此,他才会判断“遍览百国作画皆同,故今欧美之画,与六朝唐宋之法同”(13)。应该说,将欧美画风等同六朝唐宋,同样显现出康氏传统画学鉴赏能力的欠缺。在这一点上,他与陈独秀是相似的。他对中西画学之盛衰有如下表述:“吾曾于十一国画院中,尽见万国之画矣。吾南宋画院之画美矣。惟自明之中叶,文董出拔弃画院之法,诮为匠手,乃以清微淡远易之。而意大利有拉非尔出焉,创作油画,阴阳景象,莫不迫真,于是全欧为之改变旧法而从之,故彼变而日上,我变而日下。”(14)此处,康氏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中西画学之盛衰源于一个根源——“迫真”。或许,这正是他给他所谓“写形”概念的一个注脚。也正是基于这个注脚,他虽然与陈独秀在起点上不一样,但终点却大致吻合。就此而言,康氏对宋画的认可,虽然在某些理解上与陈独秀有所出入,但其根本标准却是相似的——写形抑或写实,都根源于对客观物象的逼真描绘上。
由此可见,康、陈虽然认可宋画,但他们并非真正理解宋元画学传统,而是以“形似”的西化标准作为判断基础。基于这一共性,他们才会殊途同归地倡导西画精神,并共同组成了20世纪初中国画坛的一道“革命”风景。但以金城为中心的传统派画家对宋元画风的认可、强调,却是基于对传统画学精神、价值的理解与认定:“吾国数千年之艺术成绩斐然,世界钦佩,而无知小子,不知国粹之宜保存,宜发扬,反忝颜曰艺术革命,艺术叛徒,清夜自思得无愧乎?”(15)当然,身处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金城,也偶然会有“中西画相类似”的判断,如“午后往观油画院,一为赛画处,一为新油画院,计油画四百张,水画五十张,皆十九世纪名手所绘。新画日趋淡远一路,与从前油画之缜密者不同,较与中国之画相近。中国画学,南宋以前多工笔,宣和以后渐尚写意,遗貌取神,实为绘事中之超诣,不但作画为然,凡诗文皆有此境界,至造极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今人见西人油画之工,动诋中国之画者,犹偏执之见耳”(16)。但是,细辨金城的“中西画相似”论,却绝无陈氏以“写实”等同宋元、康氏以“写形”等同“逼真”的西化倾向。相反,金氏比较的标准不是西画的造型标准,而是中国画意境中“淡远”、“缜密”之类的传统概念,双方文化立场的差异不言自明。也正是因为金氏比较标准中的东方色彩,故而他不会将宋元“写形”简单等同于西画之“写实”,自然也就不会走向康、陈以西画的方式恢复宋元画风这样的结论。
因为上述差异的存在,虽然金城对宋画及明清画风的判断与康有为有着较多相似,比如他们共同认为宋画为中国画学之高峰,而其后明清画风则走向衰败。甚至,对于这种衰迹的描述,金氏用语“率尔操觚”、康氏用语“简率荒略”亦甚相似。且,两人都提出了相似的“正宗”、“别体”之概念,康氏认为:“以形神为主而不取写意,以着色界画为正,而以墨笔粗简者为别派;士气固可贵,而以院体为画正法。”(17)其“正法”、“别派”与金氏“工笔固未足以尽画之全能,而实足奉为常轨。写意虽亦画之别派,而不足视为正宗”(18)的“常轨”、“别派”、“正宗”等概念是大致相当的。甚至,金城对晚清“四王”临习画风的批判语调亦类康、陈,如“剿袭摹仿,不察其是否确为是山、是水、是人、是物也。画之末流,至是极矣”(19)。但是,金城却不会在“以西画改造中国画”上与康、陈同步。无论他们对传统画史判断的倾向有着怎样雷同的语调,但金城没有康、陈由于传统审美经验的缺失而引发的误解,故而不会出现康、陈之结论。
应该说,金城对传统中国画的审美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如其连载于《湖社月刊》的《画学讲义》,大量谈及中国画之画法,兼及画理、画论。从古至今,由“形而上之画意”进而“形而下之笔墨”、由“画中之造境”进而“画外之装裱”、由“画法之表现”进而“材料之运用”,皆以饱含私人经验的描述见长。这种直观、细腻的传统审美经验是康、陈等人无法企及的。故而金城对宋元之肯定,带有感性细节的审美判断,与康、陈流于表象的判断截然不同。虽然他们都“共尊宋画”,但一方却落入“西画写实”的怀抱,另一方却提出学画之三要素——“一考察天然之物品,二研究古人之成法,三试验一己之心得。盖非考察天然真物类,凭空臆造,如使南人画骆驼,北人画船舰,不特逼真未能,尚恐或至错误,然见是物矣;而不研究古人成法,徒自多费心力,而无能成功,如学文章者,知识字矣,然不于成文中求其程式,则无以组织成篇,能观察物类矣……”(20)其中,所谓“考察天然之物品”绝非布景写实,而是传统“外师造化”精神的恢复。并且,在金城看来,这种所谓“师造化”仍需结合于对古人成法的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观察物类”。也即绘画是特定的视觉审美之呈现,它不同于照相之描绘客观,而是带有特定审美习惯去改造客观物象以期获得表现形式。故而,对于传统的学习成为画家能否运用这种特定习惯来观察客观物象的前提。那么,合乎逻辑的是,金城之类传统派画家自然会以中国传统画学既有的视觉表达为中心,来寻求新的突破,甚至在创作中大量临习古人,正所谓“不研究古人成法,徒自多费心力,而无能成功”,并以此来“试验一己之心得”,全然没有陈独秀那种“因临摹而需打倒”的简单逻辑。
虽然金城与康有为、陈独秀在主张的表述上有着“共尊宋画”的相似点,但他们这一论述背后的画学经验与文化立场却是完全不同的,其结论自然也就不同:康、陈由于中国画本体审美经验的缺乏而走向“西化写实”的美术革命,但金城却以其丰富、细腻的中国画本体审美经验而试图恢复宋元严谨刻画之风,并最终在西风东渐的时代坚守了中国画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就此而言,虽然金氏在“共尊宋画”上与康、陈相似,但其最终诉求却与强调文人画传统的陈师曾成为了“统一阵营”。因为,无论他们选择的对象是宋元严谨刻画的风格,还是明清写意抒情的风格,在20世纪初期共同面对的西学东渐之思潮中,他们都保持了文化选择上的一致性,虽然,就中国画内在的传统势力的划分来看,他们并非一致。于是乎,民国初年北京地区的中国画画坛,逐渐形成了两种势力:一派主张以西画改造中国画,成为观念相对激进的革命派;另一派则主张以传统画学资源为根基,不排斥新的视觉经验来推动中国画,由其自身内部向前发展,从而成为观念相对温和的改良派。两者相映成辉,共同谱写了民初中国画“思变求进”的思潮、主张。言及至此,有一个问题尚需明辨——即革命派以其鲜明的推翻过去、缔造新貌的主张而显出进步之面貌,但改良派却以维护传统自身价值而容易被理解为僵化不变的保守派。尤其是他们为了维护传统而专门发表的某些言论、观点,容易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其中,最著名的当是“画无新旧”观。因为按照我们习惯性的理解,“画无新旧”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保守性。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顾20世纪初期关于“新旧问题”的思想争论。其中“新”,当时就概念的产生而言,实为鸦片战争之后,尤其甲午、庚子之后,中国士人针对中国由“世界中心”的自我认可逐渐走向被“边缘化”之认同而提出的关于社会发展方向的思想主张。其根源在于西洋文明之输入对东方本土文明的冲击。诚如陈独秀之语:“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应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存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21)陈氏所指新、旧两派,其终极目标相似,皆为“适今世之生存”,然这种生存观上的危机引发的两种生存方向恰是新、旧产生矛盾之所在。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看似清晰的矛盾关系,在当时并不能简单以陈氏所谓主中、主西来区分,其复杂程度也绝非后世简单二分论所能厘析。正如汪叔潜于1915年《新旧问题》之开篇所言:“吾何为而讨论新旧之问题乎?见夫国中现象,变幻离奇,盖无在不由新旧之说,淘演而成。吾观夫全国之人心,无所归宿,又无不缘新旧之说,荧惑而致。”(22)而且,这种复杂性还体现为时人文化认同上的混同性,亦如汪氏之语“旧人物也,彼之口头言论,则全袭乎新;自号为新人物也,彼之思想方法,终不离乎旧”,他将时人区分为三类,一曰伪降派;二曰盲从派;三曰折衷派,并综而论其“可以一言蔽之曰:旧者不肯自承为旧,新者亦不知所以为新而已”(23)。具体到画界,当时所谓的“传统派”之陈师曾、金城,都曾留学于外,对西画是有所了解的,其视野、见解亦别于晚清正统画家,甚至还曾专述介绍西洋美术;而所谓“新派”之徐悲鸿,在当时却倡言“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24),与陈、金之论调亦相类似。诚如罗志田所言:“民初新旧的‘性质’,确有相差甚远的一面,但也有相差不远的一面。在有意识的层面,新旧的确对立;在无意识的层面,新旧间勿宁说共同处尚多。”(25)
那么,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有意识层面”上的新、旧对立?回答这一问题,应该回到引发新、旧问题的根源上——西洋文明之东渐引发国人自我认可感逐渐由“中心论”向“边缘论”偏离,并因这种偏离而产生国家命运之危机心理。此种心理,无论新、旧都不得不面对。然而,问题在于对怎样解决这一危机,双方各持己见。“新派”基于进化论的观点,将东方文明视作古代形态,将西方文明视为近代形态,“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各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26)。而由古代向近代之变革正是解决国家命运危机的良药,正所谓“此亦必取长于欧化,以史不明进化之因果,文不合语言之自然,音乐绘画雕刻,皆极简单也。其他益智厚生之各种学术,欧洲人之进步,一日千里,吾人捷足追之,犹恐不及,奈何自画”(27)。这种基于进化观而否定传统以尊西洋文明的新思潮,如“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8),绝非“旧派”所能接受。虽然“旧派”也不得不面对同样的危机,寻求中国的发展,并且同样也认识到西洋文明的优势地位,但对这种以否定自我而获取发展的观念却无法接受。他们更倾向于打破所谓的“新”、“旧”进化,将东西方文明置于平行的结构中加以比较,“综而言之,则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两种文明各现特殊之景趣与色彩,即动的文明是都市的景趣,带繁复的色彩;而静的文明是田野的景趣,带恬淡的色彩”(29),那么,东西文明便各具价值,而非一个进化线索上的前后两点。虽然他们无从解答“中国固有文明”怎样解决国之危机的问题——这是“新派”企图明确回答的问题,但他们却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中国文化自身传统的价值所在,而这正是“新派”力图否定的东西。于是,历史呈现出一种有趣的现象:两派矛盾对立的势力在根本问题上并无冲突,他们看似尖锐的矛盾并没有发生在中国是否应该变革之上,而是因为一派为“立”而“破”的方式不为另一派所认同。然而,不同意的一派并没有争论具体应该怎样去做,而只是针对另一派所“破”之对象的价值展开了辩护。这种现象,同样发生于当时的画坛,陈师曾的《文人画之价值》正属此类的代表。
然而,这种看似有趣的现象却为后人简单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契机,因为所谓的“旧派”,没有将精力置于“该怎样去做”的问题上,而将注意力集中于“传统的价值”之上。于是,他们身上求新、求变的一面便容易被忽略,并进而成为革命派的对立面——保守势力。于是,画史中“画无新旧”观自然也就容易成为“停滞不前”的保守象征。
从某种角度看,于此种争论之中,“新派”往往会因其明确的解决方案而占据主动。但占据主动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方向即为正确。而且,为了宣扬这种革命的主动性,他们甚至会以极度强烈的反传统论调,显现出“激进”的革命姿态。对此,他们自身也是有所意识的。比如,陈独秀在论及社会进化的惰性时就曾指出:“改新的主张十,社会惰性当初只能够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就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会进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损失,岂不是调和论的罪恶吗?”(30)应该说,为了防止这种损失的出现,他们只有不断地激进化,所谓“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道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31)。具有如此的潜意识,新派针对传统的批判自然会呈现出极端化的色彩,画史亦然。陈独秀对“倪黄”、“四王”一派文人画近乎谩骂的攻击,正是为了显现全盘引入西画写实主义的正确、伟大。或许,这种方式在论争中会呈现气势上的震撼力,但却未必能够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陈氏之《美术革命》尤为如此,他基于进化“新”、“旧”的革命论调,因其于中国画理解能力上的先天不足,更近乎一种口号化的演说,而非主张。但是,这种对传统彻底否定的口号,虽然不会对摆脱晚清“四王”画风的画史发展有着多大实际影响,却无疑能够形成一种舆论上“求新”的势力。并且,此中之“新”,正是基于西画代表进化方向之“新”。而“传统派”所否认的“新”,恰恰仅是这种基于“进化论”的逻辑之“新”,而非反对正常变化的“新”。也即,金城在《画学讲义》中虽曾提出“画无新旧”,却决不意味着他就是“食古不化”的保守派。诚如黄宾虹之言:“贵于古人者,非谓拘守旧法,固执不变者。”(32)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避免在“画无新旧”观上产生简单化的历史判断。
其实,黄宾虹早在1914年便对“新”、“旧”问题言及如下:“古今学者,事贵善因,亦贵善变。《易》曰:变则通,通则久。……茫茫世宙,艺术变通,当有非邦城所可限者。……尝稽世界图画,其历史所载,为因为变,不知凡几迁移。画法常新,而尤不废旧。西人有言,历史者,反复同一事实。语曰:There are no new thing under the sun,即世界无新事物之意。”(33)在黄氏眼中,“世界无新事物”并不代表事物是没有变化的,正所谓“事贵善因,亦贵善变”。但他所谓“画法常新”中的“新”并不是带有进化之价值判断的“变”,而是“为因为变,不知凡几迁移”之“变化”。并且,这种“变”的价值取决于“尤不废旧”,即与旧有所关联的变方有意义。故而,黄氏虽然提出“画法常新”,但他所谓的新、旧并非后来联系于进化论、带有价值判断的新、旧。而这一点,与后来金城提出的“画无新旧”,虽然在表述上截然相反,然其本质无疑一致。
金城提出“画无新旧”观的《画学讲义》,是于“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初期因教学需要而撰写的。该文起草于1921年秋冬间,并于第二年暮春三月成篇(34)。此时,金城面临的情形与黄宾虹1914年所面对的情形有所不同。因为在1917至1918年之前,中国画界中的“新”、“旧”思潮并非清晰,论述往往缺少针对性,中国画内部仍然在传统的方式下保持着发展的平衡。但1917至1918年间,激进思潮渐渗于中国画体系之内,“新旧”、“进步”与“西化”口号亦随之冲击了中国画原有的内在平衡(35)。故而,金城“新旧”观较之黄宾虹更为明确:“世间事物,皆可作新旧之论。独于绘画事业,无新旧之论。我国自唐迄今,名手何代蔑有,各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者,何尝鄙前人之画为旧画?亦谨守古人之门径,推广古人之意,深知无旧非新,新由是旧,化其旧虽旧亦新,泥其新虽新亦旧。心中一存新旧之念,落笔遂无法度之循。”(36)金氏之“画无新旧”很大程度是因为他认为“心中一存新旧之念,落笔遂无法度之循”,即在“革新就是学西画”(37)、“以西画写实之新改革中国画”的思潮中,刻意对新的追求——把以西画为新的进化观当作作画之前提时,中国画自身的法度便会消失。正所谓“学莫患喜新厌故,习画亦何独不然。习画而欲矫古人之意,惊眩世人,以为创新,此实钓名沽誉之徒”,“故作画之最忌者,在无恒,在好奇新,无恒则浅尝辄止。不免支离,反乎古人之成规。必至刻鹄类鹜,贻笑士林。究其极必流为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之不值识者一睬也”(38)。
在金城看来,“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颇具进化色彩的“新旧”观,在中国画领域是不恰当的,由此而提出的“美术革命”——欲以西画之新改造中国画之旧的观念亦然,因为“目空古今,是必离奇怪诞,以欺世欺人”(39)。但金氏对“新旧”的否定并不代表他就“守旧不变”。与黄宾虹一样,他认为画虽无新旧,需“依据于古人之法”,然亦需“穷变而通之”,“将古法所未尽者而尽之,就其古法所隐露者而变化之”(40)。原因何在?是因为“古人见景生情,借笔墨以抒写其胸中之逸气……摹拟既久,自然传其神而得其形。所谓心领神会,则笔墨气韵,自见灵妙矣”(41)。也即,中国画作为一种视觉经验的展现,有其历史生成的既定习惯——古人法度,以及由此法度而带来的特定的视物方式。因此,只有在古人成法的摹习与体会中,才会渐悟此中审美习惯,并能投诸自然,即其所谓“成规熟谙,智巧自生”(42)。学习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智巧自生”,而非“拘守不变而泥古法”。基于这样的认识,金城虽然否认画之新旧,但亦强调画出己意。他提出“学画有三要事,一考察天然之物品,二研究古人之成法,三试验一己之心得”,并追求“独出心裁”(43)。正如萧玮文指出的:“由于‘新’与‘旧’这两个互相对峙的概念本身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根本便不能将之作简单的分割。这对概念只是事物在演变过程中不同阶级的形态,本身并不涉及好与坏的价值问题。我们给它一个好与坏的划分与价值判断可以有许多层次的思考,却不宜有过分绝对的答案。”(44)
于是,面对激进派关于“新”、“旧”过于绝对的观点,金城等传统派虽然亦欲求变,但却在观念上抵制以新为进步的变,因为这种变中隐含了递进关系的价值判断。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虽然也强调绘画相对传统的差异之变,但由于身处大的文化激进时代,他们对传统的维护在语言方式上也时常会走向“激进”,出现令人误读的可能性。所谓“画无新旧”,正是如此——他们为了否认“新旧论”中的进化价值观,而在概念上否定了“新”与“旧”,就自然会给后人带来误解的空间,从而容易被人理解为“泥古派”,被赋予“保守派”称呼。但,这绝非他们真实的意图,他们对于“激进”的“激进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维护遭到颠覆的传统之价值,是民国初年重视、肯定传统文化价值的文化思潮之一。理解他们,首先应该理解他们与“进化”时风之差异,才会不为他们亦曾带有偏激色彩的话语所误导。或许,这也正是历史给予后来研究者解释、想象之空间的重要源泉。
注释:
①③⑦⑨陈独秀:《美术革命——答吕澂》,载《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
②(35)参见拙文《重读蔡元培“实物写生论”》,载《新美术》2006年第4期。
④⑩(11)(13)(17)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郎绍君、水天中主编《二十世纪美术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
⑤⑥李伟铭:《康有为与陈独秀——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一桩“公案”及其相关问题》,载《美术研究》1997年第3期。
⑧参见拙作《明代吴门画派》,辽宁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12)顾恺之:《画论》,《汉魏六朝书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14)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广智书局光绪三十四年初版,第78—79页。
(15)(36)(38)(39)(40)(41)(42)金城:《画学讲义》,参见云雪梅《新旧冶熔 故步不封——金城初论》附录,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1997年硕士毕业论文。
(16)金城:《十八国游历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0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180页。
(18)(19)(20)(43)金城:《北楼论画》,参见云雪梅《新旧冶熔 故步不封——金城初论》附录。
(21)陈独秀:《宪法与孔教》,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1916年11月。
(22)(23)汪叔潜:《新旧问题》,载《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
(24)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载北京大学《绘学杂志》第一期,1920年6月。
(25)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26)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载《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
(27)陈独秀:《随感录》(一),载《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4月。
(28)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1919年1月。
(29)伧父(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载《东方杂志》第十三卷第十号,1916年11月。
(30)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载《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1919年12月。
(31)《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转引自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
(32)(33)黄宾虹:《新画法》“序”,陈树人编译《新画法》,审美书馆1914年版。
(34)(44)参见萧玮文《金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2001年中国艺术史课程哲学博士毕业论文。案:《画学讲义》的主要内容是金城对于绘画的个人体会与心得,包括一些创作原则及方法,涉及画学范围甚广,但缺乏一定的体系,结构较为松散,议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失严谨,是一篇随笔品藻性质的杂录体文章。
(37)王伯敏:《中国美术通史》第七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