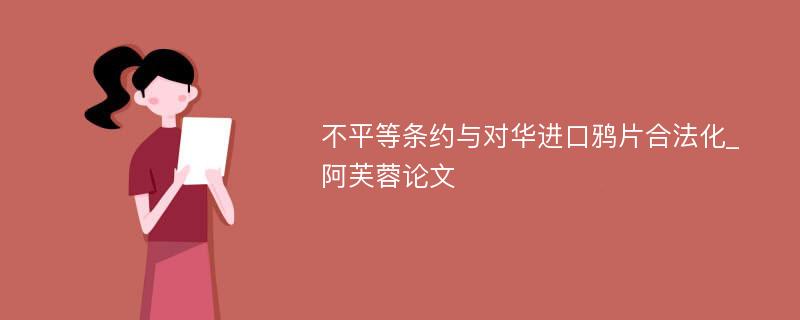
不平等条约与鸦片输华合法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条约论文,鸦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庸赘言,鸦片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外战争爆发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正因此故,这场战争名符其实地被称为“鸦片战争”。尽管某些西方人士不同意这个称谓(注:早在1841年12月美国总统亚当斯就认为中英战争不是起源于鸦片,而是起源于“磕头”。此后,否定战争起因于鸦片争执乃至否定鸦片战争称谓的观点在西方所在多有,诸如“文化战争论”、“通商战争论”等等。关于这方面详细论述,可参见《西方学者对鸦片战争性质的争论》,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9辑。),但战争因鸦片问题而引发却是不容置辩的事实,于此,英国侵华军总司令朴鼎查在当年就曾供认,“正是鸦片贸易才产生了麻烦,最后导致了战争”(注:S.W.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London Pr.1883,P.550.)。
一
令人感兴趣的是,英国为保护罪恶的鸦片贸易而悍然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但在战后强迫中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中却没有关于“鸦片”贸易的任何规定。以军事上的大炮攫取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又以条约的形式将所获特权法律化,是列强对华侵略的惯行步骤,为何独对“鸦片”暖昧其词?英国学者莱特在他那本流行很广的著述中有这样的质疑:“很多中国人都认为,1839-1842年的战争根本是为了鸦片贸易而进行的一次战争,可是战胜者竟没有坚持以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作为和约条件之一,这对他们来讲,却是一件奇怪的事”(注: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译本,第55页。)。对这件“奇怪的事”,有必要进行一番探讨并予以正面回答。因为西方学者否定鸦片战争性质的主要根据之一,就是战争后的条约中并无鸦片入华的任何条文。看来,问题不单牵扯鸦片的贸易,还涉及了对鸦片战争性质的认定。后一个问题或许对今天的研究者更有实际意义。
首先,是来自英国方面的原因。鸦片,毕竟是一个极不光彩的字眼;鸦片贸易,也是一种遭世人谴责的罪恶贸易。即使在英国国内,反对向中国输入鸦片,在政府和议会,在官方和民间,在舆论界和工业界均有很强的势力。所以,英国政府在战争伊始,就力图掩耳盗铃地在表面形式上避免战争与鸦片的挂钩。1840年2月20日,英国外相巴麦尊提出致中国宰相书,声言如果中国政府公正地“执行法律,拿获并没收在中国领土内查到的违法进入境内的所有鸦片,那么英国政府也就不会提出抱怨了。”他指责中国政府宽待中国官民走私鸦片,却单独处置英国的鸦片贩子(注: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译本,下册,第542页。)。在巴麦尊的笔下,因保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不义战争似乎成了对中国法律不公正的惩罚。英国赴华代表懿律、义律等在和中方的交涉中也一再强调:“英国政府要求鸦片烟价,不是为了烟价起见,因为英国政府是一个伟大而又慷慨的政府;而是由于强迫他们那位被非法监禁而且遭到无耻威胁的官员缴出鸦片是极不公正和侮辱性的;对这种侮辱和非正义行为,它不能不获得补偿”(注: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译本,下册,第753页。)。基于这种既要充当强盗,又要欺世盗名的思路,英国政府对鸦片在华贸易的策略至少在表面上“是要因势利诱而不能强求”,关于这一点,英国政府、驻华代表都很清楚(注: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译本,第16-17页。)。1841年2月,在义律拟定的后来被确认为无效的《穿鼻草约》草案的第6款中规定:“嗣后英国商人带进违禁货物,如鸦片烟土者,并正项货物走私漏税,任听官宪缉拿,船货入官,其人犯或交总管,或自放回国,不准再来中华,皆听上宪办理”(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版,第82页。)。虽然排除了中方对鸦片贩子的司法审判执刑权,但仍旧承认中国政府对鸦片的禁绝。1841年5月,英国政府以朴鼎查替换义律担任驻华全权代表,在巴麦尊向朴鼎查发出的赴任训令中,就英国政府对鸦片入华问题的基本立场再次作了全面表述:“女王陛下对这件事不提出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中国政府完全有权禁止输入鸦片,如果它愿意的话;从事一项违禁品贸易的英国臣民必须承担这样做的后果。但是,我希望,您应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采取您自然会想到的所有论点,强有力地给中国全权大臣并通过他给中国政府留下深刻印象
,即改变中国关于此事的法律,而且采取征收固定税的办法使他们不能防止的一种贸易合法化,对中国政府本身的利益来说将会带来多么大的好处”(注: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译本,下册,第906页。)。此后,朴鼎查便严格地循此指令行事。1842年8月英方提交的南京条约草案中,除烟价一款外,没有鸦片贸易的内容。但在同月16日,朴鼎查向中方的说帖中却提出:“鸦片一项如何可期善办,……尚须时日可成”,要求与中方代表面谈,并将英国政府起草的《论鸦片大略》的文件一份提交,这份文件指出:英国不可能在印度和其它属地禁种罂粟,也不可能完全禁绝鸦片运进中国,即便英国禁运,其它国家也要运进。与其偷运无税收,不如“议定款例,以将鸦片运进中国,与各正项货物通商无异”(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版,第210页。)。正式向中方施行以增加税收相诱使的策略。对英方“请开烟禁”的表示,中方谈判代表咸龄、黄恩彤当面答复:“烟土一节,俟姑再商”(注: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册,第109-110页。)。8月27日,朴鼎查提交备忘录一份,敦促清政府对鸦片贸易持“明智”态度,建议“除非中国能够完全阻止鸦片贸易(这一点绝对办不到),否则,只有以物物交换方式使鸦片买卖合法化”。朴氏以税收诱使不成,转以物物交换劝说,耆英答以此事“还不宜向皇上奏请”(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413页。)。此后,该议题搁置不议,南京条约除第4款规定偿还烟价外,对鸦片贸易不著一词。
其次,是来自清政府方面的原因。自1729年雍正首次颁布禁烟诏令后(注:政府首次颁发禁烟令的时间记述略有不同,有作1729年,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洋药考》,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197-198页。《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为1731年。李圭的《鸦片事略》为“雍正中”。见《朱批谕旨》第十四册载陈远一案考证,当以雍正七年(1729年)为是。详见肖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另见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第16页。),查禁鸦片便成为清朝的一贯政策。尽管各项禁令时紧时松,但随着烟毒泛滥造成的恶果愈来愈巨,清朝的禁烟举措也愈来愈严,直到1839年前后颁行“查禁鸦片烟章程三十九条”和“洋人携带鸦片入口治罪专条”达到高潮,不仅对国人贩运吸食者处以严厉惩罚,且将查禁的矛头指向外国鸦片贩子,终至演成虎门销烟威武雄壮的一幕。旋即鸦片战争爆发。在战时进行的中英交涉中,中方均一再强调中国禁烟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对此,英方也只有被迫承认,中国政府有权在中国海岸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查获鸦片,但否认中国有权逮捕英国驻华官员和商人,并以剥夺食物、饮水和生命作为威胁,强迫英国官员从那些实际上处于中国权力范围之外的人们和船只那里缴出鸦片(注: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译本,下册,第753、906、743页。)。南京条约谈判时,面对英方鸦片开禁的诱使,“中国的交涉人员,不论他们私人意见如何,都清楚地了解他们绝不能去请求他们的圣上自食其言”(注: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译本,第55页。)。据说,在南京谈判中,耆英曾对英方有过一个很不明智的答复:“关于撤销鸦片禁令,此时不宜急于向朝廷禀奏,但是,中国官吏对禁止鸦片的权力,当然只以不准中国军民吸食鸦片为限。至于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无须过问,也无须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措施”(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413页。)。研究者认为,这等于是放弃了中国政府对外国鸦片走私犯的稽查权,是在默许英国的鸦片走私。当然,耆英的答复只能是私下表示,而不敢向朝廷有任何奏报,因为清中央政府在此时和以后,均始终坚持严禁鸦片的一贯立场,多次颁发上谕,重申朝廷禁烟政策,将鸦片烟贩严惩(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册,第329、332页。)。耆英只是在事后奏报:“鸦片烟一项,上年夷酋朴鼎查在江南时,奴才即与要约严禁”(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册,第340、310页。),与朝廷的立场无二。
鸦片战后,英国对华鸦片输入面对两种选择,一是根本禁绝英属印度的鸦片出口,这是英国殖民者不可能做到的;二是诱使中国开禁,南京条约没有完成这项使命。之后,英国驻华代表继续这一狡诈肮脏的侵略政策。1843年,中英进行虎门条约谈判,英方重提旧议。7月8日及13日,朴鼎查向耆英递交说帖两份,指出中方既不能禁国人吸食鸦片,也就不可能禁外人输入,而外人将鸦片输入中国,“与英国无干,万万不能代禁”;不如开禁“收平允之税”,反使走私停止,犯罪减少,中国税收增加(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版,第212-213页。)。为了强调朴鼎查增税说词的诱惑力,英国使团秘书小马礼逊还具体开列了一个方案,称只要中国开放南澳和泉州两个口岸允许鸦片进口,估计两口岸每年输入鸦片3万箱,以每箱50元的关税计算,每年就可为中国国库增加150万元的税收。在复文中,耆英采取黄恩彤“以重税难之”以退为进的策略,声称如果英国公使愿意成为所有鸦片贩子的保证人,保证每年向中方上缴300万元的鸦片税,并预付5年共1500万元的款项,而且需作出为期10年的担保,期间不论有无鸦片进口,都必须照数缴纳。如果朴鼎查能就这一切作出担保,耆英也“愿意冒险”将“条陈奏明皇上”。对耆英的答复,朴鼎查哭笑不得,视为“完全不切合实际”(注: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译本,第19页。)。8月29日,耆英将中方态度全面照复英方,要点如下:其一,毒品为害甚烈,外商来华正常交易,“不患无利可图,何必贩此害人之鸦片”;其二,鸦片来自外洋,中国政府力争约束国人,但英商则应由英方约束,鸦片大宗来自英属印度,不能说与英国无关,如英国从源头杜绝,烟毒“自当敛迹”;其三,至于鸦片入华合法化,中国“收平允之税”的说词,英方“事无把握,又无成说,何敢率更定例。即使有成说有把握,非奏明请旨,未敢擅行,此时不敢遽议也。”(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版,第240-252页。)鉴于中方的不能通融,朴鼎查发布公告,贩运鸦片的英国商人将“不会得到女王陛下领事和其它官员的支持和保护”(注: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译本,第60页。)。但到10月30日,朴鼎查又玩弄了一个小伎俩,这天他向耆英等人发出一纸照会,要求严格履行南京、虎门等项条约的规定,禁止华民在开放五口以外地区与外商贸易,这本属正常之事,但朴鼎查在照会中又添出如
下字句,“不论鸦片与各样洋货,如于五港口之外,断不容其买卖”(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版,第253-254、257页。)。如此一来,把鸦片与其它洋货混为一谈,而且,似乎鸦片的禁绝只在五口之外,五口之内的地区便“容其买卖”。朴鼎查用隐晦语言试图实行鸦片五口贸易合法化,并未引起中方的注意和答理。11月13日,耆英向道光皇帝呈递密折叙述鸦片贸易交涉事由,指出虽然拒绝了朴鼎查抽收烟税的建议,但“禁烟则应先截其流,而利之所在,虽白刃当前,奸民亦必趋而不顾。若操之过急,则人数众多,设竟挺而走险,办理益形棘手。倘徒务禁烟之名,而任其阳奉阴为,不独贻笑外夷,即内地奸民亦将狎而生玩。”表露其只能截流不能堵源导致名禁实难禁的种种苦衷和势将引发的种种难题,“弛张均无把握,操纵实出两难”,道光皇帝对此矛盾心境亦能体味,在折上朱批:“真切”。但鸦片贸易事关重大,12月1日,朝廷在反复筹思后批示仍坚持鸦片禁绝有犯必惩的政策(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册,第353- 354页。)。其后,在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都无例外地将鸦片列为违禁品。
《望厦条约》第33条规定:“合众国民人凡有……携带鸦片……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一册,第56页。)。但正是因为英国以中国禁烟才发动了鸦片战争,战后中国还要承担烟价赔偿;更由于战后外国在华确立了领事裁判权制度,即便是外国的鸦片贩子也置于该特权的保护之下。使得上述条约规定成为具文。1842至1858年间,中国官方的禁烟政策是:禁内不禁外,以禁止国人吸食来抵抗鸦片的输入。本源不靖,律法不一,自然不可能有任何效果。
二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虽未取得鸦片输华合法化的特权,但在整个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庇护下,鸦片走私却由秘密走向公开,鸦片输入孔道也由广州一口扩为五口,香港、南澳、金门湾、泉州、上海则成为走私鸦片的最大集散地,输华鸦片数量剧增,1848年输入鸦片38000箱,1854年为61523箱,1855年为65354箱,已超过战前输入量近一倍。中国的烟禁政策名义尚存,但因外部条件的恶化,实际执行已十分有限。1844年,两广总督耆英致函港英总督兼驻华公使德庇时,“坦率地指出,鸦片贸易可以在双方默契下进行”(注:《太平天国译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辑,第283页。)。耆英此举自然不是清中央政府的授意,也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是其个人行为,但也清楚地表露了身处沿海口岸的地方大员对鸦片走私势不能禁的无可奈何实情。英国方面并不以这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局面为满足,将鸦片入华合法化明确载入约章,进而从法权上彻底摧毁中国的禁烟政策,给英属印度的鸦片造成无限广阔的需求市场,愈益强烈地成为英国对华战略的重要部分。1846年,德庇时要求耆英运用其力量使鸦片贸易“置于合法的基础上”。1848年,英国领事向两广总督徐广缙提出鸦片开禁的要求。1849年初,包令作为英国驻广州领事来到中国,其后又担任驻华公使,他的上任使英国对华鸦片政策出现些许变化,转而采取更积极更富有进攻性的姿态。据认为,这主要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公的一面,他很清楚印度每年三四百万元的收入都依靠鸦片贸易;私人方面,包令与最大的鸦片商怡和洋行有密切联系,他的长子是洋行的合股人,包令个人也得到过该洋行的好处,1848年他因事业受挫经济窘迫时,该洋行向他提供了贷款,后来他升任香港总督时,曾被公众指责凭私人感情滥用公共职权,这实际上是指控他利用总督权力来扩大怡和洋行的利益”(注:黄宇和《包令爵士与广州入城问题》,《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0辑。)。1857年,包令的继任额尔金也向中国方面提出弛禁问题,额尔金身兼英国侵华军总司令,他拥有英法联军庞大武力作为后盾。鸦片输华合法化成为每一任英国驻华公使毫无例外都要提出的索要,而且,这种索要是日趋急迫和强硬了。
清政府的态度也出现变化。此间清廷的禁烟政策主要面临着走私横行和税收无着两大难题的困扰。由于治外法权的庇护,外国鸦片贩子肆无忌惮地进行毒品走私,致使形成合法进口商品需要纳税,非法走私毒品反可以逃税的极不正常的局面。联系到仅1854至1858年间印度输华鸦片年平均值为6365319镑,而同期英国对华贸易逆差为年平均7192759镑,也就是说,英国对华贸易逆差的88.4%要用鸦片去充补,那么,这种偷税的数额就是相当的巨大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朝的财政陷入空前的危机。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增加收入的设想在清朝统治集团中酝酿,1853年,御使张谓和吴廷溥相继上奏提出开禁问题,指陈与其禁烟法令严峻而无效,不如开放贸易对进口鸦片每箱收税40两。一些地方官员也率先把寻觅财源的目光投向鸦片,1855的8月,上海道台试图对每箱鸦片征收25元的税,没有成功;又改为每箱缴税20元的办法获得解决,后又确定为每箱征银24两,宁波也开征同样税额的鸦片税(注: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译本,第61-62页。),1857年,闽浙总督王懿德“有军事紧要,暂时从权量予抽捐”,每箱征取48元。厦门道台甚至通知英国驻厦领事,“鸦片税已奉旨核准”(注:夏燮《中西纪事》第4卷。)。当然,这是一种矫旨行为。但开禁的呼声毕竟愈来愈强。1858年,两江总督何桂清正式公开奏请朝廷弛鸦片之禁,“鸦片烟我虽有禁,彼则仍然贩运,今欲改其名而弛其禁,则内地匪徒不至于聚众护送,酿成巨患,其利系在我,于夷酋夷商均无出入”(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册,第522页。)。对此建议,咸丰皇帝采取了默认态度。有清一朝奉行不替的禁烟政策从根基上出现动摇。
到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谈判时,在来自外部(英法联军武力胁迫和列强外交诱劝)和内部(走私横行和财政窘迫)的双重压力下,清政府终于作出鸦片弛禁的重大决策。鉴于鸦片贸易的臭名昭彰,鸦片输华谈判未由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出面,而由其委托李泰国和奥利芬特两人主持。据两人称,“英国并没有为了要把鸦片列入进口税率表而对中国全权大臣施加压力。”奥利芬特甚至说,在谈判时,他面告中方代表:按照额尔金的命令,“不坚持把这种毒品列入税则中,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删除的话。”奥写到,但是中方“不愿意这样作”(注: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译本,第18-19页。)。由此说来,不是英国侵略者反倒是中国人自己要坚持鸦片贸易合法化了。这当然是一种贼喊捉贼不值一驳的强盗说词。没有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和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的外国鸦片的大量走私,中国不可能接受弛禁政策。但是,在1858年10月进行的条约谈判中,鸦片问题的确并未多加讨论即予决定。中英双方在该议题上主要交涉了两项内容,一是名称,双方均感到“鸦片”的名目赫然列入国家间的条约文本有些说不出口,在中方的建议下一致同意改称“洋药”的名称,并将其列在“药材”的栏目内。残人害命的毒品一变而成了救治性命的药材,可谓煞费苦心。二是税率,中方提出每担征税60两的方案,遭英美代表的强烈反对,美国代表提出税收限度原则,即高限维持在足以限制鸦片供应,不使鸦片商因利润太高而盲目大量进口;低限维持到足以排除走私,不使鸦片商因税收太高而逃税进口。此原则乍听颇有道理,实则自相矛盾,要是低到足以排除走私,那么高到足以限制鸦片供应就是一句废话。英国谈判代表干脆把中国方案的税率砍掉一半多,提出每百斤鸦片交税银24两,最后双方妥协,而中方作出更大让步,定为每担税银30两,暴露侵略者先前所谓鸦片弛禁可以帮助中国增加税收的劝说包含很大欺骗成分。11月8日,中英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鸦片输华合法化在条约第5款,“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30两,惟该商止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嗣后遇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定货税”(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一册,第117页。)。长达16年的鸦片输华合法化交涉到此结束,鸦片成为可以自由进口的合法商品。但中国政府仍对鸦片输华设置了三道屏障,第一道,区域限制,外商只许在通商口岸,只有华商才能运入内地,运入内地的鸦片视为中国货。这道限制实际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860年后,通商口岸深入中国内地,该规定成为具文。第二道,内地税则限制,中国享有自定自征权,从1861年开始,英国就试图否认中国的这项权利,这实质上关涉到中国政府对本国商人的管理权限,与外商无关,英国的干涉是毫无道理的。经斗争,中国保护了这项权利,进入内地的鸦片每担约另征税厘50两。第三道,不照其它货物定税的限制。这项限制在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中被取消(注:参见胡维革《鸦片贸易合法化辨析》,《北方论丛》1989年第5期。)。
三
鸦片输华合法化给清政府带来的最直接的收益是税收的增加。据不完全估算,鸦片合法化全面实行的第一年,即1860年10月1日至1861年6月1日的9个月中,海关就为清政府起征鸦片税30万两银子。到1866年,这个数目增到200万,相当于该年度所有进口货征税总额的两倍。而且,这只是中央政府的收益,还不包括地方政府的进项,各地在鸦片税上的收益当远远超过中央,如1868年,中央收入为160万两,地方收入则为260万两。1879年后,外国鸦片进口有所减少,其它货物的进口增加,但直到1884年,鸦片税仍占全部进口税的一半以上。1887年,鸦片厘金并入关税(由关并征),每担征银110两,约值百抽二十五,而其它商品进口税率不过是5%至7.5%,由关并征的第一年报部厘金4645000两,第二年达到6622000两,鸦片的高关税率显而易见(注:李圭《鸦片事略》卷下。)。如果再加上土药(国产鸦片)的税收(19世纪90年代,在鸦片产区的大部分省份,土药厘金约占全部厘金收入的3%至4%)(注: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下册,第470-471页。),那么,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鸦片贸易合法化剧增的财政收入将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数字。鸦片输华合法化确乎给清王朝提供了一个重要财源,但它只是一种饮鸩止渴的举措,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更是无法估量的灾难性恶果。
首先,它使鸦片的贩运吸食全面合法化。1859年,清政府重新颁布鸦片章程,除保留禁止官员、兵丁、太监等吸食鸦片外,“其余民人,概准买用”(注: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册,第220页。)。它使银钱外流,百业凋敝,民生穷困,道德堕落,给国人身心造成极大摧残。鸦片弛禁前,中国吸食鸦片的人约300万;30年后,有人估计吸毒者在中国有4000万(注:Wakeman and Grant: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lifornia Unir.Pr.1975,P.154.);到本世纪上半叶,在四川、甘肃、云贵、湖南的若干地区,吸食者竟然高达成年人口总数的70%以上(注: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上册,第131-132页。)。
其次,它刺激了中国鸦片种植的普遍化。禁种罂粟是清政府长期厉行的政策。外烟入华合法化,对国人种植也不便限制。而且,清朝君臣们还含有“以土拟洋”“以征寓禁”的设想,就是大力发展本国鸦片以抵制外国鸦片,用重税来减少鸦片产量的方略(注:从1867年开始,中国西部自产鸦片就已经对印度鸦片形成冲击,见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165页。)。1859年3月,惠亲王绵愉等奏请将洋土药一并抽厘。同年,咸丰帝谕令云南对自产鸦片分别收税抽厘,正税解京,厘金留省,罂粟种植合法,使鸦片种植业以空前规模在各地发展。据国际鸦片委员会测算,仅1906年,中国自产鸦片为584800担,产量达同年外国进口鸦片的11倍,该年全国种植鸦片的耕地约为18713600亩,约占全国耕地的2%,全国除台湾和海南岛外的各省区,均有鸦片种植(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辑,第457页。)。个别省区的种植量甚至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如1928年甘肃的部分地区,鸦片种植竟占农田面积的75%,产值占农作物的90%(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48页。)。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基,鸦片的广泛种植严重地浪费大批农村劳动力于有害无益作物的栽培,挤占了本已十分紧张的耕地,加剧了近代中国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鸦片、大炮、不平等条约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三种重要手段,鸦片输华合法化的过程清楚地展示了外国殖民者如何将经济的(鸦片输入)、军事的(炮舰侵入)、法律的(条约体系)手段交互并用侵略中国的历史。将鸦片这种毒品贸易堂而皇之地载入国家间的条约内,是对国际公法的极大嘲弄,充分表明侵略者的寡廉鲜耻和不具丝毫人类的起码公德。这一事实也无可辩驳地确认:两次鸦片战争性质的不容更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