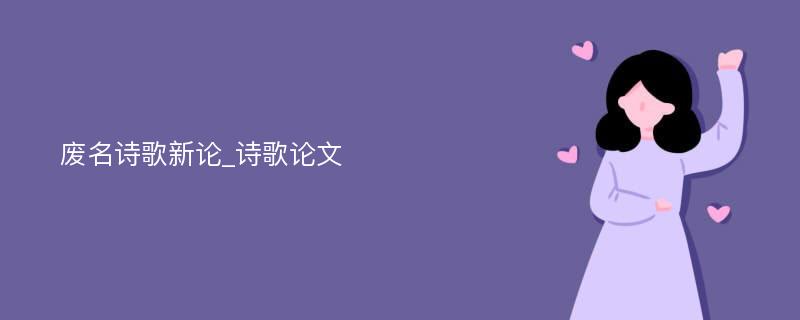
废名诗歌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10)06-0191-05
废名在文学史上主要以小说见名,他的《竹林的故事》、《枣》、《桃园》、《桥》、《莫须有先生传》都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经典之作。而他的诗歌在一般文学史教材上则没有被书写。但我认为,废名的新诗和他的小说一样独具价值,特别是在艺术探索上,他试图开辟一条新路,事实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本文将总结他在诗歌领域的成就,重新审视他的新诗研究,并结合其新诗观来探讨他新诗创作的艺术特色。
在诗歌领域,废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成绩。一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包括《诗经》研究、杜甫研究,有著作三种,分别是:《古代的人民文艺——诗经讲稿》、《杜甫论》、《杜甫的诗》。另有一些单篇论文和随笔。写作的时间主要在20世纪50年代。如何评价废名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上的成就,非笔者所长,也非本文的主旨,所以不展开论述。
二是新民歌研究和新民歌创作。研究上有《新民歌讲稿》一书,另有《关于新民歌: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冯文炳委员的发言(提纲)》一文。创作上有《歌颂篇三百首》,另有《五九年“七一”作抒情诗二首》。时间为1958年到1959年。某种意义上,不论是新民歌研究还是新民歌创作都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1958年开始的中国诗歌“新民歌运动”的产物。本质上,“新民歌”也属于新诗,可以说是宽泛意义上的新诗,但“新民歌运动”中的新民歌具有特定的含义。“新民歌运动”本质上是毛泽东发起的,所以“新民歌”的概念也是以毛泽东的说法为准,而在毛泽东这里,“民歌”与“新诗”不是从属关系而是交叉关系,所以“新民歌”不是“新诗”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一个分支,而是既有从属性又有独立性的一种诗体,他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新民歌)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1]343-344“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2]410正是因为如此,新民歌研究和新民歌创作在废名这里具有独立性,所以本文讲废名的新诗不包括他的新民歌。
但需要说明的是,废名的新民歌研究和新民歌创作,虽然由于产生于特定的政治背景中而具有特殊的时代内涵,因而具有相对独立性,但理论上,新民歌属于新诗的范畴,事实上也与新诗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本文虽然不详细研究废名的新民歌研究和新民歌创作,但它始终是废名新诗研究和新诗创作的一种比照和参考。
三是新诗研究和新诗创作。新诗研究主要成绩是出版专著《谈新诗》(又名《新诗讲义》),另有《谈谈新诗》、《新诗答问》、《诗及信》等零星文章。废名的诗歌研究成绩是很大的,孙玉石先生这样评价废名的诗歌研究:“他讲解自己的诗显示出由于诗人‘自自’所带来的一种独特的理论优势。他以诗人与批评家结合的眼光,把握一首诗传达情绪的精髓,抓住意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又不将诗阐释得过分死板黏滞而限制了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在解释程度上不要求绝对的清晰,自觉追求一种含而不露的朦胧。他的‘不求甚解’的解诗特点,能带读者进入诗的文本世界,也余下较多的遐想空间,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体味。”[3]我认为这是非常准确而精到的评价,道出了废名在新诗研究史上的独特贡献。
但废名更重要的新诗成就则是他的新诗创作,根据王风编《废名集》,计94首。其中1922-1930年11首,1931年57首,1932-1948年23首,1957-1958年3首。1957-1958年这3首诗在形式上是新诗,但内容上却深受“新民歌”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比如发表在1958年1月1日《长春日报》上的《迎新词》是这样写的:
我过去的本领都有用,
因为我今天能够参加劳动。
我过去的本领都有用,
因为我今天能够懂得歌颂——
歌颂中国共产党,
民族英雄,时代先锋!
剥削阶级出身的人觉悟太迟了,
直到1958年新年,我对工农兵才有浓厚感情,
把歌颂共产党当作我五十七岁以后的光荣,
争取新诗三百首成功。
这是典型的“节日体”。不论是思想观念还是表达方式还是审美效果,我们都很难把它和废名联系在一起。这已经不再是思想观念和创作风格的差距问题,而可以说是两种完全对立或者相反的诗歌。
过去有人曾提出“何其芳现象”,认为何其芳后来“思想进步,艺术退步”[4]。废名的极度反差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现代时期的废名强调诗的自然“天成”,批评旧体诗的“情生文与文生情”,而当代时期的废名则可以说是为“思想”和“观念”写作:“读了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就觉得我要写一首诗。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觉得要写一首诗。读了《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人人都要节约棉布》也赶忙记下来要写一首诗。”[5]3326所以有了“我没有故乡之思,/我没有家庭之念”、“我知道我决没有什么作用如果不依靠共产党员”[6]3319这样的诗句。现代时期废名最欣赏郭沫若的《夕暮》,认为它是“新诗的杰作,如果中国的新诗只准我选一首,我只好选它,因为它是天成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7]1822。而当代时期废名则改欣赏“新民歌”。“党是眼珠子,/社是命根子,/破坏党和社,/当心脑瓜子!”[8]2804废名的评价是:“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它们的价值超过了古代的《诗经》,超过了李白、杜甫。”[8]2806其评价之高让人瞠目。现代时期,连徐志摩、李金发的诗都不放在眼里,当代时期则欣赏那些无名民歌诗人。现代时期,对于自己的诗,虽然表面上谦虚,实际上非常自我欣赏,《谈新诗》一共讲到10多位诗人,其中就把自己列为一章,在具体评价上几乎是把他自己和郭沫若相提并论,“我的诗也因为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故又较卞之琳林庚、冯至的任何诗为完全了。这是天下为公的话”[7]1822。“我的诗太没有世间的色与香了,这是世人说它难懂之故。若就诗的完全性说,任何人的诗都不及它”[7]1822。要知道,“完全”可是废名评价诗歌的最高标准。在“完全”性上,废名认为他的诗和郭沫若的《夕暮》一样,而比卞之琳、林庚、冯至都要高,这可以说是极度自负的。但当代时期,他对从前诗歌的自我评价是:“我凭我的良心认为它毫无价值。到了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我更有觉悟,我曾明白地向林庚说,我过去喜欢的东西,包括自己写的在内,都是主观的,非现实主义的。”[5]3324每个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但像废名这样前后完全判若两人,各方面都表现出矛盾和对立,两种创作风格和两诗观水火不容、完全不能统一到一起,这在整个新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极为少见的。所以下文所谈论的废名的新诗,特指废名现代时期的新诗,而不包括1957-1958年这3首以及《歌颂篇三百首》,当代时期废名的新诗观念也不再作为这种谈论的根据,而仅仅作为一种比照和彰显。
废名新诗创作始于1922年,是年9月他到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这应该是他新诗写作并得以发表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之前,他已经熟读新诗特别是胡适的新诗,《尝试集》中的每一首诗他几乎都能背诵。我认为,废名虽然喜爱《尝试集》并向它学习,也可以说废名的新诗深爱《尝试集》的影响,但废名对胡适的学习并不是一味地模仿,而是在某些方面有所延伸和生发。对于自己的新诗创作废名有非常强烈的“自意识”,他在写作之前已经对诗歌有深入的思考,他的写作建立在他的思考之上,他清楚地知道他是在如何写作,他能够对自己的写作进行准确的定位。对于新诗,废名一开始就有他自己的看法,其创作一开始就是走独立之路,他的新诗创作和他对新诗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具有互文性,虽然他的《谈新诗》和《新诗答问》都是写作于40年代,即晚于他的新诗创作。
谈到废名的诗歌包括小说,“禅”一直是一个话题①,的确,废名对哲学、宗教特别是佛学有很深入的研究,对人生哲理有非常深刻的思考,这一点从他的著作《阿赖耶识论》就可见一斑。但废名的“禅学”与他的“诗学”以及诗歌创作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废名在思想方式上具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他的新诗也的确具有很浓重的“禅味”,但要说他的诗歌创作具有“禅”的思想,说他的诗学理论受“禅学”的影响,却缺乏直接的根据。我觉得,废名诗歌的“禅味”主要是阅读上的,而不是写作上的。我们可以从禅学的角度来解读废名的诗歌,这在阅读学和接受理论上都是可行的,但另一方面,我们阅读出来的“禅意”未必是废名的有意识表达。“禅意”与“诗意”在废名这里也许更是一种契合,一种性格与艺术爱好上的契合。对于评价废名的新诗,“禅学”是一种有效的言说,它能够很好地阐发废名新诗的诗意,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不用“禅学”来表达,我觉得废名的诗学理论和新诗创作都是从诗歌出发的,我更愿意回到他诗学本身来谈论他的新诗观及其审美追求。
现在看来,废名对于新诗的追求是非常独特的,可以称之为新诗的“第三条道路”。对于新诗的发展,废名在40年代初期就把它概括为两个时期:“初期新诗的背后埋伏了一个大敌人,即是旧诗。”“第二期新诗不但自由采用旧诗词句,第二期新诗于方块字的队伍里还要自由写几个蟹行文字。”[7]1733对于这个概括,我认为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不严密的,实际上,初期白话诗虽然不脱旧诗的痕迹,但它恰恰是西洋自由诗歌的产物,不论是从哪方面来讲,它的西洋因素都高于旧诗的因素。而西洋化的新诗比如象征主义诗歌,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了,所以二者在时间上也不是承接关系。但新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走的确是这“两期”的方向,即一方面向古典回归,学习旧体诗词,另一方面向西洋学习,运用现代西方诗歌的表现手法。与此相应,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诗也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古典意味的,以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的“新月派”诗歌为代表;二是西洋现代派的,以李金发、戴望舒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为代表。但不管怎样,它们都是新诗,都是建立在初期白话新诗的基础之上,只不过发扬了新诗的古典化和现代化这两个方向。
而废名的新诗则是发展了初期白话新诗的另外方向,他曾经说:“我那时对于新诗很有兴趣,我总朦胧的感觉着新诗前面的光明,然而朝着诗坛一望,左顾不是,右顾也不是。”[7]1629而对于“左”、“右”两方面他都是持批评态度的,他批评“新月派”的诗歌:“我总觉得徐志摩那一派的人是虚张声势,在白话新诗发展的路上,他们走的是一条岔路,却因为他们自己大吹大擂,弄得像煞有介事似的,因而阻碍了别方面的生机。”[7]1683而批评李金发:“他大约如画画的人东一笔西一笔,尽是感官的涂鸦,而没有一个诗的统一性,恐怕还制造不成一首完全的诗了。”[7]1735这当然是一种看法或者说一种观点,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相信大多数新诗研究专家都不会同意这种观点。但对于我们理解废名的诗歌观点,这却是非常有价值的,它说明废名的诗歌观与主流的诗歌观念有很大的差距,废名在新诗上实际是另外一种审美追求。
那么,具体地,废名是一种什么样的新诗观呢?或者说他的审美追求是什么呢?对于废名的诗观,学术界有不同的概括,我认为可以用废名自己的概念“完全”来概括。废名在讨论新诗的时候,多次使用这个概念,行文中,它既是一种诗歌观念,也是一种诗歌标准。比如他说:“我的诗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不写而还是诗的。”[7]1821这既是废名对他自己诗歌的评价,也是他对于诗歌的审美追求。这里所谓“天然”、“偶然”、“整个”特别是“不写还是诗”都是强调诗歌的特殊性,在废名这里,诗歌本质上是生命中的一种情形、趣味、感触、景象等,是包容了主观感受与客观情景的统一体,充满了意蕴,但这种意蕴难以言说或者不能言说,这种难以言说或者不能言说恰恰是一种“诗意”。新诗当然有情绪、有思想、有趣味、有情景,但这些都不是抽象的,不是在表达之外,而是在表达之内,它与其说是一种表达还不如说是一种境遇,所以废名有时又用“内容”这个概念来概括诗歌的本质,“新诗一定要表现着一个诗的内容”[7]1626。在谈到《蝴蝶》时废名说:“这诗里所含的情感,便不是旧诗里头所有的,作者因了蝴蝶飞,把他的诗的情绪触动起来了,在这一刻以前,他是没有料到他要写这一首诗的,等到他觉得他有一首诗要写,这首诗便不写已成功了,因为这个诗的情绪已自己完成,这样便是我所谓诗的内容。”[7]1610对胡适另一首诗《四月二十五夜作》,废名的评价是:“这首诗同那首《蝴蝶》是一样,诗之来是忽然而来,即使不写到纸上而诗已成功了。”[7]1613这里的“内容”显然不是文学理论上与“形式”相对的“内容”,而是包容了“形式”的内容,正如有学者所概括的:“所谓‘内容’乃是一种‘诗’的意义上的‘内容’,自有其深厚的甚至不可言传的内涵。”②我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
废名特别强调新诗的自然形态与生活形态,而轻视新诗的写作或者表现。“不写已经是诗”是经常说的话。就是说,新诗的写作不是像旧诗创作那样是先有了思想情感,有了观念,然后再用诗性的语言和形式把它表达出来。他批评胡适和沈伊默的同题诗《鸽子》和《人力车夫》:“是句子用白话散文写,叶韵,诗的情调则同旧诗一样由一点事情酝酿起来的,好比是蜜蜂儿嘤嘤几声,于是蜂儿一只一只的飞来了,于是蜂儿成群,诗一句一句的写下来了,于是一首诗成,结果造成功的是旧诗的空气。”[7]1649他把这种新诗写作称为“敷衍”,即有一点感想或者情绪或者意味便生发开去,结果便是凑成形式上完整,这种“完整”和废名所说的“完全”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废名所说的“完全”是“犹如照相师照相一样,一拍便成”[7]1736,“一首新诗顷刻成就”[7]1739,而“敷衍”的“完整”则是思考的完整,是“凑足”。如果说旧诗讲求写作和推敲,那么废名则强调新诗的把握和感受。
废名对中国古典诗词有高度的评价,也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新诗与旧诗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新诗与旧诗的分别尚不在乎白话与不白话。”[7]1608“旧诗是情生文文生情的,新诗则是用文来写出当下便已完全的一首诗。”[7]1738“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诗的价值正因它是散文的。新诗的内容则要是诗的,若同旧诗一样是散文的内容,徒徒用白话来写,名之曰新诗,反不成其为诗。”[7]1610“我发见了一个界线,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以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7]1629在废名看来,新诗与旧诗的不同不仅是外在上的,更是内在上的,新诗和旧诗在写作方式、内涵以及审美追求等各方面都具有根本的不同。新诗是先有诗,然后才把它写出来,即诗先于写作,诗在形成的时候就具有了形式,写作只是把它呈现出来,“写”对于诗来说是极次要的,这就是废名“即使不写到纸上而诗已成功了”的含义。新诗是什么形式并不重要,比如新诗不一定非要是白话不可,文言也可以写新诗,事实上,废名新诗中就有很多文言的句子。所以,新诗在形式上“自由”与其说是有体式,还不如说是无体式,因为“自由”即意味着没有体式上的限制,“自由”实际上是把诗歌形式上的限制完全给解除了,新诗的写作完全是随意赋形。而旧诗词写作则完全相反,“他们的诗要写出来以后才成其为诗,所以旧诗的内容我称为散文的内容”[7]1611。旧诗词的形式意义要大于内容意义,旧诗词也有思想和情感,也有情绪、意象、趣味等,但旧诗词的写作是由思想情感等衍生而成,也就是说,旧诗词是先有抽象或者散文的思想情感等,然后再把这种思想情感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旧诗词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情造文”,即废名所说的“情生文”。但这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旧诗词的形式本身又有意味,诗人在写作的时候不仅仅是复制最初的情感和趣味等,同时还要表现新的情感和趣味等,即“表达情感”,这就是废名所说的“文生情”。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总结废名的诗观: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旧诗的内容与形式在时间上有先后顺序,在轻重上有主次之分,在关系上可以说严格地符合文学理论所说的“对立统一”,即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二者既“对立”又“统一”。虽然从欣赏和阅读的角度来说,我们有时很难把一首旧诗的内容与形式决然区分开来,但实际上它们是可以进行二分的,即可以分为“散文的内容”、“诗的文字”。而新诗则相反,理论上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内容与形式的区分,但实际上二者是浑然一体的。废名把新诗的这种“浑然一体”称为“诗的内容”,也即“天成”或者“完全”,他认为,“一首新诗的杰作,决不能用散文来改作”[7]1611。用旧诗的方式来写新诗,不过是“新诗的古乐府”,是“诗余”[7]1649或者“旧诗的余音”[7]1650。
充分了解废名的诗歌观对于我们理解他的新诗是非常重要的。废名的新诗观和他的新诗创作是高度一致的,他的新诗观深刻地影响和制约他的新诗创作,反过来,他的新诗充分实现了他的新诗理想。废名的新诗可以说是“第三种诗歌”,既不同于中国古典诗词,也不同于西洋现代诗。在态度上,废名既不满古典化的散文化的只是调子的敷衍式的诗,也不满现代西方的过于分裂、缺乏连续性、不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诗。但有意思的是,就文本来说,废名的诗既像古典诗歌,又像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既具有古典诗歌的意境和含蓄,又有现代西方诗歌的晦涩和多重意义。废名评价卞之琳的《道旁》曾经这样说:“它古朴得好,新鲜得好,句子是真好,意境也是真好,把作者的个性都显示出来了。你若问我这首诗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这种诗是新诗的古风,很难说有什么意思的。”[7]1774这段话用来评价废名的诗也是非常恰当的,废名的新诗也可以说新鲜、含蓄,古朴而现代,诗句优美,意境深远,简单明了却又意味深长,但究竟有什么意味我们却又不能准确地进行言说。
“晦涩”和“哲理”一直是我们对废名诗歌的基本评价。从阅读的角度来说这是正确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审美风格,但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晦涩和哲理并不是废名诗歌的追求。我认为,禅意也好,晦涩和哲理也好,它从根本上是废名诗歌“完全”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特征。“自然”、“天成”,“诗的内容”才是废名诗歌的真正的特点。在《谈新诗》中,废名也专门为自己设立了一章,共选了7首诗,并对其中的6首从写作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我认为这些说明对于我们理解废名的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下面我就选其中的3首进行分析,希望以此来解剖废名的新诗。
《妆台》,这也是废名所选的第一首。
因为梦里梦见我是一个镜子,
沉在海里他也是个镜子,
一位女郎拾去,
她将放上她的妆台,
因为此地是妆台,
不可有悲哀。
林庚很喜欢这首诗,认为它很悲哀,我们读这首诗时也可以觉得它表现了一种悲哀的情调,但实际上,它表现的是美而不是悲哀。我认为,这首诗的关键是镜子,镜子在作者的心中具有特殊的含义,是美的事物,在诗中它是美的意象,这样,整首才是成立的。因为镜子是美的,所以才会梦见自己变成了镜子,因为是美的才会被女孩子拾去并放在妆台上,因为是美的,所以才应该“不可有悲哀”。如果镜子只是一般的物事,那人变成镜子就是没有诗意的,女孩子把它放在妆台上也是没有美学价值的,在意味上,“不可有悲哀”作为诗句就是毫无意义的狗尾续貂。如果作者不告诉我们镜子是美的表达,这首诗就既是不可解的,也不是一首好诗,“不可有悲哀”可以说是诗的“眼”。更重要的是,作者说:“这首诗我写得非常之快,只有一二分钟便写好的。”[7]1823就是说,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诗序其及意义,不是作者思索的结果,而是作者的一种感悟,作者自己并没有想这么多,它只是一种直觉,没有逻辑却符合逻辑性,这正是废名自己所说的“完全”。
《理发店》:
理发匠的胰子沫
同宇宙不相干,
又好似鱼相忘于江湖。
匠人手下的剃刀
想起人类的理解
划得许多痕迹。
墙上下等的无线电开了,
是灵魂之吐沫。
作者说:“这首诗是在理发店理发的时候吟成的。我还记得那是电灯之下,将要替我刮脸,把胰沫涂抹我一脸。我忽然向着玻璃看见了,心想,‘理发匠,你为什么把我涂抹得这个样子呢?我这个人就是代表真理的,你知道吗?’连忙觉得好笑,这同真理一点关系没有。就咱们两人说,理发匠与我,可谓鱼相忘于江湖。这时我真有一个伟大之感,而再一看,一把剃刀已经把我脸上划得许多痕迹了,而理发店的收音机忽然开了,下等的音乐,干燥无味,我觉得这些人的精神是庄周说的涸鱼,相濡以沫而已。”[7]1827初读这首诗,我们完全不能理解,感觉诗的每一行之间都缺乏有效的联系,具体实实在在,抽象而无边际。“理发匠的胰子沫”怎么“同宇宙不相干”?又怎么“好似鱼相忘于江湖”?“匠人手下的剃刀”和“想起人类的理解”是一种什么联系?“墙上下等的无线电开了”怎么会“是灵魂之吐沫”?完全不知所云。可以说,如果没有作者的自我解释,我们实在不能理解。
如果把作者上述解释看作是一段散文,对比诗歌和作者的解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废名所说的诗与散文之间的差别。散文所叙述的内容和诗歌的内容是同一个内容,散文所叙述的内容虽然也很独特,比如“伟大之感”、“代表真理”等都不太符合常人情理,但赋以语境,交代过程,我们还是能够理解,它实际上是作者生活中普通的触景生情、所思所想,只不过与常人相比有些怪异而已。但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意味和形象却完全相反,现实生活的时间、逻辑和过程都没有了。生活中的现实在诗中变成了抽象思考,生活中的抽象思考在诗中变成了现实;现实中的因果关系在诗中变成了并置关系,现实中的并置关系在诗中变成了顺接关系。整首诗不像散文一样具有背景和过程,也没有语境,不过是一种情景和意象,可以看作是一时的感触,但却不是联想式的,是“突发”式的,是“团状”形的。
如何解读这首诗,一直是一个难题。王毅认为“此诗看似乱七八糟,其实相当清楚。它有一条贯穿的线索和一个中心观念”[9]102。王毅的解说是有道理的,也可以说是深刻的,但我总觉得太脱离文本。这首诗有三个句号,其实也就是三句话,也是三个意象或三层表达。但整首究竟表达了什么思想和观念,究竟表达了什么情趣和意蕴,我们却似乎说不出来。每一诗句都有现实的根据和来源,但表现在诗中其诗意却完全不同。第一句话是关于胰子沫的,“理发匠的胰子沫”是实录,“同宇宙不相干”是“代表真理”的变化表达,是插入,现实中是因果关系,诗中与前后诗句则是并置关系。“又好似鱼相忘于江湖”典出《庄子·大宗师》,实际上是“相濡以沫”的代称,是含蓄的表达。“相濡以沫”也许是潜意识的“胰子沫”的联想,但它恰好地表达了理发匠与理发者之间的关系:理发时,两人是如此亲密或者说亲近,是“相濡以沫”,但理完之后则天各一方,互相都把对方忘记了。本来是“相濡以沫”,但感受却被转换为“相忘于江湖”,这是典型的诗歌的跳跃,这是诗性的表达,但却增加了我们理解上的难度。第二句是关于理发匠剃刀的,“匠人手下的剃刀”和“划得许多痕迹”是实录,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而“想起人类的理解”则是插入,是对现实中“伟大之感”的一种表达或者说描述,现实中,它和前后行诗之间是因果关系,但在诗中则被并置,是并列关系,并把诗意中断,造成“匠人手下的剃刀在我脸上划得许多痕迹”这一过程的破碎。最后一句是关于无线电的,在现实中它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在诗中它却变成了一种有效的联系,它既是一个单独的意象,但同时也是对第一句和第二句的归结。“墙上下等的无线电开了”是实录,“是灵魂之吐沫”则是抽象的想象,是“诗眼”,是诗的旨意归结点。无线电里的内容本质上只是一种声音,没有血肉之躯,所以是“灵魂”。无线电对人也是有意义的,具有精神上的慰藉,但这种慰藉是单向性的,所以只是“吐沫”而缺乏“相濡”。由此也可见废名诗歌晦涩的方式及其原因。
《街头》:
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
乃有邮筒寂寞。
邮筒PO
乃记不起汽车号码X,
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
汽车寂寞,
大街寂寞,
人类寂寞。
与《理发店》不同,这首诗即使没有作者的说明,我们也能够大致读懂。站在大街上看汽车驰过,只留下对面的邮筒,由此引起一番感受,诗歌就是写这一刹那的情景和感受。对比汽车的飞驰而过,邮筒的一动不动这是一种寂寞。由邮筒上的字母联想到汽车的阿拉伯数字号码,邮筒上的字母是寂寞的,汽车的阿拉伯数字也是寂寞的,由此,汽车也是寂寞的,虽然汽车在飞驰。进而,大街虽然繁忙热闹,但实际上也是寂寞的。再进一步,整个世界都是寂寞的,因而人类也是寂寞的。这里,情景是次要的,主观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情景是极平常的,但主观感受却是非常独特的。
内心与外在的一体性,情感与思想不是思索的结果而是在联想和描述中呈现出来的,这是废名新诗晦涩的原因,也是晦涩的结果。而这种特点在一些小诗中更为突出,比如:“我不愿意我的花带我以甘露,/我等他还我一棵鸦片/我囫囵吞枣。”(《果》)“我梦见我跑到地狱之门栽一朵花,/回到人间来看是一栈鬼火。”(《栽花》)“我的坟上明明是我的鬼灯,/催太阳去看为人间之一朵鲜花。”(《坟》)“梦见窗外一棵树倒了,举头熟视均已,/我很喜欢这个梦怎么这么轻。”(《拔树梦》)缺乏背景和语境,就缺乏过程、缺乏逻辑,因而我们难以理解。我觉得,如果作者不加以说明,不予以写作的还原,我们永远不能进行准确的解释。但不能理解也许正是废名希望的结果。
注释:
①参见王泽龙《废名的诗与禅》(《江汉论坛》1993年第6期),刘勇、李春雨《论废名创作禅味与诗境的本质蕴涵》(《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等文章。
②参见张桃洲《重解废名的新诗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