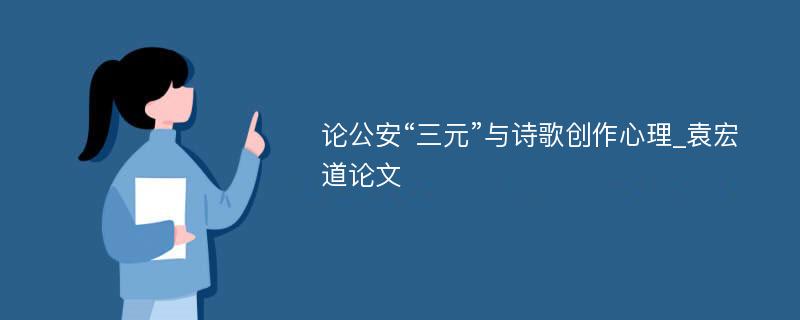
论公安“三袁”及其诗歌创作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态论文,公安论文,诗歌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5)03-0149-07 公安派基本上是一个活跃于万历时期的诗歌流派,此时政治上值得注意的现象有二:一是万历初年,由于张居正改革,诗人们一方面看到了希望,对国家前途和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思想高压和言论堵塞,心境依旧在希望和绝望中徘徊。二是张居正去世后,曾一度出现思想开放、言论自由的局面,但言官与内阁辅臣的严重对立,清议蔚起,党争激烈,使心境失落的晚明诗人陷入了更深层的人生悲哀。当时,万历皇帝厌倦了你争我夺的口水战,藏入后宫,不理朝政,生活荒淫无度,“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无奇不有。”[1]294万历的荒唐行径导致国库储备被挥霍一空,当政者转而压榨农民与工商业者,造成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社会矛盾白热化。再加宦官势力抬头,贪官酷吏也乘机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其中臭名昭著者如税官之流。正如袁中道在其《赵大司马传略》中所言: 水陆诛盈,搜肉见骨。下至鸡豚蔬果之属,皆遭攘夺。富民以资雄者,税官即奏记奉,某邑某富民塚墓地生金可采,当如旨掘伐。富民惧,倾家入资赂税官,乃得罢。……诸税官缘引日益多,民坊酒食,皆不敢征钱。浆酒霍肉,占歌舞妓,或强淫民子女,甚有污儒生妻,而捽儒生几死者。民皆怨恨思乱。[2]731 面对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时代,部分士人处则不甘、出则无路,既不能上报朝廷、下安黎庶,又不甘隐居山林、碌碌无为。他们或聚而讲学、或清议时政,在狂放不羁中恣意挥霍生命,其表面的无所顾忌、自我自适和麻木不仁,实际上是其内心深处痛苦与压抑的流露,其恨之切源于爱之深。以“三袁”为首的公安派就是在如此情境下登上了历史舞台,体验人生况味,展露文学才华,经历了从万历到天启的数十年时间。在诗史发展的长河中虽如昙花一现,却也值得关注。 一、公安派的形成与主要活动 公安派是一个由有着共同志趣和理想的文人们组成的文人集团,其形成之初的主要组织方式是文人结社。何宗美详细考订了公安派结社的具体情况,他在《公安派结社的兴衰演变及其影响》一文中写道:“公安派结社始于万历八年,讫于天启初,前后持续40余年,共达37例之多,即使其中有个别相重的现象,除其重者也将超过30例。”[3]足见其社集次数之多,影响之大。贾宗普《公安派成员考》初步考订公安派成员有45人之多[4],很显然其成员实际人数应当不止这个数字。刘大杰先生认为,到了晚明,“反拟古主义的力量扩大了,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运动,领导这一运动的,主要是公安派。,”[5]918这一认识,符合公安派发展的历史事实。 公安袁氏实有兄弟五人,除文学史上常说的“三袁”外,尚有两位庶出的兄弟。由于父亲早逝,作为长子的袁宗道便担当起了父亲的角色,成为其他兄弟幼时的依靠与偶像。另外,公安“三袁”多受其舅家龚氏的影响,龚氏家族不仅人才辈出,科场扬名,甚至不乏官运亨通者,龚氏对“三袁”的成长影响深远。袁宗道科场扬名、官场显贵,更兼诗文俱佳,无疑是公安派初期的标志性人物。钱谦益云:“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6]566明确指出袁宗道在公安派中的重要作用。朱彝尊也认为:“言作俑者,孰谓非伯修也耶?……自袁伯修出,服习香山、眉山之结撰,首以‘白苏’名斋,既导其源,中郎、小修继之益扬其波,由是公安派盛行。”[7]465可见,袁宗道以其思想和社会地位影响了初期的公安派,在公安派形成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当时,在宗道周围聚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诗文之士,其顿悟见性之说也启迪了宏道、中道、黄辉、陶望龄等人。据袁中道《石浦先生传》可知,宗道属于早慧之人:“先生生而慧甚,十岁能诗,十二列校”,“二十举于乡”;而其“十二列校”时即慷慨陈志:“吾终当俎豆其间”,后来果应其愿。在其乡试中举后,“益喜读先秦、两汉之书。是时,济南、琅琊之集盛行,先生一阅,悉能熟诵。甫一操觚,即肖其语。弱冠,已有集,自谓此生当以文章名世矣。”[2]708可见,宗道当初也是熟知前后七子的创作路数,后来才在思想上倾向阳明心学并以反复古为旨归。任访秋先生曾明确指出:“伯修有论文两篇,作的年月虽不可考,但大体看来比中郎的反李、王的一些文字要产生得早,因为伯修文中是粗枝大叶的来抨击复古派的错谬,不如中郎的深入彻底,倘若中郎的反复古派的一些文字已出现,像伯修这类作品大可不必再作了。”[8]28钱伯诚先生的《白苏斋类集前言》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论文》上下篇没有著明写作时间,但可以相信当在中郎立论之前。”[9]3不难看出,公安派提出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宗道的首倡之功毋庸置疑。 公安派形成之后的频繁社集活动是公安派存在和发展的支柱。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袁”、黄辉、潘士藻诸公倡议,苏惟霖、刘日升、顾天埈、李腾芳、吴用先、陶望龄等人在京城崇国寺的葡萄园结社论学,号葡萄社。秦京、谢于楚、钟起凤、黄炜、谢肇淛等数十人先后被延入社中。同年,公安派诸人又集显灵宫,诗酒唱和,评议时政,声势浩大。他们标榜“异学”,绝非空谈性理,而是关注时事,有着浓烈的“清议”味道。中郎诗《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其二云: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10]651 此诗记录了他们集会时的“清议”盛况。毫无疑问,这种以狂狷姿态抨击时政的行为与东林诸君子之讲学别无二致,由“异学”思想而“清议”时政,引起了为政者的恐慌和不满,遂酿成祸端,终于导致了万历二十九年势头凶猛的京都攻禅事件。攻禅事件以捕拘年逾七十的李贽和达观禅师,并导致卓吾惨死狱中而终结。这一事件也给思想渐趋开放的文人们当头棒喝,直接扼杀了公安派的继续发展,加速了它的衰落。陶望龄《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云:“此间诸人日以攻禅逐僧为风力名行,吾辈虽不挂名弹章,实在逐中矣。一二同志皆相约携手而去。”[11]436很显然,此次攻禅事件不仅仅是针对李贽或达观等个别学者。陶望龄后来在《与周海门先生》中还回忆说:“此间旧有学会,赵太常、黄宫庶、左柱史主之,王大行继至,颇称济济!而旁观者指目为异学,深见忌嫉。然不虞此祸乃发于卓老也!七十六岁衰病之身,重罹逮系,烦冤自决,何痛如之!”又云:“客岁之事(指李贽死难),吾党自当任其咎。”[11]405按照陶望龄的说法,公安派的讲学早已被一些人“深见忌疾”,李贽不过是偶然的直接受害者。当然,攻禅事件引起了公安派的恐慌与困惑,陶望龄在《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中还说:“卓老之学,似佛似魔,吾辈所不能定。”[11]435并认为李贽之死是出于“多口好奇,遂构此祸”。他在《与周海门先生》一文中呼吁士人应走“韬晦”之路,远离狂狷之风:“弟意著书立言,凡以砭世,不宜惊以奇特,令之龃龊而突入三帝。”[11]406就连袁宏道也一改往日狂狷之风,主张学者应“韬光敛迹”,万历三十二年他在《德山麈谈》中说:“学道人须是韬光敛迹,勿露锋芒,故曰潜曰密。若逞才华,求名誉,此正道之所忌。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张,去将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学者尤宜痛戒。”[10]1297这显然是李贽之死引起的文人畏祸自保心理的体现,这种心态自然导致了公安派成员的大量消减和社集活动的骤减。 万历三十年之后,公安派主要成员相继离世:如江盈科卒于万历三十三年,寿五十三;陶望龄卒于万历三十七年,寿四十八;袁宏道卒于万历三十八年,寿四十三;黄辉卒于万历四十年,寿五十八,骨干成员仅余袁中道一人。中道在《书名公便面册》中悲伤地写道:“庚子以后,伯修去世,友人相继或逝或隐,去年复失中郎。寒雁一影,飘零天末,此中萧飒,岂可言喻。”[2]889这些骨干成员的纷纷离世,尤其是宗道和宏道相继去世后,尽管还有中道勉力坚持公安派的主张,但毕竟独木难支,他既不能吸引新成员的加入,又无法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公安派走向衰落的颓势已无法挽回,退出历史舞台的结局也无法避免。 二、公安派诗学主张的产生背景与要旨 公安派诗歌思想的形成深受阳明学派的影响。公安派成员尊崇王阳明,视王龙溪与罗汝芳等人为阳明心学的真传,以“二溪”为精神导师,并以此为傲。袁中道在《答左心源御史》中曾云:“自谓于龙溪、近溪之脉,可以滴血相证。即不敢谓廓清涤荡之功便同前辈,而觉此一路,至平至淡,至简至易。”[2]986又在《寄中郎》中赞叹道: 日在斋中,猢狲子奔腾之甚,一日忽然斩断,快不可言。偶阅阳明、龙、近二溪诸说话,一一如从自己肺腑流出,方知一向见不亲切,所以时起时倒。顿悟本体一切情念,自然如莲花不着水,驰求不歇而自歇,真庆幸不可言也。自笑一二十年间,虽知有此道,毕竟于此见在一念,不能承当,所以全不受用。[2]988 中道认为王阳明及“二溪”之说均发自肺腑,其顿悟本体之说似乎为公安派指明了精神方向,并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说形成了某种契合。另外,黄卓越先生对公安派思想追根溯源,认为袁氏兄弟的主要思想源自心学倡导者的李贽和焦竑,而袁宏道甚至被目为李贽思想的传人。黄先生说:“第一代即王阳明本人,第二代领袖为王畿、王艮,第三代为徐樾、王襞、王栋、颜钧、赵贞吉等,第四代为罗汝芳、耿定向、何心隐等,第五代为杨起元、周汝登、李贽、焦竑、管志道等。”[12]7考察晚明文学思潮发展的轨迹,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史实:是“唐宋派”向复古派发起了第一次冲击,是以徐渭、汤显祖为代表的“主情”文人向复古派发起了第二次冲击。而无论是哪一次冲击,均与心学领袖或佛教高僧有着密切的关系。 公安派的诗学主张当以袁宏道的“性灵”说最具代表性。宏道在宗道反复古主张的基础上,对“性灵”概念进一步阐释,概括发展了这一理论,进而使“性灵”语汇逐渐成为袁宏道文学思想的一种标志性概念,也被世人广泛承认。如果说《论文》的写作标志着袁宗道反复古思想的成熟的话,那么《叙小修诗》的推出则是袁宏道正式扯起“性灵”大旗的标志。在《叙小修诗》中袁宏道明确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10]187的著名观点。宏道《叙梅子马王程稿》又说:“诗道之秽,未有如今日者。其高者为格套所缚,如杀翮之鸟,欲飞不得;而其卑者,剽窃影响,若老妪之傅粉;其能独抒己见,信心而言,寄口于腕者,余所见盖无几也。”[10]699他认为,诗人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彼此不同的个性与诗风,而不该文人相轻、彼此诽谤,文人相轻是阻碍文学发展的陋习。《识张幼于箴铭后》又通过一系列历史人物形象地说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不应该因彼此不同而相互讥诮,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这一个”。这显示了公安派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尊重,对人的个性与不同创造力的推崇。此文写道: 余观古今士君子,如相如窃卓,方朔俳优,中郎醉龙,阮籍母丧酒肉不绝口,若此类者,皆世之所谓放达人也。又如御前数马,省中秘树,不冠入厕,自以为罪,若此类者,皆世之所谓慎密人也。两种若冰炭不相入,吾辈宜何居?袁子曰:“两者不相肖也,亦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10]193 公安派是反对复古的,三袁中尤以宏道最为猛烈。袁宏道在读了友人丘长孺的诗后,曾明确指出一代有一代之作家,一代又有一代之文体,模拟因袭就意味着倒退。如《丘长孺》即云: 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袭者乎?至其不能为唐,殆是气运使然,犹唐之不能为《选》,《选》之不能为汉、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果尔,反不如一张白纸,诗灯一派,扫土而尽矣。夫诗之气,一代减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10]284 袁中道也继承了其兄的诗歌主张,强烈地反对复古和模拟剽窃,提倡诗歌创作应力求诗人真性情,不拘格套,打破一切束缚诗人个性的条条框框。他曾在《解脱集序》中称赞袁宏道主张的“造物天然,色色皆新”,对拟古主义思潮进行猛烈批评: 夫文章之道,本无今昔,但精光不磨,自可垂后。唐、宋于今,代有宗匠。降及弘、嘉之间,有搢绅先生倡言复古,用以救近代固陋繁芜之习,未为不可。而剿袭格套,遂成弊端。后有朝官,递为标榜,不求意味,惟仿字句,执议甚狭,立论多矜。后生寡识,互相效尤。如人身怀重宝,有借观者,代之以块。黄茅百苇,遂遍天下。[2]452 中道虽然是坚定的反复古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全盘否定古人的一切,其《珂雪斋前集自序》将古人与今人进行比较,认为:“今者虽有制作,率尔成章,如兔起鹘落,决河放溜,发挥有余、淘炼无功。”[2]19他能客观地评价自己与古人作品之优劣,这无疑是对公安派“率性而为”、“任意而发”弊端的纠正。同时,他还强调要学习古人之精神,而非拘泥于字模句仿的因袭,一味地在形式上模仿,形成不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这种主张与其后的竟陵派极为相似,也是袁中道诗歌主张发生转折的体现。 袁宗道在探究明代文坛发展轨迹时,还深刻反思盲目的、形式主义的复古所带来的弊端,进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文贵立本”的创作主张,认为“运才之本”在于诗人自己的宏远博识,“立本”就是主张诗歌要有独特的思想内容,这种诗学思维也是晚明实学思潮萌动的体现。他在《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一文中写道: 夫士戒乎有意耀其才也,有运才之本存焉。……本不立者,何也?其器诚狭,其识诚卑也。故君子者,口不言文艺,而先植其本。……其器若万斛之舟,无所不载也;若乔岳之屹立,莫撼莫震也;若大海之吐纳百川,弗涸弗盈也。……信乎器识文艺,表里相须,而器识狷薄者,即文艺并失之矣。虽然,器识先矣,而识尤要焉。盖识不宏远者,其器必且浮浅;而包罗一世之襟度,因赖有昭晰六合之识见也。[9]91 文章强调了“器识”的重要性,即先要有一种思想作为文艺创作的立足之本,才能形成诗人宏远博识的气度,“器识”是诗人“运才”创作的前提。在著名的《论文下》中,宗道更详细地阐述了这种观点: 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无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必号痛,大怒者必叫吼动地,发上指冠。惟戏场中人,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项学问,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丝意见,徒见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说,又见前辈有能诗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纸,入此行市;连篇累牍,图人称扬。[9]285 他批评了当时文人连篇累牍以求声誉的浮躁行为,认为有一派学问便有一派意见,有一派意见便能创出一派语言,强调诗文的语言风格出自作者心中的学问,其观点虽有失偏颇,但亦不无道理。他在《论文下》中又说:“沧溟强赖古人无理,而凤洲则不许今人有理,何说乎?此一时遁辞,聊以解一二识者模拟之嘲,而不知其流毒后学,使人狂醉,至于今不可解喻也。然其病源则不在模拟,而在无识。”[9]285在袁宗道看来,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派领袖人物盲目拟古复古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识”。 对诗歌“真”的追求是公安派反复古的另一审美观念。要求诗人做“真人”,诗歌发“真声”。力求“独抒性灵”是公安派求“真”的具体体现。袁宏道曾以此劝导袁中道,希望他不宗法汉魏,不学步盛唐,而能够任性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其《叙小修诗》云: 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10]188 在《冯琢庵师》一文中,袁宏道也进一步重申“宁今宁俗”,也不要从人脚跟的观点。他说: 宏实不才,无能供役作者。独谬谓古人诗文,各出己见,决不肯从人脚跟转,以故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10]781-782 为追求“真人”、“真声”、“真性情”的理想人生与诗歌境界,袁宏道内心充满了对仕途的厌倦,以致他在出仕与致仕的矛盾中身心俱疲。其在吴县知县令所作《兰泽、云泽叔》云: 聚首村中,一樽一杓,便足自快,身非木石,安能长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从所恶?语语实际,一字非迂,若复不信,请看来春吴县堂上,尚有袁知县脚迹否?[10]211 公安派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派别,除主张“求真”外,亦主张“求变”,主张诗文应该“守其必不可变者,而变其可变者。”他们敏锐地感觉到“求变”才是一个诗文流派的发展出路,强调文章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袁中道《花雪赋引》写道: 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还有作始。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是故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穷,法律之持,无所不束,其势必互同而趋浮。趋于浮,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穷。夫昔之繁芜,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窃,又将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变之势也。[2]459 袁宏道《江进之》亦云: 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10]515-516 他认为诗歌不必模仿前代,既然时代是发展变化的,那么诗歌创作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求真”是公安派诗歌主张的根本,它要求诗人在诗文创作中“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打破一切束缚诗人抒发真性情的形式藩篱。在那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公安派要求诗文创作撇开门户之见,是其兼收并蓄“求变”精神的具体体现。 三、蔑视科举的表象与汲汲功名的内心 从现有资料来看,公安派的很多成员都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对功名富贵的蔑视,对自由洒脱生活的向往,但在他们不厌其烦地表达轻视科举想法的表象下,正是那一颗颗难以掩盖的热衷功名之心。这要从袁氏改姓谈起。 公安袁氏其实非公安本地人,据《袁氏族谱》载:“公安之有袁氏也,出于江西丰城之元氏。”公安袁氏在明初是江西丰城人,原姓“元”,非姓“袁”。公安袁氏姓“袁”,始于袁宗道。对于中国人而言,改姓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由“元”到“袁”的姓氏改变颇具传奇色彩。据康熙《公安县志》卷十一《袁宗道传》载:“公本姓元,讳宗道,……年十二应童子试,督学金公一见奇之,曰:‘子当大魁天下,但姓同胜国(元朝)号,恐不利首榜,吾为子更之。’遂易‘元’为‘袁’。”[13]袁宗道应童子试为明隆庆五年(1571),三袁之父袁士瑜尚在世,他一生才名卓著却困顿科场,显然是赞同改姓的。而袁氏子孙对此次改姓并不以为耻,因为此后袁氏家门科名大显。袁士瑜十五岁应童子试,名列榜首,一举成名,此后几乎将一生的精力放在了科举之途,可天不遂人愿,任其“头悬梁,锥刺股”也未得一第,但袁士瑜的经历与心态却影响了“三袁”兄弟。一方面,他一生“生命不息,考试不止”的屡败屡战的经历,影响了袁氏锲而不舍的科举精神;另一方面,科举失意导致其在佛学与诗酒洒脱中寻求心灵慰藉,也是三袁涉足心学与诗酒风流的先导。但重视科举功名无论如何都成为此后公安袁氏的家门风尚。 袁宏道曾宣称自己轻视科举,并出现了多次致仕又出仕的闹剧,其实这正是其对仕途功名无法释怀的表现。“三袁”中,受科举功名创伤最大的无疑是袁中道。中道在《心律》中自述:“追思我自婴世网以来,止除睡着不作梦时,或忘却功名了也。”[2]961可见科举功名在其心中扎根之深,而奋战科场的屡战屡败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灵创痛。他在给友人的信《答秦中罗解元》中曾感叹:“弟已如孤雁天末,哀云唳雨。且老矣病矣,一生心血,半为举子业耗尽,已得痼疾,如百战老将,满身箭瘢刀痕,遇风雨辄益其痛。”[2]1053 他将自己比作一位久经沙场的百战老将,“箭瘢刀痕”遇风雨则痛彻心肺,足见科举对诗人生命的销蚀和心灵的创伤。热衷功名而屡试不中使诗人产生严重的逆反心理,轻蔑功名富贵实是爱之太深的表现。可以说不少晚明诗人身上那些狂放恣肆甚至怪异的行为正是他们热衷科名的另一种极端显现。晚明诗人或醉心狂禅,或纵情酒色,正是其宣泄功名未得的内心苦闷的一种途径。《珂雪斋集》中有不少作品表达了中道科场失意有心归隐的想法,如《龚惟用舅谢诸生归隐赠》云: 黄鸡唱罢惨无欢,万事劳人转觉难。君自爱看《高士传》,予今欲溺腐儒冠。朝耕西岭云千亩,夜钓南湖月一滩。身似闲鸥心似水,才离火宅便轻安。[2]8 又如《寒食郭外踏青,便憩二圣禅林》写道: 禅堂诗社亦何有,古钟千岁绝龙纽。况复人生非金石,能保形质不衰朽。我自未老喜逃禅,尘缘已灰惟余酒。一生止用曲作家,万事空然柳生肘。终日谈禅终日醉,聊以酒食为佛会。出生入死总不闻,富贵于我如浮云。[2]10 视功名富贵如浮云,终日谈禅饮酒,但内心却极为痛苦。其他如《同丘长孺登雨花台》也表达了相似的人生态度:“纵使千年能几何,虚名虚利空奔波。不登雨花台,不知行乐好。生不行乐求富贵,试看雨花台上冬来草。”。[2]31无以排遣的心里之痛,使他不断吟诵:“兴来得意恣游遨,飘风吹作天涯客。影落三江与五湖,游戏宛洛醉京都。”[2]61醉生梦死,自暴自弃,聊以慰藉内心压抑的苦闷。有时他又不问事业前途,惟祈生命长久,《过赤壁》其二云:“半生寥落暗悲伤,百病相侵守一床。事业于今那敢问,只祈年寿胜周郎。”[2]25袁宏道说:“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撙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10]188宏道是深深理解其弟内心痛苦的。但面对晚明政局,即使取得功名进入仕途又能如何?入仕艰难,入仕之后不仅很难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且还不得不面对官场烦难与党争的纠葛,此时,自由闲适的隐居生活就成为诗人心中的美好向往。但当他们真正隐居林泉时,却又很难彻底放弃为官之理想。于是,晚明有太多的诗人矛盾地徘徊在仕与隐之间,袁宏道多次辞官又出仕的闹剧便是这种心态的典型体现。 袁宏道也有大量诗歌表明自己对待为官态度,如他在待选时,似乎认为有人与其争夺位置,《秋夜感怀》即表明自己的立场:“莫以千人和,遂轻白雪歌。支离常调失,突兀此生过。薄俗论交尽,秋风阅世多。鹓雏终万仞,嚇我待如何。”[10]100以庄子与惠施的典故表达自己对官位的态度。另如他做吴县令时所写《戏题斋壁》云: 一作刀笔吏,通身埋故纸。鞭笞惨容颜,簿领枯心髓。奔走疲马牛,跪拜羞奴婢。复衣炎日中,赤面霜风里。心若捕鼠猫,身似近羶蚁。举眼尽无欢,垂头私自鄙。南山一顷豆,可以没余齿。千钟曲与糟,百城经若史。结庐甑箄峰,系艇车台水。至理本无非,从心即为是。岂不爱热官,思之烂熟尔。[10]116 诗人以游戏之笔表达自己对官场生活的不屑。实际上,宏道为官是相当认真的,或许正是他为官太认真才会为官所累,也才会屡次辞官,以致他在给舅舅龚惟长的信中说:“甥自领吴令来,如披千重铁甲,不知县官之束缚人,何以如此。不离烦恼而证解脱,此乃古先生诳语。甥宦味真觉无十分之一,人生几日耳,而以没来由之苦,易吾无穷之乐哉?计欲来岁乞休,割断藕丝,作世间大自在人,无论知县不作,即教官亦不愿作矣。实境实情,尊人前何敢以套语相诳。直是烦苦无聊,觉乌纱可厌恶之甚,不得不从此一途耳。不知尊何以救我?”[10]222把做官视为“千重铁甲”的束缚,认为是“没由来之苦”,而欲“割断藕丝,作世间大自在人”。又如他在《荒园独步》中写道:“寒食春犹烂,东风草自芊。花燃无焰火,柳吐不机绵。宦博人间累,贫遭妻子怜。一官如病旅,直得几缗钱。”[10]121-122在宏道看来,做官不仅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带来光宗耀祖的荣华富贵,反而使自己深陷其中,疲于奔命,左右为难,给心灵造成难以排遣的重负。他还在《龚惟长先生》中痛苦地说:“数年闲散甚,惹一场忙在后。如此人置如此地,作如此事,奈之何?嗟夫,电光泡影,后岁知几何时?而奔走尘土,无复生人半刻之乐,名虽作官,实当官耳。”[10]205在宏道看来,做官不仅毫无乐趣,空虚无奈,甚至使他身心俱损、人格受辱。在宏道的诗文中,如此厌恶官场的表述俯拾即是,如《与丘长孺》、《杨安福》、《沈博士》、《罗隐南》诸札写道: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10]208 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人苦令邪,抑令苦人耶?[10]213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十围之腰,绵于弱柳,每照须眉,辄尔自嫌,故园松菊,若复隔世。[10]219-220 人未有不佝偻其腰,足恭其面,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百苦备尝,而至三台八座者也。必百苦备尝,而后台座可望。是在官一日,一日活地狱也。人亦何为而乐地狱也哉。[10]227 袁宏道辞去吴令,除自己的心理和身体原因外,还与官场的矛盾险恶有关,直接原因是天池山之讼。他还在《王以明》中明确道出自己的苦乐观:“故人有苦必有乐,有极苦必有极乐。知苦之必有乐,故不求乐;知乐之生于苦,故不畏苦。故知苦乐之说者,可以常贫,可以常贱,可以常不死矣。”[10]240袁宏道深感晚明官场争斗的复杂,稍有不慎便横祸飞来,认真为官或惨遭陷害,他痛苦地说:“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10]242天池山之讼是场原委不清,牵扯甚多,历时数年的诉讼案,它促使袁宏道在心理上彻底厌倦了官场,转而在阳明心学中寻找心理慰藉,讲究珍生,提倡纵欲。其《人间世》曰:“亲之不得,疏之不得,名之不得,毁之不得,尚无有福,何有于祸?处人间世之诀,微矣微矣。”[10]806袁宏道所说处世之诀,是指在现实生活中应虚与委蛇,尽量不表现自己的意见,以躲避祸端,虽出于现实的考虑,但实际上是功利主义的体现。 综上所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万历不理朝政造成的政治混乱与激烈党争,正好刺激了张居正十年专权压制下的疲软士风,晚明各种思潮如开闸泄洪一般奔涌而出。阳明心学的传播与流行一定程度上安慰了诗人们创伤的心灵,泰州学派的崛起,李贽思想的传播,催生了一批批与以往任何时代不同的狂狷者。但是晚明几任首辅血淋淋的结局,以及政绩卓著的张居正死后的悲惨境遇却始终萦绕在诗人们心头,成为诗人脆弱心灵中挥之不去的梦魇。一方面,传统儒士的政治理想依然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怀着积极的参政理想;另一方面,残酷腐败的现实往往使他们心灰意冷、无所适从。因此,以公安“三袁”为代表的晚明诗人生活在一个可悲的时代,心灵在出仕与致仕间犹豫徘徊、备受煎熬。公安“三袁”以其先进的思想、敏锐的心灵、绝世的才华,感受到了时代脉搏的发展变化。他们在“复古”与“主情”、模拟与创新的诗歌之路上焦虑痛苦、徘徊探索。他们用自己的诗歌思想与创作实践,为在“复古”主义道路上彷徨不前的明代诗歌打开了新的出路。他们的行为、心态和诗歌创作风格是晚明诗人与诗风走向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