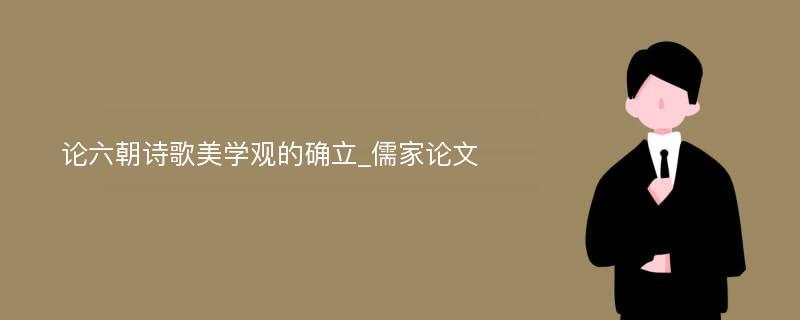
论六朝诗美观念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用现代的观点看来,诗之作为诗,它必须具有两大美质:从内容来说,它必须是抒情的,能够以情感人;从形式来说,它能给人以美感,特别是,由于诗的语言是诗的物质外壳,是直接诉诸观者的视觉和听者的听觉的,它就更应当是美的。对于诗的这种美质的认识,古今人其实是相通的,古人对这种美质很早就有所认识。不过,最初的认识是并不明确、并不自觉的,或者说很多人的认识是并不明确、并不自觉的。从并不明确、并不自觉到比较明确、比较自觉,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直到六朝时期,诗美观念才最后确立,诗歌创作和诗歌审美才最后走向自觉,从而使诗坛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从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为唐诗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一
在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上,诗歌的抒情性最早受到人们的重视,《尚书·尧典》所提出的“诗言志”就是对这一特征的最早理论概括。对“诗言志”中的“志”,古人曾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把志理解为意,如汉人许慎《说文解字》:“志,意也。”郑玄注《尚书·尧典》:“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另一种是把志理解为情,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产之言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所谓“六志”,亦即“六情”。唐人孔颖达《正义》将此说得更为明确:“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在上述两种说法之间又并没有截然的鸿沟存在,志与意、情在先秦及其以后的长时期中往往是通用的,如孔颖达《诗大序正义》中的一段话即将三者糅合到了一起:
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按照今天的理解,志与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志主要指理性的活动,属思想的范畴,情主要指感性的活动,属情感的范畴。因此,将其适当加以区别并不是没有道理、甚至并不是没有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志与情在思维活动及创作实践中又确实不太可能截然加以分割,因此在某种情况下予以通用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不是不可以接受的。问题的关键是,诗歌的本质是抒情的,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言意、说理、表现政治教化的。因此,是承认诗歌的抒情性并让这种特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还是要求诗歌去言意、说理、表现政治教化,就成了人们能否正确理解“诗言志”的一个关键。先秦时期,儒家由于看重政治教化,往往将“诗言志”这个特定概念中的“志”理解为志意和抱负,而对诗歌抒发情感、以情动人的特点缺少认识。孔子以“思无邪”概括《诗》三百篇,以“兴、观、群、怨”说规范诗歌的社会功用,荀子将《诗》三百说成是圣人之志(见《荀子·儒孝》),便都说明了这一点。由于“诗言志”是我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注:朱自清:《诗言志辨序》,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 ),由于儒家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是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先秦儒家对“志”的这种褊狭的理解,对后来诗歌的创作和鉴赏批评都产生了长期深刻的影响。
到了汉代,情、志二字仍然常被混用。如《诗大序》既说“吟咏情性”、“情动于中”,又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再如庄忌《哀时命》:“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王逸注云:“意中憾恨,忧而不解,则杼我中情,属续诗文,以陈己志也。”由于儒家地位的空前巩固和提高,汉儒比起先秦儒家来更经常地将诗与政治教化联系在一起。如《诗大序》虽有“吟咏情性”一说,但却又给它附加了两个条件:一是要在“美盛德之形容”的同时,“吟咏情性,以风其上”,“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发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治功用和伦理道德功用,积极为封建阶级的统治服务;二是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即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性、限制情性。这样一来,诗歌的功能就只剩下社会功能,而不再有审美功能,社会功能也只有“美”、“刺”两端,“美”即赞美统治者的盛德,“刺”即讽刺统治者的失德。作品的抒情性在实际上被抹煞了,“吟咏情性”的情,实际上已不是作者的一己之情,而是诗人对王政得失的感受之情,也不能随意放纵,而必须因势利导,使之归于“正”,使之合乎封建的道德规范。作品的语言美,虽然孔子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样的话,但实际上也被忽略了。扬雄《法言·吾子》:“或问圣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诸?曰:吁,是何言与!丹青初则炳,久则渝,渝乎哉?”认为丽辞华藻无益世用,久则渝变,是不值得肯定的,这是代表了汉儒对于诗歌语言美所持的态度的。
但是,“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注: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见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上册,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59页。),因此,汉儒虽要求诗歌“顺美匡恶”,充分发挥其“美刺”的政治教化功能,并确实使一部分诗成为了伦理道德的说教工具,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抒真情之作却仍然不绝如缕地存在着。如汉乐府民歌中就颇多“感于哀乐”之作,虽然统治者采集这些民歌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注: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三十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6页。); 到了汉末,由于社会离乱,民生凋敝,人生短暂,文士们被越来越浓重的悲凉慷慨的忧世忧生气氛所笼罩,抒情性更成为这一时期诗歌的显著特征。但是,从理论上强调诗歌的抒情性,却在一个长时期内阒然无闻。一直到了建安时期,这一局面才有了明显的改观。曹植说自己的文学好尚是“雅好慷慨”(注:曹植:《前录自序》,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4页。),所谓“慷慨”, 即直抒胸臆、意气激荡之意,这是在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对于强烈感情的爱好和崇尚。《三国志·魏书·钟繇传》裴松之注引《魏略》钟繇答曹丕书引荀爽言有云:“人当道情,爱我者一何可爱!憎我者一何可憎!”“人当道情”,自然也是对诗歌功能的一种规范和要求。这一时期,刘劭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人物志》,提出了“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的见解,并认为人性有所偏,人的情感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对诗人情感个体独立地位的确立、进而对诗歌情感独立地位的确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曹丕则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典论》,在其中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气”就作品而言指其气调风貌亦即风格,就诗人而言指其气质个性。而气质个性从其心理功能来说,是与情感有关而与理性思维无关的。诗人只有实实在在地抒写了个人的情感,才有可能使其作品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文气”说的提出,也是对诗人情感个体独立地位的确立和诗歌情感独立地位的确立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曹丕更为突出的贡献,是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诗赋欲丽”的命题。“丽”,指文辞华丽,是对诗赋语言风格的一种要求。汉人形容美多用“丽”字,对汉代文学的代表——大赋更常用“丽”字来形容。如扬雄《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班固《汉书·艺文志》:“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又《王褒传》:“上(汉宣帝)曰:‘……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可见对赋这种文体文辞华丽的特征,汉人早有认识。至于说诗“丽”,则为曹丕的首倡之言,这标志着人们对于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诗歌特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东汉后期以来,文人创作五言诗的风气日盛,诗歌语言日趋华丽,“诗赋欲丽”无疑是对这一现实的反映和理论总结,而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这种情况的发展,所以鲁迅说:“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注: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4页。) 这一时期,曹植发表过“摛藻也如春葩”的见解(注:曹植:《前录自序》,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4页。 ),与“诗赋欲丽”犹如桴鼓之相应,也是代表了当时对于诗歌语言特征的新认识的。
总的来看,建安时期人们对于诗歌应当重视抒写诗人个人的真情实感、诗歌应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其语言应当精致华美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这同汉儒关于诗歌功能的狭隘理解相比有了很大的区别。这说明人们的思想开始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走向自觉,而人的自觉又带动了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在实际上又不只是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自觉,而是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形式的自觉。所以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引了曹丕《典论·论文》中的“诗赋欲丽”和“文以气为主”二句之后分析说:
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即按照艺术的固有特征来进行艺术创作,是相对于汉儒要求诗歌“厚人伦,美教化”的说教而言的。人的自觉为诗歌创作注入了新情感、新内容,而文的自觉则为诗歌创作确立了新准则,带来了新面貌,为六朝的情采说奠定了基础。这一变化可以曹丕为最早标志,曹丕“提倡的功劳”确实不可埋没。
二
建安以后,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更为大胆地向封建伦理道德发出挑战,置政治、社会的功利目的于不顾,去追求属于个人生命的真实的喜怒哀乐,爱己之所爱,恨己之所恨,悲己之所悲,当笑则笑,当哭则哭,任性而行,任情而行,绝不矫揉造作。试看《世说新语》中的几则记载: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伤逝》)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任诞》)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惑溺》)无论父对子,子对母,妻对夫,都流露出一派至性至情,而决不顾念名教观念、礼法传统。显然,这是对长期来人性被扭曲、被异化的一种反拨,所以晋人裴頠说:“历观近世,不能慕远,溺于近情。”(注:见《晋书·裴頠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43页。)卫铄说:“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注:卫铄:《笔阵图》,见严可均校辑《全晋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290页。)这种重情的风气,自然要反映到诗歌创作中来。孙楚的爱妻胡毋氏病故,孙楚极为悲痛,并作了一首悼亡诗,诗云:“时迈不停,日月电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礼制有叙,告除灵丘。临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济读了这首诗后,深受感动,说:“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丽之重。”(注: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见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8页。 )作诗者以抒写至情为宗旨,评诗者以是否抒写了至情及情感是否强烈作为评论的标准,就是对当时诗坛重情风气的一种反映。
确实,既真实又充沛的感情对于诗歌来说是重要的。但是,由于情感不能直接地说出来,也不能用缺乏美感的语言来表现,而必须借助华美生动的语言外壳,因此追求语言的风格之美,也成了这一时期人们合乎逻辑的越来越自觉的行为。讲对偶,重声律,尚丽辞,越来越成为风气,到西晋太康时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所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又在《时序》中所说,西晋诗人“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而陆机、潘岳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东晋孙绰曾称:“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注: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见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上册,中华书局1984 年版, 第143页。)人们越来越将诗歌作为一种遣辞造句、 敷陈藻彩的技艺看待,诗歌语言越来越向美的深层次迈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见解: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诗缘情而绮靡”,第一次将诗与赋等别的文体分开,专论诗在内容与形式上的主要特征,这比起曹丕“诗赋欲丽”以诗赋并提并只言及其语言形式之“丽”来,显然是前进了一大步。“诗缘情”,即谓诗歌乃因情感激动而作。与“诗言志”相比,应当说二者之间有联系,它们都看到并强调了诗歌是对作者内心世界的表现,因此有的论者将二者理解为一事,如《文选》李善注云:“诗以言志,故曰缘情。”五臣李周翰注亦云:“诗言志故缘情。”其实,二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即此前汉儒多将“志”理解为思想,即儒家所要求的政治教化、伦理道德;即使理解为感情,也要“发乎情,止乎礼义”,让“情”经过儒家伦理道德的净化。陆机却只是实实在在地谈了“情”,一种摆脱了儒家礼义羁绊的情,从而第一次明确地强调了“情”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及其作为诗歌本体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从此,“缘情”说与“言志”说在许多情况下成了两个彼此对立的概念,而由于“缘情”说更为符合诗歌的本质特征,得到了不少后人的肯定。
对“绮靡”的理解不尽一致。《文选》李善注:“绮靡,精妙之言。”芮挺章《国秀集》:“昔陆平原之论文曰‘诗缘情而绮靡’,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张凤翼《文选纂注》:“绮靡,华丽也。”陈柱《讲陆士衡〈文赋〉自己》:“绮言其文采,靡言其声音。”黄侃《文选评点》:“绮,文也。靡,细也,微也。”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对此更有较详的论述,云:“‘绮’,本义是一种素白色织纹的缯。《汉书》注:‘即今之所谓细绫也。’而《方言》说:‘东齐言布帛之细者曰“绫”,秦晋曰“靡”。’郭注:‘靡,细好也。’可见,‘绮靡’连文,实是同义复词,本义为细好。……原来‘绮靡’一词,不过是用织物来譬喻细而精的意思罢了。”(注:《诗言志辨》,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所论虽不尽一致, 但大体均就语言的精美而言,当是没有疑问的。在陆机看来,诉诸视觉的文辞须有一种形态色泽之美,也就是说必须讲究修辞。而其修辞的范围,包括了必须注意辞藻的色泽、声律、骈偶、用典等诸多方面。这从《文赋》的下列论述不难看出:
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文选》五臣张铣注:“妍,美也。”许文雨《文论讲疏》释前四句:“按四句见陆氏文尚妍丽之主张。”《文选》五臣李周翰注:“音声,谓宫商合韵也。至于宫商合韵,递相间错,犹如五色文彩以相宣明也。”《文选》李善注释后四句:“谓文藻思如绮会。千眠,光色盛貌。”五臣吕延济注:“绮合,如绮彩之合文章也。”又:“五色备曰缛。音韵合和故若繁弦之声。”均颇合《文赋》本意。这表明,陆机已在相当严格的意义上从“属文”、从修辞、从藻彩的角度理解文学,特别是理解诗,他不仅要求词藻应当华美,还要求有抑扬顿挫的音乐美,也就是要有纯粹的诗美。对语言音声之美的要求,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对后来南朝永明声律说的提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刘勰所说的“声有飞沉”,沈约所说的“浮声”、“切响”、“低昂互节”,都是与陆机“音声迭代”的说法一脉相承的。
总的来看,“诗缘情而绮靡”以明确而精练的语言,突出地强调了情感与辞采美的结合,将诗歌的两大美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这在中国美学史上尚属首次,所以朱自清认为“陆机的《文赋》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注:《诗言志辨》,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 “寓训勉于诗赋”的一类教条在这里更被远远地抛到了一边,代表了当时作家对于诗歌特征的新认识,所以朱自清又认为“陆机实在是用了新的尺度”(注:《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诗言志辨》,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在从“人的觉醒”到“文的觉醒”的历程中,“诗缘情而绮靡”可说是树起了一个崭新的里程碑,为六朝情采说打下了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从而开创了六朝诗歌既重情又重文的崭新局面。
三
陆机之后,“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更成为人们生活的信条,名教礼法的约束进一步被抛弃,人们更为大胆地毫无保留地宣泄自己的喜怒哀乐。试看《世说新语》中的几则记载: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玡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言语》)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言语》)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言语》)
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伤逝》)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任诞》)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玡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任诞》)再看《晋书·王羲之传》:
王右军既去官,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爱亲人,爱朋友,爱山水,爱艺术,爱生命,爱国家,悲可以“恸绝”,“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注:宗白华:《艺境·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 页。),这种无遮无碍的表达情感的方式,可以说真正是前无古人!《世说新语·轻诋》:“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纵心调畅”、“情性自得”,正是他们的生活准则和人生目标。而其所谓的“情性”,乃是不折不扣的天然真性。还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对人物的品评多注意人物的德行或风神,而这一时期对感情的品评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前引材料中“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的评论即属其例,反映了当时人的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和人生价值观念的根本性变化。
到了南朝,人们的行为表现或有了不同,但崇真斥伪、对“情性自得”的追求却一点也没有变化,谢惠连《秋怀》诗:“未知古人心,且从性所玩。宾至可命觞,朋来当染翰。”鲍照《答客》诗:“专求遂性乐,不计缉名期。欢至独斟酒,忧来辄赋诗。”均表明了这一点。南朝人也许不像东晋人那样过分地纵情,但重情的程度却是更深了,就像河水可以汹涌澎湃,但汇聚到湖海中后,却反而显得平静了。
在这种情况下,表现感情更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爱情、友谊、相思、羁愁、物感这些人生最普遍最常见的感情,在六朝诗中都有大量表现。对“情性”、“缘情”的性质、功能,在理论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和宣扬。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五情发而为辞章”,除专设《情采》篇论述感情和辞采的关系之外,在《明诗》、《诠赋》、《神思》、《风骨》、《体性》等各篇中都探讨和强调了感情的问题。即使在《宗经》中,刘勰所说的“六义”,第一义也是“情深”。可以说《文心雕龙》是始终把“情”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的,《熔裁》所云“万趣会文,不离辞情”,反映了刘勰对于诗美的一个基本的看法。钟嵘在《诗品序》中也强调“吟咏情性”,并对诗歌抒情内容产生的环境因素及其功能作了具体描述。萧子显也是吟咏情性的积极鼓吹者,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对“典正可采”而“酷不入情”的诗风进行了抨击。这些,都鲜明地将诗歌视为作家个人情性、性灵的表现,都代表了当时人对诗歌基本性质和特征的认识。
在这方面,萧纲和萧绎的看法可能是最突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了。萧纲《与湘东王书》在批评了京师文体的“懦钝殊常”之后说:
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佳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裴子野《雕虫论》:“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所谓“六艺”,即儒家六经。裴子野对当时诗坛置儒家政教于不顾而一味“吟咏情性”的作法不满,而萧纲又对裴子野的说法不满,上述言论即是针对裴子野而发的。萧纲认为,抒情写志(“志”与“情”在这里同义)和描绘自然风景的作品,不应以儒家经典为模仿对象,如果这样做了,那是有违《国风》、《楚辞》以来诗歌抒情写景的优良传统的。言外之意,“摈落六艺”乃情理中事,是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吟咏情性”应按其自身规律办事,应有其动人的情感力量,应有形象和文采。萧纲的说法,无疑又为新时代的“情性”说谱出了一个强音符。
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萧纲再次为“情性”说喊出了一个强音: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在这里,萧纲明确地提出了为人与为文不必一致的二元化主张。“立身先须谨重”,即还是要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讲究做人的规矩,不得放荡;而为文则不一样,不仅不必“谨重”,而且还须“放荡”。这里所说的“放荡”,乃与“谨重”相对而言,是通脱随便、不受拘束的意思。具体说来又可指两个方面:思想内容“放荡”,指什么内容都可以入诗,什么感情都可以抒发,不必畏首畏尾、多所顾忌。艺术形式“放荡”,指不必为传统的形式和法则所拘束,可以大胆突破和创新。这里恐主要指思想内容的“放荡”而言。立身与文章是很难截然分开的。朱光潜就曾指出:“在中国文学中,道德的严肃和艺术的严肃并不截分为二事。”(注:《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萧纲却在这里将其“截分为二事”,就其本意,实是要将文学与儒学政教进一步分割开来,使其真正获得独立的品位。在萧纲看来,以“礼义”持身者不必甚至不要在文章中顾及或言及“礼义”,因为“礼义”是用来持身的,而文章却是用来抒情的,用“礼义”持身可以使人“谨重”,而用文章抒情可以使人愉悦,两者功能不同,不能提出同样的要求,不妨各行其事,各自朝其特定的目标发展。这无疑是与“纵心调畅”、“情性自得”的主张一脉相通,而与强调文学政教作用的观点大相悖逆的,是充分体现了文学自觉时代的特色和精神的。
萧纲主张“放荡”地“吟咏情性”,这种主张是否值得肯定,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予肯定,还有必要考察一下他所说的“情性”的内涵。其《答张缵谢示集书》云:
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又《答新渝侯和诗书》云:
垂示三首,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跨蹑曹、左,含超潘、陆。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在这里,萧纲虽将描写“影里细腰”、“镜中好面”即女子体态美、容色美的作品视为“性情卓绝”之作,但同时也要求诗歌表现“或乡思凄然,或雄心喷薄”的感受,甚至提倡表现边塞生活。总的要求是“寓目写心,因事而作”,写亲眼所见的内容,表达自己内心的切身感受。可见,萧纲所提倡的“情性”还是有比较宽泛的内涵的,“吟咏”这样的“情性”,“放荡”这样的“情性”,从理论上说,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认为描绘女子的体态、容色之美,抒发男女之情是出自“性情”即人的本性,与“食色,性也”(注:《孟子·告子上》,见杨伯峻《孟子译注》下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5页。 )的说法并无二致,也是无可厚非的;认为对此体会越深、描绘越精便是“性情卓绝”,似也没有大错。但如一味专意于此,“放荡”于此,则不免偏激,不免片面,这是需要指出的。
萧纲的弟弟萧绎发表了与萧纲相似的见解。他不仅在《与刘孝绰书》中公开主张“吟咏情性”,同时在《金楼子·立言》中,将作为抒发性灵的“文”与作为实用文体的“笔”作了严格区别,认为“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认为:“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即认为文须像民间歌谣那样表现摇荡的性灵和流连的哀思,同时还要有华丽漂亮的词藻(“绮縠纷披”)和抑扬悦耳的音律(“唇吻遒会”)。不难看出,萧绎所理解的“文”的特征,包括情感、词采、声韵三个方面,这个“文”已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纯文学大致相当,代表了当时对于抒情文学审美特征认识的最高水平。
这一时期,人们对于辞采之美大都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认为作品应该是情感美、形象美、声韵美的结合。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要求写出“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的作品,认为“断章之功,于斯盛矣”。《情采》、《夸饰》、《丽辞》、《熔裁》、《章句》、《练字》、《指瑕》各篇都论述了用词造句、文采修辞的问题,《情采》一篇,更集中讨论了“情”与辞采之间的关系。萧统《文选序》要求作品“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要求精心结撰,讲求文辞的美丽(其“翰藻”包括讲究遣词、用典、对偶、声律诸方面)。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也说:“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沈约、钟嵘等人,也都对“遒丽之辞”、“盛藻”持肯定态度,“词采华茂”的曹植、“举体华美”的陆机、其诗”烂若舒锦”的潘岳等在《诗品》中均被列入上品。讲究辞采,已在这一时期蔚然成风。
应当看到,六朝时虽有不少人对情、采的问题发表了通达的看法,但凡事都得有个“度”,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并不都是得当的,对情、采之间关系的认识与把握也并不都是比较辩证的。一些人由于身为贵族中人,甚至身为王侯、太子、帝王,思想感情相当贫弱,生活面狭窄,生活情趣低级,因此“放荡”性情、对文学社会功能极度轻视的结果,便只能一味的“嘲风雪,弄花草”(注:白居易:《与元九书》,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甚至一味地驱驰声色之美,视情性与女色的欣赏同义,便显然是过“度”了。一些人过分追求辞藻的华美,风格过于浓艳,也是一病。但是,主张文学应注重“情采”,特别是主张“情性”就是不受拘束地表现自我,在当时确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吟咏情性”是对“缘情”说的进一步发展,它彻底背弃了美刺比兴的诗学传统,标志着诗美观念的最后确立,标志着中古这个文学自觉时代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在“吟咏情性”的思想指导下,诗人们倾全力追求作品的美学价值,在诗歌史和美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四
总的来看,汉魏六朝诗歌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功利逐渐走向非功利,是文学与非文学逐渐走向分离。人们逐渐从着眼于诗歌的外部联系(特别是与儒家经学、政治教化的联系)转向着眼于诗歌的内部联系,着眼于诗歌所特有的美质,从而使诗歌一步步地摆脱了政治教化的羁绊,走向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自我。这个过程之所以能在六朝时期最后完成,大约基于下列原因:
一是儒家思想的衰微,老庄玄学的兴起。东汉末年,随着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式微,一直被大一统封建王朝标为旗帜的儒家名教也就逐渐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而取而代之的是道家玄学思想。儒家名教和道家玄学对人、对文的看法与要求有很大不同。儒家虽并不绝对否定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但它却认为群体、社会是无限地高于个体的,个体应当绝对地服从于群体,服从于仁义道德,从本质上说它实际上是否定个体的存在、个性的独立和人格的自由的。而道家则恰恰相反,它尊重人作为个体的存在,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尊重个性的独立和人格的自由。于是,从东汉末年起,自我开始被发现,感情、欲望、个性开始被发现,一个大写的“我”字开始被堂而皇之地崇奉。试看《世说新语》中的两则记载:
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庚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方正》)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品藻》)这种对于自我的理直气壮的强调,在儒家名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不会被认可的。于是,在魏晋时期形成了“尚通脱”的风气,不受礼法的拘束,任情率真成为时髦。与主体个性密切相关的情感被提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王弼公开主张:“圣人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情。”(注:《老子道德经》,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7页。)认为自然的情感不可革除,高扬了情感的意义和价值。虽然道家的思想和主张绝非十全十美,比如个体就不能绝对地脱离群体而存在,而情有雅俗,性有善恶,一味地放纵情性也并不都是可取的,但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思想和主张对个体独立地位的确立、对人性与个性的张扬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而个体独立地位的确立,对诗歌情感独立地位的确立和诗歌本体地位的确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此,诗歌开始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独立发展,开始从群体的工具、政教的工具变成了个体生命意识的一部分,开始自觉地把情感表现放到重要的位置,从情感的体验和抒发中去追求美、展示美。一句话,诗歌开始回归到人自身,回归到个人的心灵和情感。抒情不仅成为诗人们在创作中的自觉追求,也同时成为诗论家们在理论上的自觉认识。从曹丕到刘勰、钟嵘,他们重个性、重气质、重情感,实际上都是重视自我,重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其发展的轨迹是清晰可寻的。
二是帝王士族的好尚娱乐。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坛的主力是由帝王、贵族和士族构成的,他们不仅创作了大量诗歌,而且左右了当时诗歌创作的方向。东汉末年,由于生命无常,人生苦短,在士人中已经兴起及时行乐思想,魏末以后更日趋发展。东晋张湛在其编定作注的《列子》中,更大张旗鼓地鼓吹享乐哲学,认为人应当在有限的人生中尽情享乐,而享乐的基本手段是“丰屋、美服、厚味、姣色”再加上“音声”,包含了物质生活的享受、精神生活的享受、官能欲望的满足等几个方面。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帝王、贵族和士族,他们自然不可能超脱于外,应当说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还很突出,不过在享乐的程度和侧重的方面上有所不同而已。对诗歌创作而言,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把这当作娱乐的手段来看待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不少文学团体,团体中人常常在一起饮宴赋诗,常常夜以继日,乐此不疲。作诗既与饮宴结合到了一起,就很难说是纯粹的严肃的创作活动。实际上,在这样的场合,赋诗确实往往只是一种炫耀词藻和才华的娱乐活动。他们在诗歌中“畅情”,目的往往也是为了“自适”。为了“华丽好看”,他们因此醉心于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在辞采的华美、对偶的精整、声律的谐协、用词的工巧等方面倾注了不少的精力。应当承认,诗歌是有娱乐的功能的,所谓审美愉悦,所谓审美快感,就包含了娱乐的成分在内。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审美愉悦,诗人在创作中努力追求诗美,表现诗美,不仅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是应大力提倡的。不过,这一切都应限定在“审美”的范围内,前提是诗人所表现、所追求的一切都应当是“美”的。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六朝诗人们的表现并不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把诗歌视作一种娱乐手段的风气,在客观上却为诗美的发现营造了氛围,创造了条件,从而推动了诗美观念的最后确立。
三是得益于长期的创作实践。从诗歌最初产生的时候算起,到六朝诗美观念的最后确立,诗歌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在这个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诗人们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总结,因而逐渐地认识和把握了诗歌的美质,这应是六朝诗美观念得以最后确立的最根本原因。实际上,诗歌的美质是固有的,儒家思想不可能长期地扭曲它、掩盖它,道家思想也不可能去生成它,它最终是会被人们明确地认识和把握的。到了南朝齐梁时期,这种认识和把握就越来越趋向“纯粹”,趋向明确,比如萧纲等人提倡“吟咏情性”,他们所理解的“情性”,就既不同于儒家的传统观念,也不同于魏晋玄学的观念,也就是说,这已是对于诗歌根本特征、内在美质的最“纯正”的把握和理解。而诗美观念也只有到了这时,才算是真正地确立了。
标签:儒家论文; 诗歌论文;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论文; 文学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文选论文; 诗言志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