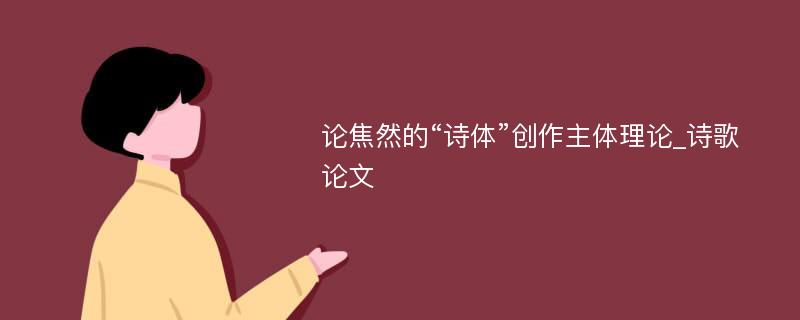
论皎然《诗式》的创作主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论文,论皎然论文,诗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唐的皎然既是一位诗僧,也是一位诗论家。据赞宁《高僧传·道标传》记载,他的诗歌与当时著名诗僧灵澈、道标并称于世,有“之昼,能清秀”的口碑。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则称:“释皎然之诗,在唐诸僧之上”。其诗论专著《诗式》脱颖于唐代诗格之林,别有建树。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指出:唐人诗话“唯皎然《诗式》、《诗议》二撰,时有妙解”。清人毛稚黄《诗辩坻》则曰:“论诗则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皎然《诗式》、严羽《沧浪诗话》、徐祯卿《谈艺录》、王世贞《艺苑卮言》,此六家多能发微。”细心研绎,皎然诗论的“妙解”、“发微”之处,在于他以诗人之胸次,提出“真于性情”、“苦思”、“文外之旨”的观点,论述了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的独特心态,艺术传达的独特过程以及主体所期盼的理想境界,漾溢着诗人智慧的氤氲,构成了创作主体动态研究的理论体系。
一
皎然论诗推重谢灵运,《诗式·文章宗旨》称谢诗“发皆造极”,“上蹑风骚,下超魏晋”,之所以达如此境界,乃因其诗“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所谓“真于性情”是诗人创作伊始的特殊创作心态,正是这种心态使诗人妙笔生花,创造出千姿百态的作品。由此可见,“真于性情”是皎然创作主体论的核心,也是他研究诗歌创作主体的基点。皎然重视“性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释福琳的《唐湖州杼山皎然传》称皎然:“特别留心于篇什中,吟咏情性,所谓造其微矣”。从皎然的《诗式》和《诗议》看来,“性情”既是诗歌创作的出发点,也是诗歌创作的旨归。《文镜秘府论》南卷引有皎然的一段话:“夫诗工创心,以情为地,以兴为经,然后清音韵其风律,丽句增其文彩”;地卷引其论诗歌六义时亦云:“赋者,布也,匠事布文,以写情也。”“性情”是诗歌之源,一切的艺术手段也只是为了抒写情性。因此,他论诗将“不用事”的“格情并高”之作尊为第一格,是诗之至也。在辩诗体十九字中就有诸如“高”、“逸”、“贞”、“忠”、“节”、“志”、“气”、“德”、“诫”、“闲”、“达”、“悲”、“怨”、“静”、“远”等十五字属于主体的思想情志性质。“放词正直曰贞”、“风情耿介曰气”、“情性疏野曰闲”,皆以人的禀性、德行描述诗歌的风格。甚至对诗境“静”乃“意中之静”,“远”乃“意中之远”的解释也是强调主体的心境。
由此,我们有必要回到“吟咏性情”这个中国古老的诗论命题中。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以其卓越的文学识见,将诗歌的功能概括为“兴观群怨”四字,以“兴”为先导,指出诗歌的功能是通过“兴”,即情感的兴发来实现的。然而诗歌所抒之情必须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从而实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终极目标,把情感限制在儒家伦理道德的范围中。至《毛诗序》则明确指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质,并反复论说情之所以生及情之所以往。“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国史明乎得失之际,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即是说,情感因感时伤政所兴,而吟咏情性的目的则为“风其上”,要受礼义的限制。“吟咏情性”说仍局囿在社会伦理道德的范畴中,必然产生束缚个性发展的消极因素。西晋的陆机著《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之说,这“情”是创作主体情感、志趣、理想的融合。皎然沿着“诗缘情而绮靡”之说向前走去,跨越儒家诗论的樊篱,强调为诗必“真于性情”。他激赏苏李诗,盖因“二子天予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诗式·不用事》)。或以“天真”一词代“真于性情”,如《诗式序》云:“至于天真挺拔之句,与造化争衡,可以意冥,难以言状。”
皎然论创作主体心态的“真于性情”、“真性”和“天真”颇得禅理之助,然又有所区别。释家言“天真”、“真性”指的是天然本具的心体。如《传心法要》云:“天真自性,本无迷悟”。《坛经·定慧品》云:“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可知释家的“天真”、“真性”是抽象、绝对、虚无的本体意义的佛性。诚如皎然在《诗式序》中所说:世事喧哗,非禅者之境,假如博识的仲尼和骨肉至亲终日在眼前论道说义,必然会扰乱“真性”。禅者心仪的是与孤松片云相对禅坐,因其至静而性同啊!释家的真性乃“真如本性”,并非我们一般人所说的真情实感。皎然借用释家之语论创作主体心态“真于性情”,有着特殊的涵蕴。关于谢灵运他有这样深深的感喟:“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澈,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诗式·文章宗旨》)显而易见,“性颖神澈”指的是诗人的天然资质和禀赋,皎然认为“文章关其本性”(《文镜秘府论》南卷),它是诗歌创作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天赋之“性颖神澈”须得才识之助,因为“识高才劣者,理周而文窒;才多识微者,句佳而味少”(《文镜秘府论》南卷)。而才识是指审美的认识能力和艺术的表现能力。“性颖神澈”的谢灵运为诗“发皆造极”,还因为他幼即好学,博览群书,“及通内典,心地更精”之故。才识得于博览群书的深厚文学修养,以才识辅天赋,凭天赋运才识,才是真正的诗人,才能创作出句佳而味永的诗作。一个真正的诗人不仅要有“性颖神澈”的资质,还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这是“真于性情”的重要内容。其次,“真于性情”还强调创作主体心态的自由狂放。皎然在诗歌中常常抒写这种情状。《出游》诗曰:“狂发从乱歌,情来任闲步。”《戏作》诗云:“不知独悟时,大笑放清狂”。这是何等旷达豪放、无拘无束、任性自然的真性情啊,它“性野趣无端”(《独游二首》),具有深远的审美意蕴。《诗式》评《邺中集》指出在邺中七子中,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的诗作“不拘对属,偶或有之,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流一也。”曹植诗歌中的对偶句是据情兴的需要而为,创作的情感是内心兴发感动的真情实感。《诗式》在比较江淹《拟班婕好咏团扇诗》和班之原作后谓江诗“画作秦王女,乘鸾向烟雾”的兴象是“兴生于中,无有古事”,从诗人内心自然勃发,故而“情远词丽”,有独特的韵味,给人以审美的愉悦。“真于性情”乃诗人所拥有的自由的审美心态,艺术美的清泉就从这渊薮中汩汩而出。再次,“真于性情”还注意到创造性思维的无限想象性、扩展性和包容性特点。“真于性情”是诗人创造性思维的原动力,情感体验中的诗人,其思绪“精鹜八极 心游万仞”。《诗式序》云:“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彼天地日月,玄化之渊奥,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皎然将诗列为六经之首,称颂诗人的情思能抉隐烛幽,妙通万象,而诗作为艺术创造的精华,“妙均于圣”。将作诗与圣人治经相提并论,真乃振聋发聩之语。皎然在诗作中也反复咏叹着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其《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云:“如何万象自心出,而心淡然无所营”;《周长史昉画毗沙门天王歌》云:“吾知真象非本色,此中妙用君心得”;《张伯高草书歌》云:“须臾变态皆自我,象形类物无不可”。诗人们“真于性情”,创造性思维随着情兴的自然迸发,“前无古人,独生我思”(《诗式·立意总评》),“取由我衷”,展现出诗歌美的独特魅力。
二
创作的过程是情感意旨外化的过程,即艺术传达的过程。诗人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应超越现实生活的功利性情绪进入“真于性情”的审美心态。基于此,皎然标举自然之美。他认为好诗是自然天成,如夺天功的,它们“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诗式·诗有六至》),这里所说的“自然”显然不是自然主义对客观事物的照搬及主观感情的宣泄,而是艺术化的自然,它产生于“至难至险”的苦思中,这就是艺术传达过程的重要特征。他颂扬谢灵运诗歌“真于性情”而风流自然,同时又指出他“尚于作用”。这“尚于作用”就是指苦心构思,锻字炼句,录求恰当的艺术表达方式的艰苦过程。《诗式·取境》中矫正了一般人认为作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的说法。他指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皎然藉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苦思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优秀的诗歌毫无斧凿之痕,在欣赏者看来浑然天成,仿佛是顺手拈来,“不思而得”,这就达到了“自然”之境。但创作过程中这种境界的取得是“至难至险”,颇费气力的。至于灵机忽通,“意静神王,佳句纵横”思如泉涌时,也决非神助,只能是“先积精思”,赖长期的文学修养和苦心琢磨的结果。深思苦研,才能于“意静神王”中欣然有所得。因而,皎然能在艰苦的创作中优游不迫,乐在其中。“断壁分垂影,流泉入苦吟”(《赋得啼猿送客》)、“山情与诗思,烂熳欲何从”(《送丘秀才游越》),这是何等惬意的境界啊。
关于创作过程中“苦思”的特点,汉代的两位作家扬雄和桓谭体会甚深,据桓谭《新论》载:子云言“每上甘泉,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精苦。赋成,遂困卧小倦,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桓谭自己“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精思太剧,而立感发病,弥日瘳。”这是多么艰苦的创作情景,而他们却不辞艰辛,呕心沥血。唐代的杜甫提倡苦思,他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为诗歌创作的理想境界,肯定创作的苦思和锤炼。他说自己写诗“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之七),“觅句新知律”(《又示宗武》),“遣词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字斟句酌,刻意求工,寻求美,创造美,展现由必然而至自由、重法度而又穷变化的艺术境界。他欣赏苦思的诗人,感叹裴迪“知君苦思缘诗瘦”(《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赞扬曹霸善画马得之于“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并非率意而为的急就篇。讲究苦思的创作风尚在《诗式》中升华为理论的表述,对于“苦思”和“自然”这看似矛盾的一对概念,皎然在阐述中表现出严密的逻辑性。皎然以其对诗歌的深刻领悟,高度肯定了艺术主体纵横驰骋的创造力。
诚然,艺术的创造是对生命的感受,是心灵的外现,诗人须进入“真于性情”的审美心态,而心灵的表现则要凭藉语言形式和一定的艺术手段,将心灵情感转化成具体可感的形式。诗歌有其特殊的规律,诗人必然得遵守规律,创造出形式和内容完美统一的佳作。皎然从创作诸方面强调苦思,第一:谨守法度,因自然必是合乎法度的自然。诚然,他批评过沈约等人的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桎梏了诗人的情感,使风雅殆尽。但是合乎自然的声律规范是必须遵从的。因为诗歌的“轻重低昂之节,韵合情高,此未损文格”(《诗式·明四声》)。而自然之声律决不妨碍自由地创造和表现。《明作用》条云:“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以《神仙传》中卖药壶公的典故形象地说明了创作中的自由是深谙艺术规律、遵从艺术规律的自由,惟此,才能创造“至苦而无迹”的自然之境。皎然特别强调诗歌的法度是自然规律的艺术表现,他在《诗式》中论对句时说:“夫对者,如天尊地卑,君臣父子,盖天地自然之数,若斤斧迹存,不合自然,则非作者之意。”第二:修饰丽藻。他提出诗应“至丽而自然”,“丽”从狭义方面看指修饰言辞文彩。他在论取境时说:“或云:‘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无盐阙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诗以情感人,而内在的情性应外现为辞藻之美,华辞丽藻而现情性乃是自然的表现。因此他反复强调言辞之美,诸如律诗以“情多,兴远,语丽为上”(《诗式·律诗》),“虽欲废言尚意,而典丽不得遗”(《诗式·诗有二废》)皆是。第三:构建变化无方的体势。《诗式·立意总评》提出诗人立意应是别出心裁,变化万端无所依傍的,《明势》条亦云:“高手述作,如登衡巫,觌三湘,鄢、郢山川之盛,萦回盘薄,千变万态。”皎然以山川风云的变化比喻诗的体势,亦是强调自然美得之于苦思的表现。
在论述创作过程“苦思”的特点时,皎然提出了著名的中道说:“是知溺情废语,则语朴情暗;事语轻情,则情阙语淡。巧拙清浊,有以见贤人之志矣。抵而论属于至解,其犹空门证性有中道乎?”(《文镜秘府论》南卷引)皎然从释家借来“中道”一词,以论诗的自然美。《文镜秘府论笺》对空门论性有中道作了这样的注释:“离有离无,斯为中道。”离有离无,意为不偏不倚。《诗式》所说的诗有四不:气高而不怒、力劲而不露、情多而不暗,才瞻而不疏;诗有六至: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等,就是对诗家之中道的具体说明。诗歌应创造和谐的自然美,这似乎是先秦时期儒家已提出的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再现。遗憾的是儒家的要旨在强调艺术的教化作用,皎然论诗之中道是为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诗式序》),从诗歌内部规律着眼,使诗人领悟创作的奥秘,在诗的王国里作逍遥游。好诗在苦思和锤炼中孕育,表现出优美和谐、含蓄蕴藉的风貌。
皎然的“苦思”论对后世诗论家有深刻影响。司空图《诗品》论精神:“妙造自然,伊谁与裁”;梅尧臣谓:“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六一诗话》引);王安石《题张示昌诗后》云:“看似奇崛却平淡,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些创作经验之谈与皎然的苦思而不丧自然之论是一脉相承的。
三
艺术创作的过程是主体创造能力实现的过程,诗人们在“至难至险”的苦思小路跋涉,步履艰辛而满怀憧憬地仰望着“文外之旨”的艺术之颠。
皎然在谈到审美特质问题时指出好诗具有重意,重意即多重意蕴,他抽象为“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诗式·重意诗例》)。他认为谢灵运“池塘生春草”诗句妙在“情在言外,故其辞淡而味”(《诗式·池塘生春草》)。对传统的比兴手法他的解释是“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诗式·用事》)。文外之旨、情在言外、象下之意指诗歌的审美价值并不在容易感受的明晰的语辞形象,而是被语辞形象所暗示、并蕴含于其中的多层次情思,这就是优秀诗歌具有永恒魅力的奥妙所在。
“文外之旨”的理论依据是释道学说。老庄哲学以无为本,道是老庄哲学的最高范畴,具有超自然的神秘性,且是无可言状的,《老子·道经》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知北游》亦云:“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正是在对于宇宙本体的这种认识中,产生了老庄哲学的言意矛盾说,并得出这样的结论:“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欲求至理,虽从语辞入手,但心智必须突破言语的局限而浮想联翩,才得其真谛。释家亦以无为本,但将抽象的、绝对的、虚无的本体——真如当作世界的本源。《维摩识经》云:“凡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即相,见如来。”因此,禅宗强调悟性,力主“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以防“言语道断”。皎然“文外之旨”说吸收释、道诸家关于言意关系的论点,揭示了诗歌美的真谛。
皎然“文外之旨”说的核心是性情,“旨”,即情意,即如他所阐明的“文外之旨”是“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诗式·重意诗例》)。他认为作诗要“废词尚意”,这里词是广义的,指诗歌的语言、声律、艺术手段诸种形于外的因素。如前所言,皎然是讲求诗歌艺术形式的,但一切的形式都只是表情达意的媒介物,是抒情的工具。“废词尚意”并非废黜言语形式,而是要求以准确、生动、精炼的语言表现丰厚的内容,而诸种艺术形式都消融在丰富的内蕴之中。“文外之旨”要求诗歌有可以反复体味的情思韵味,因此我们不必拘泥于皎然所说的二重意、三重意、四重意。其实它们指的就是诗歌感受的形象之外那空灵、朦胧、义旨深杳、不可穷尽的多重意蕴。试以皎然四重意中第一例《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说明。这平淡无奇的诗句既展示了动态的离别场景,又写出行者渐行渐远,居者衣带渐宽的凄伤,一去不复回的悲恸。与君别离乃抒写忧伤的事实,加一“生”字,“与君生别离”悲情更深。杜甫《梦李白》诗云:“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乃指出生别之悲更甚于死别。“死别”是人生的必然归宿,尊卑贵贱,概莫能外。而“生别”则有人为的成分。人生如朝露,为何要“同心而离居”,咀嚼相思的苦痛呢?字字句句,弥漫出人生不尽的忧思。
“文外之旨”对于创作主体来说要超越有限的文字追求无穷的意蕴,这就涉及到创作过程中诗歌情景的结合方式。皎然《秋日遥和卢使君》诗云:“古罄清霜下,寒山晓月中。诗情缘境发,法性寄筌空。”诗之写景实是抒情,“诗情缘境发”指出诗人之情外感于古罄清霜、寒山晓月的景色,触景生感,发为诗歌,景是情思之缘。他在《诗式》中所举的李陵《与苏武诗》:“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濯长缨而兴生离死别之哀;《古诗》“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则四顾茫然发人生之悲。这些都是自然景物及社会人生兴发感动之境。造境为了抒情,情赖景而出,犹如法性寄于言筌,法性本空,寄于言筌可见;诗情无形,托于境而明朗。诗是情和景的统一,所以他在《辩体有一十九字》中说:“缘景不尽曰情”,乃指出诗中之景实是诗人之情,这是韵味无穷的情意,所以说“情在言外”。情与景结合的理想境界是“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要求性情委婉含蓄地涵蕴在景物之中,“旨冥句中”,与客观景物水乳交融。就象他在《洞庭三山歌》中所说:“盼睐方知造境难,象忘神遇非笔端”那种情景结合,虚实相生的意境。皎然的“文外之旨”论影响深远,是为司空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诗与极浦书品》)、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之先导。
《诗式》对诗歌从创作的缘起到终结的动态过程作了系统研究。尽管皎然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限制,但他毕竟在传统诗论领域中创立了以审美为中心的创作主体论体系,昭示着美学新思潮的到来。因此,在诗歌理论史上,《诗式》的重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