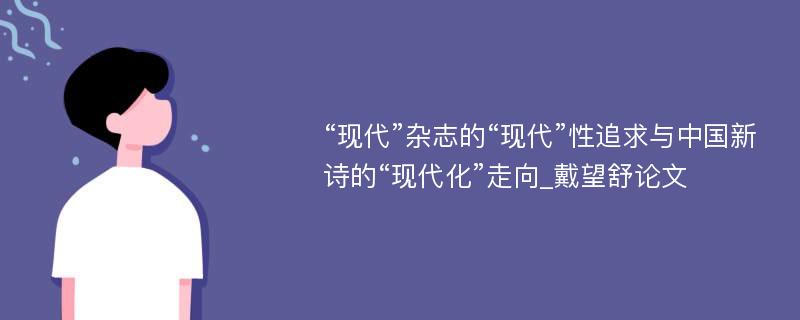
《现代》杂志的“现代”性追求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动向论文,中国论文,杂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新文学发生之初,虽然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派别正共时性地蓬勃发展着,但却未能在中国大地上引发大的回响,尽管不成系统的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几乎是始终伴随着新文学运动的,而且译介的广泛性也几乎涉及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各个大小流派。显然,“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性特征使它从一开始就兼容并包地广泛汲取异域文学营养,这当然包括了“五四”时期被称为“新浪漫主义”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虽然就西方而言,在一战后西方现代主义确立和繁荣之时,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已在走下坡路,这在当时许多“五四”人士也已自觉认识到。比如,茅盾就曾指出,当时的西洋文学“已经由浪漫主义进而为现实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我国却还停留在写实之前,这个显然又是步入后尘。”〔1 〕然而,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现代主义基本上是依附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存在的,始终没有得到独立的长足的发展。符合时代精神的浪漫主义文学,具有某种“实用理性”精神的写实主义,因为与当时的中国现实需求有更多的切合,也因有更多的人提倡和实践而得到相对充分的发展。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新文学补西方文学的课,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进程,现代主义的发展也当然有待于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之发展的相对饱和之后。
因而,现代主义文学在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即约20年代中后期开始而得到重大的发展,当是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创办于1932年5 月的大型文艺月刊《现代》杂志正是适时地诞生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关节点上。它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继它的前身《无轨列车》、《新文艺》之后更为系统化、更具影响力的第一个具有非常鲜明的现代主义文学价值取向、具有自己相当独特的个性特点的文艺杂志。《现代》杂志以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带有鲜明倾向性的译介和对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现代诗创作的积极倡扬,从而形成了现代诗的“大本营”〔2〕, 继而又带动了《水星》《文学杂志》《新诗》《现代诗风》《星火》《今代文艺》《菜花》《诗志》《小雅》等一系列具有现代主义风格追求的诗歌或文学杂志,从而串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诗潮,形成了1936—1937年这一“为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一个不再的黄金时代”〔3〕。无疑,无论从创刊之早、份量之重、 持续时间之长、“现代”风格之鲜明等各方面看,《现代》的意义都是无可替代的。如果说历史必然性要通过历史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在三十年代蔚为可观的现代主义诗潮中,《现代》正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偶然性。
在《现代》杂志的《创刊宣言》中,编者在宣布“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等几条之后,还有一条颇为耐人寻味,即:“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
这“编者个人的主观”为何?显然,要更好地理解《现代》,理解其风格、特色,理解其所以能在不可遏止的现代主义诗潮中承担起历史重负的主观原因,必然应对这“编者个人”有较好的了解。该刊虽然只署名施蛰存一人主编,但实际上戴望舒与杜衡也参予了一定的工作。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他们一起编的。直到“戴望舒出国,杜衡的论文引起了‘第三种人’的轩然大波。以后各期的编务,才由我独自承担。 ”〔4〕而到了第三卷开始,杜衡又正式加入编务,与施蛰存共同署名主编。施蛰存、戴望舒、杜衡曾被赵景深称为上海文艺界的“三驾马车”。这“三驾马车”个人人生经历都比较相似,都出身于小康富裕之家,都是热忱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同时,又追求进步,倾向革命,都参加了共青团。然而,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们都经历了一次从“左”(戴望舒和杜衡曾被捕入狱)转“中间”的思想波折。他们在“五卅”和“大革命”失败的血淋淋现实面前,感到了幻灭和怅惘,他们试图走一条同情革命而不实际参加革命却专注于文学艺术的纯粹知识分子的道路。他们在文学中找到了寄托,恰如杜衡说戴望舒那样,写诗“差不多是他灵魂的苏息、净化”〔5〕。施蛰存后来在回忆他们那时的心态说, “‘四一二事变’国共分裂后,我才晓得我们这些小共产党员只有死的分,没有活的机会。……从此我不再搞政治。戴望舒、杜衡和我都是独生子,我们都不能牺牲的,所以我们都不搞政治了。”〔6 〕他们选择了一条“消极的道路,即退避到Tour divoire(象牙之塔)里去,讴歌着那与自己的社会环境离绝的梦想”〔7〕。 这形成了“三驾马车”自由主义的立场和“中间人”的心态,这种立场和心态不可能不表现于《现代》杂志,虽然施蛰存在《创刊宣言》中宣布《现代》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而且即使在几十年之后,仍持这种观点,极力表白自己为保持《现代》的这一宗旨所作的努力,并对当年谷非(胡风)在《文学月报》上发表文章,“把《现代》看作‘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深表不满。〔8〕但综观《现代》, 我觉得施蛰存等倾向于自由主义立场与“第三种人”的心态还是很明显的。胡风的批评并非毫无根据,空穴来风。《创刊宣言》中“非狭义的同人杂志”,“不预备造成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的宣言,以及“我要《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的“私愿”〔9〕等虽都可以视作真诚的肺腑之语,然而, 也可能不自觉地与编者作为书局老板聘请的雇员的身份有关。这种身份不能不使《现代》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商业利益,这也必然使《现代》不能不考虑到最广大的作者群和读者面。自然,曾经参加过革命的经历,使他们仍然保持了一份对革命的同情,这也是事实。这也同样会使《现代》并不拒绝左翼作家和作品,客观上使它保持了“非狭义的同人杂志”的立场。然而,自由主义立场与“第三种人”的心态则是骨子里的。施蛰存后来曾明确说过:“《现代》杂志的立场就是文艺上自由主义,但并不拒绝左翼作家和作品。”〔10〕
我们不妨举几则《现代》中的史料来说明。首先,在《现代》上挑起关于“第三种人”论战的就是杜衡发表于《现代》杂志一卷三期上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而在经历过你去我回、难分胜负的回合之后,编者在同期编发了苏汶(即杜衡)的文章之后的“社中日记”中写道:“苏汶先生交来《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关于这个问题,颇引起了许多论辩,我以为这实在也是目前我国文艺界必然会发生的现状。凡是进步的作家,不必与政治有直接的关系,一定都很明白我国的社会现状,而认识了相当的解决的方法。但同时,每个人都至少要有一些Egoism,这也是坦然的事实。我们的进步的批评家都忽视了这事实,所以苏汶先生遂觉得非一吐此久鲠之骨不快了。这篇文章,也很有精到的意见,和爽朗的态度,似乎很可以算是作者以前几篇关于这方面的文字的一个简劲的结束了。”〔11〕这里,编者鲜明的倾向性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在《现代》一卷五期上,施蛰存翻译了英国赫克里莱的《新的浪漫主义》,他显然对作者倡导的一种调和个人主义和集团主义的中间思想,表示极大的赞成。他在《译者记》中说:“我觉得在这两种纷争的浪漫主义同样地在中国彼此冲突着的时候,这篇文章对读者能尽一个公道的指导的。”〔12〕戴望舒在1933年从法国寄回的《法国通信》〔13〕,也不无倾向性和针对性地说:“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
我在这里当然不想对《现代》的这种心态进行价值判断,而只是想说明这种心态客观上与他们之独立、纯粹、自觉的,从“新月派”,初期象征派那里一路继承下来的“为诗而诗”的“纯诗”的艺术立场和艺术态度取得了契合,无论如何,这种立场对于他们的诗艺,对于他们倾心办《现代》,以鲜明的现代主义取向而顺应历史,为现代主义诗潮推波助澜,应该说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的。正如卞之琳论及他们这些“大约在1927年左右或稍后几年初露头角的诚实和敏感的诗人”时指出的那样,正是因为“回避现实,使他们中其余人在讲求艺术中寻找了出路。”〔14〕
编者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中间人”的心态以及相关的“纯诗”的艺术立场,自然会相反相成地影响并形成为《现代》杂志的其它一些鲜明的个性特点。比如,《现代》杂志给我以最强烈的印象的一点,是它的具有相当鲜明的“现代”的时间观念和价值立场。
在创刊号的“编辑座谈”中,施蛰存写道:“这个月刊既然定名为‘现代’,则在外国文学之介绍这一方面,我想也努力使它名副其实。我希望每一期的本志能给读者介绍一些外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在“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导言中,更是把这种“现代”观念表述得极为清楚:“……现在,二十世纪已经过了三分之一,而欧洲大战开始迄今,也有二十年之久,我们的读书界,对二十世纪的文学,战后的文学,却似乎除了高尔基或辛克莱这些个听得烂熟了的名字之外,便不知道有其他名字的存在。”〔15〕于是,正是有感于五四一代作家主要接受西方十九世纪文学影响的不够“现代”〔16〕,《现代》杂志在引进介绍西方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文艺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的工作。
所谓现代,其实是源自西方的一个词,按李欧梵的说法,是指“自现代以排斥过去的现时意识”〔17〕。这种“现代”的时间观念和价值立场,受五四以来“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他们之强调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的文学思潮,不是把它看作世界文学诸种潮流之一种,而是视作文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必然趋势。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种“以现时为主”的现代意识就相当强烈,在精英知识分子那儿,“现代意识”不仅仅只是以现时为主的信念,而且也是往西方求“新”、求“奇”的探索。因此,这种现代意识往往表现为:“在不同程度上继承西方‘中产阶级’现代风一些司空见惯的观念:进化与进步的观念,实证主义对历史前进运动的信心,以为科技可能造福人类的信仰,以及广义的人文主义架构中自由与民主的理想。”〔18〕《现代》编者的现代的时间观念和立场,显然也是这种现代意识作用的结果。
从对《现代》上译介外国文学的篇目来看,基本上都在时间上有着“现代”的特点,很少译介20世纪以前的外国文学,对于20世纪以前的文学大家,《现代》往往只是把他们当作历史人物加以尊重和纪念,如“司各特百年祭特辑”〔19〕“歌德逝世百年纪念画报”〔20〕等,都主要以照片画报的形式出现,极少详细的文学评介。这与他们对20世纪以来外国文学的译介构成鲜明的对照。不用说,《现代》上几乎每期都不惜篇幅,详细译介最新的西方文学,如:《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文学》《最近的意大利文学》《一九三二年的欧美文学杂志》《一九三二年的欧美文坛》《新的浪漫主义》《英美新兴诗派》《意象派的七个诗人》《诗歌往哪里去?》等。“国外文艺通信”(即请求学于外的文人写信通报当地最新文坛动态)栏目的设置,更产生与西方文坛共时对话的效果。基于这种“现代”的时间观念和价值立场,《现代》对美国文学情有独钟,精心策划,长期准备,发了一个“美国文学专号”〔21〕。在编者看来,“在各民族的现代文学中,除了苏联之外,便只有美国是可以十足的被称为‘现代’的。其它的民族,正因为在过去有着一部光荣的历史,是无意中让这部悠久的历史所牵累住,以至故步自封,尽在过去的传统上兜圈子,而不容易一脚进‘现代’的阶段。”编者显然还从美国文学的崛起于新大陆,冀望能对中国的新文学能有启发、引导、借鉴的作用:“诚然,美国文学的创造,是至今还在过程中,而没达到全然成熟之境。但是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在成长中,而不是在衰落中的文学;是一个将来的势力的先锋,而不是一个过去的势力的殿军。假如我们自己的新文学也是在创造的途中的话,那么这种新的势力的先锋难道不是我们最好的借镜吗?”
从《现代》编者的这种良苦用心,我们又不妨引申出它的较强的主观性的个性特点。显然,《现代》的编者对于办刊是抱有极大的热诚和极为自负的责任感的。它要“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22〕在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中,谈及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的隔膜与时差时,编者写道:“这一种对外国文学的认识的永久的停顿,实际上是每一个自信还能负起一点文化工作的使命来的人,都应该觉得惭汗无地的。”正因如此,编者的主观导向性是很明显的,尤其在外国文学的译介方面。在三卷一期上的“本刊征稿规约”上,在宣布本刊内容的七个部分之后,特别着重提出,“除第七项(指翻译、介绍……引者注)暂时不征外稿外,其余各项均欢迎投稿。”〔23〕这恐怕是很能说明编者在译介导向上不肯放手的良苦用心的。恰如他们自称的:“我们觉得各国现代文学专号的出刊,决不是我们的‘兴之所至’,而是成为我们的责任。”〔24〕
在译介上如此,在作品发稿,尤其是诗歌上,均能看出编者的主观意图。对称《现代》杂志上的诗为“谜诗”及对杨予英的诗歌的批评的读者来信〔25〕,编者在“社中座谈”的答复中也大有一种真理在握、得理不让人的架式。显然,对于《现代》上的,“至少可以说它们都是诗”(施蛰存语)的诗歌,编者的维护是不遗余力的,而编者维护的这种个人主观标准就诗歌来说,显然是编者心目中已经基本成型的关于现代诗的观念。施蛰存在《现代》第四卷一期的《文艺独白》上发表的《又关于本刊的诗》无疑正是这种现代诗观念的表露。这种主观性产生的凝聚力和排他性,当然使得《现代》极易形成为相对统一的现代诗风格,从而成为现代诗的“大本营”。
关于中国现代新诗,鉴于它自身的先天不足,梁实秋先生曾说过如下具有“片面的深刻”特点的惊人论断:“我一向以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大的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26〕卞之琳也曾经精到地指出戴望舒写诗和译诗的关系“望舒译诗的过程,正是他创作诗的过程。译道生、魏尔伦诗的同时,正是写《雨巷》的时候,译果尔蒙、耶麦的时候,正是他放弃韵律,转向自由诗体的‘时候’。”〔27〕这些情况都说明了中国现代新诗跟西方诗歌的密切关系。因而,《现代》杂志在现代主义诗潮中的历史意义和独特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它之译介倡扬西方现代主义诗潮而突出地表现出来的。据笔者粗略的统计,《现代》杂志从1932年5月1日第一卷第一期到1934年11月1日第六卷第一期共31 期中(不包括汪馥泉主编的最后三期),在外国诗歌的译介方面,共译诗歌83首,(如果算上《无轨列车》和《新文艺》上的诗歌,共115首), 几乎全是有着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的。而在推出形式上,《现代》显然精心策划,有明显的编辑意图。它常以“小辑”的方式集中译介(如“夏芝诗抄”、“桑德堡诗抄”、“现代美国诗抄”、“邓南遮诗抄”等),又常配以简评性的文章,在简述中则往往毫不掩饰地赞赏有加,这显然会对读者产生极强的审美趣味的导向作用。综合性评论的撰写或翻译,也很能说明《现代》的现代主义取向。这些文章也大多关涉一战后的新兴文学,绝少谈及十九世纪的文学。译诗及评论突出或提到的重要诗人,有夏芝、桑德堡、果尔蒙、庞德、艾略特、马里奈谛、核佛第尔、勃勒东、艾吕雅等。我们几乎可以说,在《现代》,几乎所有西方较为重要的现代主义的各个时期和各个流派的诗人,都有所介绍和涉及,但又有侧重和取舍,体现出鲜明的价值取向。兹择要分述之。
其一是“后期象征主义”,它是指在以波德莱尔、魏尔仑、兰波、马拉美为代表的“前期象征主义”之后,从法国扩及英、美、德、西等国家的象征主义诗潮。它与前期象征主义既有同与继承的一面,更有异与超越的一面。袁可嘉在论及“后期象征主义”时曾指出:其“作品往往涉及重大的社会题材,有更鲜明的主知色彩,更能表现现代意识,技巧上更富有实验性,因此,狭义的现代派文学以它为起点,是更有理由的。”〔28〕总的来说,前期象征主义刚脱胎于浪漫主义,与之有更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注重诗歌的音乐性,把大自然看成向作为“通灵者”的诗人传递信息的“象征的森林”,肯定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相通及色香味各种官能的交感,它继承消极浪漫主义颓废、感伤的诗风。而后期象征主义诗歌中更多感性的具体现实和主知的色彩,对浪漫、浮夸、感伤的诗风有更大的背离,对音乐性也不再过分强调,诗作形式上偏于散文化和口语化的自由体。
以《现代》为代表的文艺刊物,译介了后期象征主义代表诗人的许多诗作。如安移译《夏芝诗抄》〔29〕,戴望舒译果尔蒙《西莱纳集》〔30〕《耶麦诗抄》〔31〕《道生诗抄》〔32〕《保尔·福尔诗抄》〔33〕。
在理论译介上,《无轨列车》创刊号就载有徐霞村译的《哇莱荔的诗》(L.Galantie're著)一文, 文章中说:“哇莱荔的脑筋是被一种一半属于分析机械学,一半属于形而上学的见解占据着,但这种见解却是不能归入任何种学问系统……他的诗,他称它们做‘练习’……”则显然道出了哇莱荔诗歌知性的特点。而在“附记”中译者称“他可以算是世界诗坛的近世的表现。”《新文艺》一卷三、四、五期连载有施蛰存译的《近代法兰西诗人》(美·Ludwig Lenisohn)。 此文揭示了法国近代诗歌从前期象征主义到后期象征主义的转变。肯定了耶麦、保尔·福尔、凡尔哈仑等的诗歌探索。其中谈到:耶麦“抛弃了一切的诗底虚夸的华美和精致,即使象征主义者底更纤巧更安静的娇美也遭摒弃。他底调子是会话似的,几乎是偶然的,他底句子有着散文底结构。他使用着韵脚或半谐音,或忽然的索性不用韵了。他好象只专在竭力安静地讲述他心里的简单而美丽的东西。”这一段评价与戴望舒在译《耶麦诗抄》的附记中所表述的对耶麦诗的理解和赞赏几乎毫无二致。
《现代》(包括《无轨列车》《新文艺》)对后期象征主义的译介与戴望舒等对主要是接受前期象征主义的李金发等人的反思有关。正是因为“从中国那时所有的象征诗人身上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一派诗风的优秀来的”,因而便“力矫此弊,不把对形式的重视放在内容之上”〔34〕,把摄取的目光投向了后期象征主义。在后期象征主义中,诗质委婉清丽,处处以色彩香味表达细微感觉的果尔蒙与“抛弃了一切虚夸的华丽、精致、娇美,而以自己淳朴的心灵来写他的诗的”耶麦或许更符合中国人注重现世的民族审美心理,对戴望舒们尤感亲切,因而成为译介的重点。至于瓦雷里式的冥思,里尔克式的刻画精细、风格凝重的雕塑性,艾略特式“思想知觉化”、“非个性化”的追求,虽已经有了一些零星的介绍,则主要要到三十年代中后期乃至四十年代,才发挥出其影响效应。
英美意象诗派的译介也是《现代》的一个重点。意象诗派反对在诗中直接抒情,反对浮华奢靡感伤柔弱的浪漫诗风,而是提倡“客观化”的抒情,“直接处理事物”。主张诗是由感性意象组成的人类情绪的方程式。意象派领袖庞德特别指出意象是“刹那之间感情和理智的复合”,则把知的因素引入了以情为主的诗歌,这是预示了以后现代主义诗的知性化趋势的。
《现代》杂志在第一卷第二期就推出了施蛰存的“意象抒情诗”五首,这几首诗简洁凝练,意象新颖独特耐人寻味,果真颇得意象诗的深髓。继而,安移(即施蛰存)译“美国三女流诗抄”,在附记中称其中的H·D与英国诗人李却·亚尔丁顿“共同创造了英美意象诗派,为现代英美诗坛的主力”。此外,施蛰存在《美国文学专号》中独力翻译了“现代美国诗”,其中大多是公认的意象派诗人。如,A.Lowell(现译洛威尔)F.Pounol(现译庞德)H.D(希尔达·杜里特尔)J.G.Fletcher(弗莱契)再后,徐迟撰写的《意象派的七个诗人》〔35〕、邵洵美撰写的《现代美国诗坛概况》〔36〕,对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作了非常系统的介绍与论述。戴望舒译的《叶赛宁与俄国意象诗派》主要描述叶赛宁等意象派诗人在俄国革命后的活动。
徐迟在文中详细引述了“意象诗派”的六个信条。特别强调意象的物质性和客观性:“意象是一件东西!是可以拿得出来的!意象是坚硬。鲜明。Concrete(具体的……引者注)本质的而不是Abstract(抽象的……引者注)那样的抽象的。是像。石膏像或铜像。众目共见。是感觉能觉得到。”并定义“意象诗派”是“一个意象的抒写或一串意象的抒写。”徐迟对意象派诗评价极高,他是从时代的物质文明不断发展、丰富的趋向和诗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评价的。他写道:“有些人说,自由诗解放了诗的型式,而意象诗却解放了诗的内容。其实意象派是自由诗所倚赖的,故意象派不独是解放了型式与内容以为功,意象是一种实验。经过了一种运动,诗开始在浩荡的大道上前进了”。
邵洵美在文中准确地指出了意象派诗人“像高蹈派和象征派一样,他们是反对放诞的浪漫主义的”。称意象派诗是“个人的情感与这情感的表现;外形的简洁与内在的透明。”
对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的译介,也是《现代》杂志现代主义取向的一个重要方面。戴望舒化名“月”撰有短文《阿保里奈尔》〔37〕介绍他的立体未来主义,化名陈御月翻译了他的小说《诗人的食巾》〔38〕,化名江思,则写有《马里奈谛访问记》〔39〕,通过马里奈谛之口介绍,“未来主义的艺术,在产生的时候,是醉心于机械的。受人崇拜的机械,是被视为新的艺术感的象征,源泉及支配者的”;高明的论文《未来派的诗》〔40〕,详细地介绍了马里奈谛的未来主义理论。在译诗方面,戴望舒译有艾吕雅诗八首,化名为陈御月选译了《核佛尔第诗抄》〔41〕五首,并在附记中称“用电影的手腕写着诗”,“捉住那些不能捉住的东西”的超现实主义诗人核佛尔第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别人和他比起来,便都只是孩子了”。此外,李金发也曾译有超现实主义诗人邓南遮的诗歌(《邓南遮诗抄》〔42〕)
西方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是欧美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不断城市化、工业化、机械化,而在诗歌艺术当中的一种表现。它们歌颂力量、速度、机械,甚至战争,在美学上强调直觉,否定逻辑和理想,表现玄秘、病态梦境甚至死亡。也许,它们的无庸置疑的现代性和超前性与当时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要求有一定的契合,因而得到了较多的介绍。然而,从根本上说,它们的艺术理想和诗歌实验都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及中华民族务实的文化性格严重背离,这种介绍犹如文化沙漠中的呐喊,除了徐迟、路易士等少数诗人的诗作中有所表现外,基本上渺无回音。当然,这些诗派的题材均取自都市生活,对《现代》杂志上为数不少的带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都市诗”,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中国“现代都市诗”发生影响的另一重要源泉,当是《现代》对桑德堡〔43〕、林德赛〔44〕、黎·马斯特斯〔45〕等美国“芝加哥诗派”的译介。这一诗派适应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热情洋溢地讴歌美国现代大都市,具有一种强劲雄健而有富于抒情气质的现代诗风。
此外,我以为更有意义的是《现代》对以艾略特为代表的,可以称得上“狭义现代主义诗歌”,真正代表了现代诗之最新流向的诗歌进行了介绍。虽然艾略特《荒原》的翻译要迟至1937年,其真正发生影响也并未在《现代》的诗创作中表现出来(我以为如艾略特提倡的“非个人化”、“思想知觉化”等创作原则及《荒原》美学思想在中国诗坛的发生影响,在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创作中表现并不明显,直到30年代中后期才在戴望舒的后期创作、卞之琳、何其芳、废名、路易士及“九叶诗派”那儿有较集中的表现。)然而,这个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中意义深远的“《荒原》冲击波”的最初源头,则不妨追溯到《现代》。
高明的《英美新兴诗派》〔46〕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在艺术的意义上的新的诗派”,即“英美的所谓近代派(Modernists)”。显然,文中所说的“近代派”就是指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英美现代诗派。高明指出:“近代派乃是极端20世纪的。它乃是知识的、物质主义的、从艺术方法论上讲来,乃是形式主义的。”而这种形式主义,“它的态度乃是非常的理智主义的,并且含有冷彻的科学的精神。……它排斥着浪漫主义的以为个人的感情有无限的可能性的思想,和神秘主义深刻主义的倾向。”高明甚至指出近代派对意象主义也显示了反动。而近代派的代表在高明看来正是艾略特的《荒原》一类的作品。他认为《荒原》“是堆积着强烈的虚无的精神,自我意识,知识力,和意识的无意识的象征的可惊的作品。”
邵洵美的《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也盛赞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他称为“世界主义的诗”或“国际主义的诗”)“不被国界所限止”,“不受时间的限制”。与之相比,“桑德堡不过是改换了字汇:意象派诗不过是改换了表现的态度;林德赛(Vachel Cindsay),邦德等不过是改换了题材,只有现代主义的诗才改换了一切。”因此“最伟大的作品当然是爱里特的《荒土》”,它是“过去和将来的桥梁”,是“一个显示,一个为过去所掩盖而为将来所不会发现的显示”。不用说,邵洵美是极富真知灼见的。这仿佛是替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在此之后的发展而预言的。
邵洵美在此文开头,还曾表示过一个困惑,即“英国诗坛和美国诗坛究意应当并在一起考察呢?还是应当完全分开考察?”当然,邵洵美后来还是因为艾略特的“中间性”等原因而将英美诗坛合起来考察了。而在我看来,英美诗坛本来就不必分,因为它们同属英语系统,而且狭义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潮正是以艾略特等的英语系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因而,这种困惑还是一个信号,它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从以法国为中心的象征主义,经由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英美意象派等的中介和过渡,已经逐步转向以英美为中心的,以艾略特等为代表的狭义的、英语系的现代主义。而综观《现代》杂志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的译介,也正暗合或者说顺应了这种重心转移。显然,正是《现代》杂志的鲜明的“现代”性追求,它的在诗歌译介上的现代主义价值取向,使得它能够承前启后、推波助澜、引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动向进而开一代诗风,以至于在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涌中形成了类似于“大本营”的巨大凝聚力和号召力,从而围绕着它形成了一个“‘现代派’诗”〔47〕。
注释:
〔1〕雁冰《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1920年《改造》3卷1号
〔2〕施蛰存在1933年4月28日致戴望舒的信中说,“有一个南京的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诗。”见于孔另镜编《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
〔3〕路易士《三十自述》,见路易士诗集《三十年集》, 诗领土出版社1945年4月版。
〔4〕〔8〕施蛰存《〈现代〉杂议》,《新文学史料》1981年1,2,3期。
〔5〕杜衡《望舒草序》。
〔6〕施蛰存《中国现代主义的曙光——答台湾作家郑明俐, 林耀德问》,原载台湾《联合文学》1990年6卷9期。
〔7〕戴望舒《诗人玛耶阔夫司基的死》,《新文艺》第2卷第2 号。
〔9〕《现代》1卷6期。
〔10〕施蛰存《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答新加坡作家刘慧娟问》,新加坡《联合早报》,1992年8月20日。
〔11〕《现代》2卷1期。
〔12〕《现代》1卷5期。
〔13〕《现代》3卷2期。
〔14〕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15〕《现代》5卷6期。
〔16〕施蛰存后来在谈到他们这一代人时,曾说:“这一批人都可以说是 Modernist。因为这批人和五四运动以后第一代新文学作家不同。五四运动以后,第一代的新文学作家,所受的西方影响还是十九世纪的。到了三十年代,我们这一批青年已丢掉十九世纪的文学了。我们受的影响,诗是后期象征派,小说是心理描写,这一类都是Modernist, 不同于十九世纪文学。”出处同注〔10〕。
〔17〕〔18〕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
〔19〕《现代》2卷2期。
〔20〕《现代》1卷3期。
〔21〕《美国文学专号》,《现代》5卷6期。
〔22〕〔23〕《现代》3卷1期。
〔24〕《现代》5卷6期。
〔25〕分别见于《现代》3卷2期和5卷2期。
〔26〕见于1931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见31年1月20 日《诗刊》创刊号。
〔27〕卞之琳《〈戴望舒译诗集〉序》。
〔28〕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第125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29〕《现代》1卷1期。
〔30〕《现代》1卷5期。
〔31〕《新文艺》创刊号1卷1期。
〔32〕《新文艺》1卷3号。
〔33〕《新文艺》1卷5号。
〔34〕杜衡《〈望舒草〉序》,《现代》3卷4期。
〔35〕《现代》4卷6期。
〔36〕《现代》5卷6期。
〔37〕〔38〕《现代》1卷1期。
〔39〕《现代》1卷3期。
〔40〕《现代》5卷3期。
〔41〕《现代》1卷2期。
〔42〕《现代》6卷1期。
〔43〕《现代》3卷1期。
〔44〕《现代》4卷2期。
〔45〕《现代》5卷6期。
〔46〕《现代》2卷4期。
〔47〕孙作云早在1935年就“因为这一类的诗多发表于现代杂志上”,且“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而用“现代派诗”名之(参见《清华周刊》43卷1期《论“现代派”诗》一文)。
标签:戴望舒论文; 施蛰存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现代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荒原论文; 现代诗论文; 文艺论文; 象征主义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