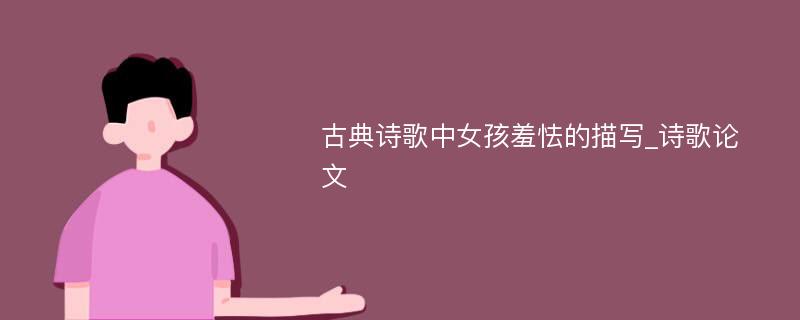
古典诗歌中的少女羞怯心理描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羞怯论文,诗歌论文,古典论文,少女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羞怯是爱情生活中“极力掩盖男女两性接触和亲昵温存”的一种心理现象。反映两性关系的羞怯与反映道德关系的羞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的羞耻感同人意识到自己的过失有关,而性的羞怯则是害怕伤害两性关系的精神美”(瓦西列夫《情爱论》)。羞怯作为人类高于动物的一种特殊心理,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即使在推崇裸体美的古希腊罗马时代,一些伟大的女性裸体雕塑,也隐约地表现出某种羞怯感、拘谨感。一些艺术史家认为,米洛的阿罗狄忒雕像那只短缺的左手原本就是用来托着从腿上滑落的衣服的。
分析我国古典诗歌中反映出来的少女羞怯心理的表现形态,探索古代少女羞怯心理的描写艺术,对认识我国古代的女性美和情爱美,提高爱情的精神境界,发展现代情诗的创作,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古典诗歌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在各种情境中少女的羞怯美,并且无一例外准确地指向了羞怯的本质——爱。
这里没有纯粹的“羞”,“羞”,总是伴随着复杂的心理因素出现,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白居易《采莲曲》:“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一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小船穿行之处,波涌风生,片片菱叶打旋,朵朵荷花摇颤;就在这清香四溢的荷塘深处,忽然两只小船迎头碰接。“通”,使人想起“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通”,真是未见其人已先有意了。此时少女该是何等惊喜,心里该有多少话想说;尽管羞得“欲语未语”,但一个“笑”字,却胜过了千言万语!这岂止是外在的欣喜,实是内心深情爱意的最好传递。“笑”而“低头”,使“笑”带上一种隐秘动人、脉脉含情的性质。一低头,碧玉搔头便落入水中了。这羞喜难掩、情思荡漾的神情心态,描绘得栩栩如生。
如果上面主要写的羞中含喜,那么欧阳修《渔家傲》则着重写羞中带慌:“一夜越溪秋水满,荷花开过溪南岸。贪采嫩香星眼慢,疏回眄,郎船不觉来身畔。罢采金莲收玉腕,回身急打船头转。荷叶又浓波又浅,无方便,教人只得抬娇面。”有位眼亮如星的少女正在“贪采嫩香”,她采呀摘呀,以致连心上人悄悄来到身旁也不知晓,太突然了,太激动了,你看她这一刹那间有多么慌乱:赶紧抽回快摘到荷花的“玉手”,急急地掉转船头,真像一副要溜走的样子。但“荷叶又浓波又浅”,船像是搁浅了;“只得抬娇面”,似乎她是迫不得已,无可奈何,实则她何尝不想抬头瞅他一眼呢?幸得有船划不动的机会,却偏怨不给人“方便”的“老天”。再说,“叶浓波浅”也可疑,前面不是说“秋水满”吗?亏得少女想出这一大篇真真假假的道理来掩饰,而我们是决不会批评少女的“抬娇面”。我们倒是从这些托词中看到了少女那一腔纯真炽热的情怀,从她一见情人就羞涩难当、手忙脚乱的举动中,听到了她那颗爱心在激烈跳动。
有的不仅慌乱,甚至紧张。明代沈仕《锁南枝·咏所见》:“雕栏畔,曲径边,相逢他猛然丢一眼。教我口儿不能言,腿儿朴地软。他回身去,一道烟。谢得腊梅枝,把他来抓个转。”他们骤然相逢在栏畔曲径。碰到他的目光,少女浑身流电,竟然紧张到说不出话,走不动路;那年轻人也慌得回身就溜,幸得他走得匆忙,被梅枝挂住了,这才转个脸来,使少女得以多看他一眼。这里的“谢”字、“抓”字用得妙,原来这姑娘尽管紧张,却不糊涂,她对“谢”什么,要“抓”什么,心里清清楚楚的。
有的不仅紧张,还担心受吓。晚清庄棫《蝶恋花》:“百丈游丝牵别院。行到门前,忽见韦郎面。欲待回身钗乍颤,近前却喜无人见。
握手匆匆难久恋。还怕人知,但弄团团扇。强得分开心暗战,归时莫把朱颜变。”少女思念情郎,她那长如“游丝”的相思被“别院”的情郎所牵引,不知不觉“行到门前”,突然碰见了情郎。她此刻可说是既惊又喜,既羞又怕。“钗乍颤”是说头上金钗陡然摇颤不止,这正是她内心受到强烈震动的反映。但爱情最终给了她力量,便向前靠去。但仍是提心吊胆的,“虽喜无人见”,但“还怕人知”;她不敢与情人有太多的亲热,只是默默抚弄手的团扇,与情人匆匆握手告别。即使如此,还是“心暗战”。结句更是把这种羞怯、惊惧推进了一层。
还有因羞怯、激动、喜悦,竟至痴迷了的。杨维桢《珊瑚鞭》:“侬出青桑下,郎来渌水边。相看成自语,马脱珊瑚鞭。”这可能是早先定下的约会,也可能是不期而遇。他们四目对视,两情脉脉,彼此有多少话要说,但一句也未出口,只是嗫嗫嚅嚅的,好似在絮絮自语;他们已进入痴呆醉迷的境界,连“马脱珊瑚鞭”也未发觉。
还有羞中不失矜持的,这更是羞得可爱。宋代陈郁《东园书所见》:“娉婷游女步东园,曲径相逢一少年。不肯比肩花下过,含羞却立海棠边。”一游园少女,于曲径遇某少年,怎么办?她不肯迎面而行,与那男子“比肩花下过”,也不是掉头回走,退避三舍。单看她否定了上面两种选择,就隐约知道少女未免动了情、起了心。“比肩”也者,只不过是她的主观想象,并且颇有点想入非非之嫌。因为客观情况并不是这样,再狭窄的曲径,两人对面从容通过该是没问题的。再说用词也很有意思,“比肩”,大概少女已顺着“比翼(鸟)”、“比目(鱼)”这些方面去想了,岂不是想得深了一点?恋爱中的少女常是这样,越是自己喜爱的人,越是不敢接近他,而心里却想时刻同他在一起。了解这,也就不难理解结句的全部丰富内蕴。她“含羞却立”,是因她有少女的娇矜,是她有情于他,不忍遽去而要观察、估摸他。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不管少女羞怯中伴随或夹带何种心理——喜悦、慌乱、紧张、惧怕、痴迷、矜持,不管羞怯以何种形态表现出来,都是源于爱的萌动,因爱而引起,都是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爱的泄露,爱的表示。无爱便无羞,从这种意义上看,可以说“羞”是“爱”的别名,“爱”是“羞”的本质。“羞怯”的美也就在这里。羞怯之所以美,不仅因为它是人类情爱的一种反射,还表现在它能给情爱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能唤醒两性关系中的精神因素,减弱纯粹的生理作用,能促进男女双方在交往中真正建立起和谐、健康、高尚的爱情。马克思在《致拉法格》中说:“在我看来,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谦恭甚至羞涩的态度,而绝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他主张“必须保持一段距离来谈爱情”。那种肆无忌惮、纵情恣欲的行为,必将使最美好纯真的爱情受到玷污和伤害。可见羞怯是男女情爱的一种净化和升华。
2
古典诗歌在表现少女羞怯这一微妙心理时,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艺术手段:一是构置典型环境。羞怯总是在男女交往、恋爱的某些特定的环境、气氛中发生的;环境越典型,羞怯就表现得越自然真实,优美可爱。因而古代诗人很重视典型环境的营构布置,常选择邂逅相遇的场合、月暗雾笼的幽会、隐秘幽静的荷塘深处、红烛高烧的新婚之夜、笙歌飞场的筵宴舞场等,来描写少女的羞怯。徐再思《沉醉东风·春情》:“一自多才间阔,几时盼得成合?今日个猛见他,门前过,待唤着怕人瞧科。我这里高唱当时水调歌,要识得声音是我。”正是少女与恋人久别后的相思烦闷,为下面的意外见面作了铺垫,而这不期而遇又有力地烘托出少女的羞涩、矜持。一个“猛”字,活画出姑娘霎时间一愣、一惊、一喜的激动神态。但那男子从门前过,却并未发现她。此时此刻,她很着急:欲追,已来不及,更羞涩难当;待唤,又怕人瞧见。内心如焚之际,慧巧的姑娘高唱起昔日两人幽会时传情表爱的水调歌,她相信情人能听得真真切切、甜甜蜜蜜,定会回身来找她的。“要识得声音是我”,此句天籁自然,妙不可言。“要”,有“非得这样不可”的意思;“是”,肯定有力,不容置疑;“我”,置于句末,特别加以强调。其娇矜、自信之状,宛然在目。清代完颜守典《新婚词》:“乍时相见已相亲,斜面窥郎起坐频。烛影摇红人静后,含羞犹自不回身。”夜静人散,只有新人相对。“窥郎”的时机终于到了,但又不好意思正眼直觑,只能“斜面”一瞥。“起坐频”,更是传神,既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偷看,也是借此达到多看几眼的目的。后两句写夫妻即将同床共枕这一“关键”时刻新娘的表现。“犹自不回身”,低头而坐,她的忸怩作态,正是为了等待新郎主动上前,这样方可顺水推舟,鱼水和谐。烛影摇红的新婚之夕,心醉神迷的洞房氛围,更增添了新娘的羞怯美。李珣《南乡子》:“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雨过天晴的傍晚时分,刺桐花下,越王台前,一位少女瞥见了一年轻男子,禁不住怦然心跳,暗中回头,频传秋波,深情致意。当她确信小伙子也有心时,便佯装不慎,撂下信物金钗,然后避开旁人,悠悠然、喜滋滋地骑象涉水而去,她将在对岸的树林深处等他。明丽清新的自然美景,独特浓郁的南国风物,邂逅相遇的动人一幕,更衬出这位天真慧敏少女的娇羞迷人。
二是突现矛盾冲突。羞怯常表现为既想与对方接触又不敢主动行动。古代诗人总是充分揭露这些矛盾冲突,让它们在尖锐的对立中互相映衬、互相加强,生动真实地展现少女的羞怯心理。李白《越女词》:“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这位采莲女,见到意中人,心想迎上去,却偏“棹歌回”。“羞”是外表,是装的;“笑”是内心,是真情。她身虽“入”,其心实在外;或者说,她“笑入荷花”以回避,实为了在荷花丛中来相聚。正是借助这些矛盾而又统一的神情动作,曲折传出羞涩情态背后难以言传的内心隐情。皇甫松《采桑子》:“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在这里,一方面是“贪”和“抛”的炽热情怀和大胆行动,一方面又是“无端”和“半日羞”的对自己冒昧举动的自责自悔。李煜《菩萨蛮》中的少女既发出“花明月黯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的醉心呼喊,表现出无限欢欣鼓舞的情绪,却又有“刬袜步香阶”的紧张惊悸,更有“一向偎人颤”的不胜羞怯;而在心情稍稍稳定下来后的“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又是火辣辣的表白,满怀情爱的尽情倾泻。爱和羞、勇敢和畏怯、坚定执著和紧张慌乱,就是如此尖锐对立而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可见少女的羞怯,决不是单纯的回避怕惧,也不是故意的矫揉造作,而是爱情流露时的自然掩饰,又是爱情掩饰时的真实流露。能够这样辩证地来写羞怯,才算对涉足爱河的少女心理体验得深细入微,才能把少女的羞怯写得入木三分、出神入化、真实可亲。
三是精心选择细节。首先是动作细节,羞怯总是在人物的顾盼之间、举手投足的动作行为中显露出来的。古代诗人很注意根据不同情境挑选最恰当的动作细节来表现羞怯。欧阳炯《贺新朝》上阕云:“忆昔花间初识面,红袖半遮,妆脸轻转。石榴裙带,故将纤纤玉指偷捻,双凤金线。”花丛中的少女,用红袖半遮面,这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愧有所不同,这是娇羞。“妆脸”不蓦然掉过去而“轻转”者,还想看看心中人也。后三句写少女用纤细的白玉般的手指暗自揉搓着石榴裙带双凤下垂的金线,这本是情急意切时一种下意识动作,但此处上加“故”字,难道不又是少女有意偷捻金线以吸引别人的目光来遮掩自己的内心感情吗?“遮”、“转”、“捻”三个动作,像一个个连续的特写镜头,再配合极有分寸的“半”、“轻”、“偷”等字的运用,使少女的娇羞情态毕现。李清照《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见有人来”,既顾不上穿鞋,也来不及整冠,“蹴罢秋千”后的慵懒更衬出“和羞走”的窘迫。“倚门回首”把稚龄少女见人来后欲躲不躲、既害羞又想观察来人的矛盾行为和心理描摹得维妙维肖。“却把青梅嗅”,是借嗅青梅的动作以掩饰忙乱害羞的行为,缓解紧张躁动的心理。这是位既天真幼稚又春情萌动的少女。欧阳修《南乡子》:“好个人人,深点唇儿淡抹腮。花下相逢,忙走怕人猜。遗下弓弓小绣鞋。刬袜重来。半亸乌云金凤钗。行笑行行连抱得,相挨。一向娇痴不下怀。”花下相逢,事出突然,仓猝间怕人猜疑,连忙走开。但真的就舍得这样一走了之么?“遗下弓弓小绣鞋”这是个极有情味的细节,是姑娘特意设计的一个小动作。果然,她“刬袜重来”了,她这次转回却有了借口:我是来找鞋子的呀!这样,也就边走边笑,半推半就地投向了情人的怀抱。少女的羞怯心理当然更要通过心理本身的一些细节来表现,这样才能使羞怯心理具体可触,生动深刻。杨守知《西湖竹枝词》:“自翻黄历拣良辰,几日前头约比邻。郎自乞晴侬乞雨,要他微雨散闲人。”诗中少女慎重挑好了日子,相约近在比邻的情人去游西湖。然后就一个劲地盼起天气来,男盼晴,理所当然,女望雨,实在可怪。然而少女盼的并不是瓢泼大雨,只是微微细雨,而这“微雨”少女是要它起“微妙”作用的:“要他微雨散闲人。”少女想:微雨中,我们可以靠得更紧一些,而这当然是躲避风雨的需要;微雨中,我可以把细长如雨丝的绵绵情话,尽情向情人倾吐;微雨中,闲人都走了,没有人窥视,没有人偷听,只有我们两人“躺”在这用雨丝织成的旖旎温柔的纱帐里……幽会还没开始,她就想得这样入迷。这是通过幽会前的某一特殊想法,来显示她的羞涩心理和对爱情的热烈追求的。
四是巧用对比衬托。即是把男子的大胆主动与女子的羞怯腼腆加以对比,并用前者来衬托后者。沈约《六忆诗》:“忆眠时,人眠强未眠。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复恐旁人见,娇羞在烛前。”诗写男女初次欢会的情景。夜深人眠时,女子仍未眠,一个“强”字,见女子似真有股硬撑着的劲儿。“解罗”毕竟不是“就枕”,所以她“不待劝”,但真的到“就枕”时,却要情人牵拉了。在牵拉中,她或许慢吞吞地移动了几步,可最终又怯于被旁人看见而依倚在烛前。这种羞答答的情态,更因男子的“牵”和“不待劝”的欲擒故纵的写法而得到强化。张泌《浣溪沙》:“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此词描写了曾被鲁迅先生戏称为“钉梢”的一出爱情喜剧:傍晚,一辆香车返城,被一个多情年轻人尾随;忽然一阵风来,掀开了车上的绣帘,他看到了车中女子那双笑盈盈的娇眼,更是装着酒醉,紧随于后。不过“佯醉”却逃不过那女子的“慧眼”,她终于从车中抛出一句娇滴滴、羞答答的话:这小子也太轻狂了!但联系“慢回娇眼笑盈盈”一句来体味,这女子对他也不是无情的。此词也正是在男子追逐女性的一系列镜头中,把那女子又羞又恼、又喜又爱的心理和口吻,写得活灵活现的。
注释:
1.瓦西列夫著,赵永穆等译:《情爱论》,三联书店,1984年10月第1版。
2.陈宏硕著:《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女性情爱世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3.吕美生主编:《中国古代爱情诗歌鉴赏辞典》,黄山书社,1990年第1版。
4.李文禄主编:《古代爱情诗词鉴赏辞典》,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
标签: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