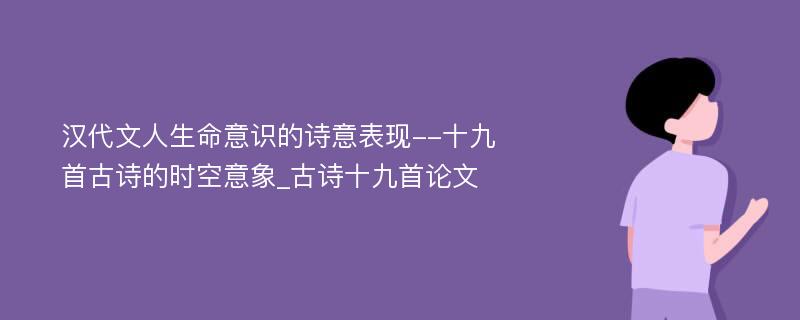
汉代文人生命意识的诗学表征——《古诗十九首》的时空意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表征论文,意象论文,汉代论文,古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13(2002)03-0076-04
如果说《诗经》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活水,那么,曾被刘勰誉为“五言之冠冕”[1](P42)的《古诗十九首》,无疑是这诗歌长河中一条充满生命活力的重要支流。自昭明《文选》面世以来,《古诗十九首》就被历代文人骚客反复吟咏、品评,千百年来引起读者广泛而强烈的共鸣。个中原委,让人深思。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它那蕴含其中的深邃的时、空意象。本文拟就此作一考察。
一、时间及其时间意象
中国古代对时间概念的理解,绝不是抽象的现代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而是具象化的。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时)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成岁焉。”[2](P518)日月运行而有时,寒暑易节而成岁,人们对日、月、年的认识均源于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观察和感悟,时间在客观物体的空间运动中得以显现。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到明代,王夫之说:“天地古今以此而成,天下舋舋以此而往,其际不可紊,其备不可遗。”[3](P127-128)这里的“此”指的也是日月寒暑的交替运行,而且他还强调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维性连续特征:
有已往者矣,流之源也,而谓之曰过去,不知其未尝去也。有将来者焉,流之归也,而谓之曰未来,不知其必要也。其当前而谓之现在者,为之名曰刹那(如断一线之顷),不知通已往、将来之在念中者,皆其现在,而非刹那也。
——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五
这里王夫之对时间的思考看似有了哲学的抽象味道,其实他仍把时间比做“流之源”、“流之归”,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4](P90)之叹一脉相承。不过,我们还应该承认,王夫之的时间观也是对中国古人时间意识的一次归结性的把握。因为:一方面他道出了时间的不可逆的一维性特征,另一方面他还无意中强调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际之间的间断性联系。而时间的一维性连续和三际之间的间断性正是导致中国诗学里横亘千古的生命意识的根源之一。中国的古人就善于借助于客观世界中的具体物象来关注时间,于是,日月流转周而复始的时间连续让人自然产生时不我待的悲悯,寒暑交替断续有别的季节变换让人顿觉生老病死的恐慌,这种文化心态,突出地在《古诗十九首》里得到了艺术化的凝结:汉代文人们用这种观物察时的方式去看待世界、体悟人生,于是,就有了那溢于字里行间的时间感伤。
《古诗十九首》表现时间及其构筑意象的形式大致有三种:
第一,对自然时光(年、岁、日、月、晨、夜、星、暮)的敏锐体察。人类早期的时间观念大概起源于昼夜的划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劳作和休息成为人们日常感觉中最明显的具有周期性变化特征的生活节奏;随后又据月亮的阴晴圆缺划分了“月”的时间范围,与此同时,寒来暑往播种收获的节奏也演化出了“年”的概念。时间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但是,“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5](P18),自然时间的流逝又让人感悟到生命的短暂;人在这无情而又无限的岁月流失中生而死、死而生,与时消没;于是人们便痴迷地去追寻生的永恒,后羿求药于西王母,嬴政求仙于蓬莱山,汉武寄望于仙道灵异……但肉体的生命永远也不可能与自然的时间相抗衡,“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5](P173)汉代的文人们对此特别敏感,这是《古诗十九首》中充溢于对年、岁、日、月、晨、夜、星、暮感伤的心理原因。《古诗十九首》中有10首诗20处明确标示出了这类意象。它们是:“今日良宴会”(《今日良夜会》),“明月皎夜光”、“众星何历历”(《明月皎夜光》),“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东城高且长》),“万岁更相送”(《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浮云蔽白日”、“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终日不成章”(《迢迢牵牛星》),“凛凉岁云暮,蝼蛄夕鸣悲”(《凛凛岁云暮》),“愁多知夜长,仰视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詹兔缺”(《孟冬寒气至》)。这里,抒情主体在“今日良宴会”的欢乐场景里感受到的是“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的时不我待的凄凉;从众星历历的夜空又品味出事业无成的虚无;皎皎的明月勾起燎人的相思;云与月的叠映里是“岁月忽已晚”的忧虑;凛凛的岁暮、悠悠的长夜、闪烁的星辰、明月的圆缺……一切的一切都从对时光的感悟出发,构筑起诗歌中那横亘千古的境界。今天读这样的诗句,仍能产生“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审美效果。
第二,用明确标示季节变化的物象表示时间、构筑诗境。“《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对季节的变化特别敏感,这些作品中明确标示出季节的有6篇,其他以物候暗示节序的诗篇亦为数不少。上述两项加在一起,占据19首诗的绝大部分”[6](P275)。诗人们用全方位的眼光观照时间,于是,“促织”、“白露”、“秋蝉”(《明月皎夜光》)、“蟋蟀”(《东城高且长》)、“蝼蛄”、“凉风”、“寒”(《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北风”(《孟冬寒气至》)等等明示了秋冬的到来;“东风摇白草”(《回车驾言迈》),“秋草萋已绿”(《东城高且长》),“绿叶发华兹”,“攀条折其荣”、“馨香盈怀袖”(《庭中有奇树》,等等则是春的景象。季节变换是自然运行的结果,但当生命之舟载满了忧愁,当心中的理想被无情的现实湮没,当往日的美丽不再拥有的时候,睹燕去莺来,看落花流水,那周流不已永无尽头的自然物象的荣衰盛枯便与生命的短暂构成了时间意象的关联,“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种关联之中蕴藏着一种心灵与物象的默契,一方面,物象是触发诗人心中情感的媒体;另一方面,诗人又借这个媒体来卸载心灵的情感,情由心溢出,景也因情而异趣。所以,淫雨霏霏,凄风萧瑟的秋景可以表达诗人们的心中苦涩(《凛凛岁云暮》、《明月皎夜光》),春风荡漾、明媚宜人的春光亦可传达主人公的内心凄楚(《回车驾言迈》、《青青河畔草》、《庭中有青树》);景因时而异,地因人而悲而喜。造成这种审美效应的主要原因就是人对时间的物化关注以及由这个关注而引发的情感波动。
第三,将时间寓于自然界无生命的物象之中。自然界中一些无生命的物象本来是没有具体的时间内涵的。但是,一旦诗人们用人生短暂的标尺去衡量它们,它们便与人生构成了一组新的时间组合。这种组合在《古诗十九首》中大致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生命与物的异质同构。如“露”的意象。“露”是无生命的自然物,但它又具有随太阳升起而迅速消失的变化特征,从有到无,瞬息之间,这恰如生命之短暂,“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明月皎夜光》)那“白露”与“时节”便同样具备了时间的内涵。“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驱车上东门》)这里干脆把生命与朝露看做了形与质的统一。二是生命与物的异质异构,如“石”的意象。自然界的“石”是无生老病死之感的,但“石”又以其坚固的物性特征恒存于世,即便有物理意义上的风化,其过程之缓慢也是“生年不满百”的人无法体察得到的。于是人寿之短与石“寿”之长便又相反相成了。“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这是仕途受挫后对生命意义的再思考;“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这里诗人们如出一辙地将人生与“金石”、“盘石”作对比,并将自然的永恒与生命的短暂两相融会,人类在大自然而前所感受到的巨大的生命压力又在这人与物的异质异构中得以显现。
另外,《古诗十九首》中的时间有时还借对个人生活流程的叙述而被暗示出来。尽管这组五言古诗是以它的抒情性影响后世的,但夹裹于抒情成分中的叙述内容也显而易见。诗人们往往借这些或隐或显的叙述成分,在再现生活场景的同时,又将人的生命时间流程蕴含其中。《去者日以疏》表现的是游子思归而不得归之时,由生死现象而抒发的情感流露,但整首诗又处处充满时光的印迹。“茫茫宇宙”‘去’‘来’二字括之。去者自去,来者自来;今之来者,得与未去者相亲;后之来者,又与今之来者相亲;昔之去者,已与未去者相疏;今之去者,又与将去者相疏;日复一日,真如逝波。”[7](P95)这正是对诗中的叙述成分与生命流程融合一体的内存时间的地道把握,可谓真知灼见。
二、空间及其空间意象
人类对空间的认识与对时间的认识一样,也源于生产生存活动。中国古代对空间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创世神话。那时,原始先民对空间的认识是一个混沌状态,“天地混浊如鸡子,盘古生其中……。”而且这个混沌的宇宙空间还充满着变量,那就是随着时间演进而发生的空间变化:“阳清为天,阴浊为地”,以及“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的变化结果。在先民的观念中“天”和“地”就是“宇宙”,《管子·心术上》:“道在天地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如本来是对“道”的解释,说“道”是一种物质的精气,它充满于天地之间,无处不在;同时他又在无意之间显示出古人对空间的进一步认识:空间不管向外、向内延伸都是没有边际的,用现代的科学术语说就是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都没有边际。这也正是空间的无限性。屈原《九章》“穆眇眇之无垠兮”,《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都是就此而言。可是古代又有天圆地方的空间认识,人们以对天地的视觉意象为根据,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周髀算经》更是自信而确凿地记录了“天离地八万里”,“天之中央高四旁六万里”,大地则是一个边长“八十一万里”的正方形。因此,宋玉《大言赋》说:“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这些又在无意中道出了三维空间可以分割的特征。古人正是基于以上的空间认识,一方面从空间的无限里产生了自身“渺沧海之一粟”的飘渺感,另一方面又从那空间的区域分割中体悟出了从此地到彼地、从故乡到异乡的身心位移所造成的空间无奈。
汉代的文人更是特殊。就东汉而言,汉时奉行养士制度,众多的士子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官僚后备军,士子与官位之间的数量比例悬殊,僧多粥少;再加上官府中贿赂与裙带关系的影响,士人们的出路更为渺茫。《古诗十九首》中的游子们正是这些士子中的一部分。他们原本抱定经世致用的信念拼命苦读,又远离家园,历尽辛酸;但严酷的现实却使他们再三碰壁,处处受阻。理想的破灭与远游的孤寂让游子们从无奈中反观自身、反思现世人生,这是《古诗十九首》空间意象得以建构的社会和心理基础。
《古诗十九首》往往用多种多样的空间表现形式来创造诗歌的空间意象。其中在景物的变换和人物的行动里移步换景是其主要的空间表现手段。而且这类诗往往表现出用单纯的空间组合构筑诗境的特征。《古诗十九首》中这样的诗共有6首:《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明月何皎皎》、《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和《迢迢牵牛星》。尽管这几首诗都以空间描写为主,但又各自不同。《青青陵上柏》的一、二句用“陵上柏”与“涧中石”一高一低的空间对比来引发诗人对广袤宇宙的思虑。三、四句承上启下,“人生天地间”的渺小感和“忽如远行客”的流浪感隐寓其中。“斗酒”以下四句是失意之人相聚之时借酒浇愁之后虚拟的狂放之态——这是个虚实相生的空间组合;“洛中”以下八句是对洛阳达官贵族之辈宅第繁华的描述。这一“穷”一“富”两个对立场景在诗中形成对立。全诗从“天地”之大过渡到“第宅”、“两宫”之小,自天空而大地,在空间的转换与映衬中凸现了游弋于豪华第宅环境里的穷困士子的形象,在这更小的空间里他们怎能不顿生“戚戚”之慨呢!与此不同,《西北有高楼》则是“曲终人不见”与“闻歌驻足听”两个场景的空间排列。歌者所处的“高楼”与闻歌者的所处是两个相互分离而又一远一近的空间组合,歌声是连接它们的机杼,陆时雍说:“空中送情,知向谁是?言之令人悱恻。”《明月何皎皎》一诗则又是移步换景式的空间组合,首先诗中的“明月”意象笼罩全篇,而后则靠抒情主体由不寐到换衣、由出户到入户的室内外场景的简单位移而传情达意,方东树《昭昧詹言》:“一出一入,情景如画。”《青青河畔草》的前六句是定点透视的空间排序,以抒情主人公当窗所见为透视点,将河畔草、园中柳、楼上女以及“纤纤出素手”的特写由远而近地组合起来;后四句则是由空间近而远、远而近的快速变换镜头组成的场景叠映。《庭中有奇树》和《迢迢牵牛星》也是在叙事与描述之中将空间组合在一起,前者是由树而花,由花而人,由人而情;后者则是由河汉而人间,由人间而室内,由室内而离妇,由离妇而离情,主人公的视线所及的场景串缀其间,“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内心感伤形诸每一个空间方位。而且这两首诗还都反映出空间由大而小,由具体到抽象的特征。构景传情如此,可谓高妙。
凭时间的穿插连缀将空间意象组合起来传情达意,是《古诗十九首》表现空间的又一种形式。从哲学上讲,时间和空间是两位一体的抽象,恩格斯说:“离开时间的空间和离开空间的时间同样都是不可能存在的。”[8](P91)在古今汉语中许多表示空间概念的词语被借去表示时间,如尔后、瞬间、早上、下半晌、上个月、五天前等等,可见时间是有着隐喻空间的特征的。[9](P495-506)《古诗十九首》中的空间表现除上面已谈到的6首外,其余13首都是凭借时间的或隐或显的穿插连缀来组合空间场景的,空间意象是一颗颗的情感之珠,时间就是隐患其中的红线。《涉江采芙蓉》抒写的是游子思妇的情怀。诗歌首先突出了游子身处异乡的客居空间:他乡之“江”与他乡之“芳草”;而“所思在远道”一句又使空间场景发生位移:由他乡而故乡、由此地而彼地。“还顾”一句又特别突出了归乡之途“漫浩浩”的想象空间。全诗在漂泊异乡、思乡而又不得归乡的长久煎熬里将一系列空间场景连缀在一起,每一个场景都是一份痴情。《驱车上东门》又是一首由空间而时间,最后仍由空间来收束全篇的意象组合。诗的前八句就空间而言,写“上东门”外墓地的萧瑟阴森,松柏夹道,白杨萧萧,道尽生者对死者的哀叹;以下六句自然由生死之忧去解读人生的无常:黄泉悠悠,命如朝露;时间上由生而死,空间上由人间而九泉。诗的最后两句以“饮酒”和“被纨”的空间意象来表达由生死之叹而引发的生命无奈和自慰之情。《行行重行行》、《去者日以疏》与《驱车上东门》异曲同工。诗人们就是这样在空间的位移中体味流离的悲苦,在流离的岁月里品味心灵的伤悲。他们在空间的阻隔里抒写新婚之别怨,“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冉冉孤生行》)。有形的距离难以超越,而思想则可以通过梦中的场景得以传达,“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凛凛岁云暮》);也可以将思念遥寄于天边的明月,“三五明月满,四五詹兔缺”(《孟冬寒气至》),甚至也可以在不同的期许与空间转换之中,将情感伸展到无限的时空里,“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西北有高档》),“思为双飞燕.街泥巢君屋”(《东城高且长》)。
《古诗十九首》在时间的回环往复和空间的移位叠映中建构的这种抒情模式,一方面是汉代文人高妙的写景言情手段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它也因此而成为了影响中国古典诗歌言情构景艺术达两千多年之久的一种基本技法;它所创造的许多时间以及空间意象也已成为中国古典诗歌里重要的抒情母题。《古诗十九首》正因这种时、空关系而赢得了千古不朽的声誉。
收稿日期:2002-0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