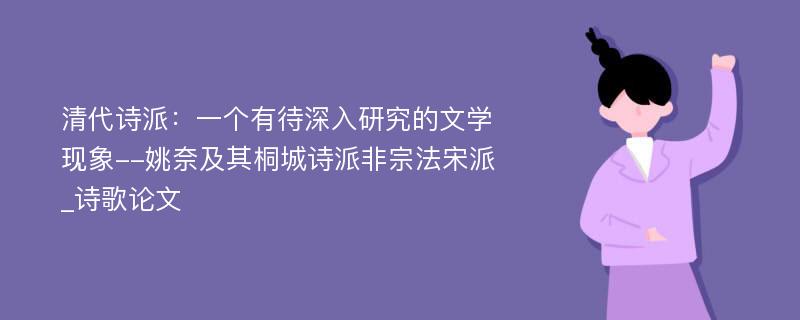
清诗流派: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文学现象(专题讨论)——姚鼐及其桐城诗派非宗宋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桐城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流派论文,现象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方苞、刘大櫆、姚鼐引领的桐城派是清代最有影响的散文流派,其实,桐城派作家中的一部分人也从事诗歌创作,并且形成了一个诗歌流派。这一点,最早由桐城作家姚莹指出,他说:“国朝持论之善足洽天下大公者,前有新城尚书(王士禛),后有吾家惜翁(姚鼐),庶几其允乎。归愚沈氏所得本浅,论诗仅存面貌,而神味茫如,其当乎人心之大公者盖寡矣。”“海峰(刘大櫆)出而大振,惜抱起而继之,然后诗道大昌,盖汉、魏、六朝三唐、两宋以及元、明诸大家之美无不一备矣。海内诸贤谓古文之道在桐城,岂知诗亦有然哉。”[1](卷1,《桐旧集序》)当代学者钱钟书对此持赞成态度,但看法略有不同,他指出:“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範发之。”[2](P370)钱钟书所说的姚範是姚鼐的伯父,字南菁,号姜坞,清乾隆七年(1742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援鹑堂笔记》。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四记载:“惜抱之世父姜坞编修範,博闻强识,诵法先儒,与海峰友善。诸子中尤爱惜抱,每谈文必令侍侧。”[3]这种说法在多部清人笔记里均有。可见,姚鼐古文创作跟随刘大櫆,原也是受了姚範的启发。
姚範论诗的观点多收在《援鹑堂笔记》里,基本看法是:肯定本朝王士禛,折中评价明七子,甚推宋代黄庭坚①。姚範曾称:“涪翁以惊创为奇,其神兀傲,其气崛奇,元思瑰句,排斥冥筌,自得意表。”[4](卷40)转看姚鼐,观点与其伯父如出一辙,正应了姚莹“前有新城尚书,后有吾家惜翁”的说法。而刘大櫆虽然也从事诗歌创作,但并未有诗学主张流传下来,因此“渊源家学”的提法的确是可信的。
长期以来,学术界多将姚鼐及其桐城诗派认定为清朝的宋诗派,钱钟书亦这样看。他在《谈艺录》中指出:“惜抱以后,桐城古文家能为诗者,莫不欲口喝西江。”[2](P371)实际上,这种看法与事实不尽相符,只要具体分析该派作家便可明了。
一、姚鼐唐宋兼容的诗歌特色
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一字梦榖,室名惜抱轩,旧时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历官刑部郎中、四库馆纂修官,不久自动退职。归后主讲江南紫阳、钟山书院四十余年。有《惜抱轩全集》。
姚鼐今存诗784首,其中古体诗218首,约占30%,近体诗566首,约占70%。不妨先看古体诗。姚氏的五古略多于七古,占六成。这部分作品以学汉魏六朝和唐代为主,即王昶所谓“诗旨清隽”者[5](卷28),姚莹《识小录》所谓“高处直是盛唐诸公三昧”[6](P133),它们与宋诗的关系较远,显然不能视作学宋的证据。这个情况是有原因的。姚鼐五言古诗遵循的乃是王士禛《古诗选》的路子。王士禛五古选诗起于汉而止于唐,未收宋诗。对此,姚鼐是认同的,他在《与管异之》一文中说过:“吾向教后学学诗,只用王阮亭五七言《古诗钞》。”[7](卷4)显然,姚、王二人之间是有承接关系的。总的来讲,姚鼐五言古诗承袭因素较多,创变之处较少,风格并不鲜明。《惜抱轩集》中受到关注的倒是七言古体,论者大多认为它们才代表了姚鼐古体诗的水平和风格。
客观地讲,姚鼐集子里的七言古体呈现为多元状态。其中,有一些接近李白,如《望庐山》;还有一些作品接近韩愈,如《桃核砚歌为庶子叶书山先生赋》。然而,更多的则是效法苏轼,如《唐伯虎匡庐瀑布图》、《紫藤花下醉歌用竹垞原韵》、《安肃道中》、《登黄鹤楼次补山韵》、《王少林嵩高读书图》、《为翁正三学士题东坡天际乌云帖》、《新城道中书所见》等。这部分作品的确以宋调为主,艺术上也比较有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句法散化。诗中较少采用对偶句式,以单行奇句为主,且不屑作局部雕饰,一气奔泻,以势取胜。其次是好用虚词作句头,上下勾连。如“由来、不惜、纵有、岂期、但愿、未免、况值”等,体现出散文化的特点。再者是讲究章法,开合有度,以古文结构入诗。如《紫藤花下醉歌用竹垞原韵》一作,开头先写京师朱彝尊古藤书屋之清幽环境,引出对昔日主人朱彝尊的怀念,然后宕开一笔,叙写作者自己的境况,接着再转回来,仔细描绘眼前的紫藤花架,由满藤的鲜花引起对人生的感慨,主客合为一处。结尾回到开头,以告别书屋收束:“鄙人欲作鸡栖桀,多士自欣鱼在藻。乘舸春水向江湖,回首花前几人好。”应该说,上述作品并非简单地模仿古人,而是带有作者个人的烙印,属于对宋诗的成功继承。当然,此类作品亦并非宗法黄庭坚的江西诗派。
姚鼐最精彩的七古其实不是上述作品,而是兼有唐宋体格,气势雄浑,带有歌行性质的长篇。袁枚认为:“太史七古雄厚。”[8](P1106)徐世昌《晚晴簃诗话》又进一步指出:“(姚鼐)七古尤晶莹华贵。晚年虽学玉局,而不失唐人格韵。”[9](卷91)所指皆为此类作品。这里,不妨引《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作歌》为例:
泰山到海五百里,日观东看直一指。万峰海上碧沉沉,象伏龙蹲呼不起。夜半云海浮岩空,雪山灭没空云中。参旗正拂天门西,云汉却跨沧海东。海隅云光一线动,山如舞袖招长风。使君长髯真虬龙,我亦鹤骨撑青穹。天风飘飘拂东向,拄杖探出扶桑红。地底金轮几及丈,海右天鸡才一唱。不知万顷冯夷宫,并作红光上天上。使君昔者大峨嵋,坚冰磴滑乘如脂。攀空极险才到顶,夜看日出尝如斯。其下濛濛万青岭,中道江水而东之。孤臣羁迹自叹息,中原有路归无时。此生忽忽俄在此,故人偕君良共喜。天以昌君画与诗,又使分符泰山址。男儿自负乔岳身,胸有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大地川原纷四下,中天日月环双循。山海微茫一卷石,云烟变灭千朝昏。驭气终超万物表,东岱西峨何复论?
上引诗阅读起来,感受明显与前作不同。具体来讲,一是挟情韵以行,爽利畅达,情感饱满,非如宋诗之以议论和陈述为主。二是景物刻画逼真感人,境界雄壮沉厚,句式在骈散之间,没有明七子的陈熟格套,令人耳目一新。三是声韵铿锵,颇具音乐之美。上引作品虽属古体诗,却具鲜明之韵律,除作者好采用带鼻音的字作尾韵外,更主要的乃得益于诗中的换韵。我们知道,换韵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规则的等式换韵,另一是非规则的不等式换韵。姚诗属于等式换韵,它们基本都是四句一换,以平仄交替为主,抑扬顿挫,读起来尤具声韵之美。前人评姚作“晶莹华贵”,“无所依傍”,所指正是上述特点。所以说,该类七言古体属于姚鼐的创格,已达到唐宋兼融、别开生面的境地。
再来看姚鼐近体诗。其近体诗作的总数超过古体,然而,五、七言之间也不平衡。诗集中五言律诗较少,仅一百余首,占四分之一。如果说姚鼐的五古以汉魏六朝和唐代为宗的话,那么,姚鼐的五律显然是以学唐为主,他曾在《五七言今体诗钞·序目》指出:“盛唐人固无体不妙,而尤以五言律为最。此体中又当以王、孟为最,以禅家妙悟论诗者,正在此耳。”[10]应该讲,姚鼐本人即持这种观念进行创作,故五言律诗比较接近盛唐,且偏向王、孟一派。但是,与此同时,姚鼐也学杜诗。他在《五七言今体诗钞·序目》里说过:“杜公今体,四十字中包含万象,不可谓少。数十韵百韵中,运掉变化如龙蛇,穿贯往复如一线,不觉其多。读五言至此,始无遗憾。”[10]相比之下,姚鼐的五言律更靠近王、孟,而长篇排律则显然宗法杜甫。如果说五律体现了温深含蓄之美,那么长篇排律就展示出阳刚浑厚之美。
姚鼐的近体诗实际上是以七言为主的,而七言中又以七律为主。七绝虽有佳作,不足成家。所以说,七律才是姚鼐近体诗的真正代表。后代评论家往往赞赏姚鼐的七律,钱钟书《谈艺录》所谓“惜抱尤粹美”,指的其实正是七律。这里且举两首为例:
高楼深夜静秋空,荡荡江湖积气通。万顷波平天四面,九霄风定月当中。云间朱鸟峰何处?水上苍龙瑟未终。便欲拂衣琼岛外,止留清啸落湘东(《夜起岳阳楼见月》)。
杨刘兵度大梁危,饮泣犹当奋一麾。乱世鸟飞难择木,男儿豹死自留皮。天连白草横残垒,日落阴风拥大旗。莫问夹河争战地,浑流徙去黍离离。(《过汶上吊王彦章》)。
姚鼐的七律的确有特点。它们气势宏大,又壮丽精切;结构沉稳,又不落熟套;浑成匀称,且不乏警联佳句。有的句子以意境铸造为重,有的又以哲理表达为主,抒情、议论兼而有之,写实、想象彼此交替,句型也是王(维)、李(颀)、杜(甫)、李(商隐)、苏(轼)、黄(庭坚)彼此交错,合为一炉。这些作品才是姚鼐七律真正的独特之处,学术界所称姚氏创格最主要的指此。
进入乾隆朝以来,综合唐宋两代诗歌的某些特点,铸造自己风格特色的作家和流派已涌现不少,实际上此并非姚鼐的独创。姚鼐的贡献应该在于:把唐、宋两代的典型作家即王维、李商隐和苏轼、黄庭坚熔为一炉,实现了唐宋诗的深层次结合,从而产生出一种似曾相识同时又耳目一新的诗歌类型。
二、姚鼐的诗学观
姚鼐的诗歌特色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作者的诗学观所导致的。概括起来讲,其诗学观主要有两个基本观点:
第一,兼法唐宋。这个观点也可说是对前人学古的纠偏。明前后七子一贯提倡“诗必盛唐”,却由倡导格调走入了对古人的模拟,被人讥为“瞎盛唐诗”。清初,王士禛曾一度提倡宗法宋、元诗,但实际上也以宗唐为主,并未真正将唐、宋诗有机融合起来,故人称“清秀李于麟”。沈德潜亦提倡格调,“专宗三唐”,结果“袭盛唐之面目,绝无出奇生新,略加变化处”[11](卷2),以上这些都是复古派的偏颇和失误。在此种情况下,姚鼐经过反省,提出了兼法唐宋的主张,试图走出一条不同于前人的道路。他明确指出:“近日为诗当先学七子,得其典雅严重,但勿沿习皮毛,使人生厌。复参以宋人坡、谷诸家,学问宏大,自能别开生面。”[12](卷下)这便是姚鼐的诗学观。姚氏不但在创作上将此诉诸实践,还专门编选了一部《五七言今体诗·钞》,宣传自己的观点。该诗选的七言诗部分与五言诗部分不同,除收入众多的唐代作家外,还编选了若干宋代诗人的作品,尤以苏轼、黄庭坚、陆游三人为最。显然,上述这些是在展示一种新的创作理念,其造成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第二,刚柔并举。众所周知,姚鼐在散文领域提出了阳刚、阴柔之说,将古今文章风格归纳为两大类,一类为阳刚,另一类为阴柔。姚鼐将此观点也引入了诗歌领域。他说:“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天下古今为诗人者多矣,为诗而善者亦多矣,然卓然足称为雄才者,千余年中数人焉耳,甚矣,其得之难也。”[13](卷4,《海愚诗钞序》)又说:“夫文以气为主,七言今体,句引字赊,尤贵气健。”[10](卷首序目)我们知道,姚鼐的散文宗法欧阳修和归有光,以阴柔委婉为主,但是他的诗歌却恰恰相反,以阳刚雄健为主。这是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恐怕和姚氏纠偏救弊的动机有关。姚鼐之前,被视为诗坛正宗的王士禛在诗界提倡神韵,其诗偏于阴柔,失之柔弱。姚鼐固然赞成王士禛的雅正观,他曾于《五七言今体诗钞序目》中声称“以尽渔洋之遗志”[10],但正因为如此,他要弥补渔洋的不足,倡导雄壮刚健之风。
实际还不仅于此,姚鼐真正的诗学理想不是一味豪雄,而是刚柔相济。他说过:“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13](卷4,《海愚诗钞序》)其弟子方东树也说:“诗文以豪宕奇伟有气势为上,然又恐入于粗犷猛厉,骨节粗硬。”[14](卷9)此又显然是针对宋诗而发的。姚鼐要用唐宋兼融的方法来纠偏,且达到刚柔相济的理想。我们注意一下《五七言今体诗钞》选诗的情况,就会发现,姚鼐所选大多接近自己的诗学标准,七言律诗尤其如此。如对黄庭坚,他所选的就往往为风格雅正、刚柔相济者。其评语亦如此,如“豪而有韵,此移太白歌行于七律内者”等。姚鼐自己的七律也基本贯彻了这一主张,前面所引数首诗可为佐证。如此看来,唐宋兼融和刚柔相济对姚鼐来说,又是互相联系,彼此补充的,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综合创作和理论两个方面来看,姚鼐在清代诗歌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之地位,他对清道光以后宋诗运动的兴起,对“同光体”的形成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余脉一直延续到清末。
当然,姚鼐以及整个桐城诗派的弊病也是十分明显的。他们以正统自居,标榜“雅洁”,反对所有偏离正统诗学、锐意革新的诗歌潮流,将诗歌框定在狭隘的所谓“雅文学”领地内。所以说,在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清乾嘉时期的桐城诗派也成为传统诗学日益走向保守、自闭的一个环节。
三、桐城诗派诸家
桐城派的成员未必都是桐城人,他们多为刘大櫆、姚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姚鼐晚年主讲紫阳、钟山书院数十年,学生尤多,其中颇有能诗者。这些作家大多秉承了其师的论诗主旨,较突出者有方东树、梅曾亮、姚莹、鲍桂星、吴德旋、鲁九皋、杨用光、朱孝纯、马宗琏、姚椿等人。这里略述其中数家。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人。雍正朝贡士,科举长期不顺,应博学鸿词科,又报罢。短暂出任过黟县教谕。有《海峰文集、诗集》。
由于刘大櫆经历坎坷,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在桐城诸家中均较为特别。可以说,他的创作很大程度上乃是“不平则鸣”意念的表达。这里选其七言古体《吴大椿置酒丁香花下》:
江南三月江水清,风喧日暖鱼苗生。客子飘零惯车辙,辜负故园春景晴。今朝喜见草芽出,丁香枝上苍玉明。延陵公子动逸兴,安排酒盏招刘伶。平生抵死荷一锸,况闻牛与羊鱼腥。侑觞复有好弦管,《连昌宫辞》《琵琶行》。吾闻阮嗣宗,因人善酿求步兵。又闻灌仲孺,一钱不值卫尉程。我辈天涯久沦落,春光入座谁能醒。化史解衣槃礴羸,淳于失笑冠绝缨。饮者身在即不朽,何须刻作钟鼎铭。君不见,此花含吐如瓶瓴,欲开不开殊有情。一夜东风起萍末,纷纷霰雪铺檐楹。
刘大櫆的诗歌基本上属于宗法唐人,然不尚雕琢,率性而行,“意兴豪迈,波澜老成”[15](卷67),能够抒写真情。语言虽不够精练,豪迈雄奥的风格却影响了桐城派后来的作家。
梅曾亮(1786-1856),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清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历官户部郎中。与方东树、管同、姚莹并称为姚鼐的“四大弟子”,“义法本桐城,稍参以己者之长,选声练色,务穷极笔势”(《清史稿·梅曾亮传》)。梅曾亮在京师二十余年,继姚鼐后成为桐城派的领袖,当时众多京城作家包括曾国藩在内均受到了梅曾亮的影响。有《柏枧山房文集》、《柏枧山房诗集》。
梅曾亮诗的散文化程度很高,用他自己的话说“以文为诗古有之”(《题桐城张元道诗稿》),作为散文家,此是有意为之的。这里录其七古《六月十二山谷生日邵蕙西舍人招吴子叙编修张石舟大令朱伯韩侍御赵伯厚赞善曾涤生学士冯鲁川主政龙翰臣修撰刘蕉云学正及曾亮凡十人集于寓斋舍人有诗属和》:
夏幄阴阴四围碧,沉李浮瓜香拍席。涪翁生日是今朝,七百年逢吾辈客。此翁翰墨如坡翁,命宫磨蝎应相同。春风官羊未饱吃,荔枝却啖戎州红。主人诗派江西续,喜借古欢招近局。槐花韭饼虽已过,黄鸡作羹鹅掌熟。新诗似拟鹤南飞,共饮一尊歌此曲。我亦低首涪翁诗,最怜作吏折腰时。只今更谪人间否,安得停杯一问之。
梅曾亮的七言古今体主要学习黄庭坚及苏轼、陆游,在这一点上比姚鼐走得更远,上引这首可见一斑,而在兼有唐调方面又近似姚鼐。总的来说风格沉雄坚实,平朴古劲,而不及姚鼐的圆润流畅。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如,安徽桐城人。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历官护盐运使、台湾兵备道、广西按察使、湖南按察使。曾多次运筹帷幄,于台湾击退英国侵略军的进犯,还因此受到过贬谪,是一位爱国志士。有《中复堂全集》。
姚莹是姚鼐侄孙,“石甫濡染家学,才思飙发。其从祖惜抱先生尝评其诗,谓其‘求进于声色臭味之外,然不可速成,俟其自至’”[15](卷120)。作为爱国志士,姚莹集中有不少慷慨激扬之作。这里录其两首七律诗:
耸身缥缈立飞楼,万里浮云作壮游。白日有灵应照我,青山抵死不埋忧。百年竞逐原头鹿,终古浮沉水上鸥。北望更须凌绝顶,黄河如带是中州(《登何氏楼》)。
崖山风雨昼冥冥,犹是当时战水腥。仓促纪年同外丙,艰难立国下零丁。人间草木无王土,海底鱼龙识帝庭。一代君臣波浪尽,杜鹃何处叫冬青(《崖门怀古》)。
七律为姚莹所长,风格近似姚鼐,“惜抱平日论诗,排律宗少陵,七律拟山谷,观石甫所作,于此旨殊多悟入”[15](卷120)。上引作品悲壮慷慨而不乏深沉含蓄,“根源忠厚,寄托遥深”,既富苍凉劲直之气,复备清转婉妙之思。
鲍桂星,字双五,一字觉生,安徽歙县人。清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工部侍郎。在朝时任事敢言,曾屡遭排斥打击。有《觉生诗钞》。
鲍桂星年少时曾从同县的作家吴定学古文,后师事姚鼐,“诗、古文并有法”(《清史稿·鲍桂星传》)。据汲修主人《啸亭续录》卷三记载,鲍桂星不满于诗坛尽学宋元诗而鄙视宗唐的明七子,尝专门选编明七子诸家的诗若干卷,“汰其浮响,择其精采”[16](《鲍双五选王李诗》),以纠风气之偏。另外,还“用司空图说辑唐诗品”(《清史稿·鲍桂星传》),进一步彰显唐诗的价值。以上既属于蹈扬其师姚鼐的思想,同时也是桐城诗派整体观念的一种表现。此处试举《阮芸台夫子属赋小琅嬛仙馆蕉花》为例:
桂海移栽近几年,清于檐卜韵于莲。羚羊挂去春无迹,野鹿衔来骨亦仙。醒酒风知香近远,护花鸟识味中边。何当手把金茎露,洒向人间遍大千。
鲍桂星的七言律诗能够融合唐、宋两代,将黄庭坚和李商隐合为一体,读来别有一番风味。
由上可知,桐城诗派的主要特点就是将唐、宋诗歌的特长加以融合,而且融合深度超过了以往其他诗派,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突破了古人。他们为清后期的作家在这方面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姚範所论明七子与黄庭坚,实际上从王士禛处来,王氏《论诗绝句》有云:“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许传衣蹑后尘。却笑儿孙媚初祖,强将配飨杜陵人。”又,《读黄诗》云:“一代高名孰主宾,中天坡谷两嶙峋。瓣香只下涪翁拜,宗派江西第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