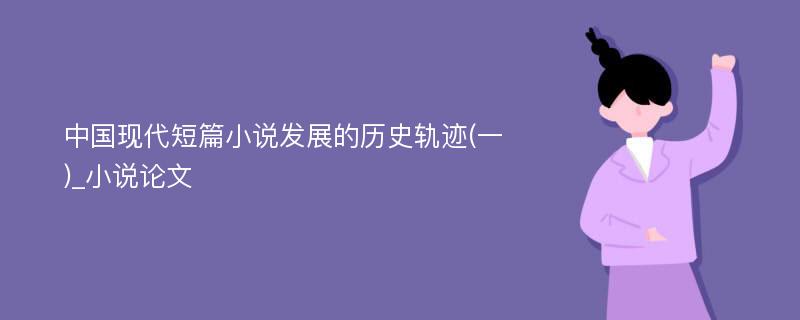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篇小说论文,中国论文,轨迹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当我们站在世纪末历史的高峰回观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的时候,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还有后来逐渐发达起来的影视文学,就像几条大的干流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社会原野上蜿蜒盘旋,一直流过来,流到我们的眼前,流到我们的脚下,并且还在继续流动奔腾,流向未来的二十一世纪。但是,在这几条大的干流中,情况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散文”的河道是宽阔的,并且支流繁多,纵横交错,水漫漫,流淙淙,色彩斑斓,异彩纷呈,因而很多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都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散文的创作成就最大,水平最高。但是,散文的河道是宽阔的,但却不是深邃的;水势是浩大的,但却不是湍急的,除了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年的鲁迅杂文曾经涌起一股股湍急的浊浪,造成过散文创作领域的千古奇观,就整个散文创作而言,它与中国古代散文在审美上并没有明显的、足以体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新的艺术追求的特征。发生更巨大变化的是理论著述,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有力地改变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性质和他们的写作习惯,像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蔡仪的《新美学》等等,与中国古代的理论著作是有更显著的不同的,但这些作品已经不属于文学散文之列,文学散文是写个人日常的实际人生感受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转变和新的审美追求的建立,更是从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而不像西方近现代知识分子一样是从自我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生的,所以一当离开对民族前途、社会命运的整体思考,情绪相对松驰地返回到个人的日常平凡生活及其细微生活感受中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就没有明显的差别了。“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代小品散文大家周作人会把中国现代散文等同于晚明小品的道理。鲁迅杂文是个例外,他对中国社会思想的毫无情面的解剖一下子把他卷入了中国现代文化斗争的漩涡之中,这不但改变了他的文化处境,也改变了他的社会感受和生活感受,但这到底是一个特例。对中国古典传统革新幅度更大的是诗歌。中国古代是一个诗国,如果说“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皇上,“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宰相,“诗”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皇后。陈独秀要革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胡适进而提出要革新中国的文学,所以他首先想到的是诗歌革新,要革我们的“皇后”。但是,“皇后”并不是那么容易革的。“皇上”倒了,不一定“皇后”也倒。正像皇后体现着女性的美,中国古代诗歌也体现着中国语言的美。“诗”的“美”和“经”的“理”并不是等同的两件事。唐玄宗喜欢像杨贵妃这样的女人,黄巢也可能喜欢像杨贵妃这样的女人,皇上变了,皇后不一定要变。没有生活实感的变化,这种语言美感感受的变化也是极难的。中国的书面语言是由单音节的方块字组成的,中国古代的格律诗提炼的就是中国语言的这种美的形式,白话文的革新并没有改变中国单音节的方块文字,因而它的有效性也没有消失。这就是为什么至今人们读起中国古代的名诗佳作来仍然摇头晃脑、赞叹不已的原因。但是,这并不能证明那些反对白话文革新的复古主义者的理论是正确的,因为一个民族的语言并不仅仅是为了作诗的,它属于全民族所有,诗人没有独占权。中国的文化要发展,要适应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学科的需要,就必须克服中国古代那种严重地言文不一致的情况。即使从诗歌创作本身来说,中国古代的格律诗虽好,但让中国知识分子摆弄了千余年,再想创作出较之古代诗人更脍炙人口的格律诗来,已经没有多大的可能性,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更大的创作空间,以便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量。现代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现代语言中多音节词汇的大量出现,也迫使中国的诗歌必须放弃旧的形式。这种困难而又必要的革新,使中国的新诗创作像一条狭窄而又绵延不绝的小溪,时缓时急,时粗时细,一直蜿蜒至今,虽然艰难,虽然不能说它较之中国古典诗歌已经有了更高的艺术成就,但它到底丰富了中国的诗歌宝库,较之陈陈相因地继续重复古代诗歌的形式要有意义得多。我认为,中国的新诗在将来的发展中还会焕发出我们现在难以预料的异彩来——我们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它的社会生活太干燥、太严峻,这是一个散文的时代,社会上、生活里、心灵中都没有那么多必须用诗歌才能充分表达的东西,诗人的乳房里挤不出那么多、那么精良的奶来,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永久地存在下去;较之诗歌,更困难的是话剧。话剧是一种更笨重的艺术形式,它要靠演出。演出要有经费,要有先期投入。而要收回成本并获得利润保证戏剧演出的持续进行,就要有愿意花钱买票的观众。散文、诗歌、小说依靠书籍、报刊可以把散存于全国各地的新文学的读者集中起来,保证它的正常的出版发行,而观念则是无法集中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化的发展还没有任何一个地域培养出足以支持话剧持续地进行正常演出的观念。剧本不一定要演出,但没有具体演出活动的促动和演出效果的检验,一个民族的剧本创作也是不可能得到繁荣的发展和艺术水平的持续提高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国的旧剧是表演性的,是让观众“欣赏”的,它用化装、表演、音乐唱腔和戏剧故事的外部矛盾冲突愉悦观念,话剧则是结构性的,是让人感动的。比起中国的旧剧来,话剧就像一只拔光了毛的鸡,没有一点外部的色彩。它依靠的完全是内在的戏剧冲突。中国固有的戏剧观众感情太粗糙,不论官僚和平民。恭维几句就高兴,听到不顺耳的话就恼火,有了矛盾和分歧就吵架,或者屈服于权威的力量,不说,不表现。这样的观众是无法进入话剧的剧情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也是无法造成适于话剧演出的情境的。这个问题恐怕至今是影响话剧艺术在中国发展的最最根本的原因。一个动不动就搞革命大批判的民族是不可能出现好的话剧剧本的,因为它的所有稍微重要的社会矛盾都用强制的办法解决了,在舞台上演出的或者是没有重要严肃戏剧冲突的絮絮叨叨的抒情,或者是恶言恶语的吵架,而这些都构不成高层次话剧的艺术情境。现代话剧在中国的运气也是不好的,在它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又遇到了电影的冲击。这样,话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像一条时而干涸、时而积水的河道,成功的话剧剧本则像羊粪蛋子一样,零零拉拉,连不起串来。在观念上,戏剧的地位提高了,被现代知识分子抬到了雅文学的圣坛上来,但就实际的创作,它还很难说有与此相称的成就;说到小说,则不同了。它的革新幅度是很大的,而成就又是令人注目的。特别是短篇小说,就更是如此。长篇小说,在中国古代有几大名著,特别是《红楼梦》的成就,还是为现代长篇小说所不及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虽然都是小说,但二者差别极大。如果说短篇小说是空间性的,那么,长篇小说就是时间性的。短篇小说也在时间的流动中组织情节,但最终给你的还是一种空间的感觉。鲁迅的《阿 Q正传》写了阿Q一生的事情,但最终让你记住的就是阿Q这个人物,这个人物所体现的中国人的脾性;长篇小说虽然在局部和整体上较之短篇小说都有更大的空间,但最终要给读者造成的则应是一个时间性的、流动的感觉。没有流动和变迁的感觉便没有长篇小说。《红楼梦》不仅仅塑造了一些人物,更重要的是写了由这些人物构成的一个封建大家庭衰败的过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不仅仅是一些个别人的故事,更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转化的过程。它们都可信地展示了一个过程,直到未来,人们仍然认为这个过程是“真实的”,是合情合理的。显而易见,仅仅这一点,就决定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可能出现像曹雪芹、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长篇小说家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像一头不听话的驴子一样令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办法,时至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今天不知明天的事,昨天看好的历史行情今天又马上跌落下来,自己的想法还一天三变,对长篇小说中众多人物和整个情节在历史上的滚动就更难具体把握了。在现代文学史上,茅盾的《子夜》,是一部在结构形式上最具长篇小说特征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柳青的《创业史》在人物刻划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它们都栽在中国历史的陷坑里,它们的作者都想把中国历史的发展纳入到一定的轨道中,但中国的历史却偏偏没有像他们想的那样发展。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精品,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历史的野马不论怎样颠荡震颤,也无法把像鲁迅的《阿Q正传》、郁达夫的《迟桂花》、 许地山的《春桃》、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金锁记》、冯至的《伍子胥》、骆宾基的《乡亲——康天刚》这类中短篇小说从自己的马背上掀翻下去。它们是以历史上的一种人生状态为依据的。历史无法抹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的任何人生状态,因而也无法抹煞这些中短篇小说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总而言之,中国现代的诗歌、戏剧、长篇小说在其总体的成就上都还不能说已经超过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散文的成就是显著的,但它也没有较之中国古代散文更明确、更具体的新的审美特征,而既具有鲜明的现代艺术的特征而又取得了较之中国古代同类题材的作品更丰厚的成就者,则是中国现代的中短篇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也就是说,最集中地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中短篇小说。
中国古代的短篇小说,不论从唐宋传奇到《聊斋志异》的文言短篇小说,还是《三言》、《二拍》中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实际上都没有完全脱离开“故事”的范畴。“故事”和“小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二者又是有严格的区别的。依照我的理解,故事是讲出来给人听的,小说是写出来给人看的。讲与听的关系和写与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听,只能接受线条较粗的东西,只能分辨彼此有较大差别的事物,实感到的是声音流动的美;读,则敏感得多,细致得多了。它能分辨极细微的差别,能感受到语言背后沉潜的意义,它直感到的主要不是语言流动的美,而是语言运用的精确和巧妙。听的对象是转瞬即逝的,读的对象则是可以在较长时间内驻留的。这使小说有更大的艺术潜力,有为“故事”所没有的更广阔的表现空间。但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还刚刚从“故事”脱胎而来,它还没有完全脱却“故事”艺术表达方式对它造成的束缚。《三言》、《二拍》原来就是与说书人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讲的一些故事;《聊斋志异》则是蒲松龄听来的一些故事,经他润饰加工而成的一部民间故事书。这种情况甚至与古代长篇小说的情况也不尽相同。由《三国》到《水浒》再到《金瓶梅》,最后到《红楼梦》,中国古代的长篇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发生着一系列的根本性变化,这个变化又是同由说听艺术向写读艺术的转变密切相关的。《三国》和《水浒》都是在讲史艺术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但《三国》更是根据正史的记载通过想象加工而成,作者所写的不是自己生活中所熟悉的人物,他们彼此构成一定的关系,但与作者没有直接的感情联系,作者是根据一种流行的思想观念表现这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水浒》中的人物则平凡得多了,它是讲史与写实的结合体,其中的人物是在作者和读者的实生活中可以遇到的,可以和作者和读者发生实际的交际关系乃至感情联系。人们对他们的感受更细致、更具体,因而也能从他们生活细节的刻划中产生出强烈的趣味感来。如果说《三国演义》听起来要比读起来有趣味得多,那么,《水浒传》读起来就比《三国演义》有趣得多了,但它仍然是能够讲的,有一个好的说书人说给你听,一定比你自己看书更加生动,更有趣味;《金瓶梅》则不再是说话人的底本,它是为看而写的,题材现实化了,是作者实际人生观察的结果。它写的是世情,是平凡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其意蕴也开始向内转化。这类的情节,别人是讲不这么具体,这么细致,这么津津有味的。《三国》、《水浒》依靠的是生动的故事,《金瓶梅》依靠的则是世态人情的描写,这些文字描写的功能很难由讲说的口头语言来代替。但这些人物仍不是作者独立人生体验中的人物,作者不在他所描写的世界的内部,而是在它的外面。他是一个冷眼看世界的评判者、揭露者,他并不为自己生存在这样一个污浊的世界上而痛苦,而悲伤,他仍企图用对这些丑恶东西的揭露而吸引自己的读者,因而它的描写中时时有过于外露的缺陷:较之《金瓶梅》,《红楼梦》所描写的世界则是作者体验过的世界。它不但是为看而写的,不但写的是日常的平凡生活,而且作者就在他所描写的这个世界里。他是站在自己特有的角度感受和体验这个世界的,因而它的思想和艺术都有了为任何其他人都无法重复的独立特征。作者体验中的东西,是精确的,是有分寸的,“过犹不及”,他不会无节制地夸饰它,也不会无节制地贬斥它,否则就离开了作者的初衷。《红楼梦》虽然也有自己的故事,但作为小说却不仅仅是这些故事。它是为读而写的,而不是为听而写的。要了解这部小说,只听别人讲是不行的,只看根据它改编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也是不行的。你必须读曹雪芹的原书,必须通过它的书面语言。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与“故事”不同的小说。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所经历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国古代的短篇小说还是没有经历过的。只有到了现代文学史上,只有到了鲁迅这里,它才真正实现了由说听艺术向写读艺术的转变。
如果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家,曹雪芹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家,鲁迅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短篇小说到了鲁迅手里才真正成了一门成熟的艺术形式。为什么鲁迅能够把中国的短篇小说提高到真正小说艺术的高度?一些客观的因素当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代报刊杂志的出版发行,维新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小说观念的变化并由此导致的小说地位的初步提高,晚清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小说读者群的扩大,林纾等人的翻译小说和外国小说的影响,陈独秀提倡的思想革命和胡适提倡的白话文革新的先导作用,构成了鲁迅小说艺术革新的前提条件。但是,只有这些外部的条件还是远远不够的。现代的报刊杂志是现代白话小说的主要载体,但它可以刊载现代白话小说,也可以刊载传统的武侠和言情小说,它自身是不会独立产生新的短篇小说的;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比附西方的文学把小说的地位提高起来,初步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小说的歧视态度,但梁启超本人仍然主要是一个政治家,他对小说的重视仍然是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对文艺的重视,他的有限的小说创作都是直接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是一些政治宣传品,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革新;小说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创造才有真正的小说艺术作品,翻译小说和外国小说是不能直接产生中国自己的优秀的小说作品的,否则,我们这些比鲁迅读过更多外国小说的人,就个个都成了杰出的中国小说家了;陈独秀和胡适的情况在文学革命问题上同梁启超并没有根本差别。他们都是观念上的革新家,但观念的革新同艺术的革新不是同样一回事情。晚清小说的繁荣并没真正实现中国小说艺术水平的总体提高,晚清的谴责小说没有达到《儒林外史》的讽刺小说的艺术水平;民元前后的鸳蝴小说即使在爱情描写上也远远不及《红楼梦》的手段,艺术不等同于思想,并不是有了一点新的思想认识就一定能够超越于以前的艺术水平。我认为,站在现代历史的高度,为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发展,重新感受自我、感受自我的生活环境,感受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和他们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是鲁迅把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推向了现代高度的主要原因。这使他从参加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群众的具体的平凡的日常生活,转向了他们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存在方式,而不是像陈独秀、胡适等人一样主要关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口头的理论和书面的宣言。这是一些活生生的具体,是一种浑然一体的感性存在,是只有用艺术的方式才能表现的对象,而这些对象,则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家未曾表现过的东西,是只用讲故事的办法无法精确表达的。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西方短篇小说艺术的影响才在鲁迅的创作实践中发挥出了点石成金的作用,才使它们成了与鲁迅的生活实感相互推动的因素。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短篇小说产生了,它们不再是一些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闲开心的奇闻轶事,不再是供说书人任意发挥的有趣的故事。它是同书面语言血肉相连、不可须臾分离的一体性存在,它的艺术就存在在鲁迅的文字表达中。鲁迅小说对我们说的是什么呢?“看,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过的生活!”这里面有你,有我,也有他。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但它又把你拉到一个你平时不容易走到的角度上来,重新观察这一切,体验这一切,使他从中感到一点平时感觉不到的东西,让你思考,让你清醒,让你在感到这一切之后走出原来的自己,成为一个更新的人,更现代一些的人。在《狂人日记》里,他让你从那个“狂人”的角度想想自己,想想自己的生活环境,想想我们民族的历史,从而知道我们还不是真正文明的人,我们还保留着很多吃人的习性。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重新设计自己,修正我们固有的文化观念,建设新的文化;在《孔乙己》里,他让你站在一个小孩子的角度看一看没有爬到权势者地位的中国知识分子,看一看我们对自己瞧不起的人的态度,看一看我们对无权无势的人是何等的冷酷无情,从而使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像平时想得一样善良,一样富有同情心,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像平时自己想得那样体面,那样高贵,那样有价值。人们尊敬的是中国官僚知识分子的权势,而不是知识分子的自身和他们的“知识”。他们在《四书》、《五经》中学来的那些教条在社会群众的眼里只不过是“回字有四种写法”,是对于实际的社会人生毫无意义的东西;在《示众》中,他把你从看热闹的人群中拉出来,让你看看这些看热闹的人的热闹,让你感到点自己精神上的空虚和无聊、……鲁迅小说写的对象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些人物和现象,但他在这些人物和现象中却能表现出你平时感受不到的一种异样的意味来。我认为,这就是他的小说艺术的本质特征,也是他能把中国古典短篇小说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的主要原因。在这里,叙事角度的选择和艺术画面的组接即结构是两个最最重要的艺术手段。每篇有每篇的独特的叙事角度,每篇有每篇的独立的结构方式,这才能把原本平常的人物和生活场景构成有意味的艺术形式,构成短篇小说。这是一种才能,一种艺术的才能,这是比讲出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更困难的一种才能。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就可以把《草船借箭》、《武松打虎》、《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画皮》讲得娓娓动听,但即使一个鲁迅研究专家也无法生动地为听众讲述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现代短篇小说。他们只能讲解它,但却不能同样生动地复述它。
鲁迅小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在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总体思想脉络中被创造出来的,故而我们可以称他的小说为“启蒙小说”。
2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间,只产生了鲁迅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他开垦了这块处女地,而开拓了这块艺术领地的是二十年代的一些青年作家。从短篇小说艺术的角度,我把这时期的短篇小说分为三派四种。这三派是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主观抒情小说、以叶圣陶为代表的社会写实小说、以许地山为代表的宗教哲理小说。它们加上当时的女性小说又可以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这三种四类小说的总特点是它们的青年文学的性质,它们都是当时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创作的,爱情、幸福、理想人性和理想社会的向往是它们共同的主题,这和中年鲁迅自觉地、有意识地用小说影响社会思想的变化的创作意图有着明显的不同。鲁迅的体验和感受是在长期人生经历中积累起来的,是在确定的社会目标和人生目标的追求中建立起来的,因而也有深邃执着的特征。他不是活在幻想里,而是活在奋斗中;他攻打的是一个最坚固的堡垒,因而他也不期望眼前的胜利。他的作品给人以更沉鸷的感觉,而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不论是情绪上偏于颓废感伤的,还是情绪上偏于昂扬乐观的,都没有鲁迅小说那种深邃沉重的感觉。他们表现的更是一个青年人瞬时的感受,一时的情绪。它们强烈具体,色彩鲜明,但也容易变化,其作品的风格也是不那么固定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着经常性的变化的。这里说的只是他们最有代表性的倾向。
以《沉沦》为代表的郁达夫小说表现的也是日常生活的题材,但他写的不是一般的社会生活,而是自己的生活。这个生活本身是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和价值的,它的意义和价值是因为它是他的生活,是他的痛苦和欢乐的源泉。他是借助自己日常生活的描写抒写自己的情感和情绪的,抒写他的欢乐和痛苦的,他的小说走向了主观抒情的道路。郁达夫十几岁被送到日本留学,在性意识受到压抑的中国文化环境中一下子跳到了性开放的日本文化环境中,在强烈的性诱惑面前表现出的是性畏惧、性恐慌。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性压抑下的苦闷,弱国子民的自卑,社会地位的低下,经济生活的困顿,全都在这性恐慌造成的震颤动荡的情绪波动过程中被强烈地感到了,也被郁达夫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了。他的小说实际就是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一张心电图,在无规律当中呈现着一种有规律的运动。他的第三人称小说实际也是第一人称的,有名字的主人公同“我”没有根本的差别。他要把自己心中的苦闷统统发泄出来,就不能掩盖,不能说谎,不能爱面子,表现的欲望一下子掀掉了传统士大夫那些繁文缛节,那些皮笑肉不笑的虚情假意。他大胆暴露自己,但这种大胆暴露恰恰因为他比别人更纯洁、更真诚,他的小说好像在一块白而又白的纱布上毫无顾忌地泼了些浓墨重彩。他玷污着它,但却把它造成了一个艺术品。他的真诚无暇被这污秽衬托得无比鲜明:他的心灵的污迹也被他的纯洁善良显示得格外突出。这是一个孩子的忏悔,一个青年的检讨,是当时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真实的心灵历程。鲁迅的小说是结构性的,他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揭示意义;郁达夫的小说则是情节性的,他说下去,说下去,把自己的生活和内心的感受不间断地倾诉给你;鲁迅的小说有一种压迫感,他把中国人的冷酷和自私放在一种特殊情景的压力下让它“自然”地流露出来,使他再想掩盖也掩盖不住了。郁达夫小说暴露的是自己,他不害怕这暴露,他的小说是自然流畅的,他率直得超过你的想象,造成的是痛快的宣泄,把平时不敢说、不能说的话在小说中尽情地倾泻出来。他是个人主义的,但他的个人主义是青年人的个人主义。他的最最根本的价值尺度是个人生活的幸福,是一个青年有权向社会提出的要求。他不再把个人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社会的工具,不是他应当为整个社会而牺牲,而是社会应当保证他的幸福和自由。他对自我的感受最清楚明白,但对整个社会、对社会中其他人的不同的思想要求和行为方式是模糊的。他明于知己,而暗于知人,社会的表现自然不如鲁迅来得一针见血。小说以自我情感和情绪的抒发为主线,一旦这种情感和情绪没有异于常人的独特之处,小说就容易流于拖沓拉杂。随着郁达夫年龄的增长,这种只有在青春期才有绝对合理性的个人主义倾向,开始发生无形的变化。他不再只是向社会倾诉自己的苦闷,同时还向着理解社会,同情更弱小者的方向发展,写出了像《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一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作品。他的《过去》也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比他以前的作品多了一些人生哲理的意味,而他的晚期名作《迟桂花》则一反开始时的颓伤情调,有了淡远飘逸的出世意味。青年时期的情欲宣泄和中年时期的情欲节制,都是他的真实的生活感受和人生感受的表现,郁达夫始终都是一个率直真诚的人,他体现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抒情化倾向。
如果说郁达夫是一个晚熟的青年,许地山就是一个早熟的青年。他出身于一个有宗教传统的家庭里,早年曾到南洋教书,受到了当时宗教氛围的影响。在“五四”学生运动中,他是一个学生领袖,而凡是学生运动,高潮期人们精神贲张,过后则易情绪低落,不论胜利还是失败,都与这些学生娃娃的个人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高潮期彼此粘连,生命感到充实,人生充满意义;过后复又分散,心灵中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反感生命的无常,人生的虚空,他的爱妻又不期然地猝然夭折,眼睁睁一个美的亲的生命毫无理由地消失于无形,这一切都使他过早地思考人生的抽象的意义,生命的形而上的价值。他的脑海里的宗教哲理就多了起来,他的小说的宗教哲理意味也就浓了起来。青年,特别是“五四”时期的青年,往往是充满幻想的,把人生想得太好,把社会想得太简单,他们要改造社会,实现理想,但又对人生的艰险没有充分的估计,因而一遇挫折,便易颓唐厌世。许地山则以宗教心承担起了这苦难,这打击,始终未曾陷入颓唐和厌恶。这是他与“五四”青年迥不相同地方,也是使他的小说有了自己独立风格的原因。他说人生就象蜘蛛结网,一阵风雨就会把你结好的网吹破,但破了再结,结了再破,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他的小说体现的就是他的这种人生观念,他常常把人物放在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中来表现,各种偶然性的变故充满于他的小说,主要人物不是依靠智慧和斗争,而是依靠坚韧的忍耐、不疲倦地等待,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处境,留下一颗平静的心和一个和谐的灵魂。鲁迅和郁达夫的小说都没有离奇的事件和曲折的情节,而许地山的小说则重新具有了传奇性的色彩,把传奇性重新引进了现代白话小说。但他的小说的传奇性同中国古代小说的传奇性实际是大不相同的。古代小说的传奇性是愉悦读者的,是由正面的冲突组成的,带来的是“热闹”感觉,而他的小说的传奇性体现的则是人生无常的哲理意蕴,是为了表现人物的精神境界的,你感不到它的“热闹”,得到的倒是一种人生的况味,一种朦胧的美感。他的小说中也有不少的议论,但这议论并不枯燥。实际上,许地山的宗教哲理,仍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宗教思想,而只是热血青年的一种抽象的人生思考,是由青春期的热情向中年的冷静转化中的精神现象。它不是为了弃绝人生,而是为了正确地对待人生。正像郁达夫的小说在白与黑的张力中透露出它们的艺术魅力,许地山的小说则在热情与冷静的张力关系中显示出它们的艺术风采。他追求冷静,正因为他热情过;他弃绝幻想,正因为他幻想过;他不主张人与人的斗争,正因为他斗争过。只是他过早地懂得了人生的艰难,这时他还没有更丰厚的人生积累,故而他的小说没有《红楼梦》那么丰厚,也没有鲁迅小说那么坚实。他的此后的小说创作,反比二十年代来得明朗,有的揭露资本家的假仁假义,有的表现知识分子报国无门的悲惨遭遇,他的《春桃》虽仍然充满人生哲理,但较之《缀网劳蛛》则更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昂扬的生命意志。
在中国青年中论中国青年,郁达夫偏于“疯”,许地山偏于“痴”,而叶圣陶则属于“厚道老实”的那一类。如果说郭沫若、郁达夫一类日本留学生是二十年代中国文学的龙头,叶圣陶这类中小学教师就是二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凤尾。他没有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膨胀的热情,也没有他们的独立不羁的开拓精神,但他仍然希望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改善。他希望的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友爱的社会,所以他揭露社会的不平等,同情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中小学教师和好学但贫苦的学生是他重点描写的对象。如果说郭沫若、郁达夫把别人的痛苦也加入到自己的痛苦中用第一人称或近于第一人称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话,叶圣陶则把自己的痛苦也融入到其他人物的痛苦中用第三人称的方式表达出来。郭沫若、郁达夫向人诉述自己的痛苦、让人同情他们自己,而叶圣陶则诉述别人的痛苦、让人同情别人。鲁迅的人道主义到了这一代青年作家身上分裂为二,郭沫若、郁达夫更体现了“五四”的个性主义,叶圣陶则更体现了同情被压迫、被侮辱的小人物的人道主义。在文学观念上,郭沫若、郁达夫把文学作为作家个人才能的表现,叶圣陶则像是把文学当个“事情”做的人,就像木匠要做手好活,铁匠要打出好的器械,不能把活做得太“糙”。所以郭沫若、郁达夫的作品中有灵气,但有时流于草率;叶圣陶的作品缺少灵动感,但却严谨扎实,很少有明显的败笔。他的作品好像是先生做给学生看的范文,修整得工稳精严,无可挑剔。在通常人的感觉中,认为叶圣陶更继承了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实际上后来中国作家的现实主义理论就是在叶圣陶这种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下发展起来的,他们以这种倾向理解鲁迅,自然叶圣陶小说就更有鲁迅的遗风。实际上,鲁迅很难说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他似乎更重视他的小说的象征意义。在思想倾向上,鲁迅并不同情人的软弱,不同情被动忍耐苦难的人,而叶圣陶则对软弱的人有更多的原宥,对处境悲惨的人也有更多单纯的同情。鲁迅注目于国民性的改造,他同情但疾视那些软弱无能的人,疾视他们对苦难的忍耐,他不把他们的软弱和苦难仅仅归于外部的社会环境,而叶圣陶则是从社会不平等的角度揭露社会的,他展示了小人物的软弱痛苦就起到揭露社会的目的,他把他们的不幸主要归到外部社会的责任上。这表现在小说创作中,叶圣陶很善于细节描写,很善于描写小人物的心理活动,但其中没有心灵与心灵的结实的对抗。鲁迅的小说不同,虽然人物与人物在外部行动上没有严重的对立,但在心灵与心灵之间,却有着残酷的精神厮杀。叶圣陶的小说平实,鲁迅的小说严峻。较之郁达夫和许地山,叶圣陶后来的小说变化不大。他总是能够随着社会前进,但不走在最前头,在艺术上也是如此。我把二十年代乡土小说家的作品也归入叶圣陶社会写实小说的一类。在鲁迅小说中,乡土,就是我们的中国;在二十年代青年乡土小说家的作品里,乡土,更是中国的一个落后的地方。前者是象征的,后者是写实的。
二十年代是中国女性小说产生的时代。中国古代有女的诗人,女的词人,但没有优秀的女性小说家。我认为。中国女性小说的出现,既标志着中国女性的自由和解放,也标志着中国小说社会地位的提高。现代教育的发展则是这二者的总纽带。现代教育招收女学生并提倡新文学,使中国第一批女性小说家就从这批女学生中产生出来。二十年代的女性文学还没有自己更强的独立性,她们在主观上还做着与男性作家一样的事情,也没有人要求女性作家必须具有与男性作家不同的独立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但他们既然有了自己的作品,自己的表现,就一定会有与男性作家不同的特点。二十年代最著名的两个女性小说家是冰心和卢隐,而凌叔华、冯沅君的小说也有各自的特点。从整体上,冰心的小说属于文研会的一派,并且常被称为“问题小说”作家。但是,“问题小说”这个概念太模糊,并不是一个小说的概念,只要我们细心品味冰心的小说,就知道她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公民来揭示社会问题的,不是向社会提抗议的,而更是作为一个小母亲、大姐姐来给世界的弱小者播种爱情的。她不像很多男性作家那样,总是对着社会的权势者揎袖挥拳,而是像一个小母亲一样把自己的爱的翅膀展开来,想覆盖住所有的儿童,所有不幸的青年。叶圣陶也描写儿童,但叶圣陶主要是在小说中为贫苦儿童鸣不平,他把贫家的孩子写得比富家的子弟要好;冰心认为贫苦儿童应当受到与有教养的家庭里的儿童相同的爱,因而她把富有家庭孩子的环境当作正常的、优良的社会环境,他们的心灵状态和生活状态也就是所有儿童应当具有的。其中贯注的都是对儿童的爱,但具体的表现却是极不相同的。叶圣陶的是父爱,冰心的是母爱。从整体上看,卢隐的作品偏向于郁达夫主观抒情的一派,但郁达夫的抒情更有淋漓的热情,痛快的宣泄,卢隐在这样做时则透露着焦躁和不安。郁达夫的小说酣畅舒展,卢隐的小说紧张逼促。这反映着在传统社会受束缚更重的女性较之在传统社会就有更大自由度的男性在进行自我表现时有着更高程度的内心骚动。这影响到卢隐小说的艺术品味,但与男性根本不同的思想角度也正产生在卢隐的作品里,在当时的男性呼唤着婚姻自由的时候,卢隐就敏感到在男性追求自我的片面的自由的时候,实际是以未解放的传统女性的痛苦为代价的。卢隐的小说躁急,冰心的小说温婉,但她们的作品都不那么优雅,最有雅感的是凌叔华的小说。她描写女性的矛盾心理,描写儿童生活的情趣,乃至描写下层劳动妇女的悲惨生活和不幸遭遇,但都不失其优雅的气质。如果说卢隐反映着冲破重重束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国女性的心理特征,冰心反映着由温馨的家庭走出来而在不和谐的社会里失去了固有心理平衡的女性的心理特征的话,凌叔华则反映着从贵族家庭通过社会的进步自然转化为现代知识女性并保持了自己固有的优雅性质的女性心理的特征。她们也有现代的知识、现代的眼光、希望着中国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性的完善,但她们并不焦急,并不迫切,所以她的小说既不在急剧的外部矛盾中进行,也不在急剧的心理冲突中发展,而是把矛盾隐在小说情节的背后,使你能够感到但又不能最强烈地感到。冯沅君则是四人中写得最实在的,她写的是“五四”女性青年在自由恋爱过程中的实际体验,那种初次到爱河里探险的女性青年的心理状态,在她的作品里有着不带夸张性的描写。她们透露着大胆,也透露着羞怯;有着反抗性,也有着屈服性。但不论大胆或羞怯、反抗或屈服,都不是依照男性青年的观念可以界定的,只有女性,才这样大胆,这样羞怯;这样反抗,这样屈服。她的小说,曾经给人以新的惊疑。但总起来说,她的描写还不够精致,也过早地放弃了小说创作,影响不及前三位大。
二十年代还有很多小说家,但我认为,他们的作品大都可以划归这三种四类小说之中去。(待续)
标签:小说论文; 鲁迅论文; 郁达夫论文; 散文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短篇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话剧论文; 文化论文; 红楼梦论文; 读书论文; 青年生活论文; 三国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金瓶梅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鲁迅中学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