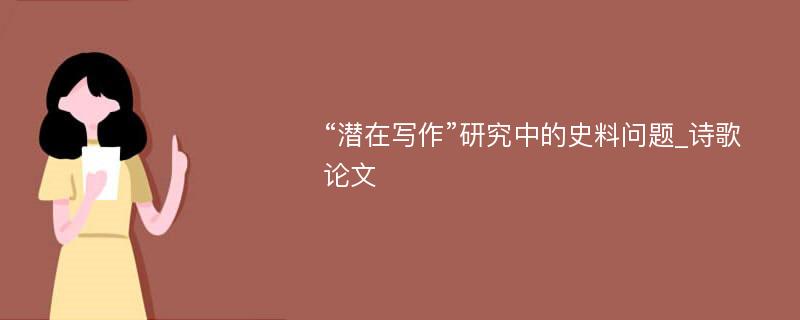
“潜在写作”研究中的史料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以下简称《教程》)对“重写文学史”做出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潜在写作”作为《教程》引入的一个基本文学史概念,为当代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新的述史构架和研究思路,集中体现了编写者打破“一元化”历史叙述的努力,以及试图以“共时性”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多层面”文学的整体史观。不过,“潜在写作”涉及的基本史料、史实却出现一些错讹。具体而言,这些错讹有三类:一是对“潜在写作”真实的创作年代考证有误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二是基本史实的错误和文学史叙述的随意性;三是对版本不一的“潜在写作”文本未作比照、甄别和认定,致使具体作品的引用出现许多错讹。本文仅就与“潜在写作”相关的一些具体史料问题做一些辨析和校正,以就教于该书编写者和学界同道,主要涉及刘志荣执笔的第九章和王光东执笔的第十五章中的部分内容。
一
按照《教程》主编在前言所述,“潜在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主要是“以作品的创作时间而不是发表时间为轴心”来整合文学史。这样,在搁置了“效果历史”之后,创作时间的认定就显得相当重要了。但是,由于对许多潜在的史料缺乏深入细致的考证与辨伪,导致《教程》在以讹传讹中未能辨析清楚作品真实的创作年代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教程》第九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把食指的《疯狗》一诗认定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创作的作品,而且作为一首代表作,引出对食指诗歌创作的论述:
……其著名作品有《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疯狗》等。他的诗歌一方面有一种基于对未来执拗真诚的信任的基础上的纯洁与清新,另一方面在这种单纯美好的信任被现实击碎之后,也写下了一代青年绝望辛酸的真实心态。前者如《相信未来》(引者注:此处引诗从略)……后者如《疯狗》中让人心灵颤栗的诗句(引者注:此处引诗亦从略)……食指的这两首诗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做底子,如《疯狗》是他失恋以后的作品,但这两首诗所表达的情绪,在当时的青年中很有普遍性,或者偏于前者,或者偏于后者,或者在不同的环境下这两种情绪都经历过,所以食指的诗在当时流传甚广。(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1~172、274、274、414、170、180、263、188、169、264-265、410、274、379、7~8、14页。)
事实上,食指的《疯狗》并非“文化大革命时期”创作的诗歌,它真实的创作年代应为1978年。它最初发表于“民刊”《今天》的第2期,1979年2月出版,对该诗评论的文字最早见于徐敬亚写于1979年12月的《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一文:“……生活实在是给了他们太多的鞭痕,太多的疑团,在黄沙迷茫中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信仰。请看一位著(引者注:“著”为“署”之误)名食指的青年诗人在七四年写的《疯狗》,辛酸的诗句真令人心灵颤栗——”“与其说这是他们在嘲讽自己发了疯的灵魂,不如说是在用愤怒的鞭子狠狠地抽打发了疯的年代。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们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诗正是四五诗歌浪潮的潜流。”(注:徐敬亚:《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引自1980年7月出版的《今天》第9期。该文原载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会自办的油印刊物《红叶》,1980年第2期,后收入徐敬亚著《崛起的诗群》一书,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徐敬亚的这些论述为后来许多论者当做对《疯狗》的经典阐释而不断被引述,尤其是在杨健著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引用过之后,对徐文的引述就变成了对杨著的转引。根据《教程》附录中所开列的主要参考书目推断,其许多史料出自杨著,《疯狗》在杨著中被标明是1974年所作,杨著对《疯狗》的评论基本是前述徐文的摘录。(注: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杨健在该书第94页说:“1974年郭路生其时已经精神崩溃,他写下了《疯狗》”,“恰巧这是一首能恰当形状当时知青心态的诗歌,或许这是一种巧合,但是却意味深长。到了1974年,一代青年人实在已经不堪压迫,失去了盲目‘相信未来’的勇气。”紧接着作者又援引了一大段徐敬亚对《疯狗》的评论。)而《教程》对《疯狗》的分析大致与杨著相同,另外,陈思和先生的论文《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在回答“我们的抽屉里究竟是什么”时,也理所当然地把《疯狗》放在了“文革的抽屉”里,作出这些分析:“以食指的诗为例,食指比较尖锐的诗是《疯狗》,这首诗歌是由作者个人的私生活的遭遇而起的辛酸之言,自然让人联想到时代的悲剧性……”(注:陈思和:《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载《文学评论》1999第6期。)这里除了把词句上的“恋爱”改为“私生活”之外,并无新论。同样的错误也出现在其他论著中,如杨鼎川著的《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此杨著对《疯狗》的解读简直就是彼杨(健)著的翻版。(注:杨鼎川:《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该著第185页中论及食指,曾说“1974年他写出了另一首很有影响的诗《疯狗》”,并且又从杨健著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中转引了徐敬亚对《疯狗》一诗的评论。杨鼎川书中对“文革时期”地下诗歌(包括食指诗歌、“白洋淀诗歌”)的引证、评论基本上是对杨健著作的重抄。)包括李扬先生一方面对“潜在写作”的研究思路表示怀疑,另一方面自己也并未弄清一些史实,所以也把食指的《疯狗》说成是曾在“文革”中广为流传。(注: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在该文的注释③中作者这样写道:“食指的几首代表作如《相信未来》、《命运》、《疯狗》、《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引者注:此处应为《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都曾在‘文革’中广为流传,这些作品从1979年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出现,1980年(引者注:此处应为1981年)《诗刊》1月号上正式发表了他的《相信未来》与《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其实,李杨先生提出对作品真实创作年代的辨认和对文学史语境的确定等问题,都是“潜在写作”研究面临的最重要也是最可争议的问题,然而,在对史料未能辨析清楚的时候,李杨先生的怀疑本身也值得怀疑。)
既然这首诗长期被多种著作误解为是“文革”作品,那么在此就有必要澄清一下事实。《疯狗》初刊于《今天》第2期上,当时诗末署的年代是“一九七四年”,这可能是其后各种版本以讹传讹之源头,殊不知,这与《今天》最初的办刊策略以及当时的现实需要有关。据芒克回忆当时的编辑方针是“尽可能发表‘文革’中的‘地下文学’作品。”(注:《时过境迁话〈今天〉——芒克访谈录》,引自《倾向》1997年夏总第9期。该文后收入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但略有删节。)与《疯狗》同时刊出的食指另两首诗歌《相信未来》与《命运》,确实在“文革”期间创作且流传,真正属于“文革”中的“地下文学”作品,刊出时并未署创作时间。《疯狗》实际创作于1978年,曾随着《今天》张贴于北京的西单民主墙上。(注:当时《今天》一方面以刊物形式出版,另一方面是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张贴发表。《疯狗》除在1979年2月随《今天》发表于“西单民主墙”上之外,另外,根据笔者2000年10月1日对李恒久先生的电话采访,李恒久先生回忆曾于1980年4月在“西单民主墙”上看到《疯狗》。)诗中涉及了一些敏感的问题,考虑到其时的现实氛围与现实环境,整个社会都处在对“文革”的全面否定中,为避免麻烦,把它署在“文革”中,相对保险一点。于是,《今天》编辑部(主要是北岛)有意把食指的《疯狗》署为“一九七四年”。(注:根据笔者2000年10月1日电话采访中林莽先生的回忆。林莽先生曾与食指谈过《疯狗》一诗的创作情况与《今天》的年代问题,食指证实是北岛为《疯狗》署了1974年的创作时间。)这件事食指本人后来也多次澄清。据食指回忆:“《疯狗》当然是写于1978年,只是具体哪一天记不清了。在《今天》发表时署了1974年,可能是因为他们(引者注:他们指《今天》编辑部)觉得这首诗作于1978年,当时‘四人帮’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再谈人权,再写人权,怕引起别人其他的想法。”(注:笔者在2000年4月与一些见证人、知情者与研究者(比如林莽、刘福春等先生)的访谈中,曾经证实了《疯狗》写于1978年的事实。2000年10月2日,笔者再次辗转委托食指的父亲去北京第三福利院看望食指时,代为询问食指本人《疯狗》的有关创作年代和《今天》年代署错的原因,此处即根据2000年10月2日食指的回忆。)
其实,在当事人与许多见证人目前都健在的情况下,通过查访、求证完全可以还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即使没有精力去寻访亲历者与旁观者等“活的见证”,就是从已有的文字资料中也可以找到许多有关《疯狗》真实创作时间以及创作初衷的“蛛丝马迹”。食指的好友林莽在《并未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说明“食指于1978年写出《疯狗》、《热爱生命》等好作品,它们标志着诗人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注:载《诗探索》1994年第2辑,该文后又收入《沉沦的圣殿》一书。)另外,谢冕在《20世纪中国新诗:1978~1989》文中把食指作为“属于开启新的一代诗潮的前卫性的诗人”。(注: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1978-1989》载《诗探索》1995年第2辑。)该文提及并引用了《疯狗》一诗,有意思的是,谢先生明知此诗为“文革后”作品,却仍在正文中按“文革中”作品做了阐释:“可悲的是,我还不如一条疯狗,我只能默默忍受那一切折磨而无法反抗。食指此诗作于1974年,是对于‘文革’经历的痛切反思而发出的悲愤的抗议。”(注: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1978-1989》载《诗探索》1995年第2辑。)更有意思的是,在该文注释④中又把这种年代错误纠正过来,使正文与注释之间成为自反的说明:“《疯狗》一诗,实写于1978年,首次在《今天》发出时,编者因多种原因改为1974年。”(注: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1978-1989》载《诗探索》1995年第2辑。)还有一个线索就是在《诗探索金库·食指卷》书后所附的“食指诗歌创作目录(现存部分)”中1974年与1975年中没有诗作,而《疯狗》一诗被置于“1978年”中,但并未选入这首诗。《疯狗》为何未被选入《食指卷》,李恒久曾说:“……如果一定说有‘舍取’,那就是舍掉了诗人80年代初期创作的一首诗《疯狗》,但那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是编者的意见。”(注:李恒久:《对〈质疑《相信未来》〉一文的质疑》,《黄河》2000年第3期。)从这段话中至少可以看出《疯狗》不是1974年的作品。至于此文把《疯狗》认作“80年代初期”创作的诗歌,是李恒久的一种推论,后来他已澄清此诗确是1978年所作。(注:根据笔者2000年10月1日电话采访中李恒久的回忆。李恒久于1980年4月在“西单民主墙”上看到食指的诗《疯狗》,1980年5月见到食指本人,就问起《疯狗》是什么时候写的,感觉写得不错。食指当时随口说了一句“刚写的”,李恒久未细问。因为他当时刚刚回京,还不知道《今天》已在1979年2月发表过此诗,就推测为80年代所作。他后来已经查实了此诗确切创作时间应为1978年初。)。而最让笔者奇怪的是《教程》中引用食指诗时又自言依据的是林莽、刘福春编的这本《食指卷》,不知何故,竟没有去读一读该书的序言和附录,也未做深入考证?澄清了这首诗的真实创作时间后,也就确立了这首诗的时代背景和创作语境,那么《教程》中对这首诗的分析就有点站不住脚了,那一大段评论恐怕也需要改写一下,尤其是“失恋”云云,其实,除《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之外,食指尚有《命运》、《鱼儿三部曲》(后改名为《鱼群三部曲》)等被确切认定为“文革”期间创作的诗歌代表作。
笔者认为,对于“潜在写作”而言,目前的首要任务并不是急于给它们定位、下结论,而是通过对史料、史实的继续搜集、甄别和认定,把“潜在写作”的研究引向深入。对于长期湮没在“地下”状态的“潜在写作”而言,“考古性”(不是福轲的知识考古学)的史料挖掘工作显得异常重要,尤其是“出土”史料的“辨伪”工作。“辨伪”最终是为了达到“求真”,“辨伪”工作可能比“辨真”更为重要。对史料进行深入细致地辨析,对历史真实面目的还原与澄清可能要比给历史随便下一个仓促的结论或评价要有价值得多,当然也更有难度。
二
《教程》写作者似乎对文学史的写作主观随意性较强而疏于史料的考证,所以文学史知识的很多叙述都出现漏洞,经不起推敲。比如,《教程》第十五章的注释⑤和注释③明显与史实不符。先说注释⑤,原文为“⑤参见北岛的《回答》,初刊于《今天》文学双月刊创刊号,其中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句。《纪念碑》则是江河的代表作,初刊于《诗刊》1980年10月号”。(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1~172、274、274、414、170、180、263、188、169、264-265、410、274、379、7~8、14页。)这里犯了一个史实错误。既然《教程》很强调作品的“初刊”时间,而且把“民刊”与国家公开出版物置于同等地位,那么对作品的初刊时间和所在刊物的挖掘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注释中北岛的《回答》初刊于《今天》创刊号上倒是对的,但江河的《纪念碑》显然不是初刊于《诗刊》1980年10月号,而是初刊于《今天》第3期的诗歌专号上,它是1979年4月1日出版。既然写作者知道北岛的《回答》初刊于《今天》创刊号,不知为何没有“顺便”查实一下江河的《纪念碑》就在时间距离并不遥远(仅相隔四个多月)的同一刊物的第3期上。
再来看注释③:“③《今天》杂志是由‘今天文学研究会’创办的一份民间文学双月刊。1978年12月23日创刊,到1980年12月底为止,共出刊物9期。另有《今天》文学丛书、《今天》文学研究会资料等出版。其主要编辑成员有北岛、芒克等。”(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1~172、274、274、414、170、180、263、188、169、264-265、410、274、379、7~8、14页。)从这一语焉不详的注释中明显可以推测出写作者对《今天》的有关史实并不熟悉。《今天》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只是一份由“身处民间”的文学爱好者自办发行的油印刊物,称之为“民刊”倒可以,因为“民刊”具有特定意义。但是注释中以下定义的方式堂而皇之地给《今天》加了“研究会”之名且定性为“民间文学双月刊”,这恐怕既抽掉了《今天》诞生与存在的特殊语境,也淡化了其办刊的艰难与作为“民刊”的价值,同时还会给许多“初学者”带来一些理解上的歧义。《今天》,它并非是由“今天文学研究会”创办,准确地说,是由“《今天》编辑部”创办。“今天文学研究会”于1980年10月23日召开筹备组会议,正式成立于1980年11月2日,其时,《今天》编辑部从1978年12月23日到1980年8月,已经出过了九期《今天》正刊和四种《今天》丛书。而“今天文学研究会”却是在《今天》停刊之后,为求继续生存而变通成立的,即把《今天》编辑部改为“今天文学研究会”,把《今天》改为《今天文学研究会文学资料》。芒克在《时过境迁话〈今天〉——芒克访谈录》中曾回忆道:“80年中,公安部门口头通知,《今天》必须停刊,否则一切后果自负。这其实已经不是‘通知’,而是‘勒令’了。我和北岛商量,考虑到对方态度极其强硬,如被封查会波及很多人,就同意了;但我们又想人不能散,交流活动不能停,应找到另一种形式,作为文学团体继续存在下去。于是变通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注:《时过境迁话〈今天〉——芒克访谈录》,引自《倾向》1997年夏总第9期。该文后收入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但略有删节。)实际上,由于某种特殊时代背景的关系,“《今天》编辑部”不能等同于“今天文学研究会”,《教程》显然把二者混同了。而“今天文学研究会”并未如《教程》所言创办了《今天》,它从筹备到自动解散,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也仅仅出了三期《资料》(包括《文学资料》之一、《内部交流资料》之二、之三),就于1980年底“无疾而终”了。对于《今天》的模糊认识,使得上述的注释③与该书第193页所提及的《今天》创办情况有所抵牾。我想,一本书尽管是多人合作,但对于常识是否应该有个统一的“说法”?
《教程》中这种“说法不一”、“自相矛盾”之处并不少见。如前文所述该著既然引用了林莽、刘福春选编的《诗探索金库·食指卷》一文,却无视写得清楚且事实确凿的一个“细节”:食指的出生地乃在山东,非在北京(注:参见林莽、刘福春选编:《诗探索金库·食指卷》书后所附的“食指(郭路生)生平年表”,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此年表写郭路生1948年11月21日出生于山东朝城,祖籍山东鱼台县程庄寨,并且对他的出生情况作了很详尽的说明:“母亲在行军路上分娩,当时正值初冬,天气很冷,母子被送到冀鲁豫军区的一所流动医院后才剪断脐带。故起名路生。”而且,年表中还提及郭路生的两个弟弟因分别出生于河南新乡与北京而各自取名为郭新生和郭京生。《教程》所谓郭路生出生于北京之说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在1953年郭路生正值5岁时才随父母工作调动迁居北京。)。而在《教程》“附录二”的“当代作家小资料”关于食指的“档案”中,(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1~172、274、274、414、170、180、263、188、169、264-265、410、274、379、7~8、14页。)想当然地给食指改为出生于北京。除了食指的出生地外,另有关于他的作品发表(出版)年代的错误。“1979年他的作品终于在《诗刊》上首次公开发表,引起各方关注。”“1992年,《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出版,引起较大反响。”事实是食指在《诗刊》上首次公开发表作品为1981年第1期,发表的是他的《我的最后的北京》与《相信未来》;而在1979年的时候,他的许多代表性作品是发表在“民刊”《今天》上,其中《相信未来》(外二首,包括《命运》、《疯狗》)刊于1979年2月出版的第2期,《鱼群三部曲》刊于1979年4月出版的第3期,《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即在《诗刊》发表时改为的《我的最后的北京》——引者注)刊于1979年6月20日出版的第4期,《烟》刊于1979年9月出版的第5期,《还是干脆忘掉她吧》、《酒》刊于1980年4月出版的第8期。可以说,在《诗刊》尚未正式发表食指作品的时候,《今天》已经使他引起了某种关注,另外,从“潜在写作”的角度看,《诗刊》发表的两首诗歌版本改动相当大,不能引为例证。而《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出版于1993年,而非1992年,这些史实在《教程》引用的《诗探索金库·食指卷》中均有线索说明。
还有,第九章第170页对穆旦这样表述:“他在‘文革后期’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创作了几十首杰作……”(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1~172、274、274、414、170、180、263、188、169、264-265、410、274、379、7~8、14页。)在第180页中再次有类似表述:“穆旦去世前给我们留下的几十首诗,现在看来,无疑属于‘文革’中的潜在写作中最优秀的诗歌之列。”(注:根据李方编:《穆旦诗全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确切地说,穆旦在“文革后期”创作了28首诗歌,其中1975年只有一首,其余是1976年所作,有些甚至已到了1976年底的创作,(注:这是陈思和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后记中对该书编写原则的一种自我定位。)而“28首”与“几十首”之间似乎还有些距离。如果一定要用模糊语言或“近似值”来表达,那也似乎应表述为“二十几首”或“近三十首”。如果说举此例是笔者的吹毛求疵,那么下面一例则的确让笔者颇费了一番思量。《教程》一个新颖之处是在书中附了许多图片,但在那帧:“诗人赵振开”的照片说明中,却令人费解。赵振开并不用他的本名发表诗歌,对赵振开似乎更应该定位为“诗人北岛”,是北岛以诗名、诗人闻世。把“诗人”与“赵振开”联系起来,多少有点不伦不类,这就相当于说“作家童忠贵”、“诗人龚佩瑜”、“写《随想录》时代的李尧棠”一样让人觉得别扭。我在猜想编写者这样表达的真意是什么?我宁愿认为这是一种“曲笔”,而非信手拈来之笔。
三
“潜在写作”的许多作品在最初写作、传抄及后来的发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字句的改动而引发一个“版本不一”的问题,这是最值得警惕之处,也是一些学者质疑“潜在写作”的主要原因。(注:比如李杨在《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一文中就“版本不一”现象对整个“潜在写作”的真实性和文学史意义提出怀疑,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所以要求研究者必须尽可能以最充分的依据,找到离创作真实最接近、最原始的版本,这样才能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才能切实为“潜在写作”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做出定位。由于对“潜在写作”中“版本不一”的现象缺乏足够的重视,《教程》对收入各种版本的作品未作比照、甄别和认定,致使具体作品的引证错误更多。这些错误或者是引用版本的不够“原始”而造成潜在作品的真实面貌无法还原,或者是不同章节和上下文之间引用、表述不一带来的“自相矛盾”,或者可能是“统稿”或“校对”的疏漏。其中,有些错误已与作品的原意背离,有些甚至还影响了对作品的理解和阐释。
《教程》引用食指的诗歌较多,出错也最多。比如第十五章引用了食指诗歌《命运》的一节,第一句就引成“我的理想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1~172、274、274、414、170、180、263、188、169、264-265、410、274、379、7~8、14页。)其中“理想”为“一生”之误。这首诗创作于1967年,初刊于1979年2月26日出版的《今天》第2期,这是比较可靠的原始版本,而《食指卷》对此诗做了字句的改动,尚不算这首诗最准确、最原始的版本。而从《教程》注释中可以看出《教程》参考过《沉沦的圣殿》和《食指卷》,这两本书中都有《命运》一诗,其中《沉沦的圣殿》第123页还引用了全诗的手写体,且与《今天》刊行时一字不差,均无“理想”之说。
《命运》的错误不算太多,出错最多的是食指的另两首流传颇广的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按照《教程》第九章的注释(16)所言:“《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原是地下手抄作品,初次发表于《今天》文学双月刊第4期,后被编入多种选本,本教材依据的是林莽、刘福春编《诗探索金库·食指卷》,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1~172、274、274、414、170、180、263、188、169、264-265、410、274、379、7~8、14页。)然而只要一对照,就可发现《教程》第182~183页所引用的诗句与《食指卷》并不相同,且不说整首诗的标点问题,单就字句而言,“一片手的波浪翻动”中“波浪”应为“海浪”,“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中”,“雄伟”应为“尖厉”,且引号应打在“鸣”之后。可见,它依据的不是这个版本;而对照《今天》,发现也不完全依照《今天》版。这就让人纳闷了,《教程》究竟依据的是哪个版本?抑或是各种版本的杂烩?这需要编写者来答疑。
《教程》分别在两处引用了《相信未来》一诗,错在两处所共同引用的第一节上。且不说两处所引均有字句错误,单就所引的同一首诗、同一节,却在同一本教材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版本:第172页是“我顽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第202页是“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看来“统稿”并不严谨。而这首诗的第一句应为“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教程》中两处引用都漏掉了“蜘”字。提出这样一个“小题大做”的问题,实在是因为这与诗人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食指的诗非常注重字数、行数、押韵,形式整饬,讲究格律,富有节奏感,擅长用四行一节、形式感很强的“黄金诗体”,所以有时一、二字句的增删往往会造成形式美的破坏。食指曾在《诗人谈诗》中说:“有人说,现代格律诗是豆腐块,我说是窗户,更准确地说是心灵的小窗,应是‘窗含西岭千秋雪’。”(注:《诗人谈诗》,载于“今天文学研究会”1980年10月23日出版的《文学资料之一》中。)他追求的正是一种“窗式美”。其实,只要写作者稍稍留意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引成“蛛网”、“顽强地”之后造成诗行的错乱不齐,已没有了形式上的“窗式美”,而且与对应的第二节中整齐的诗行也不相符合。《相信未来》这首诗在“文革”期间流传甚广,初刊于《今天》第2期,这是较早刊行、也较好的一个版本,后收入多种选本,有不少字句上的出入,错讹最大的是正式发表于《诗刊》1981年第1期上的。现在看来,较为原始、较能体现最早创作真实风貌的是李恒久回忆的《相信未来》。(注:李恒久:《郭路生和他的早期诗》,载《黄河》1997年第1期。后来李恒久又针对刘双发表在《黄河》2000年第1期上的《质疑对〈相信未来〉诗的诠释》一文,发表了《对〈质疑《相信未来》〉一文的质疑》,《黄河》2000年第3期,此文中再次抄录了《相信未来》这首诗。)李恒久是食指的好友,几乎是这首诗的第一见证人;另外,又根据笔者所查阅的林莽先生“文革”时期的诗抄本,所抄《相信未来》与李恒久回忆的相一致。而《教程》依据的似乎是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杨著引用的《相信未来》错讹相当多,其中就有“蛛网”、“顽强地”等词。
又如《教程》第9章引用根子的诗《三月与末日》和多多的诗《青春》,触目所及,是其中赫然写错的《三月和末日》,“与”、“和”尽管意思一样,但保持原貌岂不更好?姑且把这视为“校对”或“统稿”的疏忽,我宽容地想。但紧接着发现作品引用的以讹传讹不能不让人更加忧心。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它们又是从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中摘录过来的,既然杨著是《教程》的主要参考书,这就需要对杨著做一点“怀疑”了。毫无疑问,杨著对于“文革地下文学”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但书中史料的错讹、疏漏委实不少,而且书中所摘引的很多是第二手资料,再加上杨著本来就有“急就章”之嫌,(注:杨健曾在该著后记中说:“是在出版社催稿下,用4个月写成的,其中还包括钻图书馆、跑采访。在匆忙‘交卷’时,心中不免有些恍惚。”客观地说,作者所说的匆忙“交卷”不完全是自谦,而是一种诚实。)杨著实际上只是为这一研究打开了一扇门而已,真正的探访与深入研究应是后来者。作为高校的教材,《教程》可能在无形中将被权威化,按理应该是严谨审慎地选取、引用作品(尤其是“潜在写作”的作品),而不能仅凭第二手资料中的断句残篇就拿来并使之进入文学史。
根子的《三月与末日》正式发表的版本并不多,较为准确的版本是“《今天》创刊10周年纪念号”(1988年12月23日)与《倾向》1997年夏总第9期以及《中国知青诗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而多多的《青春》则是其《万象》集中的一首,较为准确的版本是多多的油印诗集《里程》(多多诗选1972~1988年)。上面提及的根子与多多诗的这些版本与杨著、《教程》均有字句、分行甚至意思的出入。所以,笔者建议编写者如果不能分辨其真伪的话,最好注明所引作品的版本,同时最好也注明其创作时间。创作时间的意义自不必说,版本的重要也不容忽视,版本的不同可能带来文本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给文本的“经典化”造成困难。而“潜在写作”在创作和发表之间往往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差,在此过程中,作者本人、见证与旁证在传抄与发表中出现的改动就引发了版本的不同一。除上述提到的诗人之外,还有如《教程》中所引黄翔的诗《野兽》,它在《在黎明的铜镜中》(谢冕、唐晓渡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就不同于《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纽约:天下华人出版社,1998年8月版)和《黄翔禁毁诗选》(台湾:明镜出版社,1999年5月版)。
还有些版本改动并不大,不属于“潜在写作”范围的诗歌,在引用时也常出现错漏。笔者想不到的是《教程》中居然把舒婷的诗《致橡树》(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1~172、274、274、414、170、180、263、188、169、264-265、410、274、379、7~8、14页。)与《一代人的呼声》(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1~172、274、274、414、170、180、263、188、169、264-265、410、274、379、7~8、14页。)也会引出错误。她的这些诗可以说是“朦胧诗”的名作,许多人(包括笔者)可以背得烂熟,一眼扫过去,感觉错得很“惊心”,读到错处,更是如鲠在喉。再如牛汉写于“文革”时期的诗歌《悼念一棵枫树》(1973年秋)在《教程》中引用时“枫树”被简化为“树”,成了《悼念一棵树》(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1~172、274、274、414、170、180、263、188、169、264-265、410、274、379、7~8、14页。)。在徐敬亚那篇著名文章《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1~172、274、274、414、170、180、263、188、169、264-265、410、274、379、7~8、14页。)的注释中,同一页码之下,两次注释,一为“我国”、一为“中国”。而作为《教程》“潜在写作”主要参考书目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置于《教程》“附录一”中的“本教材参考的主要书籍”时却变成了“形神兼似”的另一书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1~172、274、274、414、170、180、263、188、169、264-265、410、274、379、7~8、14页。)
作为一个刚入了门的读者和即将拿《教程》做参考教材的“教者”,也作为《教程》“潜在写作”研究方向的同道,我希望《教程》的编写者能对书中的错误做出校正,并且能再认真校读其他章节。如果真作为教材的话,也应给学生同时发一份“勘误表”,或者尽快出一个“修订版”。
标签:诗歌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相信未来论文; 陈思和论文; 回答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