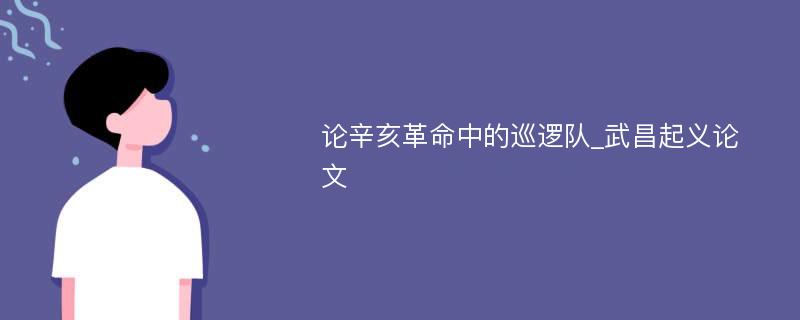
论辛亥革命中的巡防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巡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9)06-0016-08
晚清巡防队是清政府军政改革中存留的一种新旧混杂的军队,它的前身是防营和续备军等,一直存在到辛亥革命时期。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辛亥革命时期军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军上,且研究的模式过于单一①;对于辛亥革命中巡防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至今仍看不到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少数文章曾对辛亥革命中的防军进行研究,其研究模式过于强调防军在辛亥革命中的正面作用,忽略了它的负面作用,以及新旧军队的蜕变,而对于革命政府如何整合新旧军队等问题尚未涉及②。究其原因,防军和巡防队虽是清末两个不同时期的军队概念,但其间存在很多的关联,由于这种军队属于旧式军队的范畴,学术界对它们存在的意义存在怀疑,因而对它们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忽略的。
本文认为,辛亥革命中军事问题的研究存在更多的空间,而不应只注重研究新军问题,研究的模式不应过于单一,因此提出一些新的思考问题,诸如辛亥革命前巡防队是如何组建的,有何独特的制度;辛亥革命中巡防队是如何表现的,它的正作用大还是负作用大;革命军政府对于巡防队是如何进行整合的等等,希望能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来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的性质和作用,其意义应当是不可忽视的。本文的模式和意义不仅仅在于史实的构建,而更期望能发现辛亥革命中那些藏在史事背后的具有更大意义的历史规律。
文中希望达到的目标可能远不止此,史家著史的目标如果仅仅为史而来,也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站在民族和国家的高度来审视辛亥革命时期的巡防队和新军,可能会有非同一般的并与原有史学观点产生离异的新思索,因为它涉及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冲突与新式文化意识的构建问题,而这些又影响了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
一、巡防队的创建及其特点
清政府创建巡防队的背景并不复杂,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首先,当时各省的防军名目繁多,杂乱无章,错综复杂,影响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其次,新军创建的同时还面临诸多复杂的事情,中央政府令各省裁汰旧军(绿营兵额已议全裁),这样旧日的防军就面临生存危机,如何安置这些旧军成为清政府必须思考的一大问题;再次,清政府创建新军的目的是强军卫国,限期成镇,专供征调,不便零星驻防,而地方治安(巡缉奸宄、弹压地方)就成了守土疆臣必须考虑的一大问题,地方疆臣因此纷纷奏请酌留旧营以防内患,北京的练兵处也随机应变,奏请改编巡防队。这是巡防队得以创立的基础。
巡防队的队伍来源主要是防营和续备军。1905年练兵处奏请,因为各省防营名目错杂纷歧,拟令一律正式改名为巡防队,自第一营起次第排列,将零星队伍归并成营,随地分防,统一制度,并将原有营制逐渐改编。1906年,练兵处和兵部联合会奏将各省续备军一律改为巡防队③。1907年陆军部奏定巡防队营制。其营制主要有三部分内容:(1)规定各路统辖制度:先按该省各路编列号数,再按每路各营编列号数,设统领官1员,帮统官1员,书记官1员,执事官1员,司书生2名,马弁2名,护兵14名,伙夫2名;(2)规定步队营制:每营3哨(左中右),每哨8棚,每棚正兵9名,设管带官1员,哨官3员(每哨1员),哨长3员(每哨1员),什长24名(每棚1名),正兵216名(每棚9名),书记长1员,司书生5名,鼓号目1名,鼓号兵6名,护目1名,护兵16名(管带用4名,哨官哨长各用2名),伙夫24名(每棚1名),以上官弁兵夫共301员名;(3)规定马队营制:每营3哨(左中右),每哨4棚,每棚正兵9名,设管带官1员,哨官3员(每哨1员),哨长3员(每哨1员),什长12名(每棚1名),正兵108名(每棚9名),书记长1员,司书生5名,鼓号目1名,鼓号兵6名,护目1名,护兵16名,伙夫12名(每棚1名),马夫12名(每棚1名),马135匹(管带、帮带、正副哨官、什长、正兵、鼓号目兵、护目兵各一匹),以上官弁兵夫共189员名,马135匹④。
清政府对巡防队的改编从190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11年,各省根据中央政府的指令逐步完成了对巡防队的改编工作。各省情况不尽相同,下面分几个大区对各地巡防队的改编工作进行综述。
东北地区:黑龙江省将原有防营(中左右三路)按照新章改编为巡防队,划分五路,添设前后两路,统计马队16营,步队7营,共计23营,以马队每营189名、步队每营301名计算,估计人数为5131人。后又添练巡防马队5营、巡防游击马队1营、兵备处亲兵1哨。奉天省原有军队分奉盛两军,奉军不分旗民均可入伍,盛军由八旗官兵内挑练,1900年后奉军改练巡捕游击队,分赴各属,盛军所存无几,仅有步队两营。1906年后挑练奉天巡防队,计马步40营,分驻八路,另编新安军4营,盛军2营,总计马步46营,并开始练新军,编成陆军步队一标。不久即按照部章进行重编,分中前左右后五路,每路9营,步队21营,马队24营,共计45营,统名为奉天巡防队,总数为10857人。吉林省旧有军队共十军40营,名为捕盗队,1908年改编为五路巡防队,将原来的练军也编入其中,共计步队18营,马队15营,总数为8253人。热河原有三路防营15营,直隶练军8营,1906年开始改编巡防队,分四路设区,共15营,计步队8营,马队7营。1908年开始照部章进行整编,设中前左右后五路,增设营队,计步队11营,马队9营,共约20营,设统领,改编营制,总数为5012人⑤。
华北地区:直隶省由淮练巡防各营择要驻防,绿营基本裁撤,巡防队的改编工作基本上没有着手,淮练巡防各营全都暂时仍旧。河南省在1906年有新军步队一协和马炮队各二营;防军有正左右东南北等营以及原在绿营挑出的马步练军,这一年开始编练巡防队,原挑马兵练兵一律改为巡防队,分为左中右三路,共18营,计官弁兵夫共5157人,每月银5万余两,后来又进行改编,添募游击巡防队,到1909年全省巡防队共40营,包括步队28营和马队12营,总数为10696名。山东省原有移防长江的淮军、防营等,1907年后开始改编,建立巡防队,划分全省区域为五路,设步队38营,马队8营,每营240人,总数为11040人,中路巡防队设有炮队,计岁需薪饷银九十万四千余两⑥。
西北地区:山西省原存绿营防练各军曾改为常备续备等军,1906年将续备各营改为巡防队,分为中前后三路,原为马步22队,后添设驻省巡防队和归绥巡防队,共计24队,饷需40万,总计巡防队数量约为6000人。陕西省原有巡防九队,系由续备军改编,后又新练巡防一队,合成十队,每队305名。1907年后照部章改定,并将标营城守以及三镇各巡警军(2935人)一律改为巡防队,全省巡防队共计16队,每队301人,全省马步各队总数约为5600余人。新疆省主要将旧有各营旗一律改编为巡防队,分为五路,全省共设步队32营(每营301人),马队27营(每营181人),计马步共59营,人数为14639名,马3645匹,额外马夫171名,马594匹⑦。
西南地区:广西省于1906年将防营改为巡防队,分地编列,设有中路巡防队、左江巡防队、右江巡防队和边关巡防队,计边关巡防队1-16队、左江巡防队1-6队、右江巡防队1-2队,共24队,每队472人,另设长夫30名;新成立的中路巡防队6-7队、左江巡防队7-11队、右江巡防队3-15队,边关巡防队17-20队,共34队,每队301人,设长夫24名;中路巡防队1-5队留作编为新军;地方上还有一些亲兵营、工程队、保商营、抚标练兵营、卫队营等零星队伍,共8营。广西巡防队共有72队,后来照部章进行改编,分中左右前后五路,合计为67队,总数为20167人。云南省于1906年开始改编,开始时每营294人,随后照部章改为每营301人,计南防10营、西防11营、普防3营、江防5营、铁路巡防14营,按五路分防驻扎,共计43营,每年军饷为20万两,总数为12943人。贵州省原有防军额设20营零8队,包括原有的练军,1907年开始改编为巡防队,分东西南北中五路,每路分驻4营,共为20营,总数约为6000余人,并于四路各设统领一员、帮统一员,均归兵备处节制。四川省于1909年改编,照部章改订全省巡防队营制饷章,包括成都巡防营(3营),全省巡防队加上其他部分,约82营,每营300人,总数约为24600人⑧。
中部地区:江西省防营于1902年改编为常备一军、续备四军,每军5营,1903年将前军也改为常备军,1905年后将常备两军改为陆军步队一协两标,于是续备只有左右后三军,1906年后开始将续备三军改编为江西巡防队,陆续添募共18营,后又增加到20营,分四路驻扎,每路各5营,1909年又编成后路巡防队第21营,全省共计有巡防队21营,总数为6321人。安徽省将旧有防营20营改编为巡防队,中路为5营,南路为4营,北路为8营,共为17营,后又添募了5营,共计22营,总数为6622人。新军已练成混成一协。湖北省照部章将原有防军改编为巡防队,分设四路,有驻汉巡防队、江防巡防队(17营,5084人)、黄州巡防队(3营)、右路巡防队(4营)等,总数约为9000余人。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电请在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招募壮丁12500人,照武卫左军现行营制,编成25营,作为湖北巡防军,清政府拨款400万两。湖南省的各路巡防队由练军、保商缉私队等改编而来,南路有11营,中路有20营,加上其他三路共约30营,总数约为9000余人⑨。
东南地区:江苏省将原有防练各标一律改为巡防队,共33营,包括江宁巡防队、镇扬巡防队、江常巡防队、淞沪巡防队、淮徐巡防队,分为五路,按章改编,总数为9933人。福建省就原有的防练各营改编为巡防队16营,并划分全省区域为五路,权衡其地势而分配之,同时还将绿营中的精壮部分挑选出来,不足部分则通过招募选练,水师也改编为内河外海巡防队,原防营每营或370人,或263人,或754人,或614人,一律照章改为301员名,总数为4816人;水师巡防队为1806人。浙江省先改编浙洋水师巡防队,再将练军等改编为陆师巡防队;制定了浙洋水师巡防队章制表,建立水师巡防队,以三路分区,照表共编成11营,总数为3311人;其练军改编为巡防队,分左右中前后等五路,共计约9000余人⑩。
从上述改编情况来看,清政府的这次巡防队改编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其一,巡防队主要由原来的防军、练军、亲兵卫队、续备军、巡警等改编而来,个别省份因为不足额而采取招募的办法。各省情况不同,因地制宜,所以巡防队的来源比较复杂,并不一致,扩招的巡防队多半是由招募而来,如直隶古北口所添募的2营巡防队,系由当地土著合格者(多系制兵后裔,专恃食粮为业,此外别无生计)选充,按照新章认真编练的(11)。但一般省区所招募的巡防队并没有要求非从土著招募不可,一般符合条件就可以了。
其二,各省巡防队的人数并不一致,多的达到24600人,少的只有几千人,一般按前后中左右五路分区,将各路地段划定,以专责成,只有少数省份没有按照这种标准来划分,如奉天开始按八路进行分区,后来才改为五路分区的;热河开始也是按四路分区设巡防队,后来才改为五路分区;山西省是按三路分区设防的。
其三,巡防队的职责相当明确,专司捕盗、弹压地方,这是不是与巡警队的职责产生矛盾呢(12)?其实在当时中国巡警队还没有得到有效发展的情况下,巡防队恰好替代或者弥补了巡警队的功能和作用。巡防队与新军的职责也不一样,新建陆军专重国防,巡防队职在防乱,弹压地方,前者宜整,后者宜散,其制度和作用是明显不同的,所以在当时巡防队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其四,巡防队的营制方面,各省一般都按照部章办理,马队以189人为一营,步队以301人为一营,但也有例外的,如山东省的巡防队,马队步队都是以240人为一营。各省巡防队一般只有步队和马队,没有炮队,但也有例外的,如山东省中路巡防队就设有炮队一营;有的省甚至只设步队而没有设立马队,如广西、江西等省。
二、革命党人对巡防队的运动
革命党人在起义之初因为环境所迫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巡防队的运动上,因为他们无法在国内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只好把发动起义的力量寄托在民军、巡防队和新军身上,大都是运动略有成效后就举行起义,有成功的,但更多的是失败。从1908年的广州起义到1910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都可以看到党人运动巡防队的行动,党人很想联络巡防队和新军同时起义,因为事发匆忙,准备不足,结果均未如愿(13)。其实,革命党人对于巡防队的特征多少有所了解,巡防队军人所受的教育有限,知识程度不高,思想有些保守,但是人数较多,各省重要地段都有巡防队,所以不能忽视。革命党人在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李福林曾向孙中山建议,要求对巡防队、新军及民军同时加以注重,不可忽视任何一方。李福林说广东省城中的军队只有新军和巡防队两种,党人对于新军的运动有一定的成效,巡防队数量多,战斗力不强,但不可小视,如果能与其官长保持联络,那起义时他们会保持中立,不与革命党为敌,到时候率领民军数千,集中于城乡之间,很快就可以攻下城省(14)。孙中山对此表示赞同,但是孙中山并没有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从这一案例中可以知道,当时革命党人运动巡防队的最主要目标是让巡防队中的积极分子与新军同时起义,即便他们不能起义也要以中立姿态不与革命军为敌,尽量减少革命障碍。
革命党人中黄兴是较早关注要运动巡防队的人,也是有具体可行方案的人,他采用的办法是运动巡防队官长加入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黄兴回到国内考察国情,化名张守正,到桂林运动巡防队统领郭人漳,劝说他加入同盟会,寻机起义,郭人漳说与随营学堂总办蔡锷关系不好,难以进行。黄兴于是居间联络,先后运动了学堂教员雷飚、岳森、彭新民和学堂学生曾传范、贺斌、王德润、胡锟藩、杨锐锋、刘慕贤等,还运动了郭人漳及其手下官佐林虎、杨九如、卢子富、杨祖时等人,让他们加入同盟会(15)。其他革命党人对于巡防队的运动方式和方法更是多种多样,有的党人在陆军讲武堂毕业后直接进入巡防队当连长或排长、掌管一部分巡防队,有的党人直接运动巡防队中毕业于讲武堂的军人和官佐,有的党人以会党的身份运动巡防队中的会党官兵,有的党人直接用金钱来运动巡防队中失意的部分官兵,有的党人则通过其家族亲戚来运动巡防队官兵,通过种种努力,巡防队中“革命之空气浓矣”(16)。
1908年广州革命党人密谋起义,赵声以没有恢复新军标统职位,朱执信也以民军一时不能集合起来为借口,只能响应而不能发难,于是决定由邹鲁约谭馥率领巡防队作为发难的骨干,当严国丰派会党票于燕塘营中时,不慎而谋泄,结果谭馥、葛谦、严国丰等人先后被杀,其他一些党人也被捕,当时联络巡防队最得力的人是姚壁楼,谋泄后李准想惩治参加起义的巡防队员,“一搜营中有票者十之七八,乃大惧,寝其事,而防营之革命思潮,益为增进。”(17)1910年的广州黄花岗之役中,革命党人专门设立调度部负责联络军队,一方面注意联络新军,另一方面负责联络巡防队和民军,预期三方面联为一气,其中负责运动巡防队的主要干事是姚雨平,他运动巡防队时特别注意联络作为李准心腹的吴宗禹所统领的三营,姚雨平亲自与该营哨官温带雄、陈铺臣、范秀山等人商量起义大事,同时还运动了营中的一些士兵(18)。
两湖和西南的革命党人在密谋起义时对新军和巡防队都进行了关注和运动,对于巡防队的运动只是零星地暗地进行,并没有大范围公开的进行,但一直没有放弃。萍浏醴起义前,两湖革命党人在对新军和洪会运动的同时,还对巡防队进行了运动。由于新军多驻省会,比较集中,兵精械良,官佐都是学生出身,运动起来比较容易,而巡防队分散驻在各府县,官兵多有洪会中人,所以党人决定派洪会革命同志对巡防队进行游说,由蒋翊武、覃振、曹武等20余人负责运动新军,由彭邦栋、蔡绍南、张尧卿、周治华、龚春台、刘重、黄人障、邓玉林等20余人负责联络巡防队和布置会党,“一俟军队运动成熟,约于十二月清吏封印时举事”。后来,龚春台因为迫不及待,提前于10月19日发动起义,醴陵的巡防队士兵“亦反戈相应”。党人陈作新、李金山等在湖南省城运动新军的同时,徐鸿斌等人也在湖南巡防队中进行运动,“总计常备军巡防队共代表三十二人”(19)。在西南的贵州,1911年春夏之间,革命党人对于军界分新军、征兵营、巡抚部分和巡防队四大部分进行有计划的运动,“巡防队中路统领宋绍武,由关森、杨昌铭接洽之;帮统胡锦棠、管带和继圣,由徐宝煌、萧家煌劝诱之。”(20)
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对于巡防队的运动尽管不断展开和深入,但由于时间过短,党人意见不一,结果党人对巡防队的运动存在诸多缺陷:首先,党人对于巡防队的运动一般只局限在较小的区域范围内进行,主要集中在一些省城和重要地区。由于精力有限,党人力量不足,加上清政府防范极严,他们无法在大范围内对巡防队进行运动,即使在省城中革命党人也无法对省城的巡防队进行大范围的运动,同时对省城数营、十数营巡防队进行运动并有成效的并不多见。其次,党人对于省城之外的巡防队的运动几乎很少涉及,基本上是忽略的,因为巡防队主要驻扎在省城之外的地区,一旦省城有事,清政府很快就会派省城之外的巡防队进入省城镇压,致使革命党人所发动的起义大都没有成功。再次,党人对于巡防队的运动一般只注意其官佐,对于下层士兵则关注不多,这样,革命党人与巡防队士兵之间缺乏联系的纽带,巡防队对于革命党人的敌视也在所难免。最后,从党人对于巡防队的运动方式看,除黄兴等少数党人运动巡防队官兵加入同盟会外,其他党人一般是采用会党方式来运动巡防队,或者采用金钱方式来收买巡防队,双方联系的纽带并不稳固。总的来说,党人在运动巡防队时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不是很多,所以最后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运动巡防队成效不著,还有巡防队自身的原因。巡防队士兵思想落后,为人顽固不化,以利害关系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看到革命党人起义不能给自己带来利益,有的巡防队士兵往往事先答应,最后又临时退却,不响应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时先前被运动好的巡防队,因为种种原因“临时并不一往”,有的甚至与革命党人为敌,结果让革命党人得出一些新的结论:以事势论,巡防营新军不能反,虽有党人数百,亦难望占领广东,“巡防营不足信,而新军与教练之众则不能责以不来”(21)。广东省的革命党人更加不相信巡防队了。这种情况不光发生在广东,还发生在其它省份,如云南省,党人杨振鸿在云南蛮见等地运动巡防队,对象之一就是巡防队管带杨发生,杨表面上答应,但暗中又派人对杨振鸿进行追击;湖南省革命党人张桓也是因为巡防队士兵的告密而被捕入狱的(22)。
综上所述,在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对巡防队已经有了策划和运动,但并没有真正鼓动起来,只是对一小部分巡防队士兵灌输了一些反清革命思想。武昌起义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巡防队士兵加入到反清革命的队伍中来。
三、武昌起义后巡防队的表现
革命党人在两广等地屡次发动武装起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虽然运动了军队,但始终还是以党人为中心,其力量未能成熟,而两湖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一举成功,是因为他们以军队为中心,军人就是党人,其力量倍极坚强。湖北新军有一镇一混成协,他们在辛亥时期大都成为反清的革命集团,可是让人感到困惑的是,武昌起义时武汉的巡防队有1500余人,湖北的巡防队有9000余人,他们在武昌起义时采取什么态度和立场,巡防队的行动对武昌起义有作用吗?武昌首义后其他省份巡防队的表现又是如何?他们是否构成反清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湖北省的巡防队来源于原有防军,分设四路,有驻汉巡防队、江防巡防队(17营,5084人)、黄州巡防队(3营)、右路巡防队(4营)等,总数约为9000余人。驻汉巡防队为第一路,计5营共1500余人,武昌起义时,驻汉巡防队对于发动起义的新军并没有采取敌对的态度,而是采取中立的骑墙态度,“一刹那间,全城无站岗之兵矣。”(23)当武昌革命军分兵渡江攻取汉阳、汉口时,“汉阳之兵工厂,汉口之巡防队,亦一律服从”(24);“革命军占领武昌后,所到汉口、汉阳二处,无论何项防营勇丁,均倒戈欢迎”(25)。黄州的巡防队明显支持革命反清,他们成为当地革命起义的中坚力量,该队的革命同志徐得贵、姚得胜、夏星午、黄厚钦等人与从武汉赶到黄州的党人李长庚、黄巨川、黄楚楠等一起密谋光复黄州的办法,决定于夜间发动兵变,知府琦璋、知县潘涌捷、统标张绍绪出逃,“虽鸣枪并未击毙一人,黄州于是光复矣。”(26)襄阳巡防队与湖北新军马队第八标第三营联合策划反正,起义后襄阳巡防队和宜城巡防队都改编为新军(27)。由此可见,新军是武昌首义的中坚力量,而巡防队也成为武昌首义的重要成员之一。
武昌首义后不久,全国有14个省区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独立的各省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除党人的努力和新军的发难等因素外,巡防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相当大。各省巡防队的表现虽然不一,但大部分都站在革命队伍一边,同情革命,举兵反正,或者持中立态势作壁上观,不与起义新军为敌,这种态势大大推进了独立省份反清革命事业的发展。武昌起义后各省巡防队的反应不一,表现各异,情况虽然不同,但独立省区的巡防队都有所行动,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参加了这场革命,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最激进的巡防队,他们在起义之前已经被革命党人有所运动,与党人有所联系,届时一起起义或响应,属于这种情况的省份有湖南、广东、甘肃、浙江、广西等。湖南省的革命党人比较激进,1911年5月党人陈作新、焦达峰、徐鸿斌等人对长沙的新军和巡防队进行了运动,武昌新军起义后,焦达峰于同年10月22日率领新军起义,进攻长沙小吴门,陈作新进攻北门,巡防队因为事先受到运动,并不与起义军为敌,起义军“遇巡防军,即操白布绾臂,皆笑受之”(28)。当时长沙的巡防队有2000人左右,发难的新军只有600人,如果巡防队没有受到运动而与革命党为敌,革命很难成功,“湘之反正,全在兵与下级军官之力。”(29)甘肃省在独立之前,省城的巡防队2000多人,已经被党人周昆和黎兆枚运动成熟,所以起义比较顺利,没有受到很大的挫折(30)。浙江省党人先运动新军,再运动巡防队等,其步、马、炮、工、辎各兵士,由下士运动之,下士由下级将校运动之,雷家驹运动执事官吴茂林并运动游击队管带金富有、省防哨官董国祥入会,并由俞炜派钱寿彭运动军装局哨官厉得胜、吴远等人,“于是省中巡防队,赞成举义者大半矣。”(31)广西省革命党人李德三活动相当得力,1911年1月31日南宁城新旧军人约同时起义,当时旧军驻青山塔,离城30里,有一哨官不肯同谋,众人杀之,拟于夜间占军械局,入城起义,最后事败。及武昌起义,党人各就地方举义,清巡抚沈秉堃见状,知大势已去,便于11月6日与谘议局等要人议决独立,次日宣布(32)。
第二种情况是巡防队在事先没有受到革命党人的运动,与革命党人联系很少,但受到种族思想的影响,看到新军首先发难起义,也顺势而为,自觉地响应革命起义,有的是临时被革命党人鼓动而起义的,属于这种情况的省份有四川、陕西、江西、江苏等省。如四川省,1911年9月17日,邓子完、曹笃、方潮珍等人率领数万民军起义,分三路进攻自流井、贡井等地,这些都是巡防队重点防守之区,所以党人不得不对防守的巡防队进行临时鼓动,晓以大义,巡防队很快就不与革命军为敌,其他地方如重庆、泸州、万县等地的巡防队也大都不与革命党为敌,有的“密约待命”,有的“袖缠白号章响应”,有的直接反正起义,乐至的300多巡防队也归附革命,商会士绅想推巡防队统领李湛阳为都督,被李推辞;川东巡防营水道巡警及炮队皆袖缠白号章以应;沪州的巡防队自己独立,建川南军政府;四川自宣布自治后,巡防军麇集省城,同志军就抚而来者亦众(33)。再如陕西省,武昌起义后,河南大侠王天纵密议党人到陕西鼓动革命,湖北革命党人也同时到达陕西,于是新军首先发难,巡防队响应起义,“蜂拥入省垣”,西安的新军只有一混成协,巡防队共有5营,响应起义的巡防队有3营半(34)。上海光复时,巡警总部管带陈汉钦先占总局,系民军总司令李燮和所派,民军很快得到沪军营,当时城内各官逃避无踪,城墙各处即悬白旗,商团、巡警左手均缠白布,包括吴淞炮台及防营水师、盐捕营、警察局等,均未与起义军为难。上海是全国重镇,自吴淞到南市都有巡防队分驻,戒备森严,商团乃区区之众,能有如此胜算,如果没有巡防队从中帮助,是很难成功的。当时驻吴淞炮台的姜台长,驻巡防营的梁营长,“咸湖北武备学堂学生,与李公有素,事先李公驰往劝谕,允不为抗;驻军营与高昌庙为赴制造局必经之地,驻有防营,悉由商团团员分往漩说其营长,劝毋助逆”;“驻沪巡防营管带章豹文、巡防水师营管带王楚雄,李燮和因陈汉钦招之,皆就款,反为民劳”;结果殉义者仅一人,负伤者也只有数人(35)。江西省光复时,“城守巡防水师各军,概悬白旗,手围白布”,“人心甚安”,到省的各属防营也“袖缠白布以表同情”(36)。
第三种情况是巡防队军官和旧的巡抚或督抚一起合作,共谋独立或反正,以响应周边独立的省区,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广西、江苏等省。湖南独立后,谭延闿分电周边各省,派员运动,当时派往广西的是罗松涛等人,广西巡抚沈秉堃是湖南善化人,新军协统赵恒惕是衡山人,已被说通反正,广西巡防队归藩司王芝祥掌握,王是北方人,相当勇猛,也逐渐被说通,广西遂于11月7日宣布独立,沈秉堃为都督,王芝祥为副都督(37)。江苏苏州光复时,新军马队、步队、工程队、辎重队先后进城,类皆袖缀白布,闾门及各处城关一律派兵驻守,一面巡防营,一面民军,各城墙高悬白旗(38)。
第四种情况是有些省区的巡防队在辛亥革命发生时没有什么表现,或者干脆与起义的革命队伍为敌,或者进行动乱,或者自然归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山西、云南、贵州、江苏、安徽等省区。云南省举义时,蔡锷率新军兵分三路向省城进攻,城内的巡防队及镇署卫兵进行顽强抵抗,双方展开激烈的冲突,巡防队兵力占优,机关枪发射尤其猛烈,结果新军死者50余人,伤者40余人;云南开化的巡防队在夜间进行叛变抢劫(39)。贵州省自创办新式学校后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逐渐流传,武昌起义后,11月5日新军举义,以新军及陆军小学堂学生入城,并率法政学生拥张百麟到城内谘议局,组织临时军政府,先攻军械局,巡抚沈瑜庆命胡景棠率巡防队到城外攻陆军小学堂及固守市街要地,一些卫兵最后醒觉,卫兵队长彭尔锟说,若为土匪,均应出战,今起义者为谘议局员、军人、学生,如何出战?最后双方停战,宣布独立,令各州县服从。在此之前,贵州省城新军不足一标,党人已分路进行运动,巡防队中路分统宋绍武部下为一路,自治社员涂宝煌等人已有所运动,但收效不是很大,光复后五路巡防队没有变化,贵州宣布独立当天,新军、巡防队、陆军小学堂学生排队入城,保护藩库、火药局,改谘议局为军政府(40)。江苏省巡抚程德全在士绅的决议下宣布独立,巡防队和民军负责守各处城关,秋毫无犯,保全地方治安,免致生灵涂炭,而巡防队和民军起到了共保治安的作用;而江宁的巡防队也“允不抗拒”,但江防营是张勋的部下,“谓得手后任伊等掳掠三日”(41)。安徽省新军大队进攻省城时,江防巡防等营登城,互相攻击,新军不能入城,不久新军工程营、辎重队、炮营、陆军步队六十三标全体解散(42)。
巡防队可贵之处还在于反正后服从军政府的派遣前往湖北与清军作战,这方面湖南省的巡防队表现最为突出。虽说湘军恃功而骄,但当武昌告急时,王隆中即以四十九标各营添募巡防兵编为湘军第一协出援,当时黄光为汉阳总司令,隆中会战七昼夜不休,部下多伤亡;巡防队管带刘玉堂以所部及巡防三营编为湘军第一镇第二协到湖北援助,大战而亡;中路巡防队管带甘兴典率所部及新募兵组成第二镇第三协,刘耀武率新募兵组成湘军独立标,同赴湖北战地,这些都体现出湖南巡防队优异的一面(43)。当时凡湖南练军经过王隆中等人组编成军作为援助湖北之师,新军及中左右三路巡防队较精锐者也都出发开赴湖北,而后路巡防13营经张其锽的训练,号有纪律,并以此为基础组成南武军,人数超过5000,其军事编制全如防营,其器械多德国新式,有机关枪8挺,野炮6尊,器械比较完备,当时湘军中有野炮的并不多,南武军也在随后开赴湖北监利、沔阳等地(44)。当然其它省的巡防队没有如此出色。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中,独立省区的巡防队大都有所表现,在起义的队伍中,巡防队虽然没有新军积极和出色,但已经构成了反清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起义队伍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对反清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四、辛亥革命时期巡防队的负作用
凡事都有两个方面,我们固然要肯定巡防队在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诚如当时人所描述的,“当省垣光复时,新军及巡防队军士,在事出力者,不知凡几”(45),但也要指出巡防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消积作用。由于独立省区的军政府对于巡防队的整合不甚得力,也没有十分有效的整改措施,造成巡防队在光复后存在越来越多的隐忧和后患。
由于起义后各省军政府对于参加起义及反正的军队缺乏更多的制度建设,物质上的奖励也不能有效地给予提供,一旦军饷供给稍不如意,就会引发巡防队军士的极大不满和反对,甚至引发动乱。巡防队在事发过后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趁机进行抢劫,扰乱地方治安,影响地方秩序,甚至因此引发更大的争斗和动乱,这种情况在很多省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陕西新军进城起义时,仓卒间只注意军装局和满城,不暇他顾,巡防队遂趁机进行抢劫,而新军军弁也羡之而效尤,城内无业游民及回坊之黠者,亦与之为奸,“城内无法安静,盐店街被害尤甚”,天成享一家失去现银约十万余,居民颇受损失(46)。有的省区巡防队在开始时与民军为敌,扰乱治安,川黔巡防兵数千,东迎西击,扰攘不堪,到11月22日重庆独立后战事始息,“民团死伤者以万计,巡防军数千亦所余无几,而居民之被防军杀戮者劫夺者,更不可胜计矣”(47)。贵州省起义后五路巡防队照旧,哥老会党也编入军队,曾经讨平修文等地的土匪和抚定平越叛兵,立功颇著,但是“部卒驻省者或恃功不法,扰及平民,辄捕治不稍假借”,军人治省,导致此后贵州省十多年的惨无天日(48)。在湖南,“初一日湖南之变实由余诚格、萧良臣所激而起,鄂乱起即令缴子弹军械,余、萧皆疑新军有变,此时学生数十人首先发动,新军首先攻城,巡防营即闭城掳抢,黄忠浩出而排解,防营遂击死之,余抚遂逃,新军破城入与防营大激战,自晨至暮,屠戮烧杀无所不至。”(49)
没有响应起义的巡防队更是从中进行骚乱活动,成为杀害革命志士的凶手,而新军中的一些不轨人士也以此作为自己权力争斗的阶梯。这种情况在湖南省表现得最为典型,巡防统领黄忠浩在新军起义时因为忠于清政府,焦达峰将他杀害。焦达峰成为都督、陈作新成为副都督后,谘议局绅士把持湘政,事无大小,需经他们议决,都督之命不行,谭人凤力主解散他们所创的议事机关,集权于都督,阴谋极为险恶,对人说:焦、陈的死期不远了。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二营管带梅馨根本看不起焦、陈,对人说:“焦非元帅,陈酒疯也”。该标参谋刘邦骥和镇统余钦骥也不喜欢焦、陈所为,焦并不重视五十标,梅召开军事秘密会议,要杀焦、陈,没有人敢回答,余钦翼说:“兹事体大,请不赞成,亦不反对。”梅得到默认后大胆展开猎杀焦、陈的活动。10月31日,焦达峰召集各营长及政学诸人士到谘议局,禁止军人带武器入会,谭人凤、谭延闿等人也出席,会完后梅馨侦知焦达峰返府,陈作新往北门,便兵分二队,以吴家铨领一队到府杀焦达峰,以袁富荣领一队到北门杀陈作新于途。焦、陈两个都督都死于乱刀之下,身首异处,落了个悲惨的下场。焦、陈能力有限,没有拥兵自卫,最后遭到谘议局绅士和一些军官的暗算,人心的阴险和毒辣由此可见一斑,这都是因为军队起义造成的可悲结果(50)。
军人把持地方,掌控局面,为所欲为,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及以后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巡防队与新军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甚至引发地方动乱与不安。这一问题的发生固然由于军队本身的因素,也由于独立省区军政府对旧军整治措施不得力的原因。湖南起义后不久,新军与巡防队时有龃龉,大起暴动,几至开战。湖南中路巡防营统领陈斌生是黄忠浩的旧部,怀疑黄忠浩被杀是护演团杨任主持,便与驻常德新军管带陈书田捕获在常德开会演说的杨任等7人,将他们杀害,剖其心以祭黄忠浩。当时有人说,如果梅馨不杀焦、陈,陈斌生定会举兵进攻省城,大局不堪设想。
新旧军队之间的冲突和争斗问题在独立省区中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有的省区越演越烈,最终成为社会的一大问题。如江宁城内外原有新旧两军,旧军为江北防营和江宁巡防队等,由张勋、赵曾鹏分别率领,新军为第九镇,由徐绍桢统领,“两军时相倾轧,各不相下”,武昌事起,张勋派人侦察新军动静,并到军营谋刺徐绍桢,徐大怒,与南京城内党员谋内外夹击张军,以图光复,士绅商民揭白旗于市(51)。南京11月7日民军起事,当时张勋派兵到处纵火抢劫,肆行残杀,城内积尸道左,惨不忍睹,张勋部下见有白手帕、白腰带及白帽结者均杀,以为是革命党人,见有发长或新剃头者也杀,以为是监狱中的逃犯,铁良也认为其人道绝灭,派旗兵出来镇压,于是防营和旗兵又大起冲突(52)。
总而言之,军队起义,在起义各省都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后果。新军整体素质略高一些,但新军在各省并不能完全掌控局面,巡防队在各省中的实力依然相当大,他们的整体素质较低,军政府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会起而反之,军人的势力太大,军政府又没有很好的整合措施,造成极其不好的社会后果。巡防队在独立的省区中,大都经过军政府一定程度的改编,有的改名为国民军(云南等省),更正服装礼节,有的改编为新军(如湖南等省),有的改编为陆军,有的改编为敢死队,有的省区并没有对巡防队进行改编,而是让他们仍旧在各地驻守服务。独立各省都面临一个大问题,由于经费困难,不得不对扩充后的军队进行裁编,巡防队最终也成了裁编的对象,裁减后军员的再就业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造成了极大的社会隐患。
五、结语
通过考察辛亥革命时期巡防队的表现,发现已往的研究中军队在辛亥革命中的强大表现及其作用明显地被人为地压制了,其作用也被压小了,而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作用明显地被放大了,说明近代中国史研究中“史实的理顺与重建”依然显得相当的重要,我们不能用自我所欲的史学目标来任意修改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性质,历史的本来真相是改变不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革命党人所鼓动的由军队、学生联合发动的旨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军队暴动或兵变,独立省区的军政民政全都由发动起义的军人所主持,军人主政,军政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民政事业则大受压抑,“军阀”的态势逐渐形成,大有不可遏阻之势。这次革命的主体是军队和学生,军队包括新军、巡防队、巡警和旧式的杂项军队,学生也是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的目标是就是“反满”,旨在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所谓的汉人政权,在独立的14个省区中,基本都是这种情况,商人和资产阶级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这次革命,但他们不是革命的发动者和主力军,不是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建立的军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军人,新政府的政治构架基本上是参议、军政、参谋、军务、司法、内政、教育等部门,在反正的州县地方政权中,旧式的文武官衙照常供职,并没有很大的性质改变,新式政权民主的建设依然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地方自治”的色彩更加浓厚了。
军队暴动意味着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意识的强烈挑战,自古到今,中国传统文化构成要素中,军队必须服务于国家政府,听从政府命令,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近代以来的军人教育和民众教育都是这样灌输的,但是这种文化理念在辛亥革命时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严重的背离,只要政府腐败,陷国家于危险,置生民于涂炭,不能引领国家前进了,军人就有理由起来暴动推翻其统治,建立新的法治政权,这种新的文化意识在辛亥革命时期得到了新生和进一步的培植,民国新生政府对于这种意识又进一步地强化了,最后造成了军阀政治的悲惨结局,影响了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注释:
①陈旭麓、劳绍华:《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上册,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79-296页;熊志勇:《新军与辛亥革命论略》,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303页。
②刘凤翰:《辛亥革命前后全国军事蜕变》,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上册,第140-189页;李英铨:《清末防军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10-224页。
③④刘锦藻撰:《皇朝续文献通考》卷222,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685-9686、9687页。
⑤⑥刘锦藻撰:《皇朝续文献通考》卷223,第9694,9703,9690,9696、9701-9703页。
⑦刘锦藻撰:《皇朝续文献通考》卷222,第9686-9690页。
⑧⑨⑩(11)刘锦藻撰:《皇朝续文献通考》卷223,第9699-9703、9693-9703、9688-9702、9702页。
(12)当时科布多参赞大臣溥纲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在奏折中明确指出,科布多的街市商铺仅数十家,现有的巡警队官兵分布于城乡街市,昼夜巡查,足资弹压,与巡防队的职责产生冲突,因此无须再添巡防队,清廷允其所请。《皇朝续文献通考》卷222,第9693页。
(13)(14)(15)(16)(17)(18)(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198、282、197、194,260、285-296、553页。
(20)(2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第443、221页。
(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册,第234-236页。
(23)《中国革命日记》卷上,第3页,见《满清稗史》,中国书店1987年影印本。
(24)《各省独立史别裁》第2页,见《满清稗史》;《武昌失守前因后果》,《国光新闻报》九月五日,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第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80页。
(2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5册,第177页。
(26)《黄州光复》,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页;郭孝成:《鄂省各属光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5册,第242页。
(27)《回忆马队的革命活动》,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第170页。
(28)(30)(3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第55、132、165,7-10页。
(29)子虚子:《湘事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第158页。
(31)邹鲁:《浙江光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7册,第131页。
(32)邹鲁:《广西光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7册,第219-221页。
(34)《各省独立史别裁》第11页,见《满清稗史》。
(35)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135、152-153、201页。
(36)《赣省光复史》,《时报》九月二十一日,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第1册,第421-422页;郭孝成:《江西光复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第381-382页。
(37)(43)(44)子虚子:《湘事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第157、159-160、163页。
(38)《苏州光复记》,《时报》九月十六日,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第1册,第337-338页。
(39)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第223-226页。
(40)邹鲁:《贵州光复》,冯自由:《辛亥革命贵州光复纪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第396-398、401页;《贵州独立》,《中国报》十月十六日,见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第1册,第421-422页。
(41)郭孝成:《江苏光复纪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7册,第1-2、11页。
(42)郭孝成:《安徽光复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7册,第173-174页。
(45)郭孝成:《湖南光复纪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第143页。
(46)郭希仁:《从戎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第69页。
(47)郭孝成:《四川光复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第11页。
(48)冯自由:《辛亥革命贵州光复纪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第402-405页。
(49)《追志湘省变情》,《北方日报》九月十四日,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第1册,第326页。
(50)邹鲁:《湖南光复》,郭孝成:《湖南光复纪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第133-134、153页。
(51)杨啸天:《参加第九镇南京起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7册,第77页。
(52)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第1册,第498-499页。
标签:武昌起义论文; 湖北新军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清代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新军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八国联军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