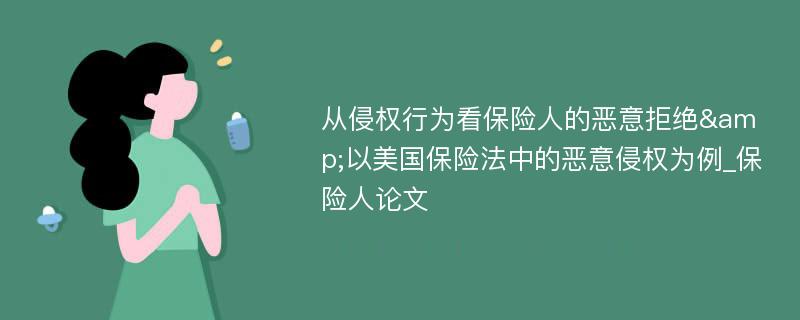
从侵权角度看保险人的恶意拒赔——以美国保险法中的恶意侵权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恶意论文,保险法论文,保险人论文,为例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43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4)03-0018-10 按照传统的保险法理论,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建立起了契约关系,当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以弥补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失。在这种理论之下,保险人恶意拒付或者拖延支付保险金的情况时,被保险人只能通过合同路径来实现自我救济,对于保险人的恶意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为了进一步保护被保险人在与保险公司交易中的利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多数州法院在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原则之下,在传统的合同原理之外构建了一种诉讼理由,人们一般将这种诉讼理由称之为“恶意诉讼理由”。①在这种情况下,保险人除了要承担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责任外,往往还要为被保险人的一些合同外的损失负责。 在中国,被保险人“理赔难”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保险业,如何突破“投保容易理赔难”的怪圈将是中国保险业进一步发展所必然面临的问题。通常而言,保险人拒绝对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或者拖延赔付,后文统称为拒赔)都会有一定的“理由”,这些理由主要包括“免责条款的认定(效力)”、“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和“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等。对于合同框架下的争议自然只能适用合同的相关法理解决,但是,对于那些“理由”明显不成立,被保险人的拒赔是恶意的,按照合同的原理进行处理,被保险人至多只能是挽回了本应所得的合同利益,对于保险人的恶意只能任其“逍遥法外”,法律的惩罚和预防功能无法得以彰显。从理论支撑和现实可能性角度出发,在现有法律制度下,要为解决保险“理赔难”找到新突破口,一方面既要强化保险行为的规范性,另一方面,就是要对保险人的恶意行为进行必要规制。而对美国法上的保险人的恶意侵权的研究,对我国如何解决类似问题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对传统的突破:从合同责任到侵权责任 (一)传统的保险人责任 传统的保险法理论认为,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是合同关系,保险人的拒付行为是对合同义务的违反,是合同责任的体现。从被保险人的角度看,于损失发生后进行给付无疑是保险人最重要的义务。给付义务具有深厚的合同法渊源——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明确承诺,一旦损失发生,自己就会进行给付。②长期以来,美国法院遵循着Hadley v.Baxendale案所确立的普通法规则,③即违反合同的损失应当限定在交易确定之时。作为一般规则,直接损失(由于行为人的非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作为侵权法的调整范围内而非合同法,但一方对合同的违反并不为侵权法所规制,即使是恶意地违反合同。④换句话说,保险人的拒付行为,无论其是有合理理由还是恶意的,其仅须承担赔偿保险合同订立时所能预见的责任。 有激进论者甚至认为,合同当事人拥有违反合同的“权利”,只要他们做好了赔偿对方当事人的合同损失的准备。⑤这也就是学界所谓的效率违约理论,按照该理论,在有些情况下,如果一方的违约收益将超过他方履约的预期收益,并且对预期收益的损害赔偿是有限的,那就有违约的激励了,存在这种激励是应该的。⑥效率违约理论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从社会利益的角度看,一方当事人选择违约而赔偿对方的合同损失,其结果是更好地实现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但是,效率违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陷入了行为结果论的泥淖之中,完全从结果的视角来审视行为的价值,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对基本契约精神的背离。如果当事人可以随意违约,则会造成当事人对合同利益期待的不确定性及合同关系的不稳定性,这对合同制度和交易秩序无疑会是一种不小的冲击。 通常有效保险合同的双方都享有自己的合同权利,但也需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如果一方没有合法的理由而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即为违约。对此当事人可以诉诸法院,法院可以依法强制执行或判决违约方执行原合同条件,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遭受损失的受害方予以补偿。⑦据此,在传统的保险法理论上,保险人拒付的责任基础在于有效的契约,它属于合同法的当然范畴。 (二)合同之外的责任:独立的侵权责任 在保险人恶意侵权属于合同领域还是侵权领域的问题上,美国的法院对此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一些法院认为,恶意诉讼理由的基础是合同的默示约定,在决定恶意诉讼理由属于合同还是侵权问题上,应当保持一致性,因此,恶意诉讼理由本身也属于合同领域。有些法院则认为,“善意和公平地进行交易”的默示约定仅仅是确定保险人义务的基础,他们的结论是,关于恶意诉讼理由属于侵权领域。⑧ 随着保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自加利福尼亚州的Gruenberg v.Aetna Insurance Co.案后的20年间,⑨美国已有至少24个州的法院趋向于认为保险人可能会对被保险人(或信托人)合同之外的损失按照侵权的理论承担责任。⑩也就是说,保险人恶意拒付的行为可能构成侵权责任而受到侵权法的规制。保险人的这种责任,其源头是一条古老的合同法原则,即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一种默示约定——双方当事人必须善意而公平地进行交易,任何一方应当留意不得阻碍对方当事人获得合同利益,且不应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方利益之上。根据《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31节的规定:“每一份合同都课以当事人在合同的确定与履行中应善意而公平进行交易的义务”,这项义务为法定义务,无论当事人在合同中是否有约定,它们都应当得到当事人的遵守。 被保险人可以对保险人提起恶意侵权的诉讼,但问题依然存在:并非保险人的所有拒赔都会构成侵权,那么,保险人的拒付行为具备什么要素或事实才构成对被保险人的侵权呢?一般而言,提起一个恶意侵权之诉,被保险人应当证明保险人的拒赔缺乏合理的理由且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拒赔缺乏合理的理由。(11)德州最高法院在Aranda v.Insurance Co.案中进一步明确了违背善意与公平交易义务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1.保险人拒绝赔付缺乏合理的基础;2.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拒绝赔付行为没有合理基础;3.保险人缺乏善意,并存在保险事故损害外的其他损害;4.损害与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12)从以上的构成要件中不难看出,法院在认定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时,遵循了侵权的基本原理,即行为——损害——过错——因果关系的逻辑架构。自此,其后的法院在认定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时基本上按照这种理路展开。 在保险人恶意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中,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保险人的拒赔缺乏合理的基础,这里的“合理”应当如何理解?所谓合理,即合乎道理或者事理,也就是一个理性人对于某事在案件的背景之下通常出现的结果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具体到保险关系中则表现为,保险人对拒绝赔付缺乏适度、合法的理由或者可争辩的理由。法院于此首先排除了关于保险合同本身的争议适用该法理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当事人的争议系属对合同的效力以及对合同的解释等,就只能按照合同法的相关法理解决问题。1981年,俄克拉荷马州最高法院在McCorkle v.Great Atlantic Insurance Co.案中陈述道:(13)“恶意的故意侵权……是保险人不合理的,恶意的行为……”“如果存在明显的证据表明保险人的行为是不合理的,至于什么是合理则由事实裁判者决定……”(14)在这里,法院将关于“合理”的认定交给了陪审团,并没有给出相应的主客观标准。直至1991年的Buzzard v.Farmers Insurance Co.案,(15)俄克拉荷马州法院才转向于用“一般产业政策”来判断保险人的行为(拒赔)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因此而形成恶意。不难看出,保险人的拒赔行为是否存在合理的理由,得结合具体的情形加以判断,而不能一概而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保险人一开始时对被保险人的拒赔并没有合理有效的理由,直到后来才发现了合理的理由,此时,被保险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独立的侵权责任?对此,德州最高法院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Republic Insurance v.Stoker案中,(16)德州最高法院认为,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索赔的拒绝,如果拒绝时没有有效的理由,即便在其后发现了有效的拒赔理由,保险人也应当承担恶意侵权责任。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认定,其实并不难理解,保险人的恶意在法律上应当受到非难,强调了恶意侵权的责任构成性,即一旦符合责任的构成要件,责任就不可逆地产生。 其次,关于保险人“恶意”的认定。美国保险法中的“恶意(Bad faith)”一般又可理解为不诚信,大致相当于侵权法上的“故意(Intention)”,只不过前者更加凸显出当事人对契约的违背,表达对行为人失信行为的谴责,而后者多指行为人不仅希望而且确信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某种后果的心理状态,其范围更为广泛。威斯康星州是最早在保险合同的违约之中提出恶意概念的州之一。(17)1931年的Hilker v.Western Automobile Insurance Co.案中,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认为,考虑到保险公司对保险关系中各种因素的控制性,这些因素往往会影响到被保险人责任的确定,因此,诚信地履行义务,就要求保险公司如同理性人对待自己的事务那样对待被保险人的事务,尽到相应的注意和勤勉义务。(18)这里法院从恶意(Bad faith)的相对面——善意(Good faith)来说明问题。20年后,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开始在第一方保险和第三方保险中形成并扩展“恶意”原则。(19)在Crisci v.Security Insurance Co.案中,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将该责任认定为善意而公平进行交易的默示约定责任。(20)法院认为,当保险人没有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对索赔进行处理,保险人对善意而公平地进行交易的责任的违反构成独立的侵权责任。其后,审理Brown v.Guarantee Insurance Company案的法院指明了恶意的实用解释不应当是什么,在确定什么是确切的恶意时,法院列出了八个因素供参考。其他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广泛地引用了这些因素。(21) 1978年,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在审理Anderson v.Continental Insurance Company案时,为确定保险人的“恶意”设定了客观的标准。根据法院的认定:“要证明保险人的恶意,原告必须证明被告否决其索赔缺乏合理的基础,且被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很明显,恶意侵权是故意的,而不可能被界定为过失。‘恶意’应当被界定为‘欺诈、表里不一、不诚信’”。(22)这实际上指明了恶意的基本表现形式。 《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将侵权行为区分为故意行为、莽撞行为和过失行为。根据该法,区分莽撞行为和故意行为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对其行为所产生结果的确定性的认识。故意和莽撞行为都含有一定的故意性,但是故意仅仅表现为行为人知道或者实质性确定地知道其行为将产生损害。如果行为人知道或者从其行为中应当知道其行为具有产生损害的极高可能性,而非实质性地确定,此时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即为莽撞。正如前文所言,保险人的恶意侵权属于故意侵权的范畴。据此,我们可以归纳出恶意认定的两个基本标准,一是从客观上看行为人是否有悖于善意而公平地进行交易的责任的行为,二是从主观上看行为人对此是否属于“明知而为之”。总之,恶意是故意的,而非过失;恶意也是具有欺诈性的且是不诚信的。 二、革新与发展:保险人恶意侵权责任简史 (一)第三方保险中的恶意侵权责任 关于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早期判例一贯支持的观点是,被保险人对和解与否享有绝对自由的权利。例如,纽约州法院在Auerbach v.Maryland Cos.Co.案中表述道:“如果保险人自己愿意给予自己机会的话,保单中没有任何能够使保险人承担和解义务的因素”;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在Long v.Union Indemnity Co.案中进一步提出:“一个保险公司有权处理他人对保险公司的被保险人提出的诉讼。这样的方式可以最好地实现保险公司的利益。”(23)他们的结论是当被保险人的利益与保险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保险人甚至无需考虑被保险人的利益。 保险人拒绝赔付的恶意侵权责任滥觞于加利福尼亚州,其概念最早见于加利福尼亚州关于第三方索赔的案件中。(24)在Brown v.Guarantee Ins.Co.案中,加利福尼亚州第二区上诉法院第一次运用善意与公平交易的默示约定原则创造了一个特别的诉讼理由,即被保险人可以以保险人在拒绝第三方的和解时未能考虑被保险人的利益为由对保险人提起诉讼。(25)第三人在侵权诉讼中要求被保险人赔偿15000美元,随后又提出以作为保单限额的5000美元进行和解,保险人在案件中提出抗辩并拒绝和解,甚至没有将和解要约的信息通知被保险人。在该案之中,法院注意到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不对保险人科以强制的负担,使其在决定诉讼的保单限额内和解问题时考虑被保险人的利益,则保险人会自由地投机,不顾被保险人在保单限额外承担多少责任;如果保险人考虑被保险人利益的义务过重,就会出现被保险人要求保险人接受第三方原告提出的不合理、甚至是欺诈的和解要约,否则保险人就会受到被保险人的起诉,并在诉讼中遭受更大的惩罚。据此,法院认为:“尽管保险公司在处理这类情况时有权考虑其利益,但是它没有权利因此牺牲被保险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必须是……善意地考虑了被保险人利益的。”(26) 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进一步扩展了Brown v.Guarantee Ins.Co.案中建立的诚信善意责任原则,保险人不仅在和解与诉讼之中应当善意,在否认保险(项目)和拒绝参与被保险人的抗辩中也应当保持善意。(27)在Comunale v.Trader's & General Ins.Co.案中,保险人证明了其拒绝处理并坚持为自己辩护——政策并没有提供这样的保险(项目)。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并不认可这样的辩护,认为:“否认保险(项目)的保险人这样做必然要风险自负,并且,尽管也许其行为并非毫无根据,如果发现这种否认是错误的,保险人就应当承担其违约给被保险人造成的损害的全额赔偿责任……”(28)在Crici v.Security Ins.Co.案中,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减轻了恶意拒绝(和解)案件的举证责任。法院将这种标准陈述为“在政策限制外,是否为一个谨慎的保险人能接受的和解提议”。(29) 通过以上判决,第三方保险中的恶意侵权责任逐渐得到多数州的认可,它在保险诉讼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紧随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演进,恶意侵权责任逐渐由第三方保险渗透到第一方保险中,责任的外延得到了进一步扩展。 (二)恶意侵权责任向第一方保险的扩张 在保险法领域,1973年的Gruenberg v.Aetna Insurance Co.案将保险人恶意侵权推向全盛期,该判决代表着商业诉讼的一个新纪元——并不仅仅局限于保险业,对合同的任何当事人来说都具有潜在的影响。(30) 1973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作出了一个标志性的判决—Gruenberg v.Aetna Insurance Co.案判决。(31)在决定利益是否应属于火灾险政策所保护时,法院重申了这样的原则,即在所有的保险合同中都存在一个善意而公平交易的默示约定,并再次强调如下规则——对契约的违反可能导致侵权责任的产生。(32)法院认为保险人在处理第三人对被保险人索赔时善意而公平交易的责任与被保险人自己索赔时善意而公平交易的责任,实际上“仅仅是同一责任的两个不同方面”,(33)法院这样论述这一责任:“善意而公平交易为法定责任,科以保险人该责任是为了使其不恶意或没有合理理由地威胁或实际扣留保险金,否则被保险人因为政策所享受的利益将被剥夺,进而遭受损害。” Gruenberg案法院在处理第一方索赔保险人的责任时,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标准——“当保险人不合理地、恶意地扣留索赔的保险金时……它应当对此负有责任……”(34)事实上,该案仍然留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保险人行为的性质是什么,它为何承担惩罚性赔偿。(35)随即,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在另一个案件——Silberg v.California Life Ins.Co.案中解决了第一方索赔时的惩罚性赔偿问题,该案显示,主张惩罚性赔偿除了证明保险人是恶意外,还需证明如下因素的存在:故意使被保险人烦恼、受伤害或者受压抑,也即保险人除了拒绝给付保险金外,还故意使被保险人处于额外的不利益状态。关于保险人恶意侵权的惩罚性赔偿问题,后文将有相应的介绍,于此不再赘述。 加利福尼亚州的判决发展了保险人恶意侵权责任的两个重要原则:1.在第一方保险和第三方保险案件之中,保险人的行为都应接受合理标准的衡量;2.损害赔偿包括保险人不合理行为造成的补偿性赔偿,也包括其他有证据表明的惩罚性赔偿。 如果说加利福尼亚州创立了第一方保险中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那么威斯康星州则是对该责任的继承与发展。在Gruenberg案判决后5年,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紧随加利福尼亚州的步伐,在Anderson v.Continental Insurance Company案中采用了第一方保险的恶意侵权责任。威斯康星州法院进一步澄清、拓展并且牢固地建立起了这一新的侵权责任。(36)Anderson案的法院在确定第一方恶意侵权行为属于侵权领域还是合同领域上显然要比Gruenberg的法院果断得多:“通过衡量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责任因此而产生,对该责任的违反构成独立的侵权责任而无关乎合同的损害”。(37) Anderson案的重要意义不容忽视,除了如前文所述的为“恶意”的认定提供了客观标准以及明确了恶意侵权的法域外,它还指明了第一方保险的恶意侵权行为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问题(后文将有相关论述)。在该判决后,美国法院的司法判例成功地指明了什么是“恶意”及其构成,进而使恶意侵权责任能够很快地在第一方保险中被采纳。 尽管每个州都认识到了第三方索赔中保险人的善意义务,(38)然而,第一方保险中各州法院对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却持有不尽相同的态度,有支持者如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但多数州法院对此持谨慎态度——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保险人的这种恶意行为,多数判决选择搁置该问题并拒绝认可第一方保险中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39)例如,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在D'Ambrosio v.Pennsylvania Nat'l Mut.Casualty Ins.Co.案中,把对第一方保险中独立恶意侵权责任的确认交给了议会。对此,法院的理由是如果要在这些案件中适用该补偿,它应当由立法机关予以实施。“无疑,它应当由立法机关进行宣示……联邦的公共政策约束着保险公司的条例……由立法机关决定是否需要由在法案之外创立的制裁以阻止那些不够谨慎的行为是公平的”。(40)从而,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否定了第一方保险中的恶意侵权责任。 (三)小结 从发展史上看,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首先见诸于第三方保险,其后发展至第一方保险。美国多数州的法院已经认可其为与合同责任不同的独立的侵权责任,但各州法院的态度在第三方保险和第一方保险上又所有不同。通常,第三方保险的恶意侵权责任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认可,但对于第一方保险的恶意侵权责任,各州则出现了不同的态度,加利福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等已经在判例中确立了第一方保险的恶意侵权责任,而宾夕法尼亚州等则对此持否定态度。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基于善意与公平交易的原则,是平衡保险法律关系当事人利益的结果,要求当事人善意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在追求自己利益时也应当给予对方利益以必要的考量。 从保险人恶意侵权责任的发展趋势来看,其未来的发展是值得期待的。 三、边际的界定:保险人恶意侵权的责任范围 既然保险人可能因其恶意而承担独立的侵权责任,那么,该责任是什么样的责任,其范围又当如何,也即应当如何对被保险人进行救济? 毋庸置疑,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在责任的承担上遵循着一般侵权责任的基本原理,其主要以补偿被侵害人所遭受的损失为主,但并不局限于此,在特定情形下,行为人可能会被处以惩罚性赔偿;在责任形式上,以财产责任为主并辅之以如赔礼道歉等其他责任形式。具体到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上,我们不难看出,该责任以恢复被保险人因保险人的恶意拒赔而遭受的保险金损失和其他损害为目的,在法定情形下并给予保险人以一定的处罚,其责任形式也主要为财产责任。 保险人恶意侵权责任从构成上看具有重合性,它既符合违约的构成要件,也成立违约之外的独立侵权责任,法院的判决之所以从侵权的角度来对其进行界定无外乎两点考虑:其一,更加强调法律对行为人恶意的非难,既实现法的矫正功能亦实现其教育警示作用;其二,恶意侵权的责任范围更为广泛,它不仅包括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所应得到的保险金,还包括因保险人的恶意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律师费用,甚至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此点也正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展开论述的。通常而言,保险人恶意侵权的责任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保险金 在保险人的恶意侵权中,保险人需要赔偿的基本部分是已经为保险人拒赔的保险金额,这也是被保险人的基本诉求,是保险人责任最为基础的部分,无论是在第一方保险还是第三方保险中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保险人可以以保险人违反保险合同为理由而提起诉讼,但是,以恶意侵权为诉由通常具有更大的好处,例如,到期的分期偿付方面,如果保险人恶意拒绝赔付分期支付的早期金部分,保险人应当对未到期的保险金部分一并予以赔付,但是,倘若以违反合同起诉,未到期的部分就不能获得赔偿。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即持此观点。也就是说,因为保险人的恶意而涤除了保险金赔付的一些限制性条件,保险人的抗辩因此而受到限制。 (二)律师费 在美国,按照律师费的一般规则,侵权诉讼中律师费不能作为补偿得以恢复。在恶意侵权责任产生之前,只有当保险人在第三方原告对被保险人的诉讼中不正当地拒绝抗辩,被保险人才能要求保险人赔偿律师费用,赔偿的范围也仅限于被保险人用于抗辩第三方原告提起诉讼的律师费用。但是,随着保险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这一情形逐渐得到了改变。最早对此作出确认的是伊利诺斯州1937年的《保险法案》,根据该法案第155节的规定,在保险人恶意拒绝赔付第一方索赔时,法院可以允许被保险人主张不超过500美元的合理律师费用。1967年该法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这主要表现在律师费的标准得到了完善,只要不超过以下标准即可:1.法院或陪审团发现的该方有权抗辩保险公司花费的所有费用的25%;2.1000美元;3.超过法院或陪审团发现的该方有权抗辩保险公司花费的所有费用的,超过部分即为保险公司行为前用于处理索赔的费用。(41) 另外,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在Brandt v.Superior Court(Cal.1985)一案中作出裁决,解决了加利福尼亚地区法院之间对律师费用处理不一致的情况。(42)根据该裁决,如果保险人恶意拒绝被保险人的正当保险金请求,被保险人为了使保险人赔付保险金,被迫聘请律师提供合理的服务,那么可以将一定数量的合理律师费作为保险人侵权行为直接造成的损害,要求保险人予以赔付。 法院也指出,只有当被保险人能够证明保险人是出于恶意拒付保险金时,比如在解释保单或制定法时出于恶意,才能由保险人赔付律师费。保险人出于错误拒付保险金的情况下,则不能由保险人赔偿律师费。当然,被保险人所能获得的律师费不应当取决于保险人过错的程度,(43)且应被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也即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就正当保险金争议进行谈判时所花费的合理律师费。 (三)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是保险人恶意侵权的又一重要责任内容,被保险人的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是由于保险人的恶意拒赔造成的。按照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原理,被保险人只有证明了这种精神痛苦是严重的,并且伴有其他可证明的损害,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尽管早期的判例也有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分析,但是直至加利福尼亚州的两个判例,即Comunale v.Traders & General Insurance Co.案和Crisci v.Scurity Insurance Co.案才对其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通过对案件和先例的分析,法院最终得出结论:当恶劣行为导致其他损害时,精神损害赔偿是可以被请求的。另外,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在Gruenberg v.Aetna Insurance Co.案中也支持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44) 因为恶意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在第三方保险和第一方保险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首先,第三方保险中恶意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尽管第三方保险的恶意常以多种方式呈现出侵权的表象,但是其精神损害赔偿扮演的角色却要比第一方保险中的小得多。(45)这或许是因为法院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一个公平清晰的保险人行为准则,且保险人明白违背该准则的后果。这样,精神损害似乎显得没有必要了。如前所述,仅当保险人在政策限定的范围内不合理地拒绝和解时才产生。无疑,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遭受精神损害的风险是可以预见的,他们在因保险人的行为遭受经济损失后,往往要承受极大的不便和焦虑,当精神痛苦达到一定程度时,精神损害由此而产生。 其次,第一方保险恶意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第一方保险的精神损害赔偿可见诸于Anderson v.Continental Insurance Company案中。在其后的案件之中,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被更好地建立起来,其基本原则是保险人缺乏合理理由而拒绝赔付,该行为是以让人难以接受的方式做出,并造成了被保险人极大的精神痛苦。(46)其与第三方保险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保险人直接对被保险人做出的行为引起,发生的可能更大。 当然,也有法院拒绝承认保险恶意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密西根州最高法院在Kewin v.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案中拒绝认可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法院认为政策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商业”,违约并不必然地导致精神损害。(47)但即便是这些否认精神损害赔偿的法院,仍然认可了恶意侵权责任的两个功能——提供更多的补偿和允许从直接经济损失中恢复过来,从而决定何为不当行为。 (四)惩罚性赔偿 最后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恶意情况下的惩罚性赔偿问题。在前文的相关案例中,笔者已经谈及惩罚性赔偿的问题,Gruenberg v.Aetna Insurance Co.案开始了对惩罚性赔偿的关注,但是并没有最终确立下来,Silberg v.California Life Ins.Co.案解决了第一方索赔中的惩罚性赔偿问题,并提出了惩罚性赔偿的使用条件。惩罚性赔偿因制定法而产生并受制于制定法,由于各州制定法不同,惩罚性赔偿的证明要求也不同。假如原告能够满足法定的证明责任,那么,无论在第三方保险还是在第一方保险的情况下,都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在Neal v.Farmer's Ins.Exchange(Cal.1978)一案中就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提出了三个需要考虑的标准:1.保险人行为的可被谴责程度;2.采用补偿性赔偿方法计算出来的实际损害;3.为了确定对保险人课以多大数额的惩罚性赔偿足以威慑保险,还需要了解保险人的财产总额。(48) 另外,在评判惩罚性赔偿金的适合程度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了一种谨慎介入的方式。在TXO Productions Corp.v.Alliance Resources Corp.(S.Ct.1993)一案中,法院拒绝保险人要求法院介入案件的请求,情况是惩罚性赔偿以巨大的差额超过补偿性赔偿,或者该数额超过了该司法辖区内任何其他惩罚性赔偿。在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时,法院支持陪审团考虑被告对原告的不公平行为,而不支持陪审团考虑诉讼理由涉及的直接主题以及被告的财富水平。(49)其后,法院重新审视了惩罚性赔偿的“度”的问题,认为惩罚性赔偿应受到政策的限制,不应当“非常过度”。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一般都需要比较谨慎,它的目的并不在于填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而是对行为人进行惩罚,因此,它常常与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有着密切的联系。通常,惩罚性赔偿在两种情况下得以适用:(50)一是如果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是怀着恶意的动机作为时,惩罚性赔偿可以适用;二是如果保险人暗含着强烈的不良心态,即便事实上没有表现出来,也有可能适用惩罚性赔偿。 综上所述,被保险人所能获得的赔偿范围因保险人行为的严重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保险金作为最基本的赔偿部分,无疑应当获得赔偿。当保险人以最恶劣的方式作为时,赔偿的范围包括惩罚性赔偿,但是该赔偿会受到保险人的恶意程度的影响;被保险人因保险人的极端行为而遭受严重的精神痛苦的,此时,精神损害赔偿也纳入到了损害赔偿的范围内。另外,被保险人为抗辩保险人的恶意支出的合理的律师费,也应当作为赔偿的范围予以考虑。 四、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在我国,“投保容易理赔难”一直是保险业的难点所在,也是社会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中国保险业的发展也因此而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美国保险法上的恶意侵权责任将保险人恶意拒赔行为责任认定为独立的侵权责任,在责任范围上远远超出合同责任,既保障了保险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对保险人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在一定意义上遏制了保险人的恶意拒赔行为。并且,保险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行业,树立、强化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心对保险业的长远健康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美国保险法上的恶意侵权责任对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理赔难,从其表现形式上看既包括理赔程序繁琐和无正当理由拒赔,也包括无正当理由的拖赔。首先,从立法上看,我国2009年修改的《保险法》第22—25条规定了被保险人理赔的相关问题:第22条是关于提供索赔损失证明资料义务的规定,第23条规定了保险人核定理赔程序,第24条规定了保险人拒赔通知义务程序期限,第25条则是关于保险人先行赔付的规定。应当说,2009年的《保险法》相较于原《保险法》在保险理赔上要进步得多,基本上确立了保险理赔的程序、要求等,从立法上限制了保险人的不当拒赔行为。但问题依然是存在的,例如,第22条规定了保险人的“及时一次性通知义务”,但并没有规定违反该义务的法律后果,这将会降低该条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51)本条义务设置的目的在于提高理赔效率,避免出现保险人反复让投保人补充提供材料、拖延理赔的情况,如果只规定义务,而无违反义务的责任,那么义务就会流于虚设。再如,第23条关于核定期限的规定,《保险法》仍然没有明确规定保险人不在法定期限内核定或者赔付的,投保人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似乎持这样的态度:对于保险人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核定的,应允许被保险人、受益人进行选择,即要求保险人在一定期限内作出核定,或者直接诉请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52) 其次,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法院在处理保险人拒赔案件时,都以保险合同为依据、在合同的框架之下来解决问题,保险人的责任始终被限定在合同责任的范围之内。这样做的一个重大弊端是忽视了对保险人行为的主观心态的考虑,也即无论保险人的拒赔或者拖赔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都不影响其最后责任的承担。固然,那些因为保险合同本身的争议或者有其他合理理由的拒赔不可冠之以侵权之名,但对于那些怀揣恶意的保险人再以同样的标准对待他们,恐怕就有所不妥了。 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本质上就是一个司法实践选择的问题,它在我国的适用是完全可能的,与我国当前的法制环境并不冲突。从构成上看,它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也符合合同责任的构成要件,至于适用侵权法还是合同法来对其进行规制只不过是一个选择的结果。就我国而言,一方面,《侵权责任法》具体地规定了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只要在要素上具有符合性,即可构成侵权责任,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在构成上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是相一致的;另一方面,《合同法》第122条确立了责任竞合时的处理方式,即当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竞合时,受害方有权选择要求行为人承担合同责任或侵权责任。概言之,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适用于我国并没有法律上的障碍。 此外,从保险业本身的长远发展来看,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的逐渐适用并不会对其造成根本性的冲击。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既有其有利之处也有其弊端存在,恶意侵权责任也不例外。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的确立并逐步适用,短期来看可能会加重保险人的负担,进而影响到保险业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它却是必要的,因为它制止了保险人恶意的不当拒赔行为,能够刺激社会公众对保险业树立更大的信心,参与到保险中来,从而使保险业更加良性地发展。 总之,针对我国现实中诸多的保险人恶意拒付保险金的案例,我们应转变固有的思维模式,在立法和司法中逐渐引入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从侵权的角度对保险人的恶意拒赔行为进行调整,这既不需要耗费巨大的立法成本,也不会对现有体制造成过分的冲击,而且也是促使保险业逐步走出“投保容易理赔难”怪圈的有益探索。 在本文的研究中复旦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李应同学做了许多工作,特此感谢。 ①[美]约翰·F.道宾:《美国保险法》,梁鹏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 ②[美]小罗伯特·H.瑞杰、道格拉斯·R.里士满:《美国保险法精解》,李之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页。 ③案情参见http://www.lawnix.com/cases/hadley-baxendale.html. ④See Roger C.Henderson,The tort of bad faith in first-party insurance transactions:Refining the standard of culpability and reformulating the remedies by statue,University of Michigan Journal of Law Reform,Fall 1992. ⑤前引④。 ⑥参见孙良国:《效率违约理论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 ⑦参见齐瑞宗、肖志立编著:《美国保险法律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⑧前引①,第273页。 ⑨案情参见https://www.quimbee.com/cases/gruenberg-v-aetna-insurance-co. ⑩See Roger C.Henderson,The tort of bad faith in first-party insurance transactions after two decades,Arizona Law Review,Vo1.37,1995. (11)See Tom Baker,Insurance Law and Policy,second edition,Aspen Publishers 2008,p.109. (12)See Jay D.Reeve,Judicial tort reform:Bad faith can not be predicated upon the denial of a claim for an invalid reason if a valid reason is later show,Texas Tech Law review,Vol.27,1996. (13)See 1981 OK 128,637,P.583. (14)See Andrew Kernan,A Tarnished Golden Rule—Why Badillo v.Mid Century Insurance Co.Demands Further Clarification from the Oklahoma Supreme Court Regarding the Tort of Bad Faith,Oklahoma Law Review,Vol.59:183,2006. (15)See 1991 OK 127,824,P.1105. (16)903 S.W.2d at 339.前引(12)。 (17)See Hilker v.Western Auto.Ins.Co.,231 N.W.257,259-60(Wis.1930),aff'd on reh'g,235 N.W.413(Wis 1931). (18)前引(16)。 (19)See Douglas R.Richmond,Truly "Extracontractual" Liability:Insurer Bad Faith in the Absence of Coverage,29 TORT & INS.L.J.740,742(1994). (20)See Crisci v.Security Ins.Co.,426 P.2d 173,176-78(Cal.1967); 前引(16)。 (21)这主要适用于第三方保险,判断恶意的八项因素为:(1)受害请求权人案子的有效性建立在责任或损害存在争议的基础之上;(2)保险人试图引诱被保险人进行和解;(3)保险人未能适当调查案件情况,以便查明对被保险人的证据;(4)保险人拒绝听取其自己的律师或代理人的建议;(5)保险人未能就第三人的和解要约通知被保险人;(6)加入拒绝和解,每一方当事人都要面临一定数量的财务风险;(7)被保险人在事实上误导了保险人,因此造成保险人拒绝和解要约,被保险人对此存在主观过错;(8)任何其他倾向于否定或肯定保险人恶意的因素。(前引①,第270页。)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个单独的因素都不能自动得出恶意的结论,提出这些因素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这些因素的考察得出恶意的结论。 (22)Id at 376.Quoting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471(1969). (23)前引①,第268页。 (24)See supra note 1. (25)155 Cal.App.2d 679,319 P.2d 69(1957).Quoting Thomas J.Verticchio,Bad Faith Refusal of Insurance Companies to Pay First Party Benefits —Time for the Illinois Supreme Court to Recognize the Tort and Resulting Punitive Damages. (26)Id.At 686,319,P.74. (27)Comunale v.Trader's & General Ins.Co.,50 Cal.2d 654,328 P.2d 198(1958). (28)Id.at 660,328,P.202; 前(25)。 (29)前引(25)。 (30)See Peter Kendall Glazer,Insurance—The "Full Bloom" Tort of Bad Faith Remains in the Bud,Oregon Law Review,Vol.57,1978. (31)案情如下:Gruenberg(原告)拥有一家餐馆,并就该餐馆向Aetna公司(被告)投保35000美元的火灾险。1969年11月9日餐馆发生火灾,翌日,保险公司派出调查员赴火灾现场进行调查,但是餐馆火灾的确切原因并没有查明,保险人就此作出陈述,认为被保险人就其餐馆获得超额的火灾险,并暗示被保险人故意纵火以骗取保险金,被保险人因此而被指控纵火罪。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保险人拒绝与保险公司谈论火灾问题,指控最终被驳回。随即,被保险人Gruenberg向加利福尼亚州法院提起诉讼,宣称保险人违反了在餐馆的火灾中善意地考虑其利益的默示义务。(参见https://www.quimbee.com/cases/gruenberg—v-aetna-insurance-co.) (32)Id.at 1037.前引④。 (33)See Gruenberg,510,P.1037. (34)前引(33)。 (35)See Gruenberg.9 Cal.3d at 575,510,P.1038,108 Cal.Rptr.at 486(Quoting Fletcher v.Western Nat'l Life Ins.Co.,10 Cal.App.3d 367,401,89 Cal.Rptr.78,93(1970)).自Gruenberg案后,保险恶意侵权的惩罚性赔偿问题被引入到讨论之中,对此,在后文之中将有相关论述。 (36)See C.Christopher Hasson & Michael F.Nerone,The 1990 Pennsylvania Auto Insurance Law:An Analysis of “Bad Faith ” and the “Limited Tort Option”,The Pennsylvania Issue,Vol.29:619,1990-1991. (37)Anderson,271 NW2d at 374.前引⑥。 (38)See 1978 DEF.RESEARCH INST.INC.,INSURANCE LAW—INSURER'S DUTY TO DEFEND,Annotated Bibliography,60—64.前引(25)。 (39)前引(25)。 (40)Id.at 508,431 A.2d at 970.前引(25)。 (41)ILL.REV.STAT.ch.73,Ⅱ767(1937).前引(25)。 (42)前引①,第287页。 (43)前引④。 (44)See John H.Bauman,Emotional Distress Damages and the Tort of Insurance Bad Faith,Drake Law Review,Vo1.46,1998. (45)See Cf.Syverud,supra note 8,at 1121 n.16. (46)前引(44)。 (47)See Jon D.Kreucher,The Tort of Bad Faith in First-party Insurance Contracts:Has Michigan Joined the Trend? McCahill v.Commercial Union Insurance Co.Cooley Law Review,Vol.7:245,1990. (48)参见http://law.justia.com/cases/california/ca13d/21/910.html. (49)前引①,第285页。 (50)前引④。 (51)参见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 (52)前引(51),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