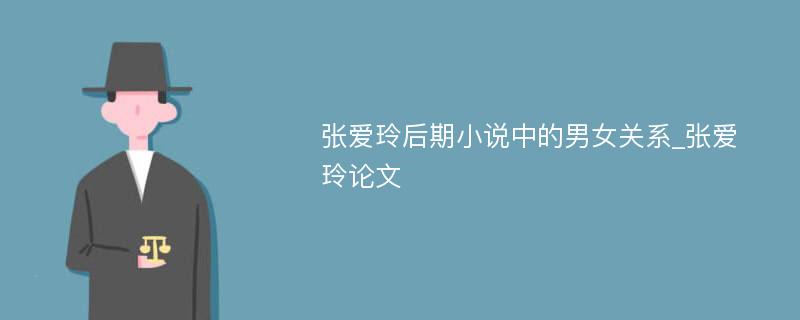
张爱玲晚期小说中的男女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期论文,男女关系论文,小说论文,张爱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放在文学史上看,我以为《小团圆》至少有三层意义。
一是确立了张爱玲的晚期风格。以前张爱玲研究,通常只看到她上海时期《传奇》的典型张氏风格和到香港后获得美新处资助写作《秧歌》、《赤地之恋》的文风转变——由流动华丽转向平淡含蓄,从都市情欲到乡村苦难。到美国以后张爱玲英文创作并不顺心(英文小说The Fall of Pagoda,The Book of Change一直找不到出版社,《金锁记》双语改写多次,影响仍不如上海初版)。电影《色·戒》使这个晚年的短篇重新引起关注,加上涉及同性恋的中篇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以及更重要的《小团圆》,张爱玲的晚年风格及其与早期传奇的比较,便成为很有文学和学术意义的话题。
还是一贯的琐碎细节,但文字华丽有了节制,瘦劲枯涩,人文俱老。五十多岁的女人回忆二十多岁的初恋及床戏,“物化苍凉”的意象仍是她的招牌。还是有局限的第三人称,常常省略主语,故意混淆叙述者的视角和人物的观点,叙述方法则从顺时序变为意识流。最重要的是故事,由“爱情战争”到乡村悲剧再到纯粹个人往事,这种转化轨迹,也是我想说的第二层意义:《小团圆》为中国文学的自传体小说增加了新的一章。
仅在现代文学的时段里,自传体文学至少有三类。
一是极端主张“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体”的郁达夫。郁达夫有意在《沉沦》、《茑萝行》等作品中坦露自己,又在《日记九种》或《我的自传》中从事无意识的创作。他的自叙体既是私人心理的忏悔,同时又具有社会时代意义——“公”、“私”两者孰更重要,郁达夫自己以及五四文学读者群的看法,不仅有犹疑,也有改变。在初版的《〈沉沦〉自序》里,郁达夫说《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①可是到1932年的《忏余独白》,在民族危机上升、文坛潮流也渐趋左倾的背景下,他又评论《沉沦》是“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使他失望之极,于是,他“象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发出了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的悲鸣”②。十余年间,两种对作品的自我诠释,从表现“青年忧郁病”、“灵肉冲突”(五四初期),到“故国陆沉”、“异乡屈辱”等民族主义符号,《沉沦》的意义,也经历了从性(启蒙)到民族(救亡)的主题演化。可见“自传体文学”在五四时期不仅有“公”、“私”兼顾的两面性,还有一个从“私”向“公”的认同(或被迫认同)的过程。
第二种“自传体文学”是从一开始就明确有意地以“私”写“公”,如巴金的《家》、《春》、《秋》。虽然作家明言觉新与他长兄悲剧相似,长兄自杀是他创作的动力,但实际上,巴金的个人家事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缩影、时代象征。原型的梅表妹在与大哥恋爱不成后嫁人,养得胖胖的,有好几个孩子。小说里的梅却因礼教扼杀爱情郁闷而病死。事实中的丫鬟的确被逼为妾,却果真入了“豪门”,并没像鸣凤一般投湖自尽以唱响反封建的主题。后来如杨沫的《青春之歌》等,也都属于这一种以个人经历写时代风云的“自传体文学”。
第三种“自传体文学”出现在40年代后,如钱钟书《围城》,又有一个由社会转向私人的倾向。《小团圆》显然沿着《围城》方向继续往极端发展。小说写于1975年,但与当时中国的时代、美国的环境毫无关系。宋淇在信中好意劝作家将邵之雍改成间谍并帮助设计情节③,其实作为好友他也没明白,对张爱玲来说不写自己隐藏私密真情,《小团圆》就没有意义了!虽然自传体文学一向以为私事入文即为公,但像《小团圆》(还有英文小说《雷峰塔》、《易经》等)那样“目中无人”(既不怎么考虑时代,也不大顾及读者),老是回述自己同一段往事,其自信心还是令人注目。“我写《小团圆》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④张爱玲不厌其烦地叙述她个人少年在上海、青年在港大的细碎往事,与她同时期翻译吴语版的《海上花》,又孜孜不倦地考证《红楼梦》有关。从“自叙传”的角度看,“上海阶段”写的是作家自己“深知的材料”(一个并无恋爱经验的女人写男女关系,至少是作家自以为“深知的材料”),但作家当时让自己并不直接现身于故事之中。“香港阶段”是获资助照提纲写自己不熟悉的红色土地,虽提早三十年开“伤痕文学”先河却也给作家自己深刻的“主题先行”教训(尤其是写《赤地之恋》的过程),使作家在她中年至晚期的“美国阶段”痛下决心,只写自己,撕肝裂肺,不厌其烦,而且基本上,只写男女关系与母女关系。偶尔,“革命加恋爱”(《色·戒》),便将历史戏剧解构颠覆得惊心动魄。
《小团圆》自传色彩再浓,归根到底这是一部独立的作品。九莉、蕊秋、邵之雍,首先是小说人物,然后才是张爱玲生平研究的参考资料。所以第三,《小团圆》的文学史意义,还在于作品分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十分罕见的两个有关“爱情”和“母爱”的复杂个案。这些人伦关系虽然奇特甚至“畸形”,却在某种意义上连接了《海上花》的传统伦理精神与今天中国的现实道德困境。母亲蕊秋和男人邵之雍,女主角九莉一生两个梦魇之间的对应关系,也是这部看似松散的小说的内在艺术结构。在怎么处理母女关系,和如何刻画男女关系这两方面,《小团圆》达到了现代文学的一个高峰。
黄锦树用一句话精辟概括《小团圆》中的男女关系,这“爱情故事”论证了“女主角何以不惜一切爱上显然不该爱的人”⑤。
这个评论带出了至少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男主人公是个“显然不该爱的人”?第二,女主角何以不惜一切去爱男主角?第三,究竟什么是《小团圆》及张爱玲晚期其他小说中的“爱”?
很多现代作家都写过不同的男女关系。第一种最常见模式是男女主角相爱,但在社会压力之下,男人敏感却软弱(《伤逝》中的涓生),正直却无力(《日出》中的方达生),或穷困多虑(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或犹豫不决(《边城》中的傩送),或忙于革命(《家》中的觉慧)……总之,女主角一往情深,最后却得不到这个“显然该爱”的男人。
第二种模式是男人开始吸引女主角,但因为某个原因(下面会讨论,通常是政治原因),女主角最后抛弃他们(丁玲《莎菲女士日记》中女主角在Kiss以后丢开凌吉士,茅盾《创造》中太太离家,留言给丈夫:我先走了,追上来,否则不等了)。
第三种模式是女人爱了很久甚至结了婚,仍不清楚这个男人是否“该爱”(如老舍《骆驼祥子》虎妞对祥子,如钱钟书《围城》中孙柔嘉对方鸿渐……)
总之,象范柳原这样既“应该被爱”又确实能与女主角相爱的“爱情童话”已经罕见,如邵之雍般“显然不该爱”却仍得女人一往情深的男女关系更是另类,令人费解。
要分析为什么邵之雍“显然不该爱”,我们不妨先看其他现代文学名著中这些为女主角所爱(或曾经所爱)的男主人公形象,究竟他们为什么“被爱”?
首先,上面提及的现代文学中为女人所爱的男主角,十之八九都是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如涓生、于质夫、觉慧、君实、方达生、方鸿渐,等等,丁玲笔下的凌吉士也是南洋侨生,范柳原虽是商人,却也爱读《诗经》,“执子之手”云云。中国现代文学很少描写书生以外的男人(商人、工人、小贩、农夫、军人等)如何谈恋爱。这种不全面“反映现实”的文学现象在中国长期存在,可有多种解释角度:如文人视角的“自我慰问”,读者“才子佳人”传统情趣的需求,作家借男女关系隐喻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启蒙愿望及困境,等等。
名作中男主角若不是读书人身份,如《边城》中的二佬傩送,却也都比喜欢他的女主角翠翠更有文化。《骆驼祥子》稍有点例外,但也曾经比其他旁人更有道德追求,而且在人生道路一接近文化人曹先生便走正道,反之便堕落。总之,现代文学中男人应该被爱的第一个条件便是“有文化”,“有才”——邵之雍显然充分符合这个条件。
但文化人通常有政治倾向。仍以上面所列现代文学作品的男主角为例,真正值得女主角去爱的,大都政治立场进步,追求民主和新思潮,如觉慧、涓生、于质夫、方达生,或至少有正义感,如方鸿渐、范柳原、傩送。前面讨论的女性pass男人的模式,茅盾笔下想“创造”妻子最后反对娴娴投身妇女运动的丈夫君实,和丁玲笔下热衷资产阶级趣味的凌吉士,便都是因为他们政治倾向不够进步而最后被女主角抛弃(更明显的例子是杨沫后来在《青春之歌》中放弃想走学者道路不肯革命的余永泽)。祥子则是由正直转向走狗的一个反面教材。看来,男人应该被爱的第二条件是“进步”——邵之雍身为汉奸官员,显然不符合这个条件。这是黄锦树所言“显然不该爱”的一个重要依据。
爱情不能只靠文化和政治支撑。经济因素在很多现代文学作品中表面不是“爱”的理由,其实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有钱或不保证爱情成功(《创造》),缺钱却足以导致爱情失败(《伤逝》)。金钱在巴金、丁玲笔下造成爱情鸿沟(《家》、《莎菲女士的日记》),财富在沈从文、张爱玲的故事里是又构成爱情的无声基础(《边城》、《倾城之恋》)。《春风沉醉的晚上》里女工陈二妹之所以对落魄文人刮目相看,不仅因为男主角看书文雅,也因为她以为他的翻译,轻易能赚“五块钱”稿费,“这样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多做几个?”《日出》里陈白露之所以拒绝有才华、政治进步的方达生,原因就是经济上“你养不起我”。祥子和虎妞的关系也证明女人若比男主角有钱,则是爱情故事的不稳定因素。祥子与虎妞的悲剧也从反面证明经济因素对爱情故事男主公十分重要——于是我们明白《小团圆》中邵之雍送给九莉一箱钱的重要性:这个细节将胡兰成“惯吃软饭”的形象打造成小说里颇肯为女人花钱的男主角(依据不同价值观,可解读为有“责任感”或“包二奶”)。
男性主角为女人所爱的另一因素应是形象、风度和身体,而在大部分现代小说中,这个因素常常被淡化忽视——这个文学现象却不应该被我们忽视。《伤逝》完全不描写涓生的外表,于质夫、方达生、觉慧、君实甚至方鸿渐等似乎也都不是因为男性特征而引起女主角们的爱慕。与男作家只注重男人视角不描写男性身体(忽视女性角度)形成对照,在女作家笔下,莎菲对凌吉士的外表十分痴迷,用想要糖果的态度,去看男主角的嘴唇。范柳原虽“粗枝大叶”,却也不失风度——而《小团圆》写这个“显然不该爱”的男人,不仅眉目清秀,而且还有“狮子老虎掸苍蝇的尾巴,包着绒布的警棍”(香港皇冠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以下《小团圆》引文,除非特别注明,均引自同一版本,只注页码),和“兽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240页)等形体表现。从女性感官出发的写男性形体及动作,无论文字的细节还是意象的具体,均对诸如“五四”男性作家如郁达夫《沉沦》中的沐浴女体及穆时英咏叹的抽象“白金女体塑象”形成对照与挑战。
在文化、政治、金钱和身体等因素之外,爱情当中更重要的一个条件当然就是情感专一。在涓生、方达生、君实、方鸿渐、乃至车夫祥子等男人考虑“爱”及婚姻的时候,“专一”是现代爱情观(西方先进文化?)不言而喻的先决条件。在觉慧、傩送等阶级地位不对等的爱情中,承诺比较会有变数,但男主角主观上(至少当时)也似乎没有妻妾成群的理想。范柳原在小说里则经历了一个满足女性梦想的被改造过程:从花花公子到“执子之手”的丈夫。凌吉士在女主角看来,则是无法改造,无可救药,故弃之亦不足惜。显然,在大部分现代爱情小说中,男主人公的正面形象与其情感专一程度成正比——《小团圆》则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反面样本。
综上所述,政治倾向和情感不专一,是邵之雍被评论家认为“显然不该爱”的两个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太有才了”、“一箱钱”和“眉眼很英秀”(163页),显然就是这个男人的“强项”了。女主角其实并没有“不惜一切”,而是不惜忽视或挑战这个“显然不该爱的人”的政治立场和情感观念——事实上,对前者,女人可以忽视、妥协;对后者,却只要斗争到底,代价惨重,“女人总是要把命拼上去的”(177页)。
《小团圆》从第四章到第十章,完整记录一场男女爱情战争的全过程,浓缩了张爱玲其他作品中各种爱情主题和情节。这场“男女战争”大致有三个阶段:一是冲动、幸福阶段(在香港皇冠版的《小团圆》里,大致从163页初识、初吻到176页“她也有点感觉到他所谓结婚是另一回事”因而跳入纽约堕胎意识流),二是纠缠、忍让过程(从180页到大约261页战争结束之雍逃亡),三是愤怒摊牌结局(从262页千里寻夫直到小说结尾)。不过在分析这“爱情战争”三阶段之前,有必要先看双方“战前”各自的“兵力准备”(恋爱观、经验与决心)。
邵之雍是小说人物,但张爱玲在给宋淇信中明言是写胡兰成,颇有赶着为自己的灵魂经验身体历史留下记录的意思⑥。在这个意义上,胡张关系也可作为我们分析邵之雍、九莉关系的一个参考。胡兰成有自传《今生今世》,后人也从中发现其中很多虚构创作成分⑦。我注意到胡兰成碰到他喜欢的女人,总先是甜言美誉,接着马上谈结婚,然后用女人钱,还有将旧情事向新恋人坦白公开(简称“胡四招”)。胡形容“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我常时以为很懂得了什么叫惊艳,遇到真事,却艳不是那艳法,惊不是那惊法”(《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下同)。还有,“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159页),也是名句。但胡的甜言美誉并非只给张爱玲,数月后武汉看到小周护士,“声音的华丽只觉一片艳阳,她的人就象江边新湿的沙滩,踏一脚都印得出水来”(181页)。“她的流泪使我只觉得艳,她是苦亦苦得如火如荼,艳得激烈”(186页)。后来对陪他回乡的寡妇范秀美,胡也是大篇的赞颂,“她其实是个亮烈人,从端正里出来温柔安详,立着如花枝微微倾斜,自然有千姣百媚”(214页)。“只觉她的言语即是国色天香。她的人蕴藉,是明亮无亏蚀,却自然有光阴徘徊。她的含蓄,宁是一种无保留的恣意,却自然不谒不尽,她的身世呵,一似那开不尽春花春柳媚前川,听不尽杜鹃啼红水潺湲,历不尽人语秋千深深院,呀,望不尽的门外天涯道路,倚不尽的楼前十二阑干”(227页)……虽是这些言词是事后回忆,当初也总有操练实习。在说女人好话以后,第二招是马上提议“结婚”。在上海与张爱玲有一纸婚书,在武汉与小周也迅速成亲。后来逃难范女士下乡一路照顾他,《今生今世》里这样写的,“十二月八日到丽水,我们遂结为夫妇之好。这在我是因感激,男女感激,至终是惟有以身相许……(233页)”这“以身相许”说,也算颠覆男性中心主义语言习惯。第三招是花女人钱:一讲婚姻,再花女人钱,女人觉得你把她当自己人。在武汉找小周后,回沪跟张爱玲怎么解释呢?说我是客己待人,咱们俩是自己人,她是外人,客人,我当然要照顾她了。而当小周问他要办婚礼仪式时,他说我和张爱玲那边还没办仪式呢?不能先跟你办。后来日本投降他要逃难,就把小周叫过去,说你等着。中国古代夫妻,男的逃难出去十年、二十年,女的在家里等着,常有的事。小周还真等着,还为他坐过牢。最后第四招是坦白。前三招所以成功,也因为第四招:跟眼前女人,详述之前艳史,绝不隐瞒,也不偷偷摸摸,且不说其他女人缺点。这点胡兰成与众不同。他说以前花好桃好,当然,你现在更好。为什么女的都信呢?那是另一个问题。
胡兰成晚年回忆情史,骄傲多于忏悔,背后自有他有关中国人家庭婚姻爱情的一套理论支撑⑧。而在张爱玲这边,《小团圆》也借女主角之口多处声明她的恋爱观,一是“她不喜欢象她的人,尤其是男人”(162页)。二是“她一向怀疑漂亮的男人”。“漂亮的男人……往往有许多弯弯扭扭拐拐角角心理不正常的地方”(311页)。三是“她一直觉得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165页)。四是作家和她很多小说女主人公一样,有结婚情结。在遇见男主角前,九莉和作家一样,二十多岁,“写爱情故事,但从来没有恋爱过”。虽然能透彻描写了乔琪乔、佟振保、范柳原等风流男性的复杂心理,但演习毕竟不同于实战。
在这部总共325页的长篇小说中,男主角直到第163页(正好过了半场)才出现。第一段关于这男人的文字是女主角和女友的一段闲谈:
“有人在杂志上写了篇批评,说我好。是个汪政府的官。昨天编辑又来了封信,说他关进监牢了。”她笑着告诉比比,作为这时代的笑话。
仅隔了数行,就写男主角放出来后来看她,“穿着旧黑大衣,眉眼很英秀……像个职业志士”。“楚娣第一次见面便笑道:‘太太一块来了没有?’九莉立刻笑了。中国人过了一个年纪全都有太太,还用得着三姑提醒她?也提得太明显了点。之雍一面答应着也笑了。”
以上文字出现在同一页上。初次见面几句话,便已经涉及我们上面列举的男人“五项基本条件”中的四项:
1.“写了篇批评,说我好”——文化人,有才,且崇拜女主角;
2.“汪政府的官”——政治身份有问题,但坐监受迫害,像职业志士;
3.“眉眼很英秀”,“去后楚娣道:‘他的眼睛倒是非常亮。’”——身体形象方面有魅力;
4.有太太——一夫多妻的麻烦。
爱情故事,通常神化“一见钟情”,渲染一见面最初神奇的感觉。诡异另类如《小团圆》亦不例外,只是在这可能是非理性、无目的的最初感觉之中,日后要长期面对的绝大部分基本问题却也在无意识中被瞬间浓缩包含了。即便张爱玲不是,至少九莉是。
次日起,男人就“天天来”了,女主角描写男人的侧面是“背着亮坐在斜对面的沙发椅上,瘦削的面颊,眼窝里略有些憔悴的阴影,弓形的嘴唇,边上有棱”。《小团圆》前半部写了很多九莉的心理、行为、感受,却很少写她的外形,直到男人登场,才出现女主角的自己的形体画像——女人需要“他者”的存在为“镜”:“九莉戴着淡黄边眼镜,鲜荔枝一样半透明的清水脸,只搽着桃红唇膏,半鬈的头发蛛丝一样细而不黑,无力的堆在肩上,穿着件喇叭袖孔雀蓝宁绸棉袍”(164页)。外貌的互相欣赏后面,其实是不同逆境中的文人的互相崇拜。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最早的“吹捧”,至今看来亦有学术分量。而九莉也承认:“她崇拜他……他走后一烟灰盘的烟蒂,她都拣了起来,收在一只旧信封里”(165页)。这个颇可以满足男人自恋的细节并没有记载于《今生今世》,看来是九莉而非张爱玲所为——又一次证实这个“爱情故事”与胡张恋史实之间的细微却重要的分别。下一页,认识数日后两人说话已涉及钱的重要性(另一“爱情基本条件”)。邵要九莉取下眼镜,第一次接吻,“九莉想到:‘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但并没有立刻解释具体理由。邵的kiss有木塞味,瞬间生理感觉并不迷人。在后来的短篇《色·戒》里,女人也有这一闪念,且伴有“头上轰地一声响”,直接动因是男人送给她一粒连太太都不送的钻石)接吻以后不久男人马上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胡四招之二)女主角回答很直接:
“你太太呢?”
他有没有略顿一顿?“我可以离婚。”
那该要多少钱?(168页)
中间这个问号耐人寻味,说明女人当时及事后都不肯定男人是否在说真话。
这段男女关系从一开始就面对主要矛盾,不过从那以后,故事就不再快速推进,而更多只是重复回旋——像张爱玲的创作历程。
女主角在政治上能够接受一个“汪政府的官”(和其他现代文学女主角的选择很不相同),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九莉对邵的政治理论可以求同存异。存疑反对部分是汪派主张,“‘和平运动’的理论不便太实际,也只好讲拗理”(166页)。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当时的政治进步几乎等同于“左倾”。但实际上,陈公博、周佛海也曾参加共产党。胡兰成也说自己在广西教书时期曾“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且“敬服托派”⑨。所以九莉觉得邵有“左派作风”且“人人有饭吃”的理想亦无不妥,这就有了求同的基础。女主角在政治态度方面也承认自己不合潮流:她一向以为“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64页)。小说后来描写全民庆祝抗战胜利时,九莉觉得自己“泥足”于世(251页)。
第二,初识男人时他在监狱,受迫害形象易遭人同情(羊为什么爱上狼,因为狼受了伤)。后来小说也描写邵之雍热心援救左派作家荀桦⑩,荀桦战后反而企图调戏九莉,视她为“汉奸妻”(荀桦或有原型,待考)。换言之,在《小团圆》里女主角认为,政治立场“反动”(反社会潮流而动)并不必然等同于道德品格低下。
第三,《小团圆》渗透这样一种价值观,尤其在男女关系中,个人情感视角比社会政治背景更重要。“比比也说身边的事比世界大事要紧,因为画图远近大小的比例,窗台上的瓶花比窗外的群众场面大”(51页)。比比的原型是张爱玲的知音、好友炎樱,“也说”意思是女主角亦持同样看法——这是张爱玲一生信奉的艺术原则,香港时期有点因政治处境而动摇,晚年更坚持到极端的方向:《小团圆》描写九莉听到日军轰炸香港心中竟暗喜——只因可以逃避考试(55页)。直到安竹斯教授被炸死,才向上天祷告:“你待我太好了,其实停止考试就行了,不用把老师也杀掉”(67页)。既然窗台瓶花比窗外政治更大,那心上人的接吻自然也比他背后的政治身份更重要。甚至日军投降前九莉还希望战事再延长一会,只为她和她的男人可以多待一会……
政治立场不是爱情的障碍,但“情感不专一”却是更严重的问题,其严重性,是自以为与众不同的男女文人情人估计不足的。
曾有一段短暂的金色时光:
他注视了她一会之后吻她。两只孔雀蓝袍袖软弱的溜上他肩膀,围在他颈项上。
时间变得悠长,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这一段时间与生命里无论什么别的事都不一样,因此与任何别的事都不相干?(171页)
这是小说中最美好的一段文学和意象,不过当时也隐约伴随着危机感:“她不过陪他多走一段路。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我们根本没有前途,不到哪里去”(173页)。
一方面预感不会“天长地久”,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只能“曾经拥有”。之后小说的主要篇幅,就是很长一段“纠结—忍让”时期。其中又可分两个阶段,以男主角在报上两个离婚广告并与九莉签一纸婚书为转折点,前一段是女主角“战胜”男人之前的两个女人,后一段是女主角“败”于男人之后的两个女人。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记载张爱玲对他有别的女人的理性态度,似乎颇潇洒:“我已有妻室,她并不在意。再或我有许多女友,乃至狎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我。”(11)
这里有三个可能:一,以上记载纯属“胡编”创作,自欺欺人。二,这是张爱玲一定程度上的宽容策略,被胡误解为她“不介意”,态度潇洒。《小团圆》里也曾这样描写女主角的谅解:“‘我是喜欢女人’,他自己承认,有点忸怩的笑着。‘老的女人不喜欢’,不必要的补上一句,她笑了。她以为止于欣赏”(224页)。“他对女人太博爱,又较富幻想,一来就把人理想化了,所以到处留情。当然在内地客邸凄凉,更需要这种生活上的情趣”(225页)。“她本来知道日本女人风流……这种露水姻缘她不介意,甚至于有点觉得他替她扩展了地平线。他也许也这样想,尽管她从来不问他,也不鼓励他告诉她”(271页)(12)。三,张理性上真“不介意”,但情感生理无意识中其实极反感。《小团圆》近结尾处女主角有痛苦自白:“并不是她笃信一夫一妻制,只晓得她受不了。”(277页)而胡对张的理性情感矛盾故意视而不见。无论哪一种可能,都充满误会曲解,而男女关系又总是注定要在误会、曲解、幻听、盲目中延续发展。
《小团圆》中有段惊心动魄的时空跳跃,打胎的意识流的上下文,恰恰是在有关婚姻的困难语境之中。邵正在说“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女主角“她不懂,不离婚怎么结婚?……也许她也有点感觉到他所谓结婚是另一回事”(176页)。接着这个“顿悟”,便跳跃到多年后纽约打胎,“女人总是要把命拼上去的”。从抽水马桶里的男胎,蒙太奇又转回邵之雍:“我们这真是睁着眼睛走进去的,从来没有疯狂”(180页)。如果说在男人离婚前,九莉说“我真高兴有你太太在那里”(188页),这是胜者故作宽容姿态,那么在男人去武汉后九莉写信:“我是最妒忌的女人,但是当然高兴你在那里生活不太枯寂”(223页)。甚至也不在意之雍与女作家文姬与日本主妇的短暂风流浪漫,其实都是处在防守地位上的无可奈何的退让。
胡兰成在武汉又“娶”了护士小周,据《今生今世》,回沪后,“我与爱玲说起小周,却说的来不得要领(此处有点闪烁其词,“第四招”不彻底——引者注)。一夫一妇原是人伦之正,但亦每有好花开出墙外,我不曾想到避嫌,爱玲这样小气,亦胡涂得不知道妒忌。……爱玲亦不避嫌,与我说有个外国人向她的姑姑致意,想望爱玲与他发生关系,每月可贴一点小钱……爱玲说时竟没有一点反感,我初听不快,随亦洒然”(13)。张爱玲虚构或利用外国情敌的“激将法”,对胡兰成并不见效。胡兰成似乎认为张当时并不怎么在意他和小周的关系,既延续“一壶多杯”中国男人传统梦想,又假装后来萨特夫妇般的现代知识分子开放潇洒。但在《小团圆》里,女主角九莉持续不断的对小康小姐怀疑、警觉、妒忌,正正构成男女主角关系变化的主线。“知道就是接受”(237页)。当男人讲起武汉轰炸时小康小姐曾要保护他,九莉虽然面带笑容,心里已被逼到忍让与愤怒的悬崖夹缝之中。
以为“总不至于”的事,一步步成了真的了,九莉对自己说:“‘知己知彼’。你如果还想保留她,就必须听他讲,无论听了多痛苦。”但是一面微笑听着,心里乱刀砍出来,砍得人影子都没有了(235页)。
这种愤怒伴随着强烈的爱,一路发展到战后下乡寻夫。这是《小团圆》和《今生今世》最接近的一段,如九莉帮辛巧玉画像未成等细节,与胡兰成记载几乎相同。不知是基于同样记忆,还是张爱玲小说创作也有受《今生今世》的某些影响甚至呼应。最后摊牌:“要选择就是不好”,也是胡的原话。九莉问的是小康,却不知眼前情敌已是辛巧玉。“三美团圆”,男人的梦,女人的恨,为小说点题。
胡兰成自己从未提及给张送钱事。2009年在岭南大学开“当代文学六十年”学术会议,会间最多被提及的名字居然是鲁迅和张爱玲。王安忆说,这箱钱如有,何以胡兰成自传不写?陈子善说,如果没有,张爱玲为何事后编造?我以为,如此事属实,可能是胡认为“吃软饭”才是光荣,给女人钱不值得写(试看《色·戒》中易先生送钻之前的独白);如不属实,那就证明是张爱玲企图以文学加工,增加男主人公的责任感与魅力。
《今生今世》只记精神恋爱,整天谈文说艺,美化传主人生。《小团圆》却不回避情色场面。回顾“五四”以来的爱情故事,如《伤逝》、《家》乃至《围城》大都基本略去“性”的层面只写男女情理、心理纠纷,《骆驼祥子》写虎妞情欲但文字含蓄,丁玲写莎菲情热也仅限于“上半身”。在男女关系中写“性”而引起争议的郁达夫,有时很做作(如《沉沦》中窥看房东女儿沐浴之后的排比、感叹形容),有时很病态(如《茫茫夜》写于质夫买小铺店女的手帕与针,自刺其颊获得快感,又如《过去》李白时在米饭中幻见恋人的脚)。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以肥皂泡沫吸吮手指写佟振保对王骄蕊想入非非,已是“五四”以后爱情故事少有的带动词的情欲象征文字。到可《小团圆》,有关“性”的动作场面,却像家常生活细节一样被若无其事地叙述。从对“警棍”紧张,到“食色一样,九莉对于性也总是若无其事,每次仿佛很意外”(229页)。再到逃亡前“扳她一只腿,让她一只脚站在床上”(248页)的高难度动作,直到终有一日,睡在一张床上嫌太挤,甚至做爱时“她终于大笑起来,笑得他泄了气”(256页)。做爱想笑,是个悲剧。果然当夜女主角便想用切西瓜刀“对准了那狭长的金色背脊一刀”(256页)的念头。文本对照,倒是对《今生今世》“民国临水照花人”的一个好注解。
总之,说九莉“爱上显然不该爱的人”,其实并非“不顾一切”,而只是不顾“政治立场”与“薄情多情”。前者不顾到底,后者终于失败。究竟《小团圆》里什么是“爱”呢?张爱玲晚期小说中的男女关系,一方面特别注重身体和物质层面的个别细节、生理感受和心理动作,因此十分理智、具体、现实(163页和168页短短两段对话却已同时道出文化、政治、身体、情感及经济多重因素的考虑),比现代文学中的很多其他“爱情故事”都更加世俗化;但另一方面《小团圆》又特别强调非理性与无目的,明知要受伤受苦受罪,依旧睁着眼睛走进去,崇拜、迷恋、纠结、且义无反顾,小说直到最后也不出“恶声”,还要在田园美梦中与孩童及邵之雍一起步入“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
究竟是张爱玲太爱她自己的情欲经历,爱恨皆忘却不了,于是要苦苦倾诉?还是作家为了她所热爱的文学,在小说中虽然无情解构,撕裂创伤,但仍然要歌颂爱情的迷思?
如果只把《小团圆》读为胡张恋史的另一版本,那我们就太低估了这部作品的文学史意义。
假设胡兰成《今生今世》记载的是他记忆中的事实,那么小说《小团圆》在情节框架乃至很多细节的重复、印证和引用(14)之外,至少作了三个重要的文学改编:
胡兰成在和张爱玲结婚之后不久又娶护士小周,后来又在逃难途中与寡妇范秀美“行夫妻之礼”,《今生今世》记载男人当时没有多少矛盾和犹豫,事后也没有表达后悔之意。因为胡兰成在理论上既不坚信来自西方的一夫一妻文化,在情感上似乎也可以同时爱上不同的女人。但在《小团圆》第236页,作家特地描写之雍的痛苦:
比比与之雍到阳台上去了,九莉坐在窗口书桌前,窗外就是阳台,听见之雍问比比:“一个人能同时爱两个人吗?”窗外天色突然黑了下来……
比比走后,九莉微笑道:“你刚才说一个人能不能同时爱两个人,我好像突然天黑了下来。”
之雍护痛似的笑着呻吟了一声“唔……”把脸伏在她肩上。
在这里,小说人物邵之雍俨然被刻画成在恋爱问题上颇有良心痛苦(因此也很有情感深度)的男人。
第二处“改编”,前面说过,《今生今世》多次记载如何获得女人金钱资助,从张爱玲处,从范秀美处,当然,更多是后来从吴四宝前妻余爱珍处。胡兰成对此似乎荣多于耻。但在《小团圆》中,男主角在听说九莉想还钱给母亲后,便提来一个箱子,“笑着把那只廉价的中号布纹合板手提箱拖了过来,放平了打开箱盖,一箱子钞票。她知道一定来自他办报的经费,也不看,一笑便关了箱盖,拖开、放在室隅。等他走了她开箱子看,不像安竹斯寄来的八百港币,没有小票子”(184—185页)。在《小团圆》里,这前后呼应对照的两堆钱,其叙述功能犹如金庸小说中的秘方、地图之类,是足以扭转并改变主人公心理情感命运的某种道具。这样的钱之后陆续送来。虽然九莉只用了一些,另一部分换成黄金,母亲不收钱后仍还给逃难中的男主角。
第三,“胡四招”之四,是一切坦白。胡兰成回忆他“娶”了小周护士后回沪即向张爱玲说明,后来遇范秀美又将张爱玲和小周事告之。到香港“娶”余爱珍当然也交待以前情史。但《小团圆》中男主角邵之雍一直都没向九莉明说他和护士的真实关系。九莉也并不如胡兰成记载的张爱玲那样坦然潇洒,而是像普通爱情故事女主角一样,一直处在猜疑、痛苦和委屈之中。悬念一直拖到小说快结束时,九莉看到小康的照片,还问男人,“你跟小康小姐有没有发生关系……”(304页)
将一个习惯享受“一株牡丹花开数朵,而不重复或相犯”(15)的传统官员文人,描写成会在阳台上痛苦发问“一个人能同时爱两个人吗”的现代知识分子;将一个不会或耻于给女人金钱的风流才子,描写成在战乱危亡之际仍接济女友的男人;将一个无奈面对多妻局面的女性处境,改写成在恋爱中犹豫、彷徨、争夺、纠结的爱情故事女主角——我们无法知道也并不关心哪些是“真”的事实,哪些是“假”的虚构(“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张爱玲从一开始写作,在《第一炉香》、《金锁记》里已怀疑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只看见这三个文学改编的效果,使小说女主角,以及文学读者们更愿意去原谅、理解男主人公,当然,原谅、理解的同时仍包含着痴迷、愤怒和疯狂。
最大的“改编”还在于小说的结尾,这个给她带来巨大痛苦(与快乐)的男人最后仍出现在女主角少有的家庭梦想里。小说最后一页,有一个梦中,五彩片“寂寞的松林径”温馨背景,“映着碧蓝的天,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着,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她的。之雍出现了,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非常可笑,她忽然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就在这个时候醒了。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325页)。而写这篇小说时张爱玲给宋淇写信,理智上照旧称胡为“无赖人”(16)。
据宋以朗的博客,《小团圆》完稿后特地修改过两页,其中一页就加上了一段口交文字(17),可见作家对这段情色细节的重视程度。是五十多岁女作家念念不忘早年情史中的亮点痛处?还是女作家有意挑战开拓现代中文爱情小说中的某些边界线?
在另一封给宋淇的信上,张爱玲说:“《小团圆》是写过去的事,虽然是我一直要写的,胡兰成现在在台湾,让他更得了意,实在犯不着,所以矛盾得厉害,……”(18)
这里的“矛盾”我以为有两个层面,一是在个人心灵史上,对过去(甚至永不会过去的)男女关系的怨恨恩仇与留恋快乐之间的矛盾;二是在个人私隐情仇与在艺术中创作“爱情故事”之间的“矛盾”。“矛盾”的结果,就是上述一系列细节“改编”——尽管张爱玲揭露自己隐私,但最终还是写成了一部独立的文学作品,一部现代文学史上“非典型”的“爱情故事”(19)。在理智上,张爱玲不想原谅曾让她受罪的男人(尤其在与朋友通信的语境下),但一片片撕开伤口检点这段感情如何铭心、怎样刻骨,也隐含着与《今生今世》某种对话的潜意识欲望(20)。现实世界男女关系恩仇无解,唯有在艺术中才能再生。一方面,借助小说疗救心创的动力,连好友宋淇当年都不理解(因此提了很多改稿方案),但我以为另一方面,为了艺术不惜动用“最深知的材料”是更重要的原因。只有在小说世界里,才能如此无情“审判”自己的母亲(严厉态度堪比五四文学“弑父”情结,超过王蒙“审父”的《活动变人形》),同样苛刻地审视女主人公,在九莉这个极端自私、极度刻薄的普通人身上,爱情则是她最高尚的一面。归根到底,作家太爱她的文学,因此才爱小说中的自我,及小说中的男主角。
相比之下《小团圆》后来写与燕山的恋情(21),既无“政治倾向”的障碍,也少“情感不专心”的问题。燕山是文化人,形象漂亮,身为编剧导演,父亲也经商。女主人公也不是不认真,有次邵之雍探访时燕山来电话,“她顿时耳边轰隆轰隆,像两发星球擦身而过的洪大的嘈音。她的两个世界要相撞了”(301页)。他们甚至也讨论婚事,一度还以为怀孕。不同之处是九莉可以想象燕山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情景,“也许是人性天生的别扭,她从来没有想象过之雍跟别的女人在一起”(322页)。再热恋时,旁观者三姑也说,不如和之雍的关系。所以张爱玲描写的男女关系,身体再世俗,欲望再现实,处处充满拌嘴、怄气、衣着、化妆、吃饭、钞票等细节,却隐隐贯穿浪漫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信仰:主人公不可能同时爱两个人,甚至不在同时也不行。
当然,九莉之所以会这样处理男女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与母亲的关系。《小团圆》中写母女关系的篇幅比“爱情故事”其实更多(是之前两部英文小说的中文缩写,所以文字、情节都有些跳跃)。和母亲的复杂关系直接、间接地影响并制约了女主角对爱情的态度:第一,从小母爱的缺乏导致女主角在男女关系中的极度甚至病态地渴求“爱”。第二,因不符合母亲现代淑女教育的要求而自卑,使得女主角在爱情方面也缺乏自信,容易委屈。第三更重要的是在母亲自相矛盾的谨慎“言传”浪漫“身教”之下,女儿的恋爱生活处处逆向挣扎。母亲的“言传”头绪纷乱,宗旨是性关系要矜持——九莉却冲动、无目的,不仅当年一见钟情,晚年仍在回忆“警棍”、“小兽”,母亲的“身教”是“多元化”,拿得起放得下(《小团圆》中至少十几个中外情人)——九莉却专一,不能自拔,不愿,不肯,不甘心,但又无法不步母亲后尘(打胎、爱情失败、晚年孤独……)。母亲和九莉的关系,在“性”的意义上,与其说是母女,像师生,不如说更似竞争对手。九莉原是“最不多愁善感的人,抵抗力很强”,为什么“只有她母亲与之雍给她受过罪”?究其原因,就是女主角一生在和很多女人争夺邵之雍,又和很多男人争夺她母亲。
爱上让她“受罪”的人,在某种程度也就是“如何爱上你的敌人”——这个主题后来在《色·戒》中才最后完成。而怎么“敌视你的亲人”,张爱玲在描写母女关系方面也达到现代文学的一个高峰。当然,这已是另一篇论文的题目了。
注释:
①《沉沦》,泰东书局1921年版。
②《忏余独白》,见《忏余集》,天马书局1933年版。
③宋淇致张爱玲的信,1976年4月28日,见张爱玲:《小团圆》,皇冠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④张爱玲致宋淇的信,1976年4月4日,见张爱玲:《小团圆》,同上,第13页。
⑤黄锦树:《家的崩解》,《读书人》,《联合报》2009年3月8日。
⑥“赶写《小团圆》的动机之一是朱西宁来信说他根据胡兰成的活动手写我的传记……”(张爱玲致宋淇的信,1975年10月16日,见宋以朗《〈小团圆〉前言》,《小团圆》,皇冠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⑦参见秦贤次《胡兰成生平史事考释》(提交香港浸会大学2010年9月“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⑧“中国人男女之际,远离圣灵与罪恶那样的巫魇,女儿家亦明理无禁忌,……”(《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男女之际,中国人不说是肉体关系,或接触圣体,或生命的大飞跃的狂喜,而说是肌肤之亲,亲所以生感激。”(《今生今世》,228页)“西洋人的恋爱上达于神,或是生命的大飞跃的狂喜,但中国人的男欢女悦,夫妻恩爱,则可以是尽心正命。孟子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姻缘前生定,此时亦惟心思干净,这就是正命。……秀美……竟是不可能想象有爱玲与小周会是干碍,她听我说爱玲与小周的好处,只觉如春风亭园,一株牡丹花开数朵,而不重复或相犯。她的是这样一种光明空阔的糊涂。”(《今生今世》,第237页)除了强调男女关系的亲情因素以及赞扬女性明理宽容(没说男人是否也要有“光明空阔的糊涂”)以外,胡兰成更主张中国人的男女之“爱”,其实就是“知”,见本文注(20)。
⑨见《今生今世》,台北远景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164页。秦贤次则推测,胡兰成当时由广西南宁一中同事古咏今介绍加入托派。《胡兰成生平史事考释》(提交香港浸会大学2010年9月“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⑩《小团圆》,第230页。
(11)《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12)《小团圆》,第271页。《今生今世》中确记载胡兰成与日本女房东的一段情,不过是在逃亡日本以后。《小团圆》所描写邵之雍与日本主妇露水姻缘发生在国内,或是移花接木借用胡自己的炫耀作为虚构小说情节。
(13)《今生今世》,第194页。
(14)如与日本主妇的露水姻缘等。
(15)胡兰成语,参见本文注⑧。
(16)张爱玲致宋淇的信,1976年4月4日,见张爱玲:《小团圆》,皇冠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17)“兽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泊泊的用舌头卷起来。她是洞口倒挂着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遗民,被侵犯了,被发现了,无助,无告的,有只动物在小口小口的啜着她的核心。暴露的恐怖揉合在难忍的愿望里:要他回来,马上回来——回到她的怀抱里,回到她眼底——”《小团圆》,第240页。
(18)张爱玲致宋淇的信,1975年11月6日,见张爱玲:《小团圆》,皇冠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19)张爱玲自己的解释:“《小团圆》……是个爱情故事,不是打笔墨官司的白皮书,”见张爱玲致宋淇的信,1976年1月3日,载宋以朗《〈小团圆〉前言》,《小团圆》,皇冠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20)张爱玲后来在美国曾写信向胡兰成索取《今生今世》,不知女作家看到胡兰成的这段话如何感想——“我与女人,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知。中国人原来是这样理智的一个民族,《红楼梦》里林黛玉亦说的是‘黄金万两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却不说是真心爱我的人一个也难求。情有迁异,缘有尽时,而相知则可知新,虽仳离决绝了的两人亦彼此相敬重,爱惜之心不改。人世的事,其实是百年何其短,寸阴亦可长”(《今生今世》,第316页)。
(21)小说中所写的燕山,据宋淇信中所言是电影导演桑弧(宋淇致张爱玲的信,1976年4月28日,见张爱玲:《小团圆》,皇冠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但桑弧对他与张爱玲的关系一向保持沉默。
标签:张爱玲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沉沦论文; 今生今世论文; 色戒论文; 胡兰成论文; 围城论文; 小团圆论文; 边城论文; 伤逝论文; 自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