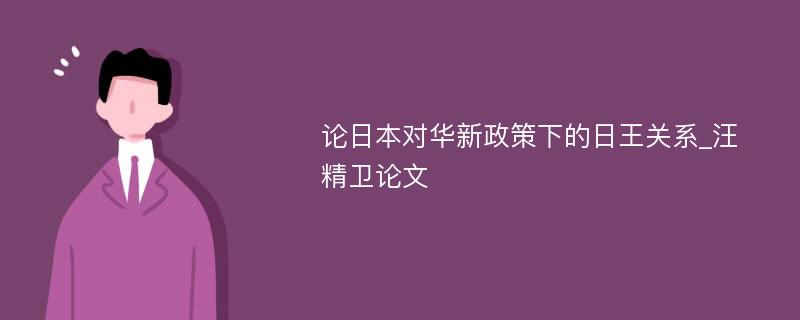
论日本对华新政策下的日汪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新政策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42年与1943年之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出现重大变化。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严酷的战争形势面前,为了竭尽全力动员其本国及中国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决定重新审订其对华政策。
1942年9月1日,日本政府决定设置大东亚省,作为实行对华新政策的组织准备。长期以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进行掠夺和统治有许多分歧的地方:在机构上有外务省、拓务省、兴亚院的磨擦,对中国采取的‘分治政策’,使现地军人之间,傀儡政权之间纠葛颇深,而各大财阀又竞相渔利”[①a]。设置大东亚省正是为了调和日本各种势力在中国沦陷区的矛盾,弥补各傀儡政权间的裂痕,将治权归一,以利于对华新政策的出台和实施。11月1日,大东亚省成立,下设总务、满洲事务、中国事务、南方事务4局。同时,日本政府决定撤销原拓务省、兴亚院、兴亚院联络部、对满事务局,并将原外务省所属东亚局与南洋局、原拓务省所属拓南局与拓北局的业务,一并划归大东亚省主管。同日,日本政府任命曾任汪伪政府最高经济顾问的青木一男为首任大东亚相,奏响了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前奏曲。
11月8日,日本第81届帝国议会开幕。日本政府发表“转换”对华政策声明。随即,日本政府、军部、驻华各机关间,以及日本政府与汪伪政府间进行了一系列磋商。12月18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以《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为基础的具体策略”。21日,又由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策,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这是日本军部和垄断财阀相勾结的产物,是推行“对华新政策”的总纲领。
该文件规定了对华新政策的总方针:“帝国认为国民政府(汪伪政府)的参战是打开日本和中国的现状的一大转机,应根据日华合作的根本精神,专心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应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日的口实,和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完成战争而迈进”;要求“对照世界战局的演变,在美、英方面的反攻到达最高潮之前”,“设法使对华的各种措施获得成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该文件确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在政治方面,以“加强国民政府(汪伪政府)的政治力量”为中心,规定“尽量避免干涉”汪伪政府,“极力促进它的自发活动”;“调整占领地区的地方特殊性”,加强汪伪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以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的精神为基础”,设法尽速撤销或调整“在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殊的各种形态”;促使汪伪政府“以坚定的决心和信念,在各方面讲求自强之道,广收人心”,“增进必要的生产,普及官民对战争目的的教育”,“加强维持治安”,“不遗余力地在战争方面与帝国合作”;根据汪伪政府充实加强及对日合作的情形,“及时考虑对《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加以必要的修改”等。在经济方面,以“增加获取战争必需的物资”为中心,规定“设法重点开发和取得占领地区内的重要物资,并积极取得重要的敌方物资”;“实行经济措施时,一面力戒日本方面的垄断,一面利用中国方面官民的责任心和创造精神,实现积极的对日合作”等[①b]。
日本对华新政策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的“基本国策”,只是在策略和手段上有所变化。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解释说:日本在新形势下采取的新策略是“举全大东亚之民族,以所有之资源,集中于贯彻圣战之一途”,为此,“依日华提携之根本精神,以加强国府(汪伪政府)之政治力,覆灭重庆抗日之根据地,及同盟统一后进中国,以期贯彻圣战”[②b]。显然,日本对华新政策的中心环节是强化汪伪政府,而以“尊重主权领土”、“经济合作”、“全面和平”等为招牌,从中国占领区掠取“所有之资源”,保证“大东亚圣战”的进行。日本对华新政策的提出,既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确定不变的国策”的狂妄和顽固,又暴露出它为了挽救危局而不得不强调依赖中国占领区的虚弱和没落。
二
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开场戏,是汪伪政府所谓的对美、英“宣战”。此举是由日汪共同密谋策划的,也是日本对华新政策下日汪关系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日、美开战后,汪伪政府曾发表声明,表示决心与日本“同甘共苦”,并在各种场合反复宣传。汪精卫撰文说明“同甘共苦”包含三个内容:第一是“确立治安”;第二是“加强军事力量”;第三是“增加生产,节约消费”,他认为这三点“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而又是我们现在所能做的”[①c]。当时汪伪政府尚没有涉及“参战”问题。
1942年夏,汪伪政府开始改变态度。7月,汪伪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访日,向日本政府表示愿意向英、美“宣战”,称汪伪政府“不仅和友邦同甘共苦”,而且要“共存共亡,同生同死”[②c]。9月,日本平沼骐一郎访问南京,汪精卫又亲自表示要求“参战”,但未为日方接受。
日本政府一度不让汪伪政府“参战”,主要原因是当时日本大本营曾下达过为攻略重庆的5号作战进行准备的命令,日本政府设想在实施5号作战以后的某个时机,诱迫重庆政府订立“和平条约”,因此不同意汪伪政府“参战”。但是,到了10月,随着太平洋战局日趋恶化,逼降蒋介石毫无希望,遂决定停止5号作战的准备,并于29日由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准许汪伪政府“参战”,时间待定。11月27日,进而决定将汪伪政府“参战”的时间定在次年1月中旬。
12月20日,根据日方安排,汪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汪精卫偕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萧叔萱等赴日,与东条英机等秘密磋商“参战”及实施对华新政策的有关问题。此次汪日密谋的主题是:“两国如何协力大东亚战争,如何使国民政府有效地发挥其意志和力量,分担完成战争责任等问题。”[③c]双方约定:汪伪政府“参战”日期为1943年1月15日。25日,汪精卫在东京发表《告日本国民》,表示“决与友邦日本同心协力,共安危,同生死”,使“大东亚战争”得到最后胜利[④c],发出了即将“参战”的暗示。
1943年1月初,日本政府秘密获悉:美国国会即将审议通过“中美平等新约”。为了抢在美国之前,实施日本“交回”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和汪伪政府向英、美“宣战”,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于1月7日深夜往访汪精卫,要求汪伪政府配合东京提早宣布“参战”[⑤c]。
1月9日,汪伪政府发布文告,宣布:“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汪精卫和重光葵签署《共同宣言》,声明“为完遂对美国及英国之共同战事,兹以不动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作完全之协力”。随后,重光葵又照会汪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要求对中国境内除美、英以外之敌性国财产,“与帝国采同样措置”。褚民谊复照表示同意。
对于日本来说,汪伪政府的“参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意义超过军事上的意义。日本统治集团完全明白:汪伪政府并无实力,不可能在对美、英作战中起作用。日本政府的意图,主要在于运用汪伪政府为工具,在中国沦陷区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从各方面“协力”日本与英美的“决战”。对此,《东京每日新闻》评述说:“国府参战之实质”在于“大东亚战力的培养”,由于汪伪政府实力不足,不能要求它“参了战就派兵到第一线去,前线的武力战争依然不能不成为日本的单独战争,而如果没有大东亚的战力培养,则长期的武力战将发生困难,这重大的使命应由国民政府负担起来”[①d]。
对于汪伪政府来说,在太平洋战局已朝着不利于日本方向发展时,汪精卫集团为什么反而主动要求“参战”呢?首先,汪精卫等人对于日本战胜美、英抱有侥幸心理。他们认为如果日本“胜利”,“参战”就可以“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占一席位”。当有人建议不宜主动向日本要求“参战”时,汪氏回答:“万一抗战失败,吾人非此不能取得战后之国际地位。”[②d]周佛海更直率地指出:“假如英美打胜仗,这个时候我们难道因为没有参战而能得到英美的原谅,而能免去英美对我们的宰割吗?万万不能的”;“我们绝对不能以为不参战,就可以获得重庆方面的原谅,而为将来留余地”;“不成功,便成仁,假使失败,我们还能腼颜乞怜以求苟全吗?”[③d]汪氏集团对于太平洋战争发展的形势估计是比较乐观的。他们认为:“就军事说,太平洋的军略要点,都被友军占领了;已占领的各地,一年以来已巩固了坚强的防御准备,这就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英美以为持久战,可以获得胜利,殊不知时间越久,友邦在占领地的地位越巩固,建设越发展,英美反攻,更不容易”[④d]。其次,汪伪政府的“参战”也是为了实现他们企盼已久的“统一”目标,提高“独立自主”的地位。再次,汪伪政府还打算以“参战”为条件,向日本要求“收回”租界,“撤废”治外法权,“接收”英、美等在沦陷区的权益,并进而谋求废除《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另订新约。
汪伪政府“参战”后,针对其内部的种种疑虑和议论,汪精卫等撰文说,他们参战完全是“自动的参战”,是“以独立自主完全自由之立场,与东亚诸邻邦,及世界诸友邦,同心协力,步于保卫大东亚战争之联合战线”[⑤d]。但是,汪伪政府实际上并未派兵作战,而是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将中国沦陷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使日汪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
三
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日汪调整关系的又一重要内容,是日汪交涉“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
早在1938年11月20日,日汪在上海重光堂会谈中就曾商定:“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内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承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日本在华租界”,作为“议和”条件之一[①e]。次年12月30日,日汪签署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再次重申:日本政府“考虑租界及治外法权等之交还”[②e]。1940年11月30日,日汪签署的《基本关系条约》又对此作了类似的规定。然而,这些约文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仅是为了标榜“中日亲善”而开出的空头支票,并不准备兑现;汪伪政府却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有机会就与日方交涉,催其兑现诺言。汪伪政府外交部曾拟定《关于收回租界之研究》,设想“以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为中心,以次推及其他各租界”,并准备了对内对外的各种具体方法[③e]。由于日方反应冷淡,这些设想毫无结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英美等国在华租界,名曰“代管”,实即占为己有。延至1942年2月18日,日本占领军才将广州、天津英租界移交汪伪政府,但同时又作了种种限制性规定,如将两租界区域暂定为特别行政区,“关于行政上之机构及行政之实施,应与当地日军最高指挥官密切联络”,“一切事项应经由特务机关长”;租界内接收之英美公馆及其他权益,除在行政实施上有必要移管外,其余“仍由日本军管理”;租界地治安警备,应受日军警备司令处理,“由中日两国军警互相协力担任之”;“日本军为管理所接收之权益及保护监视敌性人,在特别行政区内配置一部分之军队”等[④e]。如此“移交”,连后任大东亚相的青木也承认:“在名义上,虽然将租界退还中国,但租界内之仓库、房屋、及其他值钱物品,均将收归我有。于是,在租界内,不复残留一丝一缕,这种退还方式,中国民心之离反,殆属势所必然。”他极力主张“重新考虑,改弦更张”,将“归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作为推行对华新政策的重要内容,以适应太平洋战局变化之需要[①f]。
日汪间原来约定于1943年1月15日签约实施“归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但是出于催促汪伪政府提早“参战”同样的理由,签约日期被提前至1月9日。这天,由汪精卫和重光葵在南京签署《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主要内容是:日本政府将中国境内之专管租界行政权“交还”汪伪政府,承认汪伪政府尽速“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及北京公使馆区域行政权;日本政府“速行撤废”在华治外法权,汪伪政府承诺“开放其领域,使日本臣民得居住营业,且对于日本国国民不予较中华民国国民为不利益之待遇”等[②f]。
3月9日,汪日签署了《日本交还在华专管租界实施细则条款》及《附属谅解事项》。规定日本于3月30日将在杭州、苏州、汉口、沙市、天津、福州、厦门及重庆之日本专管租界行政权实施交还,专管租界内之道路、桥梁、阴沟、沟渠及堤防等设施“无偿移交”汪方;汪伪政府按照现状,“尊重并确认”日方在专管租界内所有不动产及其他权益,并接用从来日方雇佣之中国籍巡警及从业员等[③f]。同日,重光葵照会褚民谊,提出5项希望条款:1.汪方承担租界内日本居留民团等为建造公共设施负有的债务;2.确认各地租界原约中以永租、租借、借地等文句所规定的权利“一律改为永租权”,其地租“避免急剧之变化”,“暂时维持现行之税率”;3.“所有旧租界地域不设立类似过去之特别行政区,而并入所在都市的一般行政组织”;4.日本居留民团代表与中国当局“定期或应需要随时会合举行恳谈”,疏通双方意思;5.保障侨居租界内之日本臣民之居住、营业及福祉等[④f]。说是“希望”,实质上是“指令”,汪伪政府自然只能照办。3月30日,除重庆外,其他7地的日本专管租界行政权分别“移交”汪伪政府接管。
3月22日,褚民谊和重光葵在南京签署《关于日本交还北京公使馆区行政权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谅解事项》。日汪约定:3月30日,由汪伪政府“实施收回”该区行政权;该区域内之道路、桥梁、阴沟、沟渠、障壁等设施,应与隙地同时无偿“移交”汪伪政府;汪伪政府承诺按照现状,“尊重并确认”日方在该区域内所有不动产及其他权益,“并应对此取必要的措置”等[⑤f]。在日本政府的干预下,与汪伪政府有“外交关系”的意大利政府、法国维希政府、西班牙政府,或与汪伪政府签署相关条约,或发表有关声明,同意“交还”北京公使馆区行政权。
3月27日,褚民谊和重光葵在南京签署《关于日本交还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了解事项》。日汪约定:3月30日汪伪政府“实施收回”该区行政权,条件类似“收回”北京公使馆区行政权。同日,重光葵照会褚民谊,提出了关于确认租界内日人土地权利、厦门中日军事协力及经济提携等希望条件,并赞同汪伪政府将厦门市改为直属于伪行政院的特别市[①g]。5月28日,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工部局宣布解散,该租界行政权由汪伪政府“接收”[②g]。
自1943年1月开始,褚民谊先是与重光葵,后又与日本新任驻南京大使谷正之就上海公共租界的“交接”进行谈判。6月30日,褚民谊和谷正之在南京签署《关于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条款》及其《附属谅解事项》,内容大体与日汪关于日本“交还”日本专管租界条款相似。同日,褚民谊和谷正之互换照会,确认“鉴于上海所占地位之重要”,在“中日协力”方面应采取下列措置:1.“市政府令其所接用之工部局职员及其他被雇佣者之日籍人员退职时,事前由中日两国当地地方官宪间协议之”;2.“市政府经中央政府之许可得聘用日籍经济顾问,必要时得聘用日籍技术顾问”;3.设置中日联络恳谈会,“由市政府高级人员及日本居留民方面代表合组之”,凡影响于日方的重要市政事项须预先咨询,并充分尊重日方所陈述之意见等[③g]。这表明日本仍然保持着在该区域的重大权益和影响。
8月1日,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举行“交接”仪式,汪伪政府由此“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随即,汪伪政府对原租界的行政、警务、司法机构作了全面调整,以使其归于“统一”[④g]。
日汪间“撤废”日本在华治外法权的交涉经历了更为复杂的过程。1943年1月,双方的交涉委员会即告成立。3月24日,举行首次会议。但是,由于日方的原因,谈判迟迟没有取得进展。
“撤废”治外法权将使长期以来在华横行不法的日本侨民受到限制,因此首先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日本各方意见也不一致。经反复协调内部意见,7月2日,日方在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召开会议,确定最后成案。7月3日起,日汪交涉委员恢复会谈,日本提出“撤废”治外法权先从课税问题着手,也就是说,日本政府只同意部分地“撤废”治外法权。
7月31日,褚民谊和谷正之签署《日本在华臣民课税条约》及《附属协定》、《了解事项》。同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发表谈话,对该条约及有关规定作了有利于日本侨民的解释:1.日本在任何场合下,“不受较次于中华民国国民之待遇”;2.日人应服从的法令范围及适用方式,应由汪伪政府事先通知日方,“无通告,即无服务之义务”;3.汪方应根据“战时中特殊事态,及其他理由”,对日方军人军属、军用供给物资、民团民会等公共设施的课税,“加以减免之特殊考虑”;4.日本在华领事裁判权未撤废前,日人“违背法令之司法上措置”,“仍由日本国领事馆行之”;5.日人违反法令,只能“用行政处分,不用强制力”,汪伪政府官宪不能对日商实行“检查、查封、拍卖等强制执行及没收等强制行为”,当日人对汪伪政府官宪的行政处分有不服时,汪伪政府应有“适当之纠正措置”;6.汪伪政府对于日方认为不适当的“通过税及其他不适当课税”,“应从速整备”等[①h]。由此可见,日本政府虽然允诺自8月1日起,在华日人须“服从中华民国课税法令”,作为日本“撤废”在华治外法权的第一步,然而,在如此苛刻的限制之下,所谓的“服从”也就大打折扣了,而全面“撤废”在华治外法权更是成了一句空话。
“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表明日汪关系在日本对华新政策影响下已有所变化,为此被日汪吹捧为“中日亲善史上最光荣的一页”[②h]。汪伪政府头目更是满意地认为:“百年来英美等国经营中国之根据地从此消灭,租界亦成为历史上之名词矣。和平运动是否成功,固属将来问题,但历史总可算有一笔交代矣!”[③h]然而,实际上这却是日本侵华史上最富于欺骗性的一幕,连汪伪政府本身都完全在日本占领军严密控制之下,一言一行无不受到日人监督,在此种情况下,所谓的“交还租界及废止治外法权”岂不是最可笑的骗局吗?
四
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日汪调整关系的第三方面内容,是日汪废弃《基本关系条约》,重订《同盟条约》。
1942年11月27日,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在讨论制订对华新政策时,东条英机就提出《基本关系条约》是否“应加以修订”的问题。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表示赞同,认为目前的根本目的是对美英的战争“战胜第一”,“对于以前条约,也不妨重新加以检讨”。藏相贺屋兴宣也主张:“既有条约,苟有不正之处,即应加以修正。”[④h]于是,12月21日御前会议决定将修正《基本关系条约》作为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内容之一。
在汪伪政府方面,自1940年11月该条约签署以来,就一直表示不满。周佛海认为:该条约“处处表示日本控制及分割中国之心,盖驻兵规定为其一,华北及内蒙等地特殊化为其二”[①i]。陈公博则批评说:该条约“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条约”,日本口口声声赞扬“东亚新秩序”,但该条约的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②i]。日本政府实施对华新政策后,汪伪政府趁机要求日本政府废止该条约及秘密协定和附件。
3月起,日、汪高级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互访,就解决华北特殊化等日汪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及废止《基本关系条约》等问题进行磋商。3月13日至14日,东条英机作为日本战时首相首次访问南京和上海,和汪伪政府要人进行会谈,讨论了日本军事援汪和取消华北特殊化等问题。4月1日,汪伪政府以感谢日本“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为由,特派陈公博为特使访问日本,其真实意图则“以修订条约、取消华北特殊化为要点”[③i]。此行虽然没有取得结果,但双方无疑已就修订《基本关系条约》问题正式进行了接触。
8月19日,日本政府特派大东亚相青木一男访问了南京、上海、北京以及东北各地,了解实施对华新政策后中国沦陷区实况,为修订《基本关系条约》作准备。9月21日,日本政府邀请汪精卫、陈公博秘密赴日,商谈修约问题。东条表示:如果全面和平实现,日本不仅撤退在华全部军队,而且放弃《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兵权。目前,将努力取消各地特殊化的情况,以加强汪伪政府的权力[④i]。日汪间初步商定了修改的基本原则。随后,由汪精卫和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继续进行谈判。
10月13日,谷正之将日本政府草拟的“新约”共5款面交汪精卫。该草案“将二十九年(1940年)所签之各项条约以及附属文件完全取消,即驻兵及各地特殊现象、经济上优先要求均取消”,但“中日满共同宣言仍然有效”,并且“条约所规定者,均须和平实现后始能实现”等[⑤i]。汪精卫等认为:该草案乃“望梅止渴”,提出“除撤兵须待战争终了始能实施外,其余在全面和平实现前亦宜逐步实施,即一面高悬理想,一面仍宜改善现实也”[⑥i]。自15日起,日、汪双方就该草案举行了三次会谈,达成协议。30日,汪精卫和谷正之在南京正式签署《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主要内容是:1.“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2.“为建设大东亚并确保其安定起见,应互相紧密协力,尽量援助”;3.“实行两国间紧密之经济提携”;4.《基本关系条约》及其一切附属文书等一并失效;5.日本承诺在战争状态终了时撤去其派在中国境内之日本军队,放弃在中国的驻兵权等[①j]。
《同盟条约》被汪日吹捧为“中国近百年来独一无二的平等条约”。汪精卫在庆祝该约签署大会上发表长篇训词,颂扬该约“在中日关系开一新纪元,在东亚开一新纪元,中日两国从此以后,完全站在平等互惠立场,结成永久友好关系,以共同致力于大东亚之建设”[②j]。陈公博甚至在战后接受审判时还在辩解:“同盟条约内容,已取消一切密约附件,更取消所谓华北驻兵及经济合作,而且更将内蒙返还中国。所剩下来的,只有一个东北问题了。”[③j]然而,不管日本军国主义者如何吹嘘,也不管汪伪政府头目们如何辩解,这终究仍是一个骗局。就在签约的同日,汪精卫和谷正之又互换照会约定:“现在中华民国所存既成事实,如鉴于本条约之旨趣,须调整者,应于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终了时,准据条约之旨趣,加以根本的调整。”[④j]也就是说,只要战争状态继续存在,日本占领军当局就可以自由决定在何种程度上履行条约,或者根本不履行条约。
五
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日汪调整关系的第四方面内容,是“树立民国政府(汪伪政府)的中心势力”,并由汪伪政府来“统一”华北、华中、华南各沦陷区由日军扶植的地方伪政权。
汪伪政府是由日本侵略军一手扶植和控制的,不仅一切行动须听命于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而且名为“中央政府”,实际管辖地区只限于上海、南京、广州、武汉以及苏、浙、皖、赣等沦陷区。“华北政务委员会”管辖着北平、天津、青岛以及冀、豫、鲁、晋等省沦陷区。“蒙疆自治政府”则统治着绥、察等省沦陷区,完全独立于汪伪政府之外。此种状况,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实行“分而治之”策略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军阀和财阀内部、中国亲日派内部的利害矛盾和冲突的反映。
1942年12月,日本御前会议在关于对华新政策的决定中,确定了由汪伪政府“指导”各沦陷区日军扶植的地方政权的原则,并把“极力调整占领地区内的地方特殊性,加强国民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作为“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的主要措施。日本大本营、政府制定的“具体策略”更强调“加强国民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领导”,“消除中央和地方之间无意义的摩擦”,“酿成融洽的气氛,使中央和地方一起成为更新中国的构成部分,同心协力为完成战争而迈进”[①k]。同时,对于汪伪政府同“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及武汉、厦门、海南岛、蒙疆地方傀儡政权间的关系作出了调整的安排。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汪伪政府开始调整各沦陷区傀儡政权间的关系。汪伪政府最为不满的是,“华北政务委员会”自成一体,与南京“中央”分庭抗礼。在他们看来,“武汉、广州之不能实行国府统一管理,因为战争关系,接近前线,尚可理解,而华北俨然独立国,最不能令人信服”[②k]。汪伪政府为此首先企图实现华北的“中央化”。措施之一,是任命“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兼任汪伪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和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由汪精卫兼任华北新民会名誉会长,在经济上,以“统制经济”为借口,向华北渗透,在思想上,以一个主义(大亚洲主义)、一个党(汪记国民党)、一个领袖(汪精卫)为旗帜,“统一”华北。措施之二,是进而逼迫反汪的王揖唐辞职,改组“华北政务委员会”,以朱深代王揖唐继任委员长,从而扫除实现华北“中央化”的一个障碍。措施之三,是汪伪政府与“华北政务委员会”间互相派驻代表,协调双方行动。
汪伪政府与“华北政务委员会”之间的联系经过此番调整有所加强。2月9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宣布自即日起禁止悬挂五色旗,改悬汪伪政府使用的“国旗”,此举被汪方吹嘘为“从此不但在实质上,并且在形式上表现了南北的统一”[③k]。7月14日,新任委员长王克敏(朱深于7月2日去世)赴南京“晋谒”汪精卫,报告就职经过,并向记者发表谈话称:“华北为中央之华北,华北政委会系属国府编制下之机构,今后一切庶政措施,自当秉承中枢意旨办理。”[④k]从表面上看,“华北政务委员会”已“归顺”中央,但实质上由于日本华北方面军的严密控制,其独立王国的地位没有也不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汪伪政府与日方交涉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淮海地区的管辖权问题。淮海地区是指华北、华中接壤的苏北、皖北地区。1939年底,日汪在组建中央政府的谈判中,日本军方曾同意华北疆界南延至山东省为限,将原由华北临时政府管辖的该地区划归汪伪政府管辖。但实际上该地区却始终为日本华北派遣军及其所控制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掌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方稍作让步,同意将该地区“从华北分离,改为国民政府(汪伪政府)的直辖区域”[①l]。据此,1942年1月15日,汪伪政府在该地区设置了直属行政院的苏淮特别区,在徐州设立行政公署,任命郝鹏举为行政长官,辖区包括江苏、安徽的1市21县。但是,该地区虽在行政上归属汪伪政府,但根据日本军方意见,“为了防止因急剧变动引起人心动摇”,该地区的“财政、治安、教育、交通通信事业、通货等仍保持现状”[②l]。因此,该地区的管辖权问题实际上仍未得到解决。
1943年1月,汪精卫偕同周佛海、林柏生等视察徐州,并在苏淮特别区公署成立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表明决心掌握该地区行政权的态度。然而,延至次年1月13日,汪伪政府才得以决定将苏淮特别区改称淮海省,由郝鹏举任省长、保安司令兼汪记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2月19日,汪伪政府财政部宣布自3月1日起在淮海省禁止发行“联银券”,但不禁止流通。4月进而实行“中储券”与“联银券”的兑换,10月禁止“联银券”在市面流通。由此,取得了该地区的金融统治权。然而,日本占领军决不会让汪伪政府真正“统一”治理华北、华中沦陷区,“直至战争结束为止,在华北华中一体化问题上仍是一个悬案”[③l]。
如果说汪伪政府在“统一”华北、淮海沦陷区问题上与日本军方的交涉还取得某些表面的和局部性的进展,那么,它为“统一”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而与日本军方的交涉,可以说是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日本占领军利用德王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晋北、察南、绥远地区建立的傀儡政权。1941年春,在日本军方的压迫和操纵下,汪蒙双方虽曾签署“协定书”,确定双边关系[④l],但是,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方面却始终不承认汪伪政府的“中央”地位。6月,当汪精卫去张家口视察时,遭到德王的冷遇,双方关系益见紧张。1943年春,汪伪政府将其“统一”活动推及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所辖地区。为此,拟定了“蒙古自治法草案”,表明汪伪政府“统一”蒙疆地区的企图。同年3月,汪精卫委派和平建国军第四路总指挥杨中立将该方案送往张家口,然而这个方案还未与德王见面,就被当地日军否定。虽然汪伪政府的举动本是在日本军部支持下进行的,但日本当地驻军此时为了防止苏联从北部发动袭击,仍然加紧对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直接控制,不容汪伪政府“越权干涉他们在蒙疆的既得利益”,毫不留情地将杨中立顶了回去[⑤l]。7月12日,汪精卫等在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会谈时,再次提出“统一蒙疆”的要求:“蒙疆虽称自治,但另有年号,另有旗帜,俨然为一独立国,盼日方援助,促成中国统一,勿令此分裂状态长此下去。”[①m]但汪氏的要求没有取得结果。实际上,日本占领军依然不允许汪伪政府过问“蒙疆”的事情。
六
日本对华新政策下日汪关系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假手汪伪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谋和”,企图实现所谓的“全面和平”。
日本的这一策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利用汪伪政府的所谓“独立自主”作广告,引诱重庆政府和日本握手言和。日驻南京大使重光葵认为:“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订立“同盟条约”等,实行此种政策的意思就是“对中国(指重庆政府)之政治策略工作,它与武力的压迫相策应,同为对中国政府之极大压力”[②m]。另一方面,是利用汪伪政府对重庆政府进行“劝降”。日本政府认为,当时由蒋介石“统率之中国抗战阵营之核心,在反轴心国之战局有利之现况下,仍具有强国之继战意志”,再要强迫蒋介石订立城下之盟是不可能了;然而,他们又认为,重庆政府正面临着许多困难,“视条件之如何,亦难谓为并无实现和平之可能性”[③m]。根据日本政府的情报:重庆政府在宋美龄访问美国时得知,“英美对于苏联潜在实力之强大重新作估计,大为恐慌。可以对此防御的,西为德国,东为日本,所以认为彻底打倒两国,并非得计。从这个观点,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与日本谈判”[④m]。因此,日本政府极力谋求利用汪伪政府对重庆政府进行“劝降”。
1943年1月,汪伪政府对美、英“宣战”后,就不断派人就“中日全面和平问题”与重庆当局联络,其核心人物是周佛海。1月4日,周佛海委托国民党“中统”特工陈宝骅“带缄交孔庸之(祥熙)、钱新之、杜月笙及果夫、立夫、布雷六人,劝其时机如到,主张和平,余在外力助其成”[⑤m]。2月2日,汪伪政府又让国民党“军统”特工刘百川转告渝方:“国际关系瞬息万变,英美必留日本之势力以牵制苏联,故日美妥协尽早必实现,渝方应注视此点,如日美有妥协之倾向,即宜着先鞭与日和平,不可追随美国之后与日妥协,盖前者为主动,后者为被动,利害得失固可预见也。”[⑥m]4月5日,在周佛海等人一再活动疏通下,日本占领军当局同意将在上海抓获并已软禁1年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用飞机送广州,转道回重庆,传递“和平信息”。
在此前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不断与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以及军部代表辻大佐、都甲大佐、永井大佐、川本大佐等商谈所谓“全面和平”的条件。9月,汪精卫多次与谷正之会谈,“最关心的是撤兵问题,如果蒋提出与英美切断关系,希望日本也撤兵时,日本是否肯答应”,要求日方明确表示态度[①n]。10月2日,周佛海向日本军部代表川本大佐指出:“重庆对日不信任,如何取信于渝,乃为先决问题,而欲取信于渝,先须见信于南京政府下之人民,今日本所约定者多不能实行,其能使重庆信任日本之诺言耶?”[②n]10月4日,周佛海又直接向谷正之指出:“中日全面和平”之能否实现“全在日本做法如何而定,如以在和平区日本之做法视之,则重庆决不和。‘言必信,行必果’为日本做法今后应取之途径”[③n]。这表明汪伪政府在帮助日本政府劝降重庆当局时,也利用日本决策者们急于“谋和”的心情,迫使日方在某些问题上作出让步。
1944年7月,日本东条内阁倒台,继任的小矶内阁面临比前任更为严重的局面。8月,日本新成立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对外政策“以斡旋德苏和解及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为中心课题”[④n]。9月5日,该会议又制定《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规定对重庆政府的“政治工作”经由汪伪政府进行,由汪伪政府派遣适当人员到重庆去,“制造彼此之间直接会谈的机会”,必要时“使苏联成为这项工作的居间人”[⑤n]。
4天后,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制订了“对国民政府传达有关《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的要点”。9月中旬,日本陆军省次官柴山兼四郎抵达南京,向汪伪政府要员陈公博、周佛海等传达日本政府的决策。9月13—14日,柴山兼四郎与陈、周进行会谈。柴山表示:“日政府虽明知形势不利,时机不顺,不易成功,但仍盼积极进行全面和平合作”,但此次“谋和”由汪伪政府出面进行,“且不可使外间知系日方所发动”;日方实行“全面和平”的条件是:1.纯以平等立场讲和;2.如美国撤退在渝空军,日即全部撤兵;3.渝与英美之关系,尊重渝方意见决定;4.关于保证问题,俟确知渝方意见后决定;5.关于宁渝汪蒋问题,乃中国内政问题,由双方商办等[⑥n]。为了保证“谋和”的顺利进行,柴山还特别说明该项工作“由首相和外相联系,一切要南京政府采取措施,不让当地军方干预”[⑦n]。经过会谈,陈公博表示对于日方企图“当努力求其贯彻”,周佛海也说要“遵命办理”,“无论如何都要抓住机会,完成预定目标”,并商定:“通过无线电与重庆联系,不是很好的办法”,必须直接派人去联络[①o]。9月28日,陈、周决定派遣重庆要员张公权妹婿朱文雄赴重庆,向重庆最高当局转达日方和谈条件。然而,朱文雄一去,便杳无音信。直至次年5月底,朱氏才返回上海,但“并无具体结论”。
1945年春,由于汪伪政府的“谋和”工作毫无进展,小矶内阁决定改变方针,“由日本政府自己直接进行缪斌工作”。至此,日汪策划“全面和平”的活动终于被迫全部收场。
综上所述,日本对华新政策是在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发生激烈变动的情况下提出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并将中国沦陷区建成“大东亚战争后方基地”,不得已改变对华政策,放松对汪伪政府的某些限制,这使日汪关系出现了某些变动。汪伪政府一方面屈从日本要求,对英、美实现“宣战”,全面实施战时体制,疯狂掠夺战略物资,强化对沦陷区人民的军事独裁统治;另一方面,也利用这个机会,力图从日本占领军手中争取若干权益,如“收回”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废除《基本关系条约》,改订《同盟条约》等,以此改善自身的形象。然而由于日本对华政策的本质没有变化,汪伪政府的傀儡政府地位也没有变化,日汪关系“调整”的结果是微乎其微的。它既不能挽救日本军国主义的最终失败,更不能改变汪伪政府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必然命运。
注释:
①a启常:《日寇对占领区统治一元化的企图》,1942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
①b〔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东京1969年版,第580—581页。
②b黄和材:《日寇对华新政策的分析》,《新中华》复刊第2卷第1期。
①c汪兆铭:《勖中国民众》,《政治月刊》第3卷第1期。
②c周佛海:《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政治月刊》第5卷第2期。
③c林柏生:《在东京答日本记者问》,1942年12月23日《新中国报》。
④c汪兆铭:《告日本国民》,1942年12月26日《中华日报》。
⑤c《周佛海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1943年1月7日。
①d廖今天:《汪逆参战与敌寇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1943年3月25日《解放日报》。
②d褚民谊:《参加和运经过自述》,藏江苏省档案馆。
③d④d周佛海:《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政治月刊》第5卷第2期。
⑤d汪兆铭:《告将士书》,1943年1月19日《中华日报》。
①e《日华协议记录》,转引自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页。
②e《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转引自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建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2页。
③e汪伪政府档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件署1939年6月,有误。按照中文内容推算,文件形成时间当在1940年3月汪伪政府建立以后。
④e《移管广州沙面英租界行政之纲要》,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①f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第2卷,台湾军事译粹社1978年版,第176、177页。
②f《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500—501页。
③f1943年3月15日《中华日报》。
④f汪伪政府档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⑤f《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502页。
①g汪伪政府档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②g《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499页。
③g汪伪政府档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④g唐学明:《上海租界收回后的新猷》,《政治月刊》第6卷第3、4期。
①h《日使馆当局谈话》,《政治月刊》第6卷第3、4期。
②h1943年3月5日《中华日报》。
③h《周佛海日记》,1943年8月1日。
④h《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第2卷,第177页。
①i《周佛海日记》,1943年9月24日。
②i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藏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档案室。
③i《周佛海日记》,1943年4月5日。
④i蔡德金等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
⑤i《周佛海日记》,1943年10月13日。
⑥i《周佛海日记》,1943年10月14日。
①j汪伪政府档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②j汪兆铭:《永久友好关系之结成》,《政治月刊》第6卷第6期。
③j陈公博:《对于起诉书的答复》,藏江苏省档案馆。
④j汪伪政府档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①k《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580—581页。
②k1943年4月15日《中华日报》。
③k汪正禾:《一年间的国内大事》,《申报年鉴》,1944年度,第9页。
④k1943年7月17日《中华日报》。
①l②l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67页。
③l《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卷,第68—69页。
④l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1页。
⑤l《蒙古“自治运动”始末》,第257页。
①m《周佛海日记》,1943年7月12日。
②m《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第3卷,第247页。
③m《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第3卷,第19页。
④m〔日〕《木户幸一日记》,1943年9月18日,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
⑤m《周佛海日记》,1943年1月4日。
⑥m《周佛海日记》,1943年2月2日。
①n〔日〕《木户幸一日记》,1943年9月18日。
②n同上书,1943年10月2日。
③n同上书,1943年10月4日。
④n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世界形势的判断及战争指导大纲》,转引自《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601—604页。
⑤n《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605—606页。
⑥n《周佛海日记》,1944年9月13日。
⑦n《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21页。
①o《柴山中将报告》,转引自〔日〕参谋本部《战败的记录》(1967年),第177—179页。
标签:汪精卫论文; 褚民谊论文; 汪伪国民政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治外法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