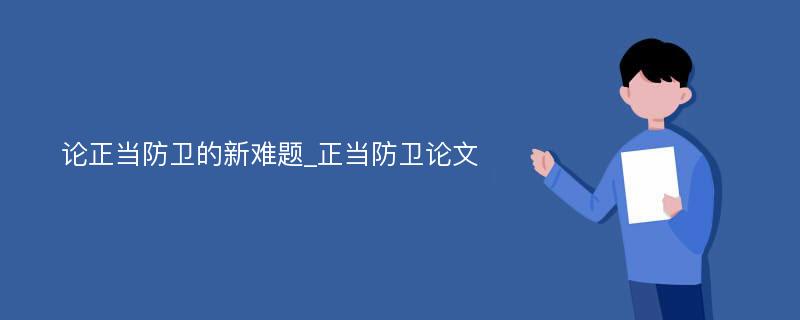
正当防卫新型疑难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当防卫论文,疑难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246(2001)04-0025-05
我国1970年刑法典第17条第2款曾规定:“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指明,防卫必须在必要限度之内,才是正当的。但是,如何认定和把握防卫的必要限度,法律并未作明确规定。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正当防卫之必要限度的理解成了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在争论中,主要产生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1)基本相适应说。认为所谓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就是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在性质、手段、强度和后果上要基本相适应。(2)必需说。认为所谓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就是防卫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限度。只要所造成的损害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不如此就不足以制止不法侵害,即使防卫在强度、后果等方面超过对方可能造成的侵害,也不能认为是超出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3)相当说。认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在原则上应以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为标准,同时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在手段、强度等方面,不存在过于悬殊的差异。
与1979年刑法典相比较,新刑法典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有了重要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明确和放宽了(一般)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其二是增设了关于特殊防卫的规定。上述修正引起了刑法理论对于正当防卫诸问题的新的思考。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新规定的理解和把握不一致,也出现了执法不尽统一的状况。为了推动理论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给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意见,本文拟对这两个新问题进行研析。
一、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问题
(一)对基本相适应说、必需说和相当说之回顾
上述三种观点中,基本适应说提出了必要限度的特征,即承认相适应不是绝地等同,而是可以超过,但同时又强调不能明显超过,差距过大,此种学说有利于保障公民正当防卫权的行使,也能防止防卫者滥用权利,故而有其合理之处。但它仅从防卫和侵害两方面的性质、强度等客观特征上加以权衡,没有考察防卫者的主观目的,因而缺乏考察问题的高度,有可能导致将那些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虽然基本相适应,但却非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情况作为正当防卫处理,从而会不适当地扩大正当防卫的范围。而客观需要说以防卫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作为必要限度的标准,强调了防卫目的的正当性,因而抓住了理解必要限度之关键。但是这种观点过分强调客观需要,而完全忽视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的相当性,没有对防卫者设定必要的约束,有可能导致防卫者滥用防卫权,从而给不法侵害人造成不适当的损害。上述相当说实际上是客观需要说与基本适应说的有机结合,既抓住了理解必要限度的本质的、关键的特征,有利于鼓励公民实行正当防卫,又提出了对防卫者的必要约束,有利于保障正当防卫的正确行使,从而汲取了基本适应说与客观需要说的合理之处,避免了两者之不足,可谓是合理而可取的主张。正是鉴于此,相当说后来逐渐成为我国刑法理论上的通说和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的主导理论。
(二)在新刑法典规定下,相当说是否仍有价值
针对1979年刑法典关于正当防卫之限度条件规定不尽明确、难以操作、不利于划分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界限、不利于鼓励群众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缺陷[1],新刑法典对之作了重大修改。根据新刑法典第20条第2款“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应该说,这一修改对于充分体现正当防卫旨在鼓励和支持人们积极地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有效地保护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纠正以往司法实践对正当防卫之必要限度把握过苛的偏颇,争取我国社会治安状况尽快好转,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何谓“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仍有待明确,仍得求助于刑法理论的研究。显然,对“必要限度”作出正确认识和阐释,是理解何谓“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前提。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此前的刑法学界的“基本相适应说”、“必需说”和“相当说”之争仍有重要的回顾价值,“相当说”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仍应得到充分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认为,新刑法典放宽了对正当防卫权的限制,根据新刑法典的规定,基本相适应说是不能成立了,相当说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只有必需说适合新刑法典的规定。事实证明,必需说是正确的。必需说并不主张对防卫手段不加任何限制,“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这就是限制[2]。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即使在新刑法典第20条第2款规定之条件下,必需说容易导致防卫权的滥用、给不法侵害者造成不适当损害(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重大的损害)的缺陷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该种观点仍然是应予摒弃的。的确,新刑法典放宽了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但是,并未放宽到凡是为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需都不为过当的程度,而是仍然强调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的相当性,只不过与旧刑法典相比,新刑法典对正当防卫之相当性的把握标准作了适当放宽(如前所述),而这一放宽也才真正是新刑法典对正当防卫权的放宽之处。换言之,根据新刑法典,如果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即失去相当性,纵使是为“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仍然应当认为防卫已经过当,而不能成为正当防卫。
(三)如何理解和把握“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以及“造成重大损失”
基于上述论述,我们认为,新刑法典中所谓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是指防卫行为不是非常显著地超出了制止不法侵害的需要,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与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不是过于悬殊。所谓的“没有造成重大损害”,应当是指防卫行为虽然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并未造成重伤、死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等重大的损害[3]。
应当注意的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实质是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一体两面。“造成重大损害”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具体表现;“超过必要限度”是“造成重大损害”判断标准。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所谓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换言之,只是在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才存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问题;不存在所谓的‘手段过当’而‘结果不过当’或者相反的现象”[4]。
二、特殊防卫问题
新刑法典第20条第3款的规定是全新的。该款设立后,在刑法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学者们对该款规定是否必要、是否合理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析,各自提出了见仁见智的主张。本文立足于实务研究,同时为篇幅所限,不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仅准备结合已有立法,谈谈与特殊防卫之正确适用有关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如何妥当贴切地概括刑法典第20条第3款所规定的内容
对这一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尚存在着意见分歧。主要有三种不同见解:第一种见解将刑法典第20条第3款的规定称为“无限防卫权”;第二种见解将之概括为“无过当防卫权”;第三种见解则称之为“特别防卫权”或者“特殊防卫权”。
在我们看来,这三种概括其实并无实质区别。“特别防卫权”或者“特殊防卫权”的特别、特殊之处主要也正是体现其无防卫之必要限度或者说不存在过当情形上。持上述最后一种见解的学者认为,刑法典第20条第3款规定的防卫权并非一概无限度;称之为“无限防卫权”或者“无过当防卫权”容易致人误解而导致滥用这种防卫权,因此,“无限防卫权”或者“无过当防卫权”的提法不甚妥当[5]。我们认为其理由并不尽充分,甚或可以说并不完全正确。事实上,按照刑法典第20条第3款的规定,特殊防卫就是不存在限度问题,上述学者之所以认为其并非“一概无限度”,乃是由于他们自己对该条规定有关内容的不正确认识有关(对此,下文将作分析);解决这一问题后,其另一反对理由自也不复成立。当然,考虑到“无限防卫权”可以在多种意义上使用[6],确有引人误解之虞,宜尽量避免这一提法。
同时,我们认为,对刑法典第20条第3款,无论将之概括为“无限防卫权”、“无过当防卫权”还是“特殊防卫权”、“特别防卫权”,均不够严谨、妥切。因为,我们在概括刑法典第20条第1款的内容时,一般均径直称之为“正当防卫”,而不是“正当防卫权”;刑法典第20条第1款与第3款之间实质有某种对应关系,二者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因而,从此角度考虑,对刑法典第20条第3款,更为妥切的概括应当是“特殊的正当防卫”(或者无过当的正当防卫),简称“特殊防卫”(与之相对应,今后在概括刑法典第20条第1款的内容时,应当尽量使用“一般正当防卫”这一提法)。
(二)如何把握特殊防卫的起因条件
1.对刑法典第20条第3款规定的语法结构分析。
特殊防卫规定后,一些学者在特殊防卫到底是否一概无限度,以及如何理解刑法典第20条第3款之“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时产生了认识分歧:有些学者认为,刑法典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特殊防卫不是一概无限度的,“比如说,采用投毒方式进行杀人,利用迷魂药、麻醉药抢劫的,行为的暴力手段不明显,甚至不为人所知,如何行使特殊防卫权?又如‘行凶’,法条这一用词的含义就不太明确,动手打人一拳、推人一把从广义上也可称之为行凶,但为此可以将不法侵害人打死打伤,恐怕亦难于理解”[7];刑法典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杀人”即故意杀人罪,“抢劫”即抢劫罪和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强奸”即强奸妇女罪和奸淫幼女罪,“绑架”即绑架罪;至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的手段如何,亦即是否是以暴力手段实施,并非所问[8]。有些学者则认为,刑法典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特殊防卫不存在任何过当的可能,也即一概是无限度的;并不是对任何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进行防卫都可以适用刑法典第20条第3款的规定,而只有当这些犯罪是以暴力手段实施,并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时,才存在特殊防卫的问题。“例如,行为人以抢劫故意采用麻醉方法取得他人财物的,属于抢劫罪,但这种犯罪并非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对之进行防卫的,不适用上述规定(即刑法典第20条第3款的规定——笔者注)”[9]。
我们认为,对以上问题,之所以出现认识分歧,主要的原因是,不同学者对刑法典第20条第3款规定的语法结构分析有异:如果认为“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与其后的“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是并列关系,也即前者不受后者之“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限制,那么,对该问题无疑得出第一种结论;反之,若认为上述二者之间是例示与概括的关系,也即前者要受后者之“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的定语的限制,那么,对该问题显然会持第二种观点。究竟哪一种理解是正确的呢?我们认为,从文理来看,后一种理解比较科学。关键是要看到刑法典第20条第3款中的“其他”一词。“其他”一词表明,“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只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几个例示,只是其一部分,换言之,只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以暴力手段实施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才存在特殊防卫的问题。这样理解,也符合谨慎适用、防止曲解或滥用特殊防卫的精神。事实上,即使是持前一种观点的学者,大多也认为不能对任何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行为都进行特殊防卫。
2.对刑法典第20条第3款中有关用语之内涵的分析。
(1)“行凶”。
在解决上一问题后,显然应当有这样一种认识:“行凶”是指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以暴力手段实施的、构成犯罪的行凶。基于此,对未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非以暴力手段实施的,或者尚未构成犯罪的行凶进行防卫的,均不能适用刑法典第20条第3款的规定。那么,“行凶”是否必须是使用凶器或者是持械进行的行凶呢?有的学者对此持肯定意见[10]。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违背了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也不尽合理。根据刑法典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只要行凶行为已属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即可以对之进行特殊防卫;而某些并未使用凶器或者械具的行凶行为,比如,在不法侵害人的人数、侵害能力与被害人或者防卫人的人数、防卫能力相差悬殊情况下的行凶行为,同样也具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性质,对之自然可以依法进行特殊防卫,否则,也不利于保护被侵害人的合法权益。
附带指出,“行凶”一词出现在刑法典第20条第3款中,无论是从立法用语的严谨性考察,还是从条文的内在逻辑结构看,或者从谨慎适用特殊防卫之规定防止其滥用、误用的角度看,都是一个立法缺憾。对此,众多学者已经提出其中肯的批评意见,在日后修法时应予完善。
(2)“杀人、抢劫、强奸、绑架”。
大多数学者认为,“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是指以暴力手段实施的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绑架罪。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即是指具体罪名,也可以是指四种形式的犯罪手段,易言之,“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不仅是指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绑架罪,还包括这四种犯罪的转化犯罪(如使用暴力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而构成的故意杀人罪等)、根据立法推定而涵括的犯罪(即奸淫幼女罪)以及以这四种手段所实施的触犯其他具体罪名的犯罪(如以绑架方式实施的拐卖妇女、儿童罪、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等)。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理解在实际运用效果上实质是一致的。因为,如果将“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只解释为具体的罪名,则可以把以杀人、绑架等方法实施的犯罪等包纳在“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之中,从而得出对这些犯罪也能够进行特殊防卫的结论。但是,从文理上分析,前一种理解似更为妥当。理由在于:其一,“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中只有杀人和绑架可以勉强地认为是一种犯罪手段,而抢劫、强奸都是一种危害行为;不同层次上的范畴并列在一起,在逻辑上有难以说通之处。其二,将“杀人、抢劫、强奸、绑架”解释为既是具体罪名又是犯罪手段,易造成认识混乱,不如直接以是否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作为判断是否能够对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绑架罪以外的其他犯罪进行特殊防卫的标准。
(3)“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其一,此处的“犯罪”,显然是在刑法学的意义上使用的,是指违反刑法规定的,应受刑罚处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一般违法行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的具有客观危害性的行为,都不是“犯罪”。有些学者认为,“无限防卫权的起因不一定都是特定的暴力犯罪。对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的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如果防卫人不知侵害人的主体状况,则完全可以行使无限防卫权,如果知道这种状况,原则上也可以行使无限防卫权……。倘若将无限防卫权的起因限定在特定的暴力犯罪,则事实上剥夺了防卫人对这种不具有主体性的暴力侵害行为进行防卫的权利,被侵害人只能忍受暴力的侵害,这显然不公平。”[11]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这种观点把法条中明确使用的“犯罪”扩大解释为“侵害”,与罪刑法定原则有明显的悖离之处。其次,在特殊防卫之外,还存在一般防卫。因此,对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的暴力侵害不能进行特殊防卫,绝对不意味着被侵害人只能一味忍受此种侵害。他完全可以进行防卫,只要条件符合,他完全可以得到不构成犯罪、不负刑事责任的公平对待。
其二,此处的“暴力”,应是指进行有形的物理力的打击或者强制的犯罪手段。犯罪学意义上的“暴力”,或可理解为还包括以暴力相威胁的[12],但此处的“暴力”并不能作类似的理解。有些学者对此尚持不同看法,认为此处的“暴力”亦包括暴力胁迫。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13]。理由是:一方面,如果做这样的理解,将有破坏侵害与防卫的平衡状态、滥用特殊防卫之虞。因为,毕竟暴力胁迫尚未对被侵害人造成实质的危害,如果此时就允许被侵害人进行没有限度节制的特殊防卫,则对不法侵害人来说,是有失公平的;另一方面,将暴力胁迫排除在此处的“暴力”之外,并不会招致什么不利后果。因为,在特殊防卫之外,还有一般防卫,通过适用刑法典第20条第1款的规定,同样可以充分地保障被侵害人的正当防卫权。
认定某一不法侵害行为是否属于“暴力犯罪”,关键要看该侵害行为本身是否是以暴力手段实施。申言之,对暴力犯罪的界定,重要的并不在于刑法分则条文本身是否明文规定以暴力为犯罪构成要件,而在于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所采取的手段是否为暴力行为。不宜说所有规定有暴力为犯罪成立的要件的都是暴力犯罪,只有法律对犯罪有规定,并且行为人事实上是以暴力行为实施犯罪的,才能归入暴力犯罪的范畴或称之为暴力犯罪(如以利用他人处于昏迷状态强奸的犯罪就不能称之暴力犯罪)[14];也不能说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暴力手段的犯罪就一概不属暴力犯罪,举凡在事实上是以有形物理力方式实施的犯罪,均可纳入暴力犯罪的范围(如暴动劫狱罪、劫夺被押解人员罪等)。
其三,此处的“危及人身安全”,应是指不法侵害威胁或危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行动自由权或者性自由权等。
据此,上述的“暴力”,虽就其本身的内涵来看,既可以是对人实施,也可以是对物实施,但在加上“危及人身安全”这一限定语后,在实际上,显然只能是指对人采取暴力。换言之,对危及财产权的不法侵害,不论其性质和危害程度如何,都无进行特殊防卫之余地。
其四,此处的“严重”,是就不法侵害对人身安全的威胁和危害程度而言的,但是究竟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属“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尚难确定具体的、统一的认定标准。有些学者提出可以从具体罪名、具体案件中是否具有致人重伤、残疾或者死亡的威胁以及法定刑等方面来确定不法侵害是否已达到“严重”之程度[15],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比较可取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认为,为了防止滥用特殊防卫权,在判断某一侵害行为是否属于此处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范畴时,不能仅以该侵害行为本身是否“严重”(在法律上表现为要处以较重的刑罚)为据,而应当结合案发当时的具体情况,考察该行为是否已对被侵害人的重大人身权利有现实的或迫切的危害,而防卫人是否对之不进行特殊防卫就不足以制止不法侵害、不足以维护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安全。反过来说,如果根据案发时的具体情况,防卫人不需采取特殊防卫,照样可以制止不法侵害,照样可以有效保护本人或他人的人身权利的,就不应当允许他进行特殊防卫。比如,某一身体单薄的犯罪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手持匕首抢劫(单从该抢劫行为本身的性质来看,其无疑属于一种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恰巧该交通工具上有两个曾受过特殊训练的退伍军人。该两军人完全可以不费什么力气地夺下抢劫犯的匕首,并将其制服。此时,就不能允许他们进行所谓的“特殊防卫”,将抢劫犯致于伤残甚至死亡境地。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加上“严重”这一限定语后,上文的“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在实际上已不应包括那些危及住宅权、隐私权、人格权、名誉权的暴力侵害(主要是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侮辱罪等),因为,从这些犯罪的法定刑和实际危害来看,它们是无法容纳在“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范畴之内的。
总之,“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暴力”以及“犯罪”之间有着层层递进、相互制约的关系,此四者密切联系,共同构成特殊防卫实施之起因条件。
(三)特殊防卫与一般防卫的关系
我们认为,特殊防卫是与一般防卫相对而言、相比较而存在的,其构成仍应具备一般的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对象条件和主观条件。其区别于一般正当防卫的特殊之处在于:
第一,起因条件特殊。特殊防卫的起因条件只限于有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发生。详言之:(1)特殊防卫只能针对犯罪的侵害行为实施,而不能针对一般违法的侵害行为实施,也不能针对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实施。我们认为,对无责任能力人实施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性侵害,可以进行一般正当防卫;但因该种侵害不是犯罪,因而不能按特殊防卫处理;(2)特殊防卫只能针对暴力犯罪行为实施,而不能对非暴力性犯罪实施;(3)特殊防卫只能对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行为实施,而不能对危及人身安全以外的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实施;(4)特殊防卫只能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实施,而不能针对较轻的或者一般的暴力犯罪行为实施。
第二,限度条件特殊。对于特殊防卫而言,事实上并不存在防卫限度的问题,即使因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也不属于防卫过当,也不负刑事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对上述观点,有学者尚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新刑法关于特别防卫权的规定是单纯地以特定的犯罪客观条件为前提的,而不是以防卫人的特定的主观心理状态作为特别防卫权的前提”[16]。这种观点,委实令人不敢苟同。若依此观,一些不具备防卫目的之正当性、应当依法以相应犯罪论处的行为,如偶然防卫、相互侵害等,均将可以成立特殊防卫,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