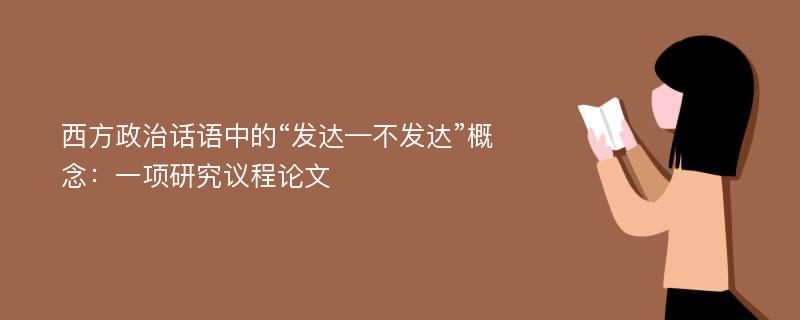
西方政治话语中的“发达—不发达”概念:一项研究议程
张 桐1
(1.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等相关词组是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十分流行的用于指称不同国家的基本概念,也是当代由西方国家把持的世界话语体系的最基本构成。然而,鲜有研究系统而深入地探讨和反思这些基本概念背后可能包含的西方意识形态与话语权问题。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四项假设:“发达—不发达”等概念及其编织的话语反映了一套孤立的世界观;它无视“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的落后应负的历史与现实责任;它抹杀了“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事实;它塑造了一种从“不(欠)发达”向“发达”跃迁的线性发展模式与发展神话。基于既有研究的优劣,本文提出了一项基于话语分析的研究议程,即利用语言学中的话语分析法对包含“发达—不发达”等词语的语料进行深度解析,揭示这些看似客观和中立的词组背后所裹挟的西方价值观与话语权。同时,本文通过一个话语分析的实例来展示话语分析之于西方政治话语研究的独特意义。最后,面对这些暗含西方话语霸权的基础概念,其他国家可能有三种选择:完全抛弃并寻求替代表述的激进方案、继续沿用却时刻保持警惕的温和方案,以及介乎二者之间的折衷道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为反思和批判当前的西方话语体系进而重构新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奠定关键性的基础。
关键词: “发达—不发达”;话语分析;话语体系;全球治理
一、问题提出:“发达—不发达”等流行概念背后的西方话语权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当今世界的形势做出了一项准确判断:“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且“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同时也对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的下一步任务做出了明确要求,即努力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进一步变革。显然,要对当今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反思与改革,要在全球治理中谋求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首先就需要对当前由某些西方国家把持的国际话语体系进行反思与批判,尤其是,如果我们将全球治理的话语视为一场发生于“国际舆论场域的话语竞争”的话,那么“分析和研判西方国家谋求及护持其世界霸权的政治修辞术,就可以被设定为反观当代中国话语竞争战略和策略的一个基本参照”① 张凤阳:“国际竞争格局下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一份研究纲要”,《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3页。 。
对一种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反思理应从构成该话语体系的最基本概念开始。这些基础概念被以特定的方式编织成特定的观念、主张或价值,进而形成一套稳固的话语体系,话语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也依赖于这些基础概念而进行。尤其当某些基础概念在表面上看来并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或者说这些概念的外表具有客观性与价值中立等特征时,这些概念及其附带的观念与理论就更容易向外传播,也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其背后所裹藏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等问题也就更难被察觉。“发达—不发达”的系列表达(包含“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y)、“欠发达国家”(lessdeveloped country)、“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等)正是这样一些值得关注的基础概念。就其流行程度而言,它显然是描述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最为基础的词组之一(其他概念例如国家、国际、民族等);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一词组所表现出的客观性或中立性“外衣”,它就应当是众多概念之最了。“发达—不发达”等词组似乎是一些价值无涉的表达,似乎只是对某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客观描述,其在日常表达中如此流行,在人们的大脑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等问题很少被提出并给予充分讨论。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类似概念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问题?西方国家是如何往这一“客观化”外衣内添置自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经由西方国家装扮的这些“客观”概念是如何影响其受众对相关问题的理解的?正如张凤阳教授在讨论话语竞争时提出的问题,“其现代性表达又采取了怎样的隐蔽形式?如何透过纷纭复杂的表象来揭示西方话语霸权的深层机理?”② 同①。 那么,“发达—不发达”等表达是否是西方国家话语权所采取的“隐秘形式”之一?透过这些“表象”我们能够揭示出西方话语霸权怎样的“深层机理”?
所有这些都应当首先作为一个问题被郑重提出,继而作为一个研究议题被严肃对待,而不是采取完全无视或想当然的态度。一方面,在未进行系统分析和学理研判的情况下,我们既无法先入为主并令人信服地主张这些概念背后就必然存在西方的话语偏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妄下结论说这些概念只是一些客观的描述性词语,或者对相应的问题熟视无睹。
其次,就现实来看,全球范围内依然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落后国家依旧难以获得长足的发展,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真正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与实践界探索的重大问题。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发达—不发达”等描述国家发展与国际关系的基础概念是否扮演了某种角色?由这些概念所构筑的西方式发展策略是否对一些落后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这些看似客观中立的词组是否将落后国家引向了某种不恰当甚至相当错误的发展道路之上?从话语角度展开的此类分析将会对相关问题做出独特的解释。
最后,以中国为例,根据不同国际组织的概念界定与指标测量,中国一直都被划归为“发展中国家”③ 例如:刘伟、蔡志洲:“如何看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管理世界》,2018年第9期,第1-15页。 ,中国自身也一直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④ 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我们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16年7 月 1 日, 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702/c64093-28517655.html。 ,然而,为中国贴上“发达国家”标签的西方声音却一直存在,尤其当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或者借此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时,这种声音就更为响亮。类似“被发达”① 例如:唐仁伍:“中国‘被发达’的陷阱”,《人民论坛》,2010年21期,第117页。 的声音以及其他主张均表明,相同的“发达—不发达”语词在西方话语与中国话语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属性。另一方面,近年来,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是,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甚至出现了一些要求抛弃“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的主张②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6 (English)”,World Bank,April 27, 2016,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 /en /805371467990952829/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16。 ,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此类声音的前提就是系统性地探讨作为一种西方政治、外交或治理话语的“发达—不发达”概念,深刻揭示其背后所包含的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只有这样,才能明辨西方话语的背后意图,也才能更好地坚持中国话语。
本研究议程将聚焦作为西方政治话语基础的“发达—不发达”概念及其相关理论。首先研究西方政治话语的相关基础理论;基于文献综述与前期成果提出作为西方政治话语的“发达—不发达”概念的理论假设;收集整理包含“发达—不发达”等概念的语料信息,并通过话语分析法对其进行深度解析,以对假设进行验证;最后探讨面向西方“发达—不发达”概念及其理论的应对策略。
二、文献回顾:作为一种西方政治话语的“发达—不发达”概念
2.1 西方政治话语研究
目前,关于西方政治话语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对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总体性阐释,例如从权力与权利的角度解读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历史逻辑③ 佟德志:“现代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形成及其内在逻辑”,《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第4期,第25-30页。 ,基于国际话语竞争的场域对中西方的政治话语体系进行比较研究等④ 张凤阳:“国际竞争格局下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一份研究纲要”,《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8页。 ;第二,从不同的知识领域或专业视角对西方政治话语进行分析,从而形成了政治话语研究的不同分支,较流行的比如对西方媒体话语⑤ Norman Fairclough, Media Discourse ,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1995, pp.1-50.、西方经济话语⑥ 例如:余斌:“浅论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阶级性与欺骗性”,《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第32-37页。 等的探讨;第三,对西方政治话语中某个具体概念或理论的反思,例如对西方“民主”概念、“普世价值”话语⑦ 例如:陈先达:“论普世价值与价值共识”,《思想理论教育》,2009年第17期,第94页。 等进行分析与研判。就概念研究而言,尽管国内外已有许多成果问世,但在总体上,关于政治话语中具体概念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在研究方法上,尽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语言学转向为人类敞开了重新理解和认知政治问题的路径,但既有研究仍较多采用哲学思辨或简单的文献研究,而较少借鉴语言学中的话语分析法等更为精细的系统分析工具对相关话语进行深度解析。
2.2 学术表达中的“发达—不发达”概念
不仅是在普通大众的日常沟通中,在学术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也通常将“发达—不发达”等概念视为客观的中立性词语,在其研究中未对相关概念做基本考察或特别说明就直接使用。在概念的操作化方面,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公布的测量体系及其测量结果已成为某种“客观”或“权威”的通行标准而被广泛使用。尽管诺曼·希克斯(Norman Hicks)与保罗·斯特里顿(Paul Streeten)、林·尼尔森(Lynge Nielsen)⑧ 近年来,相关研究不断涌现,例如刘纯:“CDA与PDA共现视角下美国国情咨文之中国形象分析与建构”,《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1期,第26-38页。 、张启良等学者也曾围绕这些统计指标做过讨论,⑨ 诺曼·希克斯、保罗·斯特里顿:“发展中国家发展指标的衡量问题”,《外国经济与管理》,1982年第10期,第1-7页;L.Nielsen, “Classifications of Countries Based on Their Level of Development: How It is Done and How It Could be Done”, IMF Working Papers , Vol.11, No.31, 2011, pp.1-45;张启良:“高收入国家(地区)的衡量标准及其相关概念”,《中国统计》,2014年第12期,第28-30页。但相关讨论大都仅限于经济与统计等技术层面,而较少触及概念背后的修辞、话语权或意识形态等深层问题。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就曾对“发达—不发达”这一表面客观的概念的广泛流行做过严厉的批判,“选择‘不发达’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它把‘不发达’与一般意义上的‘贫穷’等同起来”,“然后,喋喋不休地描述贫穷的不同表现(分类指数:健康、扫盲率、营养、死亡率等,或综合指数:人均收入)”。这种将“不发达”视为客观的、中立的、可量化的、只关乎落后国家自身的论调“构成了课堂上不发达理论的核心,这在有关发展经济学的任何大学课程中都能找到”① Samir Amin,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p.7.。换言之,总体来看,在学术表达中,使用“发达—不发达”等概念的大部分研究都将其视为一组客观的中立词组,而未关注到其背后的西方意识形态修辞与话语权支配等问题。
2.3 “发达—不发达”概念背后的西方话语权研究
基于文献综述,结合话语分析的特点及前期研究的初步成果,关于“发达—不发达”等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权问题,本研究议程提出四项基本假设。
陈艳收款时一看多发了30元,疑惑地对龚正银说:“小伙子,你多发了30元。”龚正银对着陈艳笑着说:“姐姐,您可能不认识我了。九年前,您赊了我30元话费。后来,我外出打工一直没有回老家,话费也就一直欠着。”停顿了一下,龚正银又问陈艳:“姐姐,30元多少利息?”当时,陈艳既吃惊又感动,她对龚正银说:“9年了,我都忘了这事,没想到你还记着,利息就不用了。小伙子,好样的,姐姐给你点赞。”龚正银见营业厅顾客越来越多,怕耽误陈艳做生意,他还是像九年前一样,隔着柜台深深地给陈艳鞠了一躬,然后就离开了。
该教学设计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是任务设计,开放性的任务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任务要有可操作性,整个教学过程就是围绕任务的创设、布置、完成、总结与评价来进行。
2.4 西方“发达—不发达”话语中的中国定位
鉴于中国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对中国之国际地位与发展情境的定位也成为西方“发达—不发达”话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2009年,老牌发达国家口径一致地给中国贴上了“发达国家”的标签。对此,我国刘志勤、王帆与鲁沪京等曾进行过一次有益的讨论。① 刘志勤:“中国,‘半发达’国家”,《环球时报》,2010年1月20日;王帆:“中国应慎提‘发达’二字——兼与刘志勤商榷”,《环球时报》,2010年1月22日;鲁沪京:“做好当‘世界老二’的准备——兼与王帆、刘志勤两位先生商榷”,《环球时报》,2010年1月26日。 王帆认为,中国现阶段要慎重使用“发达”二字,相比中国是否是“发达国家”的疑问,更重要的是认清相关争论背后的逻辑。发达国家为中国贴上“发达”的标签有其明显的意图,即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而减少他们自己的责任,让他们在未来的竞争中继续保持发达国家的领先地位,这在事实上会延缓中国发展的进程。为此,一些学者还创造了“被发达”一词,来反映西方发达国家之于其他国家的话语霸权地位② 唐仁伍:“中国‘被发达’的陷阱”,《人民论坛》,2010年第21期,第117页。 。中国曾一度“被”西方国家定义为“发达”国家,即使中国未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经济指标;但同时,即使中国将来达到了相关指标,西方国家都更愿意将中国视为经济发展的“暴发户”,而不是真正的“发达国家”。因为在西方国家看来,“发达”不仅指向经济维度,更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它们不可能接受社会主义的中国加入这一行列。③ 李伟涛:“刍议‘发达国家’概念的意识形态成分:基于对我国国家定位的思考”,《魅力中国》,2010年第23期,第210页。 这些研究表明,作为“发达—不发达”概念及其话语的创造者,西方发达国家享有授予其他国家“发达”桂冠的话语霸权。但对“developed-underdeveloped”等英文概念的语言解析,将更有助于理解西方发达国家是如何通过概念、语法和修辞等手段来建构这一话语霸权的。
为了对“发达—不发达”概念背后的话语权问题做更为细致而深入的分析,本研究提出了一项基于话语分析法的研究议程。话语分析是自20世纪中期以来逐渐兴起的一种分析方法。在话语分析法看来,语言不仅仅是生冷的文字,而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包括信息传递、社会行动、身份确认等——的(小写的)话语(discourse),加上这一话语表达时所伴随的肢体语言、技术手段与价值观念等更为丰富的非语言材料,它更是一种(大写的)话语(Discourse)。① [美]詹姆斯·保罗·吉,杨炳钧译:《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话语分析法就旨在通过对语言的深度解析——包括语言本身的语法结构、遣词造句、表达技巧,语言表达的非语言形式,以及语言的使用环境与背景等——揭示人们如何通过使用语言进而达成某种目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析任务就是揭示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
三、研究假设:西方“发达—不发达”等概念背后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一项运用话语分析法探讨西方政治话语中“发达—不发达”等概念的研究议程。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主要源于理论、现实和未来三个层面:就理论研究而言,既有研究大多完全忽视“发达—不发达”背后的西方话语权这一问题,少数富有洞见的论断确实为本研究提供了部分启示,但它们均停留在主张宣示上,而缺乏系统的分析。就现实来源来看,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是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长期困扰,基于话语分析来揭示“发达—不发达”等全球治理基础概念背后的内涵,能够为这一议题提供有益的独特视角。最后,就未来而言,要想在全球话语竞争的场域中实现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构建,就需要对现存的西方话语体系进行反思与研判,而其中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这一话语体系的基础概念进行分析,尤其是那些看似客观中立的基础表达。
“数字矿山”与“智慧矿山”建设都包括对于矿山开采状况及次生地质环境变化的监测。传统的监测依赖于一线调查,受限于天气、地形等因素,特别是针对突发性的地质灾害,人工往往难以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近年来三维激光扫描、合成孔径雷达干涉(InSAR)、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遥感卫星、无人机及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AI技术蓬勃发展,为监测预测矿山地质环境提供了有效手段[5]。本文主要探索遥感卫星、无人机、大数据、云计算和AI技术等数字化手段的应用。
教练员在平时训练时应制定一个合理的训练计划,不能以高水平运动员的比赛水准,来打击运动员比赛的积极性,运动员自信心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需要在训练中给予运动员鼓励,而不是过多的苛责。
尽管如上所述,大部分研究未能触及相关概念背后的深层问题,但庆幸的是,个别学者曾就此发表过一些富有启发性的主张和论断,为本文提出与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除了上文提到的萨米尔·阿明,依附论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曾在1966年《不发达的发展》一文中富有洞见地区分了“不发达”(underdeveloped)和“未发展”(undeveloped)两个概念,并就“发达—不发达”等概念有过一句经典的阐释:“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development)(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进程”②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载[美]查尔斯·威尔伯主编,高铦等译:《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146页。 。简言之,“不发达”与“发达”同属一个历史进程,正是后者对前者的剥削与压迫才造成了前者的“不发达”和后者的“发达”。因此,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的落后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与现实责任,而“发达—不发达”等表面中立的概念却在无形中掩盖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责任。马丁·格里菲斯(Martin Griffiths)等人在其经典著作《国际关系关键概念》中写道,“发展”(development)的概念“盛气凌人,尤其当它被用来区分‘发达国家’和那些被描述为‘发展中’或者‘欠发达’国家时”③ [澳]马丁·格里菲斯、[澳]特里·奥卡拉格汉、[美]史蒂芬·罗奇著,朱丹丹译:《国际关系关键概念》(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2页。 ,这些表述看似只关注经济维度,事实上却在宣扬一种指向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生活方式的唯一发展路径④ 谭丹燕:“从文化哲学对人的本质的定义看‘欠发达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160-169页。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在讨论相关概念的起源时指出,考虑到“发达—不发达”的表述可能激化其他国家同自己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主动创造了“发展中国家”这个更具策略性的“外交术语”和“委婉语”(euphemisms),它们希望给落后国家传达这样的幻觉,即后者“正在发展,而且在未来能够(can)而且将会(will)进一步发展”⑤ Gunnar Myrdal, An Approach to the Asian Drama :Methodological& Theoretical ,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pp.33-36.。南非一位心理学家舒斯·凯西(Shose Kessi)同样指出,所谓“发展中”的表述是“将西方社会的景象描绘为一种理想状态”,而被冠以“发展中”的国家正处于通往这一理想境界的康庄大道之上,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发达—发展中”这一词组只是“替代了原有的殖民—被殖民的关系”,因为后者的表述由于带有明显的暴力和不平等色彩而被发达国家抛弃了⑥ Marc Silver:“If You Shouldn’ t Call It The Third World,What Should You Call It?”NPR,2015, https://www.npr.org/sections/goatsandsoda/2015/01/04/372684438/if-you-shouldnt-call-it-thethird-world-what-should-you-call-it? utm_campaign=news. 。国内学者陈明明则将有关国家的称谓进行了分类,其中,“不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低收入国家”等概念同属一类,它们都将经济落后简单地视为一种贫困匮乏的状态,而我们应当对其中可能包含的或引申出的历史观保持警惕。⑦ 陈明明:“‘不发达’与‘欠发达’:历史与结构——关于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等概念的一个讨论”,《复旦政治学评论》,2007年第5辑,第111-126页。 张康之等人也指出,“发达—不发达”等概念及其理论是那些率先发展起来并掌握了全球话语权的国家创造的,它们潜在地把不同国家视为孤立的存在物,且刻意掩盖国家间不平等的事实。⑧ 张康之等:《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页。 总的来看,尽管上述学者针对“发达—不发达”概念中的意识形态成分等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启示性的论断,但它们大都是研究者在某种预先持有的价值观指导下从概念上演绎出来的,而不是从语言文本等证据中归纳得出的,即这些论断缺乏坚实的论据与系统的论证予以支持。
3.1 假设1:“发达—不发达”等概念背后的孤立世界观
“发达—不发达”等表达及其所编织的主张所采用的是一种孤立的世界观。“发达”、“不发达”的词组预示了:“发达”(developed)是一种独立的状态,“不发达”(underdeveloped)是另一种独立的状态,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这种观念没有将各个国家及其发展视为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甚至通过“发达—不发达”等相互割裂的词语刻意地排斥这种看待世界的整体观念。弗兰克关于“发达”与“不发达”同属一个历史进程的观点就鲜明地指出,“发达”与“不(欠)发达”并不是两个相互孤立的状态,而是同一个历史进程中紧密相连的两种境遇。当采用一种整体的世界观时,构成世界体系的各个国家及其发展之间就必然是相关的。
3.2 假设2:“发达—不发达”等概念抹杀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责任
基于假设1,既然“发达”与“不(欠)发达”是相互独立的两种状态,那么后者的落后就不可能是前者造成的,而只能从其自身寻找原因。如此一来,发达国家就通过“发达—不发达”等概念及其主张巧妙地为自己洗清了罪责。今天,发达国家对其他落后国家的帮助并不是出于其责任意识,而是被粉饰为高尚的道德援助,而且它们仍能从这种援助中获取多种利益,当援助无利可图或无暇顾及时,发达国家随时都可以抽身而出。但事实却是,今天的“不(欠)发达国家”正是因为受到了所谓“发达国家”的历史剥削才导致了今天的落后状态,反过来,那些所谓“发达国家”也正是因为曾经压迫其他国家才实现了今天的发达。
3.3 假设3:“发达—不发达”等概念掩盖了国家间不平等的实质
“发达—不发达”等表达背后所隐含的另一种观念是,这些国家之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其差异仅仅在于发展的“量”上的差异。即在发展的量化水平上,一些国家现时处于得分更高的水平,被称为“发达国家”;另一些国家暂时得分较低,相应地被称为“不(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此,二者之间也就不存在不平等的问题,而且这种简单的量上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会被抹平。加之相关概念所持的孤立世界观(假设1)以及对发达国家剥削其他国家之事实的掩盖(假设2),国家间的不平等实质进一步被掩盖。但事实上,国家间的不平等一直都存在,不仅存在于国家发展与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也存在于“发达—不发达”这样的概念与话语中,国家间的不平等也为这种西方话语的建构与传播提供了基础与背景。
3.4 假设4:“发达—不发达”等概念所暗示的线性发展策略与发展神话
诚然,在这一孤立的世界观看来,“发达国家”与“不(欠)发达国家”这两种相互独立状态之间并非完全不相关,其至少存在一种关联性,那就是“发达国家”的“发达”对“欠(不)发达”的落后有着一定的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性经由“发达—不发达”这一直接的词汇关联显现得更加明显,也更具说服力,这就构成了一条“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线性发展策略。基于假设3,正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那么实现发达国家那样的发展就是可能的甚至是容易的;正是因为二者的差异仅仅是量上的,其他国家追上发达国家也就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要实现这一追赶则只需遵从由发达国家制定的线性发展策略。但是,正如弗兰克所言,就连发达国家自身在其历史上都未曾经历过“不发达”状态(其所经历的只是“未发展”状态),这条从“不发达”到“发达”的线性策略也就不可能指导其他落后国家实现真正的发展,因此,这一线性发展策略就只能是一种由发达国家编织的发展神话。
四、研究方法:话语分析法以及一个分析实例
综上,既有研究对“发达—不发达”概念背后的西方意识形态问题探讨相对较少,少数论断富有启示性和批判性,但缺乏坚实的论据和系统的论证,因而未能激发更为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可能逐渐被遗忘。因此,就研究方法而言,我们需要一种更为扎实的分析来探讨这一问题。借鉴语言学中的话语分析法对相关概念和话语进行深度解析,有助于更系统地阐释和揭示其背后的西方意识形态修辞和话语权问题。
运用话语分析法来研究“发达—不发达”等概念,就是要搜集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群(包括研究者、政客、官员、媒体和社会大众等)在不同场景(如学术研究、政治演说、政府文件、大众传媒和日常交流等)使用“发达—不发达”等语词的语料信息,运用话语分析法解读相关话语的言说主体所持的思想、意图或意识形态,相关话语的受体对该话语的认知、理解与思考,以及二者之间形成的权力关系等,以揭示相关概念及其主张背后暗藏的或超越语言本身的意义。对于采集到的每一段文本,除了分析整段文本的结构、含义和作用等要素,重点分析“发达—不发达”等语词的意义是什么?与其他文本成分的关系是什么?在整段表达中的作用是什么?言说者或写作者是如何通过这些词组构建含义的?而聆听者或阅读者又是如何通过理解这些词组进行思考的?这些词组反映了言说主体和受体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具体而言,依据话语分析法代表人物詹姆斯·吉(James P.Gee)的主张,话语分析可以从七个方面入手,也即语言的七项建构任务:语言如何为事物确立了“意义”(significance)、语言促成了什么样的“活动”(activities)、语言确立了什么样的“身份”(identities)、语言促成了与他人怎样的“关系”(relationships)、语言反映了怎样的社会价值观念或“立场”(politics)、语言如何建立或打破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connections)、语言强化或贬低了哪种“符号系统与知识”(sign systems and knowledge)。② 同①,第12-14页。
本文选取了两份语料,尝试运用话语分析法对其进行解析,并借鉴詹姆斯·吉的分析框架尝试解读其语言背后的深意,以此来展示话语分析法对于研究“发达—不发达”等政治概念的独特意义。
(1)第一份材料来自世界银行的官方报告。作为以援助“发展中国家”为己任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无疑要经常使用“发达—不发达”的系列语词。同时,世界银行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国家组别进行的测量与划分也早已成为某种通行标准。因此,世界银行对“发达—不发达”话语的塑造与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最具影响力的官方文件当属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这也成为研究西方“发达—不发达”话语的重要素材之一。显而易见,将全球国家区分为“发达”或“不(欠)发达”的一个重要目的或用途就是进行国家间的比较,但是,这种国际比较的目的是什么却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语词使用者背后所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世界银行曾多次表示,其所使用的“发达—不发达”等语词仅仅“是出于便利性的考虑”,例如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就指出,“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ies)概念的使用也许只是一种便利(as a matter of convenience)”① Souleymane Coulibaly, etc., “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English)”, World Bank, December 3, 2008,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730971468139804495/World-development-report-2009-reshapingeconomic-geography. 。 世界银行提醒说,这些语词的使用并不是要“反映”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也并不意味着所谓的“发达国家”就比“不(欠)发达国家”实现了更好的发展。② Yoon Je Cho, etc.,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9”,February 28, 2013, World Bank,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 /en /667381468339905228 /World-development-report-1989. 世界银行给出的类似特别说明显然是为了将自己从相关的争论中抽身出来,然而,其对“发达—不发达”等语词的具体使用却恰恰违背了上述的宣示,而话语分析则有助于揭示相关语词背后所隐含的价值观。
总体而言,简单从党内整风的角度认识群众路线活动,虽然会不可避免地忽视“群众路线”这一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深层次指导意义,甚至一些国外媒体就此提出的观点我们也并不认同,但是其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却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回味的。
综上,“发达—不发达”等词组以其表面的客观性或中立性已然成为国际事务中最为基础和流行的概念之一,但鲜有研究系统而深入地探求其背后的话语权问题,本研究议程希望通过对相关概念的话语分析揭示其背后可能暗含的西方政治话语权和意识形态倾向。具体而言,“发达—不发达”等词组及其塑造的话语体系可能暗含了一套孤立的世界观;它掩盖了“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历史责任;它抹杀了二者严重不平等的基本事实;它编织和传播了一套线性的发展策略。
1893年,荷兰的乌德舒恩首次引入臭氧作为饮用水处理的消毒剂。随后,臭氧在许多欧洲国家被用于水消毒。臭氧可在食品加工中以气态或含水态使用。一般而言,气态臭氧用于储存应用,而含水形式的臭氧则用于食品、设备或包装材料的表面去污。
(2)除了组织颁布的正式文件,话语分析另一个主要的语料来源是演说。与以文字和图形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件不同,演说的目的则是通过声音以及演说者的表情、肢体动作等要素实现信息的传播。本文在此选取美国前总统奥马巴在2010年9月22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峰会(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Summit)上的讲话中的一个段落,尝试运用话语分析法来阐释“发展中国家”这个“发达—不发达”话语体系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背后的西方意识形态问题。“千年发展目标”是联合国通过的一项旨在消除全球极端贫穷与饥饿、对抗疾病、抵制性别歧视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2015年是这一计划的截止日期,至2010年许多指标与预期目标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此次峰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加速项目推进的进程。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回顾了该计划的成绩与问题,描述了美国在这方面的贡献,为此还提出了一项被称为“美国新方案”(America’s new approach)的规划,当谈及消除贫困与促进发展的多方责任时,奥巴马首先指出了美国与其他伙伴国的责任,然后转向了发展中国家,说道:“现在(Now),对于发展中国家(to developing countries),这也必须(must)是你们(your)该负责任的时候。我们想让你们(We want you)繁荣与成功——这不仅关乎你们的利益,也关乎我们的利益。我们想帮你们(We want to help you)……但没有什么能替代你们的领导力。只有你们和你们的人民可以(Only you and your people can)……只有你们可以(Only you can)……只有你们可以(Only you can)……我们可以(can)成为伙伴,但最终你们(you)必须(have to)发挥主要作用(take the lead)。”①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Summit in New York”,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2, 2010,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0/09/22/remarks-president-millennium-development-goals-summit-newyork-new-york.联合国网页发布的一个前期演讲稿与最终的演讲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参见:“Remarks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As Prepared for Delivery”,The United Nations, September 22, 2010,http://www.un.org/en/mdg/summit2010/debate/US_en.pdf。 可辅助话语分析的演讲视频参见:“The Obama White House.President Obama at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Conference”, YouTube,September 22, 20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VsfX8mN_ASw。
分析可见,在整个演讲中提到“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的所有5次用法中,这是唯一一次将该词以“对于”(to)引导而特别前置,以显示其特殊的重要性。而且,本段以“现在”(Now)开启,以提请听众特别注意,并表明此处即将阐述的是与前面完全不同的观点。同时,本段也是整个演讲中唯一一次大量使用第二人称“你/你们”(you)来进行表述的,包含“你/你们”(“you”或“your”)的用法多达 15处② 除了演讲末尾的致谢(Thank you),另一处用到类似表述也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陈述:“由外国资本控制你们(your)发展的日子必须结束!” ,在语言表达中,第二人称由于能够将听众或读者迅速带入特定情境之中而有助于信息、情感或情绪的直达。显然,在这里,奥马巴代表美国以一种训诫的姿态向发展中国家明示,发展中国家应当对其自身的落后和未来的发展负责。考虑到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如何帮助消除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和促进全球发展,奥马巴不可能完全不谈美国的责任或将未来发展的责任统统置于落后国家身上,甚至在演讲稿的布局上,奥马巴也是先谈美国和其他援助国的责任,最后才讨论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责任问题。但是,用“现在”(Now)提请注意,将“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特别前置,选用第二人称“你/你们”(you),加上文本中的“必须”(must)、“我们想让你们”(we want you)等词语,以及“只有你们”(only you)所引导的强烈的排比句式都在表明,美国就是在以一种训导的姿态来教育发展中国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直接用第二人称“你/你们”(you)的表达方式像极了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对本国被统治者的训诫,或者一位严厉的家长对其子女的训导。尽管文本显示的意义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对自身的落后与发展负责,但其所强调的意义却变成,对这种落后与发展该负责的就是发展中国家自己。该段文本的基调似乎将矛头指向那些将发展中国家落后的责任归咎于发达国家的说法,尽管文本自身丝毫未提这一点,但奥巴马正是要用强烈的句式去抨击和否定这种观念① 奥巴马曾在华盛顿举办的一个针对非洲年轻人的领导学培训课程中说,不要为经济落后找理由,不要把责任归咎于历史,归咎于西方。参见 Maeve Shearlaw,“Africa Should Stop Blaming History for Its Economic Problems— is Obama Right?” The Guardian,January 14,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l/30 /-sp-obama-africa-colonial-excuses-poll。 。本段末尾,奥巴马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们可以(can)成为伙伴,但最终你们(you)必须(have to)发挥主要作用”,这句话从语句结构上明确地表达道,在发展中国家的自身责任(“你们必须发挥主要作用”)与发达国家的援助责任(“我们可以成为伙伴”)二者之间,前者才是最关键的,后者不仅是次要的,“可以”(can)甚至暗含着后者是无足轻重的,是发展中国家乞求的,自然也是由发达国家决定的。有意思的是,本段的这一句总结陈词在美国呈递给联合国的早期文字稿中并不存在。如果考虑到“千年发展目标”生成的过程与大背景,发达国家的姿态就更容易理解了,即在总体上该目标是一些西方国家基于其政治诉求和政治考量而制定的,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参与度十分有限。② David Hulme and James Scot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DG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fortheWorld’ s Biggest Promise”, New Political Economy , Vol.15, No.2, 2010, pp.293-306.
依据詹姆斯·吉的分析框架,通过对这段语料的话语分析可以看出,本段语料所要传达的“意义”就在于,是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对其自身落后与发展必须承担的责任,而且是对这一责任的特别强调;希望促成的“行动”就是发展中国家主动承担起自身发展的责任;确立起的“身份”是美国对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说教姿态;建立的“关系”是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训导—被训导的关系;反应的“立场”就是强化发展中国家对自身落后与发展的责任,而相应弱化(如果不是完全掩盖)发达国家的责任;意在打破与社会上存在的一种批判声音——将发展中国家落后的责任归咎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观念“联系”;所要强化的“符号系统与知识”就是美国所宣扬的发展观念与话语体系。总的来看,对本段语料的话语分析最明显地印证了假设2,即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不发达”概念试图抹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落后应负的历史与现实责任,该段语料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就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自身责任的特殊强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假设1,即将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视为孤立的存在体,这样一来,落后国家的落后与发展就是其自身的事情,发达国家的援助完全是出于一种高尚的道德关怀。
可见,话语分析有助于透过表面生冷的语言材料去窥视其背后更为隐秘的意义,这些意义未能显性地被写作者或言说者公开而明确地表达,却可能隐性地镶嵌于相关语料的语法结构、语音语调等形式中,话语分析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隐秘显现出来。这些隐秘的意涵有可能是表述者希望主动表达和传播的,也可能是它们所持有的却未能意识到的观念,但无论如何,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它们通过对语料信息的接收与自我解读,可能在无意中已经接纳了其背后的价值观念,或者说被这些观念所俘获。
五、小结与展望:对全球治理的基本概念的反思与超越之路
通过话语分析发现,世界银行不仅认为“发达—不发达”等语词就是对某国“发展水平”的判断,也坚持“发达国家”显然比其他国家处于更理想的发展阶段,而更重要的是,世界银行背后秉持的是一种线性的发展观念和路径。因而,将不(欠)发达国家的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就成了一种惯用的方法,尽管世界银行也承认这二者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③ 例如,2017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今日的世界与当今发达国家曾经起飞时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从前,跨国流动的程度很低;国家不接受援助;它们并不会受制于大量的跨国协定、规则与规范。” 。例如,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的序言就写道,“该报告分析了发达国家的早期历史,并为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政策提供了实践性的启发(practical implications)”。④ 同①。 在讨论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时,世界银行会说,“尽管在过去45年中,发展中国家在该指标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落后很多年(still lag many years behind)”⑤ Samantha Lach,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Conte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Tolerance Towards Corruption:The Formation of An Elite-Citizen Coalition In Mexico(English)”, World Bank, February 20, 2017,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348651487587907882/Contestability-and-changes-in-tolerance-towards-corruption-the-formation-of-an-elite-citizen-coalition-in-Mexico. 。“仍然落后很多年”的表述就在无形中将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纳入同一条单线程中进行各自定位,以至于其他国家所要做的就是努力“追赶”(catch up)发达国家。当然,考虑到一些不(欠)发达国家在最近几十年取得的发展成就,在与发达国家的历史所进行的并列比较中,后者并不总是胜出。例如,在提到其他国家的快速城市化时,世界银行说,“这种转型的速度与今天的发达国家(today’s developed countries)在其历史转型中所经历的并无两样”⑥ 同①。 ;而早在1978年第一份《世界发展报告》中,在谈及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惊人速度后,世界银行随即指出,“更重要的是,这一速度远超当今的发达国家(now developed countries)在其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增长速度”⑦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78”, World Bank, February 27,2013,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97241468339565863/World-development-report-1978. 。因此,无论这种超时空的比较结果如何,世界银行总是要将今日的不(欠)发达国家放置到以发达国家为基准的一条历史线条中去,以后者为参照物而为前者定位。更重要的是,这种定位不仅是对前者的现状进行定位,更要对前者的未来进行定位。也就是说,当基于现状与历史的比较被自然而然地纳入同一线条时,当这种线性发展观被普遍接受时,不(欠)发达国家在这一线条上的未来以及为此要采取的行动也就是清晰可见的了。例如,在谈及技术革新对工作技能的影响时,世界银行说道,“目前这种影响开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而这早已在发达国家得到了证明(already evident in developed countries)……那么,发展中国家对哪些技能的未来需求将逐渐减少?发达国家的证据早已表明(evidence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points to)……”⑧ Simeon Djankov, etc.,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9: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Main Report (English)”, World Bank, October 12, 2018,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 /816281518818814423 /Main-Report. 。可见,不仅其他国家在今天所发生的许多改变早已(already)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得到了验证,其他国家的未来也可以从发达国家的过去中求得预见,或者说发达国家过去所走过的路就是在为今天的不(欠)发达国家指明(points to)方向。这就是假设4所描述的一种典型的线性发展观,它在无形中限制了当前的不(欠)发达国家谋求其他发展道路的可能。
本研究试图揭示“发达—不发达”等流行语背后的话语权问题,一方面,是为了促使人们(包括研究者和社会大众)——尤其是落后国家的人们——在使用或接收这一词组时保持足够的谨慎,防止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通过这些词汇流进人们的大脑进而左右人们的思考和行动。“发达—不发达”等表达规划和强化了一种孤立的世界观和从“不(欠)发达”走向“发达”的发展神话,至于落后国家的人们,要么故意向这些神话献媚以换取有限的利益,要么已经被这种神话深深蒙蔽,其结果都是:落后国家放弃了立足本国历史和现实谋求发展的努力,而是在既有的由发达国家确立的框架内谋求有限的“发展”,但实际上,它们难以获得真正的发展,相反进一步巩固了发达国家在既有体系中的地位。斯塔夫里亚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曾批判了所谓“欠发达”状态,并指出,真正的发展必须是依靠自身内在主动性而获得的变化,而不是被周围的世界拖拽前行。在当前的世界体系中,如果遵从发达国家所宣扬和灌输的发展策略,“不(欠)发达国家”即使获得了经济增长,也是缺乏自主性的,这也就不是真正的发展。① [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迟越等译:《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页。
我到里间给姑娘热米饭,端碗出来的时候,却见她正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一边烤火,一边烤衣服。她长得本就非常漂亮,而当时橘红的火焰又正映照着她的全身,更加显得她娇艳无比。
由于不同的物质具有不同的蒸发常数,所以其饱和蒸汽压值也存在差别。在同一温度条件下,不同物质具有不同的P*值。基于此差别,可以通过比较相同温度条件下各物质P*的大小来判断它们蒸发的先后次序。表2所示为含银铅锑多元合金组元的蒸发常数值。将表2所给A、B、C、D的具体值代入式(1)可计算出Sb、Pb、Ag、Au、Te、Cu、Bi纯物质状态的lgP*值,将计算所得数据绘制成T-lgP*图,结果如图6所示。
另一方面,本研究希望推动学术界对诸如“发达—不发达”等全球治理的基本概念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反思,进而为批判西方话语权和重构国际话语体系做概念上的准备。显然,落后国家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冲破发达国家给他们框定的发展模式,必须从发达国家编织的发展神话中觉醒。在思想和理论方面,这就要求努力打破西方话语体系和霸权,而这一努力理应从反思那些广为流传的基础概念开始,这也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组成。
最后,如果上述研究假设得以证实,如果恰似少数学者所言,“发达—不发达”等概念背后确实存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某种话语霸权与意识形态倾向,那么,应当如何对待这组已广为流传的基本概念?理论上,至少存在两种道路:一是较为激进的方向,即落后国家完全抛弃甚至抵制相关表述,并寻求替代性的表达——正如发达国家尽量避免“殖民”、“野蛮”等对其不利的表述而选择更具策略性的“发达—不发达”甚至创造出“发展中国家”一词一样;二是较为温和的方向,即继续使用相关表述,但对其背后暗含的话语权保持清醒的认识与足够的警惕,并在实践中努力避免沦陷于这一词组所裹挟的世界观与发展观之中。
就第一种方向而言,也至少存在两种具体的方案,即要么完全创造一个崭新的概念来描述全球治理;要么从现有的诸多替代性表达(如三个世界的划分、按收入水平划分、“南方—北方”、“中心国—边缘国”等)中选取更有利于落后国家发展和有利于构建新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的基础概念。就第二种方向而言,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是在反思和批判“发达—不发达”等词语本身,而是力图通过对词语的分析来揭示其背后隐藏的话语权问题,进而对相关的理论主张与价值观进行反思与批判。这样一来,即使选择了第二种方向,即使选择继续使用“发达—不发达”等概念进行表述和沟通,也可以对其背后的理论与意识形态继续保持批判的态度。
一定程度上,我们正处在生存于既有世界体系却又寻求打破现存体系的困境之中:我们不可能完全脱离既有体系而走闭关锁国的回头路;又不希望在既有体系中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面对描绘既有世界体系的基本概念,同样如此:我们似乎很难完全抛弃“发达—不发达”这个十分便利的词组,这种抛弃可能意味着我们难以同既有的话语体系进行有效沟通;但我们又不满足于既有概念,尽管我们可以保持警惕而继续使用这些概念,但概念裹挟的价值观已深深植入许多人的大脑之中并将继续如此,我们也不可能在“发达—不发达”等概念每一次出场时都对读者与听众再赘述一遍其背后的话语权,以警示人们把相关概念仅仅视为冰冷的词语,以预防这些概念可能带来的不良导向。
妊娠期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妊娠期疾病类型,会对孕妇及胎儿产生极大的影响,容易导致胎儿宫内窘迫和产后出血等多种不良后果[4]。临床对妊娠期高血压产妇进行剖宫产术治疗之后,存在一定的产后出血风险,严重威胁产妇健康和安全。为此,临床需要积极做好相应的预防措施[5]。
因此,就现实的考虑来看,在完全抛弃并寻求替代的激进道路与继续沿用却保持警惕的温和道路两者之间似乎还存在一条可能更为现实的折衷道路,那就是,仍然使用“发达—不发达”的概念,同时,继续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但在许多时候或场合,尤其当我们需要强调某些与“发达—不发达”概念所传递的价值观所不同的内涵时,我们应当大胆地选择其他的替代词组进行表述。寻求多样化的概念,不仅是因为每个概念只能窥探局部因而多个概念才可能理解整体,也是因为这是我们在强大的旧体系面前能够采取的变革策略之一,更是因为多元共存乃是一个理想的和谐体系所必需的。
The Terms of“Developed” and “Underdeveloped” in the Western Political Discourse:A Research Agenda
ZHANG Tong1
(1.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China )
Abstract: The “developed country”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y” along with other relevant terms are prevailing concepts used to classify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field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king the base of the existing global discourse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However,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western ideology or discourse power behind these terms and related theories.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ated literature, the paper proposes four hypotheses: the relevant terms as“developed country”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y” (1) reflect an isolated worldview, (2) neglec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est to those “underdeveloped” or“less-developed” countries, (3) disguise the fact of inequality among countries, and (4) promote a linear development strategy which propagates the myth of development for“undeveloped” and “less-developed” countries.The paper thus proposes a new research agenda in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analysis,taking advantage of the linguistic method of discourse analysis to dig into the corpus database including related terms and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western ideology and discourse power.Meanwhile,an example is demonstrated to show the distinctive usefulness of discourse analysis.With all this as the background,there are three choices for other countries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se basic concepts implying Western hegemony:a radical approach to totally reject these terms, a modest way continuing the use while with prudence, and an eclectic plan.The study would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existing Western discourse system and thus contribute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new discourse system for global governance.
Key words: “developed” and “underdeveloped”;discourse analysis;discourse system; global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9)04-0013-12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9.04.002
张桐:“西方政治话语中的‘发达—不发达’概念:一项研究议程”,《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4期,第13-24页。
ZHANG Tong, “The Terms of‘Developed’ and ‘Underdeveloped’ in the Western Political Discourse: A Research Agenda”, Pacific Journal ,Vol.27, No.4, 2019, pp.13-24.
收稿日期: 2018-11-08;
修订日期: 2019-01-25。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面上资助“‘发达—欠发达’概念背后的西方话语权研究”(2017M61176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桐(1989—),男,宁夏彭阳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治理话语。
∗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编辑 邓文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