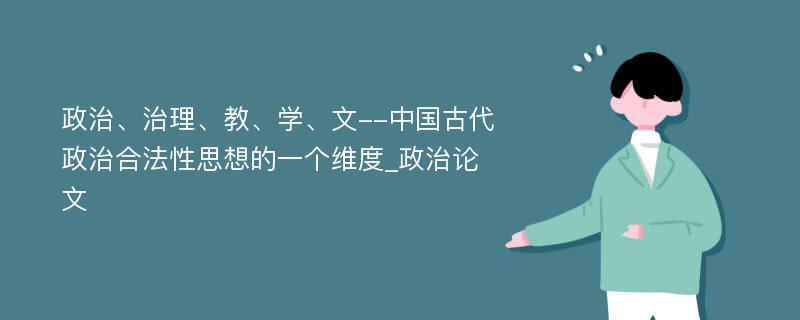
政—治、教—学与文—化——古代中国政治正当性思想的一个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古代论文,思想论文,政治论文,正当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从来没有任何支配关系自动将其延续的基础,限制于物质、情感和理想的动机上,每一个支配系统都企图培养并开发其正当性。① 相对于希腊的城邦学(politeia/politikon)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特异性在于,它从一开始就将“政”(政也者,正也,万物之各正性命也)与“治”(治,理之者也)加以分离,从而导致了“政治正当性”被交付给政道与治道两个层面分别加以处理的复杂情形。②
政道或政的正当性与治道或治的正当性的分别具有重大意义,它划分了一个界限,政的正当性原则在于万物也即一切存在者之各正性命,这在《管子·法法》对“政”的解释中已经特别突出。这样,政的正当性判准,不再是专注于人类的,相反,它着眼于天地之间的一切存在者,这些存在者之间的和谐与有序被界定为最原始性的和谐——这一和谐被称为“太和”,“政”的正当性尺度就在这种原始的和谐中。治的正当性或治道必以政道为依归,只有当其成为政道之展开与落实时,它才获得将自身正当化的基础。但政道却不必仅仅由治道来展开或落实。
既然万物之各正性命构成了政道的核心,那么,治道的典型公式便不外于事物自己管理自己、治理自己(自正性命),因而治理活动不再负责普遍的规范法的确立——在政道中即便可以发现某种普遍的法则,但亦不是立法意志与欲望的表达,因而更高的规范法的单纯运用并不能概括中国古典思想中的治道,同样,个人意志与权威命令也没有触及治道的根本,相反,它们的实际角色是倾听并给出事物的自命。看看以下的几个表述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③
凡事无大小,物自为舍。逆顺死生,物自为名,名形已定,物自为正。④
镜仪而居,无执不臧,美恶毕至,各得其当;衡虚无私,平静而处,轻重毕悬,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虚而静,令名自命,令物自定,如鉴之应,如衡之称。⑤
可以肯定的是,治理或管理的因素远较立法、司法、(今日意义上的)行政等因素更为重要,治的正当化方式显然不能从严格意义上的立法型国家、民主法治制度以及君主专制或帝制独裁等视角加以理解,因为这一理解不是将我们引向政-治的全面国家化或政府化,就是引向政-治直接交付给某一或某些个人进行替代的处理方式。⑥ 这两种情况在今天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基本境遇,但在古代思想中,国家、政府与治理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唯一性的,毋宁说这种直接性与唯一性是被坚决地抵御的。例如,修身作为一种治理活动本身就是个体之人自正性命(政)的环节,作为一种自我治理,一种直接将“政”直接接收在“治”中的活动,它远较外在的治理更为基本,因而,在古代思想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表述:政治的根本在于身体,而不是国家(《孟子》);自天子到庶人,壹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其实,同修身一样,齐家也是政道与政府治理活动之间的中介,由政府推行的治理活动尽可能地面向这些中间环节,让事物充分释放自己管理自己的可能性,这便是治道的极致。所以,治的正当性或者被归结为无为,或者被归结为德治,其实此二者都是《庄子》所讲的不治之治。“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囿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⑦ 治理活动取消了外在的支配,转变成事物自我治理的引导时,治理活动便获得了自己的正当化方式。⑧ 显然,“无为”只是用来描述“治”道的,却不是用来描述“政”道的:可以说“无为之治”,但却不能说“无为之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只有“为政”、“行政”,但却没有“为治”、“行治”,⑨ 因为“治”道必须作为对政道的引导,才能获得自己的正当性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为政”描述的是治理术,但却同时规定了治理术必须以政道为依归,换言之,“为政”这一表达从一开始给出了治道与政道的关联。
对政与治的如上分化,表达了对实体性政府、国家、权力机构的限制,政并不能仅仅由治充分实现,事实上,对一切存在者之各正性命的引导,并没有被限定在由政府或官僚执行的治理活动中,教学过程对于这一事业具有更为深远的重要性。“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⑩ 由“教”(学校承担的教学将教学过程制度化)与“治”(政府承担治理活动将治理本身制度化)共同托举“政”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主体。在荀子那里,这一思想通过圣与王的分别得到表达:圣者尽伦,王者尽制。这就不难理解,治的承担主体“君”与教的承担主体“君子”(师与士),在命名上的内在关联。(11)“君”与“君子”皆以“群”立义,所谓,“君,群也。”这里所谓的“群”,即是共同生活的群体,君主与君子分别以自己的方式,促进了共同生活的可能性。所以,君主有自己的“为政以德”,君子也有自己的“为政以德”,二者各不相同,但却以面向教-学的共同体,或通过教与学走在自正性命道路上的共同体的形成为最终归宿。在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便在于开发这种教-学的共同体。
就更原始的层面而言,教-学并不局限于学校,它弥散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场域,在家庭、在地方、在政府等等任何一个处所,都有前制度性的教-学活动在发生,它是人类无法从根本上加以分离的事情,如同友谊、君臣、父子、夫妇、梦与觉等等那样,是生活世界的最基本的元素。通过它来开启的各正性命的生活境域,远较由政府官员执行的治理活动更为本源。不仅如此,教-学活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这与政府治理总是不可避免地求助于权力-权利的逻辑具有极大的不同。文-化的逻辑,就是通过修裁身心而文身、文面、文言、文为的活动,而每一个文身、文言、文为的活动都既将行为的个体保持在自正性命的“学”之道路上,又具有以其“文”化育其他个体的身、言、面、为的力量,换言之,同时也把修道为学的个体保持为立教的个体。这意味着,个人可以在他那里打开教-学过程,借助于感化与自化的浸染而导致自发或自觉的转化,相对于治理中的权力-权利诉求,“化”展示了其“文”的向度。当治被规定为以政为核心时,文便获得了其特殊的位置,因为“文”打开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政”(正)的区域,以至于治理活动也得在很大程度上与“文”的化成作用相协调。事实上,在《周易·賁卦·彖传》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意味着,政-治生活已经被上升为文-化的过程。
教-学活动所开启的是自觉的文-化过程,而那种自发性的文-化过程则往往被命名为风-化,它沉降在风俗、习气、惯性等等之中。文之行化,若风之行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2) 文-化即是文之风化过程。《诗经》开篇记载各国之国风,这样的安排一开始就体现了对政治的特殊理解,在古代中国,诗歌如同音乐那样,一直是政治生活的基本事情。《庄子》所构想的不治之治,没有采取教-学的文-化方式,而是在自然的风化过程中寻求独化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这才是各正性命所以可能的真正途经。不治之治便是通过这两种文-化过程获得其现实性,而这两种文-化方式都深深地将政-治生活延伸到政府治理的狭隘空间之外,但却进一步地逼近了“政”。而孔子与庄子那个时代由政府主导的治理过程已经远离了“政”的语境,出现了以“治”代“政”的实际情形--一旦如此,治理活动无法获取自身的正当性。
这种自发的文化过程与基于学习的“教-化”不同,它可以被概括为基于自-然的“风-化”。风意味着风土、风气、风习、风俗、风范等等词语所传达的风化境域,而且这一风化境域不是来自由上而下的建构,也即它不是基于为政者的意志、欲望与筹划等等的人为设计,而恰恰是自发地生长起来的,它的根基在不同的地方的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等等。在《论语·为政篇》第二章,紧接着“为政以德”后,我们看到了对诗歌的叙述:“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在思考政治事物的时候,为什么会谈论诗歌?显然,这里的思路是将诗歌作为政治生活的基本元素来看待的。所谓孔子删诗、从而奠定了“诗三百”的规模,就是一种为政,或者说是一种政治性的行动。何以如此?诗歌作为一种教化的体系、或文化的体系,在古代思想中乃是一种共识,古代即有“诗教”、“乐教”之说。诗歌对各正性命的政治目的所具有的根本性力量,在于它是“风”,能够“兴”起、提升人性。所以,在《诗经》中,不同地方的诗歌被称之为不同地方的风,如豳风等,构成诗经主体的是风雅颂,而风无疑具有至为重要的位置。将作为这不同地方风化境域的体现与塑造者的诗歌,引入政治生活,恰恰是藏天下于天下的方式,不是把天下收归于某处,作为某种所有物或专有物,而是将其交还给不同的地方,由此而使得地方性的因素进入到作为政治境域的天下的基本维度之中。《庄子·齐物论》关于风的论述值得注意:“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显然,庄子向我们描述了一幅天地自然之气息相化相感相动相和的壮观场面,彼此牵引、相互缘发、氤氲流荡,无有止息。风化的力量将事物保持在自然的过程之中,或者用弗朗索瓦·于连的话来说,“促使自然发生的事物来临”。这就是风化,也就是风气,或者一种气象、一种氛围。风化是一种潜移默化、然而却又无所不至的巨大力量。不仅如此,风化的过程中发生的,是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而这种影响又保持了事物自身的状况,也即事物保持了自身之正性正色。因为,在风气或风化中发生的,或者是“相造”(13)——相互的塑造,或者是“相因”、“互生”情境下的“自化”或“独化”;即便是彼此的“相造”,在风化过程中,也是“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与无相为”。在这个意义上,诗所展示的风化境域也是一种“无邪”,也即事物的自性得以被保持的境域。
弗朗索瓦·于连在《迂回与进入》中对风有着十分精彩的分析:“风使大地上所有的洞穴轰鸣,它是悠悠乐曲的源泉。再者,风在自身中是不能感知的,人们不能直接感受它,但它在通过的地方留下明显的影响:风过之处,‘草上之风,必偃’。唯有风在外部激起的震动能向我们揭示它的经过。最后,因为风不可触摸,它能深入到所有地方:它弥漫在我们周围,迂回穿行直至诸物的内部(参见《易经》:巽卦)。中国古代思想在以不同方式挖掘风的动机的过程中,不断使我们遐想风的无限能力:它的无形的渴求在穿越自然景致时摇撼着直至最细微物并使之颤抖;风非物质性的固定存在,从不中止侵占和推动。隐藏着的影响——无休止的深入:中国人正是以‘风’借以不断出没世界的方式设计了诗的语言。”(14) 在诗歌所塑造的风化境域中,上下的交通获得了极其微妙的形式:“风行无所不遍,遍则会通之德大行。”(15)
于连向我们解释了通过诗而达成的这种非基于强迫与权力的上下交通:“与直接向受话者施加压力、同时向他描画出一种计划并给他规定秩序的政治言语相反,诗的语言根据‘风’的信码含而不露地影响接受者,使之活跃起来,并且由于诗的言语在它这方面间接活动的,故更加深入地浸透到接受者之中。诗的言语使思想的进程改变方向,而不是强压,它轻轻地蜿蜒而行。它并不提供确定、清晰的意义,它以弥漫的方式向它激励的情感显示,而不是以指令的方式指名道姓自我表现。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内容,它同样不可能遇到抵抗,依靠其灵活、散漫的无限流程而侵入意识:这样它能够偷偷地左右意识的方向--但是以更加全面、连续因而也就更加有效的方法。”(16) 因而,以风的方式开放自己的诗歌,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7) 从而实现多种政治功能,但同时又将政治转化、提升到一个风化的境域中去。对于由上而下的层面而论,为政者的治理活动经过诗歌的风化境域巧妙地转换为教化过程,它不是风化过程的解体或替补,而是其提升,从自然的风化进升到向着学习过程而开放的教化、文化的层次,由此,移风易俗,风俗的提升与纯化,就构成了为政者的责任。正因如此,“为政”这一工作就不能仅仅被交付给君主(或政府、大臣)来从事,事实上,在《为政》的语境中,被提及的却更多的是君子(以及师)。君主与君子共同托举政治生活境域,是《为政》的深层结构。因而,在《论语·为政》中,我们看到了连续几则关于师、君子的语录,这绝非可有可无,而是整体结构的一部分。
当然,风不仅仅是从上而下的,另一方面,从下而上的运动,也在风中展开,例如下层对上层之讽谏,诗歌作为一种风化的力量,包含了这一类型。弗朗索瓦·于连说:“通过这些诗歌,君主被看作‘影响’百姓,或百姓被看作‘批评’君主。但是,双方都是间接地,以一种不可见的方式,其影响只是感觉到的,正如‘风’所起的作用那样:风高或风低,它渗入每个最小的缝隙,人们却看不见它是怎样行动的。诗歌形象按风的样子在发挥‘影响’,却不被人们所察觉,因为它不局限于提及的事物,便显得更加含蓄。尤其是当人们由下向上表达时,透过其动机的模糊性传达的批评被参照物的谨慎性所缓解,但正是通过此种缓解,批评却增强了渗透力:我所言足以令他分明,然而不过分,以免遭杀头之祸——即谨慎地,以影射方式,隐含地,转弯抹角地,含蓄地表达。”(18) 由此,诗歌发挥了其讽谏功能,采诗纳谏就成为一种“观风”,而诗歌本身呢,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具有造、化力量的“风”,通过它,民之群与怨得以可能,并且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得以转化,成为整个风化境域结构总体的有机构成部分。
与此整体结构相关,诗歌正是通过这种风化的生活境域的塑造而承负“春秋之志”(19),承负作为政治生活境域的“天下”:“诗者,持也,以手维持,则承负之义,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20) 在这个意义上,当《论语》在《为政》的脉络中讨论《诗》三百时,它传达的消息是,发现、提升甚至塑造风化境域,而不是建立基于主体意志的权力结构,恰恰是“为政以德”的真正方式。
若个体仅仅处在风化的境域中,由风行所化,那么,他就还生活在风俗、习惯、风气等等的推动中,相对于风化的运行,它还仅仅是一种接受者。他的生命还未上升到自觉参与着风化过程本身,这就要求他进一步从风化所浸润的生命转向通过学习过程而打开的教化的生命。这种生命的可能性,存在于转化自然的风化境域的可能性之中,也就是,在于《为政》第3章所说的德与礼之中。“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不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构成了“为政以德”的进一步的要求。因为,同风化境域的敞开不同,这里的要求是进一步的,是提升、转化风化境域,从而引导个体向着教学过程开放自己的生命,从自发地正性命转向自觉地正性命。
而承载教—学的学校,由此更是彰显了其在政—治思想体系中的独特位置,它把自发的风-化过程转化为自觉的文-化过程。故而,对于承载文—化与教—学活动的学校,黄宗羲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21) 当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时,治理本身也就转化为教-学或文-化的过程,支配便从政治中自我瓦解。现代思想家梁漱溟通过未来的国家将来应转变为教育团体的观念所表达的,正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这一基本精神。而这一精神在董仲舒与王符那里,其实已经表述得极为清楚: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22)
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务厚其情而明则务义,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后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乃以防奸恶而救祸败,检淫邪而内正道尔。(23)
学校在于养士,培育君子,而士君子之间构成的正是教—学共同体的成员,作为一个承载“文”并通过“文”而“化”育世界的共同体,它塑造了某种精神的、道德的、生活的风气或氛围,这一氛围“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24) 更为重要的是,在学校中,不同人们之间的“共学”本身不仅造就了基于教—学过程的自觉的文—化共同体,而且也生产基于理性的公用而形成的公意。如此,学校成为一个公—共之域,在其中,“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在此意义上,“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25) 换言之,在古代政—治思想中,学校最主要的是作为公域而被定位。但正因为学校承担如此功能,所以,现实的权力阶层总是在侵蚀着学校的这一功能。但总体上看,学校为士君子不从官僚权力机构的治理活动切入政—治提供了可能性。
换言之,在中国古代,政主要是由官僚的治理与学校的教学分别承担,通过君与君子分别以治与教共同托举政。但当二者发生紧张时,便展开了权力性官僚机构(君主一方)与士(君子一方)在教学上的争执过程。即使在当今之世,这种争执也并不停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校作为教学的共同体的制度化形式,是保证各正性命的最基本的公共之域,它通过教学活动开辟各正性命的可能性。但与政道脱离的治道无法获得自身的正当性时,便不得不诉诸于治理的合法性,并将之输入到在政道与治道分离时还可能保持着政道的学校之中。因而,改变教学内容,封闭各正性命的可能性,转而开启治理的合法性,就变成了治理术的主要内容。但无论如何通过强制性力量转换教学内容,而教学过程却不能由治理者完成,而是由士君子来从事,这样,使得士君子可以较为从容地应对治道通过教学对政道的消解,而保持以非政府的方式向着政道开放。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士君子那里发生的独特的为政方式:“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26)
因而,政与治的分离在中国思想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政—治过程没有被集中在政府权力的狭隘空间内,无论多么强大的权力,总是有其不能抵达的空间,但即使是在这样的空间,政—治生活依然可以开启,因而,在中国思想中,没有形成家政学(经济学)与政治的对立,也没有形成西方意义上的私人空间与共有之域的对立。(27) 即使是在希腊意义上的家政学领域,即使是在希腊意义上的非共有之域,政—治生活在中国思想中仍被保持了某种可能性。
不仅如此,政—治生活恰恰被指向了这种可能性,这就是说,“政”的可能性在于通过“治”,并将“政”从“治”中解放出来,交还给每个个体的自正性命本身。而“治”在此拒绝被作终极性的理解,但也并没有因此而消解治之存在的合理性。不治之治来到自身的过程,固然是文—化的力量,但即使是后者仍然是在“治”已经成为世界的现实的状况下展开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正当性的政治将其奠定在文—化的基础,而不是基于个体要求的权力与权利基础之上的现象。
注释:
①《韦伯作品集》Ⅱ《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9页。
②陈赟:《“藏天下于天下”:政-治生活的境域》,见《思想与文化》第五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③《韩非子·扬权》。
④马王堆帛书《经法·道法》,见魏启鹏《马王堆帛书〈皇帝书〉笺证》,中华书局,2004年,第10页。
⑤贾谊:《新书·道术》,见阎振益、锺夏《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302页。
⑥在严格意义上,治理活动固然可以由少数人来从事,但“政”的维度却不能由治理者来完成,而是必须由治理者交付给每一个个体,由其自身来实施。
⑦《庄子·在囿》。
⑧陈赟:《自发的秩序与无为的政治:中国古典思想中的政治正当性问题》,《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⑨与此相应,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可以看到“行政”这一表达,但却没有“行治”这个说法。
⑩《礼记·学记》。
(11)《中庸》、《论语》等典籍在展开其政治哲学时,便同时兼顾“君子”与“君”,而尤重“君子”。这无疑是值得注意的。
(12)《论语·颜渊》。
(13)《庄子》之“大宗师”等文本一再将我们引向这种彼此“相造”而又保持着自化的可能性的境域。
(14)(16)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56-57、58页。
(15)《周易郑康成注·同人》。
(17)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小于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羣,可以怨。迩之事父,逺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18)《(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第126-127页。
(19)廖平在其《知圣篇》卷七中,谓诗歌之志,志在春秋之志。
(20)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校《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4页。
(21)《明夷待访录》“学校”条,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22)《汉书·董仲舒传》。
(23)王符著、汪继培笺:《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97年,第376页。
(24)(25)《明夷待访录》“学校”条,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26)《论语·为政》。
(27)李陀在回忆八十年代的时候,指出中国八十年代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公共空间,它不与私人领域对立,甚至,privacy的缺乏,恰恰是那时候“公共空间”形成的条件。(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60页)这的确已经接触到活生生的中国式的公域与共域问题,只不过他还用“空间”以及没有区别的“公共”来表述这一场域。我在《学海》2005年第5期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已经谈到中国思想中的公与共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