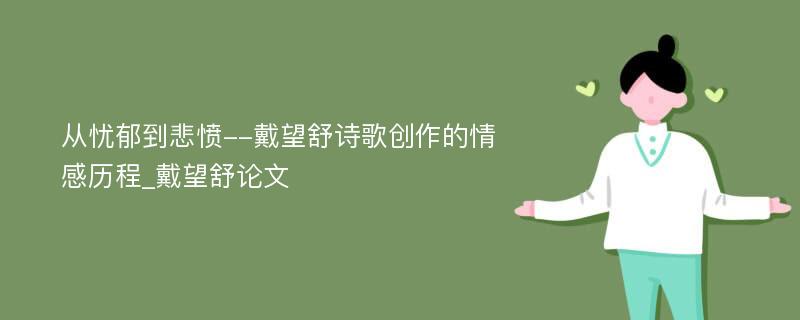
从忧郁到悲愤——戴望舒诗歌创作的情绪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愤论文,历程论文,忧郁论文,情绪论文,诗歌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戴望舒其人其诗,已经说得够多了。但翻看近年有关研究文章,内容多不出诸如戴诗的外来影响、戴诗的民族传统、戴诗究竟是不是“现代派”之类,难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这类文章外部研究多,内部研究少,似有隔靴搔痒之嫌。有感于此,木文试图从一新的角度,对戴望舒的诗歌作些有益的探讨。
诗歌是一门主情的艺术,“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1]。作诗无非是为特定的情趣寻找某种恰切的意象,在实际的人生世相之外自造一个独立自足的小天地。因此,本文拟找到某种贯串诗人作品始终的情绪为经线去探讨戴望舒的创作历程。
走进望舒的诗歌世界,你会感到一种浓重的忧郁扑面而来。它是那样的浓郁,那样的持久,几乎弥漫于诗人创作道路的始终。直到最后那段“灾难的岁月”,民族和个人的双重苦难,才迫使诗人由忧郁的抒写转向悲愤的控诉,蘸着血泪写下了最后几首风格迥异于前期的诗篇。
戴望舒生前共出了四本诗集:《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与《灾难的岁月》。其中,《望舒诗稿》基本上是前两本诗集的汇编,无单独讨论的必要。另外三本诗集则大体标志着望舒诗歌创作的三段历程。因此,本文在对忧郁作些理论上的剖析之后,将主要沿着这三本诗集所指示的方向去感受戴诗中那种无所不在的忧郁与深入骨髓的悲愤。
一、忧郁的解剖
说起忧郁,不由得令人想起弥尔顿的诗句:“贤明圣洁的女神啊,欢迎你,/欢迎你,最神圣的忧郁!”代尔(Dyer)在《罗马的废墟》中亦写道:“那是给痛苦以抚慰的同情,/把健康与宁静唤醒,/多么悦耳……/忧郁之神啊,你的音乐多么甜蜜!”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则喜欢大自然阴沉的样子,因为只有这种样子才与他心中的忧伤更为和谐一致:“再见吧,最后的美好日子:大自然的悲凉,/才与忧伤的心情相称,使我喜欢。”在谈到拜伦时,海涅写道:“他们因为他很忧郁而怜悯他。难道上帝不也很忧郁吗?忧郁正是上帝的快乐。”[2]
看来,有一部分诗人确实对忧郁偏爱有加。忧郁对于他们是一种宗教,一种精神的安慰。雪莱说得好:“倾诉最哀伤的思绪的才是我们最甜美的歌。”[3]可是,“最哀伤的思绪”真的能成为“最甜美的歌”吗?忧郁真的能给人以快感吗?且听朱光潜先生的解释:
一切受到阻碍的活动都导致痛苦。忧郁本身正是欲望受到阻碍或挫折的结果,所以一般都伴之以痛苦的情调。但沉湎于忧郁本身又是一种心理活动,它使郁积的能量得以畅然一泄,所以反过来又产生一种快乐。……所以,任何一种情绪,甚至痛苦的情绪,只要能得到自由的表现,就都能够最终成为快乐。……我们所谓“表现”,主要是指本能冲动在筋骨活动和腺活动中得到自然宣泄,也就是说,像达尔文说“情感的表现”时那种意思;其次是指一种情绪在某种艺术形式中,通过文字、声音、色彩、线条等等象征媒介得到体现,也就是说,是“艺术表现”的意思。[4]按照朱先生的说法,忧郁是“欲望受到阻碍或挫折的结果”,而忧郁的情绪只要得到自由的表现,便会“最终成为快乐”。因此,要使“最哀伤的思绪”变成“最甜美的歌”,关键还在于自由地“倾诉”。
我们承认忧郁的情绪只要在筋骨活动和腺活动中得以自然宣泄抑或在某种艺术形式中得以自由表现便会最终成为快乐,但我们认为忧郁并不一定产生于欲望的受阻或受挫。比如说,在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历程中,忧郁几乎贯串始终,难道都是由于欲望的受阻或受挫吗?在最后那段“灾难的岁月”里,戴诗开始告别忧郁,走向悲愤,难道居然是欲望不再受阻或受挫?抑或是诗人彻底消解了欲望?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其实,忧郁跟人的气质有关。气质不同的人,趣味爱好也不相同。在文学方面,有的人拥护六朝,有的人崇拜唐宋,有的人赞赏苏辛,有的人推崇温李,这都是气质不同的结果。尹在勤先生认为:气质对诗人的观察体验、意态倾向、艺术风格都有着深刻的影响。[5]的确。每位诗人的作品之所以都打上了个性的烙印,气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人的气质可分为多血质、胆汁质、粘液质、抑郁质四种类型:多血质者活泼、好动,注意力易转移,情感丰富易变且直接表露于外;胆汁质者性急、暴躁,精力旺盛,动作敏捷,情感强烈且迅速表露于外;粘液质者沉稳、迟缓,能忍耐,情感深藏,注意稳定但难于转移;抑郁质者孤僻、寡言,情绪体验少,但体验深刻而持久,情感不轻易外露,善于观察别人不易觉察到的细小事物。
如果按气质归类,戴望舒应该是属于抑郁质而兼粘液质类型的。戴诗往往爱用暮天、残日、枯枝、死叶、怪枭等意象,表现出一种忧郁、孤独而凄冷的情调,这固然可以从诗人所处的时代和具体生活环境得到解释,但笔者认为这更与他独特的气质有关。这种气质使他不想也不适合像郭沫若那样进行热情洋溢的呼喊与痛快淋漓的抒写,而只能“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只能作一个“最古怪的”夜行者,对着“已死美人”似的残月唱“流浪人的夜歌”;或者抱着“陶制的烟斗”静听着记忆“老讲着同样的故事”。
笔者认为:戴望舒忧郁的气质与他所抒写的题材和情调在其诗歌艺术中得到了和谐完美的统一,这就是戴诗至今还能强烈地点燃我们的心灵的原因。望舒总是真诚、质朴、忠实地表现着自己的思想和情趣,“他不夸张,不越过他的感官境界而探求玄理;他也不掩饰,不让骄矜压住他的‘维特式’的感伤。”[6]这使其诗华贵中有质朴,忧郁中见真诚。啊怕是到了那段“灾难的岁月”,在改变风格后的戴诗中,感人至深的还是像《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在忧郁中抒发愤怒的诗篇,而不是像《元日祝福》这类呼号式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望舒的后期作品抒写的主要是悲愤,而不是激愤。
在进行这番理论解剖之后,我们该走进戴望舒的诗歌世界,再品尝一下那种魅力独具的忧郁了。
二、《旧锦囊》、《雨巷》:缠绵悱恻的古典式忧郁
望舒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于一九二九年四月由水沫书店出版,共收诗26首,分为三辑:第一辑题为《旧锦囊》,收诗12首;第二辑题为《雨巷》,收诗6首;第三辑题为《我的记忆》,收诗8首。这三辑诗歌基本上显示了诗人这一时期创作思想演变的轨迹,诚如施蜇存先生所说:“这种分法,表示了作者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这五年间作诗的三段历程。”[7]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如果考虑到诗人的整个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旧锦囊》与《雨巷》还是有许多明显的共同点,比如诗中明显的中国古诗词的痕迹,对形式美的高度重视,等等。因此笔者把它们同视为戴望舒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至于《我的记忆》,里面的诗歌除《断指》一首之外全都收进了《望舒草》,属于戴诗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后面再论,此不赘言。
李泽厚先生认为:“二十年代的中国新诗,如同它的新鲜形式一样,我总觉得也带着少年时代的生意盎然和空灵、美丽,带着那种对前途充满了新鲜活力的憧憬、期待的心情意绪,带着那种对宇宙、人生、生命的自我觉醒式的探索追求。”[8]李先生的说法实在是以偏概全,戴望舒该期的诗歌即是一个反证。望舒的天性和气质,使他的诗歌一开始就对前途和命运既没有什么憧憬与期待,也不想对宇宙和人生进行什么探索与追求。诗人这时还没有接受时代的磨难,他只想沉湎于一种与自己气质相合的古典式忧郁之中,寻求快感和解脱。
望舒认为:“不必一定拿新的事物来作题材,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9]这一阶段,戴诗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明显的古诗词的痕迹。艾青早就指出过:“望舒初期的作品,留着一些不健康的旧诗词的很深的影响,常常流露一种哀叹的情调”[10]当然,古诗词的影响一直贯串诗人创作的始终,只是这期尤为明显罢了。
由于接受不同的外国诗的影响,《旧锦囊》与《雨巷》中的诗毕竟有某些不同的特征。为了论述线索的清晰,下面分别进行阐述。
1.《旧锦囊》:忧郁的直接宣泄
阙国虬在《试认戴望舒诗歌的外来影响与独创性》一文中谈到:“从他存留在《旧锦囊》那一辑中的少年之作看来,他是带着中国晚唐温李那一路诗的影响进入诗坛的。其时,正值新月派诗人大力介绍英美浪漫派诗歌及其理论,提倡新诗格律化,给诗坛以极大的影响。在这个背景下,他接受了法国浪漫派作品的影响。”[11]以上影响无疑都是存在的,但阙文显然忽视了“世纪末”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对这期戴诗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施蜇存先生说得很清楚:“作《旧锦囊》诸诗的时候正是郁达夫在《创造》季刊上介绍了英国诗人欧纳思特·道生,同时美国出版的近代丛书本《道生诗集》到了上海,我们都受到影响,望舒和杜衡以一个暑假的时间译出了道生的全部诗作,这期间,目营心受,无非是道生的诗,《旧锦囊》里的那些作品,无论是思想情绪,或表现方法,都显然可以觉得是道生诗的拟作,不过这中间还加上了一点中国的诗的意境和词藻。”[12]卞之琳先生也指出:“在望舒的这些最早期诗作里,感伤情调的泛滥,易令人想起‘世纪末’英国唯美派(便如陶孙——Emeser Dowson)甚于法国的同属类。”[13]。
如此看来,《旧锦囊》中的诗至少受到四个方面影响:中国古诗词、新月派、英国诗人道生与法国浪漫派。笔者认为,这四种影响对这期戴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使戴诗富于古典气派,颇具民族特色;新月派的影响使戴诗形式整齐,音韵和谐;道生的影响则使其诗忧郁中更带一种颓废的色彩;法国浪漫派的影响则给了诗人直抒胸臆的表现手法。下面举《寒风中闻雀声》一诗为例。
该诗共四节,每节四行,每行字数相等,每节二四句押韵。从形式上看,分明是新月派的拟作。诗的第一节提到的“薤露歌”在汉乐府中是出殡时挽柩人唱的挽歌,“薤露”意指生命短促,就像薤叶上的露珠一样容易消殒。这一古典的运用,使全诗飘逸出一种古雅的民族气息。诗的第二节这样写道:“大道上是寂寞凄清,/高楼上是悄悄无声,/只有那孤零的雀儿,/伴着孤零的少年人。”这很容易叫人想起柳永“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离愁,黯黯生天际”的词意。全诗使用了枯枝、死叶、寂寞的大道、无声的高楼、孤零的雀儿等意象,忧郁之外更逸出某种委顿、颓废的气息。另外,这首诗的抒情方式也很特别。诗的前三节都是从“少年人”的角度以客观铺叙的方式渲染一种感伤、颓废的气氛,到了最后一节,诗人终于抑制不住情感的涌动,第一人称“我”取代了第三人称“他”,“我”直接打开情感的闸门,让久蓄的忧郁情绪奔涌而出:“唱吧,同情的雀儿,/唱破我芬芳的梦境,/吹吧,无情的风儿,/吹断我飘摇的微命。”
2.《雨巷》:忧郁的象征化
这一时期,望舒主要接受了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影响。“在这个阶段,在法国诗人当中,魏尔伦似乎对望舒最具吸引力,因为这位外国人诗作的亲切和含蓄的特点,恰合中国旧诗词的主要传统。”[14]魏氏诗歌的主要特点是:追求诗歌的音乐美、形象的流动性与主题的朦胧性。这些特点都可以在望舒该期的代表作《雨巷》中得到印证。
读完《雨巷》,我们很容易想起李璟“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浣溪沙》)与李商隐“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的诗句,但这首诗决不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稀释”,它是中国古诗词的意境与法国象征派诗人某些诗歌主张融合后产生出来的艺术奇葩。杜衡曾借一位朋友之口说望舒的诗歌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15]朱自清先生也曾对戴诗的象征作过一段评价:“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征派。他译过这一派的诗。他也注重整齐的音节,但不是铿锵而是轻清的;也找一点朦胧的气氛,但让人可以看得懂;也有颜色,但不是像冯乃超氏那样浓。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处。”[16]对照《雨巷》,确实如此。
走进《雨巷》,首先看到诗人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梅雨季节江南小巷的阴沉图景。抒情主人公忧郁、孤独、寂寞,在绵绵细雨中,“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然而,“丁香姑娘”内心也充满了“冷漠”、“凄清”与“惆怅”。最后,她“哀怨又彷徨”、“像梦一般地”走尽这雨巷。这是一个富于浓郁的象征色彩的抒情意境。那“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分明象征着当时黑暗而沉闷的社会现实。“丁香姑娘”则象征诗人怀着的一个美好希望。最后,姑娘的飘逝则象征希望的破灭。
这样理解当然未尝不可,但如果仅止于此,我们则会失去一次认识《雨巷》深刻意义的机会。《雨巷》产生的一九二七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年代。白色恐怖使一部分原来拥护革命的青年一下子从火的高潮坠入夜的深渊。他们找不到革命前途,在痛苦中坠入迷惘,在失望中渴求新的希望。望舒忧郁的气质自然很适合表现这种彷徨、无奈的时代情绪。当时,他隐居松江,在孤寂中咀嚼着“在这个时代做中国人的苦恼,”[17]此时写就的《雨巷》无疑成了黑暗时代的一面镜子,是当时很大一部分进步青年无奈心境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雨巷》不仅是诗人忧郁的象征,而且还是时代苦闷的载体。
三、《望舒草》:内在忧郁的自由释放
对于诗歌艺术,望舒始终都在进行艰苦的探索。到了《望舒草》时期,他已经开始对早期诗作进行勇敢的反叛了。“就是他在写成《雨巷》的时候,已经开始对诗歌的他所谓‘音乐的成分’勇敢地反叛了。”杜衡回顾了望舒写出《我的记忆》时的狂喜:“‘你瞧我的杰作’,他这样说。我当下就读了这首诗,读后感到非常新鲜;在那里,字句底节奏已经完全被情绪底节奏所替代,竟使我有点不敢相信是写了《雨巷》之后不久的望舒所作”。[18]戴望舒的这首使杜衡“感到非常新鲜”的诗,表明他已经找到了诗歌艺术的一种新的可能性。“我们就是说,望舒底作风从《我的记忆》这一首诗而固定,也未始不可的。”[19]
当然,望舒反叛的仅仅是早期诗作的形式,而不是情绪。考察起来,望舒该期的诗歌基本上是“新瓶装旧酒”,形式与早期诗作迥异,情绪则一脉相承。
这时,望舒已经疏远了象征派诗人魏尔伦。从一九二八年起,他开始翻译后期象征派诗人果尔蒙、耶麦、保尔·福尔等人的作品,逐渐倾向于这派诗人自由自在、朴素亲切的诗风。正如施蛰存先生所说:“译果尔蒙、耶麦的时候,正是他放弃韵律,转向自由诗体的时候。”[20]
戴望舒认为:“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适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21]如果说《雨巷》时期他还在选择鞋子的话,那么这时他已经开始自制鞋子了。这样,望舒终于从新月派的阴影中走出来,真正成为他自己,并确立了他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卞之琳先生说得好:他这期的诗歌,“达到了恰好的火候,也就发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声调,个人独具的风格,而又是名副其实的‘现代’的风味”,“这种艺术独创性的成熟,却也表明他上接我国根深蒂固的诗词传统这种功夫的完善,外应(或拒)世界诗艺潮流变化这种感性的深化,却再也不着表面上的痕迹。”[22]
《望舒草》是戴望舒诗歌的代表作。诗人自己也比较看重这个集子,“就是望舒自己,对《雨巷》也没有像对比较迟一点的作品那样地珍惜”。[23]施蛰存先生认为:“望舒对自己在三十年代所宣告的观点,恐怕是有些自我否定的。”[24]确实如此,望舒编《望舒草》时不收《旧锦囊》与《雨巷》中的任何一首诗,清楚地说明了他对早期诗作的态度。在《望舒草》里,诗人那种一以贯之的浓重忧郁几乎浸透了集中的每一片诗叶。另外,由于诗人自动放弃对形式的刻意追求,这就使得那种内在的忧郁得到了更为自由的释放。
观赏形式,或许能见出“新瓶”的诸多妙处;玩味意象,大概会品出“旧酒”的独特风味。下面,笔者分别从形式与意象两个角度对望舒该期的诗歌进行分析。
1.走出形式的樊笼
早期的望舒是个彻底的形式主义者。这种对形式美的执着追求,某种程度上固然是给自己编织樊笼,但形式一旦与诗人所要表现的情绪达到妙合无间的程度,便会激发出艺术的火花,使他写出像《雨巷》那样的杰作来。但对形式美已有成功经验的戴望舒,到了《望舒草》时期,却义无反顾地走出形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诗歌主张:“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25]这些新的主张,使他找到了释放忧郁的新途径。
《望舒草》对形式的勇敢反叛,使它开创了一片新的诗歌美学天地——散文美。说起诗的散文美,不能不提到艾青的著名论文《诗的散文美》。其实,这种新的诗歌美学主张是戴望舒的首创,艾青只是作了发挥而已。艾青自己说得很明白:“我说的诗的散文美,说的就是口语美。这个主张并不是我的发明,戴望舒写《我的记忆》时就这样做了。”[26]“这是他给新诗带来的新的突破,也是他在新诗发展史上立下的功劳。”[27]
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诗歌的目的就是要颠倒习惯化的过程,使我们如此熟悉的东西‘陌生化’,……以便把一种新的、童稚的、生意盎然的前景灌输给我们。”[28]望舒这期诗歌所显示出来的散文美,无疑是对早期诗歌的“陌生化”。正是这种富有创造性的“陌生化”,使其诗获得了新的、更为广阔的前景。
且看这些诗句;“说我是一个在怅惜着,/怅惜着好往日的少年吧,/我唱着我的崭新的小曲,/而你却挪揄:多么‘过时’!”(《过时》)“——给我吧,姑娘,那朵簪在你发上的,/小小的青色的花,/它是会使我想起你的温柔来的。/——它是到处都可以找到的,/那边,你看,在树林下,在泉边,/而它又只会给你悲哀的记忆的。”(《路上的小语》)这里没有整齐的形式,看上去形式自由,结构松散,但字里行间自有一股回肠荡气的忧郁情绪在流动,给读者带来回味和想象。这种诗,“在亲切的日常生活调子里舒卷自如,锐敏、精确,而又不失它的风姿,有节制的潇洒和有工力的淳朴。日常语言的自然流动,使一种远较有韧性因而远较适应于表达复杂化、精微化的现代感应性的艺术手段,得到充分的发挥”。[29]
诗的散文美并不是诗的散文化。“五四”时期,一些白话诗的先驱者认为诗只要写得明白如话,用口语分行排列便是诗。这种诗歌“散文化”的主张实在是对诗的一种误解。《望舒草》中的诗歌尽管也写得明白如话,但诗中总是贯注着一股内在的诗情。如《我的记忆》,全诗共五节,每节形式各异,诗行词句之间开合有致,随意灵活,给人一种闯出樊笼的舒展之感。在第一节中,诗人只用了两行诗切入主题,简洁地交待了“记忆”与“我”的关系:“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得甚于我最好的友人。”第二节中,诗人用一连串的意象让“记忆”纷至沓来,交叠映现。细细体味这些意象,我们会发现一种忧郁情绪的恣意涌动左右了诗句的构成和布局,仿佛一条骤然涌来而又自然流淌的河流奔腾起伏于诗人的笔端。因此,这首诗尽管形似散文,字里行间却始终奔涌着一股浓郁的诗情,体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散文美。
2.多姿多彩的意象组合
意象是诗歌的基本语汇。它是诗人主观情思的客观对应物,不受理性逻辑与语言规范的制约,只忠实于诗人的情感逻辑与想象逻辑。因此,诗人独特的情感个性往往决定着意象的选择与组合。
望舒的气质决定了他忧郁的情感个性,这种情感个性直接影响了其诗的意象选择。打开《望舒草》,像萎谢的蔷薇、颓垣的木莓、梦的灰尘、残的音乐以及夜行人、单恋者、薄命妾、寻梦者之类的意象翩然而来,直把我们带进一个孤独、忧郁、空虚、凄冷的情感世界。
戴诗的意象组合决不平板单一,而是多姿多彩的。这种多姿多彩的意象组合,使诗人忧郁情绪的释放不拘一格,摇曳生姿。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组合方式:
A.内涵相同(或相近)意象的排列。如《印象》,全诗十二行,充满了一些看似零乱破碎、实际上却是具有同一指向的意象:有听觉范畴的“幽微的铃声”与“浅浅的微笑”;有视觉范畴的“小小的渔船”与“颓唐的残阳”;有幻觉范畴的“坠到古井的暗水里”的“真珠”。(这正应了望舒的主张:“诗不是某一个感官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30])这些不同类型的意象的杂置,似乎随意性很大,但细细读来,却不难发现它们在总体内涵和情调上的一致性:都是弱小的,又都是美好的、易逝的;都是渺远的,又都是抑郁的、感伤的。这些意象实际上是形断意连的一体,直接指向诗人寂寞、忧郁、感伤和怅惘的内心世界。
属于这种类型的还有《三顶礼》、《秋天的梦》、《烦忧》等。
B.内涵相异(或相反)意象的叠加。这种方式往往以不同意象的互衬以展示主体的情绪变化。《二月》、《小病》、《微辞》、《深闭的园子》等诗都是好例。这里且看《深闭的园子》:“五月的园子,/已花繁叶满了,/浓荫里却静无鸟喧。小径已铺满苔藓,/而篱门的锁也锈了——/主人却在迢遥的太阳下。在迢遥的太阳下,/也有璀灿的园林吗?陌生人在篱边探首,/空想着天外的主人。”一个“五月的园子”,花繁叶茂,浓荫密布,该是一个小小的欢乐的王国呢。但与自然风光的美丽同时出现的却是人类生活气息的荒寂。“深闭的园子”本身就是一个唤起寂寞与忧郁的荒芜性意象,何况“小径已铺满苔藓”,“篱门的锁也锈了”。主人已弃园子而去,园子里寂无人影,甚至连鸟雀的喧闹声也听不到了,而“陌生人”却在’篱边探首”,“空想着天外的主人”。全诗表现出来的不是一种寂寞与忧郁的情绪又是什么呢?
C.主次意象的交错映衬。这种方式往往在中心意象的逐步展示中,体现主体情绪的变化,其间还常伴有次要意象的映衬。这种类型,比较典型的有《寻梦者》、《秋蝇》、《夜行者》、《妾薄命》等。如《寻梦者》一诗的中心意象贝(珠),“深藏”“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我们只有经过“攀九年的冰山”、“航九年的旱海”与“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等磨难,才能见到“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球”。这一过程显然象征着“寻梦”——追求理想过程的艰难。其间,次要意象像“大海”、“冰山”、“旱海”、“云雨声”、“风涛声”、“海水”、“天水”等则映衬着“寻梦”的历程,体现诗人对人生理想的整体感受。最后,“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但这是“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此中,诗人的忧郁与怅惘之情依然清晰可辨。
D.动态意象的流动、变幻。《古神祠前》即属这类。诗中首先出现的是一只“蜘蛛”,接着变为生出翅翼的“蝴蝶”,后来化为一只“云雀”,最后幻化成一只翱翔于蓝天的“鹏鸟”。蜘蛛—蝴蝶—云雀—鹏鸟,这些意象随着诗人潜意识的流动而不断流动和幻化,由小变大,由低到高,逐渐扩展,暗示生命的流逝如虫鸟的变幻,缥缈不定,无从捉摸,也暗示蛰伏在诗人心底的忧郁、寂寞之情越来越深广。
四、《灾难的岁月》:走向悲愤
抛却《旧锦囊》,走出《雨巷》,告别《望舒草》,望舒走进了《灾难的岁月》。
这一时期,诗人在艺术倾向上转向了瓦雷里、艾吕雅、许拜维艾尔、洛尔迦等人。同时,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与苏联文学也给诗人以影响。[31]当然,前两个阶段所接受的影响仍然沉潜于诗人的心中。这多方面的影响,使这期的戴诗呈观出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兼收并蓄的多元态势。
如果说《望舒草》时期的诗作是“新瓶装旧酒”的话,这期则大体为“旧瓶装新酒”,形式方面体现了诗人早期创作思想的回潮。但诗人并不拘于形式,他只是想把前两个阶段几近对立的形式统一于该期的创作中。
思想情趣方面,《灾难的岁月》已表现出了某种新的因素。具体说来,以《元日祝福》为界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表现的仍是那种一以贯之的忧郁,可视为诗人创作中忧郁的余音;后期则一反常调,跳跃出一连串悲愤的音符。如此看来,《元日祝福》在望舒的诗歌创作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显示了诗人创作观的重大转变。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转变,必须先来消除一个误解。艾青认为:
望舒所走的道路,是中国的一个正直的、有很高的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的道路,这种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人民失去了联系,只是读书很多,见过世面,有自己的对待世界的人生哲学,他们常常要通过自己真切的感受,有时甚至要通过现实的非常惨痛的教育,才能比较牢固地接受或是拒绝公众早已肯定或是否定的某些观念。而在这之前,则常常是动摇不安的。
……他始终没有越出个人的小天地一步,因之,他的诗的社会意义就有了一定的局限性。[32]卞之琳先生也作过类似论述:
大约在1927年左右或稍后几年初露头角的一批诚实和敏感的诗人,所走的道路不同,……面对狰狞的现实,投入积极的斗争,使他们中大多数没有工夫多作艺术上的考虑,而回避现实,使他们中其余人在讲求艺术中寻找了出路。望舒是属于后一种人。……直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才转而参与了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有责任感的诗人的行列。[33]依照艾、卞两位先生的说法,望舒早期属于那种“回避现实”,躲在象牙塔中咀嚼着自己小小的悲哀的诗人。只有在经历了“非常惨痛的教育”之后,他的思想才发生转变,成为一个“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有责任感的诗人”。因此,“他的诗的社会意义就有了一定的局限性”。
这其实是一个误解。望舒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爱国诗人,并非“始终没有越出个人的小天地一步”。下列事实可以为证:一九二六年,他“和施蛰存、杜衡一起加入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上海卢家湾地区搞地下宣传工作”。一九二七年,“因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激进,与杜衡一起被孙传芳军阀当局拘留”。一九二八年,与冯雪峰、杜衡、施蛰存等人“决定办文学刊物《文学工场》,编好两期,因内容过激,未能出版”。(写于一九二七年夏天的《雨巷》,即发表于这年八月的《小说月报》。诗人的实际人生与诗里人生差异何其大!)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大会,并为第一批成员”。一九三四年,去西班牙旅行,声援国际作家的反法西斯运动。一九三八年,“春夏之间,大批文化人转道香港、九龙去汉口,但戴望舒仍留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一九四○年,与冯亦代、叶君健等编辑《中国作家》,“向海外朋友介绍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一九四二年,“因从事抗日活动,被日本宪兵逮捕”。[34]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问题了。那么,为什么诗人前期诗作总是表现一种浓重的忧郁情绪,而不反映自己进步的思想追求呢?这除了决定于诗人的气质,还与他前期的诗歌创作观有关。那时,他“把诗当作另一种人生,一种不敢轻易公开于俗世的人生”。[35]诗歌既然是俗世人生之外的另一种人生,我们怎么能够简单地根据诗风的变化来评判诗人的生活道路与思想历程呢?事实上,早期的望舒是把满腔爱国热情倾注到了苏联文学及其它国家无产阶级文学的翻译与介绍中去了。
因此,戴望舒追求理真理、追求进步的思想前后期并没有什么变化,他并不是“几经变革”,才“终于发出战斗的呼号”的。在“灾难的岁月”里,民族矛盾(抗战爆发)与个人苦难(被捕入狱)的双重刺激,只是导致了诗人创作观的变化。事实上,当时的社会现实已经不允许诗人在“俗世的人生”之外营造“另外一种人生”了。于是,《元日祝福》之后,诗人直面社会,直面人生,悲愤的控诉代替了忧郁的吟唱,民族与社会的苦难代替了个人的悲苦,终于完成了诗风的重大转变。
下面着重谈谈《灾难的岁月》中的“悲愤”。其实,这种悲愤情绪,诗人自己在《等待》之二中已有清楚的揭示:“你们走了,留下我在这里等,/看血污的铺石上徘徊着鬼影,/饥饿的眼睛凝望着铁栅,/勇敢的胸膛迎着白刃。/耻辱黏住每一颗赤心,/在那里,炽烈地燃烧着悲愤。”这里举《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为例。
这是望舒在日寇的铁牢中写下的一首情真意切、撼人灵魂、催人泪下的诗篇。诗中并不存在一个有形的地图,但诗人心灵的“无形的手掌”下却有一片完整而又破碎的祖国大地:“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对祖国的热恋情怀,对敌人的无比愤怒,随着诗人手掌的摸索而不断深化:那长白山的雪峰,那黄河的泥沙,那江南水田中的蓬蒿,那岭南荔枝花的憔悴,那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既是诗人对伤痕累累的祖国大地的感受,更隐含着诗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全诗字字含泪,句句带血,流露出来的情感基调不全是悲切,也不全是愤激,而是两种情绪的水乳交融。透过诗句,诗人的一颗赤心分明在字里行间跳跃,撼人肺腑,感人至深。掩卷之余,我们的情感犹在悲愤中激动,我们的思想还在激动中升华……
注释:
[1]朱光潜:《诗论》第58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2]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1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3]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1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4]《悲剧心理学》第162—163页。
[5]参阅《诗人心理构架》第五章,华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6]孟实《望舒诗稿》,见《戴望舒》第2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7]施蛰存:《戴望舒诗校读记引言》。
[8]李泽厚:《美学散步·序》。
[9]戴望舒:《诗论零札》。
[10]艾青:《戴望舒诗选·序》,人民文学版。
[11]见《文学评论》1983年第4期。
[12]施蛰存:《戴望舒诗校读记引言》。
[13]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版。
[14]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版。
[15]杜衡:《望舒草·序》。
[16]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17]杜衡:《望舒草·序》。
[18]杜衡:《望舒草·序》。
[19]杜衡:《望舒草·序》。
[20]施蛰存:《戴望舒译诗集·序》,湖南人民版。
[21]戴望舒:《诗论零札》。
[22]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版。
[23]杜衡:《望舒草·序》。
[24]施蛰存:《戴望舒译诗集·序》,湖南人民版。
[25]戴望舒:《诗论零札》。
[26]转引自周红兴、葛荣《艾青与戴望舒》一文,见《新文学史科》1983年第4期。
[27]周佶:《就当前诗歌问题访艾青》,见《山东文学》1981年第5期。
[28]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第6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29]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版。
[30]戴望舒:《诗论零札》。
[31]参阅《文学评论》1983年第4期阙国虬的文章。
[32]]艾青:《戴望舒诗选·序》,人民文学版。
[33]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版。
[34]应国靖:《戴望舒年谱》。
[35]杜衡:《望舒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