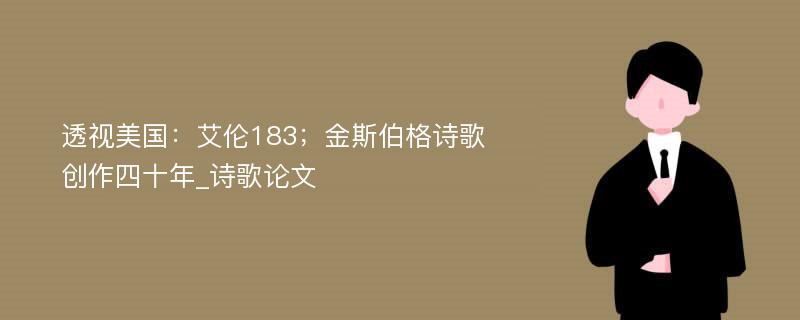
透视美国:艾伦#183;金斯堡诗歌创作四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艾伦论文,透视论文,四十年论文,金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致艾伦·金斯堡的一首诗中,琴斯劳·米斯洛斯写道:
我嫉羡你十足的反叛勇气,
充满激情的言辞,
预言家般狂烈的诅咒……
你侮慢的嚎叫依然回响在
霓虹灯闪烁的沙漠
人类部落在其中流浪,注定走向虚无
……
而你那日记风格的陈词滥调
你的胡须和念珠以及你那另一时代
反叛者的衣着都已得到原谅。
在《1947—1995诗选》的开头,金斯堡本人对“十足的反叛”予以解释:“对于令人昏昏欲睡的媒介力场控制机构,包括政府秘密警察和军队,耗资巨大、惰性十足,散布虚假消息,给人洗脑,使公众沉湎于幻想等现象,我设想了一种语言力场与之分庭抗礼。”
1956年,金斯堡30岁时,他的“力场”随着他的诗集《嚎叫及其它诗选》的出版而引起世人注意。这部诗集的题名篇谴责美国毁灭年轻一代,犹如异教神摩洛吞食献祭给他的儿童那样。金斯堡曾看到他的母亲纳奥米——一位俄国移民——患有受迫害妄想症并被送往精神病院,而他自己在顺利地从新泽西州帕特森市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后,由于卷入了朋友们的轻微犯罪行为而被送往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以代替判刑坐牢,后来,他离开纽约去了旧金山。象他作中学英语教师的父亲路易斯一样,金斯堡喜欢写诗。不同的是,他父亲的诗因袭传统,情操高尚,而儿子的诗有的充满痛苦,有的则充满狂喜。在旧金山,金斯堡同其他几个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思、杰克·克鲁亚克、加里·斯奈德,罗伯特·邓肯)以垮掉的一代脱颖而出,以其坦率的态度以及致力于社会和性改革在创作领域引起了一场风潮。美国海关把在英国出版的诗集《嚎叫》当作淫秽作品没收,旧金山警察局派两名警察前往出售第一版《嚎叫》诗集的“城市之光”书店,逮捕了该诗集的出版商诗人劳伦斯·费林赫蒂。后来在审判时,法官宣判该诗集并非淫秽之作并宣布费林赫蒂无罪。出席审判的传媒机构使诗集《嚎叫》和金斯堡一举名声大振。
继诗集《嚎叫》之后,金斯堡又出版了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作品,其中最出名的是诗集《祈祷及其他诗选》。这部诗集的题名篇是金斯堡悼念母亲的一首长篇挽诗,通过融入犹太移民的极度痛苦,进一步扩大了美国抒情诗的同情对象。后来金斯堡郑重其事地给他的另两部诗集取名为《行星新闻》和《美国的堕落》。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曾写道:“很难从诗中得到新闻。”然而金斯堡地大胆而戏谑地把当天的新闻写进了他的诗中。有关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越南战争、同性恋生活以及城市腐败等方面的新闻,经常出现在金斯堡的诗体简报中。人们常常评论金斯堡的乐善好施、坚持不懈的政治调查、对其他作家的支持、在拥挤的人群前朗诵诗篇(伴有钹、簧风琴和颂歌)、周游世界、戏剧式的抗议活动以及他的道德训谕(针对氢弹、政治欺骗、破坏生态环境等问题),这些行为使他成了一位重要的文人。然而相比之下,金斯堡非凡的诗歌创作才能却较少论及。然而正是他的诗歌才使他成为重要的文学家。
尽管金斯堡为名声所累,事务繁杂,而且年岁渐长,他依然坚持不懈地从事诗歌创作。他的每部著作里都有令人难忘的诗篇。然而由于他神经方面两种对立的诱惑,即妄想狂和情绪低迷,还由于诗歌创作方面的两种诱惑,即民粹主义和“自发性”,他的创作成就经常受到威胁,有时还遭到破坏。在他最优秀的诗篇中,他的妄想狂为他的自嘲、幽默、智慧以及他对存在的无限好奇心所缓和;而一股感情逆流却又及时唤起了他的佛教清净思想,将任何现象都视为一种幻觉。如果金斯堡的民粹主义渴望获得一张白金唱片的话,那么它将受到艺术的检验;而在他旅途中公共汽车上录制旁白的“自发性”则被一种讲究条理的观念所包围。(当各种力量失去平衡时,他的诗篇便会变成夸夸其谈或者说教,或者是摇滚抒情诗或者是日记般的随笔。)总而言之,金斯堡的诗篇是对美国社会以往40年许多方面的透视。
金斯堡对社会弊病的悲观认识,就其想象力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患有偏执狂的母亲。他在《祈祷》中说,“从她疼痛的头脑中我第一次获得了幻象。”另一方面,在他长大成人的那个年代,美国规定同性恋为违法行为,对朝鲜和越南不宣而战,在南美和世界其他地方扶植傀儡政府,公然推行种族主义,从事丑恶的毒品交易,通过联邦调查局毫无廉耻地在暗中监视普通公民。金斯堡与那些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同代人截然不同,一方面在于他接受政治教育比较早(通过他母亲),而且在于他作为一名同性恋者处于社会边缘,为了维护自尊而同现状相抗争。而他与其他许多活跃的诗人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他终于认识到所有官僚都是一丘之貉。他在社会主义国家如同在美国一样不受欢迎(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都曾把他驱逐出境)。与大多数改革者不同,他意识到他的创作激情的潜在原因在于他自身的敌对心理,而这种敌对心理又外显出来,被误以为是他人的敌对心理。金斯堡早期诗篇中的愤怒和绝望之情一方面是他自我憎恨的产物,而另一方面又是对世界进行客观批评的产物。而他自己的感情危机却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美国年轻一代所蒙受的令人压抑的社会所带来的痛苦:
他们被逐出学校
因为疯狂和在骷髅般的窗户上
发表猥亵的颂诗……
他们要返回纽约
带着装有大麻的皮带
蓄着尽人皆知的胡须
走到拉雷多时被逮捕
他们跪倒在地铁里嚎叫
抖动看性器和手稿
被强行拖下屋顶。
金斯堡由于感受到他所谓的“听觉幻象”而从自杀的抑郁之中得以解脱。在幻象中,他听到了朗诵诗的声音,他认为那是威廉·布莱克的声音。由于金斯堡赞同采用口头形式,而反对书面抑制,他自己的诗始终以可听到的声音为特征,因此这种幻象也是听觉形式则不足为奇。由于布莱克是英国最杰出的反叛诗人,如同惠特曼是美国最杰出的反叛诗人,因此就金斯堡早期的诗歌而言,布莱克是他的鼓动者,而惠特曼则是他的指导者。惠特曼的诗句“把锁从门上卸下!把门从门框上卸下!”是《嚎叫》的卷首引用语;为了使三位革命先驱组合在一起,金斯堡把雪莱的诗句“死亡吧!/假如你将同自己所寻求的目标在一起!”作为《祈祷》的卷首引用语。
总的来说,金斯堡诗歌创作的榜样是布莱克、雪莱和惠特曼三人,而并非佛经。他的创作道路同T·S·艾略特很相似:他们俩都具有容易激动的情感,一旦受到刺激他们的精神便会极度失常;两人都曾精神崩溃;两人都曾试图寻求可以减轻、引导或消除他们的过分反应的某种明智的形式。艾略特在维托茨医生的洛桑修养所找到的东西(“给予……同情……支配”是《荒原》中引用《奥义书》的语句),金斯堡则在佛经和沉思中找到了。
在我看来,佛教对金斯堡抒情诗的影响同英国国教对艾略特抒情诗的影响大致相同:张力在其诗中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说教。畏缩不前的人因能控制住难以控制的情绪并调节神经而能够生存。我们不能驳斥在生活中能避开精神病院的智慧。然而对不可抑制而令人困惑的痛苦进行分析正是富有表现力的抒情诗句的深层根源所在。用来抑制这种痛苦的准则本身则是另一种痛苦(即自我残伤的痛苦)的根源。虽然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承认这一点,但金斯堡对此却并不感兴趣。他在佛教虚无思想中找到了慰籍,而不是痛苦。
新近出版的《诗选》并不十分令人满意。金斯堡的许多佳作,诸如《美国的变化》、《机会》、《生态学家》、《黑色裹尸布》等都被删掉了;而在1984年出版的《诗集》中所未收入的那些诗则被收入60余页的《诗选》。这些诗以表演见长,而不适于冷冰冰的印刷。金斯堡极其愉快地回忆他同鲍勃·迪兰的关系。他说:“我非常乐于进行两代人之间的这种影响交流,这肯定了艺术和思想传播的古老传统。”很难准确解释:为什么金斯堡最不可能以模仿迪兰的抒情诗而进入传统的发祥地。但可以较为准确地说:“金斯堡起初的工作是‘拓宽意识范围’,切实考查意识的本质,甚至改变意识。”这好象是对金斯堡创作的一个很好的总结。当然,正如琴斯劳·米斯洛斯和阿德里安娜·里奇的文章所起到的作用一样,金斯堡在公众面前的表现以及他的政治活动都以其特有的方式有助于他“拓宽意识范围”。然而诗歌有其自身的表达方式,不同于游行或写作劝说性的散文。
金斯堡诗篇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采用电影技巧,以一般现在时的时态及时详细地描述所发生的事情。金斯堡的诗篇会令人身临其境。例如以《曼哈顿五月一日的子夜》中,金斯堡晚上出去买报纸时发现几个工人在检查煤气泄漏。他注意到煤气检修孔处那个工人的圆圆脑袋,注意到路面沥青与花岗石的连接,发现有一辆闲荡的卡车在场:
11号街角昏暗的街灯下
地上的一个坑中
一个身穿工作服的人
毛线帽压在弹丸似的脑袋上
拿着标杆和手电弯腰站在那里
在齐腰深的坑中晃来晃去
查看脚下,直到埋没在花岗石镶边的沥青
路面中的胸部……
是的,他身上散发着城市大便的恶臭
6英尺深处腐烂的管道
随时都会被火花引爆
因为我看到
康·艾德没有灭火的运货汽车。
令人感到愉快的是诗中没有烦琐的描述。我们没有被要求同情工人阶级,或因煤气泄漏破坏生态感到惊恐。金斯堡对现实的极大兴趣,使我们心平气和地分享他的感受。金斯堡的思绪涉猎广泛,其思维方式不可预测。在另一首诗中,煤气泄漏的场面或许会使他想起自己的煤气炉,或者使他想起曾在印度见到过的类似的工人,或者使他想起夜晚散步的魅力。而在下面这首诗中,他的思想突然转向了古罗马和乌尔:
我匆匆走过,想起了古罗马和乌尔
那时可否象现在这样
检查员和过路人在同样的阴影中
记录腐烂的管道和大理石上的犹如楔形文字的垃圾堆
夜半,普通公民走上街头
打听帝国的消息
人们不可能通过使意识循规蹈矩地展开而在诗中拓宽意识(比如象思辩诗那样)。不管其意图如何高尚,循规蹈矩的方法,总会使意识受到限制。金斯堡在最佳状态时思维敏捷,不循规蹈矩,自由自在。
考查“意识的本质”是指在我们用来表达意识行为的通俗言词(例如“规划”、“回忆”、“记忆”、“伤心”和“期望”)的间隙中寻找无以数计的位置。本世纪有许多杰出的探索者对意识本质作出了探索(在小说方面有乔伊斯和吴尔夫,在诗歌方面有艾略特和斯蒂文森),探索工作好象业已完成。然而金斯堡又作出了新的探索。这便是通常认为是难以启口的一些事情(例如《祈祷》中描述他母亲在浴室呕吐、大便;《请吧,主人》中描述他自己在性生活中的奴颜婢膝;《你在忙什么?》中描述他由于贝尔患瘫疾而窘迫不堪)。尽管金斯堡详细地描述羞愧和耻辱之事,但借用他送给弗兰克·奥哈拉的称号,他自己也是“群氓古怪感情的监督者”。
艾略特和斯蒂文森并不擅长描写意识的喜剧性,而金斯堡则不然,他经常关注意识问题,其文笔非常活泼。那双带有讽刺意识的眼睛随时都会找到当代一种新颖的体裁。例如,“人事广告”,用其扫描自己的心灵:
正值暮年的诗人教授
寻觅伴侣伙伴保护者朋友……
共享下东区的床第沉思住所,
帮助激励人类征服世界,
愤怒与罪过
得到惠特曼、布莱克、兰波、玛·雷尼和弗拉迪的许可……
在纽约此地寻找我
孤独地与孤单的人在一起。
金斯堡的诗暗示,我们有谁没读过“人事广告”而又不曾在心里写过一则广告呢?又有谁还没认识到自我描写本质上的荒诞之处呢?有待探查的各个意识层面由于在金斯堡的广告中竞争位置而受到嘲笑:简略的自我绰号,如“诗人教授”,无用的陈词滥调,如“暮年”,回归古代,如“寻觅”,试图找到同性恋伙伴的别称,如“伴侣伙伴保护者朋友”。(作家精神状态随之稍有变化:从《圣经》的“伴侣”到委婉语“伙伴”,再到封建时代的“保护者”,进而变为梦寐以求的“朋友”。)兰波和玛·雷尼在同一诗行中的被迫共存,显示出意识的各个层面真是不胜枚举。金斯堡诗篇的最后一行是他的自我影像,其实是在重复莱昂内尔·约翰逊的诗句。约翰逊庄重地写道:“孤单一个,我走向孤单;也是神圣地,走向神圣”。这表明了金斯堡决定不摒弃(模仿的)崇高。
在抒情诗中,人们通常仅仅通过改变自己的意识来改变他人的意识。金斯堡通过自我意识的改变(酷似惠特曼那样)促使读者起而效之。《向日葵经》便是诗人一首较为出名的描写狂烈的自我意识改变的诗作(“你从来都不是火车头,向日葵啊,你就是一株向日葵!”)。另外,金斯堡还写了一些讽刺诗,其中最无耻也最欢快的是著名的《采我的雏菊》:
采我的雏菊
饮干我杯中的酒
我的房门全部打开
中断我的思路
为了椰子果
我的蛋都被打碎
说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不丢掉许多浮华沉冗的内容(如果有人恰巧要包含一些的话)。当读者读金斯堡的诗篇时,要使自己成为诗人本人,就要经历强烈的意识改变,哪怕是短暂的。由于金斯堡的魅力,读者会越发兴奋,越发关注,越发易受感动,越发嘲弄。幽默胜过敌对心理,好奇心胜过恐惧感,世界便随之变好。
最后,金斯堡经常采用的唤起意味的可靠方式是其富有节奏感的动力,这种动力是以滚滚浪涛似的长诗句来表达的。当金斯堡竭力对待这一问题时,节奏的紧迫性有时便会不自然,但通常是真实的,意识着部分生命需要在历史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金斯堡不曾在纽约遭到抢劫的话,我们将无从品味《抢劫》中不规则的韵律:
我走下去大声喊叫着嗷啊哼
冲着那些在门廊上观看的情侣们,
他们慢慢品味,这怎么会是抢劫?
这些奇怪的人要做奇怪的事,
比如对付我的衣袋,光脑袋,
那条骨折后痊愈的腿,我的软底鞋,
我的心脏——
他们有刀吗?嗷啊哼——
他们有能插进眼睛、耳朵和屁股的尖铁棒吗、嗷啊哼
我慢慢地倒在路上
竭力保护好毛线包
里边装有诗、地址、日历和律师记录
挂在我的肩头。
金斯堡毫不抵抗的歌唱使得抢劫者们简直要发疯,“住口,不然就杀了你”,由此,诗人得出结论:改变自己的意识远远比改变街上人的意识要容易得多。尽管这首诗开头充满了理想主义者的期望,而最后悲惨地以面对现实而告结束,但并没有消除这样一个前提,即以非暴力行为回应暴力行为是应付无休止的侵害行为的唯一的变通方法。在阅读金斯堡的《诗选》时,新的一代人会在这些诗中感受到金斯堡的“语言力场”仍然具有强有力的想象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