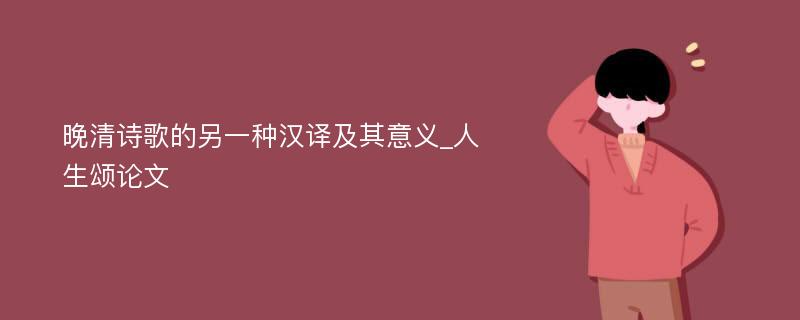
《人生颂》在晚清的又一汉译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意义论文,人生论文,汉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的考证,约在1864年,英国公使威妥玛用一种有章无韵、长短不齐的中文,汉译了朗费罗诗《人生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董恂又据之“裁以七言绝句”,从而使之成为“破天荒最早译成汉语的英语诗歌。”①直至2005年,有人发现1854年《遐迩贯珍》所刊弥尔顿诗《论失明》,才是“最早的汉译英诗”②。不过,这是把考察时间往前推,钱钟书当时的论说当然选择的是向后看。他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发现作于1882年的《舟行纪略》,其中有“也许是中国有关朗费罗最早的文评”,但这文评没点及《人生颂》。钱钟书还让我们“对读”一下1906年林纾《海外轩渠录》序文,和出洋外交官张德彝前一年的日记,看看两人到底谁比较了解西洋文学。这表明即使他论说的范围延后至1906年,仍没发现《人生颂》译本的更多信息。看来,钱先生并没读到1897年《中西教会报》所刊的一首译诗《大美龙飞罗先生爱惜光阴诗》,否则,他早为1864年的汉译《人生颂》找到了后继者,不知又要做出何等妙趣横生的论说来。
一“难得一见”与既有叙述
《大美龙飞罗先生爱惜光阴诗》(以下简称《光阴诗》),刊于1897年10月《中西教会报》第34册③,署名“沙光亮口译、叶仿村笔记”。生逢清朝末年,如此小事自然难引时人多大注意。加之时日久远,百余年后的今天,这首译诗的确已是难得一见。郭长海先生1996年时就认为,“直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是从目录学的角度认识到它的存在。”④时至今日,提及该诗的几处著述似乎仍然无缘睹其真容,在叙述中留下了几多模糊。
上海图书馆1965年编定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第一集》,可能是现今能查到记录有该诗信息的最早资料。该汇编将之记为《美国龙飞罗先生爱惜光阴诗》,署为“(英)沙光亮口译,叶仿村笔记”,与原文其实有文字出入。据上海图书馆馆藏胶片显示,目录中该诗题目实为“大美龙飞罗先生爱惜光阴诗”,只无直接署名。这里的不同,不知为编者参见了其他版本,还是抄写时的疏漏所造成。
1989年连燕堂先生《近代的诗歌翻译》一文,在引述钱钟书对威妥玛、董恂汉译朗费罗《人生颂》的论说后,写道:“1897年10月出版的《中西教会报》第34册,刊有《美国龙飞罗先生爱惜光阴诗》,署(英)沙光亮口译,叶仿村笔记。”⑤这与上海图书馆的汇编写法一致,不知是否是直接受它影响。连先生还敏锐地发现,该诗与安徽休宁人黄寿曾的《寄傲盦遗集》所录《白羽红么曲》同为朗费罗诗,龙飞罗即朗费罗,后者即今人所译《箭与歌》,两诗翻译“都并非是受了董恂的影响”。遗憾的是,连先生既没列出《光阴诗》诗句,也没明确表示读过原文,这倒让后人仍无法见其原貌,更不能判断《光阴诗》为朗费罗哪首诗作。
1994年《外国文学研究》第2期发表的程翔章先生文章《近代翻译诗歌论略》,也提及《中西教会报》刊载《光阴诗》事。其题目中的国别仍为“美国”,而非原文“大美”,署名字样也和上海图书馆目录、连燕堂先生文章相同,照样有原文本无之“(英)”。随后,郭长海先生在《试论中国近代的译诗》文中,将该诗题目简成《爱惜光阴诗》,并改变口译者、笔记者位置,写为了“叶仿村口译,沙光亮笔录”,原文“笔记”也变为“笔录”。史料的“难得一见”,的确使《光阴诗》信息不好把握。
郭长海先生之说,显然影响到了随后出版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对《光阴诗》的叙述。提及该诗,著者用脚注形式十分严谨地标明信息来自郭长海文章。但由于排印问题,这里表述为了“叶仿村、沙光亮最早译了他的《爱情光阴诗》(1897)”⑥,原题“爱惜”被误排成了“爱情”,“最早”一词也易让人误解。
近来有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也涉及一点《光阴诗》。谢向红2006年的《美国诗歌对“五四”新诗的影响》有此一笔:“1897年叶仿村、沙光亮翻译了朗费罗的《爱惜光阴诗》。”其说法可能是受郭长海先生影响,仍然是叶在前、沙在后。邓庆周2007年的《外国诗歌译介对中国新诗发生的影响研究》,附录有《外国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大事年表(1852-1927年)》,其中一则:“龙飞罗(朗费罗)的《爱惜光阴诗》由沙光亮口译、叶仿村笔录,载1897年10月《中西教会报》第34册。”《光阴诗》题目也同郭长海先生的简写一样,原文“笔记”在此依然为“笔录”,口译、笔记者倒是回到了原来位置。想来,以上两位可能也没真正读到《光阴诗》。
除此以外,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包含该诗信息的文章少之又少,且与原文无一致说法,有的甚至一再将题目误写成《爱情光阴诗》。其他翻译文学史著也大多不提该诗,更别说列出详细信息来。可见,《光阴诗》的“难得一见”,的确使之长时间局限在“目录学的角度”,让此前的研究者难识其真容。但是,如此状况,是否意味着这首译诗只能湮没于历史尘埃,是否只具有一点目录学位置的价值?
二 汉译《大美龙飞罗先生爱惜光阴诗》
细细翻阅《中西教会报》至1897年第34册,赫然就见到《大美龙飞罗先生爱惜光阴诗》!标题、署名、正文历历在目,黄纸黑字,铁板钉钉,该诗终于破云而出,真面目示人。笔者在此依样画葫芦列出该诗,只将原文竖排变横排,繁体变简体,并加上了现代标点而已。同时,列出英文原诗,以便对照。
休和我诉声音凄痛,Tell me not,in mournful numbers,
今生不过空虚梦。 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
须知打盹与死相同,For the soul is dead that slumbers,
似是而非事常众。 And thins are not what they seem.
今生属实今生率真,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
尽头路不是荒坟。 And the grave is not its goal;
物从土灭物从土生,Dust thou art,to dust returnest,
未曾论到人灵魂。 Was not spoken of the soul.
不独安乐也非忧愁,Not enjoyment,and not sorrow,
此道非我命不犹。 Is our destined end or way;
只行事使我明日彀,But to act,that each to-morrow
比今日格外进求。 Find us farther than to-day.
知识无穷年华易暮,Art is long,and Time is fleeting,
我心虽雄坚且固。 And our hearts,though stout and brave,
但如灵鼓震动形模,Still,like muffled drums,are beating
领众吊客上坟墓。 Funeral marches to the grave.
宽阔世界征战沙场,In the world's broad field of battle,
浮生如兵宿道旁。 In the bivouac of Life,
不可像那哑兽被赶,Be not like dumb,driven cattle!
须当阵上作忠良。 Be a hero in the strife!
勿倚将来景况可爱,Trust no Future,howe'er pleasant!
往不咎任死互埋。 Let the dead Past bury its dead!
今日独行切勿延挨,Act,-act in the living Present!
心在胸神在上界。 Heart within,and God o'er head!
伟人行为提醒我侪,Lives of great men all remind us
能使我一生可爱。 We can make our lives sublime,
去世也留胜迹下来,And,departing,leave behind us
仿佛沙滩脚踪载。 Footprints on the sand of time;-
踪迹恐另有人瞥见,Footprints,that perhaps another,
过此时日洋最险。 Sailing o'er life's solemn main,
船碰沉沦水手可怜,A forlorn and shipwrecked brother,
幸观足疾愁才敛。 Seeing,shall take heart again.
竭力尽心理当快赶,Let us,then,be up and doing,
寸心有志何懼哉。 With a heart for any fate;
努力争先稳步天街,Still achieving,still pursuing,
学习劳苦和忍耐。 Learn to labor and to wait.
至此,既有叙述的疏漏和原文的难得一见等问题,已得以解决。该诗题目不再模糊,口译、笔记者也不会再坐错位置,“爱情光阴诗”也该更正为“爱惜光阴诗”了。但此诗究竟为美人朗费罗哪首诗作?
1864年的《人生颂》汉译,由于有钱钟书大名鼎鼎的发掘和旁征博引的论述,在连燕堂等人著述中受到相当重视。但是,这些著述在提及《光阴诗》时全将之视为配角,只用来表明1864年后朗费罗诗偶有人注意。而且,他们都区别看待《光阴诗》与《人生颂》,在行文中似乎把它们视为朗费罗的两首不同诗作。这难道是事实吗?
细读《光阴诗》,却兀自有着似曾相识之感!开端两句“休和我诉声音凄痛,今生不过空虚梦”,与威妥玛1864年“词意格格不吐”、“生硬以至晦涩”译文的前两句“勿以忧时言,人生若虚梦”,倒是不无相似。再对照《人生颂》原文前两行,这不正是对之不够准确的汉译?次第而下,略加对照,《光阴诗》与英文《人生颂》意思竟然大致相当,与董大人译诗及英文原诗句数也是相同,都为36行。最后,《光阴诗》“努力争先稳步天街,学习劳苦和忍耐”两句,与英文诗最后两行,其表意仍是大致相符。可见,《光阴诗》就是朗费罗《人生颂》!继钱钟书考证出的“长友诗”之后,《人生颂》又变为了《大美龙飞罗先生爱惜光阴诗》。
汉译《光阴诗》形式上大致整体,但句句之间字数并不等同,单句都为八字,双句又为七字。八言诗本就十分少见,何况还有七言交错其中?这使得全诗形体稍有错落,与传统诗形明显有所不同,倒是更接近了每两行错落的原诗。看来,不管是口译者,还是笔记者,都没严格按照传统诗歌形式来翻译,且诗句读来也有不甚清楚之处。其开端两句就有歧义:“休和我诉声音凄痛,今生不过空虚梦”,是将后一句理解为“诉”的内容,还是理解为“休和我诉”的理由?杨德豫将此译为“不要在哀伤的诗句里告诉我:‘人生不过是一场幻梦!’”⑦两相比较,不难见出前者多有混乱。第三句“似是而非事常众”,也多出了原文所含意思。译文的粗糙和模糊处不仅于此处。“踪迹恐另有人瞥见,过此时日洋最险。船碰沉沦水手可怜,幸观足疾愁才敛”几句,读来简直有点不知所云,杨德豫对此的翻译就清晰得多:“也许我们有一个兄弟/航行在庄严的人生大海,/遇险沉了船,绝望的时刻,/会看到这脚印而振作起来。”可见,《光阴诗》的有些地方译得实在不怎样,同样有着钱钟书评此前《人生颂》译文时所说的“生硬以至晦涩”。
那么,《光阴诗》的汉译是否也有特别之处?钱钟书指出威妥玛翻译《人生颂》时,词汇不够,汉语表达能力很差,将“Art is long,and Time is fleeting”译为了“作事需时惜时飞去”,董恂又将之发挥为“无术挥戈学鲁阳”,与原文相去更远。《光阴诗》将此译为“知识无穷年华易暮”,与杨德豫所译“智艺无穷,时光飞逝”倒是十分切近,也还能传达出原文意趣。“不可像那哑兽被赶,须当阵上作忠良”两句,读来也明白清晰,显示出口语化色彩,避免了钱先生所批评的那种威妥玛的“不妥”和董恂把原意“一扫而光”的毛病。最后一句,“学习劳苦和忍耐”,也可说是对原文较准确的直译。此外,“能使我一生可爱”、“竭力尽心理当快赶”等句,读来也实在浅显明白。看来,《光阴诗》也有着不少理解较准确和表达清晰之处。
在韵律方面,译诗也有所注意。《人生颂》原诗四行一节,为ABAB式押韵,每节换韵。再看译成的《光阴诗》,也是每四行为一押韵单元,每单元押韵ABAB式。就连今天看来韵母有所不同的“真”与“生”、“坟”与“魂”、“场”与“赶”、“赶”与“街”等处,在查对译诗行为发生地的方言之后,也会发现它们其实极为合韵。其地不分鼻音韵尾n和ng,故“真”与“生”、“场”与“赶”韵母相同;“un”发音为“uen”,故“魂”与“坟”同韵;无an韵母,故“赶”与“街”押韵相近。⑧对韵律的这种注重,甚而影响到某些诗句表述,让“似是而非事常众”、“幸观足疾愁才敛”等处读来不无别扭。固有的韵律传统意识,虽没能严格束缚这里的译者,但对译诗还是有所影响的,再加之形式上大体整齐,这首译诗也就仍属于古体诗歌范围。不过,相对于其他完全以传统形式来翻译西诗的做法,这里的汉译又呈现出了更多自由,其形式、语言、节奏都参差错落,与形式整饬、格律讲究、平仄严谨的诗歌传统有着较多不一致。较之董恂《人生颂》译文,除开模糊不通之处,该诗的确也浅白易懂得多。
董恂1864年将《人生颂》译为整齐的七言,钱钟书评其“还能符合旧日作诗的起码条件”,算是“文理通,平仄调”。传教士所办中文刊物《遐迩贯珍》刊出的汉译弥尔顿诗,为四言诗体,形式严整,语言典雅,看来也是经过了诗文水平很高的中人润色。⑨从这方面看,《光阴诗》的译者明显没有那般水平,其遣词用语、平仄韵律远远说不上典雅谨严。不过,译诗整体上的俗白浅显,较为明显的口语色彩,倒是使之包含了另外的意义。
三 译者构成与翻译意识
原刊将译者直接标为“沙光亮口述,叶仿村笔记”,这两人身份至今也无人注意,有关叙述都只沿用上海图书馆汇编的说法。其实,两位译者的大致身份并不难确定。在能查到的《中西教会报》中,出现二人名字的文章还有几处。1892年第16册所刊《中国自行教会论》,署名“沙光亮”;1893年12月《除鸦片烟害论》署名,“西沙光亮,华达贯吾”;1896年9月《孤子堂学生信稿并序》,署名“大英国沙光亮”;1896年12月所载《醒教喻》,又署“英教士沙光亮著”。在1897年10月《中西教会报》中,紧接《光阴诗》后二人还合译了《全心归主》一诗,署名“沙普照口述,叶仿村笔记”。由“光亮”到“普照”,想来这位大英传教士不仅取了汉名,还按照中国人习惯有了“普照”这一称法。
据上海图书馆所编目录,1898年《中西教会报》39册《印度教贵妇进教说序》一文,署名“[英]滁州堂沙冯氏口译,六合县叶方春笔述”,这又提供出更明显的信息。在1998年修订的《滁州市志》中,沙光亮正被提及。他为南京基督教会教士,1887年与路光邦一同到滁州,拟租屋传教,却因百姓反对未成。1889年1月二人再次来滁,租得房屋开堂传道,是为滁州基督教会传入之始。与随后到来的传教士一起,他们开办学校,举行戒毒会和天足会,以西药治疗疾病,并编排说唱圣经教义,努力吸引百姓信教。⑩这里的“滁州堂”,定然为沙光亮所在的滁州基督教堂。但是,查阅《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等资料(11),暂时还没发现“沙光亮”或相近发音的中文名。想来,他多半为一普通的英国传教士,不过是在《中西教会报》上偶尔发表几篇文章,中文也不是太好。
叶仿村又为何许人?“六合县叶方春笔述”,与1900年2月《救世圣教论略》一文所署“棠城叶仿村”,都提供了参证信息。六合县在今江苏西南部,古有棠邑之称,“棠城”正为另一说法。在此县方言中,“春”、“存”发音几无区别,由此想来,“叶方春”与“叶仿村”完全有可能是一人。与“沙冯氏”的合译行为,也增加了他就是与沙光亮合译《光阴诗》的“叶仿村”的可能。从其宣传教义的文章来看,他与传教活动关系密切,应为一基督教徒。1991年修订的《六合县志》记载:“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基督教始传入六合,首任牧师为美国人沙各亮(译音)。”(12)虽将沙光亮误记为美人,1898年的时间也待确证,但能见出沙光亮此时到过六合传教。六合与滁州相距不远,的确也为二人合译提供了空间上的可能。不过,叶仿村看来也不是什么文人名士,在《中西教会报》露了下面,就不再有迹可寻。查《六合县志》“人物篇”及其他也寻之不得。从《光阴诗》译文及其文章来看,叶仿村的诗文水平也不见得多高。
那么,《光阴诗》整体上俗白浅显的倾向,究竟只是译者诗文水平不高造成,还是包含了其他缘由?
傅兰雅曾描述晚清时期中西人合译的情况:“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用;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13)沙、叶二人的合译大致不出这种方式,但却并没较好“合于中国文法”。从当时文人中寻求一润色高手,应该并不困难。1891年《中西教会报》第5册所刊《以诗论道(并序)》一文,其中几首悟道诗就显出较好的诗文功底。其一:“窃谈浮生若梦中,须从梦里辨非濛。迷途急返终无悮,大道前行即有功。去伪存诚循本分,黜邪屏恶悉真衷。蛟龙涸辙何甘困,待际风云入九宫。”谈的虽是劝善除恶的老话,读来却也别一番味道。要是为了“文法”,找该作者来做合伙人,定然可以译出一番典雅的诗来。
如此看来,《光阴诗》译文,不会是因寻不到润笔高手而不得不如此,而是另有因缘。1891年2月,主编林乐知在代为发刊词的《中西教会报弁言》中强调,要使“天下一道同风,咸归大道”,故而“斯报所载语,不欲过文,期于明理,词不厌详晰,期于晓众,俾令贤愚,共喻童叟,共知觉世牖民,实阴助上帝传道于天下。”(14)在此办刊意图影响下,刊物语言的确较为浅白。1891年第3册“林乐知口译、任申甫笔述”的《全信得救》一文,就有如此开篇:“美国有一教师,一日在堂讲书,四方来听者甚多。”全篇行文,几与白话相去不远。沙光亮1896年在《孤子堂学生信稿并序》中,直接引述美国儿童给中国人的信。第一封如此:“请告诉中国的男孩女孩有一个七岁小姑娘应许为他们做祷告”。其他几封都用这般语言,相较于当今口语,几乎也没多大区别。可见,沙、叶二人的《光阴诗》,也明显符合了《中西教会报》体现的语言意识。
其实,这种语言意识并非到了此时才有所表现。1815年于马六甲创刊的第一份传教士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其序言就写道:“贫穷与工作者多,而得闲少,志难于道,但读不得多书,一次不过读数条。因此《察世俗》之每篇必不可长也,必不可难明白。”(15)考虑让普通人接受,文章语言自然需要明白易懂。但是,在面对中国文化深厚传统的抵触时,西方传教士又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证明自身在文化修养、文明程度上并非蛮夷,以便获得中国人士的认可。因此,1833年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53年香港创办的《遐迩贯珍》、1857年于上海出现的《六合丛谈》等传教士所办中文刊物,都采用了符合中国文化习惯的文言形式,以减轻教义宣传阻力。如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所说,“传福音于中国,必摭采中国圣贤之籍以引喻而申说,曲证而旁通”(16),这些刊物文章往往引用儒家经典,以示自己言说有中国圣人可证。
不过,在有意模仿中国传统文学规范之时,传教士的语言意识也有所变化。据韩南统计,19世纪传教士所作具有“小说”特征的叙述文本有20多部,它们“一般是用白话(普通话或者方言)写的”,较为明白易懂。(17)洋务运动中西学大受重视,传教士在文化心态上也由最初的寻求认可,逐渐变为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审视和批评。在整个知识结构中,以科技为主的西学译介以及传教士的参与,使他们在文化心理上的压力大大降低。传教士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变动,显然促使他们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了自己的语言意识。美国传教士狄考文1881年批判中国教育问题,就指出“中国之话不入文,而文不归话,已非学问便利之门。”(18)就在《光阴诗》译出前两年,傅兰雅在《万国公报》等处登载广告“求著时新小说启”,指出当时积弊最重大者有三,其一便为“时文”,进而提出语言要求:“辞句以显明为要,语言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19)征文告一段落,他又于1896年3月《中西教会报》15册刊出《时新小说出案启》,再次强调文章语言要能使“妇人孺子亦可观感而化”。(20)
《中西教会报》正处于这种语言意识变动之中,它不仅较多采用了浅显化语言,还刊文批评文墨之邦“字奥文深,与言语相去甚远,则人不难于道理,而难于文字。”(21)如此一来,汉译《光阴诗》不仅与整个刊物语言要求相符合,还与整个传教士的语言意识有着深层联系,这一译诗事件也明显有了不止于目录学的意义。
从沙光亮的传教意图来看,翻译此诗也正合其意。沙光亮为一虔诚传教士,在《醒教喻》文中他叙述自己传教“已历十余寒暑”,并举出言不及义的例子来吸引世人信仰上帝,强调“不进天堂,即下地狱,人而无信,悔之晚矣”。(22)他对上帝有着无尽信仰,甚而认为欲除鸦片之害,只“遵上帝旨意,蒙上帝辅助”即可(23)。在与叶仿村合译的《全心归主》中,类似于“我必应你福音美旨趣”、“我行你旨意虔心虔意”这样的句子频繁出现,真正表现出他的“全心归主”。这样的意识,必然成为择取《人生颂》进行汉译的一个主导性因素。
朗费罗《人生颂》呈现出一种珍惜时日、积极行动的心态,与沙光亮《醒教喻》中表示出的“死难逆料,何悔改不自今始耶”的劝谕,正好有着较为一致的精神导向。原题中“Psalm”一词,本来就有“赞美诗、圣诗、圣歌”之意。“Heart within,and God o'er head”一句,《光阴诗》也正好译为“心在胸神在上界”。朗费罗19世纪的名声如日中天,其诗作被译成20多国文字广泛传播。在美国已有两次省亲经历的沙光亮,定然熟知这位诗人之名。加之《人生颂》与传教意图较为吻合,对此作出翻译并刊登在中文刊物上,也就十分自然。不过,他显然并不愿将此译成典雅平稳的中国诗。只要能传达出一种积极信仰,而且让“神在上界”,让社会下层群众读懂,他也就不再追求深奥的遣词造句。从1887年开始,他被派往滁州一带传教,至翻译《光阴诗》时已逾10年,他自然更清楚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平。
相较于之前的《人生颂》汉译,《光阴诗》虽然也经了华士参与,但其中意识已有很大不同。在翻译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已不是董恂这样的官员文人,而是传教士和信徒,他们的意图不是“同文远被”,不是钱钟书指出的“引诱和鼓励外国人来学中国语文,接受中国文化”,而是“期于晓众,俾令贤愚,共喻童叟”。尽管背后有着传教意图,其语言上的浅显俗白趋向,形式上与传统的不同,在1897年前后的语境中都无疑具有了积极性的喻义。对于晚清开始的西诗汉译来说,这一名为《大美龙飞罗先生爱惜光阴诗》的《人生颂》译本,理应占有一个重要位置。
注释:
①钱钟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4页。
②沈弘、郭晖:《最早的汉译英诗应是弥尔顿的〈论失明〉》,《国外文学》2005年2期。周振鹤《比钱说第一首还早的汉译英诗》,《文汇报》2005年4月25日,对此也有论说。
③《中西教会报》,1891年创刊于上海,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1893年12月后停刊,1895年1月复刊,卷期另起。此后,美国卫理、高葆真、华立熙、莫安仁、季理斐等任主编。1912年1月改名《教会公报》。
④郭长海:《试论中国近代的译诗》,《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
⑤见《中国近代文学百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页。
⑥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⑦杨德豫译,《朗费罗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⑧参见《六合县志》方言部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79-687页。
⑨沈国威:《〈遐迩贯珍〉解题》,(日)松浦章,(日)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⑩《滁州市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904页。
(11)《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2)《六合县志》,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71页。
(13)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1880),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8页。
(14)林乐知:《中西教会报弁言》,《中西教会报》1册,1896年2月。
(15)米怜:《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见汪家熔辑录《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16)花之安:《性海渊源·自序》,《万国公报》53册,1893年6月。
(17)[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8、71页。
(18)狄考文:《振兴学校论》,《万国公报》653卷,1881年8月27日。
(19)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万国公报》77册,1895年6月。启事曾在1895年5月25日《申报》刊出,前后共5次。1895年6月又刊在《万国公报》和《中国纪事》(Chinese Recorder),7月刊在《中西教会报》,另有英文广告。
(20)傅兰雅:《时新小说出案启》,《中西教会报》3册,1896年3月。
(21)长老会友谷山人:《易字通音以申教化说》,《中西教会报》16册,1892年5月。
(22)沙光亮:《醒教喻》,《中西教会报》35册,1896年12月。
(23)西沙光亮、华达贯吾:《除鸦片烟害论》,《中西教会报》35册,1893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