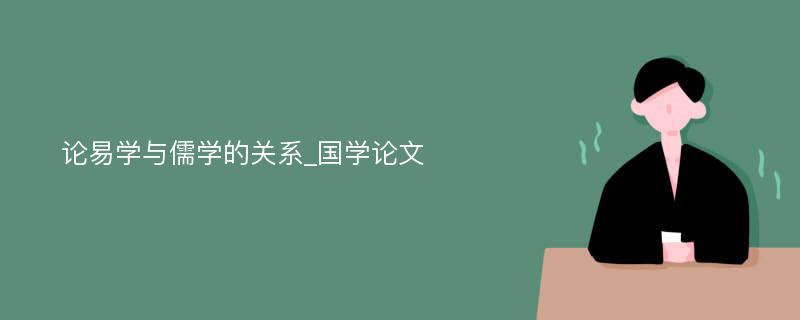
论易学与儒学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易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0)05—0117—06
《易》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庄子·天运篇》记孔子走访老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熟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庄子记事,往往荒诞不经。孔子是否访问过老子,从来就是一桩疑案,而孔子治六经出自庄子之口,同样不无可疑之处。纵览《论语》全文、孔子仅在两处提到《易》,一处是引《恒》卦九三爻辞立论,一处则是对自己学《易》太迟的追悔。孔子说:“加我数年(《史记》作“假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参照《史记》“孔子晚而喜《易》”的记载,说明孔子是人到暮年才注意易学的,因为错过了学习、研究易学的机会,才有“假我数年,五十而学《易》”的追悔和感叹。那么,儒学和易学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易学充实了儒学,完善了儒家的思想体系
儒学在先秦称显学。《韩非子·显学篇》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根据《韩非子》的记载,儒家尚孝,墨家尚俭,但都称道尧舜,而且都称自己是真尧舜。因为尧舜早在三千年之前,其事迹已无可考,且又是过时的故事,所以韩非称儒、墨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韩非把儒家的仁义说比作巫祝的祝词。韩非说: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韩非子·显学》)
韩非是法家,提倡法治,不讲仁义,也不讲民心背向,更不法先王,一切从是否有利于现实出发,言词不免有些偏激,但也说明先秦的儒家主要是从传说中的尧舜之话游说诸侯,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鼓吹效法先王。至于自己,并没有多少高深的理论,而且也不注重理论。根据儒家主要经典之一的《礼记·儒行》记载,当时的儒者们十分注意自己的仪容、志趣、作风、性格、气度、事业、责任以及交友、助人等方面,于理论则闭口未谈,于学习也仅只“儒有博学而不穷”一句。而于其他方面却阐述得深刻精当。如表明儒者志趣的“备豫”条说:“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儒者平时刻苦持敬,言信行果,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毫不吝啬自己的生命,一种十足的儒侠风度。
儒者们爱护他人,但也十分尊重自己。《儒行》的“刚毅”条说:“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儒者不仅是可杀而不可辱。就是自己有了过失,也只能“微辨”而不可当面数落,可见其自尊。
儒者的自尊不是单纯面子观念的表现,而是建立在自己严于自立的基础上的。《礼记·儒行》在“自立”条中说:“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人能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自然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得到社会承认,即使有些过失,应当“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据上所述,先秦儒家注重的是自己的修养、抱负,以及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而不注重理论的探讨。
说儒家不注重理论的探讨,并不排除他们的刻苦学习。《论语》的开篇就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接连阐述了学习中三种不同境界的快乐。孔子不仅提倡刻苦学习,而且提倡深入思考。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他不仅提倡思考,而且提倡考证。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同上)
孔子虽然提倡学习,但学习的内容只限于《诗》、《书》、《礼》、《乐》。《论语·述而》记载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自己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教育自己的儿子也只强调学《诗》,学《礼》,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见《论语·季氏》)。
孔子提倡学习,其目的在于通过学习以加强自己的修养。孔子把儒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能学以致用,不断加深自己修养的“君子儒”,一类是剽学某些词句而与自己思想无涉的“小人儒”(见《论语·雍也》)。
孔子教学生虽然也设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科(见《论语·先进》),但第一位的是修养,也就是德行,其他都是次要的。他公开要求自己的学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一生最为得意的学生是德行最好的颜回,他赞扬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在人不堪其忧的陋巷干什么呢?主要是进行自我修养的锻炼。孔子在回答哀公的提问时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同上)
孔子因为侧重思想修养,讲求实际,所以对宇宙生成、生来死去之类不加留意。《论语·先进》记载说:“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虽然如此,但晚年对《易》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司马迁作《史记》,于《孔子世家》篇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司马迁这段话虽然自相矛盾,但说孔子老而好《易》是确实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要》就明确记载道:“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自己也说:“加(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自己说的和上面引文的有关内容是完全吻合的。孔子其时已到暮年,才发现《易》的重要,所以感叹说:如果能够再给我一些时间,回到五十岁的年龄段,认真钻研易学,就可以没有大过了。(按司马迁的说法则是“于《易》则彬彬矣”)但既有“假我数年”的感叹,说明他识事太迟,动手太慢,于易学研究不深,因而追悔,成了终生憾事。如果像司马迁说的,孔子晚年喜《易》,并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诸篇,则已经彬彬然了,又何叹之有!所以,单凭孔子自己说的这段话,以及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分析,孔子绝不可能作《彖》、《系》等易传。《易传》是后儒托孔子所作。
孔子虽然没有亲自写过《易传》,自己也深以对易学研究不够为憾,但不等于完全没有注意。《论语·子路》章记载孔子的言论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周易·恒卦》九三爻辞,只是没有点出“易曰”罢了,这说明孔子已经开始引《易》立论。
孔子因为开了引《易》立论的先例,所以六经有了《易》的名目。但因为是晚来好《易》,对《易》缺乏深入的研究,而且也未像《诗》、《书》、《礼》一样将《易》列入教学的日课,所以在孔子时代《易》并未拉入儒家的理论体系,儒家的思想还只限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因此儒家在先秦也只是与墨家并列的“显学”。
儒学由先秦的显学一跃而成为汉代独尊的官方学术,一则得力于董仲舒的宣传和汉武帝的决断,二则得力于自身在理论上的充实和发展。理论充实、发展的主要标志就是《易传》(司马迁提到的“《彖》、《系》、《象》、《说卦》、《文言》诸篇”)的流传以及引《易》立论风气的兴起,而引《易》立论又是和《易传》的出现与流传分不开的,因为《易传》将卜筮之书的《易》提升到了统括一切的理论高度,在为后人开辟广阔思路的同时提供了权威性的论据,董仲舒对儒学的宣传就是借《易》立论的。董仲舒在最后一次策对中说: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这段话,除了掺入他自己一些天人合一的思想外,其他全来自《易传·系辞》。董仲舒也直接引《易》立论,他的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就是直接引《易》立论的。他说: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易传》的出现说明《易》学被拉入了儒学的思想范畴,从而大大充实和完善了儒家的思想理论,而引《易》立论风气的兴起,说明了儒家对《易》学思想运用的普及和深入。这种普及和深入在汉代达到了高潮,《汉书·艺文志》引《易》对诸家结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艺文志》在《书》九家后引《易传》总结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
于《礼》十三家后引《易传》总结说:“《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
于《乐》六家后引《易传》作结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
于小学十家后引《易传》作结说:“《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为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央》’。……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
于诸子百八十九家总括中引《易传》立论说:“《易》曰:‘天下同归而殊塗,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入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
儒家引《易》是从引经开始的,这点孔子已经作出了榜样。从整个发展历程来看,有着一个由经到传,由意义上引到全文征引的过程。上面引用《汉书》的大量材料,反映了后汉人的思想风气(因为《汉书》是后汉人的著作),其时已将《易传》与《易经》相提并论,直接称《易传》为《易》,这与西汉似有区别。西汉人引《易》多引《易经》原文,引《传》则多为意引,即使引用原文,一般不称出“《易》曰”字样,这在被称为“兼儒墨、合名法”的《淮南子》一书中反应得十分明显。以《淮南子·缪称训》为例,该篇引《易》立论共7 处,其中引《经》原文5处,引《传》原文1处,意引《易传》1处。 征引《易经》明显多于《易传》。如第153页(见《诸子集成》第7册《淮南子》,中华书局1954年版,下同)、为了说明上下一心的力量,引《周易·同人》卦辞说:“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第156页, 为了说明上下脱节,“动于上而不应于下”的危险,引《周易·乾卦》上九爻辞说:“故《易》曰:‘亢龙有悔。’”第157页, 为了说明“动而有益,则损随之”的事物发展向反面转化的道理,引《易传·序卦》说:“剥之不可远居也,故受之以复。”(与《序卦》原文“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略有出入)征引《易传》原文虽然仅此一处,但并未说明是经是传,都冠之以“易”,可知在西汉时期已有了经、传不分的苗头。但也有引《易传》不称“《易》曰”的, 如第165页说:“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易传·系辞》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这说明当时经、传不分仅是苗头,而并未成为风气。
当然,《淮南子》并非儒家经典,我们引用这些材料,旨在说明汉初人引《易》的习惯。只是《淮南子》既属杂家,其引《易》的步伐与正统儒家不一定同步。但正统儒家又有正统儒家的特点。以早于《淮南子》而又是儒家主要经典之一的《礼记》为例,其立论大量征引《诗》、《书》,《易》主要意引《易传》,而很少直接引用《易经》原文,似有把《易》拉入自己范围的意图。如《礼运》、《乐记》、《缁衣》诸篇,仅引《易经》原文1处,而明显意引《易传》5处。其中除《礼运》的大同思想是《易传·乾卦彖辞》的间接发挥,论史与《易传·系辞》大体相似外,其他或者将《易传》原文组合,或者按《易传》路数套用。如《乐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这些论“礼”的产生的文章,除了“君臣定矣”是《易传·系辞》“乾坤定矣”的套用,“小大殊矣”是“刚柔断矣”的套用、“则性命不同矣”是“吉凶生矣”的修改、“礼者天地之别也”是“变化见矣”的另立外,其他是《系辞》开篇第一段的原文照抄。《乐记》又紧接上文论“乐”的起源说:“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整段文章除了开头结尾根据需要略有增添,以及用词略有改动外,其骨干部分基本上是《系辞》“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的照录。至于套用《易传》路数,《礼运篇》关于“礼”的本源的说明就是一例。《礼运》说:“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其思想和文章结构全是套用《易传·系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段。这个例子还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礼记》的作者企图说明“礼”与“乐”的产生与宇宙生成同步,这与《易传》特别与《易传·系辞》的思想完全一致,《乐记》的几处例子亦是如此。这说明《礼记》产生的时代,大体也是《易传》形成的时代。而《易传》的形成,宣告了儒家理论系统化,特别是宇宙生成论的正式确立。
在《礼记》中还有虽不引用《经》、《传》原文,却通篇发挥易学思想的篇章,最见儒学与易学的关系,被朱熹编入《四书》的《大学》、《中庸》便是其例,我们后面将专门论述。
总之,从儒学的角度看,儒学利用了易学,借易学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后世儒家更是引《易》立论,体现了易学精华的《周易》成了儒家的首要径典。这个儒学与易学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儒家思想发展完善的过程。
二、儒学弘扬了易学、使卜筮之书的《周易》成了无所不包的理论巨著
易学之所以能成为易学,成为有着庞大体系乃至无所不包的学科,其能量并非它本身所固有,而是儒家注入、弘扬的结果。儒学在借易学充实发展自己理论的同时极大地扩展了易的内涵,乃至完全改变了它本身的面貌。
《周易》本是卜筮之书,而“易”更是一个难以解说的概念,《礼记·祭义》曰:“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地;善则称人,过则称已,教不伐,以尊贤也。”据此说法,则“易”是当年圣人为了尊天而设立的,用活人充当的偶像,但又是一种特殊的、有具体活动并具有无上权威的偶像。坐朝时“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公然与天子分庭抗礼。断事时天子即使有了明确的意见,也不敬自专,“必进断其志”,最后由“易”通过龟卜来决定。可知这里的“易”是当时官名,他的职责是通过龟卜最后决定一个国家、一个部落的行事,但既是“抱龟南面”,用的是龟卜,似又与后世成书的《易》关系不大。其实这“抱龟南面”的“易”就是后来的“太卜”,是人而不是书。《周礼·春官》云:太卜主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这里的“易”才是书。可知是先有“易”之事,而后有“易”之官,最后才有《易》之为书。但无论是事是官是书,都离不开占卜,它们的区别在于:就书而言,卦爻是《易》的全部,而事与官指的是用卦爻占卜的人和操作,甚至是没有卦爻的操作。我们今天所说的易学应该是以卦爻为基本内容、以文字为载体的《易》,而不是泛指一切占卜活动的“易”。
儒家对《易》的扩充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过程的,这个过程简单说来就是由《易》原本的单纯占卜到超出占卜的过程,也就是由原本的吉凶决断到事理分析的预言,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指导的过程。儒者们的充实是从事理分析开始的。这个过程从《左传》一书可以看出。《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有如下一段记载:
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
这是在典籍中最早出现的卦例。这段托名周史的著名解说肯定不是当时卜者的原话,而是后出儒者加工的结果。破解分两个部分,一是根据《观》卦六四爻辞(遇《观》之《否》是变卦,而《观》卦变《否》卦是因为《观》卦的第四爻由阴变阳。故第四爻称之变爻。凡是变卦,破解得以变爻爻辞为依据)。二是根据卦象,而主要是六四爻辞。周史根据“国”字,肯定孩子将来一定能继承厉公为一国之君的事业;根据“光”字,肯定孩子将来作国君不在自己的陈国,而在遥远的异国;根据“观”字又肯定作国君的不是孩子本身,而是他的子孙,因为观有旁观等待之义。
这段破解就解卦来说是十分高明的,推断大胆而有根据,解说有自己的逻辑,结论自然,有相当的说服力,比之单纯的吉凶可否的决断,已经大大提高,也决非一般“抱龟南面”的卜者所能做到的事。《左传》记载的卦例,卜卦解卦的都是“史”,而不是“卜”,说明占卜这个职业已由简单的卜疑向事理分析方面发展,儒者就在这个当儿开始向《易》注入新的内容,周史的解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周史的解析尽管深刻周到,但毕竟还是事理分析,只限于就卦解卦的预言,构不成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109年之后, 卜穆姜幽居东宫,其破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左传·襄公九年》记载: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这是一段大倒叙的文字,先写穆姜死于东宫,然后写当初被囚禁东宫卜卦的情况。穆姜是鲁襄公的母亲,在鲁国的“三桓”斗争中坚决支持叔孙侨如,几次逼着儿子襄公去掉季孙、孟孙氏,叔孙侨如也积极招拢晋国,以为外援。后来斗争失败,被囚禁东宫。就在押送她入东宫的那天,有人为她占了一卦,“遇《艮》之八”。《艮》卦卦体为艮下艮上。《艮》为山、山乃不动之物,今一山压着一山,联系她眼前囚禁的事实,定然是永无出头之日了。好心的史官怕穆姜伤心,按《周易》的成卦原则重新解释,说不是《艮》卦,而应该是《随》卦。《随》者随也,有跟着走的意思。于是史官安慰她说:“随,其出也,君必速出。”这穆姜倒有自知之明,她根据《随》卦卦辞“元、亨、利、贞,无咎”,作了上面的分析。穆姜解元、亨、利、贞并不是就某卦某爻某事解决,先给元、亨、利、贞确定界说,再加引伸归纳,可见“元、亨、利、贞”成了总括仁义礼智、嘉善贞和诸德的概念,而且是外延极大,乃至无法具体限定的概念,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因而也就形成了理论。后来《易传·文言》解释《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全文采用。这段话是否出自穆姜之口,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它开始了易学由具体卦爻破解到理论化的质的飞跃。《周易》也就因此升华了。
当然,《易》的全面理论化还是在《易传》产生之后。《易传》不仅将部分卦爻辞理论化,更重要的是将《易》的整个构成理论化,从而也使《易》的内涵也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唐人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中概括《易传》的观点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动。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因为有了《易传》的开拓,“易”的内涵变得无比深广,外延更是无比开阔,从“天地开辟”的宇宙形成,到“阴阳运行”的眼前现象,以及庶类群品的生生相续,全在其中,从而构成了易学的庞大体系,逐步上升为儒家六经之首。
前面提到,《庄子》第一次提到六经,以及后来《史记》第一次提到六艺,都把《易》排在倒数第二,但到了《汉书》情况大不一样。《汉书·艺文志》列儒五十三家,而以《易》十三家为首,而且把主要原于道家思想的《淮南子》中的《原道训》、《道应训》两篇也归入易学,成为十三家之一,并在六艺之后总括诸经大旨说: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
《汉书》不仅以《易》为六经之首,而且认定《易》是诸经之原。理由是:和解之《乐》,正言之《诗》,明体之《礼》,断事之《春秋》,都是相须而备,世有改变的,惟独《易》,探究的是宇宙之起源,人伦之根本,是与天地相终始而不可更易的原本之学。
这里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史记》与《汉书》在内容上于汉初及其以前之事多是重复记述的,而且出入不大,有些章节《汉书》甚至照抄,《史记》为何对《易》的地位的处理相去如此遥远?原因很简单?《史记》记述的是“罢黜百家”以前的情景,而《汉书》评论的是“罢黜百家”之后的盛况。
后汉、魏晋、南北朝诸史,无艺文记载。《隋书》于《经籍志》中列《易》诸经之首,收《易》69家,于“五行”收录易学有关书目百余种。并在编后详细论述了秦汉以后《周易》的传授情况及各家盛衰:
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汉初,传《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宽,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仇、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学。又有东郡京房,自云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尝立,后罢。后汉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并立,而传者甚众。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故有费氏之学,行于人间,而未得立,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
唐代扩大儒家经典,由汉代明五经扩而为九经,《旧唐书·经籍志》分诸经为12类,《易》为第一,收《易》78家。《新唐书·艺文志》分诸经为11类,第一亦为《易》类,收《易》76家。宋代立十三经,《宋史》分诸经为10类,第一为《易》类,收《易》213家, 多为宋人自己的著作,易学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至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分经部为十类,列《易》为第一, 收书167 种, 1760卷,上起子夏《易传》,下至清人翟均廉的《周易章句证异》,多为宋、清人著作。另外存目317种,2400卷。共计484种,3160卷,为经部之最。易学也就成了儒者用力最勤、学派最多、玩味不尽、精深博大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