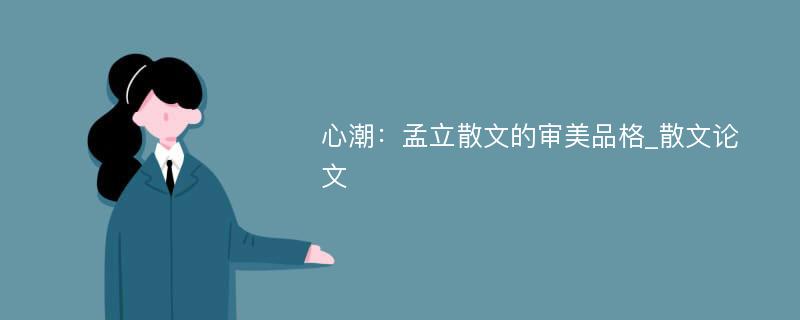
“心中的潮汐”——梦莉散文的审美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潮汐论文,品格论文,散文论文,心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泰籍华裔女作家梦莉是泰国商界颇有名气的实业家,也是一位执着于文学创作的散文作家。她在措理商务之余,援笔为文,先后发表了60多篇散文,出版了《烟雨更添一段愁》、《在月光下砌座小塔》等散文集,以独特的审美品格赢得了海内外华文文学界的普遍赞誉。
忧伤哀惋的创作基调
梦莉在《寒夜何迢迢》中写道:“在我一生中,究竟什么是欢乐?什么是幸福?这些字眼,对我,始终觉得是何等陌生!那么渺茫!你也许不会理解的。——欢乐的曙光不常见,而痛苦的寒潮,却不断地群涌而来。”作者这种痛切灵肉的感觉,不仅贯串于她的爱情散文之中,而且也浸润着她的忆旧散文。《小薇的童年》、《万事东流水》、《寸草心》、《逃离狼穴》、《片片晚霞点点帆》、《黄莲榨出来的汁是苦的》等作品,或以第一人称视角侃侃而述,或以全知视角痛陈其事,都从不同的侧面与角度展现了她童年的多蹇命运。
她家祖籍广东澄海,在当地是个望族。祖父母都受过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父亲本来在泰国经商,后因投入抗日斗争,携妻挈子回到祖国。当时年仅三岁的梦莉回到祖父母身边。尽管祖父因母亲出身低微而冷落于她,但小梦莉却由于聪明伶俐颇受祖父的疼爱。然而好景不长,祖父母相继去世,父亲又在抗战前线杳无音讯,恶伯恶姆却象豺狼般欺凌他们。在这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恶势力面前,她别无选择,只好“张开瘦弱的翅膀去袒护幼小的弟弟,和照顾患病的妈妈”。为此,她饱尝了人间最难忍辱的艰辛。她讨饭时,被施舍人“劈头盖脸地倒下来,溅了满头满脸”(《万事东流水》);全家逃难时,日本鬼子的机枪跟踪扫射,慌乱中她掉进河里,幸得一位叔叔解救才死里逃生(《小薇的童年》);八岁时为了“让妈与小弟,暂时能得温饱”,险些儿被人口骗子拐卖(《逃离狼穴》);九岁那年又为糊口去给一个富裕农民当童养媳(《黄莲榨出来的汁是苦的》)。这种种辛酸、痛苦的人生遭际,给她“幼小的心灵的每一根神经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紧张”,总是“感到受着一种恐惧心情的威胁”,使她“心灵上产生一种失落感,总觉到无法补偿”(《黄莲榨出来的汁是苦的》)。
幼时心灵的创伤本来就是难以平复的。及至长成后,又遭受爱的挫折,使她的人生又陷于失望、忧伤和苦痛之中。梦莉曾说:“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我,无论在心灵上,或在实际生活中,我的人生有着很大的反差。快乐与悲伤,幸运与倒霉,顺畅与窘迫,总是交替地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很早就体味到人世间的自私与势利,我浮沉在人生的长河中。可能由于我感受的痛苦既深且多”,因此,“当记忆和现实扭在一起的时候,我笔下倾注出来的还是苦多于乐”〔1〕。她的这种心绪,在《片片晚霞点点帆》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这篇寓意丰厚,情趣盎然的作品,写作者儿时在外婆家玩海弄沙,捡掇贝壳。突然潮水卷来,慌忙中丢了“小镬铲”。她哭哭啼啼地喊:“我的小镬铲不见了!”回答她的却是海浪滔滔。捡掇贝壳的欢乐与小镬铲失落的哀伤,从此就深深地铭刻在她的心中。因而她偏爱秋天,喜爱落叶,更“爱看变幻万千,令人捉摸不定的晚霞”。其实她并不是不爱春天,也不是不喜欢鲜花美境,只是由于她“有一段漫长苍凉萧瑟的情绪;也有一段变幻莫测如浮云的人生历程”(《片片晚霞点点帆》),这就使她“对人生体味的回嚼”,〔2〕不可避免地被涂上忧伤哀惋的色彩与情调。
其实,梦莉不惜笔墨展示忧伤哀惋的人生旅程,并非旨在“强烈地反射出怀有伤感人的心境和思想波动”,〔3〕也非钟情于“自艾自怜的心境”,而是冀图以此来“给人一种反弹的力量”。〔4〕正如司马攻所说:“你的散文不低沉,不颓放,反而是一些曾经此苦的人的一种慰藉。虽然你的文章大都是你心中的潮汐,但是,这些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都和整个社会有所关连的,你着笔在小处,而着眼却在大处”。〔5〕事实确也如此。 梦莉写抒情主人公与恋人被迫分离的爱情悲剧,在深层次上却反映了生活在异国他邦的华侨青年对祖国的向往和热爱;她摹写芝琳的悲惨人生,在于控诉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封建传统和“顽固的旧思想”的桎梏(《坎坷的命运》);她表现云云初到泰国饱尝“被排斥、蔑视和欺负”之苦,在于揭示“对当前的社会形态感到的万分失望,悲痛,和愤懑”(《泪眼问天天不语》);她叙述萍为了支付爸爸的医药费和弟妹的教育费而被迫给一个有“社会地位与财富”的人当了继室,在于展现生活在社会底层侨民的悲凉人生(《春梦了无痕》)。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并没有踟蹰于原生态生活的摹写,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审美范畴。根据作者的审美理想和艺术情趣,凭着自己独特而敏锐的人生感悟与体验,将聚光点投向了社会,投向了旧礼教和旧观念,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效应,唤起社会的注目,涤荡人们心灵中的污垢,使人们在悲凉的渲泄中获得富于理性的审美愉悦。恰如作者在《黄莲榨出来的汁是苦的》中所说:“黄莲本身是苦的,它榨出来的汁也是苦的。但是,苦水浇灌的心田,却是甜美芬芳的,心灵中却向往着能培养出那美妙的梦想与憧憬”。梦莉散文的悲剧美,正在于在特定的审美机制中培养出“美妙的梦想与憧憬”,也在于它以悲剧的力量策动了催人警省,启人深思,引人向善的艺术魅力。这种艺术力量并非全是题材本身所拥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是作者人格力量的熔铸和凝聚,因而才使作品获得了丰腴的血肉和鲜活的生命。
情景交融的诗意架构
本来,梦莉是在泰国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可是她“从小受家庭的熏陶,总算沾濡了具有五千年渊源的中华文化的一点基础”,而且她也一直认为,“生为中华儿女和她的子孙后代,热爱中华文化和它的习俗,这是应该的,也是天经地义的”(《乘风破浪一风帆》)。基于这种赤子之心,她在创作中很注意吸取和借鉴中华文化的精华。
中国散文以“敏于观察,富于感情”著称于世,〔6〕梦莉对此熟稔于心。她凭着自己的一双“艺术家的眼睛”,“以自己的生命本身,真确地来看自然人生的事象”,并将其“收进自己的体验的世界里去”。〔7〕她为文时常常“通过景物在人物心中的投影, 激起‘我’感情的心泉”,〔8〕在今昔交织,时空交错,物我交融中, 把主体与客体的情思交汇在一起,使作品呈现出物我相偕,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在《烟雨更添一段愁》一文中,抒情主人公由西湖霏霏的细雨,稀稀落落的桃花,触景生情,神思飞扬,“掀起了难以压抑的狂潮”:与恋人同赏桃花,吟诗嘻戏;月色朦胧秋夜,遥望星空,互诉衷肠;以及以茶代酒,向天盟誓,跪陈爱意等。然而这一切都已随物转星移而成为“激人情怀的历史”和“留在心里的阴影”!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时空交错的心理流程及感怀与忧伤相交织的情感状态,把“君泪盈,妾泪盈,罗结同心结未成”的沉痛的遗憾与绵绵的愁绪推向了极致。〔9〕
如果说《烟雨更添一段愁》通篇回避一个“愁”字,而令人伤怀的愁绪又统摄着全篇的话,那么《普陀之行思如潮》,虽然也在时空交错、物我交融中创造了诗意美,但却是在虚实反衬中揭示了抒情主人公“往事如烟心思如潮”的情绪。因为抒情主人公曾与恋人“携手到过”普陀山,而此次受一家公司之邀重游这佛教圣地时,睹物思情,感慨万千。这里对抒情主人公的思念之情并没有直接表述,而是通过虚幻的感觉予以抒发:
我依稀随着你的身影,踏步千步沙,登上佛顶上,穿过紫竹林,走看潮音洞,……
在幻觉上,我恍惚每走到什么地方,你的影子都跟到什么地方。陪同我的主人们离开我住房之后,我便独自到那古木参天,大海环抱的小天地里踟蹰,徘徊;希望找寻我们曾经踏过的一沙一石,坐过的一椅一凳,摸过的一花一木,说过的一言一语……这些实写的意象,是言在此而意在彼,“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10〕借助于“踏步”、“登上”、“穿过”、“走看”和“踏过”、“坐过”、“摸过”、“说过”等一系列“谓词”化实为虚,使“实”景(物)与“虚”情,自然地焊接为一体,将抒情主人公的澎湃心潮,缠绵情思,层次有致地抒写出来。这种情以物迁,物我相映,虚实相衬的艺术构思,既不“偏于枯瘠”,又不“流于轻俗”,可以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11〕
梦莉的散文善于运用景物的反衬或正衬,或以乐景写哀,或以哀景写哀,来映衬抒情主人公的情怀,从而构成相反相成或相辅相成的诗意境界。在《寒夜何迢迢》中,作者先是写春节即将来临,“日来的情绪,不但低沉,悲凉!甚至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与忧郁”之中。旋即笔锋骤转,描写了一段令人赏心悦目的景物:
椰树浅滩,天上飘来片片的白云,蔚蓝的天空,微微吹来的海风,阵阵向前掀涌的浪花,树上呢喃的鸟语,为我们而歌颂!……直至……夕阳……黄昏……。落霞映出似真如幻的蓬莱仙境!
这段景物描写似乎与抒情主人公的心绪极不相称。本来佳节将临,倍思亲人,苦闷忧郁的情绪已燃烧到顶点。可是作者并没有沿此渲染下去,而是转写湄南河边的美景,来反衬悲伤的心境,从而收到了“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乐”的艺术效果。〔12〕
在《小薇的童年》中,作者描写山村的“余晖照映的黄土路”,“落日彩霞笼罩的山头”,“伴着潺潺山间流水的曲径”,构成了令人陶醉的美景。可是饱受生活的沉重压力的小薇哪有心情去欣赏这美丽的山川呢?这种描写只能勾起更为凄凉悲惨的感触。在此篇中,还写到“一天夜晚,大地格外地黑漆漆,猛然一个闪电在窗口掠过,接着就是轰隆一声巨雷,似乎房屋里的墙壁都震动了,接着奔腾万马一般的豪雨倾泻而下”。这种电闪、雷鸣、雨啸、风吼,与小薇只身委缩在破祠堂里的处境,彼此呼应,互为衬托。前者以乐景写哀,后者以哀景写哀,均运用得当,艺术感染力昭然而现。
梦莉具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她在散文创作中或引用中国古典诗词名句,或演化诗词意境,或套用诗词句式,都恰切得体,运筹自如,有力地提高了语言的张力。这在海外华文作家中是极为少见的。
梦莉在写景状物或抒写情怀时,常常脱口而出般地引用中国古典诗词名句。如机场送别,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来衬托恋恋不舍的离情别绪(《恨君不似江楼月》);写离情,引用李清照《一剪梅》中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反映了抒情主人公思绪万端,无法抑制的情怀(《人在天涯》)等。作者还善于抓住某个意象进行生发联想。如,从眼前的湄南河吊桥,穿梭般飞驰的汽车灯光,联想到秦观《鹊仙桥》中的词句:“纤云弄巧,飞星传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在作者的意念中,眼前的吊桥犹如银河上的“鹊桥”,汽车灯光恍似闪烁的流星,从而借助于千古抒情绝唱把抒情主人公的怀念与忧思表现到命意超绝的境地(《在水之滨》)!
梦莉在散文中所营构的情景交融的意境,有着中国传统诗词般的韵味,通过景物描写,氛围的渲染来抒发哀婉凄恻的离情,令人读来淤悒不已。如《恨君不似江楼月》:
记得送你上机的那天,时近傍晚,天正稀稀落落地下着小雨,黑色的夜幕,已渐渐笼罩大地,冷风习习,这环境的凄凉更增加内心的怆恻……从家里到机场,四目相对,默默无言,临别之际说什么好呢?
这段描写与中国宋代词人柳永的《雨霖铃》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塞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
这里,送别时的典型环境和典型心理几乎别无二样,只是送别的场所是“机场”而不是“长亭”。对此我们无法怀疑梦莉袭用了《雨霖铃》的意境,因为她的散文一向是把感情的涓涓细流自然地从胸中溢出,从无生涩模仿或做作之处。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她十分熟稔中华民族独有的感情表达方式,这种巧合正是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认同和“灵犀互通”的结果。
梦莉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还体现在她常常在作品中化用中国古典诗词的名句或句式,来构成诗意盎然的况味。如:“江水与蓝天一色,白鹭与帆影齐飞,江风习习,艇上笑语盈盈,音乐飞扬”,是从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演化而来;“一夜春风来,万树梨花开”,是从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中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演化而来。这些化用的语句简赅生动,别具情趣,增强了抒情性,也加强了表现力。此外,她作品的题目更是注意创设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有的是直接引用,如“恨君不似江楼月”,是引自中国南宋诗人吕本中《采桑子》中的诗句;“聚时欢乐别时愁”、“片片晚霞点点帆”、“人道洛阳花似锦”、“云山远隔愁万缕”等都是套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句式,显得古朴典雅,诗意浓郁,别具风采。这对海外华文作家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泰国的华文文学是泰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居住泰国的华人”,“依然保留着华族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意识”,〔13〕因而使得泰国的华文文学既有与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又必然受到泰国的社会背景、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影响。从梦莉的散文来看,虽然也能从历史的时空和人类文化视角去揭示泰国社会的生存状态,但由于她特殊的人生际遇和从小受到较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她的作品常常流溢出深沉的怀念故土、故人的感情和较多的民族文化气韵。这在她的《客厅的转变》中得到情感淋漓的表现。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写她特别喜欢“那种古色古香,不静不喧的中国式厅堂陈设”;于是她在家里布置了一间中国摆设的客厅,以便在这里“独享我的‘古趣’”。待得孩子们陆续长大之后,就极力在这间客厅扩展自己的“势力”,陆续买了些泰式工艺品,还挂上了几幅泰国的景物的油画。可是在这间中西合璧的客厅里,“那套中式红木家具仍闪闪生辉,绚美隽永”,“以最神采的姿态展示在人们的眼前”,而且和泰国的摆设搭配在一起,“也显得十分融洽、协调”。她相信,中式家具的“静穆幽雅的造型”,会“永远赢得人们的重视和珍惜”的。这与其是在陈述中华文化远适他邦的适应性,莫如说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有独钟。或因如此她在创作时,尤其当她把自己的创作导向“心系祖国”的总主题时,更表现出她对炎黄文化的热烈追求与温馨的眷恋。由此,就不难理解梦莉吸收借鉴中国传统艺术的缘由了。
如诉如泣的话语方式
30年代以何其芳的《画梦录》为代表的“独语式”散文曾为散文创作带来新的气息。到40年代,张爱玲的“私语”式散文又赓续了这种以内心独白为主的渲叙性话语方式。继之,这种话语方式又为台港及海外华文作家所吸收,形成了独特的叙述景观。梦莉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形态的衣钵。她那些爱情散文选择了书信体的语境,在“我”对“你”的直接倾诉中表现了抒情主人公的见闻、联想及感受,而那些忆旧散文、记事散文,也在如诉如泣的语境中,或流畅自然地钩沉往日的记忆,或汩汩滔滔的渲泄感情的心泉,无不显示出别具一格的风采。
梦莉如诉如泣的话语方式交织着复杂而矛盾的美感倾向:一方面是对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气质的爱情的甜美回味,另方面是由于这种爱情未能绽开幸福的花朵而产生的失落感。回忆昔日的对月抒怀、挽臂而行的情景是美好而温馨的;甚至在抒情主人公与其恋人都已成家立业时,女性抒情主人公还时不时地把她的恋人作为自己的“精神伴侣”:“你是我心中幸福的泉源”,“你犹如一个避风的港湾,每当海风怒吼,海浪滔天,波谲云诡的时候,我就会渴念起那‘避风港’,这个给我安全与宁静的境地”(《心的碎片》)。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使抒情主人公感到慰藉、温暖和爱的力量。然而,这又是一种有情人不能结为眷属的悲剧,因之,她深深地体悟到,爱情“是甜蜜的痛苦,是温柔的折磨”(《心的碎片》)。这种矛盾的感情,只有在悲思的渲泄中才能获得特殊的精神愉悦。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说:“人感受美物,辄觉胸隐然痛,心怦然跃,背如冷水浇,眶有眼泪滋等种种反映。”这种悲剧性的美感特征,能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昂扬的生命力感”,〔14〕虽然梦莉笔下的美好爱情未能“兑现”,但却放射出作家审美理想的光照。她的爱情散文就是在这种甜蜜、痛苦、温柔、折磨的交织中来倾诉抒情主人公的心曲的。
梦莉的忆旧散文和叙事散文同样也交织着复杂矛盾的美感倾向。儿时家道中落后的痛苦遭遇,深深地铭刻于怀,成为抹不掉的情思;而从商后的事业有成,又使她对生活感到适意。可是,对美与丑的观照却始终萦绕于她的心怀。在梦莉的审美直觉中,不仅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眼光介入人生。她在《万事东流水》中所遣责的恶伯恶姆,在《泪眼问天天不语》中所诅咒的老板娘,以及《坎坷的命运》中的芝琳的“荒谬与专横”的母亲,《李伯走了》中小市民式的厨师锦莲和陈婶,都表现了作者对丑陋的心灵的体认与鞭笞。而她笔下的为祖国和人民的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姨妈、姨父和舅舅们(《临风落涕悼英灵》),处境悲惨的母亲(《寸草心》),忠厚善良的李伯(《李伯走了》),勤劳坚韧的阿贵婶(《寒花晚节香》)等,都是作为善和美的化身而予以讴歌的。这里,对美的激赏与对丑的贬抑构成了梦莉的情感交织着“快乐与悲伤,幸运与倒霉,顺畅与窘迫”的动因。她陶醉于对美的激赏,透视出她对生活中积极因素的肯定;而对丑的滞阻焦焚于怀,又表现了对美的缺憾和生活中悲哀的感慨。在《在月光下砌座小塔》中,她写到童年时代于中秋佳节,她象男孩子一样在家门口砌了座小砖塔,塔里放上柴草和盐,燃烧起来,“辟拍作响的声音从塔里传出,跟着便升起阵阵青蓝色的火焰,烧得通红的瓦片,使小塔显得更加明亮,更加美丽”。可是两三天后,“不知哪个男孩子恶作剧”,用几个大鞭炮把小塔给崩塌了。因此她感叹道:“天上月圆,而我心中却有几许残缺!”这种感叹是梦莉对人生独特的感悟与体验。她的作品正是在这种美好与残缺相矛盾又相统一中,把自身的感受推向审美化和情趣化的峰巅。
梦莉如诉如泣的话语方式常常采用心灵独白的切入方式来抒写她独特感性心理和敏锐的心理气质。由于她在感情上受到过损伤,也由于饱尝了变幻莫测如浮云的人生的辛酸,因而她营构的叙述语境,有着近似“神经质”般的敏锐感。她面对晚霞的瞬息万变,“顿时,心中的失落感油然而生”(《片片晚霞点点帆》),她面对霏霏细雨,顿觉“心情消沉”,“增添了无限的感触”(《烟雨更添一段愁》)。她这种切入方式,是通过物我的撞击而激起的心灵的振颤,来捕捉艺术的直觉。如在《云山远隔愁万缕》中写道:
黑暗围绕着我的周遭,已经由热闹回归了宁静!一种落寞与空虚的感觉,强烈地敲击我的心灵。我感到惘然,心里又仿佛失落了些什么?我的心,乱极了……我想你,想你,更想你……既往的情景,使我思绪如麻!你怎么样?怀念我吗?以前,我没有这个感觉,仿佛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存在,人们已遗弃了我,不再有人疼我,如今,我重新有了牵挂。
海啸象万马奔腾,浪潮一阵紧一阵,涌上来……。多少思念,离情与别绪!……象韩国的寒流,浸入心肺,直透心房,到达全身。我深深地颤栗起来,我好冷!好冷!恨不得你立刻出现在我的身边,把我紧紧地拥进你的怀里……
这段心灵独白反映了抒情主人公在孤独的境遇中的心理流程。在表述时,有些语无伦次,但正是由此透露出抒情主人公“神经质”般的心理活动。前一个层次写黑暗使之空虚、落寞、惘然,突出了抒情主人公对恋人的思念。后一个层次写海浪奔腾。既反映出身处其境的自然环境,又衬托出无法平静的心绪,以一个“冷”字呼应了前个层次的孤独、落寞。这种心灵独白,披露了抒情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反映了作者审美直觉的敏锐与细腻。作家正是在凝神观照中,“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居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从而达到了“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的往复回流”。〔15〕
在描写人物或事件时,她还将自己真挚的思想感情和偶然悟得的意趣,寓之于形象,诉之于朴实无华的文字,从而形成了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的话语方式。在《珍藏一个喜悦的拜见》中,梦莉在会见著名作家冰心时,写道:“我快步上前,紧紧地握住她老人家的手,她那双温柔的手也紧紧地握着我”。这种反复的描述,并非赘笔,它既表现了来访者对老作家的崇敬、仰慕、爱戴的感情,也反映了冰心老人的热情与喜悦。接着又写道:“我高兴了一阵之后,终于叫一声:“冰心老师,您好。”难得的拜见,使来访者喜悦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一阵之后才问好,又把作者激动、喜悦的感情进一步升华。即使是作者回泰国时,从香港买了只白色的玩具猫,也是从冰心喜爱的白猫而诱发爱屋及乌的仰慕之情的表现。作者正是借助于这些细节把她内心的喜悦和真诚的敬慕的感情付诸于笔端的。此外,在《在月光下砌座小塔》、《客厅的转变》、《在水之滨》等作品中,也都是把作家的艺术直觉,经过感情的过滤,于质朴中见真情的。
从审美期望上看,读者是渴望不断地获得新的审美感知的。梦莉的散文为读者提供了独具一格的审美品格和审美感知,从而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喜爱。勿庸讳言,她的散文所表现的思恋与纯情,虽然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篇章中出现,但使人觉得表述的内容有交叉和重复。槟榔的咀嚼以不超过限度为好。如此说并不意味着劝诱作者移宫换羽,改弦更辙,正如梦莉所说,“痛苦也是创作的泉源”,〔16〕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是无可非议的,只是希望能拓宽审美的领域,以便给读者更丰富更多彩的审美体认。
注释:
〔1〕〔2〕〔4〕〔16〕《在月光下砌座小塔·自序》。
〔3〕〔5〕司马攻:《烟雨更添一段愁·序》。
〔6〕余光中:《中西文学之比较》。
〔7〕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
〔8〕饶芃子:《烟雨更添一段愁·序》。
〔9〕林逋:《相思令》。
〔10〕语出《四虚序》,转引自范晞文:《对床夜语》。
〔11〕司空曙:《诗品》。
〔12〕王夫之:《姜斋诗话》。
〔13〕饶芃句子:《中泰华文文学比较》。
〔1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15〕朱光潜:《艺文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