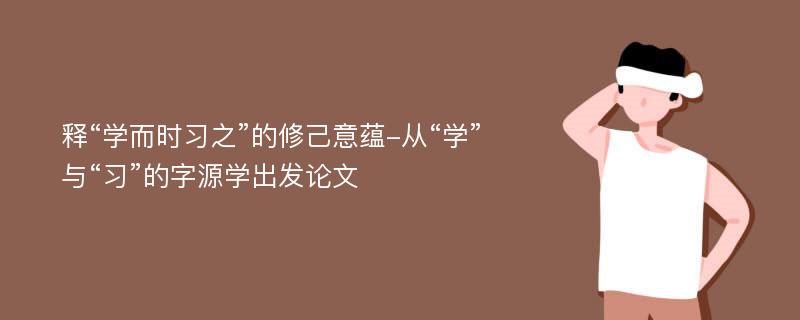
释“学而时习之”的修己意蕴
——从“学”与“习”的字源学出发
陈 兵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现代关于“学”“习”的诠译,把孔子的学问视作服务于实践的理论、知识,而非活生生的生命智慧,实则其思想是对三代文化诚敬存养践形之后的心得体会。从字源学出发,“学”“习”隐蔽的生存事实是:“学”是教和学的合一,不仅涵盖学、觉、效等现实性层面,还具有教学相长、一以贯之等具体特征;通过分析先民“习卜”和许慎“鸟数飞”的生存论意义,“习”蕴含习养、习与性成、修身等义,体现着修身养性和积习成俗的功能。具体观之,孔子学以修己,因礼乐之道自成生活习俗,在全幅生命活动中贯彻始终,从而垂教后世。
关键词: “学而时习之”;生命体证;字源学;礼乐生活;修己
《论语·学而》首章是古代圣贤下学上达,与天地交感合德,充实而有光辉的生命写照。它形象地指明了一条由博学笃行开辟广阔生活天地,从而修己自乐的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简约实惠,为常人所轻易学习和体悟,乃是一种大同于天下,内外如一又即地超拔的具象生活境界。王船山认为,“学而时习之”章讲明了圣人与天地同载同覆的上下贯通之道,并非名实不副的异端之学的权宜之辞。[1]因而要对此有贴切之阐释,须从“学”与“习”的字源学的生存论还原入手,以达到对孔子学术指归的生动把握。综观今人所做译释,超脱孔门师徒具体的为学体悟,于理论思辨方面多有发挥,虽颇能启人思考, 然细加体悟,总觉有所欠缺。笔者反复吟咏,借此抒发己意,以就教于方家。
其次,在小额诉讼与简易程序的关系上,“如果说简易程序是属概念,则小额诉讼是从属于简易程序的种概念,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12]小额诉讼与简易程序的关系可以用“俄罗斯套娃”来类比(赵刚教授语)。既然小额诉讼没有独立的程序,它仅仅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简单民事案件时的一种特殊情形,那么从逻辑上而言,小额诉讼的制度设计不应当背离简易程序应当遵循的原则和制度,简易程序实行两审终审,作为一种制度,小额诉讼也应当实行两审终审,立法规定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显然背离了简易程序的制度逻辑,构成对上位程序基本原则和制度的违反,具有合法性危机。
一、“学”“习”诠译方法反思
现代诸多《论语》的诠译版本,对“学”与“习”的意义及关系做了大量的解说。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如黎红雷先生认为,“学”“习”指学习和实践国家管理的君子学,《论语》即教育和培养国家管理者的学问。(1) 黎红雷先生搜罗了现代中外几种对“学而”章的训释,对比以后指出李泽厚以“理论/实践”释“学”“习”的观点比较好。黎先生的特别之处在于,突出孔子的“学”侧重待人接物的方面,是成德立教、治国齐家的君子之学。不仅表明实践哲学对孔子思想的某种诠释效力,也潜在地预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会通。 [2]这个论断表明了孔学精英主义的文化立场。不过,这种精英主义的文化观是深深扎根于平民立场的,在孔子看来,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民众,都仅仅是自我修养和管理的结果,二者只有自觉程度上的量的差别。由此可以引申得出一点:孔子的君子学归根究底是平民自修自为地成德立己的学问,包括权力在内的任何外在于人的力量,都不能对人的此种成长有所干涉甚至助益。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抽象地、一般地理解孔子的“学”,而忽略孔子作为下层社会的低贱士民刻苦自修的学术践履和脱俗化众的品格。成为国家管理者这个一般的目的,已经为后来孔子礼乐生命的彻透践履所超越、扬弃。因而,对“学”与“习”的准确理解、阐释,关系到《论语》思想价值的界定,也意味着对孔子及其门人生命活动的真切认识。
现代关于“学”与“习”的译释,明显朝着哲学思辨化的方向发展,不免流于空疏而缺乏生活的血肉、情趣。究其原因,在于以主客二分思维形成的儒学经典诠释理路,即把孔子的学问当成一种理智化的知识而非活生生的生命智慧,从而走上了撇开具体生活内容的纯思辨的诠释路子。反映在语言训释上,则是以哲学术语改写古汉语意涵的做法。按,学习一词从现代意义上理解,指的是人通过阅读、听讲、研究、实践获得知识或技能并效法其他对象。又按《辞源》,所谓实践是指实地履行;[3]465所谓练习是指熟悉谙习。[3]1331但在《辞海》中,所谓实践,除了履行之义外,还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感性的物质活动。[4]此处不拟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和传统意义上的“实践”进行细致的分疏,只谈两个重要的方面以简略指出二者的区别:第一,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马克思主义主张理性地批判而不诉诸于无原则地情感崇拜或贬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则注重诚敬的情感依恋以克制理性上的评判;第二,关于世界的认识,儒家认为日常人际交往的情意圆融,物质生产等其他一切因素都为这个道德情感的主题服务,马克思主义则突出了物质生产的公正、社会化对于世界和人的改头换面的主导意义。现在的问题是,今人对“学”“习”的诠释,到底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实践”一词,显得不够慎重。
回到孔子那里,“学”是广义的学、教的统一,温和地、绵密地继承古代文化典章,并立足于现实生活进行实际演练和阐发,而非一种单纯的知识性的学习累积活动。若把“学”作“效法”理解,则指学习者对古代圣贤所传会的生活、生产、生命智慧进行不折不扣的体证,以达到和古人生活天地、生命旨趣的严丝合缝,形成历史流传的一贯而下的连绵不断的整体。如安乐哲先生所批判的,“学”不是概念性的分析客观事实的求知活动,而是经验相传的直接知晓的过程。(2) 安乐哲的言外之意是,不能以西方主客二分论为背景建立的知识体系粗泛地分析探讨学的意义。他作为疏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西方学者,其深层次的考虑应该引起重视。 [5]孔子损益三代的礼乐文化,忠诚于和我们有着血肉联系的圣贤先哲,对其有着日积月累的深厚细致的体验,并非是纯粹思辨活动对客观事实的抽象把握。孔子的“学”强调的是“以诚敬存之而已”[6]16,要求对尧舜等古代仁人诚敬忠信,而怀疑、权衡只针对自身智能、修养的不完善,把学者个人现世生活的忧患和古代文化传统区别开来,既强调二者的有机联系又互不侵渎。因此孔子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自身生活游刃有余,再利用闲暇学习文化传统,成就人和传统互相助益的各得其宜的善事。个体在生活中立身正位才获得学习文化传统的资格,即出于对古代先贤的敬畏、感恩。所谓的人能弘道也即是此意。
3.法律活动的“后援团”。公职律师参与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工作,参与听证等事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出准确的处理意见,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合理性、科学性,减少行政执法的风险。
激活函数的函数值选择在闭区间[0, 1]之间,是因为这个神经元主要的任务是“做决策”;而对于一些更复杂的情况,我们要求神经元不仅能够进行决策,而且能够输出实数值。为此,我们会引入一个递归的线性函数:
归一化处理后,C1、C2、C3、C5的各权重值为:ω11=0.109,ω12=0.413,ω13=0.283,ω15=0.196.
近世殷墟甲骨重见天日,刻于其上的卜辞在古文字学家的考释下,展现了商周时期文字的意义原貌和先民的生活风貌。唐蘭、杨树达、裘锡圭等人根据甲骨卜辞中有关“习”字的占卜记录,并结合《易》《礼记》《周礼》《左传》等文献参证,认为“袭”“习”古通,具有因袭、重叠之意,但关于“习”之本义难有定论。[9]1855于省吾先生的看法是公允的。“习”之本义虽然湮没在历史深处,这一点不免令人惋惜。但值得庆幸的是,甲骨文语境中“习”字的重复、连续的引申意义被掘露出来。问题在于,如果只是从抽象的角度来把握这一引申义,那么它本身对商周先民的占卜活动的感性的直接的描摹意义,以及其具有的生存论上的深刻内涵就被忽略掉了。所以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把“习”字还原到先民具体的日常活动的情境中去。
第二天清晨,我们匆匆吃过饭,就攀上脚手架,按李大头的交待,分两片,一片王幸福带领,一片交给吴国栋。王幸福靠西,吴国栋靠东。李大头反复强调,要我们每个人占据好自己的位置,组长守好自己的区域,一组成员不能越界到另一组的区域去干。本组人占位顺序也不能颠倒。谁不遵守,扣谁工钱。
历史的本真不只在于宏大叙事的起承转合,还在于出入历史长河的个体对自身生命状态和价值的确认、归属。人自主地建构自身的生活天地,形成相较于历史洪流的稳定的生活世界,正所谓“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易经·系辞上》)。生活世界的自足和完满是通过修己来实现的,人的一切社会实践的承担以之为根基。孔子认为,即使贤圣如尧、舜,也是先通过以诚敬的情感充实挺立自身,逐步做到“修己以安人、安百姓”(《论语·阳货》)的。因此,安人、安百姓等社会实践的根基在于修己、立己。所谓修己,即在日用伦常琐细中做习养工夫,正性情好恶,平喜怒哀乐,富以其邻。也就是说,人首先是一个“生活者”(3) 岩佐茂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根基是活着的生活者的思想。生活者就是既要劳动、消费,也要享受闲暇的活着的人 。但是在孔子看来,维系着人的生存的根源性事实,是家庭日常生活的游刃有余,学习礼乐文化以充实生活闲暇,此即孔子所描述的“生活者”。 [8],修身安己然后获得介入社会生产和交往,参与改造世界的历史实践活动,具备一个实践者的资格。由此观之,《论语》中所提及的为邦、为政乃至如何做君子等问题,在孔子看来都可以归根为修己功夫。而修己必始于家庭孝悌品德的践行,自然推及乡邻民众,执敬、好学而近仁。孔子为何如此看重修己在个人的生命成德践履中的重要性呢?这似乎在提醒人们,与其认为儒学重视人的具体家庭生活是其核心特点,毋宁认为孔子率先敏锐地察觉到家庭生活的宽裕和学习以享受闲暇,对人生命塑造所具有的幽微不显的意义。
以孔子和宰予师徒二人就“三年之丧”的对话为例,孔子主张人对于礼乐文化的遵循,紧扣人自身情意的舒展绵延,成全人亲子之情爱的自然流露,尽管这样做会影响家庭、社会财富的正常积累。而宰我则注意到礼乐这种秩序性活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将礼乐制度作了均质化的理解,从而忽略了“三年之丧”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环节的深刻性和非通约性。宰我认为,三年之丧的时间太久以致延缓君子施行礼乐的速度,可见其用心之重仍是外在的利害,而不见孝子丧亲之哀的真切情意的根本性。丧礼的意义不在于其时间、形式,毋宁是人于丧亲之哀情的沉浸和对父母的无限眷恋,这是人居丧之礼自得于己的唯一生存形式。亲子之情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足以动摇此根本。为人做到仁,然后才能对礼乐传统有一个深切的认识。
《易经·系辞上》云“忧悔吝者存乎介”,“显诸仁,藏诸用”。所谓介者,指纤小微末。孔子的“学”与“习”,落实到日常琐细中,讲究以小见大,以平凡蕴神奇,折射为学者学问、修养的深浅。更深层次地看,在原始儒家那里,人的德性践履彻底地贯注到日常待人接物的细枝末节。孔门中好学的代表人物颜回,物质生活极度简约,却丝毫不影响他好学的自得之乐。生命的闲暇时光专注于学问,以此作为生命价值的根源,而对劳动、消费等其他生命活动形成涵摄,是孔子、颜回对人之本身生存最独特的探索。由此启示我们,“学而时习之”的阐释要揭示出:后世两千多年儒门子弟孜孜不倦“学”以开辟的其乐陶陶的修己安人的生命境界。
因此,在把“习”做哲学上的“实践”理解之前,有必要考察一下在孔子的生活思想世界中“学”与“习”的本真含义。以下,笔者尝试通过两方面的努力来揭示“学”与“习”的意义:一方面从字源学上,对“学”与“习”进行生存还原,揭示它们隐蔽的生存事实,获得其基本的意义脉络。在文字资料上以甲骨文和金文为准(更接近孔子时代的文字意义面貌)。这是因为当时的文化物质载体有青铜器、陶器以及玉器、石刻等,孔子于春秋末期,上述实物证据应是其喜闻乐见的学习资料。(4) 《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太庙为社稷彝器放置的场所,是供奉周公的宗庙。周代的礼乐彝器相当一部分保存在鲁国,悉数陈列在太庙中。孔子入太庙询问了解礼乐的相关事宜,必会参之彝器铭文。 另一方面则从历史学的视角,审查孔子及其门人的具体生命活动的情境,发现孔子“学”“习”的具体内容及主要特征。值得申明的是,只有基于孔子具体的生命活动情境的考察,前述两个方面的展开才是有意义的,因而也才是可能的。概言之,“学而时习之”包蕴直接而丰满的现实性,即孔子及其门人修习礼乐自得自足的生活风气。
二、“学”与“习”的字源学考察
前面已经指出,在主客二分思维宰制下的儒学经典诠释,遮蔽了儒学作为整全生命存在的本真面貌。从字源学上看,汉字作为抽象的意象,实际上隐含着人具体而微的生存事实。厕身其中的人的行为举止成了人之生存的理想范型,从而概括、规定了意象的内在结构,我们对汉字意涵的把握则在于对意象内在结构的分析。具体到字句的诠译,窃以为只有基于生命活动切实的体证领会,才会避免今人诠译之弊病,觉悟“学”“习”之真意。
以“鸟数飞也”释“习”,虽误认“习”字上半部为羽,或许包含许慎本人对“习”之更深远的洞察。鸟之练习飞翔,是其进入群类集团生存的“入世礼”,其必经过此一番刻骨铭心之积累锻炼才能在鸟类世界中立身。飞翔作为鸟类根本的生存方式,是其从稚嫩向成熟的生命转机的关键,也是鸟的类本质的具体展现而须臾不离其身。按“鸟数飞也”而自“在”于天空,可高升入云,也可下栖于地。这一生物意象在儒家看来具有深沉的、可比拟于人的生存论意蕴。第一,以“鸟数飞也”喻指的人之所“习”,意味人自身生命觉悟的提升,不断达到对“天”的亲近和契入,在天地之中自由自在地遨游,如燕雀、鸿鹄和鲲鹏。第二,由鸟飞翔而有它对生存环境进行感知和选择的能力,联想到人对自己所处时局、时势的敏感觉察,并由之引申出人择善而处、谨守本分和通达权变的德性自觉。正如:“《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大学》)又:“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论语·乡党》)
再论对“习”的训释。在卜辞语境中,“习”具有以身体为处所动态地营建日常生活的意义。先对业已形成的“习”字的训诂意义进行清理,以待有新发现。考察《说文解字》“习”字“鸟数飞也”的说解,“乃战国时期习之后起义”。[9]1853《论语》也成书于战国时期,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孔子所言说的“习”是否仅此而已?对此,笔者溯至甲骨文中以探“习”之奥义,揭开“习”字的本来面目。
可见,对“学而时习之”的释义就不是追求超绝于生命生活之上的抽象真理,而是探寻文本字句所隐蔽的孔子及其门人“人之为人”的亲情性的“生活世界”。诠释首重言说者对文本享有绝对“关照”的地位。孔子说“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7]46,又说:“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易经·系辞上》)可见孔子的言说是毕恭毕敬地生命践履所充实的思想,意味着须将其思想看成学、思、行相融的整体。因此,有必要将“学”“习”还原到孔门师徒的生活世界中,根据它们具体的表征来实现对“学”与“习”含义的贴切把握。
根据殷墟卜辞,“习”关涉古人日常的占卜事务。古文字学家认为:“‘习卜’仅仅是具体的占卜手段,在不同时间上对同一事情进行因袭占卜,用以达到神人之间交流的目的。……甲骨文‘习卜’强调占卜事情前后的因袭关系,是不同时间上对同一事情进行若干回合的占卜”[9]1854。区别于古文字学家的观点,我们认为“习卜”这种祭祀性的通神活动具有生存意义上的形而上意味。这种异时异地对同一事物的重复的连续一贯状态,抽象为人的日常生命活动的一贯性,表现为时空序列上过去、将来和现在的连续性。古人的日常生存被占卜活动填充和统摄,占卜就不只是先民进行人神交流的手段,还是人的生存绽开的仪式和节奏。人们通过占卜介入到“一个世界”的时空整体中,连续体知时间、宇宙、生命的奥秘。占卜仪式中埋藏着一种深层意蕴:“习”喻指人在时空中前后因袭的生命状态,是具有时空性的人的连贯如一的生存绵延。所以,“习卜”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对占卜仪式的无效的、机械的重复,更要深刻地看到先民在这种重复和因袭中所日益操守的宗教虔诚,甚至逐渐觉醒的心性和对自身神秘莫测的命运的掌控需求。它意味着古人的生活习俗,对商周人的心性起到了磨砺和扶助的作用,尽管它表面上是迷信、非理性的。古人习卜活动对我们理解“习”之奥义极具启发性。
先从“学”的生存事实还原入手。在《甲骨文诂林》中,文字学家们认为学与教古字相同,教人者谓之斆,受教者亦称为斆。[9]3261卜辞语境中的“学”,包含现实生命体证的两个层面:一为学,是专指对礼乐教化的领悟接受;一为教,则是指君王晓谕、教令氓民的意思,所以许慎《说文解字》解为“上所施下所效也”。古“学”字本身的意域深广,反映出人们生活践履的通达彻透。从形式上来看,它以教人者/受教者为生存结构。“学”内在指向人性的自觉悟,又面向大众世界。它始终围绕具体的人和事物展开对话,并在对话中营建互相启发促进的生命共同体,并向整个历史传统开放着。人因学而觉悟提升自我,又能教育感化他人。后世以觉训学和以效训学,[10]其实都是在不同侧面强调了生活者在学的场景里趋于圣贤的某一侧面。觉意涵丰厚曲折,体现凡夫俗子在施教者/受教者、礼乐文化/生活者的生存结构中自我挺立,实现心灵的觉醒。“‘觉’是发自内在心性的道德情感,也意指心的认知状态。”[11]凡夫学而觉之,觉而教之,亦学亦教,成己又成物。效则注重生活上自觉亲近贤哲,意味着生命的契合交感。要之,学是自我主宰的涵盖知识性认识和才能锻炼的完满的德性活动,具有纵向上的自觉性与横向上的合群性相统一的品质。
鸟数飞所摹状的人的生存样态,与“习卜”所揭示的古人的生存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揭示人类在某种生命活动中日常重复地躬行和谙熟,不断修身修己的生命积累。但不得不注意它们相异之处所暗示的古人生活方式和心灵世界的转变。如果占卜所刻画的“习”还只是外求于他力(以巫术与鬼神等超自然的力量相沟通),“鸟数飞”所重新规定的“习”之意象则意味着人自身力量的成熟。古人的日常生活的重心已经从巫术的、迷信的活动转移到对自身生存本领的掌握上来,人开始尝试凭借自己内在的力量挺立于生活世界。占卜活动积淀在人身上的宗教情感,以更具有人文气息的礼乐生活新范型,落实在周公、孔子及以后儒家学者的日常生活当中。总的来说,从“习”字的语义流变,可以看出其强调人的生活方式的因袭承继,讲究历史文化、生命证验的连续性,但不忽略人在这种连续性中精神世界的中立不倚和不断提升。“习”字最终落实到人的修身,弥漫于人日常的生活劳作中,对人的心性有生发、移易作用。正所谓“习也者,有以习其性也”[12]136。这一点在下面结合孔子及门人具体的生活图景,将有更详尽的论述和证明。
专属于“学而时习之”的修身活动具体指什么?这种人生活动就是天下百姓时刻依循的规范,贯穿于个体生命活动的始终。也就是时刻不离其身的礼乐之道,构成了现实的天下所有为学之人的生活习惯、习俗。休谟对习惯之于心灵的意义有着透辟的论述,其意义有三个扼要的方面:一是习惯和重复在损益人的情感、转化苦乐的主观体验方面有重大效果;二是习惯使行为完成和对任何对象的想象变得顺利无阻;三是形成人对熟悉行为或对象的某种强弱变化的倾向。[13]孔子及其门人弟子由学习形成的生活习惯,创生了普遍的士君子的生活格调,成了古今士人团体的身份标识。他们待人接物上仁爱亲和,“动容周旋中礼”[6]577,日常生活简约安和而不失锻炼。“《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易经·履卦》)以礼乐之道完成对周遭生活世界的迅速而有质量的应对,供给了生活世界的基本秩序的建构资源,是个体挺立存身的贞定吉祥之道。
三、“学”“习”自成礼乐生活
从“学”与“习”交融的生活整体看,“学”主虚心求教圣贤,互相启发而温柔敦化;“习”则就修身养性而言,意实为习养、习与性成、修身易俗。“学”打通了下学而上达的生命上进的通道,而“习”则指示人们在天、地、人三才之间自由出入,在修身处事中通晓天道(天命)。有学而无习,必空疏而不能服众;有习而无学,则流于习俗而不知所宗。以所“学”统贯日常之所“习”,不论得君行道还是化民易俗,要之落实在修己为根本的日常礼乐生活世界中,须以礼乐生活的修养积累为前提,待其自身人格的充实、成熟才有可能。
《论语·乡党》中记录有孔子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神态样貌,生动地刻画了他高贵典雅、从容不迫的人格气度。夫子在日用伦常中所展露的威仪,无可置疑地传达着礼乐之道的穿透力、规范性和感化力。全身心致力于生活细节上的琢磨,个体关于时间经验知觉的瞬间体悟渐至通透,世俗化的人类时间便和永恒历史之流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切点”,个人生命轨迹契合宇宙整体生生不息的节律。后世《史记·孔子世家》中部分地节录了相关描写,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学家,司马迁已经透过具体的时空感受到孔子礼乐化的人生所蕴涵的生命力。它们不是机械的摹写,而是人类心灵的永不磨灭的图象,亦是生气磅礴的人之体势。历史地看,孔子日常生活中所展现的气质风貌,是见之于肢体、悬之于天下的人之为人的典范。他是礼乐精神现实化的载体。在他看来,个人对于历史文化要姿态谦卑,圣哲先贤们的传授不以当世的实践(遇与不遇)所转移,更不为任何其他完备的理论、学说所通约。《诗》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7]46又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7]47他不务于空言,而追求思想与生命、言语与行动的统一,塑造垂教万世的健全人格。
面对被告咄咄逼人的态势,海力和龙斌脸色气得发青,竹韵的脸也涨红了,接着由红转青,手里捏着那份证据,快要捏出水来。最后,竹韵狠狠地咬了咬牙,高高地举起了手说:“审判长,审判员,原告竹韵请求发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而时习之”的诠释就落实到孔子日常举止比于礼乐的修己意蕴,现实而深切地揭示孔门学术作为人之为人的经典生活范式。至此,《史记·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作为孔子及其门人的日常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就供给我们诠释“学而时习之”的具体又现实的生命材料。
以《史记·孔子世家》观之,至少可以从以下这4个方面对“学”“习”作个综合的梳理。其一,孔子转化王公贵族之教、学为乡野士民的启发式教、学,礼乐之学习变得社会化,形成师生问学的新型社会交往关系,开启影响深远的学术之风气。其二,礼乐之“习”,讲究平日刻苦积累以至于处事从容不迫,所以有春风时雨之效,净化生活世界的同时安顿人的心性。其三,夫子会通三代之礼,其“学”无所不包而其“习”则因袭变化。以礼乐文化传统塑造成熟的人格“美玉”,又以此人格渗透实事践履,在实事践履中反促其精炼、纯粹。因此“学、习”使孔子(为学者)的生活世界富有天下,贤、圣之德师生传承不绝。其四,从会通道、艺的角度看,孔子与达巷党人的对话证明,他对射、御等六艺的体悟明显具有形上意味。“故六官以为辔,司会均入以为軜,故御四马,执立辔,御天地与人与事者,有六政。”[14]六艺之御实则从技术性的驾车活动上升到天地人三才归一的治理天下的艺术,非有精微深切的修己功夫不可。要之,孔子的“学”“习”既有道与艺融通涵摄,又通过习成一贯落实到日常生活的洒扫应对,从而伸展到天下民众及诸侯公卿的“生活世界”。
《孔子家语》中还存有孔子因礼乐之道化民成俗、亲人安乐的丰满自足的情境。首先,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时,以改易过的礼乐制度把民众的社会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制为养生送死之节”[15]2。不深察民情,则不能端正人的好恶使各尽其分;不娴熟礼乐,则不会节用爱人进至于天人共乐之境。实际上暗示着孔子深厚的修己以安天下的学识。其次,鲁哀公问儒行,孔子则从容貌、备预、操守等方面对儒者的修为的全副品级进行了细致的分辨和界定,其判断标准则是儒者依据礼乐之道由内而外的涵养的浅深厚薄。[15]38日常的容貌颜色,人所习见而不以为然。但对于儒者修身立德来看,愈是细枝末节,愈能展现其内在的觉悟之深浅。不深潜于动静几微的瞬息之化,又怎会将人的德性修养着落于举手投足之间?再次,鲁有俭啬之人以瓦鬲煮美味进献孔子,孔子如受大牢之馈而不以为陋器、薄膳。夫子的喜悦之处在于由美食而起浓厚的思亲之情。[15]76可见,器物的意义是人的仁爱德行所赋予,而不是简单地由用途和形式所固定。夫子遵循礼的规范而不悖人情物理,不囿常法,不滞于物。
再如孔子论述乐教,“行中规,旋中矩,銮和中《采荠》,客出以《雍》,彻以《振羽》。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于礼焉,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15]319。人的性情需要日常艺术生活的陶冶,好的艺术享受能使人沉醉在尽善尽美的宇宙怀抱之中,流连复归于本性之善。乐在人的日常交往生活中,可以“示情”,凭借钟磬丝竹的律动而中心之情意油然而作、沛然而兴、戛然而止,手舞足蹈而心身舒畅;也可以“示德”,让宾客在恢弘乐章的启发中想见先祖发奋图强的生活图景;还可以“示事”,同样是以艺术的方式激励众人的奋作之志。因此,“学”“习”不是孤立片面的,而是教、学相长,直面具体的生活。也不是僵死、断裂的,而是文、质互摄,道、艺融通。
孔子的“学”“习”讲究人就日常琐细的操持上安顿自己,通过日积月累的文化积淀,人能够从中洞见到整个天地万物运行的自由自为的盎然生意。“学”“习”着的人不断上达而无限接近于天人合一的境界,他的一切举动都成为自然而然的德性流露,能长养人、事物的性命。由于礼乐之道本于天道变化,而非人的理性造作,所以由礼乐之道的践履人能超凡入圣形成对天道的墨识心通,从而行无言之教,即“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乡党》)孔子已经看到人生在世,所有的向圣人之言、礼乐之道的学习体证最终可以回归到人对天道的效法,也只有道德性的天命才是每个人的最终的归宿,人亦应该唯天命是从,而不用屈从于任何外在的法则、力量。当然,也没有人能比道德性的法则之天更有资格去教育人和启发人,每个人不过依礼乐修己自成而已。
礼、乐在孔子身上不仅具有生动活泼的生活形式,还被其认为是人生之常道,本诸天道而惠及天下黎民。“丘闻之,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焉;非礼则无以辩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15]48因此,所谓的“学而时习之”,就不仅是人们所理解的对六艺的熟练掌握抑或今人认为的将所学的道理作用于实践以取得成效,而还具有注重家庭、社会伦常生活修养,承继先辈风土人情,习养身心以体察天道的意义。孔子的言传身教,向着所有学者乃至整个历史开放,于亘古星河中营造了一个好学自足的礼乐生活世界。
干部教育培训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工程,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干部教育提供了新的平台。《2018-2022 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指出要统筹整合网络培训资源,建设兼容、开放、共享、规范的全国干部网络培训体系。自2012 年中国干部网络学院开通,到十九大以来干部网络教育步入新时代,干部网络教育以其能够跨越时空局限的优势已经成为干部教育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孔子“学而时习之”所绽现的是修己自足的礼乐生命之道,凭借的是“学”“习”一贯的精神。他和弟子们以礼乐之道修养自身,在礼崩乐坏之际塑造、巩固了民众的生活风俗。正所谓“闻道反下,下交者也。闻道反己,修身者也。……下交得众近从政,修身近至仁”[12]139。结合孔子言说的时代背景,他的所学所习之于历史传统是劳身用情的。实际上,孔子的“学”“习”,教导人们乐于关注日常的生命存在,实现自己生命节奏的主宰,以礼乐传统浸润个体生活。这种“学”“习”,有着鉴往知来、生生不息的品质,实现了学以致用和学以修身的历史的统一。孔子一面是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因袭、积习,另一面如涓涓细流般除旧布新,以深切明白的行事公之于世。“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此即“学而时习之”以礼乐修己的生命意蕴。
[参考文献]
[1]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4.
[2] 黎红雷.孔子“君子学”的三种境界:《论语》首章集译[J].孔子研究,2014(3):4-10.
[3]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Z].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4]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Z].6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2058.
[5] 安乐哲,等.孔子哲学思微[M].蒋弋为,李志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27.
[6] 程颐,程颢.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7] 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8] 岩佐茂.马克思的“生活者”思想[J].国外理论动态,2014(7):49-57.
[9]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0] 赵清文.自我超越的“学为君子”之道:《论语》“学而时习之”章析义[J].孔子研究,2014(3):99-105.
[11] 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M].增订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75.
[12]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M].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3] 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60.
[14]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146-147.
[15] 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M].济南:齐鲁书社,2013.
The Implication of Self -cultivation of “Learn and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the Etymological Implication of “Learn ”and “Practice ”
Chen Bi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China )
Abstract : Interpretations of “xue (learning)”and “xi”(practice)in modern times usually take the knowledge in Confucian’s term as the theory and knowledge serving practice, rather than the life wisdom.Actually, Confucius’thought is the fruit of his experience and meditation on the culture of three generation with respect,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Etymologically, life wisdom in “xue”and “xi”tells that “xue”is the unit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which not only covers the practical aspects of learning, perceiving and imitating, but has features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mutually helpful in learning”, “a principle that is always applicable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Moreover, the existential significance implied in our ancestors’learning divining and Xu Shen’teaching of “a little bird keeps practicing flying”also indicates that “xi”has connotations of cultivating and shaping one’s habit, personality and body building, in other word, it functions in self-cultivation by forming habit through practices.Specifically speaking, Confucius learnt to cultivate himself, forming his habit of behavior by learning principles of rites and music which was practiced throughout his life, and became highly influential on the future generations.
Key words : “learn and practice”; prooving by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etymology; life equipped with rites and music; self-cultivation
中图分类号: H1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970( 2019) 12-0085-07
收稿日期: 2019-09-30
作者简介 :陈兵(1992—),男,陕西澄城人,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焦丽君]
标签:"论文; 学而时习之"论文; 生命体证论文; 字源学论文; 礼乐生活论文; 修己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