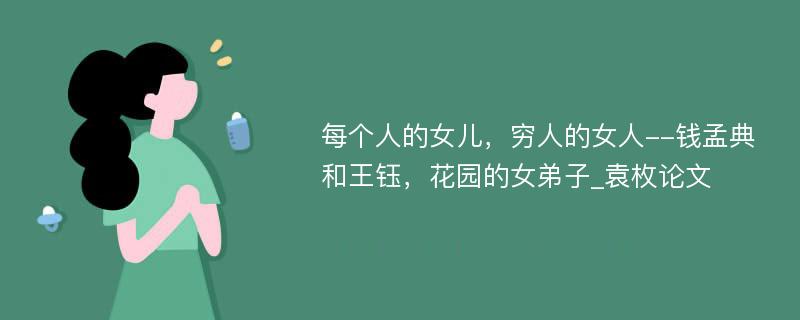
大家之女与贫者之妇①——随园女弟子钱孟钿与汪玉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弟子论文,之女论文,汪玉论文,随园女论文,钱孟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园女弟子四十来人,基本上都出身于官宦人家或书香门第,并嫁给步入仕途的文士(未入仕途的亦是秀才),多属于社会的中等阶层。但其中亦不乏大家之女与贫者之妇,分别属于社会的上层与社会的底层。尽管二者社会地位有天渊之别,但又同为随园女弟子,由此可见袁枚确实“佛法门墙真广大”(王梦楼语),有教无类。大家之女要推钱孟钿,贫者之妇则为汪玉轸。由于经济地位、家学渊源、文化教育与生活遭际的不同,亦决定了二人创作题材、诗歌体裁以及艺术风格的方面的差异,从而显示出作为性灵派之“偏师”的随园女弟子诗歌创作的多样性。因此,把钱孟钿与汪玉轸放在一篇文章里探讨对照,还是有其意义的。
一、大家之女钱孟钿
钱孟钿字冠之,号浣青,江苏武进人,生于乾隆四年(1739),卒于嘉庆十一年(1806),春秋六十八。其父钱维城字茶山,号稼轩,谥文敏,以诗画名,乾隆十年(1745)状元,官至刑部尚书。浣青是名符其实的大家之女。其夫崔龙见进士出身,曾任巡道等职,亦负才名,故袁枚题浣青夫人诗集有“嫁得才人苏伯玉”之句。(《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五引)无论婚前还是婚后,浣青家境均甚佳。吴文溥《南野堂笔记》记其“幼读书,涉览不忘,尚书为授《史记》、《通鉴记事本末》,遂能淹通故事;又授以《香山诗》一编,曰:此殊不难。试为之,清言霏霏,如写露珠,冥搜悬解,已足方驾元和也”。浣青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具有史学与诗学的根底。这是幼年贫困的汪玉轸所无法比拟的。浣青因居京师,故无缘参加西湖女弟子诗会,但会后曾题诗赞袁枚“玉局才华世所稀”,并抱憾自己“春风远隔苍山外,问字无因到绛帐”。(《续同人集·闺秀类》)浣青父与袁枚有同年之谊,她与袁枚关系亦自不疏。乾降庚申五年(1740)袁枚乘舟北上,稼轩南归,见其手抱幼女,才周岁,即浣青也。四十八年后袁枚在杭州见到浣青夫人,犹谈及此事。(见《随园诗话》卷五)袁枚于《随园诗话》中选录浣青佳作多首,并有《题浣青夫人诗册》诗五首,赞其“绝妙金闺咏絮才,一生诗骨是花栽”,“天为佳人常破例,清才浓福两无妨”。显然,袁枚对浣青其人其诗都颇欣赏。顾远芗《随园诗说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将之列为随园女弟子是理所当然的。
浣青才高而好学,尤爱读随园诗。袁枚尝记云:“严侍读从长安(按:指代北京)归,(浣青)夫人厚赠之。严问:至江南,带何物奉酬?曰:无他求,只望寄袁太史诗集一部。……有《浣青集》行世。其号浣青者,欲兼浣花、青莲而一之也。”(《随园诗话》卷五)由其号看,目标对准杜甫、李白,志向甚高,亦颇自信,有大丈夫气概,确实,“风裁不似女儿家”(《题浣青夫人诗册》)。另外,浣青“性至孝,尝剪臂肉疗尚书疾,创几殆,幸而获全”(《南野堂笔记》)。此事亦可见其性格之坚强。赵怀玉《崔恭人钱氏权厝志》(见《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五)还记其随夫驻守顺庆、荆州时,分别有“山东啯匪”与“白莲贼”(按:此乃对农民义军之污蔑,自不足为训。)袭郡城,而崔氏都有公务外出,情况紧急,但浣青夫人竟指挥若定,智却来犯者,真乃“临危不乱,动合机宜,无论巾帼之所难能,即士大夫当之,或不敢自信”。浣青胆识能力之过人,反映其性格中阳刚的一面。
“钱孟钿夫人刊有《浣青诗钞》八卷、续一卷,传本已少”(金武祥《粟香五笔》)。今《国朝闺阁诗钞》(道光二十四年刻本)有《浣青诗草》一卷十三首,《国朝闺秀正始集》(道光十一年红香馆刊本)存诗九首,其中《汉通天台铜人歌》互见,《清诗纪事·列女卷》从笔记、诗话中辑出三首,《春雪》亦互见,凡二十三首。本文即据所见诗探讨浣青创作的特点。
浣青自幼读史,“淹通故事”,具有一定史识,又曾赴秦、蜀之地,亲临古迹,颇多怀古咏史之什。这些诗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判,并寄寓个人性情,对于女诗人来说是颇为不易的。随园第一女弟子席佩兰亦不乏怀古咏史之作,但多用近体;浣青则多用古体。袁枚说:“闺秀少工七古者,近惟浣青、碧梧两夫人耳。”(《随园诗话》卷十)浣青长于古体与其学力及性格中之阳刚一面密切相联。这点不可忽视。其怀古名篇有五古《始皇冢》、七古《汉通天台铜人歌》等,分别咏秦始皇、汉武帝。秦皇汉武其功过,后人代有评论,或褒或贬,角度不一。袁枚亦有《秦始皇陵》、《和葑亭舍人司马相如诗》,对“千古一帝”之秦皇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均采取批判的角度抒写。浣青对这二位名君同样是抨击其千古之罪,显示出批判的深度。《始皇冢》以秦始皇陵为中心,既写其今日之荒凉,更联系秦皇之暴政酷刑,嘲讽其造陵过程的劳民伤财,最后归结到秦朝的灭亡。如开头四句点出始皇冢:“骊山高复高,落日霾荒台。西风吹白道,下见幽宫开。”始皇冢位于陕西临潼东骊山北麓,高七十六米,周长二千米,巍峨而有气势,但在诗人笔下乃是一派荒芜肃杀景象,这就是千古一帝的结局,全诗即此定下讥讽的感情基调。然后笔锋一转,指向墓主生前之罪:“秦政昔乱纪,刑杀如雷霆。”尽管秦皇亦有其“鲸吞六国尽”之威势,但诗人又讽刺道:“寄言镐池君,英武安在哉!”接下再回笔描绘造墓情景:“千人竞讴唱,运石清渭隈。筑之崇三坟,下锢泉水来。黄金作天地,日月为樽罍。银海停不留,人膏灿无灰。飞蚕三十箔,一一红玫瑰。知埋几皓齿,何论万匠哀?”诗人笔蘸愤慨之情,形象地写出了造墓工程之穷奢极欲,杀戮生灵,笔触有力,如同声讨。就是这样一个帝王,终于“虎视敛寸坏”,“难买青阳回”,难逃人生的法则,而且“坐使天下倾,何待长城摧!楚炬与牧火,两赭无遗煨”,其建立的王朝亦倾覆。更妙在结尾两句:“徒闻古丈夫,霞举登蓬莱。”棉里裹针,表面写秦皇生前曾求仙觅药而登临丹崖山蓬莱阁,但再与诗开头陵墓凄凉之景相对照,其讽刺可谓深矣,真乃春秋笔法。全诗三十六句,结构回旋跌宕,含意层层递转,笔力遒劲,不类闺阁。但其怀古诗少发议论,只点到为止,主要还是以形象的描绘、简炼的记事与真诚的抒情相结合,来表现诗人的思想。这大概又是女子怀古诗的一个特点。诗人对暴君秦始皇的抨击,正寄寓了她对圣主明君的向往,有其现实意义。七古《汉通天台铜人歌》乃咏通天台仙人事:汉武帝为求长生不老,于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故甘泉宫造通天台,“上有承露盘仙人,掌擎玉杯,以承云表之露”,铜仙人高二十丈,大十围。(参见《三辅黄图》、《汉书·武帝纪》等)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了汉朝国力的象征。但诗人笔下之铜人并未给汉武帝带来好运,最后结果仍是:“凄凄茂陵月,玉盘埋苔碧。”更可悲的是:“当涂代汉逾百年,铜人之泪流作铅。移经灞水亦伤别,回头立尽关东烟。”据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序载:“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上引四句正是写这个典实,其中第二句则化用了李贺诗“忆君清泪如铅水”之句。诗意是指魏代汉,仙人成了汉代衰亡的见证人,是汉武帝生前作梦亦想不到的。历史有其自身的兴衰进程,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仙人亦只能“泪流作铅”而已。诗最后乃感叹道:“君不见古今兴废皆陈迹,金石有情悲过客,化为铜驼卧荆棘!”末句用《晋书·索靖传》典:“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后铜驼荆棘指变乱后的残破景象。诗人由铜人之命运升华出古今兴废的历史规律,作为国力强盛象征的铜人最终亦会变成国家衰亡之物的铜驼,其意蕴可以说比李贺诗要深刻。
律体怀古诗值得提及的有《华清宫怀古》、《潼关》、《张子房祠》等。律体篇幅短,自然难以曲折跌宕、层层铺叙,但内容相对概括,语言亦精炼,表达比较含蓄,更耐人回味。如《华清宫怀古》:
霓裳歌吹动华清,小辇曾催花低行,池上鸳鸯怜并宿,天边牛女笑长生。空悲此日金钗擘,何事当时白练轻?一曲《淋铃》传夜雨,寿王宫内月同明。此诗乃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批评唐明皇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唐明皇为保住皇位而牺牲杨贵妃,今日只能空悲旧物“钗擘黄金合分钿”(白居易《长恨歌》)。诗人“何事当时白练轻”之问,含有谴责之意。而写鸳鸯并宿、牛郎织女长生,意在反衬唐明皇如今落个“孤家寡人”的悲凉结局,尾联尤值品味。据《明皇杂录》,唐明皇幸蜀,“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中闻铃音与山谷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所以“一曲《淋铃》传夜雨”,是写明皇有悼念贵妃之意,然而杨玉环本是明皇之子寿王之妃,寿王当更怀念杨玉环,而且杨玉环若不被公公夺去,亦不会有白练赐死于马嵬坡的厄运,故“寿王宫内月同明”句含意甚丰,留给人们想象思索的余地。
咏史怀古诗离不开人物、历史事件,必然牵涉到用典。浣青的怀古诗亦不例外。但性灵诗之用典不同于肌理诗之堆砌典故,以考据学问为诗。其用典一旨在为诗意服务,二不生僻,这样诗就具有历史感而不晦涩,并有典雅蕴藉之致。
咏史怀古诗重在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褒贬评判,从中寄寓诗人的感情。而直接抒发诗人真性情的则是浣青的思夫悼亲之作,给人以更强的感染力。《南野堂笔记》记云:“(浣青)归博陵进士今观察使崔曼亭先生时则。先生以名世之才,早年通籍,唱随风雅。洪稚存常博叙夫人诗,所谓以‘峰青江上’之篇,配‘枫落吴江’之咏,闺中知己,乐莫甚焉。”可见钱、崔伉俪感情甚笃。这又非汪玉轸与其夫之关系紧张可以相比。由于崔氏时常外任,而浣青往往不能随从,夫妻天各一方,浣青就有了《忆远词》一类诗篇,抒写其“极目天涯愁杀人”的期待,“思君夜夜复朝朝,日月有尽情无已”的相思。如七律《九日寄曼亭》:
夫君薄宦阻秋期,寥落三年寄所思。露气渐凋林下叶,霜风暗渡鬓间丝。归从白浦鸿相侣,瘦尽黄花蝶未知。屈指半生佳节过,向来尊酒几同持?“九日”即重阳节,乃“每逢佳节倍思亲”之日。夫妻分别“三年”,思念之情日深。诗人既不能见夫婿其人,只能想象其貌,因秋天“露气渐凋林下叶”的自然景象,而联想到“霜风暗渡”夫婿“鬓间丝”,诗人担忧怜惜之情尽在字里行间。颈联进而以比喻手法表现其幽怨之意。“鸿相侣”喻夫妻团聚,反映自己形单影只:“瘦尽黄花”,化用李清照“人比黄花瘦”(《醉花阴》)之意,比喻自己,“蝶”喻夫婿,蝶本恋花,然自己骨瘦形销,而夫婿一无所知,哀怨之情不言而喻。尾联乃直抒胸臆,含蓄的表现已不足以宣泄心中的忧愁,故而直言相告。由此诗可见浣青性格中柔情的一面,她毕竟是女子。这类诗重在抒发内心真情,故基本不用典,只是说家常般娓娓道来,但仍能以情感人。又如五绝《立秋》亦是思夫之作,但颇堪品味:
一叶凉风起,吹来天末情。寒衣须早寄,蟋蟀已秋声。此诗全然白描,语言自然朴素,口语化,属于性灵小诗。诗人因“凉风起”而勾起“天末情”,又自然产生早寄寒衣的想法,而蟋蟀作秋声又仿佛在不停催促。诗把浣青思夫之情写得细致而真切。
最能表现浣青真情至性的是悼亲诗《哭弟妇二首》:
忍听啾啾乳燕声,萧条门巷曲池平。九原兄弟如相见,应说孤儿渐长成。
摧残棣萼已伤神,又送孤花一朵春。今日凄凉惟剩我,举头谁是至亲人?浣青在此诗之前写过五古《代书三十韵寄弟妇循之》,写其与弟妇循之关系一向亲密,“清宵无尔我,密意总缠绵”;自“随夫行蜀栈,携子渡秦川”后,又回忆二人姐妹般的情谊,抒写怀念之意。而今弟妇忽然撒手人寰,岂能不悲?何况其弟已先逝,弟妇再归道山抛下嗷嗷待哺的幼儿,更是无法承受的巨大悲痛。而抒写此情的诗自然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当然,作者亦有其艺术构思,并非真的矢口而道。前诗乃着眼于孤儿,首句即点出孤儿啼哭声,如“啾啾乳燕声”,叫诗人肝肠寸断而不“忍听”。幼儿父母去世自是可悲之不幸,而抛下孤苦的幼儿同样是莫大的悲哀。基于此,乃想象弟妇于阴间与其丈夫相见,“应说孤儿渐长成”。这是弟妇对丈夫的安慰之词,亦是作者对死者的承诺与慰藉。浣青把对死者的感情转化对死者幼儿的感情,这是最有意义的悼念。后诗首联以比喻手法写自己相继失去弟弟、弟妇两位亲人的可悲事实,尾联则抒发只剩下“凄凉”之“我”的痛苦,向苍天发出孤独的悲号,真是一片性灵,催人泪下。这二首诗都表现出女诗人浣青善良、柔情的一面,与汪玉轸类似之作具有性灵诗的共性。
综上所述,可知钱孟钿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女诗人。一方面具有阳刚气质,有不亚于须眉的史识,这主要表现在其古体怀古诗作中,风格比较健朗,又善用典故,显示出较高的才学、较强的气力,一方面则不失女性的阴柔气质,亦有多情善感的本性,这主要表现在思夫悼亲一类直抒性灵的作品中,多为近体,感情细致真挚,风格柔婉含蓄,多采用白描,不用典故,显示出诗人的诗才、灵性。相对来说,其模山范水去作甚少,写景物亦缺乏性灵诗状物常有的活泼风趣的特点。
二、贫者之妇汪玉轸
随园女弟子大多数都夫妻和睦,甚至相互唱和,生活比较美满。只有孙云风、孙云鹤以及汪玉轸等所适不偶。但孙氏姐妹乃官宦之女,经济有保障,亦有条件读书吟诗,消磨时光。而玉轸则不仅婚姻不幸,而且“父兄夫婿,皆非士人,境遇艰辛,藉十指为活”(袁洁《蠡庄诗话》),可以说汪玉轸是随园女弟子中最苦命的人。
汪玉轸字宜人,号宜秋小院主人,江苏吴江人。其父汪蓉亭原是商人,颇好文墨,有子五人,皆愚不可教,惟一女宜秋甚聪慧。宜秋五六岁时父亲常抱置膝上,教她识字。但宜秋十岁时,其父病殁,家境顿变,乃习针黹,只有稍暇时读点书。而其家苦无藏书,除了四书之外,惟有李笠翁十种曲、蒲留仙《聊斋志异》而已;但她反复阅读,皆可背诵。十九岁嫁吴江人陈昌言,从此境遇更苦。陈氏不但一文不名,而且好吃懒做。开始时宜秋以奁中物供其挥霍,不久就斥卖净尽,加上先后生五子,家境简直赤贫如洗。宜秋只得以为人缝纫换钱买薪米,家中整日是孩子啼饥号寒声以及丈夫斥责谩骂声。陈氏还常年外出,曾一走五年不归,全靠宜秋独立支撑家政,抚养五儿。后来陈氏回来索性卖掉室庐杂物,一去不返。宜秋母子竟无处可居,只能借表弟室旁一椽栖居。表弟李铁门亦吴江诗人,心肠不错,时时过从慰藉帮助。一日表弟从宜秋针线筐发现一纸吟稿,怪而问之,宜秋乃赧然答曰:“曩过君家,见架上元人诗一册,窃携以归,俟家人熟寝后,灯下默诵,心为之开,学作数语。自知鄙俚,未敢示人。”铁门于是将自己所藏名人诗稿借给她看,且鼓励她作诗。二三年中得诗千首,皆于枕上微吟得之,有的口诵无存稿,有的亦不自收拾。后朱春生为之搜集二百来首诗,编为《宜秋小院诗钞》,今有嘉庆十六年刻本。宜秋生年五十二,乾隆后期、嘉庆前期在世。(据《无名诗钞序》、《蠡庄诗话》、《绿庵诗话》等。)
袁枚于《随园诗话补遗》卷八抄录宜秋《春夜》、《偶成》、《扫墓》诸诗,并评云:“宜秋家赤贫,夫外出五年,撑持家务,抚养五儿,俱以针黹自给,而有才如此。”对宜秋诗才颇为赞赏。袁枚编《随园女子诗选》,宜秋名列其中,只是今存本有名而无诗矣。宜秋与袁枚联系不密切,但她属于性灵派是毫无愧色的。
从上述宜秋生活之艰辛、婚姻之不幸,但都忍受下来的身世,可知她是一个性格善良、温顺的弱女子;但又是一个韧性颇强的人,所以才能在逆境中坚持读书作诗,且“诗才迥异庸流,为时叹服”(《苏州府志》)。白居易尝云:“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采诗》)吴乔亦云:“人心感于境遇,而哀乐情动,诗意以生。”(《围炉诗话·自序》)宜秋所感之事与所遇之境乃悲事厄境,这就决定了其所发之吟咏、所形之歌诗有哀无乐,而诗基本上成了宜秋宣泄痛苦的渠道。同时又决定了她的诗乃发自内心,句句情真,无须伪饰雕琢,自然朴素。加之所写皆个人生活遭际,俯拾即是,亦不必求助于经史典故,一味白描即可。
宜秋诗的感情基调就是悲衰。这与浣青有很大不同,浣青许多诗比较开朗,思夫诗亦仅是幽怨,只有悼亲诗才是悲哀之作。宜秋诗与其好友金逸相近,皆以抒发主观哀思为主旨。但二人哀叹之缘由则不同:金逸是因为病魔长期缠身,而有生命之哀;宜秋是因为婚姻不幸、生活贫困而生生存之哀。具体又有多种表现情态。
一是贫困之哀,温饱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如果赤贫到要“绝食”,那么其内心之忧愁悲哀就无法遏止了。五律《典质已穷,无以卒岁,赖竹溪诸诗人敛金相周,诗以志感》二首即是贫困之哀的典型之作:
惠比指囷赠,情同挟纩温。感深惟有泪,欲报恐无门。得食诸雏长,衰宗一线存。应知姑与舅,泉下亦衔恩。
回头语儿辈,汝勿太憨痴。不有诸君子,何堪卒岁时?可怜饥冻久,未敢再三辞。他日如成立,生生尸祝之。王蕴章《然脂馀韵》云:“宜秋丰才啬遇,贫至绝食。竹溪诸子,敛金周之,风义甚高。宜秋以二律为谢,读之凄人心脾。”可作这二首诗的题解。二诗在谢恩的深层抒写的是贫困之哀。朋友的周济当不会很多,但在“贫至绝食”的宜秋看来,就“惠比指囷赠”了。嗷嗷待哺的孩子因“饥冻久”而坐以待毙,宜秋亦就顾不上“再三辞”的客套了。而对朋友之周济,不仅子女来日要“生生尸祝之”,连黄泉下的公婆“亦衔恩”。这种种表述都说明自家已至绝境,堪称字字“有泪”,句句含悲。诗明白如话,意蕴委婉,正是比较典型的抒写真性情的性灵诗。又如七绝《风雨连宵杂然有感》之一亦是写贫困之哀的:
室无长物一椽宽,照壁残灯影怕看。风雨潇潇虫唧唧,一声声和柝声寒。如果说前二诗以议论兼抒情为主,那么此诗则是以景寓情,比较含蓄。首句诗意较露,写出陋室家徒四壁之状,次句已耐人寻味,“怕看”者何?并不赘言,自可领会。当客观之穷困勾起主观之悲哀,就有了后两句的凄凉的听觉意象,潇潇风雨声、唧唧虫鸣声以及惊心的柝声,都在诉说着贫困之哀,意境显得十深远。
二是悼亲之哀,宜秋孤独一人支撑家业,抚育五子,作为柔弱的女性是多么渴望有人扶持一把。丈夫既靠不住,那么怀念死者,渴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点精神的力量,亦就可以理解了。因此她写有七律《扫墓作》二首,其一云:
卮酒亲斟拜墓台,低头顾影不胜哀。斑斑泪染罗巾血,淅淅风旋纸陌灰。略慰九原思子意,今朝弱媳挈孙来。病躯只恐难重到,家事从头诉一回。尾句画龙点睛,道出“卮酒亲斟拜墓台”的用意,是欲向作古的公婆哭诉其贫困悲惨的“家事”,宣泄内心的痛苦。所以全诗的情调就不能不是“不胜哀”的。诗中无论是“斑斑泪染罗巾血”的情态,还是“淅淅风旋纸陌灰”的环境,都是诗人悼亲之哀的具象化。而“略慰九原思子意,今朝弱媳挈孙来”,固然表示其孝心,亦是诉说因公婆之“子”不在,自己孤苦无依之状。同题另诗首联“荒原日落野禽啼,泪眼模湖极望迷”,尾联“惆怅人归天又暮,晚风夜月草凄凄”,写墓地黄昏入夜之景,荒凉凄冷,亦形象地营造出悼亲的悲凉氛围,而骨子里仍是贫困引起的悲哀。
三是怀友送别之哀。对宜秋来说,友情是其精神支柱,她比任何人都更需要朋友的关心慰藉。金逸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其为宜秋诗稿所题的诗有“空教费尽好才华,夫婿年年不在家”之句,很是同情宜秋的境遇,并“愿化相思一双鸟,替衔红豆到天涯”,此乃为宜秋寻找丈夫的奇想,亦可见对宜秋情谊之重。可惜这样一位好友却不幸早逝,失去一根重要的精神支柱,宜秋的悲哀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怀念的感情又是郁积于心,难以消失的。其《读纤纤夫人〈瘦吟楼诗稿〉中有见怀五律,系去秋所作,当时未寄示也。感旧怆今,次韵一首。时甲寅六月晦日》云:
不管幽兰殒,霜风一夕吹。人间留我在,身后读君诗。鱼雁当时杳,心情
各自知。卷中酬唱迹,零落动哀思。此诗首联以象征手法点明纤纤(金逸)如“幽兰殒”,其余三联皆直抒胸臆,坦露哀思,语言平白无奇,但像“人间留我在,身后读君诗”这样的似乎平淡的句子,实际上蕴含着很深的怀友之情。当好友去世一年之后,忽然见到生前怀念自己的诗作,则如睹故人,亲切之极;但此时只“留我在”,诗作者已永逝,心情该是何等沉痛!这正是袁枚所谓“意深词浅”(《续诗品·灭迹》),“诗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随园诗话》卷八引《漫斋语录》语)之艺术功力。宜秋送别诗亦情真意切,如《送袁湘湄先生之淮上》、《送铁门内弟之淮上》都抒写了送别之哀。后者尤其感人肺腑,诗为二绝,录其一:
制就《阳关》不忍歌,送行难禁涕滂沱。无家我正依君住,君又飘零可奈何?表弟李铁门可以说是宜秋一家的“救命恩人”,若无表弟于宜秋走投无路时鼎力相助,恐怕已无生路了。但表弟因故远出,自己失去依靠,又禁不住涕泪滂沱,既有分离之哀,又有孤独无助之悲,甚至流露出绝望之意,读之令人酸鼻。
四是季节之哀。无论是春天还是秋季,诗人都感受不到自然的美。她仿佛看不到春之烂熳、秋之明朗,反因季节变换添了内心的苦闷,正如其所言:“情怀自笑太无端,只解愁烦不解欢。”(《答纤纤见赠之作即次原韵》)如《偶咏》愁春:
风飘柳絮雨飘花,多少新愁上碧纱。借问过墙双蝴蝶,春光今在阿谁家?春之景给诗人带来的是“新愁”,那么她本有旧愁,如今可谓愁上加愁。为何愁,答案在尾联,但并不明言,而是借问翻飞过墙的蝴蝶,可知“春光今在阿谁家”?蝴蝶虽未答,但答案已在问句本身中,即诗人之家没有烂熳“春光”,有的只是贫困。沈善宝《名媛诗话》评此诗曰“其境困厄于此可见”,正道出诗人何以有“新愁”。宜秋悲秋之什更多,因为秋季之萧瑟凄清更易触动哀思。如《立秋》之“凉风送雨雨凄清,数遍残更梦不成”,《秋夜》之“打窗落叶梦惊回,风急长天过雁哀”,凉风凄雨,落叶哀雁,每个意象都蕴含着悲思。典型的如《风雨连宵杂然有感》之一:
含情脉脉对银釭,才说悲秋泪已双。可奈西风吹落叶,夜深只管打寒窗。
“才说悲秋泪已双”乃夸饰悲秋意识之深重,而“可奈西风吹落叶,夜深只管打寒窗”,不仅描绘出秋之萧瑟景象,亦增强了诗人的悲秋意识。诗人渲染环境气氛的能力颇强,对自然的感受甚为敏锐,这是其诗人气质的表现。因此她学力虽然不足,但不妨碍她成为抒写性灵的诗人。
宜秋诗主体是抒悲写哀,已如上述。另外影响较大的是题画诗,有其独创性,袁枚所谓“超隽能新”(《随园诗话补遗》卷十)。如《题郭频伽先生水村第四图》四首之四就是引起好评的佳作:
深闺未识诗人宅,昨夜分明梦水村。却与图中浑不似,万梅花拥一柴门。据载,此诗令吴江诗人郭频伽“喜极,即请画师奚铁生补画,一时名士题咏甚多”(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卷十四)。诗之妙处在于打破历来题画诗拘泥于原画的框框,而是“改造”原画的景观,并以梦的形式构思出一幅全新的画图:“万梅花拥一柴门”。这是诗人的创造,是笔性灵的产物,具有性灵诗的特征。又如《题陈秋史亭角寻诗图》亦颇具新意:
亭空面面好寻诗,四角循环步履迟。阶下疏花墙外柳,枝枝叶叶解相思。“枝枝叶叶解相思”,花柳被赋予了性灵,有了情致,于是陈秋史寻诗就有了感情的对应物,花柳向陈秋史倾诉着诗情,寻诗者亦就无须苦思冥想而出口成章,可谓“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异质同构。此诗虽为题画,但诗人却作为实景一样描写,画面就鲜活起来。这类题画诗多少有些浪漫气息,是诗人愁思之外短暂的愉悦,或者说借这类审美性强的诗作来冲淡一下心中的愁苦。
综上所述,可知宜秋作为一个贫者之妇,生存状态限制了她的创作视野,她只能关心自家的冷暖饥饱,抒发一己之悲情愁绪,与钱孟钿的大家之气相比,难免“小家子气”。她的学识不甚高,才力亦不足,因此不擅古体。但长于近体,特别是“七绝颇饶风致”(李堂《绿庵诗话》),有“语近情遥”,“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沈德潜《说诗晬语》)之妙。而其性情之真挚,白描手法之娴熟,更具性灵诗的特点。以宜秋这样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条件,能长期坚持诗歌创作,并写出不少感人肺腑、具有新意的诗篇,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不宜对她过于苛求。在中国妇女文学史上,大概只有清代女词人贺双卿可与之相比。但贺双卿是否实有其人还是个问题,而汪玉轸却是无可怀疑的历史存在。从这一角度说,汪玉轸实是中国妇女文学史上值得刮目相看的女诗人。
注释:
① 本文系随园女弟子研究系列论文之一。另有《随园“闺中三大知己”略论》、《随园女弟子述略》、《扫眉才子两琼枝》等,将由《文学遗产》等刊物陆续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