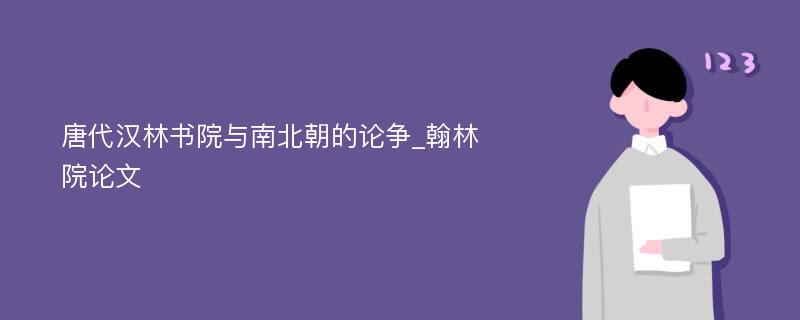
唐代翰林学士院与南北司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翰林论文,之争论文,唐代论文,学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01)01-0027-07
一、翰林院、学士院与东翰林院成立再析
唐代所谓“翰林学士院”,从文献记载和考古遗址来看,是较为复杂的建筑组群。严格说来,涉及翰林院、学士院与东翰林院的不同建置阶段。关于三者成立概况,《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四年七月乙未条胡注析述如下:
翰林故事曰:翰林院者,在银台门内,以艺能、技术召见者之所处也。玄宗初,置翰林待诏,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又以诏敕文告悉由中书,多雍滞,始选朝官有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开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别建学士院于翰林苑之南,俾专内命。其后又置东翰林院于金銮殿之西,随上所在。[1]
这里显示:(1)翰林院是当中最早成立的北面机构,乃处技艺待召者之所。(2)玄宗即位之初,翰林机构的内容逐渐丰富,有翰林待诏负责批答表疏,应对辞章等事,更发展至直接挑选具学识的朝官职居于翰林,疏理中书诏敕。(3)开元二十六年后,从前于翰林供奉的才学之士才改称为翰林学士,故于翰林院所属范围以南,分别兴建学士院,以专其制诏之职。(4)及后于金銮殿之西,又建置相对于旧院址的东翰林院,方便帝王起居所在。如此解读,有助学界探讨翰林院与学士院的异同问题。[2]从上文可知,学士院建于翰林院之南,始于翰林学士之设。此外,据马得志《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的考古发现,在大明宫右银台门以北、西夹城之内出土的六组遗址,建筑群(一)(二)(五)与建筑群(三)(四),两者互相以砖道相隔,南北对置,形制上与北厅的翰林院和南厅的学士院极为吻合。从南面建筑群(学士院)别以东侧通门(翰林门)出入,可推知两院活动分隔的意图。[3](P114-116)程大昌《雍录》卷4《大明宫右银台门翰林院学士院说》载:
翰林院在大明宫右银台门内稍退北,有门,榜曰“翰林之门”,其制高大重复,号为胡门。门盖东向,入门直西为学士院,有两厅,南北相启,而各自为门,旁有板廊,自南厅可通北厅,又皆南向。院各五间,北厅从东第一间常为承旨阁,余皆学士居之。厅前阶砌花砖为道……(南厅)东西四间皆为学士阁,中一阁不居。北厅又北则为翰林院,初未有学士时,凡为翰林待诏、(翰林)供奉者,皆处其中。后虽有学士,而技能杂术与夫有学可备询访之人,仍亦居之……翰林院又北则少阳院。[4]综合两条资料,学士院成立后性质异于翰林院,应始于开元二十六年,若以此为第三期,则在翰林学士产生以前,文学待诏之士供奉于翰林院,与技能杂术者清浊共处,大概是第二期的现实写照。从翰林院初期成立原意观之,它是异才技艺人士优养之地,随时待诏,其间文章之事渐高于他种才艺技能,是宫廷政命草制日形重要的结果,故此翰林院在第一期草创时期,早已具备第二时期的特质,情况类于第二期过渡至第三期。韦处厚《翰林学士记》曾谓学士院官所以不称供奉而称学士,乃因学士俾专内命,与夫数术曲艺,礼有所异,因此才出现其后截然分化的态度。
玄宗开元期间,长期听政于兴庆宫的藩邸旧址。吕大防的石刻图中,每能精确绘画唐代宫廷建筑细微之地,较诸程大昌《雍录》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更为详实。吕氏所绘的兴庆宫图,在南衙官署的金明门入口附近,有翰林院的设置,而翰林院的南面只有一道通门,为三面密封,背向兴庆殿、大同殿的设计,南下可直抵勤政务本楼。宋敏求《长安志》卷9《兴庆坊》条亦载:“大同门西曰金明门,内有翰林院。”又注:“《学士院记》曰:驾在兴庆宫侧,于金明门内置院。”[5]若以开元十六年兴庆宫朝堂峻工时间计算,兴庆宫内的翰林院至迟亦当于此时已经运作。《旧唐书》卷43职官二翰林院条载:“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6]三宫之内各有翰林机构侍上所在,乃为不争事实,对了解翰林待诏、翰林供奉以至翰林学士的早期成立过程,具莫大启示。
翰林院广泛分布的形态,也有助辨证某种学士的职称关系。学者辛德勇早已留意高宗至武则天主政时期,北门学士供职的地理问题,反驳前人以翰林院门在右银台门之北,因而得出“北门”的学士说法。辛氏认为,无论从文献及考古均不存在相对于右银台门以北的“南门学士”,故语意逻辑不通。若据程大昌《雍录》卷4南北学士条的解释,则翰林与学士之设较为明晰,其谓:
唐世尝予草制而真为学士者,其别有三:太宗之弘文馆、玄宗之丽正、集贤,开元二十六年以后之翰林。此三地者皆置学士则是实任此职,真践此官也。若夫乾封间号为“北门学士”者,第从翰林院待诏中选取能文之士,待使草制,故借学士之名以为雅称。其实此时翰林未置学士,未得与弘文、集贤齿也,故曰“北门学士”,言其居处在弘文、集贤之北也。[4]
这里主要析述唐代学士的源流,欲同时反映翰林机构早期,并无学士之设。乾封年间的北门学士,乃从翰林院待诏中选士,雅称学士而已,性质上未能与南衙的弘文、集贤诸馆学士的机构实职相比。同样的道理,翰林供奉发展至翰林学士,也必然经过这种由虚变实的进化过程。程大昌的《东内西内学士及翰林院图》、《大明宫右银台门翰林院学士院图》及《学士院都图》,皆着墨于右银台门之北,接近宫城西墙的翰林及学士院,对其他翰林院的性质,未加详析。玄宗当政期间,从大明宫南通兴庆宫,有夹城建筑其间,方便人主潜行,故三宫机构之间往往产生重叠、互补的政治作用。[7](P15-32)兴庆宫的翰林院职,至少说明玄宗践位之初,以翰林待诏批答表疏,应和辞章,并逐渐由学识朝官职居机构内的新趋势。此类临时制诏的职种,于开元后期遂陆续为学士院的专职取代。
夹城与重廊的设计,使翰林学士院处于近密的位置,它既处于夹城之内,如何连通于殿最方便制诏宣旨,成为政治关键所在。从考古发现得知,夹城直北之处为密封城墙,进出途径必先经翰林门,然后转入宫禁范围。重廊的构造是利于抵达殿侧,而不须绕道,以达至密速潜行的效果。韦执谊《翰林院故事》记翰林院在银台门内麟德殿西重廊之后;而麟德殿东、西两侧均有重廊亦有文献记载。《雍录》卷4载:“麟德殿东廊有郁仪楼,西廓有结邻楼,学士院即在西楼重廓之外。”[4]由此可证,大明宫城的西墙,西有夹城,东有重廊,由夹城通宫城重廊,沿横直的走廊通行麟德殿,直北抵少阳院,无疑拉近夹城建筑与宫内西侧诸殿院的距离。
大明宫内,由翰林院发展出学士院,再由翰林学士院别置东学士院的繁衍过程,同样产生了不少机构重叠的疑问。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即谓:“东翰林院于金銮殿之西,随上所在而迁,取其便稳”,即从方向上指明其新院地近金銮殿,目的是较近便起居于各殿的君主随时传召。《资治通鉴》卷236顺宗永贞元年正月癸巳条下,胡注:“程大昌《雍录》曰:金銮坡者,龙首山之支陇,隐起平地而坡阤靡迤者也。其上有殿,名曰金銮殿。殿旁有坡,名曰金銮坡。又曰:金銮殿者,在蓬莱山正西微南,龙首山坡之北。殿西有坡,德宗即之以造东学士院,以其在开元学士院之东也。”[1]按此地理,东翰林院半隐于金銮坡上,颇能达至近密目的。徐松《大明宫图》,东翰林院东出有金銮殿,南出为延英殿,西近麟德殿,二殿再东出,便是紫宸、蓬莱诸要殿,位置上显然较夹城中的翰林学士院较接近宫中各主殿。《陕西通志》所绘大明宫图,将东翰林院称为东学士院,凸现了从旧学士院中衍生的历史背景。
中唐君主常因起居之处,密召学士商议草制,旧的学士院从夹城翰林门东出,较易为结邻、郁仪等城楼监察;若从东学士院绕北背禁苑,不但同样可达靠西侧的麟德殿,并且不动声色抵东侧的浴堂殿。史书载德宗常居浴堂殿,又谓学士院以北扉之便,密封于此。单从夹城学士院地理难以解释,盖翰林以北有墙垣之隔,于东学士院北出,沿禁苑范围而下,则稍近情理。由此推之,东学士院当由于翰林学士须常候君主密封,渐次于禁中近便之处特别成立的翰林机构。此种关系,将于下文析述。
二、唐代翰林学士院与南北衙关系
唐代翰林学士院早存在于东内、西内和南内的宫廷范围内,从地理位置分析,不足以把它归类于南衙宰相机构或大明宫苑内的北衙系统。况且,其设立背景既有分执宰权限,成为内相意图,主事者又是学士官员,跟其他宦官司局本具差异。故此,翰林学士院实处于南北衙对峙下的中间组织,协调因内廷系统迅速发展,无法与律令机制衔接而可能产生的决策延误。由于身份特殊,翰林学士对两者的向背往往左右政局发展,渐成为内外廷重要的拢络对象。大抵从官僚的职掌和升迁的途径而言,宰相与翰林学士的制诏关系较为密切;惟内廷决策的草议和行动配合上,宦官中尉与内诸司却容易制控翰林学士。中晚唐的南衙北司之争,离不开宰相欲夺内廷权力,最后遭受阉竖反压的收场,翰林学士则长期处于这种纠纷中,反复拓展其政治空间。
1.从草制到决策的翰林职责
翰林学士草制的职能最为重要,由此而来的,是草拟决策时的论议角色。踏入中唐,无论是肃宗、代宗之交,或者是敬宗、文宗之间,储君承继的诏书,成为新立帝王的法理依据。两次政变的共通点都是旧主驾崩之初,所召继位人选不为宦者接纳,结果由宦官军政诸司掩护新储出起居之处,勒兵殿院之下,推翻前议。在另起炉灶过程中,宦官仍得同样以翰林学士草诏析法,说明翰林学士院由于北出少阳院之便,草诏工作渐受内廷宦官操纵役使。就平日草拟公文而言,内容轻重不一,翰林学士的权限发展,仍须视乎帝王信用的程度。关键时期应自德宗开始,盖泾原兵变,翰林学士陆贽于患难中随行在制诏,调兵遣将无出其右。《旧唐书》卷139陆贽传谓:“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6]李肇《翰林志》载其时翰林学士不但朝服班序,而且“赋权日重,于是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免三公宰相、命将相,皆出于斯。”换言之,由德宗非常时期到政局渐告稳定,翰林学士的草拟实权,已由单纯的文书起草发展至广泛参决的层面。
翰林学士能加入议政行列,与君主兴起固定的议事渠道有关。例如,裕堂殿乃德宗长年视事之所,地近绫绮殿,大明宫较东侧之处,此后帝王每于此召问学士意见。《资治通鉴》卷237宪宗元和二年十一月胡三省注:“唐学士多对浴堂殿,李绛之极论中官,柳公权之濡纸继烛,皆其地也”,即道出翰林学士应召于此的传统。李绛与白居易批评宦官专权,事见卷238宪宗元和四年九月条,以此推知,浴堂议事制度沿袭已久,翰林学士论政决事风气已然建立。例如,顺宗时期,帝主长期养病,多由王叔文、王伾与宰相韦执谊主持政事,而且“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1]由决策到宣召皆由翰林学士总揽,从前制诰的文书工作则交付中书代理,翰林学士议决地位十分明显。王叔文等权力上升,开始令部分宦官不安,继而拉拢另一批翰林学士,进行政治反扑。《资治通鉴》卷236顺宗永贞元年三月载:
上疾久不愈,时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亲奏对者,中外危惧;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恶闻之。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旧人,疾叔文……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太子制。[1]
王叔文专权,得力于一派宦官支持,情况与俱文珍、刘光琦援引其他学士,二者政治结合的方式相差无几,惟双方政治对峙,不免令学士院内部分化。史书未载东学士院成立的政治动机,《石林燕语》卷5云:“唐德宗时尝移学士院于金銮坡上”,或与泾原兵变,逐渐专委翰林别处承受要旨有关。观顺宗末年政治,东学士院有进一步巩固的趋势。王叔文等视事之所,仍以右银台门内的翰林学士院为基地,对郑絪、卫次公等反对派翰林机构成员,必然产生种种矛盾和不便。东学士院地处金銮殿的西侧,与前者俨然形成另一议事系统。宦官俱文珍以诸学士入金銮殿草制立储事宜,至近密之法当就地起用学士班底,意味着东学士院,前后经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渐告成熟。若考《旧唐书》卷159,卫次公传,以郑絪等翰林学士为代表的金銮殿议政机制,隐然于此段期间发挥功效,《卫次公传》载:
贞元八年,征为左补阙,寻兼翰林学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时东宫疾恙方甚,仓卒召学士郑絪等至金銮殿。中人或云:“内中商量,所立未定。”众人未对,次公遽言曰:“皇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内外系心。必不得已,当立广陵王。若有异图,祸难未已。”絪等随而唱之,众议方定……及顺宗在谅暗,外有王叔文辈操权树党,无复经制,次公与郑絪同处内廷,多所匡正。[6]
郑絪、卫次公等成功助顺宗登位,本为前朝功旧,但顺宗临危,竟由王叔文、王伾据银台门翰林指挥政事,制诏无所经由,自然产生矛盾。宦官集团内的互相对垒,加深了翰林政治的主导战。结果,郑絪政治选择正确,宪宗即位便提升为翰林学士承旨,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谓郑絪位在诸学士之上,“凡大诰令、大废置、承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受专对,他人无得而参。”学士承旨即翰林学士之首,由于职居学士院长,可随时单独与君主对话,秘密筹决。[8]要达到密议目的,承旨学士必须常出学士院而穿梭宫内,随君主所在入对。同时,于旧学士院北厅东第一间作为翰林承旨办公之所,有统率诸学士之意,避免出现前朝王叔文争夺权力的类似情况。学士承旨每须规范翰林学士,见于《资治通鉴》卷238宪宗元和五年六月的如下记载:
白居易尝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绛曰:“陛下容纳直言,故群臣敢竭诚无隐。居易言虽少思,志在纳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钳口,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上悦,待居易如初。[1]
白居易能留于翰林学士院,皆因承旨李绛于密议中对其持正面态度,可见帝王在承旨之设及密议制度的双重保障下,重新以翰林学士院为帝王私人腹心。由于南衙北司长期对立,帝王用人管道已尽量超越外朝宰相或内廷宦官,避免直接卷进各种人事纠纷,相反多以重用的翰林学士承旨入相,更能确保政治风险。故此,学士承旨之职已有提前培育帝王亲信的意图,方便日后进入中枢的决策层。例如裴垍任相前职居翰林,《旧唐书》卷148本传谓其“在翰林承旨,属宪宗初平吴、蜀,励精思理,机密之务,一以关垍,垍小心敬慎,甚称中旨。”[6]学士承旨职涉相权,故每为持异见的宰执不容。史书载宰相李吉甫“自以诬构郑絪、贬斥裴垍等,盖宪宗察见其情而疏薄之,故出镇淮南。”[1](卷237元和三年九月戊戌)裴、郑皆曾为学士承旨,受帝大用,宰辅因排斥二人反遭疏远,宪宗对翰林学士甚见宠信。帝王和翰林学士密议,必由学士值勤,可随时便殿召见所致,其事多涉北衙宦宫,令事态尤见机密。《新唐书》卷207《仇士良》传载:
(文宗)开成四年……退坐思政殿,顾左右曰:“所直学士谓谁?”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尔所况,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尧、舜主也。”帝曰:“所以问,帝与周赧、汉献孰愈?”墀惶骇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因泣下。[8]
君主援引学士论议宦官,为了防避阉宦视线,召对往往彻晚进行,如文宗时以批评宦官知名的翰林学士柳公权,“每浴堂召对,继烛见跋,语犹未尽,不欲取烛,宫人以蜡液揉纸继之。”[6](卷165《柳公权传》)武宗曾夜召学士韦琮草制,而宰相、枢密皆不之知,[1](卷247,会昌三年五月壬寅)益见翰林学士的近密程度。又如宣宗“召翰林学士韦澳,托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1](卷249,大中八年)凡此可见,双方密议的方式甚多,因时地而表现迥异,然帝王因学士草制之便,征以筹谋宦官良策,均为上述共通之处。
2.翰林学士与宰相制——北衙权力制控的因由
由草拟制诏发展至密议决策,翰林学士之职已非单纯的秘书顾问角色,其执行部分相权,足以改变宰相与宦官权力周旋中的政治形势,此为宰相与学士关系又得和谐共事之处。翰林学士分割相权,诚如张国刚等具体所言,是将中书舍人制诏之权纳入职责之内,使帝王政令分为内制和外制两组性质。翰林学士用白麻所撰的内制,直接由禁中发出,关乎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立后建储等重要诏书;中书舍人用黄麻所拟外制,则为一般诏书。白居易曾任中书舍人及翰林学士,其所撰中书制诏和翰林制诏,便显出了内外二制轻重之别。[9](P259-261)白麻之制本为宰相所有,《资治通鉴》卷235,德宗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条即载:
初,上置六统军,视六尚书,以处节度使罢镇者,相承用麻纸写制。至是,文场讽宰相比统军降麻。翰林学士郑絪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遂为著令也?”上乃谓文场曰:“武德、贞观时,中人不过员外将军同正耳,衣绯者无几,自辅国以来,堕坏制度。朕今用尔,不谓无私。若复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谓尔胁我为之矣。”文场叩头谢。遂焚其麻,命并统军自今中书降敕。[1]
德宗时翰林学士重提旧事,欲挫神策中尉窦文场等气焰,法制上宰相降麻名正言顺,然中官统军授麻之法前代已有发生,非文场无理般弄。郑絪的诠释,使任用权力连结于翰林、宰相之下,盖关乎将相降白麻起用之事,前一日必经中书、门下文书审批,然后付翰林草麻,最后由宰执宣敕,宦官无由干预。事实上,宰相一直着意制控北衙授官,《资治通鉴》卷246文宗开成三年九月条载:“开成以来,神策将吏迁官,多不闻奏,直牒中书令复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癸未,始诏神策将吏改官皆先奏闻,状至中书,然后检勘施行。”[1]换言之,神策宦官每有人事调动,必须“先奏闻于上,禁中以其状付中书,方与检勘由历而施行之”。[1]由过往不向君主奏请而直牒中书,到现在付状于中书检勘再施行,其精神与前者麻制一脉相承,宰相得以重夺部分任免权力。越到唐代后期,中书与翰林之间对麻制的草拟与宣行,渐取得分工默契。《资治通鉴》卷253僖宗广明元年五月乙亥条胡注载:
唐制,凡拜将相,先一日,中书纳案,迟明,降麻,于閤门出案。《会要》:凡将相,翰林学士草制,谓之白麻。韦执谊《翰林故事》曰:故事,中书省用黄白二麻,为纶命重轻之辨,近者所出,独得黄麻;其白麻皆在翰林院,自非国之重事,拜授将相、德音赦宥,则不得由于斯。史言唐未宦官恣横,监军与枢密使,恩数埒于将相。[1]
唐代后期翰林学士的职责繁多,草诏密议之余,于宰相施行任免权力中越形占优。从前黄白二麻的诏降悉属中书,渐次由翰林学士院独掌系乎军国重事的白麻,且直接关系宦官用人权限。将宰相权力移于翰林,未必不是出于帝王的本意,如是藉第三者可以重新规管重要官职。从各种迹象显示,翰林学士透过白麻之制,发挥封驳政策的权能。例如,宪宗时期王承宗叛,欲令宦官吐突承璀为行营招讨处置使,蒋偕《李相国论事集》卷2载:“翰林中屡陈从古无令中人统各镇师徒,诸道受其节制者,师出不律,军必无功。前后谏论一十八度。后宰相论,亦不允,遂依上旨,仍令学士李绛撰白麻。其日,绛又进状,称事实不可。”值得注意者是,其后“上手执一纸文书云:宰相悉言可任承璀,而学士不肯,如何?”既然上意已决,加上宰相附和,翰林若只职草麻,则君主无须多费唇舌考虑李绛奏状。显然于制麻过程中,翰林学士可就白麻内容参决可否,是翰林既得的合法权力,使皇帝在此决策上不得不谨慎考虑。
制白麻的专责,何以由宰相移于翰林,史料并无明载,然而翰林学士承旨所带职官多为兵部侍郎,而且上迁途径往往直指宰相之位。在唐的官制里,兵部侍郎为正四品官,位在正三品尚书之下,负责处理军机政令。[6](卷43《职官二》)故此,学士承旨带此职,无疑预先提拔宰执人选,便于协办将相降麻的军政重任。《旧唐书》卷43职官志之翰林院注:“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据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统计,宪宗迄穆宗之间承旨学士中,十一人已有九人参大政。若从更全面的数字统计,于德宗至懿宗的154名翰林学士中,能至宰相者有53名,占32%,而在宪宗至懿宗的52名承旨中,其后任相者共30名,占58%,后者入相比例更形明显。[10]翰林学士承旨与宰相制之间,已成为相通的亲信渠道,于决策层面上更为帝王倚重。君主以学士承旨强化皇权的同时,宦官亦设法于翰林机构内渗透其影响力。[1](卷245,太和七年至九年)例如,以新的院使职种,监控学士权力。考翰林院使最早出现时期,在宪宗初年,《白氏长庆集》卷30载:“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贤院召赴银台候进旨,五日召入翰林,奉敕试制诏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谦奉宣,宜授翰林学士也。”从翰林院使奉旨宣授翰林学士看来,院使似已监控学士的进出与任免。梁守谦为宪宗期的权阉,《资治通鉴》卷238及《册府元龟》卷665、667诸处,载梁氏于元和五年已由枢密使提升为右神策军中尉的北衙最高要职,显见翰林院使地位之重。[7](P90-101)杜元颖《翰林院使壁记》又谓该使“进则承睿旨而宣于下,退则受嘉谟而达于上,军国之重事,古今之大体,庶政之损益,众情之异同,悉以开揽,因而启发”,翰林院使乃集承旨、宣召与参议军政于一身,更肩负统领翰林学士之责,使众情归一,臻上情下达之效。《翰林志》载:“有高品使二人知院事,每日晚执事于思政殿,退而传旨”,或因应翰林、学士院之分而设置院使。
考宪宗年间宦者吕金如、刘弘规等均曾出任翰林院使,但其时并无提及学士院使,至宣宗时期则翰林院使外,已有学士院使的专职分出,位在前者之下。盖《闾知诚墓志铭》载闾氏先于大中三年拜染坊使后,再迁监学士院使,到大中十年入观,又充内坊使,累迁翰林院使。随着时代推移,尤其学士院的职责繁重,由学士院使监当其事,并充分与翰林院使共商国情,斟酌要旨,当为对两使存在的合理推论。昭宗末年翰林学士韩偓被逼令起草韦贻范起复制书,即为学士院使等主意。《资治通鉴》卷263天复二年七月甲戌条载:
命韩偓草贻范起复制,偓曰:“吾腕可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论贻范遭忧未数月,遽令起复,实骇物听,伤国体。学士院二中使怒曰:“学士勿以死为戏!”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寝。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罢草,仍赐敕褒赏之。八月,乙亥朔,班定,无白麻可宣。[1]
学士使强逼翰林学士草制不成,只能据其疏如实上奏,正反映学士使与翰林学士的矛盾日渐鲜明。盖翰林学士拥法理上的降麻权责,由此衍生各种决事功能,学士使干预的途径,一在监视翰林学士于学士院的出入活动,二在掌握学士制定旨令后的承宣渠道。胡注便谓:“时韩全诲等使二中使监学士院,以防上与之密议国事,兼掌传宣回奏。”同卷天复二年十一月甲辰条载:“上使赵国夫人詷学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韩偓、姚洎,窃见之于土门外,执手相泣。洎请上速还,恐为他人所见,上遽去。”昭宗欲见翰林学士,事前须侦探学士院使是否监院,学士院使监控皇帝与翰林学士的职能,可见一斑。
三、结论——兼谈内诸司的决策角色
由上可知,唐代翰林学士院的构造与职种关系密切,从翰林院分出学士院,特设翰林学士,本来就是因应宫廷地理建置的政治考虑。唐中期以后的君主,鉴主宦官权势日益高涨,每欲兴起另一私人渠道,寻求政治意见以相援引,学士院供职的翰林学士,正好补救了宰辅未能于禁内议政决事的角色,并且在既合作且冲突的微妙决策层面上,继续与北衙官司发展工作关系。翰林学士所以能谓内相,在于获得与帝王密议机会,又于制诏降麻的过程中发挥己见,从而成为参与中央决策不可或缺的法理依据者。此种身份,并非一般擅夺权力的宦官可以取代,形成制控宦官权限的一股法治力量,故此越引致宦官于翰林置使,作出反制控翰林学士的主因。
无可否认,南北衙互相对峙为时甚久,但彼此权力高下立见。从神策军进驻中央禁军开始,北衙使职机构日益繁衍,中央诸部寺监权力欲遭侵蚀,南衙诸卫兵徒具空名而已。中晚唐君主的废立几全操阉宦之手,已反映君主权力、宰相南衙实职不足与内官争斗。故君主倚重翰林学士,其实是在既定的形势下,确保北衙官司仍在一定程度上服膺南衙宰相的律令制度。翰林学士专掌草诏白麻,即根本代表帝王与宰相发号命令,宦官不得私夺的最高精神。宦官既不能像翰林学士草诏,惟有假以其他途径夺权,例如变更议定决策的原貌,加入修订程序,或者垄断宣令的最终过程,得以上下其手。凡此,解释了越到唐代后期,内诸司的机密、宣徽之职越具代表性。
唐末两枢密与两神策合称为“四贵”,包括中央重要决策,机密于代宗时只管理文书表奏,进呈皇帝参阅,到僖、昭时期权力至盛,由于可在堂状贴黄,无形即代替君主处分公事,宣付中书门下施行。[11](卷58《职宦十二》)枢密既能随时改动决策内容,自然无须屈于过去先由宰相奏对延英,然后纯粹承受公事的角色。[1](卷262,天复元年正月)同样道理,宣徽使于代宗时期亦已存在,惟逐渐能总领内诸司,活跃于郊祀、朝会,与其承传宣旨的职能颇具关系。由于获得宣令之便,故亦能随时矫诏,为更改决策的另一员。《东观奏记》卷下记载的其决策层的论议方式,迹近滥用权力:
上(宣宗)大渐,顾命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上院使王居方,以夔王当璧为托。三内臣皆上素所恩信者,泣而受命。时右军中尉王茂玄,心亦感上。左军中尉王宗实素不同,归长、公儒、居方患之,乃矫诏出宗实为淮南监军使,宣化门受命。将由银台门出焉……宗实叱居方下,责以矫诏,皆捧足乞命。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郓王于藩邸即位,是为懿宗。[12]
在唐后期常见的政变中,神策护军中尉以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控制最后大局,成为枢密、宣徽等中央决策要员靠拢的对象。归长、居方等矫诏,是右军中尉王宗实政治反扑的口实,而宗实亦以同类的手法,透过另一宣徽使宣诏改立新主。唐末枢密、宣徽主宰诏旨,已非中书所能控制,原则上决议程序应于延英,由宰相、枢密共商,但后来变成枢密、宣徽直接决定宣行,形同有效决议。《资治通鉴》卷250懿宗咸通二年二月条:
一日,两枢密使诣中书,宣徽使杨公庆继至,独揖(杜)悰受宣,三相(毕诚、杜审权、蒋伸)起,避之西轩。公庆出斜封文书以授悰,乃宣宗大渐时,请郓王监国奏也。且曰:“当时宰相无名者,当以反法处之。”悰反复读……复封以授公庆,曰:“主上欲罪宰相,当于延英面示圣旨,明行诛谴。”公庆去,悰复与两枢密坐,谓曰:“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两枢密相顾默然,徐曰:“当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无人及此。”渐涑而退……既而寂然,无复宣命。[1]
宣徽握宣命之权,变相为直付中书执行的政令,公庆出示斜封文书,即欲面命宰相听从,已超越正常的议事步骤,故非宰相杜悰所能接受。如前所述,若为内制诏令,应由宰执延英决事后,由翰林学士制出,方为合法程序。杜氏以此究之,枢密、宣徽固然无复宣命,但议政的被动性当越为明显。文中并无提及文书草拟工作,是否由翰林学士院中人协助,然而从上记翰林学士韩偓草制时的消极抵抗,以及翰林、宣徽、枢密等内诸司使院权力高涨观之,宦官群已建成自身独立的决策系统,渐次摆脱翰林、宰相的牵制。
收稿日期:2000-06-08
标签:翰林院论文; 宦官专权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旧唐书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雍录论文; 大明宫论文; 白麻论文; 太和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