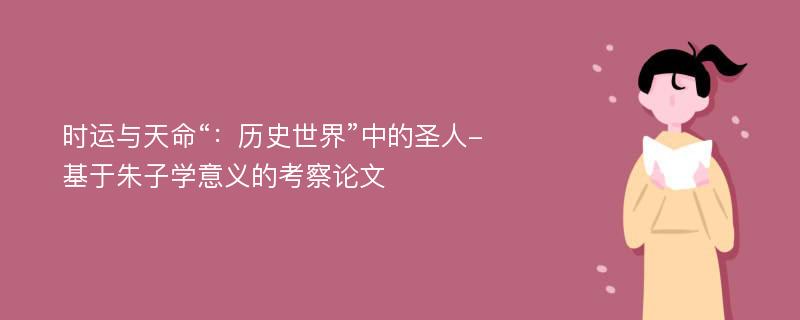
时运与天命“:历史世界”中的圣人
——基于朱子学意义的考察
王新宇
(香港科技大学 人文学部,香港 999077)
[摘 要] 作为人文世界的绝对者,圣人在“历史世界”中的遭际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这是朱子“理气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然而,正因为圣人完全地体现了天理,故而在遭逢“时运之变”之时,可以时刻把握住其后所贞常不变的“天命”,并以之作为一切出处进退的根据。这是朱子学意义下圣人的核心精神,也是儒家圣人的终极指向。本文即将从“时运”与“天命”两个方面探讨朱子学意义中处于“历史世界”中的圣人。
[关键词] 朱子;时运;天命;圣人;理气
在理学语境中,圣人是人文世界的完全者,圣人完全体现了“天理”,从而为学者之楷模。同时,圣人也与常人一样,具有“仁义礼智之性”与“五脏百骸之身”,朱子说:“圣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1]798圣人与“天理”合一,自无疑问。然圣人终究是人,虽是赤骨净尽,亦难免形质之累,若无形质之累,则与宗教之神无二。圣人同样禀受天地之“理”与“气”,因其禀受“天理”之正、“气质”之纯,故为圣人。然“气”甚为复杂,并不如“理”纯粹,人所禀受之“气”会遇到种种问题,于是在“理”之外,又要说“命”。朱子说:“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1]82“命”乃是人所得之于天者,天有理有气,则人所禀受之“命”亦存在理气之交织,本文所说的“时运”与“天命”,便是圣人在此交织下的表现。在二者的交织之中,圣人已经不仅仅是一片洁净空阔的天理,而必然羼杂时运与气数之变,但正是处在这样一种“历史世界”中的圣人,才真正显示出其作为中国传统人格精神之最高典范的意义与价值,后学者所倾慕与崇敬的,也正是这样的圣人。本文即将从“时运”与“天命”这两个维度着眼,以朱子学为考察核心,试图勾勒出儒家处于“历史世界”中的圣人样貌。
一、时运之变
(一)圣人之遇
圣人与所有人一样,都需要经历在真实的“历史世界”之中,而此一所谓的“历史世界”,必定伴随着天地之“理”与“气”的交相作用。事实上,“理”作为提供天地化生之所以然的根据,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到大化流行的过程中去,天地流行,皆一气所为。正如张子在《正蒙》里所说:
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絪缊,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与!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其感遇聚结,为风雨,为霜雪,万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结,糟粕煨烬,无非教也。[2]8
这里都在说一气之流行。虚实动静、阴阳刚柔,皆由此“气”而成,而浮降清浊,乃至于糟粕煨烬,亦莫非此气运动之结果。朱子解释说:
阴阳即气也,岂阴阳之外,又复有游气?所谓游气者,指其所以赋与万物。一物各得一个性命,便有一个形质,皆此气合而成之也。[1]2508
天地与圣人都一般,精底都从那粗底上发见,道理都从气上流行。虽至粗底物,无非是道理发见。天地与圣人皆然。[1]2508
此本只是说气,理自在其中。一个动,一个静,便是机处,无非教也。教便是说理。[1]2506
朱子意,天地之间皆为气化之流行,赋于人物则为人物之性,而此性中有精有粗、有善有恶,正如天地之气有粗有细、有精华有糟粕。圣人同于天地,故而与天地一样,其“理”是“气”之所以然,却必须依傍于“气”而后发见,而气之粗者,同样不可以说不是道理之所有,因为理在气中、不在气外,“糟粕煨烬,无非教也”,莫非至理之所寓。既然如此,圣人与天地同此一气,天地有罅隙,圣人自然也难免遭受气禀之偏,那么圣人在进入到复杂的历史世界之中时,就难免会遇到种种问题。天地之气化流行、阴阳动静,以至于生出了糟粕之气,难道不是“理”之表现吗?“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圣人处在此一理气交织的情势之下,必然会受到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由此,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圣人同样会遇到各种与道理相违背的人生遭际和处境:尧以圣王之德而有不肖之子丹朱;舜以大圣之资而有瞽叟这样的父亲、象这样的兄弟、商均这样的儿子;汤武皆为圣人,圣人本应以仁德定天下,汤武却不得不“革命”,乃至于“血流漂杵”;周公至圣,开辟守成,却不得不铲除同为宗亲、且正是由自己所设立的“三监”;孔子“贤于尧舜”,但又终身不遇,栖栖遑遑如丧家之犬……处在“历史世界”中的圣人,他们的遭际和处境往往看似都是违背了“天理”的。照理说,圣人应该处处体现出与此至善天理的贴合,为何还会产生出种种不如意甚至是大变故?朱子说:
上古天地之气,其极清者,生为圣人,君临天下,安享富贵,又皆享上寿。及至后世,多反其常。衰周生一孔子,终身不遇,寿止七十有馀。其禀得清明者,多夭折;暴横者,多得志。旧看史传,见盗贼之为君长者,欲其速死,只是不死,为其全得寿考之气也。[1]79
气禀之差别、气数之盛衰,圣人与常人一样都会有所禀受。盗跖可以“得寿考之气”,圣人却不能;然圣人得天地清明之正气,盗跖则绝不能。对于圣人而言,禀得气之不善者乃是天数时运使然,而圣人所做的,则是将自己所禀受的天地之正气,发挥到了无以复加,从而淋漓尽致地散落于天地之间。因此,朱子之“理气论”在为圣人之遭遇找到了合理解释的同时,更加强调学者应该去关注圣人是如何在此遭际之变动不居中,体现“天理”之至善的。
(二)圣人处变
圣人言“命”,是针对子服景伯、子路和公伯寮而言的,对于孔子来说,则此“命”并不能决定孔子的泰然与否。圣人准之于“天命”之至当,此气质所为之“命”无以动孔子之心。《论语》的另一章则更为明显地表现出孔子对“天命”的承当:
“尧之让舜,禹之传子,汤放桀,武王伐纣,周公诛管蔡,何故圣人所遇都如此?”先生笑曰:“后世将圣人做模范,却都如此差异,信如公问。然所遇之变如此,到圣人处之皆恁地,所以为圣人,故曰‘遭变事而不失其常’。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公且就平平正正处看。”[1]909
历史上的圣人确实都存在着不尽完美的时运,甚至都处在重大的人事变故之中。朱子说:“后世将圣人做模范,却都如此差异,信如公问。”对于常人来说,圣人是“模范”,既是模范,必然倾向于全知全能,与圣人有关的一切也都应该显现为“理”之所当然,可事实上却并不如此。这就是儒家传统中圣人之突出处,圣人并非宗教意义上的神,宗教上的神丝毫没有“人心”的作用,“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3]25,却不是“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3]23。圣人则与常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经历着同样的历史、感受着同样的善言善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正在于“遭变事而不失其常”,常人未及其变,却往往已经自行隔绝了道理。圣人则“心与理一”、聪明睿智,本来如是,且在遭逢变故之时体现得更加鲜明:
尧不以天下与丹朱而与舜,舜能使瞽叟不格奸,周公能致辟于管蔡,使不为乱,便是措置得好了。然此皆圣人之变处。想今人家不解有那瞽叟之父,丹朱之子,管蔡之兄,都不须如此思量,且去理会那常处。[1]307
综上所述,在产后妇女盆底功能康复治疗中加入护理干预措施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临床康复效果,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推广。
泰伯文王伯夷叔齐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底道理。太王汤武是吊民伐罪,为天下除残贼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变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实只是一般。[1]909
圣人逢变,能全其常道,此所以为圣人。至于常人,却常常在遭逢事变之时即滑落到道理的反面去了,更不用说类似后世五霸、汉祖、唐宗等,皆是假仁义以行其私,在遭逢时运之变时,也往往是从自身的私利出发而非“天理”,这正是其与圣人大为不同之处,而朱子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4]1592,也正是这个道理。圣人尽管会遭逢事变之无常、经历时运之盛衰,但无论如何都不变自己“心与理一”的本然状态。对于学者来说,学者尚未如圣人那样达到“心与理一”的理想境界,那么对于圣人之处变的理解则应该根据自己的目前的修养而有所限度,因此朱子常常劝勉弟子“且就平平正正处看”“且去理会那常处”,如果学者在尚未做到于常道之下处置得当的时候,就去处变,那么很容易丢失自己本心之中的“理”,这对修养是极为有害的,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3]3,正是此理。分析并体认圣人之处变,通常需要涉及复杂的历史实事,而历史最讲利害得失,如若对常理还做不到持守便去处变,往往会舍本逐末,所以朱子教学者“先经后史”。学者必须首先做到“共学”“适道”“与立”,方才可以“与权”[3]117。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朱子所以不希望学者对圣人处变进行过多的研究,尚且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圣人本身在进行处置的时候,也难免会存在难以尽善尽美的情况,这是人生气禀的无奈,也是时运所在之必然。例如朱子注解《论语》之“子谓韶”章时说:
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3]68
孔子认为,相比于《韶》乐的尽善尽美,《武》乐则未能尽善,这一差异其实就体现出同为圣人的舜与武王的差别。首先,朱子引用孟子所说的“性之”与“反之”,表明这是由于二者“气禀”之不同。舜气质清明纯粹,合下完具此“理”,故而完全地不加修为而能成其善性。武王虽然同是圣人,却经过了一个“反之”的过程,尽管最终也达到了“心与理一”,但终究不如舜之自然。其次,在历史的层面,舜揖逊而有天下,武王则是凭借征伐,相比而言,自然又未能做到“尽善”。朱子对造成这个事实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尧舜之禅授,汤武之放伐,分明有优劣不同……且如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胜殷杀纣,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让,其可谓至德也矣”!分明太王有翦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盖天下有万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权一时之变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处,即是变也。然毕竟还那常理底是……以圣贤比圣贤,则自有是与不是处,须与他分个优劣。[1]1365
汤武放伐与尧舜禅授之间分明存在着优劣的不同,此即孔子“尽善尽美”之说。至于存在这种优劣的原因,则在于天下同时存在着“万世不易之常理”和“权一时之变”。对于汤武来说,他们的本心未尝不想同尧舜一样,揖让而有天下,但当时的历史恰逢时变,桀纣为虐,生民有倒悬之危,社稷有累卵之急,如果还守着“君臣父子”之常道,对于时变可能就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所以程子曰:“成汤放桀,惟有惭德,武王亦然,故未尽善。尧、舜、汤、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时然尔。”[3]68时运的因素使得他们的做法存在了差异。但同时,在同样的时运之下,不同的圣人也有着不同的选择,如同泰伯之与太王、文王之与武王,朱子说:
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见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翦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于泰伯,则惟知君臣之义,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从。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圣人未常说一边不是,亦可见矣。[1]909
圣人无论做出何种选择,其出发点都是义理之公而绝非人欲之私,至于或“不从”、或“翦商”,则是圣人在遭逢时运之变时“各行其心之所安”所做出的选择。在时运之变的情况下,任何的选择也许都是无奈之举,但却只有圣人才能将之措置得更为妥当,这依然是因为圣人做到了“心与理一”。尽管如此,时运之变,仍旧是圣人之不得已处:
如“可与立,可与权”,若能“可与立”时,固是好。然有不得已处,只得用权。盖用权是圣人不得已处,那里是圣人要如此![1]1365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3]98
天地与圣人同此一气,非惟圣人,众人皆然。天地之气有精华有糟粕,人所禀受之气自然也难免不齐,加上时运之变、气数之异,皆是人之无可奈何处:
问:“尧舜生丹均,瞽叟生舜事,恐不全在人,亦是天地之气?”曰:“此类不可晓。人气便是天地之气,然就人身上透过,如鱼在水,水入口出腮。但天地公共之气,人不得擅而有之。”[1]76
气散在天地之间,非人所能独有,天命人以“理”,又授人以“气”,皆公共之物。理气交杂,在人文世界中就变化出丰富的历史,圣人和常人同时处在这样一种变动不居之中,而圣人所以不同于常人的,在于圣人时时刻刻以“理”来衡量措置一切事物,尽管圣人也注定要经历这一复杂的世界。
综上,本节所论述的焦点,在于解释圣人何以也会受到气禀、时运等因素的限制,并分析圣人处在“历史世界”的变化无常之中的时候,是如何体现其作为圣人的至善之理的。这个解释是立足于朱子学的。就朱子个人而言,他对圣人的这些体会都已经进入到了学问的深层次,是在“常道”之外对于“权变”的体会和理解,所以这部分的意思常常是十分复杂的,义理也颇为艰深,很难为初学者所理会。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在日用常行与圣贤经典之中,体会圣人之学。
二、天命之常
时运之变成为左右圣人的力量,圣人受此影响,也往往显得无可奈何。圣人的伟大,在于身处这样一种变化之中而能以常理常道处置事物,使得气数与时运的影响不足以动摇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选择,这皆因为圣人禀受了“天命”之正。圣人与常人一样禀受了天地之间的不齐之气,领受了因此造成的种种遭际与变故,但更为关键的是,相比于常人,惟有圣人之心最完满地体现了“天理”,故而只有圣人得以最完全地实现对“天命”的禀受与体知,“知天命”对于圣人来说是自然而然、不待勉强的。因此,圣人可以在复杂多变的气化流行之中保守住自己的“天命”之常,而尽己之心去做“天命”所当有之事,这是圣人的使命与职责,更是“天理”所赋予圣人的必然选择。对于圣人来说,无论外界的变化如何复杂,无论事变的结果如何不利,也依旧是“无不可为之时”[3]159,这是圣人体知“天命”的结果,更是因为“天理”之恒常不变而为人文世界得以成立的根本保证。圣人,则是此“天理”在人格精神中的完满彰显。
(一)圣人知命
前文已知,圣人与常人都禀赋了天所赋予之“命”,而此“命”则因为天地同时具备所以然之“理”和实然之“气”的缘故也被分成了两种:
“旅游、建设、发展”3个词汇的占比较之其他高出许多,且近3年呈现逐年大幅增长的趋势,说明历史文化村镇的建设和经济发展受到专家的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较之“资源保护”,“活化利用”在历史文化村镇保护工作中占比越来越大。“旅游”一词热度居于首位,说明旅游成为历史文化村镇近年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命,谓天之付与,所谓天令之谓命也。然命有两般:有以气言者,厚薄清浊之禀不同也,如所谓“道之将行、将废,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则为仁义礼智之性,如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谓性”,是也。二者皆天所付与,故皆曰命。[1]1463
既然天地之造化皆一气之所为,“理”只是依傍此气而行之所以然,在造化的过程中,“气强理弱”的情形是甚为平常的,故天赋人以“命”也是气化流行的自然运动过程,而“理”即在其中。因此,人之“命”也可分为两种:禀受于天地之正理者则为“天命”,此“命”主于“理”,在人则为仁义礼智之性;禀受于天地之厚薄清浊者亦为“命”,此“命”则主于“气”,在人则有智愚贤不肖的差别,乃至于贫富、贵贱、寿夭之不同等。前者因主于“理”,故而是道理在人身上的展现,所谓“天命之谓性”,是纯善无恶的。后者因主于“气”,故而并不能确定在人身上表现出的是善还是恶、是福还是祸,此“命”因为气禀之不齐而产生出种种不确定性。两种“命”交相作用,成为人之所禀受。朱子同时说,这两种“命”虽然有其所主之不同,要之,皆是统一在一起的:
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3]356-357
命之正者出于理,命之变者出于气质,要之皆天所付予。[1]78
安卿问:“命字有专以理言者,有专以气言者。”曰:“也都相离不得。盖天非气,无以命于人。人非气,无以受天所命。”[1]76
理气既然不离不杂,有是理必有是气,所以天所赋予人之“命”也必然是理与气结合相伴而成,否则便无法解释人何以同时具有“仁义礼智之性”和“五脏百骸之身”,这是自然的结果。对于圣人而言,必然也会同时受到这两种“命”的影响,正如上节所说的,圣人也会受到气禀形质之累、气数时运之变一样。圣人所以为圣人之处,并不是绝离了气质以及此气质所主之“命”,而在于圣人能够体知“天命”,能够时刻以“天命”所寓之“理”为主,从而使得主于气质的这个“命”反而无法成为左右乃至宰制圣人的力量: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3]159
这是《论语》中一条著名的记录。孔子并不以公伯寮的谗言为意,公伯寮之“愬”即便可以得逞,也是命当如此,此“命”乃是主于“气”的气运之势,并非公伯寮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事情的发展。孔子的意思是,虽然自己存在被公伯寮谗言陷害的危险,但或有或无,都是“命”所使然,在孔子自身而言,则并不会受此“命”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意志。因此朱子说:
言此以晓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圣人于利害之际,则不待决于命而后泰然也。[3]159
道路交通量的统计和轴载的计算影响着交通载荷作用的确定。按照JTJ014—199《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和JTGD30—2004《公路路基设计规范》[4-5]从车辆类型组成、轴组组成和轴重、交通量及增长率等方面进行交通数据调查,对交通荷载作用进行量化确定。
上文已知,圣人与常人一样,因为禀受了天地之气而存在着气禀的不同,又因为与天地同此一气而会遭遇种种事变。既然如此,圣人之所遇便必然不会如同“天理”的世界那样洁净空阔,而必然充满了“历史世界”的时运之变与气数之杂。这个问题在朱子的弟子那里就已经成为困扰:
2.2.4 MRI 完成MRI检查者62例,其中MRI异常15例;其预测神经系统不良预后的灵敏度为61.5%,特异度为85.7%,阳性预测值为53.3%,阴性预测值为89.4%。
小说的“摹士”一节,人物关系集中在太子丹之与麹武、田光、荆轲三人之间的递接,即由麹武引出田光,由田光引出荆轲。从提炼主题的角度,可关注他们所共同呈现出来的精神气概。
本文所开发的电动机适用于上海振华港口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风电齿轮箱试验台(ZP11-1627)所用的变频电动机项目。该项目采用的变频器为ACS6000,最大输出电压为3 100 VAC。用户对电动机的基本参数要求如下。
父亲说:“小锦,不是爸不支持你,你先康复锻炼,不用急着赚钱。我暂时还回不去,这树坑挖一多半了,明年一开春就可以种树,哪能半途而废……”
孔子在面对可能来临的危险和迫害,并没有丝毫慌乱不安。这并非常人“暴虎冯河”之勇,而是一种对“天命”承当于己身的自信。“天生德于予”,圣人之德与天等同,桓魋既然无能有损于天道,则自然也无能有损于圣人。朱子说:
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赋我以如是之德,则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违天害己。[3]98
所谓“天既赋我以如是之德”,即是圣人所禀受之“天命”,桓魋纵使蛮横,不过血气之强而已,终究是无法违背“天命”而加害于孔子的。圣人的自信,完全来自于自己对“天命”的承当。圣人承当“天命”,是因对“天命”已经有了彻底的体知,所谓“知天命”,便是圣人对“天命”体知的证明。对于圣人来说,“知天命”作为学问之序的一部分当然是“自然贯通”而不假勉强的,圣人因为天生地具有“心与理一”的状态而自然能够通达“天命”之所在,因此当圣人遭受到气质之命的影响和限制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地以自己所知之“天命”来宰制气质所有之“命”,从而不为其所动。
然而,气质所主之“命”也是天所赋予,因而亦不得不谓之“天命”,而由此“命”所影响的死生夭寿祸福,乃至于出处进退的一切变故,都会受到这一“天命”的影响,虽圣人亦不能免。否则如何解释朱子所说的“衰周生一孔子,终身不遇,寿止七十有馀”?只是,在死生夭寿祸福的限定之下,圣人依然是用自己禀受于“理”之正者的“天命”,去宰制自己不得不禀受的“气”之偏者的“天命”。孟子说:
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3]356
命有两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样;“天命之谓性”,又自是一样。虽是两样,却只是一个命。[1]1360
孟子这两句话虽然是对学者而言,但对于圣人来说也是如此,圣人区别与学者的,只是一个自然、一个勉强。对于圣人来说,夭寿祸福,莫非命也,圣人也只是“顺受其正”,“正命”便是主于“理”的天命。人能顺“理”而行,即是“顺天命”,亦是“正命”,朱子说:
“夭寿不贰”,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当;百年未死,百年要是当,这便是“立命”。“夭寿不贰”,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养性之功。[1]1429
由于乡村居民点缺少规划指导,建设混乱无序,居民点内部道路布局不合理,村庄内部缺乏对环境的营造,整体景观效果较差。由于居民点比较分散且农村人口流失较多,因此农村居民人均建设用地严重超标。乡村居民点建设用地相差较大,土地浪费严重。北部山区有大量空置房屋,有些甚至已经倒塌,破败不堪,占用了大量土地。
圣人禀受了“天命”之正,所以才义无反顾地为此使命而去努力,无论其所遭遇的是顺境还是困厄、是“乃命以位”[5]72还是栖栖遑遑。这一切都是天之所命,理之所有,在他人看来也许是“知其不可而为之”[3]159、是“凤兮凤兮,何德之衰”[3]184、是“天之戮民”[6]149,但在圣人处,此皆“莫非命也,顺受其正”的自然结果。因此,这就可以领会为何圣人在衰世乱世之中仍然汲汲于救世安民,而并不去关心常人所重视的机会利害。在圣人而言,其最大的“天命”便是治民教民,使天下之民皆能复其天生之善性,即便是最坏的乱世、最坏的人物、最坏的事情,也必定有至理在焉,因此都存在变化的可能。例如,《论语》记载了公山弗扰和佛肸两人欲召孔子为己用的故事,二人皆乱臣贼子,常人要么会以其不可以有为而避之不及,要么会迫于他们的威势而不得不降志辱身。对于圣人来说,却可以在做到“吾其为东周乎”[3]178的同时“磨而不磷”“涅而不缁”[3]178。朱子在注解的申论部分分别用程子和张南轩的两句话来说明这个道理:
3.3.4 实验室嗜酸性粒细胞检查 急性期周围血中嗜酸性粒细胞常达15%以上,因而引起白细胞总数的增高;而非急性期也可呈现轻度至中度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白细胞总数大多正常,但是随着病程后期贫血日趋显著,嗜酸性粒细胞的百分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15]。本研究结果表明嗜酸性粒细胞数或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升高共53例,对于不能从粪便中检出虫卵,结合流行病学史、血中嗜酸性粒细胞数或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升高和临床症状者,是否可以诊断性驱虫治疗,由于本研究病例数局限,还需进一步大量临床研究。
圣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便能赞化育。尧之子不肖,他便不传与子,传与舜。本是个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转,转得好。[1]1360
孔志浩没走多远,师直机动大队的人马就赶了过来,几个宪兵见了丢魂落魄的孔老一往后跑,二话不说,将他捆了个严严实实,孔老一也不言语,用死鱼白眼盯着他们。一个宪兵好奇,夺过包裹,一下被蛇咬了似的尖叫起来,衣服里的老三好像也尖叫了一声,滚出一丈多远。
如孔孟老死不遇,须唤做不正之命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1]1434
圣人能够将天所赋予的不好的“命”转化为正理,而圣人所禀受的不正之命却因为圣人的“顺受其正”转而“有差”,这就是圣人德性的伟大力量,也是“天理”至善的无穷力量。在复杂多变的“历史世界”之中,“天理”往往被遮蔽而显得“气强理弱”,圣人也因为受到各种气数时变的影响而显得无可奈何。但终究“天理”才是天地万物得以正当存续的所以然,圣人则是人文世界得以正当存续的所以然,如果没有了“天理”与圣人,则天地终将是一个无理的躯壳,人文也必然是一个无理的世界。朱子心目中的圣人,是人文世界的绝对者,圣人最终扭转了“气强理弱”的颓势,使得人文世界得以始终贞定着“天命之常”。
(二)圣无不可
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3]1
在气质之“命”的影响之下,常人往往难于“顺受其正”,这是因为他们对“天命”没有真切和完整的体知,惟有圣人自然地完成了这一过程。圣人不仅是“天命”的体知者,更是承当者,圣人肩负着“天”所赋予的使命:
我国目前针对“机动车”范围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认定,一般认为以燃烧柴油或者汽油作为动力装置的车辆属于机动车的范畴,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已经无法满足目前的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司法实践。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很多以燃气为动力的车辆,这些也应该属于机动车的范畴。同时目前我国很多人选择电动车出行,市场上的电动车五花八门,很多商家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对电动车的最高速度、重量等都进行了违法修改,这些车辆的驾驶者一旦出现醉酒驾驶情况同样也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笔者认为在日后的立法当中需要进一步扩大机动车的范围。
校园建设中,对安全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对网络设备的投入,而且还体现在对安全维护人员配备上。国内大部分高校,没有专门的编制去配备网络安全人员。网络中心的工作人员只是负责服务器、存储设备的基本维护。导致一旦发生安全问题,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快速处理。
人的祸福夭寿自有“天命”在此,而人所应当做的惟有做到穷尽“天命”所有之“理”。圣人正是做到了己心能够完满地体现“天理”,故而圣人也完全地做到了“顺受其正”,甚至在圣人处,主于“气质”的“命”反而成为了不正之“命”,此皆因圣人纯乎一理,而“理”最终是胜“气”的:
程子曰:“圣人以天下无不可有为之人,亦无不可改过之人,故欲往。然而终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3]178
张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闻,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圣人体道之大权也。然夫子于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无不可变之人,无不可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终不可变而事之终不可为耳。一则生物之仁,一则知人之智也。”[3]178
圣人之欲往,在于“天人无不可变之人,无不可为之事”,人皆有天命之善性,又岂无变化复性之理?圣人之仁,“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又安有见人之尚未复其善性而不救之理?这是圣人因其所受“天命”而产生的自然使命。然而,圣人终于不往,乃在于不可因为一味地希望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不分权宜和方法,既然“天下无不可有为之人”,也无不可有为之时,则需要时时根据时宜来调整自己的选择,圣人的出处进退时时刻刻都与“天理”合拍,无论其做出何种选择都是对“天命”的承当,这当中尽管会受到时运之“命”的干扰而无奈,但依旧是“无可无不可”[3]187的。“理”之主宰“气”、圣人之决定人文世界的方向,皆须从此处理会。朱子对于圣人“无可无不可”的出处进退作出详尽的阐释:
圣人于斯世,固不是苟且枉道以徇人。然世俗一种说话,便谓圣人泊然不以入其心,这亦不然。如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个是十分要做不得,亦有不能自已之意。如说圣人无忧世之心,固不可。谓圣人视一世未治,常恁戚戚忧愁无聊过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忧世之心要出仕者,圣人爱物之仁。至于天命未至,亦无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上看,恰似一向没理会,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漫去做看,这便不得。须看“行其义也”,便自是去就。出处之大义,亦在这里。[1]1184
圣人的忧世之心,即所谓“生物之仁”,这是当然不容已的。然气数之变常会成为圣人也难以避免的“命”,恰似前文所说。如夫子之不遇鲁公,而阳货、公山、佛肸皆乱臣贼子,反乃欲召孔子而用之,这是时运使然,无可奈何,然而如果要圣人枉道从人,却绝无可能,圣人之心一之于“理”,出处进退必以“理”为准则。只是,生活在真实而无奈的历史世界中的圣人,一旦遭遇时运之变,也一定不会“戚戚忧愁无聊过日”。圣人的“天命”就在于“先觉觉后觉”,怎么会舍天下而弗救?这也是儒家圣人与宗教之神不同的地方,与常人乃至于贤人隐者,也存在着根本的距离。宗教之神不存在气质之“命”的限制,而是完全宰制且抽离于人文世界的绝对存在。贤人隐者则往往守定自己所遵从的道理,却不能根据时宜来做出符合“天理”的至当选择,故而也只能成其一偏之德。至于常人,则往往因其对“天理”没有根本的确信、认知和持守,导致他们在时运的变化之中丧失了对道理的坚持,成为大化流行中不自觉的知觉主体。这也是为什么孟子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3]320圣人对“天命”的承当完满地做到了“顺受其正”,故而其在历史世界中的一切选择和行为都是符合道理和时宜的,此其所以能成为“集大成”者。这段话中,朱子对“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的解释正恰反应了圣人的这一特征。“道之不行”,是时运之变所导致的正常结果,圣人亦常作如此感叹,然而圣人终不会因为道不能行而不行其道,也不会因为时运之不义而不行之以义,这正是“出处之大义”。于是,受到“命”所限制的圣人最终所表现出的正是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精神,圣人完满地体现了“天理”、完全地承当了“天命”,故而可以突破时运之“命”、气质之“命”的局限,将自己的全副生命投入到行道传道的事业中去。
必须指出的是,朱子对于圣人之“命”的体认,完全出于自己的生命感知。朱子一生不仅在学问上力求“学为圣人”,在出处之道、行为事业上也时刻以圣人为唯一的标准。朱子一生为官朝廷之日不多,多数时候都是为官一方或在野讲学,这是朱子根据道理与时宜所做出的选择,而当遭遇了人生重大变故之时,朱子更是以圣人之“命”来衡量并要求自己。“庆元党禁”作为朱子晚年所遭遇的最大挫折,正可以成为学者体会朱子的“学为圣人”之路。
事实,并不像老鳜鱼想象的那样简单。四细狗不但没有吃枪子,蹲也没蹲,进去几天之后,就出来了。上级给他定性是通奸。不过,他的村长是干不成了。
在庆元党禁中,朱子被“落职罢祠”,一时所焚烧之“伪学”书籍,不计其数,受牵连者更是史所罕见。[7]1272-1318朱子此时已经六十八岁,所处之人生际遇,较之孔子,几更险恶。黄勉斋《朱子行状》载:
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8]515
时势如此,人心亦可从而见之。于是:
或劝先生散了学徒,闭户省事以避祸者。先生曰:“祸福之来,命也。”[1]2671
“祸福之来,命也。”此处之“命”,即是上文所说的气质之“命”,气数所运,人岂能料?故朱子不为所动。又载:
有一朋友微讽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于予’底意思,却无‘微服过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书自辨,又不曾作诗谤讪,只是与朋友讲习古书,说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论语》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断章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1]2670
朋友说朱子有“天生德于予”之意,即称许朱子面对困厄时所展现出来的信念,微讽朱子无“微服过宋”之意,是奉劝朱子应该像孔子一样“避祸”。朱子则说自己所做的仅仅是“讲习古书,说些道理”,无论是自己还是孔子,无论“避祸”与否,都是依准于理之是非,而绝无一毫私念计度。对于圣人来说,一切的行事准则都以“理”为先,也只有如此,才能突破并转而主宰时运之命的限制。朱子进而说到:
今为辟祸之说者,固出于相爱。然得某壁立万仞,岂不益为吾道之光![1]2671
朱子对于圣人之学的坚守于此可见。气质之“命”并非人力可以直接左右,然而“吾道之光”,则完全乃儒者生命之所系,只有“壁立万仞”,才能使义理之“天命”宰制气质之“命”,进而将圣人之道传续广大。
通过对朱子处“变”的简单介绍,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朱子对圣人在时运之变与天命之常中的所行所止的体认。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地知晓,对于圣人和一切立志从事于圣人之学的学者而言,虽然必定会受到气质之“命”的复杂影响,但只要“修身以俟之”“顺受其正”,时时以“理”来衡量、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则终将可以突破此气质之“命”的框限,并最终体知到至当“天命”之所在,而用自己的生命来完成对此“天命”的践履。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完成了一个道义的人生。圣人,便是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的人。
总结本节所论,圣人在复杂多变的时运与气化之中,与常人一样会面临着困难的遭遇,这是天赋予人以“命”时所本来具备的。圣人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时时以道理宰制气质之“命”,做到变而不失其常,使得圣人之“命”完全体现为对主于道理的“天命”的承当。朱子的理解正是结合了其理气论,圣人置身于理气交织的“历史世界”中,以理主气,从而可以时时面对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举措得宜,并且实践着自己禀受于“天命”的行道事业。正如仪封人所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天下无道,乃时运使然,却并非“天理”之常。圣人处此变故,必有以匡扶补救。“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正是说明处在时运之下的圣人肩负着“天命”之常道,天下也正因为有圣人,才能在时运不济、气数衰微、人道沦丧之时,不至于斯文扫地、道统失传。朱子的理解,也正是有本于他自己一生的学问与遭际,真切地体会到了圣人之道。对于学者来说,只有用力于格物穷理之学,努力做到使自己的“心”与圣人之道逐渐贴合,才有望在时运的变化中,不致迷失自己的本心、遗忘自己所赋的“天命”。
[参考文献]
[1]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朱熹.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5]孔颖达.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成玄英.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8]王懋竑.朱熹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
Fortune and Destiny:Sages in the Historical World—On Account of the Meaning of Zhuism
WANG Xiny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ong Kong 999077,China)
[Abstract] As the absolutes in the humanistic world,Sages are always in the midst of changes in the historical world.This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in Zhu Xi's theory on Li and Qi.However,as Sages absolutely embody the Heaven Principle,they can always grasp the constant Destiny that could be the ultimate spirit behind the Fortune,and then use this spirit as the reason of their behaviors.This is the core spirit of Sages in Zhuism and the ultimate aim of Sages in Confucianism.This paper discusses Sages in the historical world in the discourse of Zhuism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Fortune and Destiny.
[Key words] Zhu Xi;Fortune;Destiny;Sage;Li and Qi
[中图分类号] B24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2991(2019)04-0055-08
doi: 10.3969/j.issn.2096-2991.2019.04.008
[收稿日期] 2019-04-25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5M581033)
[作者简介] 王新宇(1991—),男,江苏镇江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201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学,朱子学与宋明理学。
[责任编辑 刘笑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