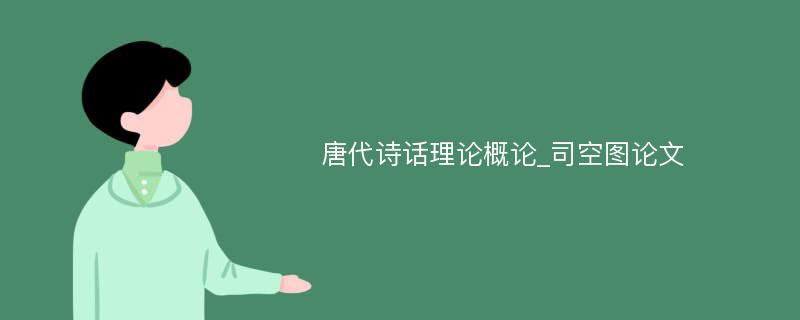
唐代诗话理论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诗话论文,唐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在唐以前就有了诗学传统的渊源。它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是从先秦著作中的论诗之语到《诗大序》、钟嵘的《诗品》等论诗专著;一是从先秦著作中有关诗事的记载到《诗小序》、《世说新语》中有关诗人言谈轶事的记载。这些都为唐以后诗话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唐代大量笔记小说中有了诗人奇闻轶事的记载,并由笔记小说发展分化,出现了纯粹记录诗人言谈遗事的本事诗,成了唐代诗话的前身。本事诗之后,唐代出现了用笔记体写成的、集记事和评诗为一体的诗学著作——诗话。它以轻松灵便的笔调,随笔漫录;以亲切平易的文风,道出重要的诗学内容。
根据何文焕《历代诗话选》和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所辑,唐代诗话有皎然的《诗式》、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孟棨的《本事诗》、旧题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 五代齐已的《风骚旨格》。其中,值得注意的有《诗式》、《二十四诗品》和《本事诗》,它们是唐代诗话的主要代表作。此外,唐代的诗学见解还散见于其他著述中,如唐五代的《朝野佥载》、《隋唐嘉话》、《大唐新语》、《云溪友议》等都有所提及。从严格意义上讲,唐代这些诗学著述并不算正式的诗话,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诗话是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尽管如此,我们重新审视唐代这些著述和记载,还是可以窥见其诗学见解和理论主张。
一
唐代诗话崇尚自然。当时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诗式·取境》)他们把自然奉为重要的美学标准和崇高的审美理想。唐代诗话中的自然美学观是一种真实的美论。它注重的是世界本体的真实。这种真实表现为“情真”和“事真”,在手法上表现为描绘的工同造化。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称为“有境界”,强调的就是艺术创造中的真情实感。唐皎然膜拜谢灵运诗的天然本色,是因为其“为文真于性情”(《诗式·文章宗旨》),他的诗语淡味隽,无一字不出于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孟棨的《本事诗》提倡诗缘情,诗由感而发,感时伤事;情由事发,情乃自然性情。这样,诗人写的“天真挺拔之句,与造化争衡”(《诗式序》)。这里的“天真”,是人的天然真性;“造化”,是自然造化。皎然极为推崇直抒胸臆、自然真切、天籁自成的诗作,这是唐人对诗意中“情真”的向往。
唐代诗话所倡的自然,还是自然人事的真实,即生活真实。早在齐梁时代的钟嵘就很注重这种“事真”。在《诗品序》中,他主张用“即目”、“所见”的“直寻”方法观察生活自然。司空图与之一脉相承。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的“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和《二十四诗品》中的“俯首即是,不取诸邻”,主张的都是创作中师法自然,注重生活真实。直接抒写眼前所见,不必冥思苦索人为的奇特,崇尚自然的“事真”,从平素耳闻目睹中感受生活,以积极的态度,最大限度地认识生活真实,“乘之愈往,识之愈真”(《二十四诗品·纤秾》),只有这样,才能识其真谛、传其真神。
唐代诗话不仅把自然作为美学标准,而且把它作为一种艺术上的风格。司空图极力推崇王维、韦应物的诗,偏好其自然恬淡的艺术趣味,并在他的《二十四诗品》中把自然列为一品。作为风格化的自然,在表现手法上不是对客观的描写和对主观的宣泄,而是以“情兴”为出发点,在法度范围内的“苦思”而得。首先,唐代诗话在创作上反对刻意于形式的的为文造情,主张“语与兴驱,势逐情起”(《诗式·邺中集》),以诗人内心感受的“情兴”为出发点,随着情的自然抒发而遣语取势。皎然在《诗式》中把“不用事”(不用典)的诗奉为第一格,即便是在“用事”的诗中,他所称道的也是从作者的实感出发,经过构思熔铸而使典实“成我诗意”的所谓“作用事”(奉为第二格)。在不赞成用典的同时,反对“声病”说,认为死板的套式会破坏诗人情性的自然抒发,“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诗式·明四声》)并斥以声病为模式的诗人为“拘忌”之徒。其次,唐人所倡的“自然”是法度下的浑然天成。真正的“高手”,声律并不妨碍他灵活自然的构思,“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诗式·明作用》)。创作中的自由灵活是深入掌握艺术规律后,自觉遵循艺术规律的妙手偶得,“俱道适往,著手成春”(《二十四诗品·自然》)。皎然论诗的“四不”、“四深”、“二要”、“二废”、“四离”、“六迷”、“六至”等,都是游刃于法度之中,从容于限制之内的自由。最后,这种艺术化的“自然”来自作家艰苦的构思和精心陶炼,“道不自器,与之圆方”(《二十四诗品·委曲》)是“妙造自然”(《二十四诗品·精神》),经过苦心炼造,天然浑成。这种“自然”是苦思而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佳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诗式·取境》)。诗的佳句虽苦索而得,但成篇之后,不露斧斤之迹。正如道家所说的“既雕又琢,复归于朴”,语意的畅达,文辞的流利,描绘上的工同造化,才成佳妙之作,“自然见于造化之妙”(叶梦得《石林诗话》)。
二
意境,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就有人提及。刘勰的“隐秀”说,“情在词外”,钟嵘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到了唐代,随着诗歌的繁荣,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创造了许多优美的艺术意境。于是,就引发了在理论上对意境问题的自觉探讨。在唐代诗话中以“韵味”说或“诗味”说为其特殊的表现形式。皎然用“文外之旨”(《诗式·重意诗例》)、司空图用“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与李生论诗书》)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极浦书》)等说法,对意境进行了探讨,使意境理论进入成熟阶段。
意境的这些提法,在唐诗话中无非是“言语”、“境、象”和“情、意”之间的关系,它以含蓄为主要特征。
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把这种含蓄说成是“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不无道理。“近而不浮”,即诗形象的具体性,在读者看来,就是景象好似近在眼前,但又不流于浮泛;“远而不尽”,则指诗的深远意境,通过想象使言已尽而意无穷。这实际上是诗意境的“实”与“虚”的矛盾统一。“近而不浮”求意境之实;“远而不尽”求意境之虚。虚实相生,实中有虚,才能传神;虚中有实,才能寄托。通过“实”使读者感情得以升华,进入“虚”的领悟。
意境是通过语言塑造的境象得以实现。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意是有限的,而意境要求的是使读者感到言外有无穷之意。宋梅尧臣提出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很能说明言语与意境的关系。在唐代诗话中早有精妙的见解。“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二十四诗品·含蓄》)、“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诗式·重意诗例》),言有尽而意无穷,透过语言文字所塑的有限形象,传达出悠远、无限的情意和内容;得其性情,忘其文字。读者超越了语言的有限意义,进入“虚”的领悟。这种说法源于佛学玄理,它认为至理在言语迹象之外,是不可言传的。
意境需要读者的感悟,意境“虚”的特点使其具备了空间的美、含蓄的美。这个空间使读者的领悟成为可能,同时给读者一个施展想象力的机会。读者的感悟首先是基于对实的境象的理解。司空图的“象外之外,景外之景”中,第一个“象、景”指的是实象实景,是具体的境象;第二个“象、景”指的是意境,指作者在作品中借第一个象、景的比喻、暗示、象征等作用呈现出来的,没有直接描绘的虚象。凡是具有深远艺术意境的作品,除本身具有有形描写外,还有一个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无形的、广阔幽远的境界,它超出了言语塑造的境界所能表达出来的内容,“境生象外”(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由实的境象生发出的虚的空间,实现了读者的审美理想。
意境以气韵生动、飞动传神为其审美特质。唐代诗话论意境的动态美的一大特点是关于“势”的论述。“势”作为事物本身内在规律和运动形态,是意境动态美的又一表现形式。这种“势”与古代文论中的“气”、“风骨”、“神韵”都存在本质上的联系。
意境的传神,在唐代诗话是形似与神似的问题。司空图称之为“离形得似”(《二十四诗品·形容》),形,形似;似,神似;这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二十四诗品·雄浑》)是相同的说法。超越具体的形体迹象之外,以契合超脱之境、传神写照之处。反之,如果只求形似,则早已逆其本意,与神似失之千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三十四诗品·冲淡》)。从庄子美在神不在形,形神分离到《淮南子》重神不重形但不排斥形,到六朝画论中只重形似、顾恺之的以形传神,形神理论历经漫长的流变,到唐代诗话的“离形得似”使形神理论的发展得以成熟。它对后代的文艺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理论表述上有相似之处:“离象得神”(明陆时雍《诗境总论》)、“不似之似”(明画家王绂《书画传习录》、“遗貌取神”(戏曲理论中的写意传神)以及小说理论中的“以幻写真”手法。
三
意境的获得是“取境”(《诗式》)的结果,取境离不开艺术构思。唐代诗话对艺术构思过程的思维特点和方式的论述有其独到的特点,它与唐代诗话“以道说诗”、“以禅说诗”有关。
在诗中寄禅意、谈禅理自唐以来甚为流行。皎然是一名僧,在《诗式》中可以看到大量的佛教用语,他常用禅意来说诗,如在《辩体有一十九字》中对“情”字的阐释,用“缘境”这一佛家意为“内心趋向事物之作用”,来指诗人之情皆因外感于境而生,诗中之情须靠绘外境而带出。此外,纵观《诗式》全书,还可以看到“顿教”、“宗源”、“心印”、“空五之道”、“心地”、“彻”、“性起”等佛家用语,皎然还以“性起之法,万象皆真”(《诗式·复古通变体》)来强调诗的本源在于诗人的主观心性,具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皎然的“以禅说诗”使诗学理论带有浓厚的禅宗色彩。
司空图说诗重“道”字,在他的《二十四诗品》中“道”字出现的频率极高。所描绘的“畸人”、“高人”、“可人”、“碧山人”,淡泊如菊,满脸道气。语言上多演化援引自老庄著作,如“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雄浑》)来自《老子》的“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和《庄子·齐物论》的“枢,始得其环中,以应万物。”在《二十四诗品》中,他追求一种“真”的境界,一再强调“虚伫神素”、“体素储洁”、“饮真如强”,接受庄子消极出世思想的影响,向往“其卧徐徐,其觉于于”的清静无为的太古,在飘然玄远的背后,表现出理想主义色彩。皎然在《诗式·立意总评》中引用《庄子·大宗师》中的“悬解”喻为文出于自然,不假人力。《诗式序》中用《庄子·秋水》的“天机”指创作时的自然灵机。从他们的“以道说诗”可发现唐代诗话的诗学见解中道家思想的影响。
“以道说诗”和“以禅说诗”在唐代诗话中体现为禅宗道学对诗学见解和理论主张的具体表述上的影响。意境的含蓄特点的表述“但见性情,不睹文字”源于《庄子·外物》:“言之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以及佛理中的至理在于言外的观点。在具体行为上,佛家通过虚静参禅,道家是通过虚静悟道,即所谓的“惟道集虚”。司空图用“素以处默,妙机其微(《二十四诗品·冲淡》)来说明作家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时在认识上的要求,用老庄对客观世界惟道集虚、静观默察的态度进行艺术思维。
在灵感问题上也同样存在虚静苦思的情况。灵感作为艺术思维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心理现象,早在陆机《文赋》中有过描述:“其致也,情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想象的闸门打开,新的境象纷至沓来。唐代诗话也有类似的描述,“好有佳语,大河横前”(《二十四诗品·沉着》),正当凝思苦虑之时顿时豁然开朗,只见佳句妙语,如大河前横,滔滔然无尽竭,他们都说出了灵感突发性偶然性的特点。但唐代诗话又有所发展,更深入探讨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感情和想象力高度亢奋的心理状态下产生的,“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诗式·取境》),同时具有道家静修时的“意静”的特点,正如《管子·内业》说的:“修心静意,道乃可得。”灵感的出现还是苦思而得,“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诗式·取境》)这与佛家苦行修道具有相似的特点。最后,还是“溥言情语”(《二十四诗品·自然》)的结果,参禅修行悟道与灵感出现时的顿时领悟是相通的。唐代诗话具体说出了这种看似不期而遇的心理现象其实来源于平时深厚的生活积累和艰苦的艺术构思,还要借助旺盛的思维热情,这种描述无疑是比较精到和全面的。
唐代诗话中,佛家参禅与道家悟道对艺术思维过程的影响而形成的“以道说诗,以禅说诗”,在宋以严羽的“以禅喻诗,以禅论诗”中用“参”和“悟”来喻钻研诗歌创作规律,认识和掌握艺术规律的“妙悟”说,得以顺承。
四
唐代诗话中关于文学的继承与革新问题在《诗式》中的“复古通变体”一章有过专门论述,并在“三不同:语、意、势”一章用“偷”字来说明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主张“偷势”而反对“偷语”和“偷意”。而有些问题,虽只是只言片语,却闪烁着理论的光泽。如主张华实相符、辞情并茂、健康充实的思想内容与深厚艺术形式统一的“大用内腓,真体内充”(《诗品·雄浑》,“风律外彰,体德内蕴”(《诗式》);主张立意上意脉贯通的“时时抛针掷线,似断而复续”(《诗式·明作用》);风格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车之有毂,众美归焉”(《诗式》)等。
唐代诗话的许多理论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留下重要地位。尤其是意境理论的“韵味”说,强调含蓄,追慕冲淡自然之美,对宋严羽的“妙悟”说、清王士禛的“神韵”说产生深远影响。司空图以诗论诗的《二十四诗品》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领域创立了一个新颖独特的体裁。为此,后人多有模仿,如魏谦升的《二十四赋品》、杨景曾的《书品》、黄铖的《画品》等。唐诗话的“以道说诗、以禅说诗”成了后人以禅、玄论诗的肇端,成为中国诗论的一大门宗,它从一种独特角度揭示诗歌的审美特质和艺术规律。唐诗话的出现,带来了宋诗话的繁荣以及宋以后诗话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