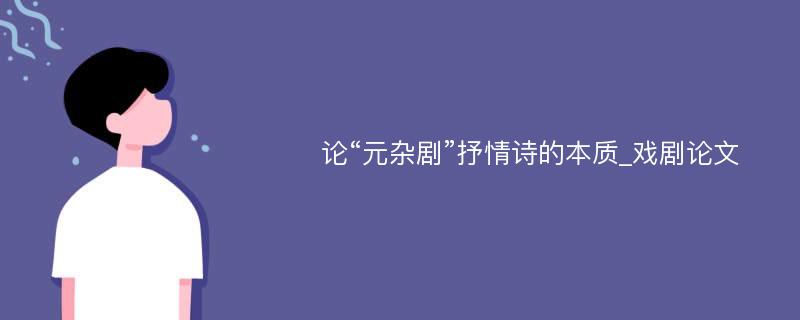
试论元杂剧的抒情诗本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抒情诗论文,试论论文,本质论文,元杂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文学的一般意义上讲,我们给予元杂剧非常高的评价,因为它为古老的中国诗歌带来新的意境,初创了“戏曲”这种中国戏剧的新样式。但是如果从戏剧文学和戏剧艺术的特殊意义上讲,元杂剧还是十分幼稚,有待成熟的。除了四折为限、一人主唱这些外在的幼稚形式之外,文学的戏剧精神的缺乏是更重要的问题。
文学的戏剧精神,不同于表演的意识。前者指以区别于诗歌和小说的第三种文学样式,即戏剧的样式,结构文本的意识,首先是对于戏剧性故事的兴趣,然后是以戏剧的方式构建文本的问题。元杂剧从戏弄、说唱、歌舞等众多的表演艺术发展而来,舞台的意识、表演的意识早已充分觉醒,有着自觉追求的强大内在动力。它所缺乏的,是文学的戏剧精神,一部分元杂剧作者缺乏对于戏剧性故事的兴趣,大部分作者则不以戏剧文学的独特方式构建文本。文学的戏剧意识沉睡不醒,是中国戏曲的“基因”缺陷,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戏曲的发展走向。
现存的元杂剧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其故事是非戏剧性的。而在这些作品中,不乏为明、清两朝曲论家盛赞的优秀代表性作品。所谓故事的非戏剧性,可以《陈抟高卧》(马致远)和《王粲登楼》(郑光祖)为例。道士陈抟设摊卖卦,算定赵匡胤日后必作皇帝,郑恩必为“一品大臣”(第一折)。赵匡胤登基后,即遣使西华山,请下陈抟入朝(第二折)。陈抟志在山林,不恋富贵(第三折),不爱女色(第四折),执意修仙。这个故事缺乏足够的情节张力构成戏剧:陈抟一心学仙,宋太祖其实不好太为难他;他自己内心也完全没有感到山中的寂寞和尘世的诱惑。《王粲登楼》展示了一个狂傲书生的求仕过程,剧中同样不存在真正的戏剧性冲突。蔡邕的怠慢羞辱是假,明激暗助是真,王粲本人除了发牢骚,并没有什么积极的改变自己命运的行动;以向皇上献“万言策”的方式解决矛盾,不过是元杂剧“召之即来”的熟套。作者所关注的,是王粲满腹经纶不用于世的牢骚和平步青云扬眉吐气后的喜悦,而并不介意于戏剧的矛盾冲突。尽管如此。这两篇作品作为元杂剧并不是失败的,历代的评论家都给予它们很高的评价。它们也远不是元杂剧中仅见的缺少戏剧性冲突、戏剧性故事的作品。
多数元杂剧作品即使采用了戏剧性的故事,也仍然不采取戏剧性的展示方式。
什么是戏剧性的展示故事的方式?就是《赵氏孤儿》的方式、《窦娥冤》的方式。五折《赵氏孤儿》紧紧围绕一个中心:孤儿的存亡及复仇。首先是反迫害的一方具备强烈的意志和在绝境中积极行动的勇气,使得冲突获得了足够的张力。其次是作者集中笔墨于核心冲突,充分展示它的张力,把冲突的张力写足。《窦娥冤》也是这样。如果关汉卿仅仅写出窦娥在蒙冤丧命之际对自己悲惨命运的痛苦观照,整个戏就会象一般的元杂剧那样,缺乏足够的戏剧张力。但窦娥不是无所作为地观照自己的巨大痛苦,她始终在行动。死前三愿及其实现,不仅是她强大意志的体现,也是她在绝无行动可能的情况之下的出人意料的行动。正是窦娥的强大意志和至死不息的戏剧行动,使关汉卿这部戏超越了一般元杂剧的烈度,成为象欧洲悲剧一样强烈的剧作。关汉卿始终把创作的注意力集中在展示窦娥的意志和行动上。王国维称《窦娥冤》与《赵氏孤儿》“最有悲剧性质”,“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注:引自臧懋循《〈元曲选〉序》。)《赵氏孤儿》和《窦娥冤》是传入西方最早,并且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中国戏曲作品,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赵氏孤儿》最初翻译成法文本时,被删去了唱词,在除去那些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欧洲人不能理解的东西之后,他们仍然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两部戏,因为他们感到这里面有他们所熟悉的东西,这就是展示故事的戏剧性方式。
但是,一个欧洲人,如果他不懂得中国的诗歌艺术,不是把元杂剧当作不同于他们所谓戏剧的东方艺术,他可能会难以把大部分元杂剧当作戏剧作品来接受。因为传统西方戏剧的概念在叙事方式上,比中国戏曲要严格得多。西方叙事作品的戏剧与非戏剧,主要地不是看其是否“代言体”,而是按其叙事方式来区别的。和西方戏剧不同,元杂剧并不介意于展示故事的方式。在这一点上,元杂剧要宽泛得多。象《赵氏孤儿》和《窦娥冤》那样采用戏剧的方式,很好;不象那样,而采用非戏剧方式,也很好。是否元杂剧,是否好的元杂剧,不是按其展示故事的方式,而是按别的标准来衡量的。
在元杂剧作家中,关汉卿对故事和情节最为关注,他的杂剧作品,最能反映元杂剧在故事和情节的安排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但即使是关汉卿,也没有完全摆脱他那个时代的艺术局限。《单刀会》描写的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本应极富冲突的张力。但作者并不看重故事中冲突的张力,他的艺术目标是直接刻划关羽这个人物。他实现这一艺术目标的手段也不是戏剧冲突,而是“曲”。第一折,是鲁肃和乔国公关于关羽的对话。
乔问:大夫你知博望烧屯那一事么?
鲁云:小官不知,老相公试说者。如此,先后“试说”了“博望烧屯”、“赤壁鏊兵”、“收西川”、“灞陵桥”和关羽的“座下马”、“手中刀”。第二折,是鲁肃和司马徽关于关羽的对话,让司马徽再次渲染了关羽的勇猛无敌。真正关、鲁交锋的场面,不仅篇幅少,而且没有给历代的读者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倒是交锋前后关羽抒发情怀的几段曲子脍炙人口,不断受到后人赞美。总之,这个戏的情节进展缓慢而草草,缺少戏剧动作,作者几乎无视这段历史故事中冲突的内在张力。然而《单刀会》展示故事的方式,在元杂剧里很有代表性。按照元杂剧所追求的艺术目标来看,这还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它在明、清两朝曲学家那里获得的赞誉,比《窦娥冤》还要多。
事实上,关汉卿写作《单刀会》的动机并不是讲故事,他相信他的观众和读者早已熟悉了这个故事。他也无意象许多采用旧故事的中外戏剧作者那样重新阐释旧题材。他的动机,是写出好曲子,写出他心目中的英雄。关羽在《单刀会》中的身份,与其说是戏剧主人公,倒不如说是抒情主人公。大众对于戏剧故事的熟悉,正好为作品的被接受准备了条件,使他有可能放弃故事,直接进入人物,展开抒情。这是元代知识分子创作杂剧的一种典型模式。
关汉卿的经历超越了一般的读书人,他“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注:引自臧懋循《〈元曲选〉序》。),因此他同时还代表了一般艺人和下层人民对于戏剧的要求,这就是故事性和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元杂剧的题材,多取自历史、诗歌、传奇、话本、传说,总之,故事和人物多是已有的,为当时人们所熟悉的。元人中,很少有谁象关汉卿那样经常地直接取材于现实,以自己构思的陌生故事和陌生人物来写作杂剧。展示人们熟悉的旧故事,有可能不在意于故事,或者集中精力刻画人物的细节和精神世界,或者直接借旧故事、旧人物来表达作者主观的情趣和理想。取材现实,说自己的新故事,就不得不首先把故事说好,然后才谈得上人物的刻划。所以取材现实和注重戏剧的故事性在关汉卿是统一的,互为因果的。他的部分作品,如《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鲁斋郎》都是现实性、故事性以及自创性很强的戏。在《鲁斋郎》里,作者就是要讲述故事,用他的故事来控诉现实。但是《鲁斋郎》展示故事的方式,仍然是非戏剧的。受迫害的张珪和李四两人在鲁斋郎面前不堪一击,逆来顺受,既没有抗争的意志,更没有抗争的行动。戏剧人物既不能行动起来,只好由作者“铺叙”苦难的过程。“铺叙”不是戏剧,人物的行动才是戏剧。这个故事中真正有冲突有戏剧、决定人物命运的地方,应是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但剧作家却对这个情节放弃了展示,改由包公叙述,一带而过。“铺叙”过程,而不是抓住冲突让人物积极地行动起来,这是元杂剧写作的另一种模式。
因为不是围绕人物的动作和戏剧性冲突构建剧本,而是要服从规定的音乐体制,元杂剧在情节结构上出现了两个很幼稚的缺陷。其一是第四折往往无“戏”可演,草草收场。明代曲学家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称之为“强弩之末”。臧懋循就说,即使大家如“马致远、乔梦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强弩之末矣”。(注:引自臧懋循《〈元曲选〉序》。)
马致远的《青衫泪》确是这种“强弩之末”现象的典型。该剧根据白居易的诗歌《琶琶行》敷衍而成。第一折写白居易与教坊名妓裴兴奴的相见和相恋。随后以“楔子”写白居易遭贬离京。第二折写裴兴奴被逼不过,嫁与商人。第三折写白、裴二人舟上相遇,终成眷属。至此故事实际上已经结束。但第四折又缀上一段白居易蒙招回京,裴兴奴奉皇帝之命叙说遭遇。皇帝则说:“兴奴,你认这文武班中,哪个是白居易?”最后,裴兴奴从群臣之中把白居易认了出来。从戏剧结构上说,这确是一段“蛇足”。然而马致远习惯以这种方式结束故事。《汉宫秋》第三折结束,不仅王昭君已死,毛延寿也已经受到了处治,第四折全写汉元帝“当此夜景萧索,好生烦恼。且将这美人图挂起,少解闷怀”。《荐福碑》第四折开头,主人公张镐的一切苦难都已经过去,范仲淹出场说:“自与兄弟张镐同到京师,见了圣人……圣人见喜,加为头名状元。今日驿亭中安排茶饭,管待状元。”这便是第四折的全部故事内容。在元杂剧作品中,这种必然被今天的剧作家视为“画蛇添足”的写法,却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写法。
甚至关汉卿这位最善叙说故事和安排情节的元杂剧大家也未能幸免。《鲁斋郎》的楔子和前三折,展示了官僚恶霸鲁斋郎先后抢夺李银匠和张孔目两人妻子的过程,第四折已是十五年后,包拯首先上场叙说了智斩鲁斋郎和收养李四、张珪两双儿女的经过,然后是李四夫妻先到云台观超度张珪夫妻,恰巧遇见前来与张珪孩儿做佛事的张珪妻,接着又与前来追荐父母的两双儿女相认,最后出家多年的张珪也来此散心,于是两家人大团聚。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悲剧的制造者已经受到惩罚,戏剧矛盾早已解决了。第二,一连串相遇的巧合来得那样勉强和草率。
元杂剧情节结构上另一个常见的幼稚缺陷是:把业已完成的人物动作再唱一遍。以《单鞭夺槊》(尚仲贤)为例。第三折展示了尉迟恭鞭打单雄信、夺下敌手兵器这一动作之后,第四折正末改扮探子上,“云:一场好厮杀也阿!”接着唱一段战斗过程。军师徐茂公说:“兀那探子,单雄信与唐元帅怎生交锋,你喘息定了,慢慢的说一遍咱。”于是探子再唱。徐茂公又说:“端的是谁输谁赢,再说一遍。”探子又唱一回。这里,戏剧情节的发展停止了,戏剧内容屈从于杂剧四套曲子的音乐形式,元曲的音乐和诗歌语言获得了展现魅力的机会。戏剧家失败了,诗人和演唱者却充分显示了艺术才能。
清代曲学家梁廷柟指出了另一种“元曲通病”,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通病”就是戏剧对话的非戏剧性。梁廷柟说:
(《汉官秋》)中有可议者:尚书劝元帝以昭君和番,驾唱云:“怎下的教他环佩影摇青冢月,琵琶声断黑江秋?”明妃死于北漠,其葬地生草,后人因以“青冢”名之。未出塞时安得有此二字?且其第三折昭君跳死黑龙江,番王明云:“就葬此江边,号为‘青冢’者。”此白又与曲目相矛盾矣。
白仁甫《墙头马上》云:“谁管我衾单枕独数更长?则这半床锦褥枉呼做鸳鸯被。流落的男游别郡,耽搁的女怨深闺。”偶尔思春,出语那便如许浅露。况此时尚未两相期遇,不过春情偶动相思之意,并未尝着谁人,则“男游别郡”语,究竟一无所指。至云“休道是转星眸上下窥,恨不的倚香腮左右偎,便锦被翻红浪,罗裙作地席。既待要暗偷期,咱先有意。爱别人可舍了自己。”此时四目相觑,闺女子公然作此种语,更属无状。大抵如此等类,确为元曲通病……(注:参看《中原音韵:序》。)梁廷柟的要求,是戏剧人物的唱词和道白应当符合人物身份和此时此地的情境。这是戏剧性的要求。在元杂剧作品里,虽然有许多唱词和道白符合这个要求,也有许多唱词和道白正如梁廷柟所批评的,不符合这个要求,而且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元杂剧的规范作品。元杂剧虽然具有丰富的戏剧因素,但它主要地并不是按照戏剧的原则写作的,它另有一套自己的规范和原则,只要符合了这些规范和原则,即使在唱词和道白上违背了一些戏剧的基本要求,仍然不妨碍成为元杂剧的代表之作。梁廷柟批评的《汉宫秋》、《墙头马上》都是元杂剧中优秀的作品。
从总体上说,元杂剧人物的语言,比较一般的戏剧作品,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较多创作者的主观色彩,往往不顾及人物特定的身份。汉元帝唱“环佩影摇青冢月”即为一例。二是较多一般抒情诗歌的空泛性,往往不顾及此时此地的特定情境。《墙头马上》男女主人公相悦的曲子,就更多带有一般爱情诗的意义。梁廷柟称此为“元曲通病”,“病”或“非病”要看是持一般戏剧的标准来判断,还是持元杂剧的特殊标准来判断,但“通”是没错的。这类唱词在元杂剧作品中不胜枚举。
元杂剧创作从整体上说在情节上缺乏自觉的追求,因此很容易地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故事“套路”。作者在“曲”的写作上刻意求新,怕落俗套,而在情节上往往毫不介意地使用这类“套路”。梁廷柟举过一例,他说:“《渔樵记》剧刘二公之于朱买臣,《王粲登楼》剧蔡邕之于王粲,《举案齐眉》孟从叔之于梁鸿,《冻苏秦》张仪之于苏秦,皆先故待以不情,而暗中假手他人以资助之使其锐意进取;及至贵显,不肯相认,然后旁观者为说明就里,不特剧中宾白同一板印,即曲文命意遣词,亦几如合掌。”(注:引自《曲话》,《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出版,(下同)第262页。 )甚至王实甫,也在他的《破窑记》中使用了这个“套路”。郑光祖的《梅香》对《西厢记》情节的模仿是一个公然的事实,梁廷柟称《梅香》“如一本小《西厢》”,他列举了二十处雷同,认为两剧“不得谓无心之偶合”。郑光祖生前即享盛名,《录鬼簿》说他“名香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皆知其为德辉也。”象这样一个“名香天下”的曲家,似乎不会去抄袭同样“名香天下”的《西厢记》。我想恰恰是他在曲界的崇高声誉和他对于掌握元曲这种艺术样式的巨大信心,使他敢于向《西厢记》“叫板”,与王实甫在“曲”的创作上一试高下。事实上,当时的人们也确实没有因为《梅香》与《西厢记》的雷同便看低了它的作者。《中原音韵》把郑光祖与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并列(注:参看《中原音韵:序》。),后人据此称为“元曲四大家”。
戏剧是情节的艺术,元杂剧作家在戏剧情节上这种漫不经心的模仿和习惯性地使用俗套的态度也是现代戏剧观念很难理解的一个缺陷。
二
不追求戏剧故事的戏剧性和展示故事的戏剧性方式,不追求人物语言的戏剧性,以及在情节艺术上漫不经心的态度,这是元杂剧因缺乏文学的戏剧精神而产生的缺陷。但这在当时的元杂剧创作者和接受者都未感觉是缺陷。站在当时中国文学发展的高度,局限在元杂剧的眼界之内,是不可能发现这些缺陷的。只有当中国戏曲中对于故事和情节的追求进一步发展,到了明清时代,才有人开始(例如梁廷柟)部分地感觉到缺陷的存在。当国门洞开,有人开始接触了西方戏剧之后,才会强烈地感觉到缺陷的存在,因此王国维会说:
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当时未尝重视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袭,或草草为之。(注:引自《宋元戏曲史·元剧文章》。)
我们今天指出这些缺陷,是因为我们站在戏剧艺术发展的现代高度,从世界范围的一般戏剧概念出发,而不是从戏曲的特殊概念出发。我们知道,戏剧除了“代言体”和“搬演”的特性之外,在文学上还应当有不同于抒情诗和史诗(小说)的特殊要求,这个要求主要就表现在情节结构上。对于戏剧作品来说,以上列举的元杂剧缺陷,带有根本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把现存的元杂剧作品当作戏剧作品来读,而不是把它们当作诗歌作品,我们从中虽然会发现一些精彩的戏剧冲突场面,一些精彩的戏剧对白,也会找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具有完整的戏剧情节结构的作品,但从总体上说,由于“关目之拙”,情节结构“往往互相蹈袭,或草草为之”,我们不能不认为,元杂剧内的戏剧因素尚未发育成熟。
缺陷存在的原因,正如王国维所说,为“当日未尝重视此事”。那么,元杂剧作者所重视的是什么呢?是音乐形式、语言风格和诗歌意境。
和情节结构的“草草为之”相反,元杂剧有着非常严格的音乐形式。“折”的概念,重要的不是一个叙事结构的单位,而是一个音乐的单位,即由同一宫调的多支曲牌联缀成的联套。情节的展示,必须纳入四个曲牌联套组成的音乐结构中。情节结构服从音乐结构,这是元杂剧创作中情节与音乐发生矛盾时(这类矛盾经常发生)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有完整的、供一人演唱的、代言体的四套曲子,就满足了作为元杂剧的基本条件。把四套曲子写好了,就满足了作为优秀元杂剧的条件。至于有没有好的情节结构,并不是必须的条件。《单刀会》有唱关公和关公唱的四套曲子就行,有“大江东去浪千叠”一曲【双调新水令】和【驻马听】脍炙人口,便是千古流传的好戏,情节够不上戏剧水准也无伤大雅。《单鞭夺槊》的故事情节已经完了,而四套曲子才唱了三套,便再唱一遍战斗场面,以适应音乐的格式,这并不算什么“蛇足”,可少了这套曲子,就不成杂剧了。
中国戏曲有一个至为深厚的不间断的传统,这就是歌舞表演。早在元杂剧形成之前,元杂剧中各种表演形式——歌、舞、对白、滑稽表演——已经存在了大约两千年。这些表演经宫廷的、民间的表演艺术家代代相传,被中国戏曲继承下来纳入了自己的表演体系。“杂剧”这个词,在宋代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概念是指包罗杂耍、武术、歌舞、演唱、科诨各种玩艺的杂乱表演,狭义的概念指“其内容是以诙谐嘲笑的题材为主,形式上侧重念诵的对白,但亦夹以歌舞或故事的表演”(注:引自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出版周贻白《中国戏剧史讲座》第34页。)。根据戏剧史学家描述的影响中国戏曲形成的多种表演形式看,中国戏剧本来也可能并不发展成元杂剧这种以一人歌唱联套曲牌为主的形式,它也可能发展成象欧洲戏剧那样以对白为主的形式,或者发展成以戏剧动作和舞蹈为主的形式。但是在元杂剧中,正旦或正末唱曲子的形式压倒了其他一切可能,成为决定其根本性质和面貌的最为重要的形式。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年的杂乱纷呈的舞台表演艺术,到元代生长出元杂剧这种规范化和诗意化的艺术样式,出现了杂剧这种样式的中国戏曲最初的成熟作品,这都不是偶然的。有一只无形而神奇的手在背后操纵了这个过程。这只无形而神奇的手就是中国文学的强大诗歌传统。元代政治上废除科举,文化上儒家正统思想统治松驰,这种社会环境把一批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投入了戏曲创作的队伍,他们成了元杂剧的主要创作者。通过他们,中国文学强大的诗歌传统被带进了戏曲。而这个传统与诸多表演艺术中的歌唱艺术结合起来最少障碍,可谓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事实上,从诗经、楚辞、乐府、唐律、宋词到元散曲,中国诗歌始终没有脱离过歌唱的传统。周贻白认为:“散曲形成在前,元剧出现在后,所以元剧在北曲的使用上实曾通过散曲这一项体制,并不是直接由“诸宫调”蜕变而来。”(注:引自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出版周贻白《中国戏剧史讲座》第75页。)散曲的创作主体,正是写作了几千年诗歌的知识分子。没有强大的诗歌传统对于两千多年来杂乱无序地发展和存在着的诸多表演艺术的整合,没有强大的诗歌传统对北曲音乐不分散曲、杂剧的漫无边界的大规模浸入,北杂剧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如此耀眼地崛起、成熟和辉煌是不可能的。元杂剧对说唱艺术“诸宫调”的继承关系,是直接的,也是肤浅的和有限的,真正对于元杂剧的面貌和本质具有深刻的决定性意义的,还是中国文学的诗歌传统。甚至连元杂剧对“诸宫调”的继承关系都是由诗歌传统这只无形的手挑选决定的。因此,比一本四折、“曲牌联套”、一人歌唱这些外在音乐形式更为重要,更须耗费精力追求的,是诗歌语言的创作。
诗歌语言的追求有两个层次,一在音韵声律方面,一在语言风格方面。音韵声律方面的追求要遵守语音外壳和音乐的共性,是规范性的;语言风格的追求要张扬艺术家的写作个性,是创造性的。越是大家,越着力于语言风格的创造,不屑于韵律的规范,他们往往无意间创造了曲牌的新形式,偶尔也有不合韵辙的破绽。越是才力有限的写手,越斤斤计较于音韵声律,无暇顾及个人诗歌风格的创造。至于才力有限又不懂韵律的人物,只能是门外汉,写不出合格的杂剧。大体在元杂剧形成的早期,曲家们率意写来,不太介意韵律的规范,而创造力却显得蓬勃旺盛。到了元杂剧创作的晚期,曲家开始总结前人的创作,制定规范,惟恐逾越,而创造的力度却大为衰减。
整个元代,只留下一部关于元曲创作规范的著作,这就是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这部著作影响深远,是我们了解元人怎样理解他们自己的杂剧艺术的最为重要的著作。《中原音韵》的主要内容是韵谱,周德清根据前人作品中所用的韵脚和当时在演唱中获得成功的作品归纳出这部韵谱。它的另一项内容是曲谱,作者把335 支曲牌分别归入不同的宫调,并指出各宫调或者“清新绵邈”,或者“感叹伤悲”,或者“高下闪赚”……的不同风格色彩。这部专著还总结了元曲的填词技法,称为“作词十法”。“十法”之中,有一半是关于韵谱、曲谱以及遵守它们的经验。很清楚,这是一部为元曲创作总结规范、制定准绳的书。它所总结的规范和制定的准绳主要是针对诗歌语言的语音外壳和音乐属性。“作词十法”的另一半内容,则大体上涉及到诗歌的语言风格。周德清在批评史上,第一个把“关、郑、白、马”并提,作为元曲的四大代表作家,他说:
……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观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补于世。(注:《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第175页。)。这里首先是对诗歌韵律的考虑,其次有对语言风格的考虑,还有对作品主题和社会效果的考虑,但就是没有对于情节安排的考虑。不仅这里没有,整部书中,也完全没有关于戏剧情节结构安排原则和技巧的讨论。
尤其需要指出,《中原音韵》对当时的散曲作品和杂剧作品丝毫未作区分。周德清不认为,杂剧创作比较散曲创作有什么特殊的规律可循,也完全没有想到需要给杂剧制定特殊的规范和准绳。他甚至没有使用“元曲”这个词,而是把以“关、郑、马、白”为代表的作品一概称为“乐府”。这说明,周德清不仅没有意识到杂剧与散曲的区别,也不认为元曲与古代诗歌乐府有何种重要的差别。应当说,周德清这种无视元曲中已经迅速生长的非诗歌因素(即戏剧因素)的倾向,在元明两朝,甚至到了清代,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明代学者王世贞说:“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注:引自王世贞《曲藻》,《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27页。)诗歌传统,是元、明学者和清代大部分学者讨论戏曲作品的共同出发点,王世贞的这个观点被后来绝大部分曲学家接受,他那种把杂剧作品当作诗歌作品来评论的方法也是元、明、清三代曲家一贯的方法。
近代学者王国维一面指出元杂剧情节结构方面的缺陷,一面又指出了元杂剧的艺术成就。他说: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注:引自《宋元戏曲史·元剧文章》。)写情“沁人心脾”、写景“在人耳目”、述事“如其口出”,这是语言艺术的境界,不是情节艺术的境界;是诗歌艺术的境界,不是戏剧艺术的境界。正如王国维所说,“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杂剧展示戏剧故事的艺术手段有三:曲、白、科。从元杂剧创作的总体上说,曲是第一的、最主要的手段。元杂剧里的曲,一方面是展示戏剧故事的手段,另一方面又有追求诗歌意境的自身目的。相对于追求诗歌意境的目的来说,戏剧故事反过来又成为杂剧之“曲”实现自身追求的手段——戏剧故事、戏剧情境为诗歌的写作提供了特定的、有诗意的背景,特别是戏剧人物使得戏剧作者具备了双重的抒情主人公的身份,获得了诗歌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广阔的抒情角度。“曲”所服务的展示戏剧故事的目的,和戏剧故事、戏剧情境、戏剧人物所服务的诗歌创作的目的,哪一个是元杂剧作者更为自觉、更为重要的目的呢?在展示情节和创作诗歌这两个目的发生矛盾冲突时,元杂剧作者将会放弃哪一个目的,维护哪一个目的呢?虽然就具体的元杂剧作品而论,情况各有不同,但是从整体上说,诗歌创作的目的是元杂剧作者更为自觉的、更为重要的目的,而戏剧情节的目的在许多情况下还是尚未觉醒的,比较地不被看重。简单地说,我们可以把这种状况概括为:元杂剧中的曲,既是元杂剧首要的艺术手段,也是它首要的艺术目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虽然元杂剧比较历史上的抒情诗要复杂得多,虽然戏剧的因素已经被引入诗歌,与诗歌结合起来,但是元杂剧在本质上仍然是抒情诗,其最本质的艺术特征仍然是抒情诗特征。
三
基于以下四点考虑,我认为,元杂剧虽然已经获得了以代言体的方式表演故事这个外在的戏剧形式,但是在精神实质上它仍然是抒情诗的:第一,在把歌舞、说唱、滑稽表演等等纷纭繁杂的舞台艺术综合成元杂剧这种有机的、纯粹的、高雅的艺术样式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中国诗歌传统是施动者,这个过程是由强大的诗歌传统来完成的。第二,在元杂剧大约130年的创作过程中,诗歌的意识、 诗歌的追求是高度自觉的,被创作主体强烈意识到的,而戏剧的意识和戏剧的追求往往是不自觉的、未被意识的、蒙昧的。第三,诗歌在元杂剧这种新样式中再次获得了尽善尽美的发展,达到了可能达到的最高峰,而戏剧的发展从总体水平上说,还很幼稚,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最后,诗歌的要求在元杂剧的创作过程中,一般处于领导的、决定性的地位,而戏剧的要求往往处于从属的、被决定的地位;当诗歌的要求与戏剧的要求发生冲突时,牺牲的总是戏剧。
但是,以上结论仅仅描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为了全面地理解元杂剧,还应当描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元杂剧作品中戏剧与诗歌结合的复杂局面。
虽然在《元曲选》及《元曲选外编》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不惜把情节发展停顿下来给曲子让路、在故事完结之后硬添上一套曲子、把最有意义的情节线索草草放过以便集中篇幅写曲子……这些让戏剧情节牺牲于四套曲牌联套的痕迹,但是,我们确实也能发现几本戏剧冲突十分强烈,戏剧情节基本完整的作品,例如关汉卿的《望江亭》、《窦娥冤》,杨显之的《临江驿》,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在这类作品里,我们很难说戏剧冲突和曲子谁是目的,谁是手段;《赵氏孤儿》第三折,一方要搜孤,一方在救孤,公孙杵臼以八十之躯身受严刑,撞死阶下,程婴亲眼目睹幼子、老友身遭杀戳,痛极、恨极、怕极,却要应对自如,不露心迹。在这里,真正惊心动魄的,甚至不是正义与邪恶伦理冲突的你死我活,而是程婴的心灵冲突。公孙杵臼巨创在身,性命不保,还体会着老友程婴的内心伤痛,唱道:“见程婴心似热油浇,泪珠儿不敢对人抛,背地里揾了。没来由割佶的亲生骨肉吃三刀”。在这样巨大的冲突的张力之下,人物心中自然充满了激情,戏剧场面为抒情诗的写作提供了极好的情境。同时,在这样激烈冲突的戏剧场面下,人物自然再不会满口“浮词”,他所唱的激情,一定具有了参与冲突的戏剧动作的意义。在这里,抒情诗就是戏剧动作。窦娥临刑就唱出的三个誓愿,就是她的戏剧动作,既有抒情诗的独立价值,更有推动情节的戏剧价值。在这类作品里,强烈的戏剧冲突提供了人物的抒情动机,也把一切抒情熔化成了戏剧动作,情节和诗歌,动作和抒情,融为一体无法区分,互为目的和手段。但是,这样的戏剧境界,作为完整的作品,在元杂剧中毕竟太少,在明清传奇中则完全没有。
《赵氏孤儿》等几部卓越戏剧作品的存在,并不能推翻关于元杂剧在本质上属于抒情诗的立论。因为我们判断元杂剧中的戏剧因素是否成熟,不能仅仅根据个别超越了这类文体基本要求的最优秀的作品,而要根据这类文体的一般要求,根据符合这类文体基本要求的大多数作品所达到的水平。如果这类文体提出了戏剧的文学要求,它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根据戏剧作品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创作出来的,都达到了合格的戏剧作品的程度,那么无论其中是否产生了天才的、卓越的作品,都应当承认这种文学艺术样式中的戏剧意识已经充分觉醒。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又产生了杰出的作品,这个样式则达到了成熟。如果情况恰恰相反,这个文体没有提出戏剧的文学要求,它的大部分作品不是按照戏剧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而是按照诗歌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创作的,不能达到合格的戏剧作品的程度,其中虽产生了个别天才性作品,但即使对于此类作品的作者来说,戏剧的原则与要求仍然没有被自觉地意识到,这类作品仍然被它的时代当作抒情作品看待,其戏剧成就并未被当时的作家和批评家发现,这个样式也只好判定它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诗歌。
《赵氏孤儿》和《窦娥冤》与当时元杂剧的创作原则、价值评判标准是有矛盾的。为了实现抒情和作曲的创作目标,元杂剧的人物一般比较抽象,较多普遍的代表性,较少特殊的个别性,演唱的“旦”、“末”成为剧中人物和曲作者难以区分的叠影。与此相仿,戏剧情境也要比较抽象,比较“虚”化,不能太特殊、太具体。《王粲登楼》、《汉宫秋》、《单刀会》、《梧桐雨》这些元杂剧的典型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抒情主人公不纯粹为戏剧人物,其中较多创作者本人的介入。这种二位一体的抒情角度,是元杂剧攀登新的抒情高度的秘诀。在《赵氏孤儿》和《窦娥冤》里,人物塑造达到了个性化的高度,这一点对于叙事作品来说非常可贵。但是如果看作抒情作品,剧中的客观性却妨碍了抒情的主观性,“旦”、“末”角色偏向了剧中人物,曲作者的抒情形象变得暗淡了、模糊了。抒情情境也太过于具体、太过于特殊,在这个层面失去了普遍性。这就是说,《赵氏孤儿》和《窦娥冤》不能代表元杂剧在抒情诗领域所达到的极高境界。而另一方面,《赵氏孤儿》和《窦娥冤》也不能代表元杂剧作为戏剧作品的情节水平之低。如果用这两部剧作所体现的戏剧冲突和情节结构原则来要求全部元杂剧作品,那么,极大部分元杂剧作品将是不及格的。总之,《赵氏孤儿》和《窦娥冤》不能看作是元杂剧这种文体的代表作。这一点,与它们作为一般文学作品反映那个时代的代表作不应混淆。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元杂剧在本质上是抒情诗,那么,《赵氏孤儿》这几部卓越的戏剧作品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从一种文体出发,走入另一种相近的文体,是可能的。而且这样兼具两种文体特征、融合两种文体风格、难以区分其属性的作品往往是天才之作。比如《史记》里一些最好的人物传记,兼具了史学和文学的特征;又比如马克思的某些政论,兼具着论文和散文的特征。戏剧本来就具备了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两重属性,用“第一人称”说话是它的抒情性,情节和冲突是它的叙事性,这两种文学样式的融合,使抒情具有动作和冲突的意义,使情节和冲突具有激发感情的作用,这就是戏剧。因此无论从叙事文体出发,还是从抒情文体出发,都有达到戏剧的可能,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抒情诗本来是戏剧的近亲,在采用“代言体”和或多或少的故事情节之后,它们就更没有什么硬性的边界了。如果不肯囿于元杂剧规范中诗歌传统的束缚,又有了对于某一故事或者某一人物的强烈兴趣和足够的才华,写出真正的戏剧作品就是可能的。从中外文学史上考察,由抒情诗歌中产生真正的戏剧,比由叙事作品中产生它们更有可能。希腊悲剧就是从“酒神颂”的合唱里产生的。元杂剧里产生了象《赵氏孤儿》、《窦娥冤》这样严格意义上的戏剧杰作,但是从叙事性很强的明清传奇里却没有产生一部这样的剧作。如果元杂剧旺盛的创作期不是那样短暂,这种文体不是最终成了文人的案头创作,其中戏剧的因素可能会生长成熟,《赵氏孤儿》所代表的方向可能会成为主流,抒情诗的元杂剧可能会最终发展成戏剧诗。
在讨论元杂剧的性质和面貌时,我们不能不谈到《西厢记》。这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首先,它用五本二十一折来展开一个故事。五本中的前四本,贯穿一个完整的戏剧情节,这在现在的元杂剧中是绝无仅有的。篇幅扩大了数倍,好比独幕剧变成了多幕剧,短篇小说变成了长篇小说,这种外在形式的变化不能不深刻地影响到它的精神实质。其次,决定这种形式变化的,是它特殊的创作过程。《西厢记》的故事在民间和知识分子中不间断地流传了500年, 它的内容被不断地发展丰富着,形式外壳也在不断地积累和确定,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在其中沉淀下来。王季思说:“全部《西厢记》故事的发展在《西厢记搊弹词》里即已定型下来。”(注:引自王季思《〈西厢记〉叙说》。)王实甫所能作的,不仅是改造《西厢记》故事以适应元杂剧的体制,更需要改造杂剧创作的某些原则以容纳《西厢记》的故事。王实甫要用这种相对短篇的音乐形式联缀,展示一个长篇的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他接受了元杂剧的抒情诗风格,用它去和一个千锤百炼的戏剧故事结合。他超越了抒情诗,锻炼出了真正的戏剧诗。然而,《西厢记》是一个例外,王实甫另外两本今存的杂剧恰恰反映了元杂剧作为抒情诗之长和作为戏剧作品之短。
四
元杂剧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体,它不同于中国文学史上已有的任何一种文学样式。从古体诗到格律诗,从唐诗到宋词,抒情诗的单纯性没有变。但是,我们说元杂剧在本质上是抒情诗,并不等于可以简单地说元杂剧就是抒情诗。在说明元杂剧本质的决定性之后,我们必须立即说明元杂剧面貌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了它的创作队伍除了诗人(知识分子),还有伶人(民间艺术家),而最好的杂剧作者往往兼有此双重身份;不仅表现于抒发情怀、作曲至上的动机并不是元杂剧创作的唯一动机;不仅表现于确有一些杂剧作品首先是叙事作品,然后才是抒情作品。元杂剧的复杂性尤其表现在那些最能反映其抒情诗本质的作品之中。即使在这类作品里,也出现了“代言体”和情节这两个戏剧因素。抒情主人公不再是作者本人,而成了有名有姓的另一人物,这位抒情主人公要有自己具体的抒情情境,这都是以往单纯的抒情诗所不曾有过的。如果说当今的戏曲史研究有时会忽略元杂剧的本质,过高评价它作为情节艺术的成就,那么,传统的曲学研究则往往无视它的戏剧因素,孤立地评价它作为语言艺术的成就。
元杂剧是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样式,我们应当从它的特殊性出发来讨论它的价值。
传统曲学所作最多的是关于音乐和语言的研究,但是,决定元杂剧的诗歌创作独辟蹊径、进入新境界的,并不是这些在音乐和语言上的追求,而是戏剧因素的引入,即采用了“代言体”的戏剧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创作者的情怀,无论是对历史悲剧和命运的感叹,对社会不公和个人“不遇”的愤慨,对仕途的厌倦和对山林之乐的幻想,对人生意义的怀疑和对佛境仙界的向往,或是对志士仁人的敬仰,对美好爱情的渴望,都必须通过一个人的形象来表达。抒情主人公由此获得了双重的身份,既是作者,又是剧中人物。在这里,最高的创作原则是这两个抒情主人公的既分离,又融合。好曲子必须首先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和此时此地的情境,这就是所谓的“本色”。如果一味卖弄才学,一看即知是作者的口吻,不像剧中人物所就,就不是好曲子。在这方面,以关汉卿为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本色”二字是后来的明清传奇不及元杂剧处。王国维概括元杂剧的“意境”所在是:“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这三条中,“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是一般诗歌的境界,唯独“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代言体”的元杂剧开创的新意境。然而,好曲子还必须同时传达作者的情怀,传达作者心中真正称得上是激情的东西。《荐福碑》中的这段曲词深深打动了梁廷柟:“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则这有银的陶令不休官,无钱的子张学干禄”他说“此虽愤时嫉俗之言,然言之最为痛快。读至此,不泣数行者,几希矣。”一目了然,这儿几句唱,其实是作者心中的激愤,借剧中人物之口直接唱出。《单刀会》关羽所唱【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叫我情惨切。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这段曲历来被人称颂,并没有谁指责作者“抄袭”了苏轼。因为关汉卿把被历史唤起的激情巧妙地置于参与那段历史的英雄之口,竟作到那样妥贴,自自然然,完全符合关羽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心境。而关羽唱出的,同时也是处于异族黑暗统治下的曲作者的伤感。
元杂剧的抒情主人公不仅在“代言体”的戏剧形式里获得了双重的身份,还获得了具体的抒情情境。这个具体的抒情情境一定是戏剧性的、使人产生激情的,例如关羽之单刀赴宴、张翠鸾之雨中流放、张镐之屡遭上苍无故挫折、汉元帝和唐明皇在家国和爱情悲剧之后的那个凄风苦雨之夜……这是一般抒情诗所没有的。元杂剧戏剧性的抒情情境本身就是抒情诗的组成部分,参与着意境的创造,赋予元杂剧以独特的精神面貌。
抒情主人公与作者分离的要求,提出了一个任务:塑造人物。语言符合人物身份性格、“如其口出”的问题,其实与运用语言塑造人物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说法。元杂剧不仅创造了意境,也创造了人物。一般的抒情诗也塑造人物,它通过抒情塑造抒情主人公的人格形象。而在元杂剧里,则要塑造一个具体戏剧情境中的戏剧人物,作者的人格则寓居于这个戏剧人物的形象之中。但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仍然是抒情诗的写作,是剧中人物在具体情境中的抒情演唱。这一点不同于欧洲戏剧。欧洲戏剧主要是通过情节,通过人物在冲突中的行动塑造性格。亚理斯多德说:“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而“语言的表达占第四位。”(注:引自亚理斯多德《诗学》第六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罗念生译。)根据这个差别, 我们不妨说:元杂剧是情节的艺术也是语言的艺术(抒情诗歌的写作),而以语言的艺术为本质;西方戏剧是语言的艺术也是情节的艺术,而以情节艺术为本质。情节的艺术和语言的艺术都以塑造人物为更高的艺术境界,有合格的情节结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戏剧,通过冲突和行动成功地刻划出了性格的戏剧,就是好戏剧;有符合元杂剧音乐规范的曲子就是杂剧,有唱出人物性格的好曲子才是优秀杂剧。在元杂剧中,动人意境的创造,总是以成功的人物塑造为标志的。关汉卿的民族英雄关羽、马致远的孱弱君王汉元帝、郑光祖的落魄书生王粲、白朴的热烈少女李千金永远活在他们自己的激情歌唱里,是中华文学史上灿烂的瑰宝。以塑造“非我”的另一个抒情主人公为创作目标,这是元杂剧与一般抒情诗的区别;以抒情诗(曲)而不是以情节和戏剧冲突为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这是元杂剧与西方戏剧的区别。元杂剧以诗歌演唱塑造戏剧人物,通常需要利用接受者心中早已存在的形象,通过“激活”这些传统的形象来实现自己的艺术目标。它所创造的人物强烈而单纯,但往往缺乏复杂的辩证的性格。
如果说元杂剧继承中国文学的诗歌传统,在抒情诗的领域里攀上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那么,它在以文学整合众多繁杂无序的表演艺术,开创一种新的情节艺术文体方面,则为后人预备了新的可能。不久,情节因素终于成长为与抒情诗因素并立的强大一方,不再接受抒情诗片面的本质规定。这就是明清传奇的出现。
标签:戏剧论文; 元杂剧论文; 中国古典戏剧论文; 艺术论文; 赵氏孤儿论文; 窦娥冤论文; 关汉卿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单刀会论文; 中原音韵论文; 西厢记论文; 鲁斋郎论文; 元曲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