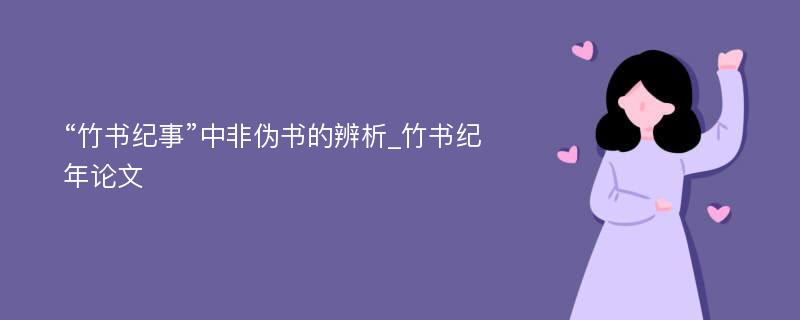
《竹书纪年》非伪书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伪书论文,纪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竹书纪年》(又称《竹书》、《纪年》、《今本》等)是春秋战国晋、魏史官所记之史书,是我国古代唯一留存的一部编年通史。此书第1卷开篇追记黄帝、颛顼、帝喾三帝之史事,但无确切的纪年;第2卷记帝尧、帝舜二帝之史事,自帝尧元年丙子即前2145 年开始了干支纪年的信史年代;第3、4卷记夏代即前1989—1559年凡431年之史事;第5、6卷记商代即前1558—1051年凡508年之史事;第7、8、9卷记西周即前1050—771年凡280年之史事;第10、11、12卷记晋国、魏国即前770—299年凡472年之时事,终于今王即魏襄王二十年。 上下有1847年的历史。
此书随葬于魏襄王墓中,于西晋太康二年即281年出土传世。 但因书中某些史事与儒家传统说法相悖而受到贬斥,继而受到冷落。传到梁朝,史家认为由沈约作了注释。从注释中可推知,传世的《竹书》可能有三种手抄本,内容略有差异。由于《今本》(现存《竹书纪年》,王国维始称《今本》与朱右曾辑录古籍中所引《竹书》本(称《古文》)的某些条文相异或益缺,从而受到清代钱大昕、纪昀、洪颐煊、郝懿行等学者的怀疑,而朱右曾在其《汲冢纪年存真》的序言里罗列12条诬证,以证明《今本》为伪书。自此开始,梁启超、王国维、范祥雍、方诗铭、王修龄等皆随声附合,继续加以否定。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等在编写史学论著时,只参考《古文》,对《今本》弃而不用,造成不少常识性的错误。
下面对朱氏的“12条”诬证进行辨析,望有兴趣的读者查证、核实,作出是或非的结论。
一,朱说:《晋书·束皙传》言“《纪年》十三篇”,《隋书·经籍志》云“《纪年》十二卷”,新、旧《唐书·艺文志》并云“《纪年》14卷”。《今本》只4卷,篇目可疑,一也。 (引自范祥雍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查徐文靖的《竹书纪年统笺》(《二十二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是12卷,另有目录1篇; 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静安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版)分上下卷,是为2卷。 卷数虽异,内容实同。朱氏之“4卷”本,当亦如是, 这有其《古文》本的注释可证。既然内容相同,而以卷数相异为据,否定《竹书》,应为诬证。
二,朱说:《束皙传》言:“《纪年》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乃述魏事”。杜预亦云,“特记晋国,起自殇叔,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今本》自黄帝元年至隐王十六年,大半依据《史记·年表》。体例可疑,二也。
查《竹书》内容,与《束皙传》、杜预所述基本相同。周平王条下有大字注云:“自东迁以后始纪晋事,王即位皆不书”。以此证明,周王更替仅作为年代符号,而记录晋国、魏国时事却是其史官之职责。
《束皙传》的作者说“纪夏以来”,并非束皙本人的观点,也不是“起自夏”。与束皙一同整理《竹书》的和峤却说“起自黄帝”,与《今本》一致。
如果说古本《竹书》“起自夏”以否定《今本》“起自黄帝”,那末朱、王、范本的《古文》不是也“起自黄帝”吗?查朱氏的《古文》在夏以前收录了黄帝、颛顼、帝尧、帝舜史事17条,其中“黄帝至禹,为世三十”的总括条文为《今本》所无。据此,朱氏不仅否定了《今本》,也否定了“和(峤)本”,同时也否定了他辑录的“朱本”。
至于说《今本》“大半依据《史记·年表》”,更属无稽。晋魏史官根本看不到后人司马迁的《史记》,却纠正了《史记》上百处的错误。如《史记》把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误为魏襄王元年;把魏襄王元年杜撰为魏哀王元年;把商王亥误为振;把商王文丁误为太丁。显然,说《竹书》抄自《史记》应是诬辞。
三,朱说:《古文》全用夏正,杜预之言可据。《今本》:“平王五十一年春三月已巳,日有食之”。“桓王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全袭《春秋》,可疑三也。
朱说“《古文》全用夏正”,意思是说《今本》不用夏正,但并未举出实证。查《古文》第152条:“幽王十年九月桃李实”;第159条:“晋庄伯八年十月庄伯以曲沃叛”,其月份皆与《今本》同。故《古文》与《今本》所用“三正”相同。
朱氏举两例证明《今本》“全袭《春秋》”。此说不对。因为《今本》除了晋魏时事外,其他史事皆应抄自存于宗周的古史或百国春秋。《春秋》是鲁国断代专史,亦应如此,谈不上谁抄袭谁的。
可笑的是,朱氏所举两例正好否定了他的《古文》夏正说。前例“三月已巳,日有食之”;《今本》是“二月乙已(应是已巳)”。前者是周正,后者是殷正,全非夏正。 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前719年2月22日“鲁隐公三年二月已巳,日有食之”,用的也是殷正; 不过,张氏却把前720年误为前719年了。后例“桓王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用了秦正,亦非夏正。
笔者对《竹书》纪有年月日完整条文的考察,在前1051年和前1050年“武王伐纣”的殷周交替的两年,前者用殷正,后者则转为周正。西汉以来,由于不知历法的变动,大多数史学家在寻找“武王灭殷”的年月日时至今争论不休。据《竹书》记载,武王灭殷是在帝辛五十三年(殷正)一月三十日,或在武王12年(周正)2月30日,即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
朱氏不懂“三正”,妄疑《竹书》。
四,朱说:《史记·正义》引《纪年》云,“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273年更不徙都。”《今本》则云,“武乙三年,自殷迁于河北。 十五年,自河北迁于沫。”不知盘庚之徙,已居河北。妄袭《史记》,又杜撰迁沫之文,可疑四也。
《史记》所言“273年”,因版本不同,另有275、773年之说。 陈梦家等相信275年,郭沫若等相信773年。三者皆误。查《竹书》前1302年盘庚迁殷,前1050年武王灭殷,其积年是253年。 问题不在于三个年数之误,而在于此条非《竹书》正文,是张守节本《竹书》里的后人读史的附加语,并且是错误的附加语。把它当成真经,又相信其积年是正确的,怎能不错上加错呢!此条在裴骃本、沈约本中皆无,故其产生年代应在梁以后,唐以前。
关于殷人迁都,朱氏妄加怀疑。据笔者研究,《史记·殷本纪·世表》所记盘庚迁殷,复渡河“南治毫”有误。此史事因《竹书》和甲骨卜辞而得到纠正。《竹书》载:盘庚十四年(前1302年)迁殷(小屯),其后世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冯辛、庚丁、武乙皆居小屯;武乙三年(前1157年)迁河北(邺),武乙十五年(前1145年)迁沫(淇县),文丁元年(前1124年)迁河北(邺),帝乙元年(前1111年)迁沫并改名朝歌,其子帝辛(纣)仍居朝歌。可见,不是《竹书》“妄袭《史记》,又杜撰迁沫之文”,而是朱氏妄疑《今本》。
五,朱说:《史记·集解》引《纪年》云,“夏用岁四七一年”。《今本》附注云:“起壬子,终壬戌”若然,则431年矣。可疑五也。
看来,朱氏是信《竹书》的附加文而不信正文的。查《竹书》帝禹“元年壬子”是前1989年,帝桀三十一年壬戌是前1559年。两者相减,正好是431年,与小字附注同。朱氏不知“471年”的条文是后人读《竹书》时的四条附加文之一,而以错误的附加文怀疑《竹书》,这是朱氏以及乾嘉学派、古史辨派否定《竹书》惯用的伎俩。譬如,顾颉刚在《古史辨一》的自序里说:“夏代的年数,最长的是《路史》,凡490年;最短的是《今本竹书纪年》,只有365年多(内有未详的数年); 最普通的是《古今纪要》,为439年。其余471年、441年、432年的都有。各个编纂古史的人的闭着眼睛的杜造,到此完全证实”。顾氏不仅批评了朱右曾,同时也批评了自己,因为他拿不出不杜造的正确年代。
同样主张“431年”的也有正误之分。 如施之勉在《史记夏本纪校注》一文里提出的“431年”是起自前2169年,比《竹书》的前1989 年提前三个甲子,即180年,当然是错误的。
为什么说《竹书》的“431年”是正确的?除了干支纪年为证外,还有《竹书》前1948年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为证。当然“仲康日食”的年代也有争论。现代天文学家提出了前2165、2155、2154、2137、2135、2127、2106、1948年八个年代。董作宾据奥伯尔子和朱文鑫推算的前2137年为基准编写了《中国年历总谱》,与《竹书》所记不合,又是孤证,显然是错误的;而《竹书》所记,不仅证之于天文学家的推算,也证之于唐代历算家一行的《大衍历议》,还证之于《尚书·胤征》、《左传》昭17年所引《夏书》的记录,五证皆合,何疑之有?
六,朱说:自来简册,俱不详周公薨于何年。《今本》于成王二十一年,书“周文公薨于丰”,而前此成王十三年,书“夏六月,鲁大褅于周公庙”。岂有周公尚存,而鲁已立庙乎?可疑六也。
周文公亡于成王21年,即前1025年,正好补上古籍的阙如,证明《竹书》自身的价值;同时也证明朱氏历史知识之浅薄,因为“周公庙”是周公亶父、周公季历之庙,非周文公之庙。该庙当建立于周初,是伯禽代父受封于鲁而帅其子孙祭奠祖先之家庙。查《竹书》商王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等。这就是说,“周公”是指周公亶父、周公季历,非指活着的周文公。
七,朱说:《书序》云,“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今本》:“成王十年,周文公出居于丰。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东都”,显非事实。可疑七也。
查《竹书》成王“七年春三月……甲子周文公诰多士于成周,遂成东都;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冬,王归自东都。”“十年,周文公出居于丰。”“十一年春正月,王如丰,王命周平公(周文公之次子君陈)治东都”。“十四年冬,洛邑告成”。“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丰”。《竹书》所记年月日皆有,与事与情皆合理,应是事实。
再查《周书·周官》:“周公在丰,将设,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这说明周文公在成王十年时,致政老归,“出居于丰”;到了成王二十一年时,“薨于丰”。在这退休的11年中,谁来营建洛邑呢?其次子君陈在成王十一年接替老父的事业是理所当然的了。
以上三方面的资料对比研究,我们认为“周公既没”是“周公将没”之误。《今本》纠正了《周书》之误,功莫大焉,何疑之有!
八,朱说:宋鼌氏、陈氏《书目》皆无此书,而《宋志》有“《竹书》三卷”,是亡而复辑之证,可疑八也。
宋、陈的《书目》无《竹书》,只能说明他们未收录,不能证明《竹书》已佚;而《宋志》有《竹书》就是强证。
至于《宋志》之《竹书》并非“亡而复辑之证”,其理由请参看“第一条”辨析。
应补充说明二点:其一,朱右曾本4卷、王国维本2卷、徐文靖本13卷,卷数虽不同,而内容完全一样。既然朱、王亲眼看过、用过这三种《竹书》,为什么还以卷数多少为据否定《竹书》呢?其二,朱氏以此为据说《竹书》亡于宋,请读者查看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的《竹书》辑本,其搜录条文来自北宋刘恕《通鉴外纪》、司马光《稽古录》、邵雍《皇极经世》,南宋罗泌《路史》、郑樵《通志》、朱熹《通鉴纲目》、张南轩《经世纪年》、元金履祥《通鉴前编》,明杨慎《杨升庵外集》、刘仲达《鸿书》等等,比比皆证明《竹书》未亡。虽然王国维有意删掉明代的条文,以掩盖真实情况,但他删不掉宋代、元代的条文。这些条文使他们强加给《竹书》的诬辞和诬证,不驳自败。
九,朱说:凡《史记注》所引“田侯剡立”,“齐桓公杀其君母”,“梁惠成王会齐威王于平阿”,“齐宣王八年,杀其王后”,“秦惠王薨”,“秦内乱,杀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壮”。《水经注》所引“郑筑长城,自亥谷以南”,“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诸如此类,确是《纪年》古文,而《今本》具轶,可疑九也。
与《古文》(朱氏辑录本)对照,《今本》何止只缺8条, 而是缺少88条。但是,《今本》却有737条为《古文》所无, 两本重复的却有317条。在重复的各条中,《今本》皆较《古文》系统而完整, 因而其可信程度和史料价值也较高。
例如,《古文》认为夏代“用岁四七一年”,《今本》则纠正其错误,计算为431年。《古文》认为商代“用岁四九六年”, 《今本》则纠正其错误,计算为508年。《古文》认为西周“凡二五七年”, 《今本》则纠正其错误,计算为280年。 《古文》认为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亡“用岁二七三年”,《今本》则纠正其错误,计算为253年。
《古文》把后人读史的大字注、小字注误为正文的甚多,皆可据《今本》加以纠正。由此可知,《古文》错误百出,使用价值甚少。
因此,不能因《今本》缺8条就证明《今本》是伪书;同理, 也不能因《古文》缺737条就证明《古文》更是伪书。两者相同的317条,证明两者皆是真《竹书》;两者相异的88条或737条,正好相得益彰, 而不是相互排斥或否定。
从《竹书》的大字注、小字注来看,注《竹书》者的案头至少有《竹书》一本、手抄本两本,而以手抄本的一本为母本,参照其他两本和古籍加以注释。在大量的注释条文中,沈约注只有7条,其他无作者。在注释条文中,分为低于正文一格的大字注和夹在正文之间、之后,或夹在大字注之间、之后的小字注。特别有趣的,在君主名的61条注释中,与《古文》相同者有22条,例如“帝厪,一名胤甲”、“帝发,一名后敬”。两者不同的,在《今本》是注,在《古文》则是正文。这有三种可能:其一,说明《今本》更接近原本《竹书》,因为正文、大字注、小字注分得很清;其二,说明《古文》漏抄39条君主的名子,并且把已抄的22条君名由注释误为正文;其三,说明古籍注释所引的《竹书》条文多数是《今本》的,而为《古文》所搜录。
附带地说明一下,《竹书》在唐以前无木刻本,只能辗转传抄,缺页、缺条、缺字、甚至笔误都是非常多的;后人搜集各种手抄本加以对比校正,查证核实,甚至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对原本进行删削补订从而发生意见分歧,也都是合乎情理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求其真。
最后,还要指出,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所辑录的《古文》有71处是参照《今本》的。既然说《今本》是“伪书”,应弃而不用,“始作甬”的朱、王、范为什么还要参考它呢?特别是“商王亥”、“魏惠成王”等找不到出处证据时,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是真的呢!
十,朱说:《纪年》不讲书法,故王季、文王亦加王号,鲁隐、邾庄皆举谥法。《今本》改王季为周公季历,改文王为西伯,改许文公为许男,改平王为宜臼,可疑十也。
查《竹书》,前1159年武乙元年“邠出于岐周”,自此始称周。前1157年武乙三年“命周公为亶父赐以岐邑”,始称周公。前1139年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周公季历继之。前1114年文丁十一年“王杀季历”,周文王昌继之为侯爵。前1097年帝辛九年“西伯初禴于毕”,文王昌称西伯;前1062年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武王发继之称西伯。这就是说,周君在商代未称王。
查《竹书》,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申侯、鲁侯、许男、 郑子立宜臼于申。”许文公在这时为男爵,故称许男;宜臼未立,故直呼其名,立后始称之为平王。
以上说明《竹书》不是不讲书法,而是特别注意书法,其例证甚多。试想,周君在商末被封为公、侯、西伯,后人称之为王,不是违背历史事实吗?同理,许文公为男爵时,后人称之为公,不是也违背史实吗?
晋、魏史官所记之《竹书》,其晋事、魏事是当时史官之实录;其帝尧、帝舜、夏、商、西周之史事应是抄自宗周所存的古史。因此,其君主之爵号皆是在立国之时被封的,其后有升降变化,史官也就按时间顺序如实记录。这是不言自明的。
十一,朱说:《水经注》引“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及我师伐齐”。我者,晋也。“梁惠成王元年,赵成侯偃、韩偃侯若伐我葵;二年,齐田寿帅师伐我围观”。我者,魏也。《今本》用周王纪年,则我皆为周,文义俱失,可疑十一也。
查《今本》,朱氏所引的4条是周威烈王九年、十八年, 周烈王六年、七年。仔细研读原文,前两条亦魏非晋也,因为晋烈公三年是魏文侯二十四年、晋烈公十二年是魏文侯三十三年。这说明朱氏未读懂“我”字。据《古文》纪年与《今本》纪年对照,以晋文侯的时事为例,所纪之二年、二十一年皆是周纪年,《古文》误为晋纪年。这说明朱氏也未读懂“纪年”。
按常理,《竹书》是通史,应是依据正统君主的立与亡纪年。武王灭殷以来,《今本》与《古文》皆应采用周纪年,有其统一于宗周之义。这是魏史官否定分裂的大一统传统思想,较之《春秋》的作者已失掉了周纪年而使用鲁纪年有一定的进步性。纪年不过是个符号,便于对比、查找、记事、计算,并不具有国别、族别的特殊含义。
附带说明,朱氏所引晋烈公十二年条、梁(魏)惠成王元年条,皆是《今本》条文,朱氏作为《古文》引用以否定《今本》,证明他的思维逻辑是混乱的。
十二,朱说:《梁书·沈约传》不言注《竹书纪年》,《隋·唐志》亦无《纪年》沈约注。《今本》采取《宋书·符瑞志》而讬为休文之注,可疑十二也。
先考察《竹书》之小字注。小字注共106条,一般认为是沈约注,但徐文靖本、王国维本《竹书》皆无注者名,可见说沈约注的根据不可靠。不过王国维本有一条:“约案,《史记》作太庚”;笔者认为“约”字是王氏所附加。此其一。其二,在12条大字注中又附加小字注,一般史家认为,大字注也是沈约注。如果都是沈约注,大字注中再加小字注是不必要的。其三,有些小字注是宋以后注的,有些显然是整理《竹书》者所注,如第83条小字注:“据温公《稽公录》“温公是北宋的司马光。第101、102条小字注:“不知何年,附此”。显然是束皙等所为。
再考察《竹书》之大字注。大字注共91条,一般认为也是沈约注。但标明沈约注者仅7条,其他皆无注者名,此其一。其二, 在大字注中有17条与《宋书·符瑞志》同,故认为是沈约注无疑。但据笔者考察,有可能是沈约的《宋书》抄自《竹书》的大字注,如第8 条大字注的“遂登庸”,《宋书》无,而明代刘仲达的《鸿书》却有。其三,有些大字注产生于沈约之后,有些大字注产生于沈约之前,如第14条大字注的“今海州”。海州是公元549年东魏合南北二青州之名。第31 条夏代“用岁四七一年”,第70条商代“用岁四九六年”,第90条西周“共二八一年”,皆在沈约之前。
只要读者仔细考察《竹书》的197条大小字附注, 就能查出这样的例证,因篇幅所限,此处不一一列举。
由此可知,不言沈约注《竹书》是有根据的, 而言沈约注者只有7条根据,其他无据。
值得注意的是,朱、王、范所辑录的《古文》中,有后人的44条大小字注冒充《竹书》正文。可见,朱氏对《竹书》的注文缺乏研究,而妄加怀疑是不必要的;相反,朱氏的《古文》本倒是值得怀疑的。
通过以上逐条查证核实,剖析说理,证明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等人任意怀疑《竹书》是毫无道理的。他们的思维定式是:《今本》现存的正文1142条,凡是古籍注已有者,就是抄袭古籍的;凡是古籍注没有者,就是伪造《竹书》者杜撰的;主观认定《今本》是毫无价值的伪书,甚至告诫后学不要读此书,以免受其蒙蔽和毒害。这种作法,使中国的信史缩短了1300年,不能认为是妥当的。
标签:竹书纪年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史记论文; 黄帝纪年论文; 读书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汉书论文; 后汉书论文; 离骚论文; 西汉论文; 甲骨文论文; 战国时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