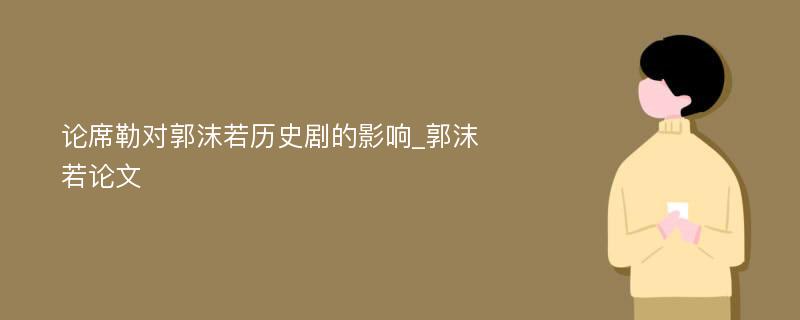
论席勒对郭沫若历史剧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席勒论文,郭沫若论文,历史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沫若受德国文学影响很深。他的文学创作在艺术构思,表现手法,结构等方面,都留下了德国文学影响的痕迹。对他影响最大的德国作家,首推歌德。其次,席勒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郭沫若的《暴虎辞》是在席勒叙事歌《手套吟》影响下写成的,“吾幕许雷《手套吟》,击鼓而成《暴虎辞》”。〔1〕《手套吟》写的是法国国王弗朗茨一世时的故事,王公贵人们聚在宫中观看惊心动魄的斗兽,库尼贡小姐的手套掉入了兽栏中,她要她的情人杜罗杰冒险从兽群中将手套拾回,以此来考验他的忠心。骑士勇敢地完成了任务,获得众人喝采和她的“爱情”,他却轻蔑地将手套掷在她面前,说:“女士,我不贪图你谢恩。”转身离开。《暴虎辞》稍复杂一些,写汉武帝同群臣看虎斗,将李禹缚束而悬入圈中,让他与虎相搏.将及地时,武帝可怜他是名将李广之孙,不忍见其葬身虎腹,命人将他吊起。李禹不堪其辱,拔剑斩断绳索,落入兽群中,与群虎相斗。后被救出,拥至武帝前,武帝赐酒奖励其勇敢,李禹却怒斥他穷兵黩武,惨无人道,遂被武帝处死。这两首诗都取材于历史故事,又加入了艺术想象和虚构创新;都采用了民间传统形式,前者是由德国民谣发展来的Ba11ade“叙事谣曲”,后者是中国说唱文学中的鼓词。两首诗情节、构思相似.在艺术手法上,都通过对野兽凶猛残暴的渲染,反衬出两位武士的沉着勇敢。《暴虎辞》中的恶虎还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它们那种争夺撕食弱小动物时的残忍,令人联想到封建统治者对于弱小百姓的残酷杀戮。至于题旨,郭沫若曾借一个女士的口说:“李禹底精神和杜罗杰底精神是怎么样相似!杜罗杰虽是反抗一个女子底权威,但是我们女子本来是有帝王一样的权威的呀!单是‘威’这一个字,不是从我女子生出来的吗?这个只不过是个笑话。总是我们所渴慕的是藐视一切权威的那种反抗精神。”〔2〕1928年,郭沫若在为《暴虎辞》所加的小序中说,“它的精神是反抗既成的权威”。〔3〕由此可见,《暴成辞》系对席勒《手套吟》的模仿和进一步深化之作。
《暴虎辞》是郭沫若唯一的叙事诗,《手套吟》虽有名,也不是席勒的主要作品,但我们由这个例子不仅可以看出二者在艺术上,而且可看出其反抗精神的联系。郭沫若虽是“中国的歌德”,但他的性格气质更接近于席勒。歌德性格平和温厚,不易激动,其中有许多市民阶级实用主义的成分。席勒则脾气急躁,易于冲动,刚直不阿。这种差异可从他俩合写的讽刺短诗集 《赠辞》中看出,歌德写得“温和而轻淡”,而席勒写得“尖锐而适当”。具有巴金所说“战士、诗人、雄辩家的雄姿”和唯心主义哲学基础的郭沫若气质上与席勒相近,在经历上,二人都是早年学医,而后又成为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
席勒对郭沫若的影响较明显地表现在历史剧创作上。席勒的九部著名剧本,除《强盗》、《阴谋与爱情》取自于现实生活外,其余都是历史剧。郭沫若在进入创作之前,就读过他的《强盗》、《阴谋与爱情》、《堂·卡洛斯》、《华伦斯坦》、《奥里昂姑娘》、《威廉·退尔》等。郭沫若在自传中屡次提到《退尔》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他还翻译过《退尔》第一幕第一场渔童在四林湖边小船里唱的民歌,1936年又译了《华伦斯坦》三部曲。席勒那种充满激情,振臂高呼为理想而斗争的姿态比起歌德的温情脉脉和追求永恒的艺术世界的和谐更易引起共鸣。我们不难从郭沫若史剧中寻出这种影响痕迹,这种影响有时延伸到极为细小之处。如《退尔》中的儿歌,“瓦得(唱):握着箭与弓,穿过山和谷,射者缓步来,清晓日初出。就如太空国,鹫鹰为其王——群山幽壑里,射者治无疆。所辖殊辽远,但任箭所及,飞离和走兽,听他来俘获”〔4〕,就同郭沫若剧中的许多儿歌和儿童剧具有一致的格调。而著名的《屈原》中《雷电颂》与其说受《李尔王》中暴风雨一场的启示,倒更象《退尔》中渔夫的一段雷电颂,“渔夫:风啊,你恣肆罢!霹雳啊,往下烧罢!乌云啊,崩裂罢!天上的洪流啊,向下灌罢,把这土地淹没!把未生的一代,彻底毁灭!你们这些野种,请来作主!熊啊,还有洪荒的老狼们,再来罢!这是你们的老家。没有自由,谁愿意在此生活!”〔5〕
如果我们细加比较,可看出郭沫若和席勒的史剧有这几个共同特征:一、都是悲剧;二、都选择有历史意义的题材,写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英雄人物;三、都通过创作来表达某种观念;四、通过写历史剧来配合、推动现实斗争。
席勒作品中贯穿始终的是不可遏止的理想主义激情。这首先因为席勒是康德的信徒,承袭和发展了康德二元论哲学中唯心的一面。这是他和唯物主义者歌德世界观上根本的分歧所在。作为自然的深邃而缜密的观察者,歌德在艺术方法上主张从显出特征的个别的东西出发,即“从特殊中显出一般”,而席勒则从主观理想或概念出发,即“由一般而找特殊”,甚至是“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简”(马克思语)。歌德认为,“贯穿席勒的全部作品的是自由这个理想。随着席勒在文化教养上向前迈进,这个理想的面貌也改变了。在他的少年时期,影响他自己的形成而且流露在作品里的是身体自由;到了晚年,这就变成理想的自由了”,“席勒特有的刨作才能是在理想方面”。〔6〕这个理想就是作为整个德国古典文学基础的资本主义上升和发展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
和歌德一起,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以及其它论文里建立了浪漫主义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的理想:理想的人是全面得到和谐自由发展的“完整的人”。这个理想是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提出了的,席勒的功劳在于给予这个理想以一种更具体更深刻的内容:人的完整性在于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他认识到这种理想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阶级的划分和严密的分工制而遭到破坏,并且指出近代文化危机的解救在于力求恢复已经割裂的统一。从唯心史观出发,他将挽救文化危机的办法诉之于人的精神世界。他认为,通过审美教育,已经失去的统一可以恢复,具体地见于“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统一于“形式冲动”,统一于所谓“活的形象”。席勒对文艺的社会作用有极高的评价。他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论述说,舞台可以滋养灵魂,并将头脑(理智)和心灵(感情)的最高点用教育结合起来。舞台是真理的明镜,惩恶扬善。“伟大的心灵和热诚的爱国志士经常利用舞台传播启蒙思想”,“毫无疑问,一个诗人的光荣使命就是提高人的道德,并且激发公民的爱国主义,缪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凡是崇高的和优美的艺术在这方面会发挥多么良好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对戏剧道德作用的清醒认识,席勒才常以人民的启蒙者自居,在其诗歌和戏剧中鼓吹其理想。在长诗《欢乐颂》中,他热情歌颂对人类的爱和献身精神,这首诗成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乐观主义的自由颂歌,它想给人类带来永久和平和社会解放。在《新奥尔良的姑娘》中,他用了热情奔放的浪漫主义手法,对法国圣女贞德的事迹进行重新处理和再创造,使她成为德国人民热爱祖国、抵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团结的精神的化身。因为要表现这种理想,席勒的优秀剧本虽然都是悲剧,但他反对为描写苦难而描写苦难,而要写出悲剧主人公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同苦难进行斗争。他引用罗马悲剧家塞纳加的话:“一颗高贵的心跟敌对势力作斗争,就是天神看来也会觉得这是充满吸引力的景象。”这就将悲剧艺术从消极的凄惨的状态上升到积极的壮丽的境地。洋溢着理想主义的乐观的英雄悲剧,这是席勒,同时也是郭沫若历史剧最突出的特色。
郭沫若在四十年AI写作历史剧时,早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又在此基础上写戏剧。因此,他在作品中贯注的理想就比人道主义者席勒所理解的要先进、深刻得多,他不仅写悲剧主人公对苦难的反抗,通过这种反抗来激发人民斗志,而且写出苦难产生的社会根源,从阶级和社会的观点来分析主人公行动和结局的必然性,指出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推动力。他在1941年《由<虎符〉说到悲剧精神》中说:“促进社会发展的方生力量尚未足够壮大,而拖延社会发展的将死力量也尚未十分衰弱,在这时候便有悲剧诞生。”但是,有意识地向作品中贯注理想,从观念出发写作,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席勒和郭沫若的历史剧给我们的印象都是一本正经和富有教育性的。“德国人所要求的是一定程度的严肃认真,是思想的宏伟和情感的丰满。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席勒受到普遍的高度评价”。〔7〕而郭沫若为什么要写历史剧呢?“在旧式的道德家看来,一定是会诋为大逆不道的,——你这个狂徒要提倡甚么‘三不从’的道德呀!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但是大逆不道就算大逆不道罢,凡在一种新旧交替的时代,有多少后来的圣贤在当时是諡为叛逆的。我怀著这种想念已经有多少年辰,我在历史上很想找几个有为的女性作来具体的表现。我在这个作意之下便作成了我的《卓文君》和《王昭君》”。〔8〕“更有人问我:‘全剧的主旨何在?仅为车力特穆尔这黄鼠狼吃不到天鹅肉,因妒而弄成这悲剧吗?’这一问倒使我感觉着失望。因为我写出的东西让朋友们看了听了,竟不明主旨所在,我真不知道在写些什么了!这原因:或许由于恋爱斗争的副题过于扩大,掩盖了主题:善与恶——公与私——合与分的斗争的吧!”〔9〕郭沫若与席勒都试图阐发某种“题旨”,而歌德就不是这样,他从来不从“题旨”出发,他认为只要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达到表现上的完满性,就自然表达出了某种道德含义。
为了达到表现理想的目的,郭沫若和席勒都有意识地选择具有历史意义的题材,他们都不掩饰对高大人物、正面人物的偏爱,有意识地拔高、突出个人作用,他们的历史剧都是一种英雄悲剧。他们悲剧中的主角都有远大的理想、崇高的品质、坚强的斗志和牺牲精神。这些英雄人物,无论是贵族或平民,都在反抗封建统治和暴君专制,都在要求“把人当成人”,最后都为这个崇高理想而献身。郭沫若常在剧中对英雄人物加以净化,这在《孔雀胆》中对段功的处理上就表现得很明显。段功本是蒙古的将领,他之屈服于异族并非他个人的过错,镇压明二的农民军也是职之所在,但郭沫若站在今天的道德和阶级斗争立场上,为了把段功塑造成符合今天的道德标准的正义的体现,却颇费了苦心。为了表示他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而非阻历史前进的反动者,就在第一幕里插入战败明二的原因是由于得到了百姓的帮助,而明二失败也是因为粮乏剽劫,失去了民心。为了替段功在异族朝廷做官开脱,在第二幕饮茶时加入了他对于蒙古人色目人的批评及对于种族偏见的慨叹,似乎段功虽未成为反抗异族的民族英雄,到底也坚持了民族融合的进步态度。郭沫若这样处理当然有他的理由,他突出正与邪的对立,进一步激发了观众对悲剧主人公的同情,更符合现实斗争的需要,这的确体现了郭沫若史剧的特色。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郭沫若对变态心理的探索是十分热衷的,历史剧中也不例外,但他的性变态者多是反面人物如汉元帝之流,在写正面人物的男女之情时,其感情都非常纯净,近于精神化、理想化,如屈原与婵娟,如姬与信陵君、高渐离与怀贞夫人,他们的关系都完全超乎性爱之外。这既是为了突出拯救国民于苦难之中,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主题,同时又显示了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席勒同样如此。海涅在《论浪漫派》中,曾提到席勒派与歌德派的争论,前者责备歌德不象席勒那样,在作品中塑造高大的英雄形象,只塑造一些漂亮的,庸俗的妇女形象,因而缺乏道德目的;后者则声称艺术与道德无关,世界上的道德观念是变化的,艺术则是永恒的,是独立的第二世界。《唐·卡洛斯)中的波沙候爵具有同《虎符》中的候赢相同的品质。他俩都有远大的政治胸襟,目光敏锐,以其智慧启发人们去救国救民。关键时刻,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自己选择了死。《华伦斯坦》中的麦克斯也是席勒凭借想象塑造的代表德国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理想的完美人物,他勇敢、忠诚,品德高尚,绝对忠于华伦斯坦,忠于爱情,忠于祖国。当他得知华伦斯坦的失败已无可挽回,就率领部下忠勇的队伍去冲击瑞典敌军,壮烈牺牲。
《唐·卡洛斯》中的中心人物不是西班牙王子卡洛斯,而是马耳他骑士波沙候爵,席勒通过他与国王、王后及太子的谈话,宣泄出一位自由战士的豪情壮志,可以说是席勒自己理想的化身。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简”主要就是指的这一部。同样,我们从郭沫若史剧中,也几乎每一篇中都可找出这么一个人物,他慷概陈词,表达出伟大的理想。如:
屈原: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里生,在和平里死,没有什么波澜,没有什么曲折。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要做成一个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贪生怕死。在应该生的时候,只是糊里糊涂地生。到了应该死的的候,又不能够慷慷慨慨地死。一个人就这样被糟塌了。 我们目前所处的朝代也正是大波大澜的时代,所以我特别把伯夷提了出来,希望你,也希望我自己,拿来做榜样。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屈原》)
这种用文艺来表现某种观念的倾向,也同表现主义的影响有关,但表现主义所表现的观念十分抽象、难解,郭沫若史剧则单纯得多,一言以蔽之,就是鼓吹民族气节,反对妥协投降。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席勒对郭沫若的最大影响在于对悲剧概念的理解上,他们都是把悲剧看作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的“悲壮剧”。古典主义主张强健、明朗的希腊式风格。郭沫若认为,“悲剧的戏剧价值不单纯的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发起人们把悲愤情绪化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悲剧的目的“是号召斗争,号召悲壮的斗争”。〔10〕郭沫若的悲剧创作所以一反一般中国传统悲剧作家缠绵、哀怨的情调,除个人气质外,同席勒的这种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于郭沫若和席勒的这种共同的悲剧观,就使得他们的史剧创作无论在内在精神还是外部形态上都有一致之处。首先是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服从现实斗争需要的意愿。席勒是一名鼓吹德意志民族自由、独立的反封建战士,他的作品都是因时而发。“狂飙运动”中,歌德的维特自杀,席勒的强盗则要反抗。他的《阴谋与爱情》通过对贵族青年斐迪南和平民女子露伊丝恋爱悲剧的描写,表现了对公候专制的强烈赠恨,成为“第一部德国的有政治倾向的戏剧”(恩格斯语)。拿破仑期间,他以笔为武器,号召斗争,写了《奥里昂姑娘》、《威廉·退尔》等爱国主义剧本。尤其是《退尔》,它回答了德国人民这样一个迫切的问题:人民是有权创造自己的幸福,反抗暴政以自卫的。它们成了1813年到1815年德国解放战争的预言。因此,席勒的友人洪搏德的夫人深信,“席勒如果活到一八一三年而还有一点剩余的健康时是一定会参军的”。〔11〕>郭沫若从事创作的出发点与席勒是完全一致的。五四时期,是为了反封建、反专制,而这时又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鼓吹全民抗战而创作抗战历史剧。我们可以看到,在选择历史素材上,他们所具有的一致性。席勒《奥里昂的姑娘》来自于英法百年战争时期领导法国人民打败侵略者的牧羊女贞德的故事,《退尔》取自十四世纪初瑞士联邦农民反抗哈布斯堡政权争取独立的故事。而郭沫若史剧中的史实也多是取自于历史上中华民族反抗民族侵略和人民反抗暴政的故事,如《虎符》《棠棣之花》、《屈原》、《高渐离》反映的是战国时期人民反抗强秦的侵略和暴政,《南冠草》反映了抗清义土夏完淳的事迹。这些作品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就《屈原》一剧而论,集中在一天的时间里概括了屈原战斗的一生,突出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人民的联系和不计个人生死荣辱,“为真理斗到尽头”的高贵品质。“雷电独白”,凝聚和汇集了国统区人民反抗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力量。那在黑暗中咆哮着、闪耀着的一切都同作者自我一道“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表明作者已同人民大众融为一体。独白中对黑暗丑恶的高度蔑视、彻底否定的的强烈感情,反映出作者对人民事业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在皖南事变后沉重的政治低气压里,这个戏在国民党中央所在地重庆多次演出,如同1804年《退尔》在魏玛、莱比锡演出一样,象雷电划破长空,收到了极为强烈的效果。
正因为历史剧要反映现实和理想,剧作家就不能完全拘泥于历史,而必须运用想像对历史事实重新加以创造。席勒和歌德都是这样做的。席勒认为,“悲剧的摹仿正和历史的摹仿相反”,史料必须非常精确,而悲剧却有“诗的目的”,表现某种动作以感动我们,悲剧可以自由处理历史题材。他说:“这是悲剧的权利——不,甚至可以说是义务——它应该使历史真实服从诗的规律,而在处理历史事实时,必须符合悲剧的要求。”〔12〕他写《奥里昂的姑娘》就完全改变了传说中圣女贞德的故事,如其中贞德对于所俘虏的英军将领发生爱情,丧失了战斗力而被捕,以后又清醒过来,挣脱枷锁,解救国王,终于在战斗中死去,都是席勒的虚构,与历史上被处以火刑的贞德的故事相去甚远。歌德在创作《哀格蒙特》时,也对其中的史实作了大量改动。后来他的学生爱克曼问他,为什么把哀格蒙特这个历史上的机会主义分子写成一个为人民爱戴的民族英雄时,他回答说,他要创造一个自己的哀格蒙特,不这样写,就不能达到创作的目的。郭沫若的看法与他们是相同的,他在1942年的《历史·史剧·现实》中对历史和历史剧的区别作了精辟的说明。他认为历史是科学,史剧是艺术,史剧家在创作之前必须先仔细研究历史。在这前提下,他说,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郭沫若在《王昭君》中虚构了汉元帝对王昭君的贪慕,在《屈原》中虚构了南后对屈原的陷害,这些可以说受到了歌德和席勒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浪漫主义诗人的共同特色。
席勒的许多戏剧都是诗剧,在散文剧中也往往插入大量抒情诗,这种形式有利于表现作家主观情绪和抒发理想。后来的德国表现主义作家借鉴了这一手法,用歌唱和韵文来强化内心情绪的表现,托勒的《群众与人》是典型的例子。对于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来说,这是席勒对他产生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郭沫若剧作不象曹禺,通过错综复杂的性格的、心理的冲突,展示人物间微妙的关系,以含蓄、凝炼、隽永的诗情来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隐秘;或田汉将传奇色彩溶入戏剧冲突中,通过悲欢离合的曲折情节以揭示人物热烈真挚、缠绵绯恻的情怀,而是在突兀跌宕、大开大阖的戏剧冲突中,使人物性格借助于强烈的对照、映衬和冲撞,出现大幅度的感情波澜,喷射出火山爆发般的激情,从剧中诗情的推涌中显示出一种雄浑奔放的美来。其抒情方式的特点,一在于直,二在于效果的异常强烈。这其中有席勒的影响,也有表现派、尼采的作用,同时也可视为他早年《女神》风格的延续。《屈原》中雷电颂一幕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它在戏剧性与抒情性的高度融合中将“时代愤怒”表达得激动人心,也使我们对郭沫若剧作壮美的特色有了深切的体会。
人物性格的单一化,这是席勒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和明显不足.勃兰兑斯谈到《威廉·退尔》时说:“《威廉·退尔》这个题材不是按照戏剧,而是按照叙事诗来构思的。每个人都没有鲜明的特性。把退尔从群众中突出出来,站在运动的顶峰,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13〕这可以说是写诗剧带来的影响,将一切人物的话语诗化,多半不能符合人物身份,如《退尔》中不管渔夫、牧童都能吟出华丽的韵文,就容易使人物性格、身份模糊。主要还是由于席勒抽象、唯心地从事创作,而忽略了历史和现实条件所致。他写剧本的目的不在于突出性格,塑造典型,而是要表现其壮丽的理想,充当时代的号角,所以就难免使人物性格由于服从主题而单一化、理想化,缺乏必要的发展,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及。后来的表现派作家继承了这一特点并推向极端,如卡夫卡的小说就以人物性格类型化、符号化为特征,却鲜明地体现着作者自己的个性、语言特色和理想。茅盾在谈到郭沫若的历史剧风格时说:“不拘泥于历史事实,而随意发挥,虽云自我作古,却非英雄欺人……。”〔14〕其中所谓自我作古就指的是郭沫若的这一特点。但对这种性格单一化特征也不能一概而论。郭沫若剧中的主要人物如屈原、高渐离、夏完淳、如姬、蔡文姬等,大都具有作者的自我气质,他们是性格相近的形象系列,其语言、个性与作者的语言、个性是同一的。相反剧中的次要人物和反面人物,大都不具有作者的自我气质,性格差别较大,人物个性化特征也较明显,如(卓文君》中的程郑,《屈原》中的张仪、《虎符》中的魏太妃等。此外这种缺陷在早期的历史剧中表现较明显,而《武则天》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人物语言的性格化特点非常突出。
郭沫若与席勒相接触于他与歌德接触在同一时期,但他二十年代的戏剧却主要受到歌德和现代派影响,席勒影响不甚明显。这说明他的戏剧中的社会政治倾向是逐渐增强的,早期剧作如《湘累》、《孤竹君之二子》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歌德和现代派的那种唯美主义倾向,而到了抗战时期,则自觉地以戏剧为武器来为现实斗争服务,提倡团结抗日。这时,席勒那种较为单纯、激昂的风格就更符合他的需要并对他的创作发生了积极影响。
注释:
〔1〕《前茅·暴虎辞》,《郭沫若全集》第一卷,第336页。
〔2〕《<苏武与李陵>楔子》,《郭沫若全集》第一卷,第344页。
〔3〕《暴虎辞·小序》,《郭沫若全集》第一卷,第336页。
〔4〕〔5〕席勒:《威廉·退尔》第88页、第126页,张威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6〕〔7〕《歌德谈话录》第108页、第38页。
〔8〕《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郭沫若全集》第六卷,第138页。
〔9〕《〈孔雀胆〉后记》,《郭沫若全集》第七卷,第272页。
〔10〕《出<虎符>说到悲剧精神》,《郭沫若全集》第十卷,第257页。
〔11〕张威廉:《<威廉·退尔>简介》,《威廉·退尔》,张威廉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12〕德文版,席勒《uberdietragischeKunst》,《Friedrich Schiller Samtliche Werke》Bd.5.Carl Hanser Verlag Munchen,1984。
〔13〕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第36页,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茅盾:《化悲痛为力量》,《悼念郭老》,三联书店1979年版。
标签:郭沫若论文; 席勒论文; 郭沫若全集论文; 德国文学论文; 阴谋与爱情论文; 屈原论文; 历史剧论文; 歌德论文; 威廉·退尔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