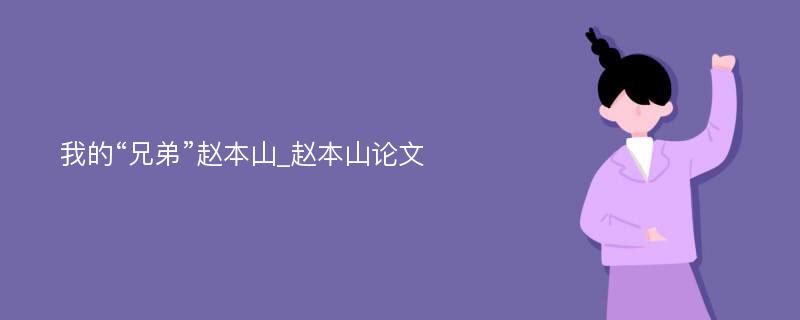
我“哥”赵本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赵本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起赵本山,首先得说说他的家乡。
从铁岭往东北方向走,有一条宽阔的大沟,直通吉林市。这条沟的南端是蒙古和罗沟,从京城通往吉林市的交通要道就从这里通过。这里古时有个驿站,叫蒙古和罗站。沟里有一条河,叫叶赫河。
蒙古和罗站设在一个叫“棉花”的地方。人们习惯地把这里称呼为“棉花街”。后来,这里成立乡一级建制的时候,嫌棉花二字太俗,就改称莲花。
在叶赫河岸边,出了两个出奇的人物:一个是清代著名的词人纳兰性德,另一个就是著名笑星赵本山。
莲花学校隶属于莲花大队,小学一至五年,初中六至九年。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
1974年9月1日,我从茶棚小学五年级升入了莲花学校六年级,念初中。星期一分座的时候,我和两个小学同学按事先的约定站在了一起,希望能分到一座。不料老师按照大小个儿重新排了一下。我恰恰遇上了一个新同学,他叫赵本山,家住在石嘴子沟,离莲花有三四里的路程。
同桌的那个“他”人到底咋样,完全是个未知数。看样子那小子挺淘的——我在心里嘀咕。
下了课,赵本山主动和我打招呼,自我介绍:“本人赵本山,赵钱孙李的赵,根本的本,大山的山,在家排行老三,大家管我叫‘小三儿’。”我放松了戒备的心理,觉得他这个人挺随和的,便也做了自我介绍:“本人李兴华,赵钱孙李的李,振兴的兴,中华的华。在家排行老二,大家的管我叫二弟,小的管我叫二哥。”
赵本山一听我的介绍就乐了,又说:“家中就我哥儿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说:“我一哥一姐仨弟弟,父母加上我,吃饭八双筷。”
赵本山说:“妈死爹出走,我的日子不如狗。”
我说:“老三老三你别愁,苦日子总会熬出头。”
那年赵本山十六,我十五。赵本山的个头比我稍高,有一米五左右。他长得挺白,这在我们农村孩子中不多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黑亮黑亮的,显露出一种精明和狡黠。正是二八月乱穿衣的时候,山区的气候变化较大,白天依然挺热,早晚却有些凉了。赵本山和我一样仍然穿的是单衣单裤,衣裤的里面就是光溜溜的肉皮儿。走路的时候两腿中间的家伙们也跟着无拘无束地悠荡,舒服自在。赵本山的脚上,是一双破旧的黄胶鞋,上面裂开好几道口子,大拇哥已经探出了头儿在外面望风呢。
本山是个苦人儿。他出生在1958年。由于严重缺乏营养,母亲的奶水不足。看着孩子饿得“吱哇”直叫,爷爷舍上了老脸抱着他东家走西家串地要奶吃。有一次老人背着本山到别人家去讨奶水,在冰天雪地里跌了一跤,把本山扔出去老远,休克了老半天。大家都以为小三儿这下完了。小三儿却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像是睡了一大觉。
本山5岁的时候,在生产队里当“大嫂队长”的母亲张淑琴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撇下了丈夫和孩子撒手而去。就在妈去世的那天,小本山一不小心坐进了火盆里,烧了一屁股大泡。本山七岁的时候,父亲赵德仁因为和队长打架,被迫背井离乡,到黑龙江去谋生,只留下本山的爷爷领着四个孩子过日子。
本山最常去的地方是五奶、老叔,还有瞎二叔赵德明家,这些好心的亲属不拿本山当外人,赶上饭就让他吃一口,这样大大缓解了本山的窘境。在二叔那里,本山还学会了拉二胡、唱二人转,得到了艺术的启蒙。
十四岁那年,本山的爷爷去世,大哥和姐姐都独立成了家,二哥去当了兵,年少的本山只好自立门户。本山不得不上山去刨些地龙骨、和尚头之类的药材,换两个钱。有时候也采些山野菜、蘑菇什么的,能换钱的换钱,不能换钱就自己吃。为了采药,本山的身上剐了多少个口子、摔了多少次跟头,恐怕他都记不清了。
为了填饱肚子,本山想尽一切办法,采野菜、挖耗子洞。这里所说的耗子不是普通的灰老鼠,而是生活在田地里的一种田鼠。这种田鼠非常“勤劳”,秋天的时候在洞里储备了大量的粮食,以应付漫长的冬天;而且田鼠有一种本能,它们所储备的粮食都是籽粒饱满的好粮食,不好的就不要。一到了秋天,几乎所有的田地里都有人在忙活,东张西望地寻找老鼠洞。
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加上在学校打打闹闹和往返好几十里的山路,我像一只饿狼一样,特别地能吃。每天,母亲都要在我的书包里装上几块大饼子或者是几穗苞米,加上一块咸菜疙瘩,这就是我的午餐。
每天的中午,我在学校的教室里吃我的午饭,其他家远的同学也都是这样。可是本山总是不在教室里,等我们吃完了饭他就回来了。我就尾随在后面偷偷观察,原来他根本没有回家,也没有带饭,而是躲到没人的地方一个人呆着,往肚子里咽口水,上课的时候,赵本山虽然故作镇静,但是他的肚子一个劲儿地“咕噜咕噜”叫。
第二天中午下课以后,本山又要往外走,我一把拉住他,说:“本山,帮个忙,我今儿个大饼子带多了,你帮我吃一个,就别回家了。”
本山说:“你别扯了,你家八口人,粮食本来就不够吃,怎么能带多呢?”
见他不要,我硬把他拉回到座位上,把大饼子塞给他。他犹豫了一下,看看手中的大饼子,冲我笑笑,就大口吃了起来。一边吃他一边解释说:“这几天闹粮荒,有了早上的就没了中午的,这老肠家和老肚家老打架。”
我说:“我妈每天都给我带三四个大饼子,以后咱俩分着吃吧。”
带大饼子还好说,带四个我们一人两个;带三个我们就一人一个半。但是带饭的时候就不行了,高粱米饭稀泡涨肚,装了一饭盒也不够我们吃半饱。我买了一个特大的饭盒。饭盒的上层有一个装菜的小盒,我把它拿掉,也用来装饭,这样就能多带一点儿,我们也能吃得饱一点儿。
回家吃晚饭的时候,我像吃“冤家”似的,拼命往肚子里填东西。看我这么能吃,我妈以为我的饭量长了,便在给我带饭的时候多带了一个大饼子,这样本山就可以多吃一个大饼子了。回到家我仍然很饿,就逮着什么吃什么,地里的大葱、白菜都没少吃。
妈觉得奇怪,就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个不会撒谎的孩子,只好实话实说。妈半晌没说话。末了,她说让我哪天把本山带来,她要亲眼看看这个苦孩子。
星期六上学的时候,我把妈的想法和本山说了,他竟兴奋得一天没上好课。
晚上,妈特意做了两个菜:一个是炒鸡蛋,一个是炸鱼干儿。要知道,这样的菜我们平时是吃不着的,只有来了贵客才能借光解解馋。
晚饭后,我们坐在一起聊起家常。妈打听本山家里的情况,本山一五一十地把家里的事都说了。
妈听了本山的叙述,心里很难过:“一个孩子家自己生活,多么不容易呀。”
本山倒显出不太在乎的样子:“习惯了,也就不觉得苦了。再说还有大伙帮我。这阵子粮食不够吃,上学没带的,就只好饿肚子了。要不是兴华发现,把他的饭分给我一半儿,说不上饿到啥时候呢。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
妈说:“感谢啥。你和兴华是好兄弟,你就和我的儿子一样。”妈把本山拉到自己身边,给本山整理整理衣服,说:“从今儿个起,兴华上学就带两份饭,你俩一人一份。大娘家再困难,还能供得起你。”
本山嘴角翕动着,眼睛里有些晶莹的东西要往外流。
本山到我家,见啥活儿干啥活儿——铲地、割地、打柴、扫院子、喂猪喂鸡等等。本山的个头儿和我差不多,他的衣服洗了就穿我的。后来妈给我做衣服时,就给他也做一件。从此他一改往日“鞋儿破,帽儿破”的形象,变成了一个衣衫整洁的少年。
有一天晚上,本山一本正经地跟妈说:“大娘,你对我这么好,给我当干妈吧。”
妈说:“只要咱娘俩感情好,认不认干妈也没关系。”
本山跪在地上说:“你这个干妈我认定了,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妈赶紧扶起了本山,眼里含着泪说:“好好,我认你这个儿子了。”
“妈——!”“儿子——!”
摘自《深圳商报》
标签:赵本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