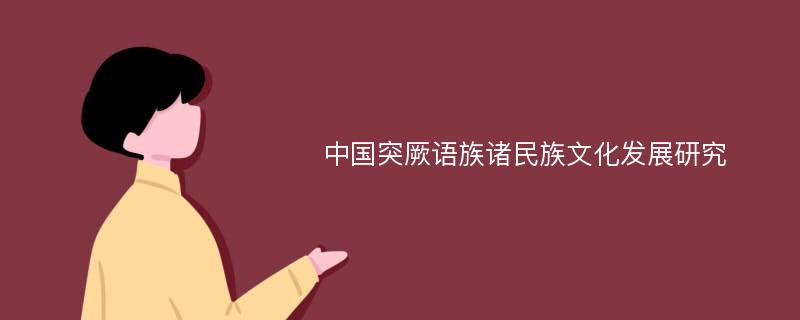
孙岿[1]2003年在《中国突厥语族诸民族文化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术界通常把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称为“突厥语族民族”。我国突厥语族诸民族主要分布于新疆、青海、甘肃一带西北地区,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撒拉、裕固七个民族,约995万人口(2000年),其中10万人以下(含10万人)的人口较小民族有4个,他们是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撒拉族和裕固族。突厥语族民族以其勤劳和智慧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各自创造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突出表现在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等各个方面。 操同一语族语言的民族,在语言上必然有共同的起源,同时在族源上也曾经有过密切的联系。但是,在文化上对现存同一语族民族,我们就很难做出肯定的结论。从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出这样两个问题:使用同一语族语言的民族,在文化上有何异同?他们分布在不同区域、受周围民族的影响,其文化的变迁又有何不同?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将突厥语族诸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前言部分简单介绍了“突厥语”一词的科学概念和突厥语族语言的共同特点,当今世界突厥语族民族的主要分布区域和我国突厥语族诸民族的民族成分、人口、聚居地区。 第一章参考近期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概述我国突厥语族诸民族的族源及历史形成过程。 第二章根据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各民族的生计方式和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特点,因此,本章结合我国突厥语族诸民族的人口分布特点及复杂的生态环境特点,把我国突厥语族诸民族划分为四种经济文化类型组(盆地草原游牧型、绿洲农牧型、高山草原畜牧型、山区农耕型)并分别加以阐述。 第叁章根据历史民族区(或称历史文化区)理论,论述新疆突厥语族诸民族既受中亚伊斯兰大历史文化区的影响,与中亚大历史文化区有着某些文化特征上的相似,同时,新疆又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突厥语族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在与中原汉民族的交 往中吸收了诸如语言、制度、道德等诸方面的因素。由于新疆处在伊斯兰 文化和国家主流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两种强势文化的交汇区, 因而处于两套文化价值观的调适阶段。而甘青地区的撒拉族、裕固族都处 在各种大历史文化区的边缘地带,远离各文化区的核心地区,因而形成了 一种复合性文化(混合性文化)。 第四章从衣、食、住、行、用五个方面论述我国突厥语族诸民族的 物质文化。在传统生计方式作用下,突厥语族谱民族的生产、生活资料多 取材于自然生态环境,所以他们的物质文化又分别表现出草原、绿洲、山 区的不同文化特点。通过这些物质文化也反映出他们传统习俗与信仰方面 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第五章伊斯兰文化是绝大多数突厥语族民族精神文化的共同特征, 本章首先分析了我国突厥语族民族的伊斯兰文化特征,通过解读完厥语族 民族的礼俗观、色彩观、数字观、方位观。来发现外来的伊斯兰文化是如 何与原来的突厥文化相结合的,再通过音乐、舞蹈、文学的分类,发现在 伊斯兰文化的外衣下,绿洲、草原、山区各民族居住环境对民族文化的重 大影响。 第六章 以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为代表的突厥语族民族亲属制分属两 种类型(肌 亘系型和二分旁系型),它们与维、哈两民族历史上和现存 的婚姻习俗有密切关系。可是,在对称时,都按照年龄把所有亲属划分为 叁个老、中、幼叁个等级,它们不仅使用于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亦可称呼 没有亲属关系的人。这也是突厥语族民族亲属称呼的共同特点。笔者认为, 这种亲属称呼泛化的现象与其相互隔离的居住环境和封闭半封闭的自然 经济社会有关系。在一片片绿洲和牧场构成相互独立的小经济区域,人们 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重合,并通过宗教得以强化。在此种社会中,人们 不得不通过扮演家庭、社会角色来维持类似亲属间的社区团结和稳定关 系。 第七章当代我国突厥语族民族信仰的两种宗教(伊斯兰教和藏传佛 教)出现了明显的相反的变化趋势,前者强化,后者弱化。本章分析了宗 教强化和宗教弱化的原因,并结合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运动,说明伊斯兰 教与现代化的关系。最后阐明,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伊斯兰教与现代化 协作的基础与前景。 第八章论述我国突厥语族诸民族文化变迁的必然性和特殊性。随着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加快,市场商品极度繁荣,突厥语族诸民族在物质文2g 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都从一元向多元化方向转化,少数民族从事多种g 经营的主动性也正在逐步提高。随着牧民定居项目的基本完成,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裕固族等民族由原先单一的游生产变为农牧兼营,传统的草.原游牧型
郭宏珍[2]2007年在《古代突厥语族诸族的家庭组织》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意义上的家庭并不是自古就存在的,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家庭组织与经济生活和文化类型密切相关。经济生活不同家庭类型也不相同,如农业民族的家庭与游牧民族的家庭差别较大。文化类型不同家庭类型也有所不同,如西方人的家庭与东方人的家庭不同;伊斯兰教信徒的家庭与基督教信徒的家庭有差异。古代突厥语诸族主要从事游牧业,其家庭组织具有浓厚的游牧色彩。自突厥语诸族信奉伊斯兰教后,家庭组织又具有
张国云[3]2006年在《维吾尔人宗教生活的人类学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是关于新疆且末县托乎拉克勒克乡扎衮鲁克村维吾尔人宗教生活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当代维吾尔人神圣宗教生活中宗教观念、宗教行为、宗教组织以及宗教场所的描写与分析,以及世俗生活中维吾尔人的人:生通过仪式和扎衮鲁克村几户典型家庭的宗教生活的描述与分析等。 本论文首次从人类学的角度将当代维吾尔人的宗教生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研究。论文以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为搜集资料的方法,以在扎衮鲁克村的第一手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运用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解释的理论,较为全面地描写了当代维吾尔人的宗教生活,分析了宗教作为社会文化形式所具有的价值和功能,为人类学的宗教研究提供了一个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个案。 论文主要包括叁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维吾尔族和田野调查点的概况介绍,包括维吾尔族族源、族称、人口分布、语言文字、宗教的历史演变、且末县概况和扎衮鲁克村概况,目的在于交代清楚自己田野点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状,为论文的写作提供一个场景介绍。正文包括两部分内容:上编“神圣的召唤”,通过围绕维吾尔族宗教意识、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和宗教场所进行的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所得资料,对维吾尔族宗教四要素进行描述和分析,展示维吾尔人神圣宗教生活的全貌,分析和说明维吾尔人的宗教意识、宗教行为、宗教组
赵金哲[4]2016年在《新疆巴里坤哈萨克族舞蹈调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巴里坤哈萨族克族舞蹈是流传在哈密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的民间乐舞,其艺术形式包含了民间传统音乐与舞蹈。舞蹈在民间表现形式上可分为生活劳作、模拟动物、宗教习俗、劳动赞美等几种类型。每种类型的舞蹈在乐律乐调、节拍节奏等音乐形态各个方面有着一定的相同或相近之处,但舞蹈表现风格、语言姿态、步伐、表现的生活场景等方面又具有自身特点。新疆巴里坤哈萨克族作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所折射出的草原文明以诗歌、音乐、舞蹈等方式逐一展示,一方面巴里坤古“蒲类国”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巴里坤处于新疆“东大门”的显要位置,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过程中都是一种先知先觉的接收过程,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融合过程突显出哈萨克族以舞蹈为媒介的重要性。巴里坤哈萨克族舞蹈作为新疆哈萨克族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舞蹈内容在表现形式与风格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由于地理位置与文化交流的特殊性,从而产生巴里坤县哈萨克族舞蹈有着自身的独特之处。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石,对巴里坤哈萨族民间传统舞蹈传承人进行个案访谈,在传承谱系的基础上对巴里坤哈萨克族舞蹈的存续现状有了基本了解,对巴里坤哈萨克族舞蹈的表演场域与流程进行观察与研究;从而提出巴里坤哈萨克族舞蹈在表演过程中可表现为“同舞不同曲或同曲不同舞”的观点,这种文化共生中的表演是巴里坤草原的辽阔性给巴里坤哈萨克族人带来胸怀上的开阔、眼界上的高瞻与视野上的多维。由史至今,居住在巴里坤的哈萨克族人的艺术传承是以“口传心授”为主,这也让巴里坤哈萨克族成为草原文明的坚守过程中以民间传统乐舞的方式来延续“自我”的记忆。巴里坤哈萨克族舞蹈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在各种活动中流露出对自然的敬畏、对力量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对秩序的恪守以及对记忆的绵延,这种非舞台性的表演形式、非稳定的方式坚守着巴里坤哈萨克族民间的文化;故而,巴里坤哈萨克族民间文化唯有仰视,方能看到巴里坤民间文化的闪亮。
王烜[5]2013年在《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女性传承人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利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和女性学的相关理念,对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女性传承人进行研究。男性与女性在文化传承中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传承模式,本文通过历时、共时与现时的视角,分析了裕固族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发现裕固族女性地位相对较高使她们成为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中坚力量。而新时期的国家非遗政策、官方认定对裕固族女性传承人的地位更加起到了促进作用。首先,绪论梳理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理论,历代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了笔者与裕固族女性传承人研究的缘起。第一章描述了肃南裕固族的文化生境,以速写的手法生动细腻地呈现了肃南裕固族的地域特征和地域文化。这一章概括了当代裕固族的叁个特点: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民族宗教信仰经历“宗教弱化”到“宗教复兴”,呈现出强烈的“宗教世俗化”倾向;裕固人思维开放、重视教育。“速写”描绘了笔者对裕固族的初步印象,在整篇文章上起到奠定感情基调和行文氛围的作用。第二章中,笔者分口头文学、手工技艺两个部分概括了裕固族“非遗”名录,并通过文化女性主义的理念和口述史的书写方法呈现了裕固族女性传承人的生活空间。她们是杜秀兰、钟玉珍、郭金莲、郭玉莲、柯璀玲、白晓琴、杨海燕等女性传承人,占整个裕固族女性传承人数量的80%。第叁章是本文的重点,也是与女性研究结合最为紧密的一章。笔者首先探讨了以裕固族特殊婚姻形式为基础的女性地位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裕固族特殊婚姻形式“帐房戴头婚”和“勒系腰婚”产生的原因并非“母权制遗俗”,而是与周边民族的文化涵化和旧社会落后的生产力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特殊婚姻形式只是裕固族女性地位较高的表层原因,深层原因其实是裕固族的游牧民族属性。游牧民族女性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因而地位相对较高。最后,笔者分析了裕固族女性地位与传承人身份的双向互动影响,提出:历史特殊婚制、游牧民族属性和传承人身份认定是裕固族女性地位较高的叁个主要原因。第四章是功能性的一章,分析了裕固族“非遗”女性传承人的传承特征和保护措施。裕固族“非遗”女性传承人具有传承机制和传承意识日趋完善、逐渐进入礼仪风俗传承体系、亲缘传承仍为主要传承方式、传承呈现“速学速成年轻化”等特征。最后,笔者总结了裕固族“非遗”女性传承人的保护措施,如积极应对民族语言流失,让传承人自己研究自己,对其进行技术培养,并要求社会为她们提供更多的传承机会和政府支持。本文期望运用一种生动的、鲜活的、知性的写作方式和深厚的人文关照向读者呈现裕固族的历史文化与时代风貌,使读者产生对裕固族及裕固族女性美好的感性认识。
李奋[6]2010年在《新疆宗教文化生态现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疆地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区,具有突出的多元化特征。民族、语言、文化习俗、价值取向、信仰等都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新疆的历史从远古开始,就呈现出开放的态势,外来的人种、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不断而且持续的进入新疆地区,长期地交融、演变以至发展到今天形成多元化的宗教文化生态格局。在新疆宗教文化生态演变的历史上,有过如今已经消逝了的祆教、摩尼教,有过叁度传入的基督教,曾经是世界的佛教中心,也曾经历过伊斯兰化。宗教的传入、流变、断裂、适应与更新、古老与生机都交织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当代新疆,伊斯兰教兴盛发展,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又一次发展,一元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是当代新疆宗教文化生态格局的最主要特征。论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介绍了宗教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来源、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将其应用于新疆地区宗教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第二章首先回顾了新疆宗教文化生态形成的自然、文化和生态生态环境,说明新疆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复杂和多样的,社会生态环境是相对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是丰富多元的。并且介绍了本论文的两个田野点喀什和伊犁地区的概况;第叁章对于新疆宗教文化生态格局的特点进行了总结:首先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文化生态区域,具有和内地以及中亚伊斯兰教不同的特点;其次,南疆以伊斯兰教一元性宗教为主的特点和北疆以伊斯兰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特点形成鲜明的对比;第叁,新疆的宗教文化生态格局具有开放性和封闭性的特点;最后,新疆宗教文化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主要是由于新疆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和宗教极端主义同时并存,新疆宗教与内地宗教文化交流较少以及大量不稳定的社会群体的存在而造成的。第四章,主要分析了在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全球趋势下当代新疆宗教文化生态所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分析了处在多重张力之中的新疆宗教文化生态现状,并对新疆地区的宗教政策和管理模式进行了反思。第五章对新疆地区宗教文化生态平衡构建的理论可能性和实践途径进行了探讨,得出平衡的宗教文化生态的构建需要的是对话和交流的结论。第六章结语,通过对于论文主要内容和观点的回顾,再次强调新疆宗教文化生态平衡对于新疆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新疆宗教文化生态研究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观照新疆宗教,在这个视角之下,首先是将新疆宗教看做一个开放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其次,是从新疆的角度出发来思考新疆的宗教问题,新疆就不仅仅是中国的西部边疆,一个民族宗教问题复杂而危险的地方,一个当今地缘政治敏感而微妙的中心,一个距离国际恐怖基地数百公里之遥的火药桶。而丰富的民族语言文化宗教是新疆得天独厚的文化遗产与优势,优越的区位优势将不仅仅是新疆经济成为周边国家经济的中心的可能,稳定和谐的新疆应该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支点,同时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展示和分享区。
刘烨[7]2009年在《新疆乌孜别克族民间信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乌孜别克族是世居新疆的民族之一,从历史上看,乌孜别克族是由古代中亚众多的隶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居民经过长期融合而成的。虽然乌孜别克族现在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但在其民族发展历史上也信奉过多种宗教。而且这些宗教信仰在乌孜别克族民间影响甚大,构成了乌孜别克族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文章的第一部分对乌孜别克族形成过程与现状进行了研究。乌孜别克族的祖先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从锡尔河以北金帐汗国境内迁来的游牧民,他们带来了“乌孜别克”这个称呼;二是中亚河中地区的原有农业定居民。然后分析了乌孜别克族宗教演变的情况。文章的第二部分研究了乌孜别克族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然物的崇拜与禁忌,对原始神祗的信仰,繁杂的鬼灵观念,对英雄祖先的崇拜,节日庆典的仪式习俗、人生重大阶段仪式中原始信仰的遗存以及受萨满文化影响颇深的宇宙观与世界观等具体的民间信仰。并提出乌孜别克族的民间信仰是在万物有灵观念基础上产生的受萨满教与伊斯兰教影响颇深的自然崇拜、鬼灵信仰的综合体,包括在这些信仰基础上产生的以巫术为基本逻辑的禁忌、占卜等活动。文章的第叁部分总结出乌孜别克族民间信仰的特点是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信仰神祗的多元性以及组织上的自发性和松散性。并且其民间信仰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具有较为松散的组织体系,是区别于正式宗教的一种较低层次的信仰方式。此外,乌孜别克族的民间信仰通过与伊斯兰教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融汇,说明宗教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对立和排斥,而是可以相互和谐共处的。文章的第四部分对乌孜别克族民间信仰与乌孜别克族社会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研究,说明乌孜别克族民间信仰在其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和影响,以便从中最大程度地挖掘其深层涵义与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正面价值。由于民间信仰广泛渗透到社会底层的每一个角落和广大民众的头脑里,因此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不容忽视的大众文化资源。在研究中国宗教现象和研究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时,必须给予民间信仰极大的关注。要对其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进行正确的引导并趋利除弊,使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努力使之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可以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王彦[8]2006年在《游牧民族颜色词的文化认知研究》文中指出颜色词是语言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有颜色词。国内外很多语言学家和学者都从不同方面对颜色词进行过研究,成果颇丰,但其中涉及我国少数民族语言颜色词的研究成果很少,且很零散。本文以我国游牧民族语言的颜色词为研究对象,结合文化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对颜色词进行研究,是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实际研究的一次尝试。 本文通过调查母语人,请教专家以及查找文献等方法收集语料,对哈萨克语和蒙古语颜色词的词汇系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写,并通过与汉语对比,着重分析游牧民族颜色词白、黑、红、黄、绿、蓝、褐色的隐喻认知特点。经对比分析,本文获得一些初步的认识:一方面,由于世界语言文化具有共同的基本内核,哈萨克语、蒙古语和汉语在隐喻认知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绿色都象征生机和活力,白色都具有纯洁的象征意义,也都有空白、穷等象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不同语言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中,不同的文化积淀会在隐喻中留下不同的痕迹。与汉民族的崇黄尚红轻黑忌白不同,游牧民族传统文化是尚白喜褐轻红的,这种隐喻认知取向可以在颜色词组成的词、成语、谚语中体现出来。论文在分析游牧民族隐喻认知特点的基础上,又进而深入到语言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中,试图从自然环境、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对其隐喻认知特点加以合理的解释。 游牧民族颜色词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表示牲畜毛色的颜色词非常
金善基[9]2006年在《新疆维吾尔族的坎儿井文化》文中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的西北部,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区,占全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除维吾尔族外,还有十多个民族聚居。维吾尔族人口有8,399,393人(2,000年),约占全自治区人口总数的45%。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区是南疆塔里木盆地周边的和田、喀什、库车、阿克苏以及吐鲁番、哈密等地,这些地区维吾尔族人口占维吾尔族人口总数的90%左右。 维吾尔族的传统经济是农业,由于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干旱少雨,发展水利灌溉就极其重要。自古以来,新疆的农业灌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开水渠或水槽引水,另一种是开凿坎儿井。与一般农业灌溉系统相比,坎儿井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水利工程,是为适应干旱地区绿洲中的自然环境与地理条件而创造的农业灌溉系统。因此本文导言部分简单介绍论题的目的和意义。论文主要运用的是民族学文化理论。坎儿井文化是属于物质文化,但它的发明、构建的过程、作用方面的成果也属于精神文化。从坎儿井的今后发展方向、怎么保护等方面来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方面都应同时考虑。论文的研究方法是实地调查法,历史文献法与文化比较法。 第一章 介绍新疆的地理环境,维吾尔族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与维吾尔族的衣食住行用中的农耕文化的影响;坎儿井与维吾尔族农耕文化的关系。 第二章 坎儿井的起源有叁种说法,其一是新疆坎儿井来源于中亚;其二是坎儿井来源于中国内地;其叁是坎儿井来源于维吾尔先民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与地理条件的创造发明。最后是本人的观点。 第叁章 坎儿井的结构与施工方法。先介绍坎儿井的类型与结构。坎儿井的类型有叁种:山前潜水补给型,山前河流河谷潜水补给型,平原潜水补给型。坎儿井的结构由竖井、暗渠、明渠、涝坝等四部分组成。坎儿井开挖时根据耕地或拟垦荒地位置,向上游寻找水源并估计潜流水位的埋深,确定坎儿井的位置。根据可能穿过的土层性质,考虑暗渠的适宜纵坡。一般从下游开始,先挖明渠的首段和坎儿井的龙口,然后向上游逐段布置竖井开挖,最后挖暗渠。掏挖空一口深十米的竖井,出土量就有上百甚至数百立方米。一条坎儿井,有数十、上百座竖井。加上绵延数千米的地下渠道,该是多大的土方工程!而在遥远的古代,这些土石都得靠人的两手,一锹一镐挖出,一筐一筐提起。惟一的机械,就是一具辘轳。这真是十分艰巨的工程。 第四章 坎儿井的特点、发展现状与问题。坎儿井在吐鲁番和哈密盆地至今仍发挥着效用,究其原因,是坎儿井具备叁大优点:其一,不用进水工具,利用地形的自流灌溉。其二,施工工具简单。其叁,坎儿井出水流量相当稳定。坎儿
步少华[10]2010年在《当代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关系探析》文中指出本文从历史、理论、现状叁个角度依次切入分析了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关系,并在文章最后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对策给出建议。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简称“双泛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后期产生的两种社会政治思潮。泛突厥主义产生于沙俄,后传入土耳其和中国新疆,主张突厥语民族的联合、统一甚至独立。泛伊斯兰主义由伊斯兰教着名学者哲马路丁·阿富汗尼首倡,宗旨是伊斯兰世界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哈里发帝国,以抗击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近现代史上,两种思潮发展出较复杂的关系:在沙俄和中国新疆,两者关系较为亲密,而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晚期),两者关系则较为疏远。从理论角度分析,双泛主义是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两种思潮:泛突厥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支,而泛伊斯兰主义属于宗教思潮。然而由于泛思潮的共性等原因,两者间的联系性也是十分紧密的。总体上讲,联系性甚至要大于差异性。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在诸多国际因素的影响下,双泛主义关系渐趋呈现出一种日益国际化、极端化的特点。鉴于两种思潮与我国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之间复杂关系,我国政府应该制定出一套更加合理有效的应对方案。
参考文献:
[1]. 中国突厥语族诸民族文化发展研究[D]. 孙岿. 中央民族大学. 2003
[2]. 古代突厥语族诸族的家庭组织[J]. 郭宏珍. 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 2007
[3]. 维吾尔人宗教生活的人类学考察[D]. 张国云.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4]. 新疆巴里坤哈萨克族舞蹈调查研究[D]. 赵金哲. 新疆师范大学. 2016
[5]. 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女性传承人研究[D]. 王烜.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6]. 新疆宗教文化生态现状研究[D]. 李奋.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7]. 新疆乌孜别克族民间信仰研究[D]. 刘烨. 新疆师范大学. 2009
[8]. 游牧民族颜色词的文化认知研究[D]. 王彦.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9]. 新疆维吾尔族的坎儿井文化[D]. 金善基.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10]. 当代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关系探析[D]. 步少华. 外交学院. 2010
标签:中国语言文字论文; 突厥论文; 哈萨克族论文; 游牧民族论文; 民间信仰论文; 巴里坤论文; 坎儿井论文; 乌孜别克族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维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