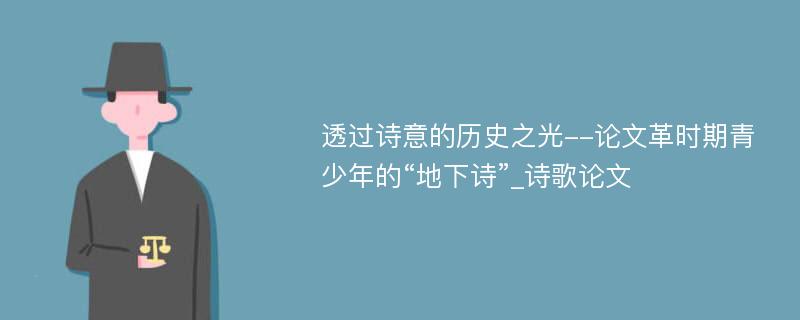
穿越历史的诗性之光——论“文革”时期青年“地下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诗论文,之光论文,文革论文,诗歌论文,地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文学史研究的深化、拓展角度来看,陈思和先生主编的“潜在写作文丛”(武汉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无疑具有突破性意义。丛书的编选者通过打捞大量零落各处的“文革”地下文学史料,把在1990年代末提出、而后遭到知识谱系层面质疑的“潜在写作”这一文学史概念重新梳理,从而实现了文本现实的物态化和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合法化。具体就诗歌这一特定文学类型而言,该丛书中的三大本诗选——《暗夜的举火者》、《青春的绝响》、《被放逐的诗神》)——分别收集了“文革”时期贵州、上海和北京这三个主要青年诗歌群落的作品,使1980年代就已发现但一直缺乏深入挖掘的“文革”地下诗歌首次获得了整体性的“出土”,让特殊年代被遮蔽的诗性之光穿越历史敞亮了自身。
“潜在写作文丛”凸显了这样一个文学史实,即虽然潜在诗歌的创作力量包括了老一代和青年一代,但“青年一代是主要的生力军,在诗歌创作的数量、质量上更具有实力”[1](PP.1~17)。而从很多现有资料来看,“文革”时期青年一代的“地下文学”实践活动基本上都是诗歌创作。这和“文革”公开创作的“非诗”局面构成巨大的张力性反差。如何索解这一文学史现象背后的奥秘?深入“潜在诗选”具体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在价值荒谬、精神贫乏的特殊年代,这些文学青年对“做一名诗人”有一种高度自觉的追求,他们对诗人身份的自我确认,正是“文革”时期产生大量“地下诗歌”的主体心理机制。
从身份标志看,诗人是人类精神和语言的探险者,“是能够感受到多数人所感受不到的东西的人,是能够表达别人想表达而表达不出的感受的人,并且这种感受只有用诗的形式才能得到最好的表达”[2]。尽管现代诗人徘徊在工具理性和审美理性之中,有的在启蒙理想的驱动下,自觉担当民族、人民的代言人,采取外向型视角,将民族苦难和人生不幸摄入笔下;有的向内转,以追求自由和纯美为旨趣,营造心灵之镜和诗性之瓮;还有的则较好地缝合了二者,将现实和艺术、个人和群体融为一体,如此种种,创作个性存在明显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文学环境正常时期,诗人们大都一致存留了自己探险于精神和语言的身份符码标志。然而,随着文学政治高度一体化的趋势,诗人的身份逐渐被固定为时代的“歌者”。早在1950年代初期,一些三四十年代成名的现代主义诗人就几乎曲尽人散了。如卞之琳一改自己空灵奇幻的艺术思维,转向写赞颂江南农村人民的新生活,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诗篇。因为处于大一统格局中,作家只能从事“颂歌”与“赞歌”式的主旋律写作,艺术形式只剩下一层单调而干枯的外壳。到了“文革”时期,公开状态下的诗坛景观是可想而知的。经历了“大众化”、“新民歌”运动之后的诗人更加“失声”了,诗歌创作让位于工农兵。如工人作者黄声笑1968年作的《长江万里一片红——热烈欢呼革委会成立》,歌词“长江两岸响春雷/红旗漫卷武汉关/处处成立革委会”,其“伪诗歌”面目昭然若揭。面对这种虚假的“诗”,任何成熟的诗人都难免对“时代诗人”的身份产生质疑甚至羞愧。
但“潜在写作”状态下的情形却不同了。当时,这些青年有的上山下乡,有的留在城市“待业”或当临时工人、代课教师,有的是“黑五类”子弟。他们身在时代中心的边缘,又处于建构自我认同的心理时期。“根据艾力·艾力克逊(Eric Erikson)的解释,青春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种稳定的身份感”,身份“认同”这个中文译词,本身给人一种“有求于外”的印象。这可以从两个意义上解释:第一,“人只有在与他人的比较和辨别中,才能使自己的身份即具有自我特性的意识得以形成,并使这种意识所参与塑造的特性呈现出来,从而获得有效的标识”;第二,对人来说,特性的确定性和统一状态是“通过其在社会环境中不断和他身外的或未曾预料到的经验相遇,并把某些经验选择转化为属于自身的东西”,因此“身份是一种建构的过程”[3](P.87)。而确认身份是人们“寻找生存意义的一种方案”[4]。面对时代精神的废墟状态,青年人渴望在个体内心中建立一种“自我认同”,因为只有通过确立这种令其满意的“自我”,他们才能抵抗身外的混乱和荒谬,不至于陷入生活意义的失落和虚空。就这样,诗人身份成为他们最终寻找到的“自我”认同目标。贵州的哑默在《美与真》中这样体认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诗人……我的诗是人类永恒的期待和向往……是心灵和情感的呼唤。”不需要谁来冠冕,也不需要外界的承认,哑默自封为诗人,并以此作为精神通道,朝向一切美的所在。即便当时没有发表的可能,哑默仍在拟想中对读者表述艺术衷肠,抒写着诗人的“墓志铭”。“我是一个贫穷的人/留给你们唯一的遗产/是没有写完的诗章……我的诗写给所有的人/一直爱着我的人们/让它能给你们一点微茫的慰安……我把自己完全献给世界”(《最后的歌》)。上海女诗人张烨勉励自己“始终热爱诗歌的金字塔/热爱这黄金光照下的孤独和博大”,做“自己的使者”(《静静伫立在海边》)。白洋淀诗人芒克则将诗歌视为心灵的救赎,“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象/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十月的献诗》)。可见,诗歌写作成为一代文学青年的存在方式。
除了个体生命意义层面的追求,青年诗人在特殊语境中这种自觉、强烈的“诗人”身份认同,也来自于对时代青年另一种身份—“造反者”形象的警惕。上海诗人钱玉林的自我身份建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比较和参照。在现实中,他看到了同龄人的荒唐举动:“他们让教授点燃/修改多年的手稿……他们让歌唱家/承认歌词是黑色的/旋律中有毒……”(《他们的1966》)诗人识破了“他们”出席各种“盛宴”的“纵火者”和“凶手”的身份,在这一外界参照下,他决心从自己的阅读经验中寻求自我价值体系,并悟到了“诗人”永恒的魅力。在《莎士比亚》中赞颂:“你浩荡的智慧像是无际的大海/你把傲慢的时间关在了门外。”以伟大诗人和诗篇作为精神引领,最终确认自我的诗人身份认同。他也清醒地看到了当时诗歌受难的命运,但依旧坚持在暗夜中守护诗神。他对缪斯女神呼唤到:“但我知道你们不会死/你们会重新降临/选择一个欢乐的日子/一如绝世的阿佛洛狄特/从大海黎明的浪花中诞生。”(《地下的缪斯》)就在不断和古今中外诗人的神会中,年轻的心以诗人的身份认同而觅取精神上的尊贵。
在白洋淀诗人多多这里,“诗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姿态显得更为先锋和前卫,达到了生命个体对语言本体意义层面的寻求。在他一个极少被研究者注意到的文本中,他把自己想象成言词魔性的附身,“披着月光,我被拥为脆弱的帝王/听凭蜂群般的句子涌来/在我青春的躯体上敲打/它们挖掘着我,思考着我”(《诗人》)。在这里,诗人似乎获得了神启,独特地领悟到了“诗人”和“语言”的关系,把诗人视为语言虔诚的尊奉者。无疑,在当时那样一个语言遭到极端强暴的环境里,多多自觉担负起诗人的使命,还语言以主动、自由之身,让自己和语词和谐交互往来,这是一种很大的超越。他的《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祝福》等文本,恰如涉险后的语言投在黯淡时代中的光晕,又似现代主义穿越寂静的一声有力回响。凭着对诗人身份本质的内省,多多创下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诗坛的一大奇迹。
无论是基于哪一层面的自我想象,在“文革”这样一个非诗的年代,这些青年内在的“诗人”身份认同都是严肃而神圣、深切而真诚的。牛汉先生正是看到了青年们对诗歌的这种拓荒精神,将不同地域的诗人命名为“群落”,他解释到:“‘群落’的概念,描述了特定的一群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个特定的地域内,在一片文化废墟之上,执着地挖掘、吸吮着历尽劫难而后存的文化营养,营建着专属于自己的一片诗的净土上。”[5]可见,文学外部环境对诗人身份的羞辱并不能遮蔽其固有的光华,沉入“潜在写作”的青年以“做一名诗人”作为自己获取新生的精神通道,还原了“诗人身份”洁净的品质。
孤立地看,“地下诗歌”属于特定阶段的文学现象,必然烙上“文革”时代的封闭性。可一旦通读完“潜在诗选”,这一“前理解”即刻得到修正。那些长长短短的诗行,总能勾起新诗爱好者对往昔熟悉的一个意象、一串句子或一种诗绪的回忆。这是因为“地下写作”的年轻诗人避开了“颂歌”和“赞歌”的潮流,紧随新诗发展的轨道,广泛地借鉴古今中外的文学资源,汲取前人的诗性精华,从而续接了现代中外诗歌的传统。
近年来,“新诗传统”是一个逐渐升温的争论性话题。面对全球化语境,有学者高度重视我国古代诗歌典雅、精练、含蓄和优美等诗性传统,批评新诗“已完全背叛自己的汉诗大家族的诗歌语言与精神的约束,它奔向西方,接受西方的诗歌标准”[6]。但也有青年学者认为新诗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传统,提出“只要有历史,就会有传统”,“在‘五四’时期,也就是新诗的草创期,新诗就已经拥有自己的传统”[7],前者批判了“五四”以来的新诗在处理中西和古今关系中出现的二元对立思维倾向,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后一种观点因着重具体的历史实践,也赢得了不少当下现代汉诗研究者和写作者的认同。客观地说,新诗历史虽然短暂,但也形成了向下延伸的传统,“文革”期间的“地下诗歌”成为可能,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新诗传统,当然也离不开古典诗歌以及其他文化诗歌传统。几年前,有学者指出“白洋淀诗群”的感受和表达方式,“大都与他们的阅读和文化积累有关”,他们“多方面地从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诗歌中寻找材料和方法”[8](P.214)。事实上,不仅“白洋淀诗群”如此,“潜在诗选”中的贵州诗人、上海诗人无一例外地化用了中外诗歌传统,并以鲜明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呈现出来。
当下学界对“文本间性”理论基本达成共识,即任何文本都不是单一的存在,每个文本的构成都是一些引文的拼接,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在“文革”地下诗歌这里,由于青年诗人并未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缺乏创作理论的指导和足够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对以往诗歌的模仿和转化显得更为合乎情理,对此研究界也相应地更为包容。
相对而言,“潜在诗选”明显留有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诗的痕迹。如上海诗人陈建华《再会了,我爱的浏河》一诗,四行一节,隔行押“ang”或“ou”韵,诗中有荡漾的清波、招手的水草、疏淡的松林、波心中的金光和弱柳般的少女等意象,以“别情”贯穿起来,表达“我”对这“自然的伟秘”、“梦中的仙乡”的眷恋。全诗从整体情思的传达,到诗行、韵律的安排,再到部分意象的建构,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很是相仿,构成显性的“文本间性”关系。不过,诗人生活所在地是乡间的浏河,而不是英国的浪漫康河,因此他安置了小绵羊、橙子、炊烟和老农等田野意象,将该诗和《再别康桥》间隔起来。若以现在的审美品位来衡量,这首着意模仿的诗在处理雅和俗的衔接上尚未达到自然圆通的程度,诗味杂陈,缺乏统一和平衡。但从另一层面上说,在那个审美感性被一场场运动洗劫而空的年代里,如果没有徐志摩对康河描绘这一先在的文本,陈建华这首诗的情思或许难以诱发出来,浏河的美可能就这样处于遮蔽状态。可见,传统为诗人提供了审美经验。此外,陈建华仿朱湘的《苍白的钟声》诗行排列,创下了《流浪人之歌》和《瘦驴人之哀吟》,通过词语序列和诗绪空间的同构,文本形式和内容的应和,产生凄迷和旷远的审美效果,余味较浓。
现代诗对“地下诗歌”的影响不只作用在单个诗人身上。何其芳早期文本中的如烟似梦、飘忽轻灵的水、光、声、色美之于哑默的《春》;“新月派”爱情诗之于食指《难道爱神是……》中的“拨弄心弦的琴”、“心舟的浆”、“湖心的印”等意象;艾青对土地、黎明和太阳的赞美之于马佳的《北方之歌》等,从意象组织到抒情方式都能看到后者对前者显性的继承。“文革”诗人对现代诗的这种模仿和化用现象不难解释。就青年心理特质来说,他们和“新月派”、“现代派”诗人都处于时代的边缘,对未来的迷茫、对个人情感生命的感伤等内心体验有某种相似之处;而艾青寄情于土地和人民的抒情模式也能引发他们的共鸣。因此,这些诗人自然而然地将现代诗建构的意象、意境纳入自己的审美系统中,通过不断反复吟咏和咀嚼,逐渐化为自身的创作。现代诗人从古诗传承过来的典雅形式和齐整格律,对“文革”时期初习诗歌的青年也很有吸引力,适合他们的审美趣味,因此,“潜在诗选”大部分诗歌结构整饰,讲究节奏与格律,富有音乐性。
此外,古典文学传统有时也绕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诗直接进入“潜在诗选”中。如歌唱柑橘“后皇嘉树,受命不迁”的屈原,“跌落在采石的波心”的李白和听潮涨潮落的苏轼,让“浸在谎言毒汁的城”中的青年诗人畅想着水边的自由(钱玉林《诗人与水》);古人登山的悲怆和怀古的忧伤也偶尔浸漫诗人的心胸(陈建华《登吴郡华山》、《皇家园林——拟波德莱尔》);古典的诗词小令形式也间或为现代青年所尝试,如哑默的“清水溪畔忆亲人/门前枫树红几遍”,其中乡思之切,古今相通。
除了本土性承继因素,外国文学对“地下诗歌”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根据“潜在诗选”序言介绍,这些青年诗人虽处于特殊环境,但他们对当时流传的“灰皮书”、“黄皮书”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猎,并作为自己的文学资源。不过,笔者认为,诗人们在处理本土资源和异域资源的策略上,存在明显区别。对于前者,他们往往借用感受和表达方式;对于后者,他们多半取来作为描述或者议论的对象、或直接吟咏、或架通对话。郭建勇的《自由的吉卜赛姑娘》、《啊,你伊甸园的毒蛇——夏娃自白》和张烨的《撒旦之歌》直接在西方文学的材料中抒情,表达青年对自由和人性的渴求。钱玉林则在《致古典讽刺作家》、《读马蒂诗选》和《咏美国作家》等诗作中游历外国作家描写的胜境,向他们表达自己对艺术的倾慕和对现实的诅咒。多多较为独特,他选择受难而圣洁的、“在诗歌中生存”(沃洛申语)的俄罗斯诗人玛·伊·茨维塔耶娃作为灵魂的同伴,拟想她贫困却高贵的人生,实现自我的人格精神归化。多多的对话方式是隐性的,“我”和“她”是互证的关系。如《手艺——和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写到:“我写青春沦落的诗/(写不贞的诗)……我那冷漠的/再无怨恨的诗……我那失去骄傲/失去爱情的(我那贵族的诗)。”其中“沦落”、“不贞”、“冷漠”、“失去骄傲”等高度紧张的修饰词涵盖了“我”和玛琳娜的生活和诗歌状态,构成双重指涉。多多的诗典型地体现了俄罗斯诗歌之于当代诗人精神资源的关系。当然,外国文学资源绝非仅仅通过素材或者精神进入“文革地下诗歌”,它还促进诗人创新艺术手法,接通了现代主义艺术流脉。
作为潜在写作状态的“地下诗歌”,因没有任何外在的诱导和胁迫,诗人无须负着“载道”使命,皆能“缘情而发”,彰显出“我”的感受、直觉、闪念及幻梦,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个人主义立场的写作。与当时充斥着语录和大字报诗风的公开诗坛比较而言,这些文本超越了时代语境的限制,以精神穿透的深度和艺术表现力的强度显示出现代质素。
从精神层面看,“潜在诗选”的“诗思”内核呈现为灵魂的觉醒和抗争。其中,多多、根子和北岛等对荒诞时代的反叛姿态最为醒目,他们都以否定、质疑的强烈语气传达了一代人对那一世界的末日审判、对“神圣”的亵渎与背叛。面对当时非理性的、混乱、恐怖的现实,多多以同样非理性的艺术形式,把社会描述为一个“黑瘦的寡妇”将“一条浸血的飘带”绑到竹竿上、四面八方的恶狗“狂吠通宵”的巫术现场,有力揭示了时代迷信的荒谬和邪恶。北岛以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回答》发出的则是直接的沉痛控诉和挑战。女诗人张烨在该时期的诗几乎不为研究者注意。事实上,她揭示现实的锐利和大胆不亚于男性。在她的笔下,上海当时是一座“血城”,到处是“孤女凄厉的哭声”、“漆黑的鬼魂”,人的暴虐连“死神”都甘屈落后,出来表白自己拾取灵魂时替人阖上眼皮的“善良”。张烨呈现了个体对肆虐张狂的“红魔”的憎恶,并用充满力度的文字表达了自己的“荒原”感。“悬铃木在红色的暴风雪中嗥叫/象绿色的狼群在着火的荒原厮咬。”(见张烨写于1966~1967年的《死神的表白》、《血城》、《愁城》、《丙午红魔》、《喧嚣》)另一位诗人宋海泉首次在“潜在诗选”中面世的《海盗船谣》,更呈现了主体独异于世的精神特质。他承接了闻一多《死水》的美学传统,索性让丑恶的世界恶贯满盈。以“给夜色增添黑暗”为出发点,诗人着意要成为“不祥的暗影”,像“披斗篷的死神”,佩戴“黑色的宝剑”,刺进黑夜的胸膛,把“抢掠来的财宝”全部沉入海底,没有一点儿留给大地。“海盗”可谓新诗中特异的叛逆形象,展示了诗人与世界的对抗姿态,散发出强烈的审美效力和持久的精神震撼力。
不过,就普遍性而言,大多数青年诗人将对现实的怀疑和对自然的赞美、对个人生命情感的伤怀糅合在一起,带有青春经验、情绪的自然抒写倾向,在情感力度和精神深度上相对薄弱。但是,考察“地下诗歌”的“拓荒”意义,不能离开“文革”具体的历史语境。以青年诗人倾心于“自然意象”描绘为例,“文革”时期人定胜天的时代自信感和社会主义乐观精神将自然完全“人化”了,一切自然和美无关,和个体的情感体验无关,仅仅是大写的“人”的力量的显示,人类与自然相互交感的契合被荡涤一空。就在这一背景上,青年诗人返回人与自然的本源关系中,捕捉万象之美,或者让自然感应自己的心灵和情绪,或者从自然中寻找自由与人性的求证。无论是空中的海鸥、鸽子、鹰、白云、雪花、雨丝,还是地上的楼、桥、树、花、水,或者从时季到星际,这些进入诗中、成为诗人寄情对象的客体,都能映照出诗人对美的发现和感知能力。哑默笔下的海、晨光、春天,纯美洁净,传达了他对爱与美的守护姿态。客观地说,“地下诗歌”的自然化风格印证了诗人在畸形时代中审美感性的解放。而他们大量对青春、爱情、生命的感怀,也是主体性释放的结果。
就“诗质”肌理而言,虽然“潜在诗选”中多数文本传达较为平白和直接,未脱离浪漫主义抒情模式和既定语言惯性的格局,但也有不少诗人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启发,自觉进行“陌生化”的原创性实践,孕生了至今读来仍让人“惊异”的诗篇。
最突出的惊奇效果体现在语言上。在一些文本里,时代流行话语的那种明朗、单向、轻浅和热烈被远远隔离出去,取而代之的是暗示的、歧义性的、富有力度甚至丑陋、血腥、肮脏、残酷的语言,续接了象征、隐喻等诗性传统。如根子《三月与末日》中的诗句,“暗褐色的心,像一块加热又冷却过/十九次的钢,安详、沉重/永远不再闪烁”,语象凝聚着诗人丰富的心理现实,暗示他经历了多次的希望和失望后,心智逐渐冷静成熟,对现实不存任何幻想。芒克的“太阳落了/黑夜爬了上来/放肆地掠夺”(《太阳落了》)采用的是隐喻,以太阳的下落指向人的主体精神以及公道、正义等价值体系的失落。比较起来,多多语言的歧义性更具张力,他常常用出人意料的组合加深文本的阐释难度。以《祝福》的下半节为例:“从那个迷信的时辰起/祖国,就被另一个父亲领走/在伦敦的公园和密支安的街头流浪/用孤儿的眼神注视来往匆匆的脚步/还口吃地重复着先前的侮辱和期望。”诗句完全打破了常规语言的逻辑,诗人给偌大的“祖国”搭上“另一个父亲”,又令其成为流浪的“孤儿”,这种大词和小词的配置构成强大的张力,要阐释其中的意义只有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在世界其他民族前行的脚步中,处于“文革”一片混乱中的国家如同飘篷,其文化根基已经迷失。显然,诗人表达的是自己对民族命运的反思,但他的语言组织方式完全个人化,以流浪孤儿的眼神和口吃的样态呈现一个特定时代的国家形象,使语言的潜在功能释放得淋漓尽致,文本透出超语义的原生性。
在词语力度上,让人感觉根子“狠歹歹”[9]的个性袭面而来。他的《三月与末日》极尽语言的颠覆功能,将人们日常经验中“明媚”的春天改为“妖冶的”、“血腥的”、狡黠的“嫁娘”和“娼妓”,毒蛇般的“荡妇”,“冷酷的贩子”,“轻佻的叛徒”。诗人不惜动用所有的“狠毒”语言来诅咒“春天”的欺骗性,字字如铁锤,对掠夺青年的虚假理想进行了彻底的宣判和复仇。其语言浓重、阴冷的色调,渗出现代主义汁液。
此外,反讽、戏拟和寓言手法也进入了一些诗人的视野。戏拟采取的是对权威等明目张胆的“误读”策略,通过对原本文的仿写和复制,表达诗人批判的立场。钱玉林善于使用模拟的笔触,他这样戏拟当时的专制者口吻——“让所有的鱼离开水”,“让花儿都改变习性”,“传令公鸡那厮闭上嘴巴”(《命令》)——活现出时代的荒诞不经。明明内心深恶“红色运动”,他故意正话反说,“我们十分幸运/生活在一个只须倾听/神意的时代”,“神圣的红色……一切的一切/从月亮到九大行星/都不许有别种颜色”(《白与红》),文字的反讽意味不言而喻。此外,根子较为成功地实践了戏剧性寓言体诗,他的《致生活》通过“我”与“狼”、“狗”的大海之行(“我”不听狼“海没有边际”的忠告,误信狗“海水是甜的”的谎言,结果溺死了),喻示人不可迷信“大脑”,而要相信“眼睛”。在整个中国新诗史上,戏剧性寓言体诗是罕见的类型,它对诗人的哲理素养、结构技艺和叙事能力有相当的考验,而处于非诗年代的根子作出了这一探险,不能不让今天的研究者震撼于“地下诗人”的先锋意识。
综上所述,正是“文革青年地下诗歌”对灵魂构成深度震撼的精神旨趣和令人感觉新异的艺术探索品质,接通了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和新时期“朦胧诗”的流脉。它们的存在进一步证明了人类对诗性追求的坚毅和执着,也彰显了“文革”时期文学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