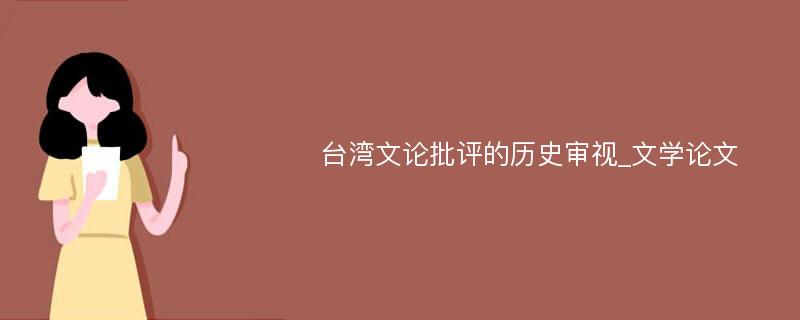
台湾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扫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台湾论文,批评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世纪后期台湾社会的转型,内地化起了决定的作用,即由移垦社会逐渐转变为与中国大陆各省完全相同的文治社会,并与中国本部成了统一的整体。尤其在文化模式上,台湾文化已成为中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
日据时期比明郑、清治时期更值得重视。其文学发展除前期1895-1920年间的古典文学时期外,其余均为新文学时期。以台湾的新文学理论批评来说,可看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对台湾深远的影响。1923年,黄呈聪等人受“五四”精神影响提倡白话文,使白话文很快成了台湾人民书写的工具。胡适的“八不主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正是在这前后登陆台湾的。大批祖国新文学作品,亦随之渡海而来。在这种背景下,由台北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习的张我军,成了台湾新文学革命的旗手。他的评论文章有《文学革命运动以来》(注:《台湾民报》第3卷6、7、9号。)、《诗体的解放》(注:《台湾民报》7、8、9号。)等等。
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诞生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时推行“皇民文学”,使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受到极大摧残。1945年8月台湾光复后不久,国民政府全面废除日文写作,台湾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重新和祖国接轨,由此获得新的转机。较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上“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这场论争既承认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又肯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大陆赴台湾作家雷石榆在论争中首次把马列主义的新写实创作方法引进台湾,比30年代由台共主编的刊物《先发部队》等引介的“无产阶级文学论”,又前进了一步。
台湾文学理论批评得到蓬勃发展,应从50年代开始。这时来台的大陆文人除国民党作家张道藩、王平陵外,还有自由主义者胡适、胡秋原等人。另有以余光中为代表的新的一代。这些作家在大陆时期就写过不少评论文章。不过,这时的“台湾文学理论批评”,是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或曰“‘中华民国’文学理论批评”面目出现的。为了配合“反共复国”的政治需要,当局颁布了“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其禁书办法为漫天撒网。本来是严禁30年代左翼文艺传播,可后来扩大到凡是中国新文学作品差不多都不许阅读、研究,造成“五四”文学在台湾的断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批评,只好走国际主义路线,其中最典型的是纪弦所制定的现代派“六大信条”(注:台北,《现代诗》总第13期(1956年2月)。),其中第二条云:“我们认为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这一主张,遭到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纪弦为此辩解说:“现代诗与传统诗是两种极端相反完全不同的文学……传统诗是‘小儿’的诗,现代诗是‘成人’的诗。”(注:纪弦:《论移植之花》,收入《纪弦论现代诗》。)纪弦将现代诗说成是从零开始的,完全不考虑文学的传承关系,后来他作了部分修正。
来台后,继续从政治上支持国民党统治的胡适,不愿做一般学者,而要做蒋介石的“诤友”。他极力鼓吹在台湾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1958年5月4日,胡适借纪念“五四”为名重新扯起“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两面旗帜(注: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台北,《文坛》季刊第2号(1958年)。),和他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主张相配合。对胡适所说的文艺“不能由政府来辅导,更不能由政府来指导”(注: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台北,《文坛》季刊第2号(1958年)。)这类不利于当局统治的话,国民党无法采纳,由高级文化官员任卓宣(叶青)出面与之“商榷”(注:任卓宣:《论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文坛》季刊第3号(1958年)。)。
在高唱“反共抗俄”的50年代,许多从大陆迁台的作家和评论家,在政治上与当局保持一致,思想显得保守僵化,容不得艺术上的半点革新。在50年代最流行的是张道藩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文艺观”:“当前文艺所载的‘道’,除三民主义而别无他道。”(注:张道藩:《论当前文艺创作三个问题》,台北,《联合报》1952年5月4日。)这里讲的“三民主义”,经张道藩扭曲为“以反共抗俄为内容的作品,即是三民主义的文艺作品。”(注:张道藩:《论当前文艺创作三个问题》,台北,《联合报》1952年5月4日。)从这种文艺主张,不难看出以“反共”与“怀乡”为主题的50年代,所谓文艺理论不过是与文艺政策的混合,政治实用主义成了许多评论家惯用的批评武器,真正的学术建设很难提上议事日程。
由于台湾社会西化的发展趋势,和广大作家出于对“战斗文学”思潮的厌倦和反叛,现代主义思潮在60年代有了蓬勃的发展。在新诗方面,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主要不是通过正面的陈述,而是由文学上的“私人战争”体现出来。如洛夫对余光中长诗《天狼星》(注:台北:《现代文学》第8期(1961年5月)。)的批评(注:台北:《现代文学》第9期(1961年7月)。),以及余光中所作的反驳《再见,虚无!》(注:写于1961年12月6日,见余光中:《掌上雨》,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版。),两人的“战争”无意中对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天狼星》作了共存互补的极为深入的“研究”。余光中另还有无论战色彩的实际批评。这批评虽然带有小圈子倾向,但对新涌现出来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分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盛行和解读作出了漂亮的示范。
台湾小说迈向现代主义的步伐比新诗迟,因而现代小说批评未有现代诗批评活跃。在现代主义时期中,如果以夏济安所编的《文学杂志》和白先勇等编的《现代文学》杂志为代表,那台湾的现代小说与现代诗所走的是两种不同路线,即以覃子豪、余光中为代表的“蓝星”诗社奉行浪漫主义路线,而现代小说却是反浪漫的;以洛夫为代表的《创世纪》现代诗晦涩难懂,而台湾的现代小说却是写实的,即使运用新技巧也不致使人如坠五里雾中。这和夏济实所倡导的温和的现代主义理论有关。还在50年代中期创办《文学杂志》时,夏济安就主张:“我们所提倡的是朴实、理智、冷静的作风。我们不想逃避现实。”(注:夏济安:《致读者》,台北,《文学杂志》创刊号(1956年9月)。)在现代诗、现代小说还未出现著名作品以前,夏济安发表过《对于新诗的一点意见》(注:《文学杂志》第2卷第1期(1957年3月)。),尤其是《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注:《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56年12月)。),被称为自50年代以来,“台湾第一篇堪称严谨的文学批评”(注:林依洁:《如何建立严肃的批评制度》,见李欧梵:《浪漫之余》,第184页。)。夏济安宽广的文化视野及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深切了解,使他担任了现代文学先行者的重要角色。只是夏济安的影响多半局限在小说领域,未能对台湾现代诗出现的极度晦涩之风起到纠偏的作用。
旅居美国的夏志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台湾文学评论家,但他的小说评论在台湾颇有影响。他曾评论过於梨华、白先勇、陈若曦等人的小说。他的文学观受周作人的影响,其批评立场主要师承艾略特。他在抨击以“现代化”为名的伪现代批评时,强调印象组合的重要性。总之,夏氏兄弟的文学观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在采用部分19世纪传统的小说理论同时,掺入20世纪新的文论。
当夏济安把文学批评的焦点从三民主义转到文本研究后,王梦鸥在60年代中期出版了《文学概论》(注:台湾,帕米尔书店1964年版。)。此书明显地受了韦勤克、沃伦合著的《文学原理》的影响。在方法上,和《文学杂志》引进的新批评观念相一致。
二
尽管西方文论以锐不可挡之势入侵台湾文坛,但传统的文学观并未完全被抛弃。这在以本土情结为本位的批评阵营中,可看出写实主义在《台湾文艺》等杂志中仍大行其道。他们以在野的姿态质疑主流文化,《笠》诗社尤其有意于建立“本土中心论”以便和前卫的《创世纪》相抗衡。《葡萄园》诗社所创导的“健康、明朗、中国”的诗风,对现代诗摆脱濒临深渊的危机,也起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到了70年代,出现了带有左翼色彩的新的文学论述方式,并很快取西化文论而代之,由此引发政治上的僵化派和西化派的反击,这就是7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乡土文学大论战”。
这场论战挂着“文学”招牌,讨论的却多半是台湾政治经济发展的性质。之所以会由“文学”出面,是为了减少讨论的敏感性与危险性。如讨论者先讲文学不应西化而应回归现实,回归乡土,应成为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的代言人,然后再推论出台湾社会有许多应批判和揭露的阴暗面,这样即使有政治干预也不是由警备总部出面而由较“斯文”的国民党“文工会”(相当于中央宣传部)劝阻,否则“乡土文学论战”还来不及“战”恐怕就销声匿迹了。
乡土文学论者大力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批判功能,以及坚持文学的民族性,宣扬文学应同情弱者。基于这一点,他们对与社会严重脱节的现代诗发起了一场讨伐运动。首先由关杰明刮起一股旋风,发表《中国现代诗人的困境》(注:台北,《中国时报》1972年2月28日、29日。)、《中国现代诗人的幻境》(注:台北,《中国时报》1972年9月10日、11日。),向《创世纪》编选的具有浓厚的“国际性”的诗选提出挑战。继之,有“唐文标事件”,即唐文标发表《僵毙的现代诗》(注:台北,《中外文学》第2卷第3期(1973年8月)。)等三篇文章,像一颗核弹落在争吵不休的诗坛。唐文林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批判“艺术至上论”,以法官判决式口吻宣判现代诗死刑,使整个诗坛乃至文坛喧哗骚动起来。
台湾社会在进行一场意识形态战争的紧急动员,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论战,其中火药味最浓的要数由台湾暂居香港的余光中写的《狼来了》(注:台北,《联合报》1977年8月20日。)。文章中包含着指控“乡土文学”就是北京“工农兵文学”的台北版、陈映真是毛泽东延安讲话的忠实信徒等用意。此外,另有王文兴、彭歌、尹雪曼等人对乡土文学进行弹劾。
乡土派也不甘示弱。在论战进入高潮的时候,哲学家陈鼓应以乡土派代言人自居,痛斥余光中的“色情主义”和“崇洋买办心态”(注:陈鼓应:《这样的“诗人”余光中》,台湾,大汉出版社1977年版。)。双方的文章充满了情绪语,论述方式极为偏激,但乡土派在现代主义流行了近20年的情况下,毕竟喊出了来自底层而非象牙之塔的声音,为左翼文学的张扬扫清了理论障碍。
乡土派的重要理论家除唐文标、陈鼓应外,另有尉天骢、陈映真、叶石涛等人。尉天骢批判王文兴的现代小说显得粗糙,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破多于立的乡土文学派评论家的弱点。乡土派的真正贡献在于他们脚踏实地重新挖掘和整理日据时代及五、六十年代的赖和、杨逵、吴浊流、钟理和、钟肇政等人的资料,其成就远大于左翼文学主张的提出(注:参看吕正惠:《台湾文学研究在台湾》,台北,《文讯》1992年5月号。)。
乡土派不少人既是作家又是评论家,可他们的理论文章尤其是实际批评,大都给人一种模棱两可的印象,远不及现代文学阵营的评论家颜元叔那样来得入木三分。自然也有例外。如陈映真在这方面比叶石涛“打太极拳”式的文章观点鲜明得多。施淑的文章也很讲究学术性,篇幅虽长但不是温吞水式的。
乡土文学论战之所以能“论”得起来,和70年代的媒体发达分不开。介入论战的报刊,除痖弦、高信疆分别在《联合报》、《中国时报》主持的两个左右文坛的强势副刊外,另有小众的民间杂志《仙人掌》及刚破土而出的党外杂志如《美丽岛》。胡秋原主办的《中华杂志》,则从学术角度,声援差点被“抓头”的陈映真等人。以文学评论为主的《书评书目》于1972年创刊后,则不是以论战而是以书评方式为评论家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较专业的评论园地。
乡土文学论战的一大收获,是文学应反映社会生活尤其是描写农村现实的原则,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然而极富反讽意味的是:论战后乡土文学作家并没有拿出沉甸甸的作品。相反,被认为近乎“经典”之作的黄春明的《锣》、王祯和的《嫁妆—牛车》,却是论战前出现的(注:参看杨照:《台湾战后50年文学批评小史》,台北,《联合文学》第12卷第2期(1995年)。)。这说明乡土文学论者过于重意识形态而轻艺术创造,理论与创作严重脱节。
在70年代,现代主义批评虽退居第二线,但仍出现了像颜元叔这样的学院派重镇。还在六、七十年代之交,颜元叔就以现代主义营垒内的反对派身份批评现代诗在结构与意象运用方面的毛病。他还于1972年创办了驰名中外的《中外文学》,其文学评论家队伍除《现代文学》后期的“遗老”外,大都是以颜元叔为龙头的外文、中文两系的“新贵”。这个刊物把西方“新批评”观念有步骤、有系统地引入台湾文坛,将原先侧重传统理论诠释的中文系学者和致力于西方理论译介的外文系学者,引导到一个中西理论相互激荡的高峰。在70年代前半期,颜元叔又连续出版了四本评论文集,使他扮演了继夏济安之后现代主义另类的“综结者”(注:参看吕正惠:《台湾文学研究在台湾》,台北,《文讯》1992年5月号。)角色。另一女评论家欧阳子以白先勇《台北人》为研究对象的《王谢堂前的燕子》(注:台北,尔雅出版社1976年4月版。),则进一步继承了夏济安引进的新批评观点,在70年代中期很有影响。柯庆明在《文学美综论》(注:台北,长安出版社1973年5月版。)中企图建构的“以生命意识为中心”的文学理论,亦有创意。
三
随着美丽岛事件的发生,台湾跨进了多元化的80年代。80年代前5年,文学批评受到冷落,乡土文学阵营出现了严重的裂痕。他们不再像70年代那样并肩作战,用反西化、反殖民的批判精神引导台湾文坛,而是因“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如乡土文学阵营中的“北派”评论家陈映真、尉天骢高扬“中国意识”,强调“台湾文学”就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而“南派”评论家叶石涛、彭瑞金等人,却凸现“台湾意识”,将其凌驾于“中国意识”之上乃至之外。“南派”强调台湾文学的自主性、独立性,其本土中心论的主张已明显地和政治上的分离主义结合起来。本土中心论者还有温和派和激进派之别。这从宋泽莱对“老弱文学”代表叶石涛的激烈抨击(注:宋泽莱:《论怕宋泽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6年版。),不难看出这派中之派的演变轨迹。
此外是“新批评”霸权的没落。在80年代《中外文学》所发表的实际批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批评已成强弩之末。虽然有龙应台的《龙应台评小说》(注:尔雅出版社1985年版。)创造了文学评论书籍最畅销的纪录,但她这种缺乏思辨性、手法单一、招式贫乏的文本解读,却不能说是“新批评”的厚重成果。王德威的《考蒂莉亚公主传奇——评(〈龙应台评小说〉》(注:《中外文学》第14卷第6期。),对龙氏批评的盲点作了深入的分析,“可以说颠覆了龙应台实际批评公式——同时也颠覆了70年代中期以降的新批评形式主义文论的独占性”(注:郑明娳:《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小说批评卷序》,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版。)。
随着“新批评”霸权地位的没落,台湾文论界真正进入了“众声喧哗”的时代。从女权主义到现象学、语言学文学批评,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新马克思主义到人权文学论,以及叶维廉所运用的诠释学、古添洪所擅长的记号诗学,还有吕正惠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均异彩纷呈地出现在80年代各种文论领域。《中外文学》及另一些文化刊物再次成为五花八门的文论大展台。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的倡导。它虽然没有形成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但对文坛的冲击不亚于60年代的现代主义。批评家们往往用比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异同的方法,去阐明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蔡源煌的《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在实际批评方面,则有张惠娟的《台湾后设小说试论》(注:载林耀德、孟樊主编:《世纪末偏航》,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罗青为鼓吹后现代亦写了不少论著。但也有大喝倒采者,如前述具有革命与批判意味的“新马派”吕正惠,就被认为是反后现代势力的代表。
叶石涛发表的《台湾文学史导论》中提出“台湾文学”的概念,其初衷是将其从“中国文学”范围中剥离出来。可后来许多人使用这一名词时,均当中性看待,泛指不同于大陆的台湾地区所出现的文学。
当本土派评论家不再使用“乡土文学”而鲜明竖起“台湾文学”这一旗帜后,台湾文学研究配合当局的本土化运动堂而皇之进入台湾各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殿堂里。此外,还出现了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注:高雄,文学界杂志社1987年版。)。这时期大学里的台湾文学座谈会、研究会不再像过去极少举行而几乎成了一股潮流。学院派研究台湾文学注重理论性和学术性,力求以文学史家的眼光为作品定位。他们还用西方文论去诠释本土作家作品,将新的研究方法和历史视野带进文学批评活动中。
80年代的台湾文学批评尽管争妍斗丽,但还没有哪一位评论家构筑起体大虑周的理论体系。他们热衷于引进西方文论,而很少有人运用于实际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张汉良、蔡源煌、王德威等人能运用不同的批评方法去审视当代小说,也就显得难能可贵。
90年代的台湾文学理论批评,仍沿袭了80年代多元并存的发展方式,所不同的是随着80年代后期的“解严”以及开放“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平反“二二八事件”等所谓民主化的进程,台湾文坛的“统”“独”之争更趋向表面化。原先想调和“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之间矛盾的叶石涛,这时也不再脚踏两只船,而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为陈词滥调(注:叶石涛:《总是听到老调》,台北,《自立晚报》1992年5月13日。)。1995年由台湾笔会等众多单位发起的在台湾各高校建立“台湾文学系”的倡议,其要害是把“中国文学系”并入“外国文学系”,为“台湾文学国家化”主张进入高校讲坛寻找新的理论依据。另有90年代引入的“后殖民”理论,这时也为分离主义者所利用。他们歪曲台湾历史,把大陆来的历朝管辖者——远至明郑、清廷,近至中国国民党均视为与荷兰、日本一类的“外来殖民者”,然后再在历史、语言上寻找与中国的所谓“相异之处”,为子虚乌有的“台湾民族文学”(注:林瑞明:《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6年版,第58页。)的问世制造舆论依据。某些台湾文学史家显然无意寻找历史,而是在“改写”历史、篡改历史。
由于本土化在90年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地位,再加上个别院校“台湾文学系”或“台湾文学研究所”的正式建立,因而90年代的台湾文学研究蔚然成风。如台湾师范大学许俊雅的《日据时代台湾小说研究》(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2月版。),是较早出现的以台湾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之一,无论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均超越前人。另有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注: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2年版。)以及陈芳明在《联合文学》上连载的《台湾新文学史》(注:从1999年8月号开始连载(未完)。)。这两个人写作原动力是摆脱传统教育建制里的“大中国情结”,常常把“台湾文学”作为国家认同的一种护身符,尤其是陈芳明说1950年后“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分离”是既成事实,还说什么闽南方言、客家话是独立的民族语言,这均表明研究历史的陈芳明既不尊重历史,也不了解语言科学。这除了说明他的无知外,只能证明他写文学史是假,宣扬台独谬论是真。
90年代的台湾文学批评尽管学院派所走的仍是严肃、厚重的路线,《中外文学》及昙花一现的《台湾文学观察》杂志也为这类批评提供了发表园地,但早先大量刊登文学评论的《书评书目》、《新已月刊》的停办及《文讯》适应市场的改版,使文学评论只好大量寄生在报纸副刊上。它虽然显得轻盈而富可读性,但毕竟过于轻、短、小。文学评论的另一空间是媒体读书版。其论述焦点多集中于情欲文学、同志文学、成长文学、旅游文学、网络文学……这些文章的作者尽管在跟媒体的编辑生态抗争(诸如限制篇幅及迎合读者口味),但作为弱势和冷门的文学批评,仍然必须使自己的学术文字尽量隐形。在这种“速食资讯化”的挤压下,菁英文化虽不会投降但也只能让地三尺。
在台湾,长期以来是新诗、小说理论批评打头阵,散文理论批评跟不上。90年代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如郑明娳自80年代出版了三种“散文论”后,90年代又出版了《现代散文现象论》(注: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和另一本《现代散文》专著,在构筑现代散文理论体系方面显示出她深厚的学养和功底。郑明娳由1996年移居国外又返回台湾,这种曲折经历也多少透露了台湾的人文环境尤其是目前动荡的政局,不利于学术人才的生长。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乡土文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联合报论文; 现代诗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