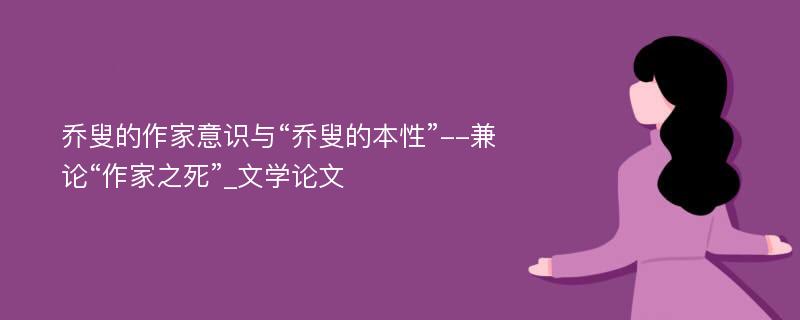
乔叟的作者意识与“乔叟性”——兼论“作者之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者论文,之死论文,意识论文,乔叟性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英诗之父”,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2?-1400)保持着几项纪录,其中之一就是他拥有英国历史上最长久且持续不断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早在15世纪,他就已被英格兰诗人们尊为“大师”(mayster)和“父亲”(fadir),而在自他生前至今的六百多年里,其形象一直在变化,在不同时代或不同人眼里呈现出很不同乃至相互对立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一部乔叟学术史就是一部乔叟形象越来越丰富的历史。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对乔叟研究的拓展与深入,乔叟的形象不断变化与丰富,但总体而言,它们大都只是从不同侧面或在不同层面上体现出乔叟诗作所拥有的独特的“乔叟性”。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世纪没有著作权观念,作品往往不署名,所以大量中世纪文学作品至今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历史文献中更鲜有关于文学家的记载。但因乔叟与王室关系密切,是比较重要的官员,有相当知名度,其经历也可谓丰富多彩,所以我们对他的生平了解较多,甚至超过了对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许多文艺复兴作家的了解。学者们经长期搜寻,在各种档案材料(不包括文学作品)中,共找到492条乔叟生前留下的关于他的记载,它们全被收入由马丁·M.克洛和克莱尔·C.奥尔森编纂的《乔叟生平记载》一书中。①乔叟能为后世留下那么多记载,其实与他是一位诗人和他对英国文学的杰出贡献毫不相干。那些记载大多涉及他的公务、年金、职务、诉讼、所受赏赐和出使国外等情况,没有一条暗示他是一位诗人,更没有一条提到他的文学作品。仅就这些记载而言,我们看到的只是王府僮仆、随主出征的扈从、多次出使国外的外交官、海关官员、国会议员、郡治安官、王室工程总管和森林管理人。人们不禁会问,这位在生前有幸留下这么多记载的官员与那位六个多世纪来在英语世界享有崇高盛誉的英诗之父是同一个人吗? 如果是的话,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似乎是,诗人在中世纪不是值得记下一笔的人物。这或许也表明,中世纪没有“作者身份”(authorship)这一观念。这种状况似乎很符合罗兰·巴特关于作者之死的观点,该观点的基础是,“作者”只不过是现代社会的虚构。他说: 在氏族社会,叙事从来不是由一个人(person)而是由一个中介(mediator)、一个巫师(shaman)或者一个演唱者(relator)进行,是其“表演”——即他对叙事规则的熟练掌握——而非他的“才智”能获得赞赏。作者是一个现代人物,他毫无疑问是我们的社会的产物;那是因为在中世纪终结之时,在英国经验主义、法国理性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对个体之信念的影响下,我们的社会发现了个体的特殊价值。② 巴特这个说法值得商榷。首先,巴特将游吟诗人的身份同他这个人完全分离开来,认为诗人只是机械地“表演”,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创造。然而这与古代文献的记载和学者们的研究并不完全相符。③的确,游吟诗人是在传统中按“叙事规则”演唱,是在大量利用历代前辈和自己积累的程式化(formulaic)语言和技巧进行表演,演唱内容也往往为听众所熟知,但这并不妨碍更不会阻止游吟诗人即兴发挥和创造。比如,在古英诗《贝奥武甫》里,就在贝奥武甫杀死魔怪凯旋的路上,一位“极富诗才”的“歌手”运用传统“曲子即兴填词”,将贝奥武甫诛杀魔怪的英雄事迹创作成“一篇动人的故事”。④这是关于氏族社会里英雄歌谣产生的宝贵记载。难道这位武士歌手的创作仅仅是与“才能”完全无关的“表演”? 其次,巴特从氏族社会跳到中世纪终结之时(从巴特提及英国经验主义、法国理性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来看,他是指16、17世纪),从氏族社会的演唱一下跳到中世纪终结之后的书写,正是为了支撑他关于作者是现代社会产物的观点。在西方世界,我们可以暂不考虑古希腊罗马,但创造了很高文明的上千年的中世纪为什么可以被轻松抹去?特别是12世纪文艺复兴之后到巴特所说的中世纪终结之时那四五百年里西欧各国拉丁语著作和书面民族语言文学的繁荣为什么可以被忽略不计?事实上,西方关于作者的现代观念正是逐渐成形于那一时期。 巴特的主要问题是,他把作者等同于关于作者的观念。作者是作家在创作作品的同时创造的,只要作品被创作出来,不论我们是否认识到,甚至不论我们是否知道作家的名字,作者就已经存在。所以,现代社会建构的不是作者,而是关于作者的观念,更准确地说,是关于作者的现代观念。而本文下面将谈到,即使在中世纪也有相当明确的关于作者身份的观念。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关于作者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中世纪,并一直处于发展之中。在12世纪文艺复兴之后,在巴特所给出的作者被虚构出来的时间上限之前的四五百年里,随着人文主义和经院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也随着这时期书面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关于作者身份的观念和理论获得了重大发展,而关于作者的现代观念也正是在此期间在中世纪原有的关于作者的观念基础上逐渐发展并在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这时期西欧社会、文化和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核心因素是人文主义的发展。巴特认为,作者的出现与人的个体价值的提高相关;事实上,他应该将作者的出现改为关于作者身份的现代观念的发展。 关于中世纪的作者身份,著名中世纪专家A.J.明尼斯做了广泛研究,他在专著《关于作者身份的中世纪理论》中首先界定了中世纪有关作者的两个术语,即作者(auctor)和权威(auctoritas)。他说,“在[中世纪]文学语境中,‘作者’这个术语指作家和具有权威的人”,因此,“一个作家的著作(writings)包含或者说拥有抽象意义的‘权威’,它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和睿智的含义”。⑤另外,“在具体的意义上说,一个‘权威’是来自某作者之作品的引文或节选”。一个书写者(writer)要被尊为“作者”,其著作必须符合“两条标准”:“‘内在价值’(intrinsic worth)和‘真实性’(authenticity)”;而在中世纪,“内在价值”必须“以某种方式符合‘基督教真理’”,如要“具有‘真实性’,一种说法或者一个作品必须是一位有名有姓的作者的真实著作”(Medieval:10-11)。13世纪的一位多明我会神学家说:有些著作“被称为伪经(apocryphal),是因为作者不明。但它们毫无疑问包含真理,所以为教会所接受……如果它们既无作者也无真理,它们就不可能被接受”(Medieval:11)。由此可见,中世纪不仅有关于作者的观念,而且把作者看得极为重要,看成与真理一道是作品权威性的两条标准之一。 更重要的是中世纪人重视作者在作品生产中所起的作用。随着12世纪经院哲学的兴起,亚里士多德关于因果关系的思想被用于研究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并以此揭示作品产生的各种因素。中世纪人往往在著作前面的“引言”(prologue)中说明著作产生的因素、意图和内容,明尼斯称之为“亚里士多德式引言”(Aristotelian prologue)。他通过研究这些引言,归纳出作品产生的四种原因,即直接原因(causa efficiens)、材料原因(causa materialis)、形式原因(causa formalis)和最终原因(causa finalis)。直接原因就是作者本人;材料原因指作者所用材料之来源;形式原因指作者的写作手法,如篇章结构等;而最终原因则指作者撰写该书要达到的目的(Medieval:112-113)。在这四个原因中,作为直接原因的作者无疑占据着核心地位,其他三个原因也都与他相关。明尼斯还进一步指出,13世纪出现的“对个体作者(individual auctor)节操的新强调产生了两个结果:在各种写作手法的运用方面对作者的兴趣和对‘作者生平’的表率作用的兴趣。在13、14世纪,所有作者,不论是基督教徒还是异教徒,都在道德和创作层面受到考察”(Medieval:28-29)。 尽管这里主要涉及宗教领域的作者,明尼斯仍然指出,同样的作者观念也适用于波伊提乌、奥维德、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等古典思想家和诗人,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世纪文学家,如意大利的彼得拉克、薄伽丘和英国诗人高尔、乌斯克和乔叟等。不过在作者意识的发展方面,明尼斯没有谈及那个时代的法国诗人们,这些法国诗人的作者意识甚至领先于并影响了包括乔叟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诗人。 然而具有悖论色彩的是,正因为中世纪人如此重视作者的作用,那些不直接阐释《圣经》和基督教神学的文学家们,其身份和声誉往往受到基督教压制,原因在于声誉十分危险地接近基督教所谴责的“七大重罪”(Seven Deadly Sins)之首的“虚荣”(Vanity)。尽管如此,中世纪诗人仍然以不同方式表现其作者身份。早在英语文学产生之初,大约生活在八九世纪之交的古英语诗人基涅武甫(Cynewulf)在其诗作《基督之二》(Christ Ⅱ)快结束时,将自己的名字用与诗文完全无关、来自古日耳曼部落且当时极少人能懂的如尼文字母(runic letters)分散安插在一些诗行里。这似乎表明,这位有可能是一位主教的诗人既想使自己的声名与诗作永存,又怕被人斥责为虚荣。⑥ 大约在12世纪末,中古英语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布鲁特》(Brut)的作者拉亚蒙(Layamon)在作品中简略谈到了自己的创作目的以及他如何广泛游历和收集材料,这表现出了这位英国诗人的作者意识。到了14世纪,英国文学家的作者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表达,更多作家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带入作品,比如《农夫皮尔斯》的作者威廉·朗格伦就是如此,而长期与乔叟齐名的诗人约翰·高尔更在其代表作《情人的自白》的结尾中,认真介绍了自己的三部拉丁文著作。 当然,在中世纪英格兰文坛,作者意识最突出的还是乔叟。他在多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与自己同名的第一人称叙述者,通过这位叙述者多次列出自己主要作品的目录,甚至还多次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论和表达自己的创作思想。在《声誉之宫》里,叙述者杰弗里还借雄鹰之口述说自己的文学创作与海关工作以及算清账目下班后闭门夜读直到“两眼发直”的生活。⑦他对自己海关工作的叙述也是学者们确认诗人乔叟与那位留下492条记载的政府官员乔叟为同一人的有力证据之一:在当时人口不到十万、文人更是凤毛麟角的伦敦,同时生活着两位同名同姓、同在伦敦海关工作⑧而在薪酬记载中却只有一人,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同样在《声誉之宫》里,乔叟描写声誉之宫门前竖立着“肩负”各自民族“声誉”的荷马、斯塔提乌斯、维吉尔、奥维德等伟大诗人,显然是为文学家的声誉正名,而他用来代表英格兰诗人的恰恰是与他同名的“英国的杰弗里”。另外,当寻找创作“信息”的杰弗里在观看了声誉如何产生的戏剧性场面后,他身旁一人问他是否也是来寻求声誉的,杰弗里以“脑袋起誓”矢口否认,并说: 如我死后,没人瞎糊弄 我的名声,我就心满意足。 我最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 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我自作自受,别无他图, 重要的是,我只需 弄明白我的诗歌艺术。⑨ 有谁能相信写出这样诗行的乔叟竟然可能会没有作者意识? 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这部他自己十分满意的诗作的结尾,乔叟很“谦虚”地将这部八千多行的诗作称为“我小小的悲剧”⑩,并说:“我的小书,不要去招人妒忌,/要向所有的诗歌表示谦卑,/步维吉尔、奥维德、荷马、卢坎/和斯泰斯后尘,亲吻他们的足迹。”(Troilus:V.1789-1792)诗人虽说要“表示谦卑”,却显然渴望凭这部著作而像荷马等伟大诗人一样百世流芳。 或许正因为中世纪文学作品一般不署名,乔叟才一再列出自己的主要诗作目录,以求流传后世。在《贞女传奇》的《引言》里,他不仅列出自己的著作目录,而且还虚构了一个很富有戏剧性的场景,说是因为翻译了《玫瑰传奇》和写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得罪了爱神,遭受“处罚”,必须传诵“节妇、贞女、贤妻”。其实,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结尾,乔叟就已经在“恳求美丽的女士,/和高贵的夫人”,不要因为该书揭露了“克瑞西达的不忠/和罪孽而对我发怒”(Troilus:V.1772-1778)。另外,在这部悲剧的结尾,乔叟还希望上帝赐他力量,“写出一些喜剧”(Troilus:V.1788)。学者们一般认为,这表明乔叟已经有了创作被称为“人间喜剧”的《坎特伯雷故事》的一些最初想法,他在作品中直接给出这些重要信息,透露出未来15年中大致的创作计划、内容和体裁,而且还表现出他试图将中、后期几部主要作品的创作整合成多少相关联的艺术统一体的意图,反映出他作为一个完全成熟的文学家驾驭创作的强烈的作者意识。 乔叟的作者意识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坎特伯雷故事》里。在这部著作中,乔叟也塑造了一个同名叙述者(学者们通常称其为“香客乔叟”或“叙述者乔叟”)。诗人通过这位同名叙述者在诗中一再表明,自己只不过是在客观描写香客们的行为举止并忠实记录他们的言谈和故事,但这些言行和故事都与自己无关。(11)他甚至还搬出柏拉图和耶稣这样的权威来支撑自己的创作思想。更重要的是,在诗作结尾,感到已临近生命终点的老诗人再一次列出自己的作品目录,对它们做了简单评判,认为其中许多译著和诗作不符合基督教观念,宣布将它们收回。不论是真心还是假意,都证明乔叟清楚意识到了自己的作者身份,否则他不会甚至无权将其收回。 巴特特别反感作者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作者的出现,“文学的形象被强制性地以作者、以他的性格、生平、趣味、情感为中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就是这样:谈论波德莱尔的作品意味着谈论波德莱尔这个人的失败,谈论凡·高的作品就是谈论他的疯癫,谈论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就是谈论他的恶习”(“Death”:141)。然而这并不符合大多数承认作者存在的批评家们的批评实践,六个多世纪的乔叟学术史也显然不支持这种说法。首先,在研究乔叟及其文学成就的汗牛充栋的成果中,专门研究乔叟生平的著述只占少数。其次,即使在《乔叟生平记载》这部使人们更加了解诗人生平的著作出版后,呈爆炸式增加的恰恰不是对乔叟生平而是对乔叟作品以及它们与乔叟时代社会文化关系的深入探讨;该书中的档案材料能从多个角度为学者们研究乔叟及其作品提供启发、线索、旁证以及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在20世纪,乔叟的全部作品,不论长短,都被研究者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而这些研究中鲜有所谓“强制性地以作者”为“中心”的讨论。就绝大多数批评家而言,他们关注的中心是乔叟的创作、文学成就及艺术手法,他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塑造,他作品中的文化意蕴和历史信息,他对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他对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后代英国文学家的影响和对英国文学发展的贡献。 如果巴特只是反对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批评,并以强调作者隐退来为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打开更广阔的空间,那么作为一种批评原则无可厚非。就对旧历史主义批评的纠偏而言,其实在他之前,现代主义文学家以及俄国形式主义者和英美新批评派在这方面就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努力。从表面上看,巴特似乎是20世纪文学批评领域“去作者化”这一重要传统的继承者,然而在本质上却并非如此。对于现代主义文学家和新批评派,“去作者化”或者说“作者隐退”是方法论(methodogical)而非本体论(ontological)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否定作者的存在,而是如新批评派著名的“意图谬误”论所说,文学批评要以作品而非作者意图为根据或标准。 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说:“一个艺术家,和创造万物的上帝一样,永远停留在他的艺术作品之内或之后或之外,人们看不见他,他已使自己升华而失去了存在,毫不在意,在一旁修剪着自己的指甲。”(12)这段被广为引用的话表明,在现代主义作家看来,艺术家并非真的不存在,只是“人们看不见他”而已。不仅如此,这种作者隐退的“客观化”创作不仅不表明作者不存在或者死亡,反而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福克纳在创作《喧哗与骚动》时,不断查看笔记本;后来在创作《寓言》时,他干脆把小说中那一个星期里发生的主要事件逐日写在书房的墙上,好随时查对,以免出错。那个精心选择每一个词,对手稿反复修改、大段重写甚至为是否使用标点或是否使用斜体而大费苦心,并因而不可避免地将自己投射进作品之中但还得费尽心机使“人们看不见他”的福克纳,显然不仅仅是“语言网络”或“社会能量”。 这些创作丰富且成就辉煌的作家似乎更能触及创作的本质,似乎也更能认识到作者的作用,巴特在《作者之死》里推崇的保罗·瓦莱利也不例外。巴特说,瓦莱利“从未停止过质疑和嘲笑作者”(“Death”:144)。然而,瓦莱利也强调作者的存在和作用:“艺术的目的和创作手法的原则恰恰是表达对一种理想状态的印象,在那样的状态中,那个拥有它的人能够自发、轻松自如并毫不费劲地创作出对他的本性和我们的命运的壮丽而结构精美的表达。”(13)瓦莱利在这里不仅没有“嘲笑和质疑”作者,反而高度肯定了他的作用,并把作者表达其“本性”和“一种理想状态的印象”作为“艺术的目的”。这似乎很难支持巴特对他的“推崇”。 当然,不同的作家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当代著名乔叟学者皮尔索尔说: [作家]“生平”与“作品”的关系可能有多种形式。它可能非常明显,如拜伦、奥斯卡·王尔德和西尔维娅的作品就几乎是他们生平的附录;它或者非常微妙,如艾米丽·狄金森等19世纪很低调的女诗人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就乔叟而言,他与自己作品的关系似乎出人意料地紧密:虽然他很少谈及自己,很少谈及他对同时代重大事件的态度,但他在其诗歌中存在的状况却在我们心中激发出非同寻常的欲望,想去了解他“究竟”如何。(14) 皮尔索尔随即指出,我们真正想探寻的并非生活中“真实”的乔叟本人,而是“他建构其诗歌自我(poetic self)的方式”(15)。虽然乔叟的诗歌自我与在海关工作甚至坐在书桌前的乔叟不能等同,但却密切相关。 巴特显然不会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作品与书桌前那个人没有关系,那人充其量只能像游吟诗人那样模仿前人: 我们现在知道,文本并非只是释放唯一的“神学”意义(作者-上帝的“神示”)的一串单线的文字,而是一个多维空间,在里面各种各样的作品——它们中无一独创——混合和碰撞。文本是由来自无数文化中心的引语组成的网……作家只能模仿先前的姿态,绝无创新。他唯一的能力是以这样的方式混合作品,用一些作品对抗其他作品,以致绝不会停留在其中任何一个作品之上。他如果想表达自己,他至少应该知道,他想“翻译”的那个内在的“东西”本身就仅仅是一部已经成形的字典,它里面的字只可能用其他字来解释,如此这般,以致无穷。(“Death”:146) 这段有关互文关系的论述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以互文关系来否定作者的作用和存在就似乎走远了。首先,如果作家想表达的“东西”是一部“字典”,那么它与寻常意义上那种“死”的字典不同,因为没有也绝不可能有两部完全等同的这种内在“字典”,而里面收录的“字”和相互“解释”的方式更不可能完全一样。其次,互文碰撞的确为文本的产生发挥着重大作用,也为文本永不停息的发展与生长或者巴特所说的书写注入永恒的生命力,但作者为什么就不能在决定与哪些作品碰撞、如何碰撞、碰的程度、角度和维度等方面有意或无意地起作用呢? 早期的乔叟和他的朋友高尔都主要在法国宫廷诗歌传统中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里都广泛存在着与同时代法国诗人以及奥维德等古典作家的大量作品的互文碰撞,但为什么在乔叟那里“撞出”的是《公爵夫人书》,而在高尔那里“撞出”的却是显著不同的《情人的自白》?乔叟的批评家们普遍注意到,一直在法国诗歌传统中创作的乔叟,其作品在14世纪70年代后期几乎是突然而且突出地呈现出在那之前英格兰文学中没有而且在他之后一段时期内也不会再现的意大利新文学的重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为什么就没有出现在高尔或其他任何英格兰诗人的作品里,难道仅仅是因为文本之间的误打误撞?英诗之父的个人经历、他的两次意大利之行、他的眼界和学识、他多年对英语诗歌艺术的实验与探索、他对意大利新诗的敏锐感悟和他诗人的艺术匠心全都无济于事?人们还可以进一步问,同住在人口不到十万且诗人屈指可数的伦敦城里,为什么乔叟时代的三位大师,乔叟、高尔和朗格伦(前两者还是相互唱和的诗友),却分别走出了三条不同的道路:朗格伦主要在古英语头韵体诗歌传统中创作,高尔从未走出法语宫廷诗歌传统,而乔叟却创造性地融合了法语宫廷诗传统、意大利新文学传统和英格兰本土诗歌传统并开拓出未来六百余年英诗的发展道路?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将“作者之死”斥为“神话”,他反问道:“如果《李尔王》和《哈姆雷特》是由‘社会能量’所写成的,那为什么这些能量恰恰在斯特拉福工匠之子的身上比在强壮的泥瓦匠本·琼生身上更具艺术生产性?”(16) 乔叟的杰出成就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来自巴特所说的各种传统的文本碰撞。但越杰出的诗人越具有独特性,在真正杰出的诗人那里,丰富的互文性只会增加其独特性,而不会将其消解。下面将谈到的乔叟作品中的那种独特的“乔叟性”,正是乔叟在乔叟时代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同大量文学前辈和同时代诗人碰撞出来的。在与乔叟“碰撞”过的文学家中,学者们一般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薄伽丘。乔叟的大多数主要著作,特别是诗人1380年后创作的重要诗作,都深受薄伽丘影响。他对薄伽丘作品的“借鉴”方式包括改写、扩展、缩写、成段翻译、情节模仿、意象借用等。比如,在乔叟中后期三部杰作中,《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大幅度扩展了《菲拉斯特拉托》,《骑士的故事》则将12卷史诗《苔塞伊达》的征战情节大规模删减,仅突出其中的爱情故事,而《坎特伯雷故事》对《十日谈》的借鉴主要是框架结构,但也对此做了创造性改进。难道所有这些都仅仅是模仿或者文本间漫无目的的碰撞,而没有英诗之父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所进行的精心操控与匠心独运? 意大利之行不一定是乔叟生平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件,但却是他创作生涯的转折点。关于他意大利之行的几条记载在乔叟及其作品之间建立起了更为紧密的关系;它们是学者们解释乔叟创作发展的重要佐证,也为解读乔叟中后期作品拓宽了视野。然而巴特不会这样看,他认为作者或者说“作者-上帝”限制甚至窒息了作品的意义:“给文本一个作者就是给文本强加一个限定,给它一个最终的所指,将书写终结”;相反,“通过拒绝给一个文本(以及作为文本的世界)指派一个‘秘密’,一个终极意义,文学解放出可以被称为反神学的行动,一个真正革命性的行动,因为拒绝禁锢意义归根结底就是拒绝上帝及其位格(hypostases)——理性、科学、律法”(“Death”:147)。对于信奉解构与多元的后现代,这个雄辩的论断特别有吸引力;然而,同《作者之死》一文里许多说法一样,这个以“解放”和“革命”的名义下的论断似乎也缺乏事实依据。 首先,将作者视为上帝,这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根据的伪命题。在前文所引用的乔伊斯那段话里,乔伊斯也将作者比喻为上帝,但那主要是就作者的“隐身”而言。相反,如伯克在《作者之死与复活》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巴特拔高作者并将其类比为上帝,这本身就是“歪曲”。上帝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其意志不容置疑,否则他就不是上帝;然而,除了巴特为达到为自己的文章增添宏大意义这一目的而仿照尼采著名的“上帝之死”宣言来宣称“作者之死”外,谁赋予过作者这样至高无上的神圣属性?伯克举例说,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的作者就绝非像神一样统管一切。(17)不仅如此,早在巴特之前,启蒙思想家们就以基督教《圣经》是人而非上帝书写为由指出其中的谬误与迷信。如果连长期以来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圣经》都因为是由人——尽管是像摩西和马太那样拥有先知和圣徒光环的权威——所书写而失去神圣,那还有什么书的作者可以享有上帝的权威?如果作者没有上帝那样决定一切的权威,也就是说,文本本就没有被禁锢,那又何来“解放”一说? 其次,这种“作者-上帝”禁锢作品意义的说法也与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与乔叟这样的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发展情形不符。尽管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旧历史主义批评曾有过分强调作者的倾向,然而人们对任何文本的解读从来也没有完全受控于所谓作者“指派”的意义;况且,就那种过分强调作者的倾向而言,其问题在于批评家,而并非由于作者的存在。实际上,在巴特通过宣布作者死亡来解放文本之前,没有任何一部作品的意义因其作者而被窒息,即使上帝无上的权威也从未能阻止人们对任何神学经典包括《圣经》本身进行各种解读。比如从基督教创建之初到宗教改革运动那一千多年里,尽管基督徒们坚信上帝是《圣经》的真正作者,但他们对《圣经》的不同解读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意义的矛盾冲突方面都超出了人们对任何文本的解读(18),而且还造成大量流血冲突。如果作者(包括上帝这样的作者)并没有或没能“禁锢意义”,那么以“作者之死”来“解放”作品似乎也就无从说起。所以,“巴特所斗争的那种作者中心论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虚构的”(19)。也就是说,巴特自己虚构出一个窒息文本意义的大写的“作者-上帝”,然后对其加以讨伐。其实,远在巴特建构“作者-上帝”的伪命题之前,“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类可用于几乎所有经典文学形象的似乎很俗的“老生常谈”实际上早已提前颠覆了巴特试图强加给作者的那种能“强加”给作品一个“唯一”意义的霸权。 同样,乔叟学术史也不支持作者终结作品研究的观点,《坎特伯雷故事》六百年的批评史证明,这部英语文学传统的奠基之作并没有因为有乔叟这样一位被尊为英诗之父的强力作者而影响其获得汗牛充栋且往往非常不同乃至相互对立的解读。乔叟学术史上一个重要发展是1968年《乔叟生平记载》的出版。现在,可以说没有一个认真研究乔叟的学者不参考这部著作。然而,自它出版以来半个多世纪,乔叟作品的研究向各个方向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当然,这绝非说乔叟学术研究的新发展全得力于这部著作,但关于乔叟生平的研究没有禁锢乔叟作品,没有终结反而促进了乔叟作品的研究,却是不争的事实。 前面提到,历代学者在各时代特定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文学语境中对乔叟及其作品进行研究,塑造出无数的乔叟形象。我们通过研究乔叟学术史发现,虽然这些形象无不闪现着批评家自己及其时代的影子,但它们也一般直接或间接来自对乔叟作品的解读,因此也都带有那种独特的“乔叟性”。正因其独特,“乔叟性”不可能出现在高尔或者莎士比亚作品中。 “乔叟性”是乔叟在创作时不可避免地投射进作品的诗人自我,它不等同于伦敦海关那位税收官或者肯特郡的治安官,但与他们血肉相连。在作品里,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在从创作意图、主题思想、谋篇布局、情节安排、人物塑造到遣词用句、韵律使用等所有层面上,都发挥着作用。虽然“乔叟性”在乔叟不同的作品中不完全相同,但它具有相对稳定性,可以被一般读者感受和被专家们识别。正是这种“乔叟性”使乔叟作品有别于任何其他作家的作品。比如,同许多后辈文学家一样,莎士比亚也深深受惠于乔叟,而且他的一些剧作也直接取材于乔叟诗作,但即便如此,他们的同名作《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仍然非常不同。伍尔夫以其杰出作家特有的敏锐与深邃,在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指出乔叟作品中那种只有乔叟才有的乔叟特性或她所说的“统一性”。她相信,如果乔叟人物闯入莎士比亚的领域,人们立即就能认出这个不速之客: 《坎特伯雷故事》具有无限的多样性,但在这种表面之下却是一种突出的统一性。乔叟拥有他的世界;他有他那些年轻的男人;他有他那些年轻的女人。如果我们发现他们漫步进入莎士比亚的世界,我们知道他们是乔叟的而非莎士比亚的人物。(20) 当然,这种“统一性”并非乔叟作品才有,所有作家的作品都必然带有其作者特有的印记,可以成为学者们鉴别不同作家作品的密码。比如,学者们经研究发现,在有幸留存下来的许多中世纪佚名手抄稿中,有四部优秀作品具有共同特性,被认为出自同一人之手。在这些作品中,《高文爵士与绿色骑士》和《珍珠》属于最杰出的中古英语诗作之列。由于对作者一无所知,学者们根据自己对作品的喜好将这四部诗作的作者称为《高文》诗人(the Gawain poet)或《珍珠》诗人(the Pearl poet)。同样,学者们也是通过对“乔叟性”的辨析,剔除了自15世纪以来托附在乔叟名下的大量伪作。 由于“英诗之父”日益显赫的声名,也由于乔叟是宗教改革运动中被容许阅读的两位英语文学家之一(另一位是高尔),因此自15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作品托附在他名下得以流传,并被收集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后来的各种乔叟文集里。在维多利亚时代,有一些伪作开始被识破,但剔除伪作这一需要渊博学识、敏锐鉴别力与耐心的工作直到19世纪末才由著名乔叟学者斯基特(W.W.Skeat,1835-1912)完成。斯基特通过长期研究,总结出了乔叟创作的特点,特别是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所特有的语法特征、语言风格和节奏韵律等深层次特点,揭示出了乔叟作品中那种如同一个人的指纹一样无法复制的乔叟特征,并以此为标准进行分析,判别真伪。他将鉴别出的大量伪作收集在一起,作为他编辑的乔叟全集的第七卷《乔叟派和其他作品》(Chaucerian and Other Pieces,1897)出版,并于1900年出版专著《乔叟正典》(The Chaucer Canon),系统分析乔叟创作的特点,说明自己排除伪作的根据。 剔除伪作是乔叟学术领域重要的基础工程,为现当代乔叟学术研究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如果作者在创作中不起作用,其作品没有独特性,学者们又如何能剔除那些伪作,确定“乔叟正典”?乔叟学术史表明,与对乔叟作品日益丰富的解读和乔叟不断变换的形象大体上同步发展的,正是乔叟作品中被揭示出来的越来越清晰的“乔叟性”,这种“乔叟性”成为了区分他的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的标志。无论学者们对他的作品的解读差异有多大,也无论他们的观点如何对立,他们都不会认为《坎特伯雷故事》或小诗《真理》有可能是他人之作。 乔叟学术史还从反面为乔叟的作者身份或者说“乔叟性”提供了一个有力而且特别有意义的证据,那就是长达一百五十余年的试图将乔叟“现代化”的运动的失败。乔叟去世后,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英语经历了从中古英语到现代英语的巨大变化,人们感到乔叟诗作越来越难懂。所以,从17世纪末到1841年的一个半世纪里,一些特别喜爱和推崇乔叟的英国诗人、学者持续不断地努力,用现代英语将乔叟作品翻译出版。这个被称为“现代化乔叟”(modernize Chaucer)的运动由桂冠诗人、英国文学批评之父约翰·德莱顿揭幕,随即许多诗人学者陆续参与,其中包括杰出的新古典主义诗人蒲伯,该运动一直持续到1841年。那一年,包括浪漫主义大师华兹华斯在内的一批诗人翻译出版了一卷乔叟作品。华兹华斯此前已翻译出版了一些乔叟故事。在1841年版乔叟译作出版后,华兹华斯等人余兴未尽,他们联系丁尼生、勃朗宁等大诗人,准备出第二卷,但这个计划却无疾而终。这个由一位桂冠诗人开启的运动终于在另一位桂冠诗人手里落幕。 在这一百五十余年里,许多乔叟作品,特别是《坎特伯雷故事》里的故事,被诗人们反复翻译出版。尽管德莱顿和蒲伯等人的译作也曾获时人赞赏,但严格地说,这些数量不小的译作没有一部真正成功,除出于研究目的的学者外,现在没有人会阅读这些译作。这些译作或许保持了原作内容,甚至在蒲伯等大诗人笔下获得了更为华丽的风格,然而在本质上,它们损害了原作最宝贵的品质,即使原作之所以那样杰出和独特的那种不可取代的“乔叟性”。 这些“译作”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作品。诗人们实际上是在按他们个人的理解,按他们时代的主流文学风格对乔叟诗作进行比较随意的改写。他们试图复制乔叟,但又不可能真正成为乔叟,他们的译作也就程度不同地都沦为平庸的模仿之作。比如,蒲伯笔下的巴思妇人低下庸俗,完全失去了乔叟原作中那个杰出形象所具有的蔑视权威、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庄严美。 其实,就在现代化乔叟的运动风靡之时,就有一些有识之士拒绝参与或提出批评。桂冠诗人和重要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沃顿(1728-90)如此评价蒲伯的译作《声誉殿堂》(The Temple of Fame:A Vision,1711): 蒲伯以他通常的典雅风格与和谐诗律模仿[乔叟的《声誉之宫》]。但正因为如此,他既没能正确表现这个故事,也损坏了它的特色……试图将整齐划一的形式和精确的意象,同按如此浪漫如此不合常规的原则建构的作品结合起来,就犹如将柯林斯廊柱(21)放入哥特式殿堂一样。当我阅读蒲伯对[乔叟]这部作品的典雅模仿之作时,我感到我是行走在一些被不合时宜地放入西敏寺大教堂的现代纪念物之中。(22) 同样,对于华兹华斯的乔叟故事译作,同时代诗人兰多(1775-1864)也给予了中肯批评。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可能写出《坎特伯雷故事》,正如他不可能写出《失乐园》、《斗士参孙》。”(23)兰多与华兹华斯交往颇多,对他十分了解。其实,兰多也被霍恩和华兹华斯邀请参加第二卷乔叟作品的翻译,但他在给霍恩的回信中断然拒绝了这种徒劳无益的所谓翻译。他说:“的确,我非常赞赏[乔叟],[但]为了换上极薄(哪怕更加清澈透明)的玻璃片而打碎他那幽暗但描绘丰富的玻璃,我绝不会参与其中。”(24) 在那一百五十余年里,不是少数诗人偶然不成功,而是包括各时期最杰出的英国诗人在内的所有那些试图现代化乔叟的诗人全都不成功。不论是不是碰巧,就在兰多发出那封信之后,现代化乔叟的运动终于结束。它不一定是因为兰多的信而终结,但兰多的批评可以说为这一运动做出了恰当的总结,也揭示了它不可能成功的根本原因:如同斯基特的深入研究一样,英格兰诗人们持续不断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乔叟的作者身份以及乔叟作品中不可复制的“乔叟性”。 ①该书一共收录493条记载,但最后一条是关于他墓碑的记载(see Martin M.Crow and Clair C.Olson,eds.,Chaucer Life-Recor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②Roland Barthes,"The Death of the Author",in Roland Barthes,Image,Music,Text:Essays,select and trans.by Stephen Heath,London:Fontana Press,1977,pp.142-143.后文出自同一文章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文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See Albert B.Lord,The Singer of Tal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④详见《贝奥武甫》,冯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868-874行。 ⑤See A.J.Minnis,Medieval Theory of Authorship,London:Scolar Press,1984,pp.10-11.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⑥希望自己声名永存是古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重要组成,这在基涅武甫同时代那些受日耳曼文化传统直接影响的古英语英雄诗歌如《贝奥武甫》里有大量表现。 ⑦See Geoffrey Chaucer,The House of Fame,in F.N.Robinson,ed,Th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Boston:The Riverside Press,1957,Ⅱ.614-659. ⑧《声誉之宫》创作于14世纪70年代后期,1374年到1386年间,乔叟在伦敦海关工作。 ⑨Chaucer,The House of Fame,Ⅱ.1876-1882. ⑩Geoffrey Chaucer,Troilus and Criseyde,in F.N.Robinson,ed,Th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V.1786.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卷码、行码,不再另注。 (11)详见杰弗里·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黄杲炘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总引》第725-745行、《磨坊主的故事》第3167-3186行等处。 (12)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黄雨石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53页。 (13)Paul Valery,"Remarks on Poetry",in T.G.West,trans and ed.,Symbolism:An Anthology,London:Methuen,1980,pp.59-60. (14)Derek Pearsall,The Life of Geoffrey Chaucer:A Critical Biography,Oxford:Blackwell,1992,p.5. (15)Derek Pearsall,The Life of Geoffrey Chaucer:A Critical Biography,p.5. (16)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康宁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4页。 (17)See Sean Burke,The Death and Return of the Author:Criticism and Subjectivity in Barthes,Foucault and Derrida,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p.25. (18)在《农夫皮尔斯》里,朗格伦对基督教上千年的历史中激烈对立的各种神学争论和引用《圣经》来打“《圣经》仗”的状况做了精彩呈现。 (19)Sean Burke,The Death and Return of the Author:Criticism and Subjectivity in Barthes,Foucault and Derrida,p.26. (20)Virginia Woolf,"The Pastons and Chaucer",in The Common Reader,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25,pp.26-27. (21)柯林斯廊柱是希腊式建筑的典型标志。 (22)Thomas Warton,The 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 from the Clos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to the Commencement of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Printed for Thomas Tegg,1840,p.170. (23)Qtd.in John Forster,Walter Savage Landor:A Biography,vol.2,London:Chapman and Hall,1869,p.506. (24)Walter Savage Landor,"From a Letter to Home",in John Anthony Burrow,ed,Geoffrey Chaucer:A Critical Anthology,Baltimore:Penguin Books,1969,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