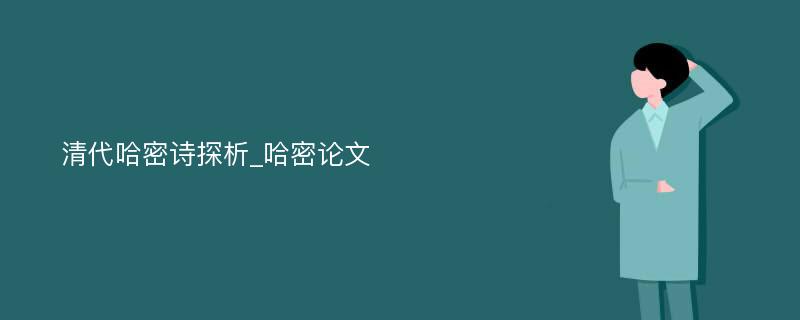
清人哈密诗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密论文,清人论文,诗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翻检清代西域诗,清人众多的哈密诗,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些诗作,反复吟咏了西域门户的重要位置,山南山北的迥异风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和闻名遐迩的地方特产,本文试作评析。
一、西域门户的重要位置
哈密,汉代称伊吾或伊吾卢,唐置伊州。它北依天山,南临瀚海,西通吐鲁番,东接嘉峪关,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有“西域门户”和“天山第一城”之称。历代中央王朝经营西域,必先取得哈密。特别是在清初康雍乾三朝统一西域天山南北的斗争中,哈密地方首领顺应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率先归附,此地遂为清军大本营和储粮转饷的后勤基地,使清朝继汉、唐、元朝之后,再次重新统一西域。此后一个半世纪,大批文官武将、满蒙八旗、汉军绿营、民户商旅、文人士子、发配之人等,都经哈密到新疆,为国戍边或开发建设,许多人建功立业,名垂史册。如满族官员秀堃在哈密东南的苦水驿作《苦水店题壁》所云:“名臣多少名千古,功业俱从此地来”。哈密作为西域门户,以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清人对此多有吟咏。
乾隆四十二年(1777),蒙古族官员惠龄以副都统衔补授伊犁领队大臣,赴任途中,在《过哈密》诗中这样写道:
西扼雄关第一区,鞭丝遥指认伊吾。
当年雁碛劳戎马,此日人烟入版图。
乾隆五十年(1785),原唐山知县赵钧彤因遭人诬陷被流放伊犁,途中在《哈密》 诗中也写道:
横扼新疆万里途,城门高榜古伊吾。
雪撑天山羊头坂,泉注山南牛尾湖。
是年,甘肃按察使王曾翼奉命随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巴里坤视察屯田,在《过哈密》诗中起句即云:“新疆南北此交冲,风土清嘉内地同”。
嘉庆十年(1805)春,宝泉局(即铸币局)监督祁韵士因局库亏铜案而无辜牵连,发配伊犁。此前他长期供职国史馆,是西域史地学的名家,在新疆更是著述丰富,其中有《西陲竹枝词》100首,开篇即吟咏《哈密》:
玉门碛远度伊州,无数瓜畦望里收。
天作雪山隔南北,西陲锁钥镇咽喉。
满族官员萨迎阿官至伊犁将军,道光十三年(1833)在哈密办事大臣任上曾赋诗《哈密》:
雄镇天山第一城,久储粮饷设屯兵。
路从此地分南北,官出斯途合送迎。
车马军台时转运,商民戈壁日长征。
瓜田万顷期瓜代,好向伊吾咏太平。
这一时期在哈密厅任幕友的姚雨春和杨泉山都有《哈密》诗,前者咏:“万笏青山围哈密,一天白雪唱伊州;”后者咏:“雪积天山摩峻岭,风高瀚海古伊州”。
以上清人诸诗,都突出吟咏哈密地处西城门户的重要位置,但又角度各有不同。惠龄作为一员武将,是驰骋马上、挥鞭指点看哈密,此时距清朝最终平定天山以北的西蒙古准噶尔之乱刚刚20年,距平定天山以南大小和卓之乱才18年,作者遥忆当年大军兵马由此开拔西征,感到欣慰的是天山南北已归入清朝的版图。发遣官员赵钧彤万里跋涉进入新疆,首先感受到哈密城横扼西域门户之势及哈密绿州北高南低的地形特点。祁韵士更是以史地学家的眼光来审视哈密,地处西域咽喉锁钥之地,横亘的天山将其分为南北两部。而萨迎阿的诗则表露出地方官的角色,作为掌管哈密军政事务的办事大臣,他镇守在西域门户,首先是屯戍之责,储粮转饷,还有对西域官员迎来送往;军台转运物资文报,关内的商人民户络绎进疆,由山北巴里坤去奇台、乌鲁木齐、乌苏、伊犁、塔城;由山南哈密去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莎车、喀什、和田,车马前后相望,连续不断。瓜代,即瓜期。指瓜熟的时候赴戍,到来年瓜熟时由人接替。多用以指期届已满等待移交的时间。作者望着万顷瓜田,不由想起自己任职将满,临别时还要咏诗,祝愿哈密太平昌盛。
这些诗作,笔力雄健,语句豪迈,景象壮观,格调高昂,作者们抒发了对西域门户哈密重要地理位置的重视和赞美,表达了作者渴望边疆安定、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情怀。
二、山南山北的迥异风光
天山横贯新疆中部,首先是把哈密地区分成了气候不同、风光迥异的南北两大部分。
山南哈密绿洲,泉甘土暖,草木繁茂,良田万顷,景色如画。这里的春天虽然姗姗来迟,却也是春意盎然,如诗如画,使长途跋涉、劳顿不堪的诗人们在感叹“春风不度玉门关”之际豁然开朗,喜出望外,嘉庆年间的李銮宣“将抵哈密,村落棋布,耕耨相望,边塞始见春光矣”,喜不自禁,写下《口占二绝句》:
黄尘不动午风喧,负郭人家水灌田。
山下桃花山上雪,柳烟笼到寺门前。
出关那识春风面,沙拥车轮雪啮毡。
何意伊州城一角,暮春恰似早春天。
桃红、雪白、绿水,柳烟,色彩鲜艳,充满生机。
光绪年间的裴景福对哈密绿洲胜景更是赞不绝口,流连不已,《哈密》二首之一:
天山积雪冻初融,哈密双城夕照红。
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好春风。
在哈密绿洲西部,以十三间房为中心地带是新疆著名的百里风区,这里一年8级以上的大风日为130多天,风速之大车马皆可掀簸空中,古代称之“黑风川”。嘉庆初年,洪亮吉由伊犁东归行至十三间房时,遭遇狂风,他在《道中遇大风,避入山穴,半晌乃定》诗中这样写道:“云光裹地亦裹天,风力飞人复飞马。马惊人哭拼作泥,吹至天半仍分飞”。
之后,祁韵士赴戍伊犁纪行诗有《风穴行》描述更为详尽:“沙碛崎岖亘千里,此穴横穿沙碛里。三间房至十三间,无端巨浪从空起。沙石错杂迷道路,昼夜狂号风不止。……须臾车亦腾空去,只轮不反人无踪。余始闻言疑过甚,亲历乃觉非无凭。”
道光年间的史善长更有《三间房遇风》:“百里三间房,屋低墙半圮。我读西域志,风穴乃在此。狂吹人上天,疾卷车如纸。今来日正中,清绝无尘滓。恨未一领略,空动子我指。忽闻声隆隆,雷转空山里。远自西南郊,徒觉振两耳。顷刻人声忙,闩车缚行李。我仆正饮马,人马仆如蚁。地轴神鳌翻,天柱毒龙毁。昆阳战正鏖,武安兵四起……”
写风声狂啸怒号,如雷霆万钧,由远而近,隆隆震耳;写风至如巨浪浊空,飞沙走石,如神鳌毒龙翻天覆地,又如鏖战激烈,伏兵四起;写风狂可以吹人上天,卷车如纸。行人遇险,面容愁惨。但作者并不感到愁苦,反而为能亲历这一西域奇观而欣喜:“仆面愁无色,我转大欢喜。奇境得奇观,陈编空载纪”。这场大风,“三日乃收声,开户作遐视。蓬裂车空存,雪净天如洗。”
由哈密北去巴里坤,要翻越东天山的库舍图岭,再经松树塘,这里在清初是清军大本营,一路以地形险要,风光秀美而著称。王曾翼有诗《南山口至松树塘》:“出关千里平如掌,行到南山窒马蹄。路入打班愁陟险,沟名焕彩孰留题。松生万树排青嶂,雪化千岩泻碧溪”。打班,今多写作“达坂”,西域少数民族语意为山中;焕彩,清初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嫌山中棺彩沟名不雅,改名焕彩沟。洪亮吉有《松树塘万松歌》24句,读罢使人感到千峰万峰,千松万松,迎面扑来,狂吟如注,既有景物的白描,也有哲理的问答,更有直抒胸臆的高歌,描绘出峰松的形态、色彩和明暗等,构成一幅气象万千的天山万松图。
嘉庆十一年(1806),直隶总督颜检以失察革职发配乌鲁木齐,途中写下109句的长诗《由南山口至松树塘》,记述所见险峻山势、嶙峋怪石、天山古庙、皑皑雪峰和千姿百态的苍松,以及置身其间的感受。十三年(1808)获释入关途中又作《由松树塘至库舍图岭》:“松塘有松松满山,千松万松盘复盘。盘山松高凌绝顶,天光云影迷青峦。青峦去天不逾咫,谡谡松涛入人耳。不知身在最高峰,但见天风落松子”。
道光年间,哈密生员张葆斋亦有诗《天山雪松》:
松雪相依耸峻岭,松青雪白两新鲜。
雪飞岭山添松态,松长山头映雪妍。
雪压青松松愈秀,松含白雪雪悠然。
天山松雪何时谢,雪积千秋松万年。
全诗八句九个“雪”字,以雪来衬托松,使苍松色彩冷峻明丽,姿态生动传情。飞雪为青松增添秀色和动态,青松使白雪更加亮洁耀眼,松与雪相映生辉,充满绘画美和意境美。
其他如庄肇奎的《由巴里坤度南山》、韦佩金的《松树塘万松歌》、方希孟《松树塘》等等,都是一首首激情洋溢的松树赞歌,展现出一幅幅美不胜收的天山万松图。正如道光年间的杨炳堃在《出得胜关抵松树塘》诗中所说:“满眼风光都入画”。
从松树塘西去就是山北著名而优美的巴里坤草原了。这里降水丰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宜农宜牧。巴里坤虽与哈密仅隔一山,却是冬冷夏凉,与泉甘土暖的哈密形成强烈反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王曾翼在《巴里坤》诗中吟咏:“伊吾五月如当暑,才度南山凛若秋,雪岭千年常冰玉,炎天一雨即披裘。”
嘉庆年间曾任哈官办事大臣的成书在《伊吾绝句》中这样吟咏巴里坤气候:
灯槽古驿乱山巅,咫尺炎凉各一天。
正是中元明月夜,雪花如掌落檐前。
作者自注:“灯槽沟在哈密极西,过岭即巴里坤界。哈密与巴里坤只隔一岭,哈密极热,巴里坤极寒”。中元为农历七月十五日。唐人岑参有诗:“胡天八月即飞雪”,可巴里坤七月十五日即雪花如掌,可见气候寒冷。清人笔下的巴里坤虽然寒色景致颇多,然而也不乏胜景使人流连,如颜检在《由巴里坤至碱泉》诗中所说:“图成西域壮山河,边外寒城胜概多。蜃海楼台呈色相,汉唐疆宇尽包罗。片云度漠随征马,丛草铺原散野驼。泉上传餐泉上宿,林泉滋味竟如何”。作者自注:“巴里坤(湖)常见蜃楼海市”。巴里坤湖古称蒲类海,在县城西北18公里处,面积上百平方公里。风光早晚有别,阴晴各异,四时不同,尤其是蜃楼海市的奇异幻景,妙不可言,令人神往。
嘉庆年间李銮宣有诗《薄类海》:“雪岭三峰矗,天光一镜涵。日高澄海市,波净壑云岚”。
咸丰初年流放乌鲁木齐的原代理湖南布政使杨炳堃也有诗《望蒲类》:
鞟壁重重勺水难,蓦教蒲海动波澜。
苍茫远与山吞吐,广袤浑如路汗漫。
可有舟航通利济?更无鳞甲长荒寒。
几时照澈天山月,濯足来看白玉盘。
巴里坤湖虽然既无舟楫,又无鱼类,但在干旱的新疆仍显得难得,作者遥想湖中倒映的明月,正是唐人李白吟咏的“明月出天山”;他向往临湖观月,不由想起李白有诗“幼儿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这湖光山色,的确给山北巴里坤增添不少秀色。 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
杨泉山的《哈密》诗咏道:“玉门关路通西域,回纥台墩傍碧流”。从中原内地首次来到西域的人们,一进入哈密便首先从这里领略到了西域维吾尔民族风情,不禁感到新鲜好奇,激发起浓厚的兴趣,咏诸笔端。
如祁韵士在《抵哈密》一诗中有“居民不改天方俗”之句。天方,即指麦加,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汉志境内,为伊斯兰教的圣地。哈密的维吾尔人信奉伊斯兰教,这就使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汉民族大不一样,主要节日是斋月之后的肉孜节和此后74天的古尔邦节。成书在《伊吾绝句》中这样描述:“走马儿郎手足鲜,靓妆少妇艳神仙。莫教尘涴新衣帽,转眼风光过小年”。诗中自注:维吾尔人过节“男则鲜衣走马,女则盛妆出看,儿童击鸡卵为戏”。维吾尔人衣着讲究,色泽鲜艳,过年更是人人盛服新装,载歌载舞,体现出这一民族豪爽乐观、能歌善舞的天性,如姚雨春在《咏(哈密)东庙儿沟》诗中所吟:“部分白帽风流远,翠曳红裙歌舞娴”。裴景福更在《哈密》二首之二中吟道:“踏残白剌过黄芦,麦秀宜禾绿似铺。更与偎郎弹一曲,不辞烂醉住伊吾。”
维吾尔人在瓜果成熟的季节里,常常以瓜代饭,瓜馕和食。成书《伊吾绝句》“剜瓜打饼过中秋”句下注曰:“土俗中秋削瓜为瓣,谓之剜瓜,以饼蘸而食之”。这里的饼,其实就是维吾尔人烤制的主食馕。赵钧彤《哈密》诗对维吾尔独特的饮食和居住这样写道:“野圃逢年瓜当饭,旗亭饷客茗炊酥。缠头王子台宫迥,牖户东开望上都。”
哈密汉城南有维吾尔城,哈密王驻此,宫殿起于台上。维吾尔人居住较为简陋,多是土木结构,以泥草涂抹,因冬季寒冷,所以门窗较小,有的只在屋上开一天窗。维语称炉子为务恰克,砌在墙根,一穴直达屋顶,以供取暖作饭。成书《伊吾绝句》还咏道:“细毡贴地列宾筵,密室无窗别有天。务恰克通风火出,不教粉壁挂柴烟”。
作为新疆门户的哈密,是东去西来的必经之地,与祖国内地的关系源远流长,如成书《黄芦冈》所云:“边民争识新都护,遗老能言旧使君”。汉唐曾在西域设都护,明朝著名使臣陈诚曾亲临哈密。各民族在这里友好相处,交往频繁,多民族文化融合现象较为突出,首先表现在语言上,许多维吾尔人都通汉语,而且多是汉维语杂用,对这一独特的人文景观,诗人们留下了生动的一笔。如国梁《南湖道中》:“缠头亦解华言好,笑指连城入市阛”。成书《哈密使署作》:“慕化藩王能国语,太平边帅似神仙”。王树楠《哈密》诗云:“彻田公守望,汉语杂胡戎”。
更多的表现在共同开发和商贸活动中。秦承恩《题长流水壁》:“当年戎马地,今日黍禾乡”。色桐岩《榆树沟》:“夷汉皆趋畎亩事,虽然绝塞乐安闲”。史善长《哈密》:“贸易杂夷夏,飞鸣有燕莺”。这种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有利于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如秀堃《邮程杂咏》所说:“声教覃无外,华夷已一家”。
四、闻名遐迩的地方特产
哈密资源丰富,物产丰饶,最著名的要数山北的巴里坤马和山南的哈密瓜了。
自古以来,西域就以盛产名马而闻名,如祁韵士在《西陲竹枝词》百首中咏《马》:“渥洼异种漫相推,宛马何须独擅才”。诗中自注:“今安集延为汉大宛。西域皆产良马,不必专属一地”。巴里坤马,向以矫健有力、善于爬山越岭著称,与伊犁马、焉耆马并列为新疆三大名马。在新疆任职多年,官至布政使的王树楠在《哈密道中》这样称颂巴里坤马:
倚天剑器冷如冰,四顾山河感废兴。
拓地已通西域马,抟天休笑北溟鹏。
“倚天剑器”即倚长天剑。想象中靠在天边的长剑。宋玉《大言赋》:“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拓地指西汉初期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终于切断匈奴右臂,在西域开拓了疆土,从此西域骏马不断输入内地中原。体态雄亦健,奔驰如闪电,是足可以与庄子《逍遥游》中振若垂天之翼、抟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相媲美的。
王树楠还在《哈密道中》之七吟咏:
天山顶上看伊州,衰草凄迷大碛秋。
一簇旌旗围猎马,黑雕呼下暮云头。
读诗前两句,不由使人想起唐人岑参《过碛》诗所吟:“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而给那衰草凄迷的戈壁之地增添生气的,正是迎风招展的旌旗下纵横疾驰的巴里坤马,与空中的黑雕一起,成为天地间的骄傲。在王树楠之前,萨迎阿于哈密所作《偕常雨帆秦小坡登南楼,即用小坡红字韵》中的“雕鹗盘空双翅雪,骅骝开路四蹄风”,不也是对巴里坤马骄捷如风的赞美吗?
关于哈密瓜,其实是新疆许多地方的甜瓜的通称,因最先由哈密王作为贡品传入内地而得名,瓜以地取名,地以瓜闻名。如杨泉山《哈密》诗云:“圣世安边开万里,年年瓜贡渡芦沟”。哈密瓜由此名扬天下。
哈密瓜虽非哈密特产,但作为瓜中珍品和甜瓜之王,哈密所产之瓜的确与众不同,乾隆年间因泄言漏密发配在乌鲁木齐的原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晓岚曾亲自访询得知“此地土暖泉甘而无雨,故瓜味浓厚”。为此他在《阅微草堂笔记》卷5中这样赞美道:“西域之果,葡萄莫盛于吐鲁番,瓜莫盛于哈密”。在他之后,王曾翼《过哈密》诗也吟咏:“碧涨瓜田渠汩汩”,一派丰收景象。
嘉庆年间,祁韵士在《西陲竹枝词》中咏《哈密瓜》:“分甘曾忆校书年,丝笼珍携只半边。今日饱餐忘内热,莫嫌纳履向瓜田”。他回想起乾隆年间在国史馆编校典籍时,曾蒙御赐品尝过哈密瓜,如今亲临哈密,可以任意饱餐了。乐府诗云:“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然而,哈密瓜的香甜可口太吸引人了,诗人戏谑说自己吃瓜时忘记了古训。这也难怪,此前秦承恩《题长流水壁》说:“老饕堪慰藉,瓜剖水晶瓤”。这可说是狼吞虎咽了。道光年间,许乃谷咏《哈密瓜》:“伊吾瓜夺邵平瓜,碧玉为瓤沁齿牙”。邵平为汉初之人,本是秦东陵侯,秦亡为民,种瓜于长安城东,相传所种之瓜味道甜美,人称邵平瓜,又称东陵瓜。诗人认为它与哈密瓜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哈密瓜如晶似玉,飘香流汁,观之使人垂涎欲滴,食之更沁人心脾。
哈密瓜不仅味道甘美,而且营养丰富,夏日食之能生津消暑,解渴充饥,冬日食之也是别具风味。光绪间戊戌变法后,积极参与维新变法的帝党要员、总理大臣兼户部侍郎张荫桓被革职流放乌鲁木齐。途中受到哈密王沙木胡索特的热情款待,向他赠送“窖藏秋蒂斑如花”的著名特产哈密瓜,虽说“春宵剖啖味殊薄”,但“冬日食瓜美无度”。他久任清朝使臣,遍历欧美各国,可谓见多识广,但对哈密瓜赞不绝口,在《哈密王沙木胡索特馈哈密瓜》诗中说:“欧罗巴洲翊奇产,持较哈密谁比数?惟期得地善滋植,汉家久已宽贡赋。旧典邮递三百枚,甘州军门慎将护”。“佳果宜留去后思,客路镇心勿他顾”。说香甜可口的哈密瓜,使人常思念回味。
最著名的要数宋伯鲁的《食哈密瓜》诗:
龙碛漠漠风抟沙,胡驰万里朝京华。
金箱丝绳慎包匦,使臣入献伊州瓜。
上林珍果靡不有,得之绝城何其遐。
金盘进御龙颜喜,龙章凤藻为褒嘉。
我从毁齿已耳熟,剖玉无缘空叹嗟。
岂知年衰忽到此,求取任汝无疵瑕。
翠滑黄皱不一种,雪中丹里人所夸。
百钱一枚趁晓市,盈筐累担来田家。
玉浆和冷嚼冰淞,崖蜜分甘流齿牙。
纵横银刀妙剖劈,顷刻欲尽群儿哗。
秋深腹冷此所忌,慎勿饱食途路赊。
宋伯鲁曾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在政变后被革职,逃亡被捕,伊犁将军长庚将他救出带到新疆,途经哈密时写下这首诗。全诗一气呵成,再现了穿越茫茫瀚海,顶着狂风飞沙,千里入贡哈密瓜受到皇上珍爱赞赏和嘉奖的生动画面,也为作者写自己对哈密瓜的品尝和赞美作了有力铺垫。哈密瓜品种繁多,颜色或黄或绿,瓜纹或光滑或网皱,内瓤不同,口感各异,任人挑选品尝。面对这玉液琼浆般甘甜如蜜的哈密瓜,诗人垂涎不止,尽情享受起来。虽然心知深秋腹冷应食之有度,也一再叮嘱自己“慎勿饱食途路赊”。却还是忍不住将切开的瓜都快吃了个净光,”顷刻欲尽群儿哗”,引起旁观孩童的一阵喧笑。
清人的哈密诗,作为清代西域文学的一部分,不仅具有表现爱国主义精神、民族友好和睦思想的共同性,还具有反映哈密独特风貌及诗人们热爱哈密之情的地域性。清人的哈密诗,给哈密的历史增添了光彩,也使后人不能忘怀!
标签:哈密论文; 巴里坤论文; 西域论文; 新疆天山论文; 哈密瓜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松树论文; 天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