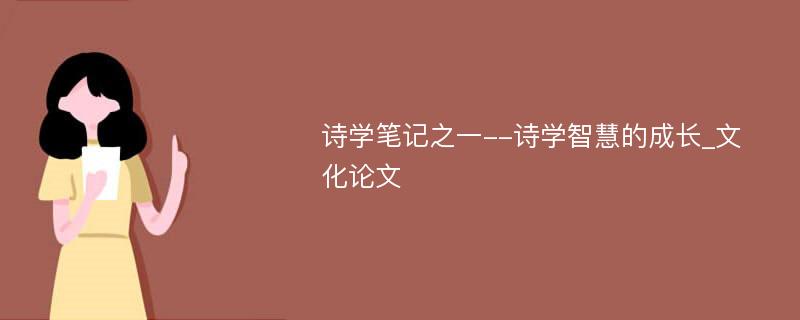
诗性智慧的生长——诗学笔记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生长论文,智慧论文,笔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德格尔在《诗人哲学家》里提出:“歌与思,皆是构诗的枝干;它们诞生于在,又入达在的真理。”这就为诗歌确定了爱智的性质与权利。凡属诗性的都是运思之诗。不过,思之诗性和诗之智性一样常常被遮蔽着。人们往往说,诗的天性是强烈的或最高的抒情性;但我愿意指出,诗歌在一定意义上,是一时代一民族情感水平和智慧水平的标志。
人类是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成长起来的。在人类文明滥觞之时,思(哲学、宗教)与诗(歌咏、舞蹈)浑然天成,统一于先民的情绪、意识和智慧。这种智慧被维柯统称为“诗性的智慧”,年复一年、一代一代地发展生长。
这是艰难而漫长的文明步履。
这种智慧的生长,最初是与朦胧的物种本能相羼和、相胶结着的。各种感官是初民们感知事物的唯一渠道,我们也只有从人心感官的内部变化中去考察与寻找诗性智慧的本原。维柯的人类学研究表明:“诗性的智慧,这种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开始就要用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像出的玄学,像这些原始人所用的。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像力。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诗就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因为他们生而就有这些感官和想像力);他们生来就对各种原因无知。无知是惊奇之母,使一切事物对于一无所知的人们都新奇的。他们的诗起初都是神圣的……”〔1〕。好奇心出自人的本性, 在初民那里,它是无知之女,知识之母,智慧之父,也恰恰是跨入诗歌之门的重要一步。
人所共知,从把人类与动物界区分开来的工具产生之日起,先民们开始了把自身力量外化于自然的旅程。在为获得衣食住所和种的蕃衍之需而付出心血汗水的同时,他们的感觉力和想像力,导向人类自我意识的最早端倪——愿望的产生。愿望(包括祈求)是生长智慧也生长诗歌及各种艺术的原始契机。愿望的出现,既反映了人类与自然又共存又对峙的处境,也倾注着先民们混沌、简朴、被动、执拗的原始精神。可以说,歌舞作为这种原始精神的载体,呈现着诗性智慧的原始风采。
在这种歌舞中,我们看到了最早使用火的山顶洞人。他们的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他们在族系成员的尸体旁撒上矿物质的红粉。“红”色对他们已不是生理感受的色彩刺激,而是参与了、积储了他们诗性的感觉力和想像力。他们把象征生命的“红粉”用于欢愉和悲哀,表现了对生命的崇拜、热爱和焦虑。这种图腾式的原始智慧活动,有祈祷的功能。在美洲印第安人那里,为了表现对太阳的崇拜,脸部和周身涂满白色粘土,用以象征太阳的白色。他们手拿吉羽装饰的舞棒,围着火堆歌舞,从东到西地来回移动,以此模拟太阳的运行。在这里,愿望体现为生命动作机能的展示,先民情绪置于再现的艺术去渲泄,原始智慧往往是生活和生命存在本身在黝古土壤中的律动。
在这种歌舞中,诗性的存在替代着现实,祈丰的愿望超越着现实,先民们得获欢乐也创造欢乐。看一下奥利西斯崇拜由西亚传入古埃及,复传入古希腊而成为“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过程,就可想见人们当初如何为这种快乐而心醉神迷。难怪尼采激扬文字,生动地描绘那个由酒神崇拜造就的诗性的世界——在酒神的魔力下,“人们之间所曾构筑起的,所有僵硬、仇视之藩篱,不论它是必然的或专利的,都粉碎了。环宇和谐之福音嘹亮地唱起,每个人都变得十分和睦,就如同马雅人的帐幔也都被扯得成为一块块碎片一般。在神妙的‘唯一’(oneness )之前,一切隔阂都杳无踪影。现在,人们都以歌声和舞蹈来表达他的意思,如同一个高境界团体中的份子。大家忘了如何走路,如何说话,人们只是达于飞舞之境。人的每一个动作都显示了一种喜悦,由着他,唱出了自然力的歌声,这个能力又使得动物能发为言语,大地涌出美乳与甜蜜。他觉得他自己简直变成了神,步伐意气扬扬,充满欢欣,犹如他在梦中新见的神祇一般。不再有艺术了,他自己已变成了一件艺术品。宇宙的创造力在他的心神荡怡中展现出来,这太初之唯一,这伟大的满足。”〔2〕他们进入“酒神”的天地, 一切似乎都是诗意地感及和思及快乐的生存,原始歌舞一如闪烁黑夜的星辰昭示他们的前程。
在这种歌舞中,歌、诗、舞、乐、咒语常常混沌一体。这就是我国乐典《乐记·乐象篇》所说的:“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也因此,中国古代有“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葛天氏之乐,有“断竹,续竹;飞土,逐宍”〔3〕跳跃性强、节奏明快、富于生活质感的《弹歌》; 有模仿种种动物动作或表现诸项农牧劳动的亦舞亦歌,以再度体验自己的快乐和冲动。也因此,在非洲原始部落,诗、歌、舞的合一成为初民以其灵性与智慧同外界应和交往的主要媒介,例如有一首刚果原始的《动物世界之歌》,是以自发性的混合媒体的仪式剧方式由全部落亦舞亦唱的:
独唱:鱼跃合唱:Hip!(拟声)
鸟飞 Vi
猴跳 Gnan!
独唱:[边唱边摹拟动物舞跃]
我向左跃腾
我向右跃腾
我是鱼
滑行水中,溜走
弯转、跳!
万物并生,万物舞跃,万物鸣唱……
独唱:鱼跃合唱:Vip!
鸟飞 Vi
猴跳 Gnan!
独唱:[边唱边摹拟……]
鸟飞走了
飞飞飞
走了,再回来,匆匆
然后飞升,浮翔,俯冲
我是鸟
万物并生,万物舞跃,万物鸣唱……
独唱:鱼跃合唱:Vip!
鸟飞 Vi
猴跳 Gnan!
独唱:[仍边唱边摹拟……]
猴儿从树枝到树枝
他跑,他跳、他飞跃
和他的妻子儿子
满嘴食物,尾向朝天
我就是猴儿,我就是猴
万物并生,万物舞跃,万物鸣唱……
独唱:鱼跃合唱:Vip!
鸟飞 Vi
猴跳 Gnan!〔4〕
以诗性而论,天、地、物、人的浑一感受,表现了原始人的感知与想像;复沓,又成了原始歌谣艺术的生命;而舞、乐、歌、词乃至部族不分主宾地全体参与舞唱,表明他们并无一己的功利观念,而是源于群体生活、发乎群体智慧、唤起全面感性的一种共同创作。他们以全然开放的喜悦与兴奋去承受造化的活动,以庆典的心绪和情感去迎接万物齐一的景观。他们并不知晓这就是诗。但诗性的原初智慧,正是从这种廓大的心胸与天放的视境中呈示出来。
这就是原始的智慧。如果按照柏拉图替智慧所下定义——“智慧是使人完善化”,那么,在人类的曙光期,原始粗鲁的舞与歌中产生的那种人、兽、草木及其想像物,都以猜测或预言来观照天神。他们祈求预兆往往出于对不可知的惊奇之物的情欲和笃爱。但在先民多少带有玄学的诗性智慧中,丝毫没有抽象,没有淘洗、凝练或精神化的痕迹,因为他们的心智浸泡在感觉里,情爱埋葬在躯体里,歌里舞里所获得的感受和渲泄的情绪便意味着一切。这是充溢天地的原始精神,也可称作诗性智慧的原始时代,歌与舞以一种自然体认为尺度。
种子一旦发芽,种子便体现在芽孢之中。原始诗性尽管粗鲁,但它不脱离土地,毕竟是有生命的足可发育的活体。随着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人类社会中的共同作用,分工出现了,人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愿望与手段、目的和过程的区分日渐清晰起来。这样,除了打猎、畜牧和耕种外,有些人就去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交通;有些人通过自然神学进一步想像出各种神来;有些人通过逻辑功能去发明和编制各种语言、文字;有些人通过经济功能去创建家族,设置村落;有些人通过天文和时历,把星群从地面移升到天上和测量时间的起源;有些用自然地理(如希腊人、中国人)把全世界都描绘为在他们的本土范围内……同样,有些人需要重温过去的狂欢与克制并从中汲取痛苦和美的力量,需要从历史的激荡和心灵的搏击中感应崇高与圣洁,需要以璀灿的幻想驾驭多艰的生存去提前感受理想实现后的喜悦,这就使人类机体上敏感的器官得以进化,诗性的智慧业经痛苦和欢乐的洗礼,既参与了艺术和科学的精神产品的共同创造,又把诗与其它艺术品种“分工”了出来。不是凭肉体而是凭精神去想像去创造,就使原始人的智慧跨入古代人的智慧,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在希腊文里是“创造者”,在汉语里是“作者”,而印度人则称作“智者”。
以颂赞大地为例。原始人的颂赞,是以一种所有感官和自我环境浑然一体、全世界似乎成为躯体的延伸、原始生命在黝古的土壤中躁动的方式,表达古昔之民的诗性智慧。非洲的一首原始歌谣是这样反复边舞边唱的:
大地与尘土
最可信赖的人
我依靠着你
大地,当我快死时
我依靠着你
大地,当我活着
我信赖着你
大地,当我活着
我信赖着你〔5〕
生死皆在自然的律动里,所有感官与大地调合齐一,呈现出全面感性的诗性意态,却因“无心”而缺乏理智的思索与灵魂的呼喊。古代人的颂赞则不同了。古印度智者的一首《大地》诗,显然以“有心”去迎接雨季中的大地:
真的,你就这样承受了
山峰的重压,大地阿!
有丰富水流的你啊!用大力
润泽了土地。伟大的你啊!
颂歌辉煌的鸣响着,
向你前去,宽广无限的女人啊!
像嘶鸣着的奔马,
你发出丰满的云,洁白的女人啊!
你还坚定地用威力
使草木紧系于土地;
同时从闪烁的云中,
由天上降下纷纷的雨滴。
——《梨俱吠陀》卷五第八十四首〔6〕
尽管这首诗也呈现了人们恒常的与自然环境的交往,也充满了神异的卑微者的谦逊,表面上看来也是把一种自然现象加以神圣化;但若作进一步解析,就可以看到古代人开始以人为座标去观察和描述自然,不像原始人以回归太和为满足,而是将自然现象予以初步的人化,“外在的旷野”化为一个“内在的旷野”,参与伟大的天作之中。这里有幻想、象征、神谕和命运,仿佛是古代人心灵的投影。一切仍很单纯,但已由童贞进至贞洁。在诗耕地上深深印记着一种庄严,一种将自然同化于人,在宗教、祈祷和信仰的三位一体中孕含万象的色彩。诗性智慧赋予歌唱兼有抒情与史诗的特征。
进入这个时期,文化诗人开始凭理智、激情和想像来从事诗创造。维柯对古代人中的智者作了这样的确认:“伟大的诗都有三重劳动:(1)发明适合群众知解力的崇高的故事情节;(2)引起极端震惊,为要达到所预期的目的;(3)教导凡俗人们做好事, 就像诗人们也会这样教导自己”〔7〕。古昔的混合媒体方式演出的舞唱, 变成了现在个体感受客体的吟咏。不过,诗的载道,表现欢乐或发出悲叹,歌唱的是那些世纪、人民、民族和国家,教化人们产生对英雄(或神与半神)的向往、对乡土(亲人与家园)的热爱和对先辈的崇敬。荷马、屈原成了巨大而普照的火炬,它代替了凡俗智慧中种种摇晃不定的灵光。
尽管地球本来是圆的,但毕竟陆地分出了天空,树根长出了枝叶,泉水流成了江河,马蹄踩出了道路,道路又通向四面八方。存在决定意识。不同的土壤上开放有异样的诗性之花,智慧以其各种意态在不同地域生长。希腊人受到驳杂地形——海湾和贫瘠的多石山地的制约与影响。对大自然既恐惧、崇拜又愤怒、抗争,他们心目中神与人的对立象征着自然与人类的相峙——尖锐而又永恒,形成了把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思索的诗性智慧方式,悲剧命运主题的突出和史诗的发达,促使他们的智慧多用于叙事能力上;印度人居住在恒河、印度河流域,大自然对他们的恩赐不能说不慷慨,但炎热、暴雨、种种病毒造成的人寿威胁,使他们对造化的恐惧与崇拜转向了唯求生命的永恒,因而对自然的奥秘与社会的结构不甚关切,倒是往往以内心反省的方式,在人神之际沉思默想的契合上倾注着诗性的智慧;中国人又不同,东临沧海,北连大漠,西为大山高原所阻,如此地理环境产生了纯正、独特、飘逸的古代灿烂文明,而周文化圈与楚文化圈的互补,形成了以两极、中和、神秘为审美心理特征的、“直观外推”与“内向反思”往复推衍的诗性智慧方式,加之重叠、回环、横向联系的思维与想像,使从屈子到李杜等一代代智者,以最诚挚而极含蓄的、浸透着酒与泪的微笑,以浓缩为掷地有声的气韻与格律,表达着对和谐与统一的彼岸世界的追求。然而,不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古代人,毕竟还受到时代、思想与智慧的局限,他们所面临的是一种神秘力量,人在那个世界中还不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众多诗篇所传达的,是无穷无尽的“天问”与“离骚”,是人类对自身无力驾驭自然和社会而生发出来的悲怆性意识,是人类渴望摆脱愚昧走向文明的痛苦的人生情调和心灵磨难。如果说原始人的智慧以自然体认作为尺度,那么,古代人的智慧则以反思自然作为尺度——尽管有不同的诗性思维方式,他们却无法从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中找到解脱。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上下以求索。
诗性的魅力继续环绕着物质并以迷人的微笑吸引着人的身心。然而,随着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世界和诗的又一个纪元开始到来。一种精神的宗教与信仰,取代物质的、外在的多神教,潜入古代社会的心脏并将其古老的城堡摧毁,而在古代文化的废墟上播撒近代文化的种子。世界和社会处于深刻的动荡中。人,在这巨大的变迁面前反省起来,对自身产生怜悯,也思索生活中苦味的揶揄。于是,我们看到了忧郁、忏悔、沉思的天使和争论、分析、辨认的魔鬼同时出现——一种新的智慧和诗学也就成长了起来。雨果用神采飞扬的笔墨描绘这种诗性思维的新变:
直到那时为止,古代的纯粹史诗性的诗歌艺术也像古代的多神教和古代哲学一样,对自然仅仅从一个方面去加以考察,而毫不怜惜地把世界中那些可供艺术模仿但与某种典型美无关的一切东西〔8〕, 全都从艺术中抛弃掉。 这种典型美在开始的时候是光彩夺目的, 但就像一切已经秩序化的事物所常有的情形一样,到后来就变成虚伪、浅薄、陈腐了。基督教把诗引向真理。近代的诗神也如同基督教一样,以高瞻远瞩的目光来看事物。她会感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她会发觉,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她还将探究,艺术家狭隘而相对的理性是否应该胜过造物者无穷而绝对的灵智;是否要人来矫正上帝;自然一经矫揉造作是否反而更美;艺术是否有权把人、生命与万物都割裂成两个方面;任何东西如果去掉了筋络和弹力是否会动得更好;还有,作品是否要不完整才能达到和谐一致。正是通过这些探讨,诗着眼于既可笑又可怕的事物,并且在我们刚才考察过的基督教的忧郁精神和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下,将跨出决定性的一大步,这一步好比地震的震撼一样,将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它将开始像自然一样动作,在自己的作品里,把阴影掺入光明、把滑稽丑怪结合崇高优美而又不使它们相混,换而言之,就是把肉体赋予灵魂,把兽性赋予灵智……〔9〕
雨果是位诗人,我们自然不必逐字逐句地推敲其表述精确与否。他的智慧与观念,实际上化作一首洋溢着浪漫精神的关于生活真实与灵魂解放的赞美诗。柏拉图不仅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还把父亲、母亲、一颗颗赤子之心也赶出理想国,使人们被封闭在经验的、理性的、神秘的顽固堡垒中;近代人则举起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旗帜、解放普罗米修斯,解放自我,把人的个性、尊严和价值从神、上帝那里归还自身。莎士比亚唱出一曲人的颂歌:“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0〕一种高度的人的觉醒成了近代人智慧的主旋律。个性解放成了普照一切的近代精神。天才的智者呼吁写人,写活生生的人,写人的七情六欲,写人的意志、力量、内在需求和思绪愿望,写人的世俗的、不掺假的、从幕后去看它的真相的生活,认为这才是个性的人、自由的人,才是真实的生活、真正的人生。
自我意识因此而得到迅速发展。人在近代文化思想中的觉醒,也是人在诗性智慧中的自我发现。诗与诗人追求一个自由的自我个体,一种人格上的独立自主。他们厌恶古代智者退隐自守、清静无为、立意鸣高的文化哲学,热烈奔放地赞美人们生气勃勃地冲击传统规范,如痴如醉地堕入情网,痛快淋漓地享受生命,创建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人生的一切痛苦和欢乐化作笔底波澜,可以命名为“自我之战”的人之歌。在近代人的智慧里,仿佛出现了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到社会上去挣扎,去奋斗,去卷入喧哗与躁动,也许凯旋,也许败归;另一个自我便带着宁静的笑容,把第一个满身汗水、遍体鳞伤、笑着又哭着、慷慨又忧郁的自我,迎回缪斯的王国里来,将成捆成堆的战利品列数给他看,连败归者也有一份。这当然不是超俗的无我的精神幻像,而是生命主体在智慧海洋里新的呼吸:
我不能离开你胸中的我的灵魂,
正如我也离不了自己的肉体;
你的胸膛是我的爱的家:我已经
旅人般流浪过,现在是重回家园;
准时而到,也没有随时光而移情——
我自己带水来洗涤自己的污点。
虽然我的性情中含有一切人
都有的弱点,可千万别相信我会
如此荒谬地玷污自己的性情,
竟为了空虚而抛弃你全部优美……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第一○九首
这也自然失去了群体意识的原有色彩和那种人与宇宙万物天然造化般的共存状态,揭开了用以掩盖人与神的那一层云雾,而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呈现于世人面前。如蒙田的自我解剖:“随着风向的转换和变化,一切矛盾都可以在我身上发现。害羞和傲慢,贞洁和好色,健谈和寡言,笨拙和高雅,机智和迟钝,暴躁和温柔,虚伪和真诚,世故和无知,慷慨、贪婪和挥霍,这一切我都不同程度地在自己身上看到了。”〔11〕如卢梭的自我忏悔:“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而,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12〕又如贵族统治集团的逆子贰臣拜伦,他对卢梭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诗人自己:
他能把疯狂的性格描绘得美丽端庄,
把不规的行为和思想涂上灿烂的色彩,
他的言语就像眩眼的日光,
使人的眼睛忍不住流下同情的泪水。〔13〕
在他们看来,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包含了人类的全部内涵和形式。以历史的目光视之,夸大“自我”创造自己命运的能力,正反映了近代上升中的资产阶级解放个性、发展自身的要求;而以诗性的智慧观之,这种“自我”的发现和表现,实质上是要求诗歌从宗教神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从陈旧的宗教故事,圣经传记和民族传奇中解放出来,去歌颂或鞭鞑现实中活生生的人,去传送“真人”的“真性情”。这是人类智慧的前进而并非倒退。批判“上帝是人的本质”的神学观点而提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学命题,正是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诚如恩格斯所指出:“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14〕诗性智慧从“神本”到“人本”的躁动,表明一种独立的艺术意识开始生长。即从传统的“模仿说”向新质的“表现说”的转移。但丁的《新生》是西方第一部人类作为个体对自己内心生活作深入自省的表现性作品;歌德的《浮士德》表现了一个伟大忏悔中的片断,亦可称作西方精神历史的一份自传。问题是,近代资产阶级的贤哲与诗人,往往把人看成抽象的人,把人的本质看成是空洞的理性、意志和泛爱,因而在揭穿了宗教与神的异化之后又面临着揭穿现实生活的异化、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的历史任务面前,就显得软弱无力了。
中西诗学,各有颛家,智慧之色面貌迥殊。言志说和模仿说是中西诗学的正宗传统艺术观念,及至近代,则呈现异途同归的发展趋势。主张“诗言志”并非否定情理和谐,但发乎性情需止乎礼义,致使多数古来诗人英华内敛而鲜逞幻想,淡漠宗教而悲情不丰,局于凡近而不乐冥思。到了晚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萌芽,李贽、汤显祖以及“公安派”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独张新帜,与传统的“言志说”相对立。李贽猛烈抨击假道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教义,主张“声色之来,发乎情性”,表现“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15〕的童心;汤显祖追求“有情之人”(即“真人”)和“有情之天下”(即“春天”),反对“以理相格”而强调心灵飞动:“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而憺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16〕,且化为杜丽娘那样包含了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艺术形象;袁氏兄弟则认为近代文人应表现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17〕的每个人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这些“真人”、“真声”、“真文”的倡导与呼喊,反映了冲破封建礼教束缚、鼓动诗人自由创造的精神。西方诗学从“模仿说”走向“表现说”,中国诗学从“言志说”趋向“情真说”,呈示方式不尽相同,但并非起迄相逆。总体上看,诗性智慧的延伸恰恰与人类历史的基本发展趋势相一致,表现了以个性解放为尺度的价值观。因为重视独立主体、自由个性、自我表现等等。这些近代智性观念,均属古代封建社会形式解体、资本主义新兴生产力崛起的产物,只是中国诗学的步履显得更沉重、更迟缓罢了。
智慧之帆在诗歌的大海里波动。潮流越过潮流,泡沫随着泡沫。每个世纪总要带走一些、也带来一些什么。进步,意味着目标不断前移,阶段不断更新,视野不断拓展。当历史揭开新页——人类进入20世纪时,诗性智慧倘若仅仅以个性解放为尺度,显然已经远远不够了。世界进入了现代。现代人要探寻更理想的尺度。整个地球发生着旷古未有的大变革。可以想见,两次世界大战都在本世纪爆发,人类心灵经过多么大的震撼和挖掘,其禀能从来没有像现代人这么深刻、复杂。“一天胜过二十年”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席卷五洲,物质影响精神,在人类智慧的精确与无穷这双重领域中,开阔的活动空间容纳着多种多样的自由创造。古来愤世嫉俗的圣贤,往往过早地预言一切都将终结或断定某个天才达到顶峰。现代人的实践与以往预言相左。在新的世纪里,诗与艺术的发展逐步披露着无穷的可能性。诗性智慧和审美需求的丰富,已无法用过去“尽善尽美”的典范来削正或放逐,而把在动态结构中寻找恒态结构作为普遍的追求。或许,每一朵花只是片刻的放射,每一瓣也将化入泥土而腐朽。但世界正是拥有灿烂的落英,那瞬间的存在屹立为美的永恒——智慧遵循着运动的规律,如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一样。
在现代人心目中,“诗性的王国”离我们既遥远而又亲近。所谓遥远,是诗学告诉人们这里始终是起点与此岸,而不是彼岸与归宿;所谓亲近,是诗人作为人类的良知,便是对众生的认同,体现在过程中,必然以心态外投的方式实行对社会、自然和现实世界的照察,自为与他为以同构的关系,运行在人生轨迹上。
诗性智慧一旦获得充分的自由,就能处于最佳状态。这种自由往往是审美判断的意志自由。审美判断力一般都介于理解与欲念之间,“理解——判断——取舍(选择)”是思维也是诗性智慧的动态模式。如果欲念先入为主以至造成审美判断力的失控,那么智慧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因为它造成身不由己,不得独立自主。但意志坚定的智者以及心魂解放的精灵,不会失去审美判断力的自由,而是努力去保持它和使用它——这使我们感到在现今尘世,作为有思想有诗情的人是何等幸福。
在本世纪乃至未来的世纪,现代人的这种幸福同样必然以智慧的痛苦为代价。在现代,诗人们似乎更沉重地背负着人类痛苦的十字架艰难地走向每一个黎明。人类和大自然、和命运的抗争,种种社会分裂和内心矛盾,使情绪从愤怒、自我折磨进到苦思、自我剖析的深化,也使诗性从感受丰富的痛苦,进至追求用更智慧的言语去照明世界。中国一位现代诗人就这样抒唱一颗颗受折磨而有韧性的诗心:
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
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
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穆旦:《智慧之歌》
这是严肃思考着智慧人生的诗人,对于生命与理性的限度、对于历史与现状的痛苦的解悟,以自谑与嘲世来表达内心的矛盾而不失向往与信念。浑浑噩噩的人自然不会有这种痛苦。对于寻求新知、不断求索的现代人,这种痛苦成了他们迎接时代挑战的一种震颤、一种焦灼、一种内驱力。
在现代,几乎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知识大爆炸”酿成的波浪,拍打着人们的激动也占有了人们无数个梦。一个人的智慧创造不出春天,千万人栽种的智慧树才告示山花烂漫。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固有的文化堤岸业经冲决,诗歌界“主义”纷呈,流派丛生,变得“越来越不像诗”了——这几乎是世界性的现象。然而,“变”中“不变”的是,诗性智慧总是只对心灵才开放,诗歌作为审美对象,既是一定时代社会的产儿,又是人性的多元心理结构的对应品,种种作品、潮流与倾向无不折射出特定社会时代不同人们的内在魂灵。不管当今诗坛有何其纷陈杂现的示意中心,作为繁富的审美创造的诗,作为有价值的情感之花与智慧之果的综合的诗,其性征总是使理性溶于感性、社会溶于个体、历史溶于心理,并将沿着马克思曾指出的诗性方向庄严地行进:“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8〕如果说,这种从“复现”到“直观”的智慧途径,经历了古典与近代诗学的解体,那末,其现代途径,也许是诗性社会学与审美心理学的溶合,是对当代现实生活的深层体验与对传统文化的开掘的交叉,是“全球意识”与一民族的“根意识”在宏观上互补,是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探寻中的多元艺术形式的均衡,是东西方智慧在面向未来时新的冲撞与汇通。过去的智慧之歌的确已经“歌唱完了”。诗一旦和人类面临的伟大斗争与辉煌前途结合在一起,气势磅礴的新文化交响乐还会奏出。我们怀有这样的热望与信心。
(收稿日期:1997年4月28日)
注释:
〔1〕维柯:《新科学》中译本(朱光潜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162页。
〔2〕尼采:《悲剧的诞生》(李长俊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3〕宍:古“肉”字,这里指原始人所要猎取的食物。 此短歌相传作于黄帝时代。
〔4〕〔5〕参见Trask,1,第66、48页,取叶维廉译文。
〔6〕《梨俱吠陀》,印度古诗歌总集,人类最古的文献之一, 总收集梵诗1017首,约三千几百年前保存至今。前辈诗人兼学者金克木教授为这首《土地》作的阐释可资参考:“诗中的‘土地’和‘大地’不是一个词。‘大地’指整个的地,从词源说是‘宽广’一词的阴性,出于动词根‘展开’。印度人传统自古就喜欢追寻词形、词义加以想像;因此‘大地’是女人,而且‘宽广’(这词不好改译成汉语中习惯的描写女人的词‘丰腴’)。印度一般认为雨是从地上的水升上去的,看来《吠陀》时人好像已经观察到蒸气成云的现象。”见金克木著《比较文化论集》,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第34—35页。
〔7〕维柯:《新科学》,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页。
〔8〕雨果所说的“一切东西”, 是指“古典美”范畴之外而又真实存在于人世间的丑陋、滑稽、荒诞的事物。
〔9〕雨果:《〈克伦威尔〉序》,《雨果论文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
〔10〕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二幕。
〔11〕蒙田《随笔集》,《诺尔顿世界文学名著》第一卷,1979年版,第1362页。
〔12〕卢梭:《忏悔录》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第1—2页。
〔13〕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146—147页。
〔14〕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651页。
〔15〕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
〔16〕汤显祖:《王茗堂文之四·耳伯麻姑游诗序》。
〔17〕参见《袁中郎全集》卷三《叙小修诗》。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2卷,第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