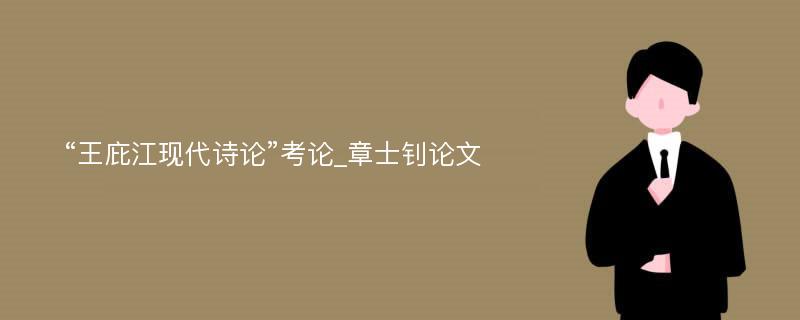
《汪辟疆说近代诗》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汪辟疆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3)03-0084-06
在近代或者说晚清诗歌的研究方面,“文化大革命”之初谢世的著名学者汪辟疆先生无疑是一位关注较早又多有成就的专家。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他的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专门汇编为《汪辟疆说近代诗》,收入该社的《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丛书,并于2001年12月出版。该书的主要部分依次为:《近代诗派与地域(附吴蔡小笺残本)》、《光宣诗坛点将录(合校本)》、《近代诗人小传稿》、《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等四种(下引篇名后括注均从略)。其中的第二种和第四种,笔者曾于1983年得到油印本各一册,分别列为《汪辟疆先生遗著》之一、之二,且同署“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整理”。如今读到这个汇编本,感觉比油印本确实要方便许多。不过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疑惑。现在就按照该书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将若干疑惑择要论列于次,或可为其他读者以及日后重新整理该书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关于黎简诗集。该书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中,曾两次提到黎简诗集,分别称《五百四峰草堂诗集》(第9页)和《五百四峰草堂诗钞》(第39页)。按黎简为清代中叶著名诗人,其诗集准确的书名叫做《五百四峰堂诗钞》。这里,“诗钞”偶称“诗集”还可以看成是一种习惯,但“草”字却显然是误加上去的。尽管前人有时也有《五百四峰草堂诗钞》这样的误称,但后人却不应该再以讹传讹。今此集已有梁守中先生校辑的排印本(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读者查找印证将不再困难。
(二)关于洪亮吉论诗绝句。《近代诗派与地域》在论述“岭南派”时,曾援引洪亮吉的论诗绝句进行阐发(第40页):
洪稚存诗云:“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今不逊江南。”虽指独漉堂而言,然雄直二字,岭南派诗人当之无愧也。[1](p.40)
又此“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今不逊江南”两句,稍后《光宣诗坛点将录》“天伤星行者武松 黄遵宪”条有关自注也曾引用一次(第83页),文字完全相同。按洪亮吉(稚存其字)该诗,原见其《更生斋诗》卷二《百日赐环集》,系《道中无事,偶作论诗截句二十首》之五,作于嘉庆五年庚申(1800),全文如下:
药亭独漉许相参,吟苦时同佛一龛。
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2](p.1244)
此诗所论,实际上是清初整个“岭南三大家”,包括梁佩兰(药亭其号)、陈恭尹(独漉其号)和屈大均共三位诗人,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王隼曾为之编纂《岭南三大家诗选》;惟屈大均在乾隆以后其著作曾遭到禁毁,所以这里没有点到他的名字。因此,汪辟疆先生以此诗“指独漉堂而言”,将它限定为陈恭尹一家,这恐怕并不符合原意。同时,在《岭南三大家诗选》问世稍前,顾有孝、赵沄曾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合辑《江左三大家诗钞》;洪亮吉此诗,意思就是以清初这两个“三大家”相比,认为“岭南犹似胜江南”(“江南”借指“江左”)。因此,汪辟疆先生所引,凭印象将此诗改动了几个字,这里的“古贤”与“昔贤”倒没有什么差别,但“犹似胜”换作“今不逊”,这个“今”字从远在其后的洪亮吉这里来说,总觉得也不是太合适。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刘德权先生点校的《洪亮吉集》(2001年10月第1版),有关作品查阅就更为方便了。
(三)关于方尔谦、方尔咸兄弟。该书《光宣诗坛点将录》“专管行刑刽子二员”,以方尔谦、方尔咸兄弟对应“地平星铁臂膊蔡福”、“地损星一枝花蔡庆”;其下杂记曾说:“地山,世所称为大方者也,己丑解元。”(第111页)但据近人徐沅等撰《清秘述闻再续》卷一记载,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恩科乡试,江南解元为“方尔咸,字泽山”。因此,这里称“大方”“地山”方尔谦为“己丑解元”,恐怕是将兄弟两人搅混了。
(四)关于顾印愚等。《光宣诗坛点将录》“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拟为顾印愚,同时,“一作沈尹默、赵世骏”(第113页)。按《水浒传》点将录,“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系“行文走檄调兵遣将一员”,但该书“行文走檄调兵遣将一员”下面仅有赞语两句和诗歌一首,已故程千帆先生(为汪辟疆先生弟子)按语曾指出“此首属顾所持”(顾印愚号所持);而“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 顾印愚 一作沈尹默、赵世骏”一行,则窜至同页稍后“考算钱粮支出纳入一员”“地会星神算子蒋敬 胡朝梁”的下面,结果同时造成了两处错误和混乱。此事在上文提到的油印本中,倒完全正确无误。
(五)关于释敬安生卒年。该书《近代诗人小传稿》“释敬安”条,正文称其于民国“二年”(1913)“以寺产事入京……归所主法源寺,一夕,愤懑而死”(享年未及),而名下括注生卒年为“一八五○——一九一二”(第133页),这里至少卒年自相抵牾。又此前《光宣诗坛点将录》“黄面佛黄文煜 释敬安”条自注,称于“民国元年”(1912)“冬,为中国佛教会事入都,不得请,愤恚圆寂,年六十三”(第120页),这尽管与该括注生卒年相合,但其本身叙述却相当模糊,究竟是卒于本年的冬天还是第二年,不易确定。而后面《光宣以来诗坛旁记》“八指头陀”条,援引近人郭则沄《寒碧簃琐谈》,则又称敬安(八指头陀其号)“年七十余,云游京师,怛化于法源寺”;汪辟疆先生于“云游京师”句曾加按语“按寄禅于民元以中国佛学会代表入京请愿,因维持全国寺产事”云云(第196页,敬安字寄禅),但对“年七十余”并无订正,如此则一书之内,歧异更加严重。好在敬安已有年谱、评传等多种翔实可靠的传记资料,其生卒时间十分具体,并且已经成为定论;今就便据今人梅季先生整理的《八指头陀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9月第1版)附录之三《八指头陀年表》以及附录之二所收冯毓孳撰《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天童寺方丈寄禅和尚行述》,即可确知其生于清咸丰元年辛亥十二月初三(公元1852年1月23日),卒于民国元年农历十月初二(公元1912年11月10日),享年以农历计为62岁。
(六)关于“宣南一老”句。《光宣以来诗坛旁记》“吴圭盦”条(第191-192页),记载有关吴观礼(字子俊,号圭盦)事,曾说:
仁和吴子俊与张篑斋皆同治辛未进士,同官翰林,陈弢庵则先一科。三人至相得……余早年在南昌,胡先骕示我《圭盦诗录》,为弢庵手写上雕……及乙丑夏秋间在都门,侍座弢庵,即从容询圭盦事。曰:“吴子俊与余及篑斋至契……诗稿甚多,而芟剔至严。死后,余从其夫人索得自定本,遂手录一册,即后此据以上木者也。今闻版已不存,印者亦稀矣。余诗宣南一老句,即指此。”[1](pp.191-192)
按此处“余诗宣南一老句,即指此”云云,是汪辟疆先生自述前面《光宣诗坛点将录》“地杰星丑郡马宣赞 张佩纶 一作吴观礼”条(第70-72页)所属论吴观礼的绝句二首之二,原文如下:
太息圭庵不假年,故人投老见诗篇。
宣南秋夜虫声急,一老灯前说往贤。[1](p.71)
这里,“宣南”、“一老”两句,意思就是自己“乙丑夏秋间在都门”,听陈宝琛(弢庵其号)叙说吴观礼“圭盦事”。因此,上引该段文字将“余诗宣南一老句,即指此”这句话放在引号之内,当作陈宝琛的结束语,这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的处理是,将最末半个引号移至“余诗”之前;同时,“宣南”和“一老”分别添加引号,这样则更为妥当。
事实上,《光宣诗坛点将录》该条论吴观礼的两首绝句,《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本条开头也已经完整引用,只是整理者并没有认真去理解。同样,本条开头还引用了《光宣诗坛点将录》该条所附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关于吴观礼的两首,但此处整理者却将两首绝句合并标点成一首诗歌,像是律诗却又乖律,这显然也是一个疏忽。
(七)关于章士钊《孤桐杂记》。《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桂伯华”条(第247-252页),后半曾录及章士钊《孤桐杂记》,其前先有汪辟疆先生的一段说明:
长沙章士钊曾示余所撰《孤桐杂记》,中有伯华遗札一通。其自为跋语中,亦有伯华逸闻。照录于此。[1](p.251)
此下共有三节文字。第一节系章士钊自述缘起:
江西彭君出桂伯华先生遗札求跋,览之不胜慨然。乙卯,余在东京最后晤伯华,伯华尚言将从习英文事。此事愚盖许之甚久,迄未践约。伯华客死东京已数年矣,思之不怿。至伯华湛深内典,余未获请益,尚不过伯华未度众生中之一生而已。札如下:[1](p.251)
第二节即“遗札”原文,可置不论;而第三节说:
作一序耳,何至身殉?此函述序之不能作处,至为曲折。有作此函之气力心思,序亦可为。凡此皆伯华拘执处。愚朋友中有两人负性特异,一杨笃生昌济,一桂伯华。伯华临死前一日尚有书抵余,为言已定一读书五十年之计划,甚觉得意。伯华求学英文,盖志在展转以学梵文耳。其衰惫不能学此,旁观至明,而彼抵死不悟。此二人也,愚皆有所负。而其方正不容一毫苟县处,以鄙性方之,愧无地也。[1](p.252)
这节文字从“遗札”内容一直说到桂念祖(伯华其字)的性格特点及其在日本东京与作者的交往,特别是“求学英文……展转以学梵文”之事,联系上引第一节章士钊自述缘起来看,这个作者恐怕还应该是章士钊;所谓“愚(皆)有所负”,当即“此事愚盖许之甚久,迄未践约”。又前面《光宣诗坛点将录》“地镇星小遮拦穆春 桂念祖 一作李翊灼”条所附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关于桂念祖的三首(第94页,程千帆先生按语误称“二首”),其一云:
江户经年德有邻,期期好我意难申。
莲花梵字无人识,惭愧才非苑舍人。[1](p.94)
自注说:“君在东京,欲从余学英文,借以径治经论。唐苑咸谙梵字,见右丞诗。”持此与上引第三节以及第一节并参,也能看出它们都出自章士钊之手。并且这两节文字,作者第一人称都是“余”、“愚”并用,这与汪辟疆先生本书自述统一用“余”字的习惯也明显不同。因此,现在本书将前面第一节和第二节用仿宋体缩行排版,属之章士钊,而将第三节用宋体字顶格排版,属之汪辟疆先生,这种处理恐怕不符合事实。检油印本《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该处第三节尽管转页,但还是看得出它与第一节相互对齐,同样都比第二节“遗札”原文高两格,而比汪辟疆先生文字低两格,这应该是准确可信的。只是章士钊的《孤桐杂记》笔者未获亲见,所以不能提出更直接的正面依据;至于反面,即使《孤桐杂记》中没有这节文字,那也有可能是章士钊后来删掉了——当然,如是原本则另当别论。
类似这样的问题,本书《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赛金花”条所录顾肇熙撰《吴县洪文卿侍郎墓志铭并序》(第176-179页),首尾两节已用仿宋体缩行排版,而中间一大段文字却仍用宋体字顶格排版,前后贯穿三个页码,这个做法显然也是不妥当的。而当初的油印本,此处却依然不误。不过尽管排版失误,好在这一大段文字读者还是很容易辨别出来,并不至于像上文所说章士钊的《孤桐杂记》那样,有可能导致误解。
(八)关于溥儒。《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溥心畬”条(第277-279页),介绍清末宗室溥儒的诗词创作与身世,开头说:
近三十年中,清室懿亲,以诗画词章有名于时者,莫如溥贝子儒。溥儒,字心畬,为□□□之子。[1](p.277)
这里所缺三个字,盖指溥儒父亲,但具体未详。曾见溥儒《寒玉堂诗集》(新世界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卷首有一篇节录的当代著名学者启功先生所撰《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第一节《心畬先生的家世》曾说:
溥心畬先生讳儒,是清代恭忠亲王奕之孙。亲王有二子,长子载澂,次子载滢,都封贝勒。载澂先卒,无子嗣。恭亲王卒时,以载滢长子溥伟继嗣,袭王爵。溥儒行二……
滢贝勒号清素主人,夫人是敬懿太妃的胞妹,是我先祖母的胞姐。我幼时先祖母已逝世,但两家还有往来。[3](p.5)
此后第二节《我受教于心畬先生的缘起》,启功先生还谈到他早年与溥儒的直接交往,因此,他的有关叙述自然十分清楚可信。按照这个叙述,则可知上文所缺的三个字,应该补为“滢贝勒”。
又该条曾摘录溥儒的若干诗词作品,其中“题画《北新水令》”一首如下:
西风疏柳带秋蝉,画桥边。绮霞红乱夕阳寒,照水衰草暮连天。何处里,笛声怨?[1](p.278)
按此首亦见上及《寒玉堂诗集》所包含的《凝碧余音词》,文字仅“何处里”的“里”字作“羌”,但标点符号却没有一个相同,兹照录于次:
西风疏柳带秋蝉。画桥边,绮霞红乱。夕阳寒照水,衰草暮连天,何处羌笛声怨。[3](p.97)
两相比较,别的不论,这“夕阳寒照水,衰草暮连天”两句构成一组工整的对仗,却无疑十分正确。尽管《北新水令》原来属于散曲,其变调形式很多,但这个位置的两个五字句对仗,至少在元人散曲中就屡见不鲜;特别是在溥儒作品中,更明显都是这样处理的。现将《凝碧余音词》此题后面的另一首《北新水令·探梅》一并转录于此,便可提供印证:
微香红破小梅梢,又东风早春初到。鸟啼芳树苑,人倚绿杨桥。浑不似故乡好。[3](p.115)
最后说说本书中普通文字方面的刊误,几乎也多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即以人名字号之类而论,例如“陈子龙”作“陈了龙”(第3页,“了”字误),“黄梨洲”作“黄黎洲”(第4页,两处,“黎”字误),赵执信“字伸符”作“字仲符”(第5页,“仲”字误),“蕴端”作“蕴瑞”(第57页,“瑞”字误),“左宗棠”作“左宗堂”(第126页,“堂”字误),张荫桓“百石斋”作“白石斋”(第160页,“白”字误),邓汉仪字“孝威”作“孝咸”(第215页,“咸”字误),潘博“原名之博”作“原名又博”(第264页,“又”字误),“刘慎诒”作“刘诒慎”(第265页,两字误倒),方尔谦字“地山”作“地上”(第268页,“上”字误),朱彝尊号“竹垞”作“竹坨”(第285页,“坨”字误),以及“程恩泽”作“程春泽”(代序第12页,程恩泽号春海)等等,对于本来就不太熟悉而希望通过本书获取知识的读者来说,无疑会造成更多的误导。其他一般文字,错误频率最高的大概是诗歌的“诗”印成“时”,全书前后不知道出现过多少次;特别是像《光宣诗坛点将录》“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张之洞”条评语所谓“广雅尚书时,才力雄厚,士为精妍”一句(第62页,张之洞别号广雅),读起来根本没法懂,后检油印本才知道,“时”原作“诗”,“为”原作“马”。而这许多文字错误,除了极个别系作者当初偶然笔误以外,绝大多数恰恰都是本书在印刷过程中首次产生的,这只要稍稍对照一下油印本就可以得出结论。
《汪辟疆说近代诗》全书规模不大,但有关疑惑却远远不止这些。如前所述,该书是作者多种相关研究成果的汇编,它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了集中阅读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为人们提供了相互校勘的条件。上文叙述的若干问题,有些就是从这种横向比较中得以发现并解决的。而从纵向的角度来看,该书中如《光宣诗坛点将录》,民国年间曾经在不同的杂志上发表过两次,1983年又出过程千帆先生整理的油印“合校本”(卷末原有程千帆先生该年8月25日所写的一篇《后记》),稍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收入《汪辟疆文集》正式出版(1988年12月第1版),到如今再编进本书,前后至少已有五个版本。照常理说,目前这个最后的版本经过几代著名学者之手,在质量上应该是最好的。然而事实上,其中非但不少原有的问题一直保留至今,而且还另外出现了大量印刷排版过程中形成的错误;虽然《汪辟疆文集》笔者未做比较,但很明显不如二十年前的油印本。本来以为有了该书,原先的油印本都可以废弃,现在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大抵同一种书,重版越多,错误也随之越多。
[收稿日期]2002-0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