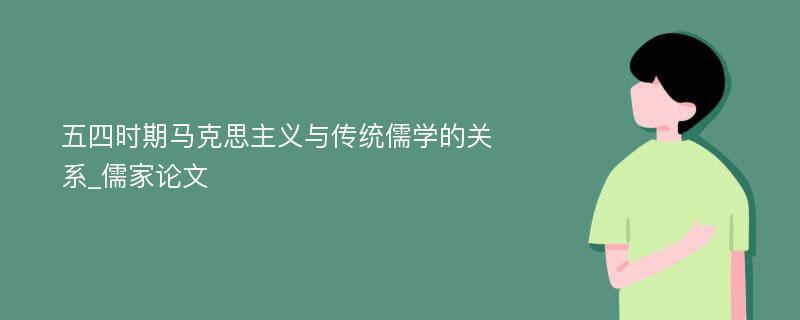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时期论文,关系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的近代化是在中西文化撞击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文化采借、重组、交汇、再造的过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五四”时期发生了重新估定中西文化价值的东西文化论战,中西文化的冲撞和交汇形成了近代以来的高潮。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惨祸和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中国的先进者既想撷取容纳外来的近代文化,以适应和追赶世界潮流,又想保存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重振和弘扬民族精神。
十月革命的炮声,使急于寻求出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说:“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作为“第三种新文明”崛起的“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注:《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0页。)。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最初是把它当作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其知识结构、思维框架、理论水平仍不免受到传统思想文化的制约,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在其中发挥着潜在的作用,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国的传统方式介绍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因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的某些思想出现了相容、相通和相融。
首先,中国先进者以儒家“求善”、“均平”的道德价值观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以社会主义为前途探索社会改造问题,使传统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一种相容的关系。
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特点在于以“求善”为目标的道德本位主义,即侧重道德标准对社会进行认识和批判,其社会理想为道德社会。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面临的深刻危机和价值取向的急速转换,使马克思主义与儒家道德本位主义价值观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中产生了某种相容状态。中国先进者一面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揭示资本主义从兴盛走向崩毁的经济运动规律;一面以儒家追求道德社会的传统价值尺度对其进行道德批判,阐发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伦理进化法则。李大钊认为,人类进化的基础“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所谓“家族精神”,正是儒家道德本位主义伦理观念的基础。他断言:“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要“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注:《李大钊文集》(下),第43页。)。
儒家从道德本位主义出发,以“均平”为价值观,需求平均享有一切社会财富。“均平”观念经过两千余年传承,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心态。中国先进者最初也是以传统的“均平”观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如李达说:“资本家借了金钱和势力,压抑劳动者的辣手段,真是惨无人道咧!结果弄到贫者愈贫(这是劳动者),富者愈富(这是资本家),贫富相差愈远”。“社会上受了这不平等的刺激,自然会生出近世的社会主义来了”。“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注:鹤(即李达):《社会主义的目的》,1919年6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传统儒学讨论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重心显然不在于如何提高生产力和增加社会财富,而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中国先进者论述社会主义,首先关注的也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而是其道德目标:共同富裕和平等原则。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还吸收了儒家注重通过道德规范的践履和伦理教育的感化改造社会的思想。最初,马克思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面貌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唯物史观也一度被认作只是“历史之经济的解释”而称为“经济的历史观”(注:《李大钊文集》(下),第359页。)。因此他们认为,除了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进行社会经济组织的改造之外,还应注重人类精神的改造。李大钊说:“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注:《李大钊文集》(下),第18~19页。)在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注:《李大钊文集》(下),第68页。)。这表达了希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与儒家的仁爱互助思想构成互补的愿望。
其次,中国先进者以儒家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诠释和描述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使传统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上形成一种相通的关系。
中国传统儒学有一种悠久的社会理想,即《礼记·礼运》篇勾勒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蓝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构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体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让社会的生产、财富、权力、制度乃至社会的一切领域都全面地达到公正、合理、平等的原则,使人类最终实现自身解放的理想,也正是千百年来人类普遍追求的理想社会的基本框架的基本原则。人们惊奇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竟似曾相识。他们自信两千多年前《礼运》篇中关于大同世界的描写,“确可以代表社会主义底神髓”(注:邵力子:《东荪君底〈又一教训〉》,《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如蔡元培说:“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礼运记孔子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孟子记许行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餮飧而治。’就是‘泛劳动’主义。”(注:蔡元培;《社会主义史序》,《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1920年7月23日。)
儒家描绘的大同世界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激励了历代的有识之士为美好理想而奋斗。中国先进者从对大同世界与社会主义的联相中,再一次树立起了改变中国现状和建设中国未来理想的信念。1919年9月,李大钊疾呼:“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号召人们“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使“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农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义的信徒”,“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注:《李大钊文集》(下),第44页。)。青年毛泽东也接受和相信过儒家的大同世界,他曾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注: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又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大同思想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因而把社会主义理想理解为“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这种带有儒家色彩的政治理想,尽管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然而,理想既是目标,又是向导,它具有强大的社会吸引力。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想追求,正因为近代中国灾难深重,就更需要树立一个远大的奋斗目标,以激励民族的精神。中国先进者正是从传统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的联想中,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美妙的未来,从而树立起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信念和信仰。
儒家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思有一定的吻合之处,而实现理想社会的前途却大相径庭。儒家着眼于未来社会蓝图的描绘而脱离现实,使大同世界始终只是一种虚无飘渺的空想。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践唯物主义”,着眼于现有社会的改造而提出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到达共产主义。因此,中国先进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只是倾心于它所预示的美好憧憬,更重要的还认识到了无产阶级自身的历史地位和力量。1917年毛泽东说:实现大同之法,是从哲学,伦理学入手。1921年,他表示确信“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基础”(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并且“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蔡和森也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在于取消阶级,“不能取消阶级,则世界永不能和平大同”(注: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1921年8月1日。)。他们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大同的有效方法,第一次把大同社会原则置于现实的基础上,正因为有此思想,传统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才会形成一种相通性,马克思主义才会赢得更多的拥护者。
第三,中国先进者以儒家“明道救世”、“兼善天下”的处世态度,仿效马克思为实现理想献身治学的人格品质,与马克思主义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上形成一种相融的关系。
中国传统儒学主张积极入世,具有“兼善天下”的进取精神,倡导“明道救世”,以天下为己任。儒家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治学之道的影响至深。这种精神体现在政治上,是“为学”不离“求治”;体现在学术上,是“经世致用”;体现在文学上,是贯穿古今的“文以载道”思想。马克思一生追求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和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崇敬和仰慕。如1919年,渊泉说:“吾今日介绍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实有两大用意”:一欲引起诸君“研究社会主义之兴味”;二欲使诸君“知古来贤哲学身术学之生涯。”又说:“马氏之奋斗生涯即献身著述之生涯”,他的《资本论》是“不朽”的“空前绝后”的名著,《共产党宣言》则是“历史上学问上最有价值”的著作,“吾侪深信马氏之学说,乃现代万恶社会之唯一疗法也”(注:渊泉:《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1919年4月1日—4日《晨报》。)。中国先进者积极介绍马克思生平和马克思主义,也正是为了“明道救世”。
为了追求“道”,传统儒学要求知识分子应具有崇高的精神修养和人格力量,并且从“内圣”与“外王”两个方面阐述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内圣”指个人内在德性修养上的造诣,“外王”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事功与作用。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正是儒家对个人修养与发挥社会作用的联系所作的说明。“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格外仰慕马克思的人格品质和人格修养。渊泉说:“马氏著作《资本论》第一卷之七年间,生活极为悲惨。吾侪今日读之,犹不禁拍案太息彼苍之不仁也”。又说:“孟子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马氏大著作,实成就于此种境遇之中,此殆天所以造就马氏者欤!”(注:1919年4月1—4日《晨报》。)从传统的理想人格观看来,马克思“其坚忍不拔之决心,献身救世之精神”,无疑已达到人们崇尚和追求的极高境界。这种理想人格以完美的形态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对先进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产生了巨大的精神感召力。
“五四”前后,先进的知识分子都非常注重人格的精神修养。毛泽东仰慕“圣人通达天地,明贯现在过去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无不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为此潜心研究过古人关于心物、圣贤修身、治乱的大道理。周恩来则把人格的确定提到人类进化基础的高度:“茫茫天壤,莽莽大地,所以得生存于世界,而向全盛之境,大同之世以共趋者,岂非恃此一线之人格耶!”(注:《敬业》,第5期,1916年10月。)对理想人格的崇尚和追求,对于这一代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道路,不唯不构成障碍,反倒可以视为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驱动力。渊泉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其坚忍不拔之决心,献身救世之精神,吾侪于数十年后读之,犹跃跃纸上。我亲爱之青年诸君,阅此当知所以自奋矣。”(注:1919年4月1日—4日《晨报》。)1922年5月5日出版的《马克思纪念册》载文说,马克思不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大思想家,而且是一个社会改造之实际运动的战士。文章号召人们学习马克思发现的独特的剩余价值说、唯物的历史观、阶级斗争和劳工专政的学说,学习马克思“苦战奋斗的精神和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这表达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立志以马克思为其理想楷模,为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献身的决心。
二
中国先进者以传统儒学的某些观念和语言去诠释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容易使中国人产生亲切感,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地传播开来。同时,由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的不足,以及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清除的不够,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曲解,甚至将马克思主义降低到中国传统儒学的水平上。但这种状况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学习与探索,他们逐渐正确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的关系。
首先,中国先进者明确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无论其时代内容还是其思想体系,都存在着根本的差别。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近代大工业基础之上和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科学理论,传统儒学主要反映了封建宗法社会和小农经济的思想观念。1920年,李大钊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对传统儒学的思想体系展开批判。他指出:孔子思想代表专制社会的道德,之所以长期支配中国社会,“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中国进入近代,农业经济发生动摇,导致大家族制度的崩颓,“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中国今日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都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打破孔子主义的运动”(注:《李大钊文集》(下),第179~182页。)。
当时出现的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认为,只有东方传统文化可以挽救西方文化的颓运,主张把中国人和西洋人导向“至美至好的孔子路上来”。翟秋白反驳说,东方文化是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的宗法社会的文化:一是宗法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农家手工业、农业的土地制度等;二是畸形的封建制度的政治形式,一盘散沙之上的中央政府、世家、官僚、疆吏、地方官等形成的似诸侯而非诸侯的地方统治制度;三是封建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如伦常纲纪和孝悌礼教思想。在当今剧烈变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潮流中,宗法社会的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代之而起的只能是“通过世界革命走建设世界新文化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的文明”。显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是马克思主义被传统的儒家思想融合和同化,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武器和批判力量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儒学的统治地位,使中国文化的主流和态势发生了突变,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了。
其次,中国先进者明确界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均平”观存在着根本的差别。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传统儒学的均平主义则是植根于小生产的基础上并以平均分配社会财富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主义。1919年,李达最初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就是救济经济上不平均的主义”(注:鹤(即李达):《社会主义的目的》,1919年6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5月,他则从理论上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与古代“均平”思想的不同之处。他说:“共产党底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就是主张一切生产及交换工具都归公有,不许私人把财产用做生产或交换工具来增加他的私有财产;却不是‘平均财富’这类浅陋的主张,也不是‘彼此通财’那样普通的习惯。”(注:《〈共产党〉第四号短言》,《共产党》第4号,1921年5月7日。)陈独秀也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其宗旨固然也是救济无产阶级底苦恼”,但不是“简单的均富论”,而是“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这样“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注: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1921年7月1日。)。
再次,中国先进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道德理想主义存在着根本的差别。
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传统儒学道德本位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则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的空想伦理主义。陈独秀论述道:“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建设在伦理上面”,而“不曾建设在社会底经济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中得出来的必然结论,因而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空想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注:《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1921年7月1日。)。施存统也指出:“把‘共产主义的社会’当做理想来描写的思想家,在马克思以前,也很多很多。可是他们都只能在他们底头脑中描写那个理想,至于可以实现那个理想的‘物质的基础’却都不能发见,所以他们都只做一个空想家就完了。”(注:施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1921年8月14日。)施存统进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平等观。他说:“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以为自由平等是绝对的真理,现在的社会不自由不平等,所以非改造不可。”马克思却认为,“要建设自由平等的社会,必须先打破资本家社会。这样一来,无力的社会主义,就变成有力的社会主义了;空空洞洞无根据的自由平等,就变成实实在在有根据的自由平等了;抽象的理论,也变成具体的事实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马克斯底功劳”(注:光亮:《马克斯主义底特色》,《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9月23日。)。
最后,中国先进者还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存在着民族性的差别。
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里发育成长起来的。尽管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它与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结合。为此,李大钊一面激烈批判孔孟封建伦理道德,一面提出了仔细寻找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珍品,发扬光大“孔子固有之精华”(注:《李大钊文集》(上),第246页。)。陈独秀也说:“近世学术,竞尚比较的研究法,以求取精用宏”,“所谓‘取长补短’,即是此义。吾人生于20世纪之世界,取20世纪之学说思想文化,对于数千年前之孔教,施以比较的批评,以求真理之发见,学术之扩张。”(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页。)瞿秋白说:“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辅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已“开辟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注:《赤都心史》。)。
总之,从1920年至1921年间,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先进分子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传统儒学思想体系中的专制主义、均平主义、道德空想主义观念进行了批判,进一步推进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早期共产主义先进分子又强调发掘中国文化优良传统和中西文化结合重构中国新文化,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建设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文化打开了思路。
标签:儒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社会主义道德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李大钊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