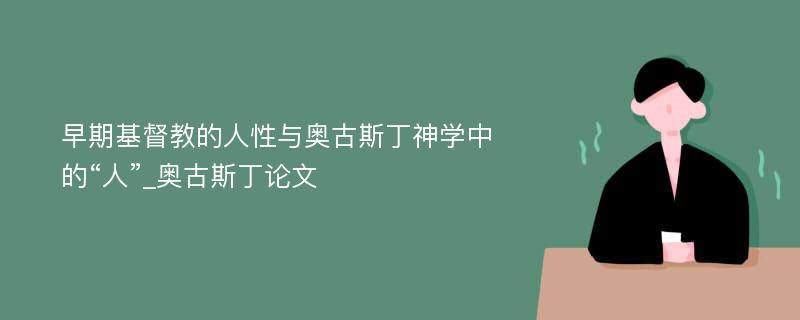
早期基督教的人性与奥古斯丁神学中的“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古斯丁论文,基督教论文,神学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世纪西欧的思想领域里,基督教神学无疑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既然人不过是实现神学目的的手段,人学就无法脱离神学而单独存在,人性也只好依附于神性。但是由于神学既要处理人、神关系,又要关注人的终极幸福问题,因此神学便不得不包容人学的一些基本原则;虽然新约的福音书和保罗书信倾向于把人们的期盼从现世引向来世,但旧约毕竟已经把现实世界及生活其间的人列入了上帝伟大创造的主体工程之列,因此对于古代及中世纪的神学家来说,关心作为社会组成要素的人,与关心作为宗教信徒的人,便具有了同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从早期基督教神学、尤其是长期被钦定为教会正统思想的奥古斯丁神学中找出西方人学理论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某些历史联系。
一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独立的“人学”的确是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才开始的。不过,在谈到文艺复兴中所涌现出来的人文主义思潮时,人们不是刻意强调它创新的一面,就是把它与希腊罗马的古典学术直接联系起来,而对隐含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中的人学理论在其间的承接作用则不屑一顾,这种态度看来并不可取。实际上,希腊罗马的古典学术传统和精神——自然包括对于人自身的理解——不是由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直接加以继承的,古代及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在其间所进行的诠释、附会和递传等工作,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阶段;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一开始就直接钻进希腊罗马的故纸堆里,他们大多是首先从早期教父的神学著作中窥见理性之光的;而后期的许多人文主义作家更因与圣经诠释及教理阐发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被称作“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瓦尔特·乌尔曼教授曾以其独到的眼光注意到了这一关系,他认为:学术界中再没有比中世纪及文艺复兴的学者更加忽视“人的再生”是如何孕育于中世纪当中的了,其实人们只要从基督教的“洗礼”中就能看出中世纪的信仰是十分重视人的价值的,因为人们正是经过宗教洗礼期盼做一个“再生之人”的”。(注:Walter Ullmann: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Renaissance,See Andre Chastel & Cecil Grayson:The Renaissance——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Methuen & .Co:Ltd,1982,p34.)
作为一种一元论宗教,基督教首先要处理的关系自然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新约所塑造的基督这一角色我们可以看出该宗教对于神人关系的基本理解。《约翰福音》直接把基督说成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基督的种种行迹显示出他具有神与人的双重属性,其中作为人的证明的是:他的降临是通过凡间母体自然怀胎分娩而成,他与凡人一样生活和受苦,也像凡人那样死去;而作为其神性的证明则包括:他是在其母体未被交媾玷污的情况下成孕的,他在传道时施行了各种各样的奇迹,以及他的死而复活和升天等等。从神学的意义上讲,由于上帝无法为世人所认识,他必须通过具有人性的耶稣(即道成肉身的上帝)来接近世人,而为了避免混同于凡人,他又不得不通过一系列表明其神性的证据来坚定世人的信仰。通过基督的人性,人类找到了为自身赎还罪责的替罪羊,从而体现了上帝的至公至正(根据“有债还债、有罪赎罪”的原则);通过他的神性,人类则获得了神恩的无限宽宥,从而体现了上帝的至仁至慈。因此,这个具有神与人双重属性的基督便成为上帝与世人之间的中保,他是两者进行和解的象征。从社会伦理的意义上讲,基督教通过基督在人间的行迹为世人树起了一个道德楷模:谦卑(耶稣的贫寒出身)、勤勉和坚毅(在传道过程中的坚持不懈)、仁慈和无私的爱(医治病残者和救济饥寒者)、守贞(终身不娶)以及宽容、服从和忍耐(宽恕出卖者及从容受难)。(注:参看新约福音书的有关内容。)不过,道德理想毕竟只是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基督教在涉及到人类事务时必然与其他的信仰体系那样要面临种种令人困惑的问题,如:与人发生关系的这个世界(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的真正面目如何?人在这个世界中处于何种地位?人从何而来并归于何处?人的本性是什么?等等。基督教神学对于这类问题的解答是从诠释和阐发圣经的意义开始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圣经(尤其是旧约)各卷甚至各章节间常常存在着自相矛盾甚至相互排斥的现象,这既为各式各样“异端邪说”的频频出现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为历代正统的诠释家留下了极大的自由发挥余地——就此而言,我们通常所说的天主教“正统”(Orthodoxy),便具有很大的相对性和弹性。在一般情况下,教会当局根据功利主义的目的及实际的需要,在裁定各种理论纷争时对某个神学权威的学说作原则性认可,而把与之相悖的学说和思想贬为“异端”(Heresy)或“旁门”(Heterodoxy),但这并不意味着被确定为正统的神学理论的每一项具体内容都必须与教会的意图相一致,实际上,权威神学家的学说常常与教会的利益相左, (注: Jaroslav Pelika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4 )Reformation of Church and Dogma(1300-1700),The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1984,pp 14-22.)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官员就会及时地对神学理论作必要的变通以达到妥协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来,天主教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宽容性和灵活性——正是这种宽容和灵活,使古典的人学理论得以有效地保存下来,并通过一种普世信仰的形式得到进一步的阐发和伸张。
基督教的世界观比较接近人类现实的认识水平,它不像佛教那样把认识领域从现存世界延伸到“三千大千世界”和“六道轮回”,而只是专注于对人所能观察和感悟到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今世与来世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在上帝的受造物中,人大致处于中等的阶位。神学家们在诠释旧约中有关上帝的创造时,明显应用了古希腊的分类传统,从自然功能的意义上把受造物分成五类:不生者(天地山川河流等)、生者(草木)、觉者(禽兽)、灵者(人)及神者(天使),人除了与草木一样拥有生命力,与禽兽一样拥有趋利避害的直觉本能,还拥有这些物类所不具备的推理的能力——亦即灵魂,这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类的根本性标志;在时间概念上,天地、草木、禽兽及人的驱体,是属于有始有终的造物,人的灵魂与天使则同属于有始无终的造物,一切受造物既然由造物主按先后等级顺序创造出来,那它们也必然由低到高向上倚属,各以高一等的种类为实现自身存在的目的,而无始无终的造物主则是最终和最高的目的。(注:见孟儒望《天学略义》,载《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二),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850-855页;又见利类思《不得已辩》,载《天主教东传文献》,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 250-251页。)人的这种自然阶位无疑是基督教人学理论的起点。 在人的社会伦理意义方面,正统神学认定:《旧约》通过上帝的创造提出了一种人、神和平共处的道德理想,随后又通过人的堕落揭示了人、神对立的严酷现实;而《新约》则通过一种神学目的论来解决《旧约》所提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即上帝的创造是依据一个预定目的进行的,上帝在创造人类时,曾经赋予人在从善和作恶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意志,人类的堕落,是他选择了恶的结果,人类为了获救,必须重新作出选择,去恶从善,这一过程则需通过上帝的拯救计划来完成,于是才有了道成肉身的基督的死难和复活,从而在人类与上帝之间搭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当人类洗清罪孽、重新回到上帝的身边时,人类便分享了上帝的至善,上帝也便最终实现了其预定的目的。在这里,世俗的伦理被巧妙地融入了宗教教理之中,对于现实社会规范的遵从与对于上帝的忠诚不二获得了统一。这些信条就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后来的新教)千古不易的“真理”,一切基督教派别之所以被认同为一个同一的信仰,正是基于对这些信条的确认之上。既然在上帝的诸多受造物中,人被赋予了一个中间的阶位,那么从自然意义上说,作为灵与肉的结合体而存在的人,便具有了天生的两面性——它介于神灵与物质之间,是神中的最低者和物中的最高者;与此相应,从社会伦理的意义上看,既然一方面人因堕落而造就了与神相对立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因上帝的拯救而复归于神的期盼,这就给人提供了选择弃恶从善抑或拒善作恶的自由空间。这种自由空间在上帝的创造中就已呈现出来,《创世记》第1章第26和27节提到上帝是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而在第3章第23节中则提到上帝用以造人的质料是泥土。神学家们大多以象征主义的手法去阐发旧约中这一有关人的最初起源的表述:由于基督教正统认定作为无始无终、无大无小、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造物主是没有形状的,因此有关依上帝的“形象”所造之人,就被解释为是上帝按自身本体创造的灵魂之人,而不是指肉体的人或人的外形,在这方面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解是一致的。(注: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2页;托马斯·阿奎那《反异教大全》, 转引自《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7页。)上帝依自身形象造人,寓意为人有从善的天性;人是用泥土为质料制成的,则预示着人有悖理作恶的趋势。这是否就意味着天主教神学主张人具有善与恶两重属性呢?如果作出如此结论,那么我们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基督教的一元论思想,并在实际上把基督教的世界观混同于本属势不两立的摩尼教教义。我们也不能以中国传统的世俗儒学的思维习惯为标尺去衡量基督教的思想,因为在基督教那里,人性并没有单独被从神性及自然属性当中剥离出来而成为一个只具有世俗伦理意义的概念,如果有人完全撇开信仰的或自然的定义去提出这样的问题:人在本质上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那么天主教神学家会认为这问题本身就是完全不切题的。在他们看来,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两码事;就其自然的方面而言,人的本性就在于他具有灵魂,因为在造物主的所有受造物中,人由于被赋予了灵魂才得以从根本上与其他的受造物区别开来。从这一角度看来,作为人之本质而存在的灵魂,并没有被直接赋予善或恶的价值判断,它不过是其自然属性的体现,这与一开始便把人性与社会性联系起来的中国传统思想的确有分歧——此点因已有行家作过详尽的剖析,(注:参看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四章。)故不赘述。我们感兴趣的是:当人性被从自然方面转向社会方面的时候,基督教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在教会思想家看来,既然人不过是上帝的受造物,他在社会伦理的意义上就不可能有脱离上帝这一最终本体而单独存在的属性;由于上帝本质上就是至善,模仿上帝的形象而制成的人分享着上帝的至善,(注:见《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07;21-22、43、45、68、114、116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性可以说是属于善,但这里是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的,即人首先必须向往上帝。所以确切地说,善应被看作是人的一种潜能,而不应是本性。既然作为上帝至善这一整体分流出来、并作为部分而存在的人类之善尚且不能体现人的本性,作为善的对立面的恶,便更加不可能是人之本性,这是显而易见的:至善的上帝怎么会制造出一个对立面并让自己的受造物来分享它呢?如果人性真是邪恶的和不可救药的,那上帝的拯救计划不是变得毫无意义吗?也许有人会以“始祖的堕落”作为反证。的确,奥古斯丁是通过对于《创世记》及《罗马人书》等的诠释演绎出了“原罪”的理论,但只要我们仔细推敲一下《忏悔录》中的有关内容,就会发现奥氏只用“原罪”来表明人的弱点,而并没有用它来证明人的本性就是邪恶。在他看来,肉体及其行为是受灵魂命令的,而灵魂在命令自己时却抗拒不服,这是因为命令者是在不愿意的情况下发出命令的,这种情况叫“意志的游移”,是由“灵魂的病态”引起的。(注: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52-153页。)在奥古斯丁的心目中,不管是“灵魂的病态”,还是由其引发的“意志的游移”,都仅仅是人违背上帝意志的结果,而不是人性本身。托马斯·阿奎那虽然把灵魂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但他也认为理性既可为情欲所败坏,也可因向往上帝而获得与天使同等的地位。(注:见《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07;21-22、43、45、68、114、116页。)显然此论在人的社会性方面并不与奥氏观点相悖。
基督教之所以没能像中国传统思想那样就人性问题作出一个直截了当的价值判断,其直接的根源就存在于中世纪西欧宗教生活至高无上的现实中。在一个以上帝的信仰为依归的宗教社会里,既然一切本属世俗的知识都被包容进基督教神学的范畴以内,纯世俗的人性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就难怪当著名的基督教耶稣会士利玛窦于1599年在南京名流李汝祯家中看到中国士人为人性善恶问题争论不休时感到大惑不解。(注:见《利玛窦全集(4)·利玛窦书信集〈下〉》,台湾辅仁光启1986 年版,第311-317页。)因为,对于一名正统的基督教徒来说,离开上帝的创造目的和拯救计划是谈不上人的本性的,上帝如同光源,人只有借助上帝的光才能感受明亮的喜悦,当人归趋上帝时,他见到的是白昼的光明,这就达到了美与善;而当人背离上帝时,他见到的是黑夜的昏暗,这便陷入了丑与恶。
然而,透过中世纪的宗教黑幕,我们仍能隐约看到古典人性的灵光在闪烁。其实,这种一元论的信仰体系不仅部分保存了希腊罗马人的遗产,而且终究造就了比希腊罗马人更有生气的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基督教没能在人性问题上作出专横的价值判断,而是把它与神的自由意志联系一起,这一方面表明了古典传统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又给作为个体的人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和余地:既然作为世俗社会的人是无法加以定性的,那么只要最终能达到上帝的善,走什么路才能达到目的就是信徒自行决定的事情了。
二
众所周知,肇始于14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潮以及更晚些时候才出现的“新教革命”,一开始都并不是以外部敌对势力的面目出现在正统神学及教会当局面前,而是作为这种正统思想中的一个变弃的分子从其内部孕育成长并最终分裂出来的,这意味着教会的正统思想就是产生自身对立面的母体。虽然天主教正统神学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奥古斯丁体系与托马斯体系之别,但在很大的程度上后者是前者的直接继承物而不是对立物,何况最初的人学理论与貌似冷酷无情的奥古斯丁神学之间有着更多的亲缘关系,因此我们对于西方“人学”思潮的历史渊源的追溯,便不得不从奥古斯丁的神学开始。
与偏爱亚里士多德理论和较为关注人的社会性的托马斯的“自然神学”体系不同,奥古斯丁体系由于偏重于信徒的个人感受而被称作“体验神学”。奥氏本人接受柏拉图、西塞罗及斯多噶学派等道德学家的影响较多,他心目中的“人”主要是个体的、精神性的和注重内修的。奥古斯丁在阐发圣经的过程中,就人的社会伦理意义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认为人的意志具有两面性。奥氏是通过驳斥摩尼教二元论信仰提出该思想的,他认为摩尼教的所谓“两种本体”和“两个灵魂”实则为一个本体或一个灵魂之下的“双重意志”:一个向善的意志和一个向恶的意志,这两重意志都归一个单一的灵魂指挥。(注: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52-155页。)奥古斯丁从自身由摩尼教信仰向基督教信仰转变过程中的痛苦感受出发,最终认定一个人的内心苦闷本质上就是他的“双重意志”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体现了上帝对人类罪过的惩罚,他说:“我和我自己斗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这分裂的形成,我并不情愿;这并不证明另一个灵魂的存在,只说明我所受的惩罚。”(注: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54页。)由于从灵魂中分裂出来的双重意志各有所向,才造成了心灵的痛苦:“永远的真福在上提携我们,而尘世的享受在下控引我们,一个灵魂具有二者的爱好,但二者都不能占有整个意志,因此灵魂被重大的忧苦所割裂:真理使它更爱前者,而习惯又使它舍不下后者。”(注: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55页。 )使我们感兴趣的倒不是由“双重意志”的斗争所引起的内心痛苦的体验,而在于由这种相互对立的“双重意志”所构成、并作为单一的整体而出现的人类录魂本身。实际上,奥氏并不因赋予“双重意志”以截然相反的社会伦理意义而完全否定向恶的意志的合理存在,他没有要求一个现实之人应当彻底摈弃向恶的意志而使灵魂拥有单一的意志,在他看来,只要承认肉体为构成现实之人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以肉体为象征的向恶的意志便永远与向善的意志形影相随,因此他说:“……可见我们有双重意志,双方都不完整,一个有余,则一个不足。”(注: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53页。)从另一方面来说, 既然由“双重意志”的斗争所引起的痛苦体现了上帝的惩罚,这种惩罚的过程同时就是人类赎罪的过程,尽管上帝的惩罚终究会以人类赎清了罪过而告结,人的灵魂终要彻底摆脱肉体的束缚、成为真正单一的向善意志获得完全自由,但现实之人存在的意义毕竟不在于赎罪的结果,而在于过程,而这个过程尽管充满着痛苦和不幸,支配“双重意志”的自由仍然被留给了每一个人及其灵魂。如此一来,奥古斯丁的神学就为人的自由权利的伸张设置了一个广阔的空间。的确,奥古斯丁是主张人的理性须绝对服从信仰的,但他既然已经承认了现实人生存在的合理性,他就不可能否定理性生活对于现实之人的必要性。他指出,人既凭借信仰认识上帝,又依靠理性统治世间百兽万物;(注: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322页。 )他把上帝用以创世的质料理解为“智慧”,人类的理性正是从上帝的智慧中借来的光,因此他虽然反对人类为了好奇心及肉欲的满足而追求世俗的知识,但并没有反对为了信仰的目的而追求这种知识。(注: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70、219页。)在有关上帝的“永福”与人的世俗生活的问题上,奥古斯丁思想的两重性也极其明显:一方面,他把现实人生看得十分暗淡,认为人们的“灵魂因追求世俗而死亡,惟有逃避世俗才能生活”。(注: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07、309页。)另一方面,他又感到“整个物质世界虽则不是处处完美,但即使以我们的大地为基础的最差的部分也有其美丽之处”。(注: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60页。 )他虽然反对一味沉湎于世俗愉悦的纵欲主义,却也不主张过度的禁欲主义,显然,他所要的是一种有节制的和理性的世俗生活。例如,对于饮食,他认为须以满足身体健康需要为限度;(注: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12-215页。)对于音乐,则应以能激发虔诚情感为目的; (注: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16-217页。)至于婚姻,尽管他曾因自己没能仿效圣安东尼信守独身而深感懊悔,但他仍把人类的婚姻看作是上帝的杰作,他在诠释保罗书信时指出:只有极少数品德超群的人才能信守独身,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以过婚姻生活为宜,夫妻间为了生殖的目的而交媾不是罪,不是为了生殖而是为了肉体愉悦的目的而交媾也只能算是可以谅解的小罪。(注:Emilie Amt ed,Women'sLives in Medieval Europe——A Sourcebook,Routledge,1993,pp26-28.)奥古斯丁即使在追溯人间邪恶的起源时也给世人留下了选择的余地。有关人类犯罪的问题,圣经中是有不同说法的,《创世记》通过伊甸园的故事把罪的产生归咎于人类始祖对上帝的背叛,而新约的《启示录》则把罪与一个堕落了的天使首领撒旦(即魔鬼)联系一起。从本意上,奥古斯丁是比较倾向于前一种说法的。他最初时对于这样一个在表面上与摩尼教中善神之对立物很相近的魔鬼的出现表示不解:“如果是魔鬼作祟,则魔鬼又是从那里来的呢?如果好天使因意志败坏而变成魔鬼,那么既然天使整个来自至善的创造者,又何从产生这坏意志,使天使变成魔鬼?”(注: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16页。 )但他很快就悟出了其中的道理:“魔鬼”实为人类向恶意志的一种象征性说法,在人类的傲慢发展到竟敢使自己处于与上帝平起平坐的地步的时候,本应由人类统治的万物也会模仿人类的榜样起来反抗人类的统治,这就整个打乱了造物主既定的秩序,这种连锁性的犯上作乱都应被理解为魔鬼的行为。(注:见奥古斯丁《忏悔录》, 第122页。)但由于奥氏在这里并没有明确否定一个外在于人类心灵的魔鬼的存在,这就给后人提供了发挥的空间,于是有人对此作了折中的调和,认为由始祖继承而来的先天之罪为内在的罪,由后天外界诱发之罪为外在的罪。(注:Richard Cavendish:Mythology—— An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Orbis Publishing Limited,1980,pp163-164.)该解释显然为人类的各种各样的世俗行为找到了一个开脱责任的借口,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意志对于造物主的最初胜利。
当然,奥古斯丁主义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由于奥古斯丁主义以实现对于上帝的精神归趋为目的,其主旨在于个体心灵的修习,这必然导致对于物质性的世俗人生的忽略乃至轻视,并在客观上诱发了悲观遁世和禁欲主义思潮——尽管奥氏本人未必真正赞同这一思潮;奥氏主张理性对于信仰的绝对服从,使人性完全依附于神性,有关人学的理论便不得不淹没于神学的海洋中而无法自立。不可否认,相对于后起的托马斯主义而言,奥古斯丁主义的确是过分看重现实人生的苦难与来世永福间的对立。在他看来,人们以自爱构筑了“地上之城”,因而他们蔑视上帝,而在“上帝之城”(即天国)里,人们爱上帝,即蔑视自我;他充分发挥了《罗马人书》中的经文,指出地上之城的人因知识而傲慢,因傲慢而背叛上帝,上帝之城的人则仅以虔诚获取上帝的奖赏。(注:Augustine:The City of God,See Weslsy D.Camp ed,Roo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Vol.I:From Ancient Times To 1715,John Wiley &.Sons,1983,pp58-59.)需要进一步弄清的是, 奥古斯丁这里反映主题的两个概念——俗世的人与天国的人,具有绝然不同的内涵:前者的确是指把灵魂与肉体结合一块的人,后者则是指摆脱了肉体束缚而获得了独立和自由的灵魂,奥古斯丁在这里把这种独自存在的灵魂挂附于一个虚位的“人”之下,这种把生物学引入神学的“移位”现象,在宗教史上是十分常见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奥古斯丁相信灵魂必须要有一个附体才能存在,恰恰相反,在他看来,作为受造物的灵魂与同样作为受造物的躯体是两相排斥的,灵魂受之于上帝的“光明”,躯体则代表背离上帝的“黑暗”,两者的结合从时间上看无异于永恒中的一刹那,灵魂脱离躯体而独立才是人获救的正确方式。(注: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88-294页。)对世俗人生的否定也就包含着对世俗政治权力的贬低,这在客观上必然有利于教会权力的崛起。奥氏实际上把人贬低为被动的拯救对象,他说:“但那一部分得到上帝允许、蒙赦免、被复生、承受上帝之国的人,怎样得救的呢?他们能靠自己的善行得救吗?自然不能。人既灭亡了,那么除了从灭亡中被救出来以外,他还能行什么善呢?他能靠意志自行决定行什么善吗?我再说不能。”(注:奥古斯丁:《教义手册》,转引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20页。)人在拯救过程中无能为力的状况, 决定了他不可能与救世主之间进行直接的交流,因而教会的中介权威的存在便无疑是无经地义的,这就说明了早期教会当局何以偏爱奥古斯丁的体系,同时也说明了后来的托马斯·阿奎那在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何以要充分利用奥氏的思想。
然而,过分渲染奥氏“灵魂净化”思想的消极影响显然是不适宜的。实际上,在一切憎恶教会制度的人看来,教会权力本身就是信仰世俗化和道德堕落的产物,因此奥古斯丁所力求摆脱的“肉体束缚”,便往往被用来指教会及其非法窃取的种种世俗特权。奥氏“灵魂净化”思想的确对于整个中世纪从未间断过的修道运动曾经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修道运动在发展到某个特定的阶段时可能会在客观上刺激教权的增长,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修道运动的最初兴起却完全具有反教会当局的性质。据勃兰达·波尔顿的考证,早期的修道运动以个人分散隐修为形式,后来教会当局才以一种修道院的“共修制”逼其就范;从12世纪开始,修士们重新走出修道院,向世俗社会进行非官方的巡回宣讲,这种行为“传送了一个暗示:教士不是可能找到拯救和进入天堂道路的唯一之人;无论是对于一名基督徒、基督教信仰或基督教的生活方式,都萌发了一种新觉悟:普通的个人应再现其重要性并能象在使徒时代那样有助于上帝福音的传播”。(注:Brenda Bolton:The Medieval Reformation,Edward Amold Pty Ltd,1983,pp18-22.)可见,不同阶段的修道运动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无疑隐含着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否定教会权威的内容。此外,修道运动由于把独身主义从教士等级扩及到普通阶层,这既遏制了基督教人口的繁殖,使教会在反对异教和异端的十字军战争中处于不利境地,同时对教会的税收政策也是一个打击,因此教会当局常通过各种法令对俗人独身修道进行限制,例如12世纪的格列西昂教会法就明确规定:已婚者如未获其配偶的同意及其所在地主教的批准,不得擅自离家独身修道。(注:Emilie Amt ed ,Women's Lives in Medieval Europe —— A Sourcebook,Routledge,1993,pp79-83.)这些事实说明奥氏思想之突出精神皈依和心灵修习,对于缓解此后教会制度的世俗化及教权的专横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奥古斯丁虽然反对人类滥用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去背离上帝,但并不拒绝使用它去认识上帝。其实,摆脱世俗桎梏、向往精神自由并期盼最终与至善上帝的结合正是奥古斯丁思想的精髓所在;而奥氏在诠释人的过程中以神的名义赋予了社会的人以一种追求个性完美的自由权利,这应当被看作是奥氏思想中最具有革命性的内容。就奥氏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言,正统的神学家无疑会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他的神学论证上,但后人却往往更加关注他那种反抗世俗的勇气和精神。奥古斯丁在谈到自己与异教信仰作决裂的感受时曾充分利用了保罗书信的有关教诲来阐发这一观点:“主,我们的天主,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情感一朝摆脱了促使我们趋向败亡的耽玩世俗之心,我们的灵魂才度着良好生活而开始真正的生命,这样实践了你通过使徒而诰诫我们的话:‘不要随从世俗’,因此也实践了你接着说的:‘要变化气质,重建新心’。”(注: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310页。 )他认为正是可恶的传统习惯把自己的青年时代拖入了无耻淫乐和迷信盲从的深渊,他说:“人世间习俗的洪流真可怕!谁能抗御你?你几时才会枯竭?你几时才停止把夏娃的子孙卷入无涯的苦海,即使登上十字架宝筏也不易渡过的苦海?”(注: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9页。)这种本属批判异教影响和谴责世俗友谊的词句到了后人手中却成了反抗既定社会成规和追求个人思想自由的有力武器,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就是这样做的。人文主义既以“复归传统”为旗号,他们对于自身濡染其间并于不久前被教会钦定为正统的托马斯体系自然不抱好感,因此他们把奥古斯丁那种彻底摆脱了肉体束缚的独立自由的灵魂当成是一个解放了的个性来追求。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过渡性诗人但丁便深受奥古斯丁的影响,他的《神曲》因散发着自由气息而渗透出人文主义的最初曙光,他赞美炼狱中死者的灵魂“追求自由”,因为“自由是如何可贵,凡是为它舍弃生命的人都知道。”(注:但丁:《神曲·炼狱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这里他所需要的“自由”自然包括他在佛罗伦萨为之奋斗了大半辈的公民政治自由,但与这种政治自由相比,精神的自由在但丁看来显然更形重要,他借诗中天堂向导俾德丽采的口表达了自己对意志自由的向往:“上帝在当初创造万物的时候,他那最大、最与他自己的美德相似,而且最为他自己珍爱的恩赐,乃是意志的自由,他过去和现在都把意志的自由赋给一切有灵的造物,也唯独他们才有自由的意志。”(注:但丁:《神曲·天堂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我们之所以把但丁的这种精神追求与奥古斯丁的思想联系起来,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前者与后者一样地把肉体及现实人生的存在当作是精神自由的一种羁绊而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丁通过维吉尔的口断言炼狱中的灵魂正是由于“亚当的肉躯的重累”才无法登上天堂的;(注:但丁:《神曲·炼狱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76-77页。 )他在借助天堂的美景去阐发对俾德丽采的爱情时刻意使“邪恶人类的现世生活”与“心灵的天堂”形成鲜明的对照;(注:但丁:《神曲·天堂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页。 )他宣称离开肉体的心灵才能摆脱思想成见的影响。(注:但丁:《神曲·炼狱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而正是从这些与旧时代难解难分同时又散发着新世纪气息的诗句中,我们看到了奥古斯丁神学中的“人”并没有死去,而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作为“人学之父”的彼特拉克,更是直接从奥古斯丁主义当中获得思想灵感,据说他对奥氏的《忏悔录》爱不释手,他在谈起自己的读后感受时说:“我似乎不是在读别人的历史,而是在回顾我自己的人生历程。”他的自传《我的秘密》即模仿《忏悔录》而成,由于奥古斯丁极力推崇柏拉图和西塞罗,因此彼特拉克在该书中甚至断言:如果这两位古典哲学家被给予机会的话,也可以成为一名基督教徒。(注:Jaroslav Pelikan;The Christian Tradition——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4)Reformation of Church and Dogma(1300-1700),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p 20-21.)据雅罗斯拉夫·皮里肯的考证,由于奥氏《忏悔录》中的内省思想与《论三位一体》相关内容的结合所造成的神秘主义效果对于教会权威的正统性来说也是一个潜在威胁,因此在14和15世纪期间没有一个重要的教理问题不牵涉到对奥古斯丁的研究,由此可见他的影响力是如何之大。(注:Jaroslav Pelikan;The Christian Tradition——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4)Reformation of Church and Dogma(1300-1700),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p 21-22.)后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斯对奥古斯丁神学的总体态度如何,我们知之甚少,但在人性的挖掘方面,我们在伊拉斯谟斯身上仍可发现奥氏思想的某些影响。伊拉斯谟斯通过还原圣经文本的本来面目和重写圣徒传记等方式从早期基督教中找到了品德高尚的人的典范,这必然导致对于人的灵魂深处的关注——而只要触及到该问题,他就不可能不与包括奥氏在内的早期教父发生关系。马苟·托德曾经指出:从圣经上得到的关心个人道德的那种直觉,把伊拉斯谟斯等人吸引到了罗马的斯多噶主义;他们立志沿着那被认定为最有教益的古代文本——圣经、教父的作品及希腊罗马道德家的作品——所指明的路线去重新设计个人、社会及政治行为。(注:Margo Todd:Christian Humanism and the Puritan Social Ord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23.)而这种注重个人德行和蔑视世俗性外在形式的风格,正是奥古斯丁神学中所要塑造的人必须具有的基本风格。
本文1999年2月收到。
标签:奥古斯丁论文; 基督教论文; 忏悔录论文; 上帝的教会论文; 人性论文; 西欧中世纪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中世纪论文; 创世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