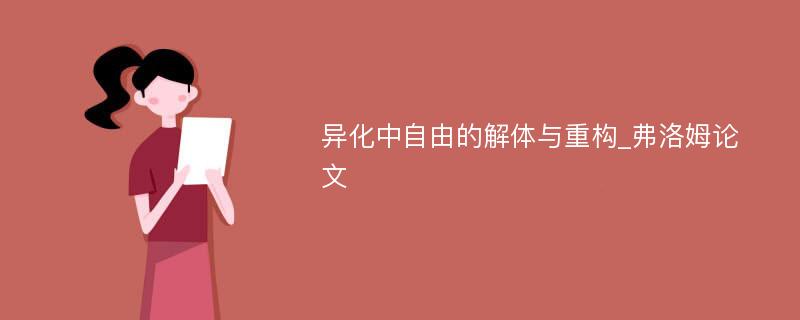
自由在异化中的解体与重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3)S1-0109-03
一、异化下自由的解体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饱满的人道情怀揭示出,体现着人自我 创造的属于人本质的劳动,正在由于它和它的生产者与产品的分离,而沦落为被动的、 无意义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的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 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异化了的劳动 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商品拜物教的物化的力量正在把人置换成物质的筹码。
致力于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统一的赖希认为在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家庭及宗 教等通过对人的性的压抑,把意识形态锚定在人的性格结构中。社会和家庭作为制造驯 化动物的工厂,是同人的性满足的需要根本相对的,而性的压抑是社会的统治阶级完成 其对人们经济奴役的心照不宣的手段,并且社会通过性压抑把人沦为消极被动的牺牲品 ,使他最后磨损掉自由意识和人格的棱角,向外在的权威俯首称臣:“对性需要的压抑 造成智力和情感作用的普遍衰退;尤其使得人们缺乏独立性、权力意志和批判能力…… ,正是通过强制的父权制家庭,性道德的固置以及它在人身上引起的变化,造成了一种 特定的心理结构,这一心理结构就是任何权威主义的社会秩序的大众心理基础。”[2] 以此出发,赖希把性和本能的根本解放发展为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理论,这种性的解放 是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相抗衡的一种特别的潜力。
比赖希更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马尔库塞在提出他的“非压抑性文明观”的同时又批判 道:这种特定的压抑不仅造成了人的快乐原则被废黜,而且还导致了人性的根本异化和 创造精神的消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工业文明所修饰的整个社会(如美国)反映了一 种奇特的悖谬:它增加了人的资源和物质需要的满足,同时又以外部控制和官僚管理的 现代社会的总体异化,反映了人已经不能在劳动中实现自己,相反,却在现代社会的各 种控制形式中不断地沉沦,沦为物化的牺牲品。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继续了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批判,指出现代发达的工业社会以面包和牛排的小恩小惠把人改 造成了一种单向度的人,技术通过建立富裕的生活而成了一种对人的新型的控制方式, 使那些不满和反抗社会制度的人得到了安抚,从而平平静静地用消费的平均化把人的激 进的反抗抹平,这正是解放的障碍;而意识形态成为把人的丰富而特殊的灵性打制成“ 一个文化机器的齿轮”的工具。这也正是卡夫卡在《乡村婚事》中所描写到的“我手无 寸铁地面对着一个形体,他安静地坐在桌旁,望着桌面,我围着他绕圈子,感到自己被 扼住喉咙快窒息了似的。第三个人围看我转圈子,觉得被我扼住。第四个人绕着第三个 人走,感到被卡住喉咙,就这样持续下去直到星辰运行到宇宙之外。万物都感到被卡住 了脖子。”——这种“被卡住了”的感觉与状态。[3]
赖希和马尔库塞的研究深深地启示了弗洛姆,同时,弗洛姆又把人的性格放到更广阔 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考察,不是把极极主义性格的形成归结为性的压抑,而是归结为人 在与世界相分离的处境下所产生的逃避孤独和不安全感的需要。他认为,现代社会技术 的非人道化发展,使得人类在追逐科学的过程中,获得了驾驭自然的知识却丧失了关于 人文主义精神、生命价值的知识;获得了技术与物质的价值,却丧失了喜悦与悲伤等层 次的情感体验能力。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运作方式客观上要求人身自由,然而,这种 自由因人的异化而给现代人带来了更难解决的一个二难困境,这也就是弗罗姆所看到的 现代人的特有困境就在于资本主义的自由,这种自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解除了传 统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种种束缚,个人获得了独立;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又使人感到 不安全,感到孤独和恐惧。传统社会安全而不自由,现代社会自由而不安全。正是这种 不安全的自由使人产生种种逃避倾向。人在孤独恐惧的困境中,会不由自主地屈从于一 个权威,甚至在权威的感召下,去虐待、侵略和破坏。在弗洛姆看来,欧洲的中世纪是 最安全、最稳固的。在中世纪的教会和世俗社会中,每个人有确定的地位,虽没什么自 由,但却有归属感和安全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摧毁了中世纪的堡垒,人从封 建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较大的自由。但是随着社会进到资本主义,人的社会 地位却越来越不稳固。人虽有了自由,但却感到孤独,感到不安全。
于是,这种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Freedom to),而是使人失去了保障的自由(Freedom form)。较之中世纪,现代社会确实是免除了人的奴役之苦(Free from slavery)。每个 人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但却没有中世纪的那种安全感与归属感。人虽无牵挂, 但并非真正自由地存在,自由地发展,自由地享受人生。人总是处在危险之中,因为他 的存在、发展等等总是依赖别人对他的认可(Accepted)。于是,弗洛姆断言,现代人准 备放弃自由,逃脱现行社会制度,走向极权主义或扭曲的精神世界;认为现代人的人格 向消极方面倾斜(向往极权主义或发生精神变态)是现行社会制度的不安全与人对安全感 的追求这一对矛盾造成的。看来,异化社会下的现代人,的的确确是已经“自由的一无 所有”,不是马克思所谓的生产资料的一无所有,而是一无所有到一种从肉体到精神的 真空状态。
二、逃避自由还是超越自由
弗洛姆认为,当人从与自然同一的状态中脱离出来,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与自然界、与 他人有别的整体时,就开始了人类的社会发展史。他把一个人日渐从其原始状态脱颖而 出的过程称为:“个体化”;当社会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个性化”过程似乎发展到 了顶点。在个体化过程中,同时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是自我力量的增长,意味着人越 来越自由;另一方面,孤独感疏远感也日益加强。弗洛姆认为,人性虽是人类进化的产 物,但人性中也有某些固定不变的因素,“这就是:力图满足由生理条件所制约的内驱 力的需求,以及逃避孤立和精神孤独的需求”。可见,弗洛姆是将人的害怕孤独和疏远 也看成和吃喝性交一样,是一种本能。于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到了垄断时 期,人便越来越陷入这样一个怪圈:“人,他所获得的自由愈多(从人和自然的原始浑 一状态中产生出来这一意义上的自由),他愈加‘个人化’,他就愈别无选择,或者通 过自发性的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来与世界联结起来,或者通过那些会破坏他的自由和他个 人自我完整性的与世界的联结方式来寻求某种安全。”(《爱的艺术》)这种爱是一种能 动性的爱,是一个人的力量的体现。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就会自发地去爱他人,通过这 种对于他人的爱克服分离恐惧,而实现对结合的无处不在的渴望。“这种结合不仅仅是 感官上的,而是包括智力、想像力、感受力等在内的我们整个个性的结合。”(雪莱)也 正是通过这种融合体验,个人与他人维系起来,同时“施予”感受使个人重新认识自己 。于是,在爱里,个人虽然依然存在,但却是作为结合为一体之物,然而,也正是在爱 里,个人通过这种能动性,自发地重新认识自己,把握自己,他们又是各自独立的。融 合感觉克服了分离恐惧,而自我意识的增强又使个人体会到了发自内心的力量和进一步 施爱的动力。这是一个释放的生命,是一种倾流的爱。也正是在这种能动性的爱欲倾流 中,人才成为了一个积极实践之人。而人是“由于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 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这与极权独裁制度通过控制个体的自由 使个体绝对服从从而寻求安全的行为不同,它实质上是一种对于自由的超越,而非逃避 自由。
异化通过将人的创造性活动的成果与人们进行该项创造性活动的劳动相分离,带给了 现代人孤独的自由,然而,也正是这种孤独的自由,带来了现代人对自我的远远超过古 代人的更多的思索,而本着对人的尊敬,打碎了宗教神学的牢笼和专制政治的枷锁,点 燃了人性解放的火种。尤其是20世纪战争灾难更引发了后现代对于个性扼杀的抨击和对 于斯大林式的“唯物”的排斥。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众多有理智的人(包括马克思· 韦伯在内,他也曾欣喜地说大战终于来临)对于不是为了获取食物而杀戮的战争依然趋 之若骛,爱因斯坦就曾致信弗洛伊德表达他的不解。而弗洛伊德也不得不承认“我至今 也不明白,对于这种无所不至的侵犯性和破坏性,我们竟没有给它一个适当的位置。( 《文明及其缺陷》,1930)。事实上,这一战争的悲剧也恰恰是弗洛姆所说的人们被动 地为了克服异化带来的分离恐惧的迎合性格所致。个人为了避免使自己陷入孤立无助的 处境,完全放弃自我,成为了权威的附属品。于是,后现代主义才死命地解拆黑格尔的 “绝对”,排斥斯大林式的“唯物”,拒绝各类“形而上学”,而承接了尼采的“上帝 死了”,由福柯这位猛士喊出——“人死了”!这“人死了”并非一个事实判断,而是 一个价值判断,是“人该死了”,如同尼采的“该死的上帝”。福柯准备谋杀的人是“ 同一”的人、“清一色”的人。福科要培育的是“异质”的人,“异质性”、“延异性 ”则成了他们的追求。无限分化、多元决定、树状分叉、多样发展的异质性和延异性, 必然决定人的存在有无限的自由度。正像斯蒂芬·柯维所认为的,在“刺激—反应”之 间,人有选择自由。正是这个选择自由体现了人的异质性,事实上,这个选择自由也正 是人性的复杂的体现。依我看来,可以套用生物学上的细胞膜选择透过性的含义,来诠 释这种人的存在的自由度。细胞膜的选择透过性通过三种方式表现:一、由浓度高低所 定。分子总是从高浓度向低浓度扩散,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正如人,不可避免地具有某 些本能与存在性,就像是弗洛伊德的“本我”;二、通过消耗能量,将物质从低浓度向 高浓度的逆向移动的主动运输。这就像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等等的教化作用 ,于是乎,中国人便有了为世人所惊讶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高度统一性”(蒙罗) ,也即弗洛伊德的“本我”。三、通过细胞膜的变形内折,把物资“吞”入的“胞饮” 作用,或把物资排出的“胞排”作用,套用在人性上,这也就是卡西尔所忽略的人本身 的作用,人与文化的吸收和排斥作用,人的能动性(proactivity)。选择自由使我们成 为了无与伦比,不可替代的人。除了自我察觉,我们还拥有想象力——超越自我目前的 现实在我们的心灵里进行创造的能力。我们拥有良知——对是非和支配我们行为举止的 那些原则的深层内在意识和我们思想行为在多大程度与这些原则保持了一致的感觉。而 且我们还有独立意志——摆脱所有其他的影响,根据我们的自我意识采取行动的能力。 也正是这种人自发性的选择自由带来了异质性与延异性。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所 理解的自由的源泉。如果行动就是一切,我行我素即是人生。这不是独裁者的自由、唯 一者的自由,而是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同时,这种异质性是在弗洛姆的“爱”的基础上 的差异性,是有着融合体验的各自独立的人的差异性,它是各人的自由,同时也是协调 中的各人的自由。异化从本质上有着与其对立的一面,然而,无疑,也正是异化带来了 这种“差异”,不是彼此孤立的人之间的差异,而是彼此协调的人为了独立而存在的差 异。显然,正是这种差异引导我们现代人不必“逃避自由”而是“超越自由”,作为实 践性的主体完成对于自由的超越。相信,这也是弗洛姆更希望看到的结局。
收稿日期:2002-10-07
标签:弗洛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