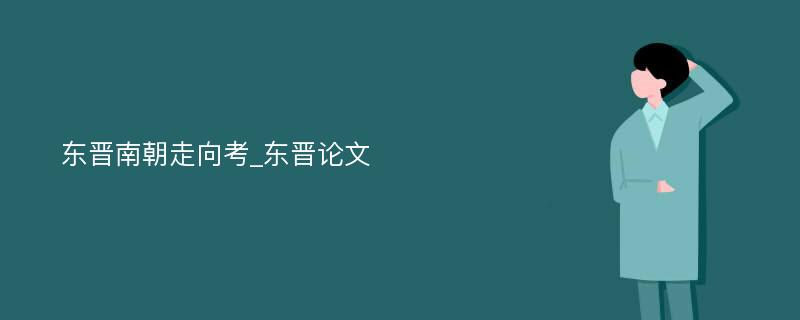
东晋南朝的方位州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晋论文,南朝论文,方位论文,州考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4-0057-07 在东晋南朝史书中有不少关于东州、西州、南州、北州的记载。这些以方位词称呼的“州”,不是正式和法定的名称,而是州级政区、城镇或官府的别名,含义较为复杂。周一良考证:“西州指扬州刺史廨舍”,“江州一带”可称南州①。这仅是西州和南州的一个用法。此外,尚未见学者对此问题予以探讨。本文拟对这些方位州的含义进行全面考察,并阐释其得名的缘由。这不仅有助于对相关史料的解读,也有益于对东晋南朝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认识。 “西州”一词在东晋和南朝的史书中频繁出现。它具有多个含义,使用最多的是指代扬州刺史的官衙。例如,沈怀文“迁别驾从事史,江夏王(刘)义恭迁,西阳王(刘)子尚为扬州,居职如故。时荧惑守南斗,上(孝武帝)乃废西州旧馆,使子尚移居东城以厌之。怀文曰:‘天道示变,宜应之以德。今虽空西州,恐无益也。’不从,而西州竟废矣……扬州移会稽,上忿浙江东人情不合,欲贬其劳禄,唯西州旧人不改。”②由扬州和扬州刺史可以断定,此处的四个“西州”都指扬州刺史的官衙。在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城内的西州都是这个含义,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东晋南朝宰相所居在台城(即官城)之东,称东府;扬州刺史府因位于台城之西,被称为西州③。得名体现了其重要性。此外,西州还用作州级政区的别名,具有两个含义,最多的是指代荆州,其次是指代益州。 大宝元年(550年)二月“丙午,侯景逼太宗幸西州”;六月“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鸦仁自尚书省出奔西州”;“冬十月乙未,侯景又逼太宗幸西州曲宴”④。第一与第三个“西州”指扬州刺史的官衙。但第二个“西州”的含义与此有所不同。《南史》的记载是:大宝元年六月“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鸦仁自尚书省出奔江陵。”⑤荆州的治所为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因而第二个“西州”应指荆州。羊鸦仁本传的记载也可为证:“台城陷,鸦仁见(侯)景,为景所留,以为五兵尚书……(太清)三年(549年),出奔江西,其故部曲数百人迎之,将赴江陵,至东莞,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诸子所害。”⑥《南史》所载“三年”,皆有误,应为“四年”,即大宝元年,因为《资治通鉴》的记载与《梁书》《南史》的本纪相同,也是大宝元年。《南史》与《资治通鉴》也都记载羊鸦仁“出奔江西,将赴江陵”⑦。进一步佐证“西州”指代荆州。侯景控制建康期间,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时位长连率,有全楚之资”⑧,成为抗击叛军的政治中心,很多大臣纷纷前往投奔。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魏使节徐陵,向荆州刺史萧绎所上的劝进表中称:“既挂胆于西州,方燃脐于东市”⑨。此“西州”也是指荆州。 西州指代荆州的事例早在《宋书》中就有。建平王刘景素,“泰始六年(470年),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左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如故。征为散骑常侍、后将军、太常,未拜”。宋末,他举兵反叛,兵败被诛。齐初,刘景素当年举荐的秀才刘琏上书为他申冤说“王之在荆州也,时献太妃初薨,宋明帝新弃天下,京畿诸王又相继非命,王乃征入为太常……于是弃西州之重,而匍伏北阙。”⑩这里的“西州”显然指代荆州。 西州指代荆州的事例在《南齐书》中更多。萧齐大司马、豫章王萧嶷,曾任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南蛮校尉、荆湘二州刺史。他病故后,其最亲信的属官之一乐蔼,给竟陵王萧子良的笺中说:“辄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垄首……下官今便反假,无由躬事刊斫,须至西州鸠集所资,托中书侍郎刘绘营办。”他给太子右卫率沈约的信中自称:“吾西州穷士”(11)。乐蔼,“南阳淯阳人……世居江陵。”(12)西晋时南阳郡属于荆州,南朝时南阳郡隶属于雍州。乐蔼所说的“西州”,不是指自己原来的郡望,而指渡江后的世代居住地,即江陵所在的荆州。刘宋后期,沈攸之长期担任都督荆湘雍益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萧道成称他“拥戎西州”(13)。此处的“西州”也是指代荆州。 荆州被称之为西州,是因为它在当时军事和经济局势中的极端重要性。东晋录尚书事何充曰:“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14)。齐梁时的史家沈约说:“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宋武帝刘裕)使诸子居之。”(15)沈约又说:“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此二州“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晋世幼主在位,政归辅臣,荆、扬司牧,事同二陕。宋室受命,权不能移,二州之重,咸归密戚。”(16)扬州与荆州是东晋南朝最重要的两个州,被世人比拟为先秦的西陕与东陕,荆州在西边,故被称之为西州。顾祖禹总结历史指出:荆州府“自三国以来,常为东南重镇,称吴、蜀之门户……东晋而后,以扬州为京师根本,荆州为上流重镇,比周之分陕,号为‘西陕’云……终六朝之世,荆州轻重系举国之安危。”(17)由于荆州在军事和经济上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备受朝廷和世人重视,西州的称谓就突出反映了这种现实状况。 西州有时也用来指代益州。萧齐时,王玄载“出为持节、督梁南北秦三州军事、冠军将军、西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进号征虏将军。寻徙督益宁二州、益州刺史、建宁太守,将军、持节如故……在梁益有清绩,西州至今思之。”(18)王玄载担任梁秦二州刺史的时间很短,因而此处的“西州”指益州。何妥,“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19)郫县隶属于益州的蜀郡,萧梁的武陵王萧纪当时为益州刺史,结合“通商入蜀”可知,这里的“西州”显然指益州。 益州被称为西州,一是因为它位居南朝疆域的西部边陲,二是因为它经济富庶,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地。诸葛亮向刘备分析天下形势时就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20)。顾祖禹总结历史说:“志称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21)三是因为益州是江左政权的军事屏障。王鸣盛指出:“江左不可无蜀……险既可恃,吴楚溯流直达,由汉中可窥关陕。晋灭蜀,吴不能救,失犄角之势,晋之取吴易矣。”隋灭陈与此同(22)。 东晋南朝时记载的东州具有两个含义,最多的是指代扬州,其次是指代东扬州。 如前文所述,荆州和扬州被世人比拟为西周时的二陕,荆州位居西方,被称为西州,扬州位居东方,故被称为东州。扬州的这一别名,在东晋时就出现了。“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及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士,邈既东州儒素,太傅谢安举以应选。”(23)东莞郡属于徐州;东晋时京口(今江苏镇江)隶属于扬州的晋陵郡。因此,这里的“东州”并非指徐邈的原籍徐州,而是指其家族渡江后的世代居住地扬州。“琅邪临沂人”、刘宋丹阳尹颜竣,上表让中书令中称:“臣东州凡鄙,生于微族。”(24)此处的“东州”可考。颜竣的高祖颜含,“随元帝过江,已下七叶,葬在上元幕府山西。”(25)唐代的上元即东晋南朝的建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多数官员归葬家乡祖先墓地,过江后则葬在侨居地。”(26)颜氏过江后世代葬在建康,说明他们侨居建康。颜竣的郡望虽然是徐州琅邪,但他所说的“东州”并非指徐州,而是指颜氏过江后世代居住的扬州。 东晋南朝时的京师在建康,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扬州是京畿地区,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还是国家赋税的首要来源地。沈约明确指出:江左政权“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27)顾祖禹评论说:“(应天)府前据大江,南连重镇,凭高据深,形势独盛。孙吴建都于此,西引荆楚之固,东集吴会之粟,以曹氏之强,而不能为兼并计也……王导亦云:‘经营四方,此为根本。’盖舟车便利则无艰阻之虞,田野沃饶则有转输之藉,金陵在东南,言地利者自不能舍此而他及也。”(28)荆州被誉为西州主要源于军事与经济因素,扬州被誉为东州则主要由于政治与经济原因。东晋南朝时扬州与荆州并举被视为二陕,所以朝廷认为控制了这两个州,就掌控了全国的局势。萧遥欣“迁使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右将军、荆州刺史……高宗子弟弱小,晋安王宝义有废疾,故以遥光为扬州居中,遥欣居陕西在外,权势并在其门。”(29)“陕西”指荆州。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分扬州东部的会稽、永嘉、东阳、新安、临海五个郡为东扬州;大明三年(459年)以扬州为王畿,东扬州称扬州;八年王畿改为扬州,扬州改为东扬州;前废帝永光元年(465年),东扬州并入扬州。梁武帝普通五年(524年)三月,再次设立东扬州,除以上5个郡外,还包括江州的建安和晋安两郡,治所都在会稽(今浙江绍兴)。相对于扬州而言,东扬州也被称之为东州。“时武陵王在东州,颇自骄纵,上召革面敕……乃除折冲将军、东中郎武陵王长史、会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门生故吏,家多在东州,闻革应至,并赍持缘道迎候。”(30)由会稽郡丞可以推知,此处的两个“东州”都指东扬州,武陵王萧纪的仕历再次佐证。丹阳尹萧纪“出为会稽太守,寻以其郡为东扬州,仍为刺史,加使持节、东中郎将。”(31)由此可知,以上两个“东州”都指代东扬州。在陈朝,仍然称东扬州为东州。在天嘉“三年(562年),始兴王伯茂出镇东州,复以(程)文季为镇东府中兵参军,带郯令。”(32)同年六月,“以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新宁、晋安、建安八郡置东扬州。以扬州刺史始兴王伯茂为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33)据此可知,前文的“东州”也是指代东扬州。 东扬州被称为东州,除位置在建康之东外,还由于该地区当时经济发达、物产富饶。晋元帝任命诸葛恢为会稽太守时对他说:“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34)沈约评论说:“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35)这都反映出会稽郡的富庶。 “南州”一词在东晋南朝的典籍中出现的频率更高,其含义也更为复杂。首先,它是指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王敦兄含为光禄勋。敦既逆谋,屯据南州,含委职奔姑孰”。对后者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曰:“初,王导协赞中兴,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刘隗为间己,举兵讨之。故含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备也。”程炎震据此将前文的两个“南州”都解释为姑熟:“盖(桓温)遥领扬州牧,州府即随之而移,以姑孰在建康南,故得南州之名,如西州之比矣”;“敦以太宁二年,下屯于湖,自领扬州牧,故姑熟得蒙州称。若永昌元年,但进兵芜湖,未据姑熟。刘注引邓粲《晋纪》,足以正本文之失也。”(36)《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也将前一条史料中的“南州”解释为姑熟:南州,“亦作南洲。姑熟城别名,即今安徽当涂县。《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宣武(桓温)移镇南州。’”(37)这些诠释都不妥当。“永昌元年(322年),(王)敦率众内向,以诛(刘)隗为名……敦至芜湖,又上表罪状刁协……敦兄含时为光禄勋,叛奔于敦。”(38)《资治通鉴》的记载与此同:永昌元年正月“戊辰。(王)敦举兵于武昌,上疏罪状刘隗……敦至芜湖,又上表罪状刁协……敦兄光禄勋含乘轻舟逃归于敦。”(39)这都证明,《世说新语》的记载并不误,而是邓粲的《晋纪》有误。王敦在“永昌元年,但进兵芜湖,未据姑熟”,而《世说新语》称之为“屯据南州”,说明此处的“南州”并非指姑熟。“晋江左胡寇强盛,豫部歼覆,元帝永昌元年(322年),刺史祖约始自谯城退还寿春。成帝咸和四年(329年),侨立豫州,庾亮为刺史,治芜湖。”(40)侨立的豫州治芜湖(今安徽芜湖),王敦屯据芜湖,所以被称为“屯据南州”。显然前文第二条史料中的“南州”指代侨置的豫州。桓温“加扬州牧、录尚书事,使侍中颜旄宣旨,召温入参朝政……温至赭圻,诏又使尚书车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让内录,遥领扬州牧。属鲜卑攻洛阳,陈祐出奔,简文帝时辅政,会温于洌洲,议征讨事,温移镇姑熟。”(41)《晋书》的记载与此相同:兴宁二年(364年)“八月,(桓)温至赭圻,遂城而居之。”(42)对此《元和郡县图志》也有类似的记载:“赭圻故城,在南陵县西北一百三十里。西临大江。吴所置赭圻屯处也,晋哀帝时,桓温领扬州牧,入参朝政,自荆州还至赭圻,诏止之,遂城赭圻镇焉。后城被火灾,乃移镇姑熟。”(43)桓温“城赭圻”与“制街衢平直”为同一件事。桓温修筑的是赭圻城(今安徽繁昌县西北三十里赭圻岭北麓赭圻冲),后来才移镇姑熟。这足以说明桓温移镇的“南州”,也不是指姑熟,而是指侨立的豫州。桓温“移镇南州”、王敦“屯据南州”,都是指自荆州移镇侨立的豫州。 宋武帝刘裕分侨立的豫州为豫州和南豫州。永初三年(422年)二月,分淮南为南豫州,治所在历阳;淮北为豫州。此后,人们便称南豫州为南州。“(宋)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罚过度,校猎江右,选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从至南州,得鞭者过半。”(44)大明七年(463年)十月“戊申,车驾巡南豫州”;“十一月丙子,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巡幸所经,详减今岁田租”;“十二月丙午,行幸历阳……癸亥,车驾至自历阳”(45)。“校猎江右”就指这次巡狩南豫州。历阳在江北即江右,孝武帝最远到达历阳,因而上文中的“南州”指南豫州。永元三年(501年)九月甲辰,“义军至南州,申胄军二万人于姑孰奔归。”(46)《梁书》对此记载:义军的“前军次芜湖,南豫州刺史申胄弃姑熟走,至是时大军进据之。”(47)义军到达的是芜湖,因而上文的“南州”不是指姑熟。《南史》对此的记载是:永元三年“九月甲辰,萧衍至南豫州,辅国将军、监南豫州事申胄军二万人于姑孰奔归。”(48)据此可知,前文的“南州”也是指南豫州。 由于侨立的豫州一度治姑熟(今安徽当涂县治),人们习惯上又称姑熟城为南州。“(桓)玄将出居姑熟,访之于众……遂大筑城府,台馆山池莫不壮丽,乃出镇焉。既至姑熟,固辞录尚书事,诏许之。”(49)“初,桓玄于南州起宅,悉画盘龙于其上,号为盘龙宅。”(50)此处的“南州”就指代上文的姑熟。《桓玄传》曰:“玄居南州,大筑斋第,以郡在国南,故曰南州。”(51)这里将淮南郡解释为南州,是不准确的。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李善注引《水经注》曰:“淮南郡之于湖县南,所谓姑孰,即南州矣。”李善解释说:“姑熟,桓玄所出,大筑府第于此国南,故曰南州。”(52)郦道元和李善的解释都不妥当。侨立的豫州被称为南州,而姑熟一度是豫州的治所,故被称之为南州。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骑五万北伐。百官皆于南州祖道,都邑尽倾。”(53)《资治通鉴》记载:太和四年“夏,四月,庚戌,(桓)温率步骑五万发姑熟。”(54)桓温北伐从姑熟出师,百官为他祖道自然就在这里。因而上文的“南州”指姑熟。“王敦镇南洲,欲谋大逆,乃召璞为佐。时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问太史:‘王敦果得天下耶?’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单骑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与璞食。”(55)此“南洲”即“南州”,也指姑熟。 南朝沿袭东晋的惯例,仍然称姑熟为南州,而且这种用法更多。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是冬,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西流民于姑孰,合万许家。”(56)同书又载:元嘉“二十八年,使(沈)庆之自彭城徙流民数千家于瓜步,征北将军程天祚徙江西流民于南州,亦如之。”(57)此处的“南州”即姑熟。中兴二年(502年)三月“车驾东归至姑孰。丙辰,禅位梁王。”(58)《梁书》对此事记载:相国左长史王莹,“奉法驾迎和帝于江陵。帝至南州,逊位于别官。”(59)此处的“南州”也指上文的姑熟。“臧质、(刘)义宣并反,(王)玄谟南据梁山,夹江为垒,垣护之、薛安都渡据历阳,(柳)元景出屯采石。玄谟闻贼盛,遣司马管法济求益兵,上(孝武帝)使元景进屯姑熟。”(60)同书对此事又载:“(王)玄谟见贼强盛,遣司马管法济求救甚急。上遣(柳)元景等进据南州,(垣)护之水军先发。”(61)这里的“南州”就是上文的姑熟。当时臧质向刘义宣进计曰:“今以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缀(王)玄谟,必不敢动。质浮舟外江,直向石头,此上略也。”(62)这里的“南州”也是指姑熟。指代姑熟的南州还有很多,此处不赘。 南州主要是用来指代侨立的豫州、南豫州及其治所姑熟,是由它们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决定的。《金陵记》曰:“姑孰之南,淮曲之阳,置豫州。六代英雄迭居于此。以斯地为上游焉。”(63)东晋南朝时朝廷的主要威胁来自上游的荆州,东晋时的王敦、桓温、桓玄、刘毅、司马休之和刘宋时的谢晦、刘义宣、沈攸之都以荆州刺史举兵或因猜忌被讨伐。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及其治所姑熟,因为在建康的上游,并且邻近建康,从而成为捍卫京师的重要防线。顾祖禹深刻论述说:“(太平)府控据江山,密迩畿邑。自上游来者则梁山(今安徽芜湖市北长江东岸东梁山)当其要害,自横江(今安徽和县南得胜河)渡者则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街道江滨)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熟为必争之地。东晋以后,尝谓京口为北府,历阳为西府,姑熟为南州,而南州关要,比二方为尤切,地势然也。王应麟曰:‘太平,江津之要害也,左天门,右牛渚,铁甕直其东,石头枕其北,襟带秦淮,自吴迄陈,常为巨屏。’”(64)诸多事例证明,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是建康的军事屏障,姑熟是其中的重要关口。“及(王)敦举兵,(豫州刺史祖)约归卫京都,率众次寿阳……进号征西将军,使屯寿阳,为北境藩扞。”(65)元徽二年(474年)三月,太尉、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举兵反,右卫将军萧道成主张全力坚守建康,“中书舍人孙千龄与休范有密契,独曰:‘宜依旧遣军据梁山、鲁显间,右卫若不出白下,则应进顿南州。’太祖正色曰:‘贼今已近,梁山岂可得至……’”(66)“依旧”二字显示,一般情况下长江中上游发生叛乱,王师需要进驻南豫州,特别是梁山和姑熟,来进行防御。因为中上游的叛军顺长江东下,必须要经过南豫州,因而成为京师建康的门户。江北军事势力南下一般从横江、采石渡江,姑熟成为防御长江的军事要塞。西晋“大举伐吴,(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率师出横江”,后从此处渡江(67)。苏峻叛乱,“峻遣将韩晃、张健等袭姑熟,进逼慈湖……峻自率(祖)涣、(许)柳众万人,乘风济自横江。”(68)侯景叛乱,“自采石济,马数百匹,兵千人,京师不之觉。景即分袭姑熟。”(69)隋军攻陈,先锋韩擒虎“率五百人宵济,袭采石,守者皆醉,擒(虎)遂取之。进攻姑熟,半日而拔。”(70)由于姑熟是扼守江津的军事重镇,它所在淮南郡太守的人选备受朝廷重视。齐高帝萧道成对刘善明说:“淮南近畿,国之形势,自非亲贤,不使居之。”(71)由于姑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普通七年(526年)四月,“南州津改置校尉,增加俸秩”(72)。《南史》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普通七年,改南州津为南津校尉,以(郭)祖深为之。加云骑将军,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严清刻……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73)“淮南太守”佐证上文的“南州”指代姑熟。在姑熟设置校尉,也说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南州有时用来指江州。庐陵王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府事江革,“以清严为属城所惮。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革以正直自居,不与典签赵道智坐。道智因还都启事,面陈革堕事好酒,以琅邪王昙聪代为行事。南州士庶为之语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骑,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74)由江革的官职可知,此处的“南州”指江州。“(王)琳平,(华皎)镇湓城,知江州事。时南州守宰多乡里酋豪,不遵朝宪,文帝令皎以法驭之。”(75)这里的“南州”也指江州。江州被称为南州,是因为民户众多、经济富庶。“庾亮领(江州)刺史,都督六州,云以荆、江为本,校二州户口,虽相去机事,实觉过半,江州实为根本。”(76) 南州还可用来指代广州。萧子显说:“至于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77)此“南州”指广州。广州称南州也是因为经济富实。“南土沃实,(广州刺史)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78) 南朝史书中的北州有两个含义,主要是指青州,其次是泛指北方诸州。 封延伯,“渤海人也……州辟主簿,举秀才,不就。后乃仕。垣崇祖为豫州,启太祖用为长史,带梁郡太守。以疾自免,侨居东海,遂不至京师。三世同财,为北州所宗附。”(79)此处的“北州”可考。唐长孺指出:南北朝时期“青齐地区完全是地方豪强掌握的世界,而这些地方豪强却不是土著,多半是随慕容德南渡的河北大姓……跟随慕容德南迁的还有渤海封氏和高氏。”(80)封懿,“渤海蓨人”,其同族曾孙封灵祐,“仕刘义隆为青州治中、渤海太守。慕容白曜平三齐,灵祐率二百人诣白曜降,赐爵下密子。”(81)两汉以来的惯例是——州郡僚属都辟召本州郡的人。又,“(晋)惠帝之后,冀州沦没于石勒。”(82)据此可知,封灵祐是祖辈从冀州渤海迁居青州的,所以担任青州治中;此处的渤海郡也是设在青州的侨郡。与封灵祐类似,封延伯也是祖辈从渤海移居青州的,他“州辟主簿”,也是青州主簿,即上文的“北州”指青州。刘怀珍,“平原人,汉胶东康王后也。祖昶,宋武帝平齐,以为青州治中,至员外常侍……(怀珍)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451年),亡命司马顺则聚党东阳,州遣怀珍将数千人掩讨平之……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孝武大惊,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数千人,士人怨之……(刘)休宾,怀珍从弟也。”(83)而刘休宾,“本平原人。祖昶,从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之都昌县。父奉伯,刘裕时北海太守。”(84)唐长孺指出:“据此,平原刘氏也是随慕容德南度的河北大姓”;《刘怀珍传》“所云‘冀’者,实指侨置于青州之冀州”(85)。刘宋时,平原郡隶属于冀州,青州的治所在东阳城(在今山东青州市阳水北),而冀州寄治历城(今山东济南)(86)。刘怀珍的祖父担任过青州治中,他平定东阳的叛乱,这都证明他担任的州主簿也应是青州主簿,即他的“本州”指青州,而不是冀州。刘怀珍与刘休宾一样,也是本为平原人,其祖父跟从慕容德南渡黄河,定居于青州北海郡,青州就成为他们的本州,因而被青州刺史辟为主簿。因此,上文的“北州”也指青州。清河东武城人崔祖思曾任青、冀二州刺史,平原人刘善明曾任冀州刺史,萧子显称赞说:“淮镇北州,获在崔、刘。”(87)当时黄河以北地区的冀州在北魏的占领下,冀州侨置于青州。因此,这里的“北州”也是指青州。 其次,北州还用来泛指北方诸州。《宋书·州郡志》“南徐州”条记载:“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同书“南兖州”条记载:“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88)此处的“北州”就泛指上文的幽、冀、青、并、兖、徐诸州。元嘉二十三年(446年),“索虏侵逼,北境扰动”(89)。《南史》对此的记载是:“魏攻边,北州扰动。”(90)这里的“北州”即上文的“北境”,泛指刘宋靠近北魏的北边诸州。 南朝时的北州主要指青州,也是由它的战略地位决定的。潘聪劝慕容德攻占青齐地区时说:“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既据之后,闭关养锐,伺隙而动,此亦二汉之有关中、河内也。”(91)慕容德占据青齐地区后,建立了南燕政权。刘宋时期青州成为南北方争夺的焦点,战事接连不断,就因为它是经济富饶、战略位置重要的形胜之地。 综上所述,荆州和益州被称为西州,扬州和东扬州被称为东州,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及其治所姑熟、江州、广州被称为南州,青州被称为北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它们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周一良曾对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有深刻论述:“东晋南朝偏安江左一隅,沿江多为要地。上游之荆州与下游之扬州尤为重镇”;“长江中下游,则江州(镇寻阳)、南兖(镇广陵)、南徐(镇京口)皆属重镇。南兖南徐为建康之北门,而江州则‘国之南藩,要害之地’”;“保有益州乃立国江南之根本保障”(92)。这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只是就战略地位而言,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其重要性要在江州之上。“会稽王(司马)道子惮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为江州,督豫州四郡,以为形援。(豫州刺史庾)楷上疏以江州非险塞之地,而西府北带寇戎,不应使愉分督,诏不许。”(93)王鸣盛更明确指出:“南朝州郡侨置虽多,大约总以南豫州为最要,南雍州次之。”(94) ①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州”条、“南江、南川、南州”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296页。 ②《宋书》卷82《沈怀文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3—2104页。 ③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4“东府”和“西州”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530—532页。 ④《梁书》卷4《简文帝纪》,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6—107页。 ⑤《南史》卷8《梁简文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0页。 ⑥《梁书》卷39《羊鸦仁传》,第563页。 ⑦《南史》卷63《羊鸦仁传》,第1549页;《资治通鉴》卷163,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047页。 ⑧⑨《梁书》卷5《元帝纪》,第136、129页。 ⑩《宋书》卷72《建平王刘宏传附子景素传》,第1861、1865页。 (11)《南齐书》卷22《豫章王萧嶷传》,第418、419页。 (12)《梁书》卷19《乐蔼传》,第302页。 (13)《南齐书》卷25《张敬儿传》,第471页。 (14)《晋书》卷77《何充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30页。 (15)《宋书》卷51《临川王刘道规传附子义庆传》,第1476页。 (16)《宋书》卷66《王敬弘等传史臣曰》,第1739页。 (1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8《荆州府》,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652—3653页。 (18)《南齐书》卷27《王玄载传》,第509页。 (19)《隋书》卷75《何妥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09页。 (20)《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12页。 (2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6《四川》,第3129页。 (2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57“江左不可无蜀”条,第445页。 (23)《晋书》卷91《徐邈传》,第2356页。 (24)《宋书》卷75《颜竣传》,第1964页。 (25)颜真卿:《颜氏家庙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26)杨恩玉:《东晋宣城内史桓彝墓考辨》,《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 (27)《宋书》卷54《孔季恭等传史臣曰》,第1540页。 (2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0《应天府》,第921页。 (29)《南齐书》卷45《始王道生传附子遥欣传》,第792页。 (30)《梁书》卷36《江革传》,第524—525页。 (31)《梁书》卷55《武陵王纪传》,第825页。 (32)《陈书》卷10《程灵洗传附子文季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73页。 (33)《陈书》卷3《世祖纪》,第55页。 (34)《晋书》卷77《诸葛恢传》,第2042页。 (35)《宋书》卷54《孔季恭等传史臣曰》,第1540页。 (3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55、98、156页。 (37)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4页。 (38)《晋书》卷98《王敦传》,第2558—2559页。 (39)《资治通鉴》卷92,第2893页。 (40)《宋书》卷36《州郡志二》,第1071页。 (41)《晋书》卷98《桓温传》,第2575页。 (42)《晋书》卷8《哀帝纪》,第209页。 (4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8《江南道四·宣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82页。 (44)《南齐书》卷56《茹法亮传》,第976页。 (45)《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33—134页 (46)《南齐书》卷7《东昏侯纪》,第102页。 (47)《梁书》卷1《武帝纪上》,第12页。 (48)《南史》卷5《东昏侯纪》,第150页。 (49)《晋书》卷99《桓玄传》,第2591页。 (50)《晋书》卷85《刘毅传》,第2207页。 (51)《太平御览》卷170《宣州》引《桓玄传》,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26页。 (52)李善等:《六臣注文选》卷22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李善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05页。 (53)《晋书》卷98《桓温传》,第2576页。 (54)《资治通鉴》卷102,第3214页。 (5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神仙传·郭璞传》,第854—855页。 (56)《宋书》卷5《文帝纪》,第100—101页。 (57)《宋书》卷77《沈庆之传》,第2000页。 (58)《南齐书》卷8《和帝纪》,第114页。 (59)《梁书》卷16《王莹传》,第274页。 (60)《宋书》卷77《柳元景传》,第1988—1989页。 (61)《宋书》卷50《垣护之传》,第1450页。 (62)《宋书》卷74《臧质传》,第1919—1920页。 (63)《太平御览》卷170《宣州》引《金陵记》,第826页。 (6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7《南直九》,第1320—1321页。 (65)《晋书》卷100《祖约传》,第2626页。 (66)《南齐书》卷1《高帝纪上》,第7—8页。 (67)《晋书》卷42《王浑传》,第1202页。 (68)《晋书》卷100《苏峻传》,第2629页。 (69)《梁书》卷58《侯景传》,第842页。按,“兵千人”,《南史·侯景传》作“兵八千人”(第1998页)。《资治通鉴》卷161也作“兵八千人”(第4984页)。据此可知,《梁书》的“千人”前脱“八”字。 (70)《隋书》卷52《韩擒虎传》,第1340页。 (71)《南齐书》卷28《刘善明传》,第524页。 (72)《梁书》卷3《武帝纪下》,第70页。 (73)《南史》卷70《郭祖深传》,第1723页。 (74)《南史》卷60《江革传》,第1474页。 (75)《陈书》卷20《华皎传》,第271页。 (76)《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第260页。 (77)《南齐书》卷58《王惠等传史臣曰》,第1018页。 (78)《南齐书》卷32《王琨传》,第578页。 (79)《南齐书》卷55《封延伯传》,第960—961页。 (80)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士民》,《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页。 (81)《魏书》卷32《封懿传及其同族曾孙灵祐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60、764页。 (82)《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25页。 (83)《南齐书》卷27《刘怀珍传》,第499—501页。 (84)《魏书》卷43《刘休宾传》,第964页。 (85)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士民》,《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95页。 (86)《宋书》卷36《州郡志二》,第1099、1093、1098页。 (87)《南齐书》卷28《崔祖思传、刘善明传及史臣曰》,第521、523、532页。笔者按,“淮”字疑为“怀”,音同致误。 (88)《宋书》卷35《州郡志一》,第1038、1053页。 (89)《宋书》卷61《衡阳王刘义季传》,第1655页。 (90)《南史》卷13《衡阳王刘义季传》,第380页。 (91)《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第3166页。 (92)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条,第75、77—78、81页。 (93)《晋书》卷84《庾楷传》,第2187页。 (9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57“南豫为要南雍次之”条,第440页。标签:东晋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南朝论文; 历史论文; 桓温论文; 南史论文; 梁书论文; 荆州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唐朝论文; 东汉论文; 淝水之战论文; 鲜卑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