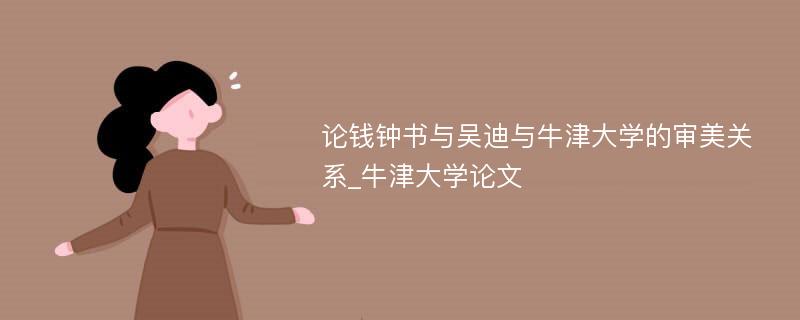
论钱锺书与“吴地”、“牛津大学”的美学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牛津大学论文,美学论文,论钱锺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5)06~0176~07 在中外学术和文化史上,颇不乏这样的名家,他们生前著述等身,但并不为人所知,有一种生前内心的深深寂寞。但也有这样的学术文人,在他们活着时就享受着泰山一样的荣崇,却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地读懂得或者了解他们的作品。大概钱锺书就属于后一种当中又罕有的一位。人们在读钱锺书时,一方面惊叹他汪洋般的知识征引,感觉即便是调动千军万马来在他的著作中抽丝拔线,也很难将其端委理得分明;另一方面,也诧异何以在如此广博的征引中,还能够睿智地传达出自己对中西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学深入透彻的认识。钱锺书就像一部自己锁定了信息元码的百科全书,除非阅读者具备真的进入这一库藏的密钥,否则只能是望洋兴叹有余,品味咂摸不足。然而,如若仅是这一重困惑也便罢了,钱锺书还给后人留下了精彩绝伦的小说和随笔,在那里面渗透着钱氏风格的智慧和幽默,人们读着他的小说和随笔,仿佛自己背后有一副深框黑色眼镜正在端详着自己,不禁有一种高处阅读的春寒,道是料峭,也风流难却!时值今日,对钱锺书学术与文学的阅读和研究,越来越成为人们内心想解开的一道谜。而我若是亦偷一种钱氏智慧来观照钱氏,便能凭地拥有一种观照钱锺书学术与文学的“瞳孔”,在我看来,这便是钱锺书个人经历中,由“吴地”到“牛津大学”所缔结的空间文化心理,似乎他后期所有的学术和创作文字,都与这两地建立的一种微妙的美学关联相关。 一、精神母胎的相似孕育 钱锺书自小受到国学大师钱基博的指导,到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兼通中西的知识结构基础已经完成,其学养、功力之深,连当时已很有名的钱穆也见文叹服,悄焉领受。钱穆《师友杂忆》记述,曾请钱基博为其《国学概论》作序,钱基博慨然答应,很快递交序文,钱穆收文后不易一字用到书里,但他根本没想到,这序是钱锺书代父写的,行文老辣居然没让钱穆看出来,足见钱锺书的学养、功力之深和钱基博知子之深。1935年,钱锺书携新婚的妻子杨绛越洋到了英国,在牛津大学的埃克塞特学院学习。这个新的经历对钱锺书非常重要,它不仅使他的传统文化学养,可以更系统地从西方视野进行观照,而且他在牛津大学读的专业就是文学。而牛津大学又是英国的大学里面出文学家最多的。这里,我们引用一段台湾作家杨牧谈牛津大学的话,可以体会到钱锺书读牛津大学的副博士是多么的重要: 读英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英国历代诗人作家出身康桥大学的特别多,其大名鼎鼎的如史宾塞、马罗、约翰·邓、马服尔、米尔顿、培根、杜雷登、葛莱、华茨华斯、柯律治、拜伦、丁尼生等等,占了全部大作家的一半,其余来自牛津大学(爱得生、史提尔、安诺得、史云鹏、王尔德、霍普金斯、赫思曼、葛列弗士、奥登,以及辍学的琼森博士和被勒令退学的雪莱),都柏林大学(史威夫特最有名),爱丁堡大学(好像只有一个卡莱尔),和伦敦大学(勃朗宁读了一半就自动退学了),当然还有无正式学历的乔叟、莎士比亚、顿普、布雷克、济慈……① 杨牧文章的原题是《我所不知道的康桥》,出于对康桥和徐志摩的偏爱。诗作牛津大学还是他侧重要介绍的,但他括号里列举的牛津大学的作家,却是最多的,说占了英国作家的一半,这个数字比例很大,可以窥见英国文学史的某种真实。而钱锺书来到的正是这样一所大学,这其中的因缘自然非同寻常了。在牛津大学期间,钱锺书和夫人杨绛住在牛津公园路110号,那是一条欧式古老的街道,两边有耸立的哥特式建筑,从寓所出来的街道不远拐入broad street,步入穿拱半空的虹桥,便径直可以去上课或到博德莱安图书馆了。博德莱安图书馆1488年就开始起用,是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在这里曾有许许多多的名作家用过功,钱锺书也在这里享受到欧洲最好的教育条件,得到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文学滋养,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充分条件。 无锡是钱锺书最早接触古典文学,培养他形成独特的气质、个性的地方,后来他就读于美国教会的一所学校,这个学校办在苏州。他在一篇自叙性的文字中提到:“余十六岁时与从弟锺韩自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桃坞中学)返家度暑假,先君适自北京归,会同为文课,乃得知《古文辞类篡》、《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②显见,正是这个时期,他不仅对古典濡染至深,而且对苏州文化也有了较多的接触,这两个地方,都属于东吴之地,但与更东面浙江孙氏祖祠所在地——富阳一带——还有不小的区别,因此我们简称无锡、苏州一带为吴地。把吴地与牛津大学比较,我们发现,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首先,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文化传统悠久。吴地水草莽莽,通巷民居将江南文化和生活的气息扑面送来。牛津大学公园秀美清静,特别是钱锺书常走的虹桥,在上面可以眺望毗邻的街道,浓郁地传达着厚重的历史感和人文气息。其次,吴地和牛津大学都有重智性的思维传统。这种重智性,不是单纯指在科学或学术方面,有很好的基础,而是说在对待生活、人生和感性的艺术、文学等对象方面,都很看重智性的把握。例如,牛津大学出名的那些作家,不论其作品表现得多么生动、感性,骨子里张扬的却是理智和理性,像作家约瑟夫,他因敏锐的批评文字著称,在悲剧《加图》中,塑造了一个和西泽大帝对抗的智者形象;诗人艾略特,他虽然在牛津大学就读时间不长,但他的作品重智性的特点很鲜明,在创作主张上他也反对用诗来表达个性,认为诗是一种客体化的主体对世界的态度;现代诗人奥登,他追随艾略特,有力地推进了他的诗重智性的主张;……这些按理说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但我们还要提一下杨牧说到的史文朋和雪莱。史文朋创作了很多批判基督教和末世堕落的诗歌,雪莱的诗则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那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吧”就是有代表性一种智性表达……总之,重智性,是牛津大学出身的作家、诗人一个共同特点,这种重智性显示了超越自我意识,甚至超越地域和民族意识的价值趋向。而在东方吴地,同样也具有重智性的传统。吴地的重智性,是一种渗透在民俗、生活和历史文化中的智性传统,有着似乎比牛津大学基于文学的价值观而表达的智性还有所不同。在生活、风俗和历史文化传承中,吴地很早就普遍性超越了原始的、素朴形态的民间巫文化,而这在其它甚至是现在都不见得摆脱干净。原因何在,就是因为重智性。重智性是儒家文化的特色,原本吴地属于吴、越、楚交界之地,被儒家文化流行的中原地区视为荆蛮之地,但中国文化有意思的是它受地理空间因素牵制很多,因而发展规律也大不同,比如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对于说明齐鲁文化是很适应的,而荀子也讲“矫枉过正”,这对于说明吴地可谓恰中肯綮,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吴地的仗打得太多,破坏严重,所以到汉代无锡的锡就没有了,都被造武器用完了,而此后吴地就很少战争,魏晋南北朝以后,吴地一直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唐代也有吴越王钱镠的适时归顺而避免了战争,因而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得到很好的保存和传承,这里的人也因此养成重理性,并将之寓于温和而不乏幽默的性情之中。吴地所形成的重智性传统,对于学术文化和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就相对而言,比中国其它地区的更为细致和深入,而在文学方面,这种智性在与隋唐以后的禅意识结合后,更透出超越世俗和虚旷怀古的特点,如唐代诗人常建有这样的名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题破山寺后禅院》);张继题寒山诗的诗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锺声到客船。”(《枫桥夜泊》),这些诗句中“对象客体化”的意识,显示了很高的美学水平,吴地历来文人名流如云,文学流派涌现很多,因此类似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至于学术方面,我们只提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清代著名的经学家惠栋,学问做得就非常好,论理析文绵密无隙,但他不发怪论、狂论,因而显得保守,正反映了与此地重智性又温和性情的文化气质的一致。 从吴地和牛津大学走出的钱锺书,继承并发扬了两个不同空间的文化思维和气质特色,在漫长的学术和创作道路中,凭借着个人的天赋和颖悟能力,将这种相似的气质、传统很好地表现于自己的创造成果,从而形成了具有钱锺书个人特殊标记意义的美学趣味。 二、“微观式集合”的精神结构 钱锺书与吴地和牛津大学的美学关联,首先突出地表现在以一种智性传统来统驭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形成了“立木以造林”、“微观式整合”的思想、精神结构。 钱锺书博通中西,考稽文献,阐释意涵,发掘精神的蜕变,都能做到详备而深刻,此早为学界所共识。藏克和《钱锺书与中国文化精神》一书谈到钱锺书治学善于“打通”,指出钱锺书的学术方法,有着多种“打通”,要之,有学术“类”与“型”,将文学意象与汉语文字学、文化学术的打通、地域学术思想的“打通”等,可谓纵横连贯,气机幽深③,讲得非常有道理。而这在《管锥编》和《谈艺录》得到充分体现。我们以为,所谓打通,藏克和更多强调了经、史、子、集等的学术融会贯通,若就学术研究的路径及方法而言,用“立木以造林”可谓更合适,此用理论味重一点的话来表述,就是“微观式的集合”,“管”与“锥”,管就是树木,扎下去,扎得多了,便成了森林。森林的枝叶连缀一体,集合为学术整体的大观。这种立木以造林的方法、路径与吴地和牛津大学有紧密的美学血缘。从西学逻各斯传统来看,由普遍到特殊,即由形上范畴推衍出体系结构。钱锺书不同,他从“树木”切入,形成一个个读书“心得”,这些“心得”,自由穿梭于中西经典中,有正与反的疏证,有同与异的比鉴,仿佛深海之流,漩涡湍搏,不露痕迹而成涌流。因而,每一“心得”,既是水珠,也是大海;水分子的融渗密合,映射思理的波澜、纹理,这是西方逻各斯推衍的学术体系所难达到的。以钱锺书论“巫”为例,他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拈出“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展开“集合式”讨论,先引述佛经、史传、类书等十余条文,再转入“夫初民之巫即医耳”的评断,继而以二十余条的史传、解诂、类书、集注、诗的引证,对巫医关系及其连类合称加以诠释和证明,形成“医始出巫,巫本行医”的确实看法,再由巫医医药和事神并用,谈及巫医治病的尚鬼虚设、误人颇多,对巫医的非科学本质完成到位的揭示,到此还不够,在再版时又增补资料,进一步评断说:“盖医以不见信,乃至自托巫之容、以售医之术。所覩古书写医绌于巫之状,无剀切如是者。”④这个结论,与最初“视见”之引文形成响应,整个学术讨论的结构,集合了大量的古籍经典,贯穿了真实与虚妄,科学与经验,理智与情感的辨析,却丝毫没有铺摛之感。在钱锺书的学术研究中,类似这样的行文可谓随拾即是,习惯于现代阐释性文本阅读的读者,可能会感到“云雾翻卷”,“金玉闪烁”一片,不像西人那样逻辑化,因而甚至会感到“没有思想”,更甚者,会感到在网络时代,数据搜集已不那么繁难,那么像钱锺书这样萃集式的做学问方式,大概优势不那么明显了。但他们并不知道,学问并无定法,越是学养博瞻的学者,越是善于驾驭细节,而钱锺书无疑是超强的,这与他自小在吴地就得到的古典训练,和在牛津大学通摄了英国式文学智性剖解传统密切相关。学术与文学的结合,是认知与直觉的结合,微观升华到宏观的集合,它使枯燥的学术吐光发丝,缠结为一个涵容理性的直觉整体,这是非常高的学术美学境界。在电子信息化时代,如果不具备像钱锺书那样的学养,以为用计算机集合数据,就可以达到钱锺书那样的成果水平,实在是痴人说梦,因为数据用计算机来搜集、罗列,的确可以做到很充分,键盘一敲,出几万字,甚至上百万、千万字都不难,但内在的魂没有,数据不过是散乱的碎片,怎可与钱锺书的治学同日而语! 三、“智力想象”的创造性格 文化气质与地域性格的血缘联系,似乎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因为前者在被学术文化符号装载之后,就披上了神秘的色彩,似乎学者的修养及其精神个性更多是文化赋予的个人养成,而凡是来自文化的都是普遍的,缺乏个性的。其实,地域性的文化,也包括大学所传承的文化气质和精神取向,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偏爱,面对这种已有的传统,自我天性的选择,倘若与地域性文化传承的气质特别吻合,就能将这种来自外在的潜移默化的偏爱,以一种移植乃至超越移植的方式,在接受传承的自我者那里给予强化,从而,在优秀的地域文化和优秀的大学里,总是涌现出最优秀的人,成为人类文化传统和地域精神的杰出代表和体现者、创造者。 对于钱锺书来说正是这样,“吴地”和“牛津大学”的智性文化传统和地域性格,培养他拥有了非凡的智力想象,他将这种智力想象淋漓尽致地渗透到了学术和创作之中。 学界有观点认为钱锺书首先是一个作家,然后才是学者。我们从钱锺书从吴地到牛津大学,然后又归国,经湘西到上海的经历来看,其实学术和创作在钱锺书这里是相辅相成的,他的创作始终不曾疏离学术,他的学术也始终融合了文学、美学性质的体验与思考,这使他的学术与文学意象形成美学上的浑融关联。理解这一点很重要,特别对于理解钱锺书的小说更显重要。因为在他的小说中,学者的理性溶解了文学想象,仿佛清新的溪流被山石、树木和落英的物质气息给熏染过了,不再是单纯清新、活泼的清流,更是蕴有物质的精神脉流。对此,我用“智力想象”来形容那种流动的精神铸合体。 智力想象与本能想象和情感想象不同。本能想象带有肉体的粗放气息,奔腾骚动,呈向外铺泻的扩张态势,惠特曼、巴尔扎克、哈代、郭沫若、巴金是这样气质的诗人和作家;情感想象则对本能有抑制,注重内心对感受、意绪和情感的咀嚼,且把它们积淀为醇厚的情感浓液,舒缓地加以品尝。因而虽然情感想象也可以升腾和燃烧,但那是内心储备得忧虑、愤怒和爱恋之情能量达到很大,才彻底地爆发了,它与本能想象的瞬间燃烧不属同一个层面,而中外文学史上,像普希金、歌德、狄更斯、高尔华斯绥,还有拜伦、艾青、郁达夫、何其芳等,都是这样气质的诗人、作家。至于智力想象,则属于另外一种类型,这种类型拥有敏锐、深刻的洞察力,能够超常地把控情绪、情感,对外部事物具有对象化、客体化的认知能力,用于文学创作,这种想象更多了一双背后凝眸的眼睛,所有的感受、情感,冥想与思悟,都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下展现。由此缘故,它属于最有智能质量的想象。在中外文学史上,秉有这种想象气质的人不多,譬如同样是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可以算上,巴尔扎克则更冲动一些,不能算在列;同样是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席勒、海涅都理性很强,想象力非凡,因而属于这个类型,歌德则太世俗,乔治桑也情感太浓烈,不能算在内。至于英国的诗人、作家,让我们不无奇怪的,是出自牛津大学的大多具有这种气质。如前面提到的几位,他们都不那么主观,不属于内倾型的诗人、作家,对于社会、人生的认识,他们的作品都达到了时代的深刻认知与批判,起到了对时代精神的引领作用。而且,出身于牛津大学的诗人、作家,在文学形式方面也善于运用诗意来浇铸理性,向世人展现别致而不无怪异的文体、句式。钱锺书和他们一样,也具有这种特点,这大概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结果,但奇怪的是确实有这么一种传承,以致连当下甚受牛津大学青睐的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北岛,也属于这种类型的智力想象的杰出创造者。 牛津大学的智力想象库库藏深厚,它滋养、启动、催化了钱锺书的文学创作意识,尽管这种意识实际表现已经是多年之后,但钱锺书重新回到吴地,又将从小在吴地孕育的智力想象雏形,与牛津大学熏染、升华了的智力想象迭合了起来。美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叫“直觉即表现”,其核心是强调审美经验的形成是关键,至于直觉的外化、赋形并不困难。吴地的理趣、智慧,与牛津大学学到的重智性的思维传统,都促成钱锺书秉具了独特的创作潜能与智慧素质。 钱锺书的“智力想象”在《围城》中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围城》作于上世纪45、46年,首版于1947年,距牛津大学留学约十年之后,期间他辗转湘西、困陷上海,“在人生边上”体验生命和学术,文学想象和美学意识都磨砺到精纯境界。刘中国《钱锺书:20世纪的人文悲歌》引钱锺书的旧友徐燕谋和郑朝宗谈论《围城》的两段话,徐说:“《围城》一书虽成于沪,而构思布局实在湘西穷山中。”郑说:《围城》是创作欲望的“激愤情绪下产生的”⑤。两位旧友的忆述表明《围城》的产出砥砺多年,但为什么会在毗邻吴地的上海“槐聚”之时,才把这本书写出来,此前却没有,显然与重温吴地气息密切相关。一旦吴地又能真真切切触摸到、感受到,钱锺书所有的学识、经验便被调动起来,使他的“智力想象”一下子找到了“喷发口”,因此,《围城》可以说是人生智性观照与学术、审美想象的完美联姻。《围城》鲜活而充分地记录了气质涵养和美学追求。在小说中,他写的每一个人,都不完美,似乎他们都沾溉了民族性格里的善良、韧性,似乎都拥有自我的生存心机与情怀,然而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类人,在钱锺书笔下,都有着不同于其它类型人特殊的“精明”标记,例如,貌似精明而实则难拔情痴与善良的方鸿渐,貌似迂腐又精明赛猴的李梅亭,还有貌似精明聪慧,实际上甘愿以肝肠之断来维护纯粹爱情的唐晓芙,而貌似糊涂的赵辛楣拥有大智慧的精明,还有貌似憨笨,却很精明地经营了自己婚姻的孙柔嘉……这些人物身上的精明,折射出作者对人性和命运的审视,它通过自我、自我与他人精神世界的反差对比,深刻地揭示出动荡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本质。 四、“批判性幽默”的美学旨趣 钱锺书得益于吴地和牛津大学的又一个方面,是他在研究与创作中表现出的批判性幽默。从吴地的影响来看,理性的精明转化为学术和创作意识,对形成批判意识特别重要。而论及精明,无锡人比苏州人还胜一筹。历来所谓“小无锡”的称呼,就指无锡人的精明而言。虽然这个称呼也不无贬义,如精明到有失较真和尖刻,但褒扬之意占了主导。在现实生活中,精明依人的性情而有不同表现,涵养好的,辅以学识的儒雅渊博,就会养成“绵里藏针”的功夫,化针砭于无形,通对立为达观,置妨害于戒律。而对于钱锺书来说,形成这种修养可谓水到渠成。一旦到了把后天的学养和环境、传统造就于人的气质、性情等很好的融合,幽默的智慧就不唤自来,而钱锺书的幽默正是基于学识和理性的淬火,在文学作品中,甚至在学术中转化为批判式幽默的。相比之下,出自牛津大学的那些名作家和诗人,由于缺少东方文化的重整体、重意象的涵咏,反而在批判方面或许很有力量,但幽默感相对要逊色很多。究其原因,语言的逻各斯要求明晰和准确,幽默成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借助意象与直觉的包裹,但在逻各斯语言层面这种东西不易伫留,除非是作家本人能以外在审视的智能,缓减对对象的直接否定,但这样得来的幽默,依然比基于东方智能所形成的幽默感要差一些。以奥登、王尔德、雪莱等人为例,他们的批判意识都表达得十分显豁,并且也有一定的幽默感体现于价值观与世俗社会的冲突方面,但并没有与文学意象、形式形成美学上的统一感。在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中,道林让拥有了一幅画家专门写照其灵魂的画像,他经常私下拿出画像来欣赏自己的青春美貌,却在实际生活中腐化堕落,纵欲无度,结果当生活中的他越来越放纵,为所欲为到要杀人犯罪的时候,画像中的他反而变得丑陋不堪,衰老得不可目睹。这通过两相对照,颇能让人们产生“自作恶,受其果”的快感,并对道林美貌的转为衰丑产生幽默快感。但这样的幽默不耐咀嚼,画像对灵魂的写照基于艺术唯美的象征观念,属于本体性预置的一种价值判定,理性的表达过于显露,限定得过于明确,使美貌与善,丑陋与恶的对应距离拉得过近,呈直线性契合,回旋余地过小,从而批判意识虽凸显了,幽默感却不能充分发散出来。而钱锺书的幽默就不同,他特别擅长用东方的文字、意象来过滤批判意识。当一个人物、事件被描写时,他的言语、行为及由此奠定的整体形象,无不闪现着幽默的光彩。譬如方鸿渐给唐晓芙写信,对用什么称呼反复考虑,一下子把留过洋的酸劲儿和本性上的质朴,情感上的那种欲亲近又有策略性的考虑,都渲染了出来,末了还将话语向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延伸,进一步用喻像包裹“幽默”,显示出方鸿渐作为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清醒和对自我无奈的自嘲:“他深知自己写的英文富有英国人言论自由和美国人宣言独立的精神,不受文法拘束的,不然真想仗外国文来跟唐小姐亲爱,正像政治犯躲在外国租界里活动。”再譬如方鸿渐与孙柔嘉关于“鲨鱼嘴”吃掉“大船”的对话和赵辛楣向方占穿他会被孙“塞到牙缝”里的提醒,都十分有趣,耐人寻味。在小说中这样有幽默感的对话和细节,可以说无处不在,这样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个人物都有鼻有眼的,举手投足,活灵活现,但同时又让我们时时都能看到他们的弱点与缺陷,并在感情上对他们产生美感“同情心”。 钱锺书用文字和意象过滤批判意识,并没有淡化批判力量,反而在“微观的集合”中强化了整体形象的批判力度。因此,就《围城》而言,他让我们看到柔嘉不柔,结婚后露出了“刁钻”的本来面目;辛楣不辣,是一位真正需要时就能出手相助的“仁者”;鸿渐没有大的前程,一路走来就是一个倒霉蛋……只有唐晓芙,它的美学意象是一个闪退的象征,与方的相遇如此短促,误会带来的遗憾又如此之深,别添一种美是“抓不住的”的洞观实相的幽默感。 对于学术研究中幽默智慧所闪现的批判意识,限于篇幅我们不拟展开讨论,但我们从钱锺书对每一个问题点的梳证、评断和大量文献的参引,都可以在逻辑上曲折有致地体味到作者意味悠长的智能,他每每把涵义对立的文字引入同题,使看似枯瘪的经、史、子类文字符串连成思维意象,再辅以集类喻象的“调味”加以中和或定型,让那些引用的证例仿佛树木矗立起来,葱葱茏茏地呈现出森林的苍郁和摇动之美,这种美有力地把陈腐的意识、错误的观念,不屑地覆盖在下面,这正是学术性批判意识达到的美学效果。因此,读钱锺书的学术文本,须以如此美学态度进入,不奢求对整个森林的体系性把握,得其一花一木,便况味绵远,再由此及彼,涵咏沉淀,形成对中国古代文化宏观性的整体把握。而若是试图以逻辑切入方式,一开始便要抓住钱锺书学术的核心意图,恐怕多半要空手而返,因为学问是人家的,不读那么多书,没有经过学术上的涵养积淀,是不可能体会到其中的褶皱的,这也恰是钱锺书学术的美学旨趣所在。但这样讲,只是从发掘和充分体味钱锺书学术旨趣及其对文化精神的提炼而言的,若就学术研究的具体逻辑而言,则剖题拾珠,聚槐观花,聚焦于相关论题的精髓论证与阐述,自能得到一番收获。大体说来,钱锺书的学术因其美学意义上的深邃和婉曲,使研究者面对他也面临着诸般风险,特别是在他对传统的批判方面,每每通过对不同体类文化形态的串连式疏解,节节相贯地推移其深厚的蕴籍,研究者从其每个选题的链条,截一段则可能遗漏其余重要的节段,何况还有反证、对证和否证等种种分别,这还不算,还有破与立往往是互训的,彼此相映成理、成趣,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上不同选目、选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其网络的结点呈放射状展开,所以,若要一下子把握其所有的关联,掌握其精髓,风险自然是非常之大,而这也正应了钱锺书自己的字号,“默存”于心,淡泊于名,文有限而意蕴深远无限。 注释: ①杨牧:《柏克莱精神》,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90年,第104页。 ②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46页。 ③藏克和:《钱锺书与中国文化精神》,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 ④钱锺书:《管锥编》(补订重排本),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554页。 ⑤刘中国:《钱锺书:20世纪的人文悲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第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