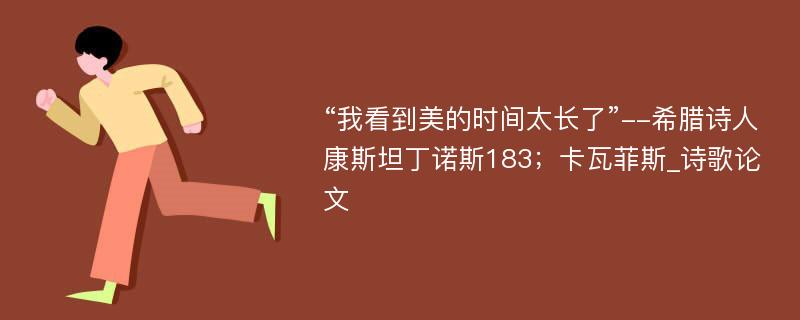
“我对着美看得太久”——读希腊诗人康斯坦丁诺斯#183;卡瓦菲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对着论文,看得论文,太久论文,诺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45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2-5529(2007)03-0033-06
在人类的语言符码中,隐喻绝非仅是一种修辞手段,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意味着人对自己存在的诗性发现,既是人对世界加以符号化的过程,又是人超越自然、超越自身的精神努力。而从更广泛的涵义上说,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本身便是人对世界作出的一个隐喻。正如当代中国一位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隐喻在人类的精神存在中,牢牢地保留着人与自然的原始关联。隐喻以此种方式包藏着诗、美和真理。诗是以隐喻为基础的。”“隐喻不仅是诗的根基,也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根基。”(耿占春:5)由此可见,隐喻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它们为诗歌的蕴藉、深邃、丰富与复杂架设了众多隐秘的路径。尤其近代以来,隐喻几乎已成了浪漫主义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元素之一。
可是,19世纪末走上诗坛的卡瓦菲斯却自觉地走上了一条放弃修辞隐喻和语法隐喻的书写道路。这位被埃利蒂斯认为与艾略特“并驾齐驱”的希腊现代诗人在诗中基本不使用隐喻和意象,而是遵循最基本的语言表达方式,自觉地挖掘词与句在沟通和交流过程中的原生态,也很少使用形容词与感叹词,力求回到语言的原初意义上从事创作。例如,他描写一扇“窗”:
在这度日如年的黑屋里,
我走来走去,希望能找到
几扇窗子。哪怕只开一个窗子
也该是不小的安慰。
但窗子并不存在,或者只是我没有看见
它们。看不见也许更好。
也许到头来,光只是另一种暴政。
谁知道会有什么新的事情败露出来。
全诗通篇使用的都是描写和铺陈的语言,诗歌惯常的抒情被还原到小说式的叙事性,体现了直白和明晰的特征。这种明晰性恰好建造了一间理解的“黑屋”,以“看不见”来见证更大的“光”,接下来的“也许”则像一个小孔,隐约透露着“光是另一种暴政”的说辞。显然,卡瓦菲斯的写作带有某种现象学的意味。现象学的口号就是“面对实事本身”。“现象”的本义就是显现出来的“物”,而“物本身”的现象学理解就是世界本身,而非传统哲学所理解的现象背后另外存在着的本体或本质。现象学的重要方法便是“还原”,而所谓的“还原”包含了“悬置”、“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三个步骤。通过这三个步骤,抛弃一切先入之见,把认识重新集中到纯粹的原意识领域,抵达认识的客观和始源,重新找回真实的实在性、具体性。这一方法与卡瓦菲斯“返璞归真”的诗歌理念非常吻合。
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中国诗人也曾经发出了“拒绝隐喻”的呼声,他觉得:“隐喻后依赖于历史,它具有文化专制主义的一切功用。它是强迫的、权力的,它强制读者接受那些‘喻体’。……它是生活在一个以集体无意识为基础的‘相似性’世界中的读者们的‘快乐文本’。它的垂直性和封闭性导致奴性的读者。”(于坚:309-10)作者觉得,由于文化的积淀使得诗人无法在一个词本来的命名意义上来使用它,因此,他希望抛弃一切文化的束缚,摆脱语言的惯性,回到口语、回到人的日常性中,倡导一种具体的、片断的、细节的、档案式的写作,企冀在“零”的起点上重建一个崭新的诗歌世界。
那么,诗人拒绝了隐喻和明喻后如何从事写作,这种写作会在何种可能性里营造诗的意蕴,又会在多大程度上损害诗歌的抒情性?这无疑是诗歌美学的一次冒险。如前所述,语言的存在,便是人的存在一个最根本的隐喻。放弃语言的隐喻性,意味着诗人必须完成一项审美还原的工作,他面临的是近乎上帝在虚无中创造世界一般的巨大困难。那么,卡瓦菲斯在这条实验之路上又能走得多远呢?
遗世独立的卡瓦菲斯在诗歌作品里极少涉及风景,给人的印象是仿佛他对大自然的山川万物向来熟视无睹。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即便在一首题为《清晨的大海》的“疑似风景诗”中也不例外:
让我在这里停下。让我也看看大自然。
清晨的大海,无云的天空那明媚的蓝色,
金黄的海岸;全都那样可爱,
全都沐浴在光里。
让我站在这里。让我假装我看见了这一切,
(其实在刚刚停步的一刻,我真的看见了)
而不是我在这里做过的那些白日梦,
不是我的记忆,也不是那些肉欲的想像。
在这首诗中,没有比喻、没有意象,也没有渲染,只是像一个被美丽的大海所震撼的旅人在喃喃自语。不过,第二节的后半截“让我假装我看见了这一切”是一个极富深意的句子,看似漫不经心,却折射着语言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作者把描述的现实带入了怀疑的场域,指出语言在敞开的同时,也宿命地存在着屏蔽的功能,它在表达真实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歪曲着真实。有此识见,卡瓦菲斯便在使用了极简单的形容词以后,以否定句来肯定自己的“大海”,对浪漫主义的“白日梦”、失真的“记忆”和“肉欲的想像”予以清除,恢复其“真的看见”。
卡瓦菲斯对自然风景“无动于衷”,却对历史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远古的神话和传说。浏览他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用典之多在现代诗人中恐怕无出其右。这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出生背景。1863年,卡瓦菲斯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父母是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少年时代,卡瓦菲斯曾求学于英国伦敦。十六岁时返回亚历山大。不久,随母亲去君士坦丁堡居住了三年,而后又重返亚历山大城。此后,除了因病到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希腊做短期旅行之外,他都一直居住在该城市。诗人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供职于当地公共工程部的水利局,直至1922年退休。期间,他偶尔也从事股票交易以补贴家用。卡瓦菲斯生前不曾正式出版过任何诗集,作品也极少在公开刊物上发表。
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所居住的城市亚历山大曾经是埃及文化与希腊文化冲撞、交错和混融的一个重要空间。公元前305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部将托勒密占领了埃及,随后自立为王,从而开创了埃及历史上的托勒密王朝时期。鼎盛时期的托勒密王朝包括埃及本土、地中海的一些岛屿、小亚细亚一部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一些地区。托勒密一世在位时即鼓励文化事业,发展工商业,在埃及推行希腊化。首都亚历山大城内矗立着著名的亚历山大灯塔、世界一流的图书馆和地中海沿岸遐迩闻名的医学院等重要建筑。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等著名学者都曾经慕名来此从事研究。除文学、艺术、哲学和历史以外,数学、力学、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也在当时居于世界的领先水平。可以说,它是当时世界文化和商业的中心之一。与灿烂的文明相伴随,亚历山大城的享乐主义风气也首屈一指,其骄奢、绮靡和颓废的程度令世人瞩目,以至于让罗马派来的使臣乍见之下大为震惊,留下了“亚历山大城是爱神阿佛洛狄忒之宫,其中万事皆备……”的文字。公元前30年,罗马大军攻入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七世自杀身亡。托勒密王朝随之灭亡。繁华的亚历山大也在战火中毁于一旦,昔日的辉煌仅留下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和地址。
希腊的血统和亚历山大的出生地,对卡瓦菲斯的心灵引发的是一种特殊的东方主义想像,一种骄傲与伤感、光荣与耻辱并存的感受。《托勒密王朝的荣耀》一诗指示的也就是那一段历史。诗中,卡瓦菲斯借“拉吉底斯王”之口,大加赞颂一个崇尚物质和肉体欢乐的强大帝国,恣意炫耀权力和财富给他带来的快乐和名声。但是,接下来他话锋一转,一语道破使托勒密王朝光耀千秋的秘密:不是由于它发达的商业和高筑的城邦,而是因为在亚历山大城有一位名叫克利奥帕特拉的“泛希腊世界的女王”,有“最辉煌的一代宗师”,并且汇聚了众多的知识与艺术的天才。这样,对一个王朝的凭吊被巧妙地融入了关于历史的思考。
卡瓦菲斯自称是“历史诗人”,确然与诗人渴望还原历史的雄心有关。但考察他作品中的“历史”,它们更多地诞生于作者的想像,其艺术成分显然大于事实或科学的成分。作者关注的并非历史的那些宏大场景,也不是著名的历史人物的传奇,而是历史的细节、局部,甚至缩微到一个点,或者说他更关心历史中的个人,以及个人生涯的某一个特殊的生活片断。佚事和趣闻更能触发他的灵感,他通过对历史的考古式修复,挖掘散居在历史残砖与断瓦缝隙处的诗意。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区别于伟大的荷马,从而体现了一个现代诗人的历史观。
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率军进攻希腊,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分水陆两路沿色雷斯西进,迅速占领北希腊,南下逼近德摩比利隘口。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希腊联军约七千人,率先扼守地势险要的温泉关。温泉关是从希腊北部南下的唯一通道,其关口极其狭窄,仅能容一辆战车通过,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波斯军队连续发动进攻,但因地势险恶,收效甚微。但两天后,在叛徒的帮助下,薛西斯的一支部队趁夜沿着迂回的山间小道插到了希腊人的后方。列奥尼达获悉这一情况后,命令各盟军队伍向雅典撤退,本人则和三百名士兵一起留守山口。他们四面受敌,最后在白刃格斗中全部阵亡。
关于希波战争中的这次战役,当时和稍后的不少诗人都写有献诗,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摩尼德斯的《温泉关铭文》:
陌生人,请给斯巴达人捎个口信:
我们长眠于此,遵守着他们的训令。
这首诗简洁,除了为勇士们建立了一座超越时空的纪念碑以外,也为自己赢得了不朽的荣誉。
卡瓦菲斯的《温泉关》则在西摩尼德斯等人之外另辟蹊径,并不从以往人们称颂的“勇敢”、“坚毅”等品质切入,而是着眼于温泉关勇士们日常生活的信念。这些古老的勇士坚持“在所有事情上始终如一,恪守公义”,“同时又体现出同情与怜悯”,“慷慨于点滴之间”。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自己一辈子只讲真话,却并不憎恨那些背信弃义的人,从而显示了平凡中的高贵和世俗间的忠直。死亡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他们走向永恒的一个出口。他们肉体的被消灭恰恰反证着人性和真理的胜利。
卡瓦菲斯对典故的特殊癖好令人想起中国宋代的黄庭坚。这位江西诗派的创始人在给朋友的一封书简中写道:“老杜做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黄庭坚:316)为贯彻自己“点铁成金”的诗歌写作理念,黄庭坚发明了“换骨夺胎”法。所谓“换骨”,就是借鉴古人的诗意,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至于“夺胎”法,大体上就是点窜古人的诗句,在相近的词句之重新排列中表达与之不尽相似的含意。依循这一写作理念,他搜猎奇书,掇拾异闻,在佛经、语录、小说等杂书中寻找生僻的典故、稀见的字词,有时甚至违背通常的诗词格律,不惜用拗句、押险韵、造硬语,在反常性里挖掘诗意,以“拗体”自成一格。黄庭坚的理论和实践深为同时代诗人和后世诗人赞同,在他身后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宗派——江西诗派,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其影响。该派的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诸诗人。
与黄庭坚相似,卡瓦菲斯的不少作品所使用的也是“换骨夺胎”法。根据《马太福音》记载,莎乐美受母亲希罗底的唆使,设计杀死了施洗的约翰。在圣经中,它叙述的只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为布道作出牺牲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所蕴含的艺术元素却远不止于此。它那潜在的衍生性、辐射性不断地成为后世很多诗人和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原型。著名画家卡拉瓦乔、莫罗、克里姆特、亨利·勒尼奥都曾经以莎乐美为题画出了自己的杰作。海涅、福楼拜和马拉美等分别以此为题材写过诗歌和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爱尔兰诗人王尔德创作的一出独幕剧。比亚兹莱为该剧本所作的插图则更突出了莎乐美身上骄蛮、妖艳、肉感、邪魅的特征。后来,理查·施特劳斯以王尔德的作品为蓝本创作了歌剧《莎乐美》,借助音符使莎乐美这个艺术形象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流传。
莎乐美的故事在19世纪末已基本定型。她是古巴比伦国王希律的继女。在巴比伦的神庙里,她得到了一个神谕:“世界上只有两种感情能把人永恒地联系在一起,要么是爱,要么是恨。如果他不能爱你,那么就让他恨你吧。”某个偶然的契机,莎乐美对施洗的约翰一见钟情,渴望能够得到他的一个亲吻。但约翰却高傲地拒绝了莎乐美的请求。不久,在希律王的一次生日宴会上,他要求莎乐美为自己跳舞,并承诺可以答应她的任何要求,哪怕是自己的半壁江山也在所不惜。而此刻的莎乐美则由对约翰的示爱被拒绝而滋生了极端的仇恨,绝望的怒火让她成为了一个“复仇女神”。于是,她在希律王面前跳起了著名的七纱舞,这段舞跳得美妙绝伦,令希律王心旌神摇,魂飞九天。舞毕,莎乐美提出了割掉约翰的人头的要求。最终,希律王被迫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莎乐美亲吻着心上人失去了生命的嘴唇,发出了“爱之神秘远比死之神秘更神秘呵。爱才是唯一应该考虑的”,“人们说爱情有一种苦味……不过那又怎么样?”(王尔德:376)的感叹,被约翰的追随者们以盾牌击杀。
《莎乐美》一诗则从传说故事的结尾处展开,卡瓦菲斯虚构了一个热衷于思考诡辩论哲学的青年智者,并让莎乐美爱上了他,进一步说明莎乐美之所以砍掉约翰的头颅,目的只是为了取悦这位“智者”。可是,这位习惯了智力游戏的智者对莎乐美的感情无动于衷,并对她开了一个玩笑,“我更希望带来的是你自己的人头”。结果,信以为真的莎乐美在第二天居然真的砍下了自己的头颅,派仆人给他送去。可惜,这名智者早已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诗人的描写在此冷静到了残酷的境地:
他看到滴下来的血,觉得恶心
他令人把这个血淋淋的东西
从他的眼前拿开,然后继续钻研
柏拉图的对话录。
一个“继续钻研”把他内心的冷漠,或者说冷酷极其生动地摹写了出来。诗人捕捉了一个情感和理性的死结,以极端化的方式来状写一种反常的心理,进而抨击异化了的人生,对极端理性的反生命特征予以揭露。如果说莎乐美炽烈的情感像脱缰的野马那样无法控制,最终不惜用死亡来攫取情人冰冷的嘴唇和亲吻,那么,这名“对爱无动于衷”的“年轻智者”,恰恰从相反的一面,证明了极端理性的疯狂。表面上看,年轻智者绝对不会像莎乐美那样为爱情丧失理智,但他的冷酷无情揭示出,在摒除了情感以后,技术理性至上的人无论做什么,都会像怪眼的墨杜莎一样,令它的目光接触到的一切事物变成冰冷的石头。
如果说关于历史和神话的爱情诗歌为卡瓦菲斯戴上了一个模糊的面具,使作者的主观动机隐匿在客观化的描叙中,那么,涉及他个人隐私的那部分爱情诗则要求他摘下面具,赤裸裸地呈现自己,袒露诗人最具个性特征的那部分灵魂。考察卡瓦菲斯的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依然留有克制、客观 (或者说模拟客观)、理性的特征,但直白的描述却使欲望以更灼热的方式膨胀着,甚至略微夸大了感官的刺激,带有暧昧的情色意味。这自然令人联想到他的同性恋经历。或许正是这种非常态的性取向使诗人在道德上天然地拥有叛逆的支点,为他语言上的惊世骇俗编制了一份独特的词汇表。
在《伊梅诺斯》中,卡瓦菲斯借用信札的口吻表述:“更应该珍惜的是通过病态而腐朽的方式获得的快感”,因为,“它偶然地揭示,肉体能感知它到底需要什么”,那种方式“能制造通过健康的性取向无法产生的色情强度”。另外两首抒情诗《在那座房屋外》和《进来安睡》描述的是情欲的诱惑,前者以“漫步”故地的场景催生往日情爱的回忆,赋予“店铺”、“人行道”、“石板”、“墙壁”、“阳台”和“窗子”等物以爱欲的意味,让它们在爱的魔力下闪烁异样的美丽。后者描述的是一则热烈的情欲事件——“肉体的欢乐在两件敞开的衬衫之间展开”。这里,我们遇见了卡瓦菲斯诗中罕见的一个比喻:
那是迅速绽放的肉体,像一个梦
翻越二十六个岁月
来到这首诗中安睡。
这里,卡瓦菲斯让他的创作不由自主地回到了抒情的起点。可以说,在叙事的悬崖边,抒情为他架设了一座跨越天险的桥梁。在这首诗中,抒情与叙事被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而由“像……”牵起的明喻获得了隐喻的意向性。诗歌在美的熏染下摆脱了世俗道德的羁囿,而在想像的烛照下,放纵的欲望获得了思想的过滤,喧嚣的现实被引向了精神的安宁,历史作为现实融进了生活,恰似法国作家尤瑟纳尔对他的评价:“肉体的模糊回忆使艺术家成为时间的主人;他对肉欲体验的忠实最终引向一种永恒。”(尤瑟纳尔:322)
综观卡瓦菲斯的整个创作,可以得知,诗人对隐喻的拒绝,实际只是一个策略而已,如果将它推到极端,无异于彻底取消诗歌、取消我们的语言。就骨子里而言,卡瓦菲斯是一名抒情气质极为浓厚的诗人,但是,他在创作中有意地压抑了它们,以理性、冷静和客观的姿态来从事自己热爱的诗歌写作,令情感在反弹中产生了更大的能量,从而获得了理性与激情相互交融、相互提升的美学效果。他的独特魅力也在于此。因此,必须指出的是,卡瓦菲斯的诗歌道路实际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陷阱,如果无视其抒情的底色,一味去模仿那些叙事意味浓厚的作品,极有可能把诗歌的亚元素夸大成基本元素而误入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