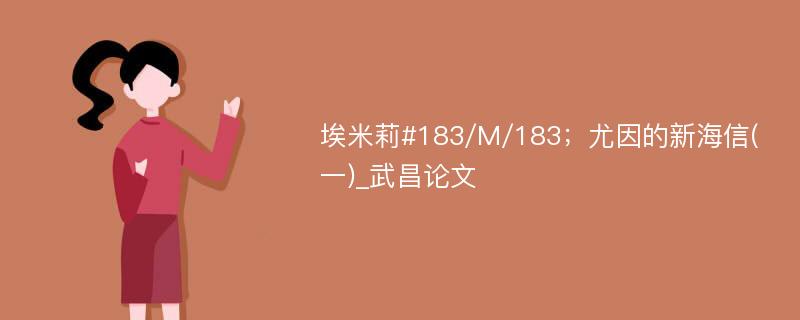
埃米莉#183;M#183;尤因斯的《辛亥家书》(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书论文,尤因论文,埃米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题记
2000年春,我在英国剑桥与几位清末民初英国入华传教士的后代的接触中,获得英国人华女传教士埃米莉·M·尤因斯(Emily Marry Ewins)的《辛亥家书》(注:英文全称:Letters Home from Emily M.Ewins--An on the spot record of revolutionary events in Hangkowand Wuchang,Central China,1911-1912,按字义译为:《埃米莉·M·尤因斯家书——1911-1912中国武昌汉口革命事件的现场记录》。),由尤因斯的长子H·M·拉滕伯里(H.Morley Rattenbury)于1989年12月编辑作注成册,共辑录尤因斯从中国汉口、武昌英国租界循道会(Wesleyan Mission)发回英国的八封家书,分别写成于1911年10月15日、10月17日、10月29日、11月9日、11月19日、11月26日、12月10日和1912年11月3日。前七封家书是尤因斯在辛亥革命爆发期间(内容所述的时间起始于1911年10月2日,迄止于12月10日)、在辛亥革命爆发地(武昌与汉口)的所见所闻所历。第八封信写于1912年11月3日,内容则是对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周年纪念日的追忆。
尤因斯其人,未见载于任何人物工具书,仅在H.M.拉滕伯里撰写的私著《拉特—赖梅——一家四代五牧师详传》(注:H.M.拉滕伯里,《拉特—赖梅——一家四代五牧师详传》(未标印刷年份)(H.MorleyRattenbury,Rat-Rhyme:A Screed Recording the lives of fivemembers of onefamily who in four generations were all Methodist Ministers)第21-28页。)中有关其丈夫H.B.拉滕伯里的传记里有些述及。尤因斯,英国布里斯托尔港市人,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入华的英国循道会(注:循道会(Welseyan Missionary Society),英国教会组织。总部设在英国伦敦(Wesleyan Centenary Hall,17 Bishopsgate St.Within,London,E.C),1852年入华,布道区为两广两湖地区,1907年统计有41位男教士、34位女教士,中国信徒3449人。参见D·麦吉利夫雷主编:《中国新教徒教会百年——百年庆典历史卷》,上海,美国长老会出版社,1907年,第89页。[D.MacGillivray (Ed.),A Century Of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Shanghai:Printed at theAmerican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p.89.])女传教士,主要从事教会医院的护理工作。辛亥革命爆发期间,在滞留武昌、汉口的英国传教士中,尤因斯是为数不多的女传教士之一。她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用家书的形式记载了她所经历的辛亥革命过程。在辛亥革命一周年纪念活动庆典现场,尤因斯是被邀请而赴会的十一位外宾中的两位女性之一。
尤因斯是H.B.拉滕伯里(Harold Burgoyne Rattenbury)的第二任妻子(她在第四封、第七封和第八封家书中,提及了H.B.拉滕伯里)。除了《拉特—赖梅——一家四代五牧师详传》中的传记外,H.B.拉滕伯里也未见载于其他人物工具书。H.B.拉滕伯里生于1878年,1902年被循道会委职派往中国湖北传教,直至1934年被召回英国总部,死于196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H.B.拉滕伯里的第一任夫人布鲁尔(Edith Brewer)和两个孩子被疏散到上海,1912年全家团圆,但1912年11月布鲁尔在分娩第三个孩子时死亡。
尤因斯是于1914年嫁给丧妻未及两年的H.B.拉滕伯里的,因此,她的《辛亥家书》一直由其姐姐希尔达(Hilda)保存着。20世纪80年代,H.M.拉滕伯里从其娘姨希尔达的女儿里格利(Barbara Wrigley)手中获得母亲的《辛亥家书》,并于1989年编辑、作注、打印、装订成册,分发给亲朋好友共享,而将原件(包括H.B.拉滕伯里的信件)保存在曼彻斯特大学的赖兰兹图书馆(Rylands Library at Manchester University)。经辗转联系,笔者最终从居住在康福斯市(Carnforth)的H.M.拉滕伯里处获得了对《辛亥家书》的利用和引用权(注:《辛亥家书》的编者拉滕伯里(H.Morley Rattenbury)于2000年9月6日给我一个亲笔简笺,全文如下:“我已经准许维民利用和引用我母亲(尤因斯)于1911至1912年发自中国的信件,这些信件目前已存放在曼彻斯特大学的赖兰兹图书馆。拉滕伯里(遗嘱执行人)2000年9月6日。”("Weimin has mypermission to use and quote from my mother's (Emily Ewins)letters from China 1911-12 now lodged in the Rylands Libraryat Manchester University.H.M.Rattenbury (Executor),Dated:September6,2000."))。
《辛亥家书》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辛亥革命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作者以旁观者的身份,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在辛亥革命爆发期间所见所闻的一些具体细节,可以补现有资料之不足。2.《辛亥家书》中所涉及的多位英国循道会传教士,均名不见经传,故成为英国来华传教士研究的新资料。3.西方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态度与涉入的过程,均在《辛亥家书》的字里行间隐约显现,为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资料。4.《辛亥家书》中所记录的一些细节,为寻找新史料提供了线索。
现将《辛亥家书》的八封家书全部译出,除第一封由我译外,第二至第八封均由沈昌洪译,最后由我通稿、校注。原注为尤因斯长子H.M.拉滕伯里所作。文中英文人名的中译以《英语姓名译名手册》(注:新华通讯社译名资料组编,《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为准,第一次出现时,括注英文原名。文中所述的星期某日,均在每段第一次出现时括注某月某日。
(阙维民)
家书一
亲爱的家人们:
我想你们一定会为远在他乡的我们感到焦虑,因为家书告诉你们的事件将足以使你们焦虑。我将往家发此信,此信已在Brecknock大街4号(注:Brecknock大街4号,是凯特(Kate)姨妈的地址,显然也是埃米莉和其他人的“家”。)被传阅过,希望你们能转递给希尔达(Hilda),并请她将此信给我在学院的朋友们传阅。
我想从头讲起,告诉你们我所经历的一切。上周我将帕特(Pat)和皮洛(Pillow)小姐生病的情况告诉了希尔达,而贝尔(Bell)也在武昌刚从疟疾的肆虐中挺了过来。所有病号都已康复,但随着我的疲劳之极,便决定与贝尔一起回汉口度周末。因此,上星期五(10月6日)我就打点简装,渡汉江抵达汉口。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我仅带着一两件白色单薄衣衫,身着外套和黑裙。我本打算于星期一(10月9日)返回,但抵达汉口后,我很想卧床休息一二天。我的确没有想得更多,因为我实在太疲倦了,只想休息。正因为如此,我没有看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武昌的一切骚动。大家知道,武昌是湖北省首府,军队的司令部所在地。驻扎着许多部队,他们均由德国和日本的外籍教官训练。由于满汉之间的种族反感情结,多年来中国已产生了大量的不满情绪。汉人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一直居住在中国,却在几百年前被满人所征服。现在满清皇帝仍然在位,所有中国的主要官员均是满人,他们欺凌汉人,残酷压制汉人,一切法规条令对满人之利要远优于汉人。然而,汉人最后决心不再忍受,长期以来,他们一次一次地努力,以求在政府中获得更多的席位。上星期一(10月2日),整个汉口都被下列消息震惊:警方获悉在汉口俄国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存有一些炸弹,还有一份革命党进攻武昌的计划。当警方前往搜查时,该幢房子已人去楼空,根据情报,所有造反者都到了武昌。因此,警方渡江前往武昌,关闭城门,全城搜捕。警方逮捕了30名造反者并就地处决。所有人都认为事情将就此罢休,但恰恰相反。星期二(10月10日)晚,武昌的许多士兵起义。整个夜晚,武昌城都处于混乱之中,到处都是枪声。在我们所住的院子周围,枪声似乎更为激烈。我们紧挨着军营,士兵射出的子弹在我们房屋的上方呼啸而过,一发炮弹打中了医院,但没有造成进一步破坏。夜晚,三十名忠于政府的士兵到我们院子里避难,其中一名士兵一大清早就派到我们这里购买白布供需品。因为一条白布绑扎在臂上就是革命党人的标志,所以他带着白布回去后,每个人都在臂上扎了一条,然后穿后门而出。他们前脚刚刚离开,一队造反者后脚就进院搜查,他们将一挺机枪架在大门前以防万一。星期三(10月11日)整整一天,武昌城都处于这样的极度恐怖状态,汉人士兵穿越于城镇里弄,凡是满人见者格杀勿论,所有士兵都成了造反者,但未伤及外国人。然而,我们的院子恰在枪炮射线之内,住在那里并不安全。医院的所有病人都被清撤回家,护士们也都撤离医院。阿伦(Allan)先生一家打算出城,但政府当局不允许他们出去,并向他保证他和他的家人都相当安全。但是阿伦夫妇仍然十分害怕,所以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离开武昌。因此,阿伦夫妇及其孩子帕特(Pat)和皮洛(Pillow)小姐决定从城墙上用吊篮外逃,由我们的厨师和医院的厨师将他们往下吊到城外。城墙垂直到地面距离为四十英尺,两位厨师的手掌被吊绳磨擦得鲜血淋淋,但他们仍然坚持到所有人都逃出城外为止。一行人出城后就到了我们的高级中学大院,该大院位于城外,相当安全。他们在那儿一直呆到星期四(10月12日)下午,我国领事(注:据《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华书局,1985年),当时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为禄福礼(Harry English Fulford)。)命令他们渡河到汉口。因为担心一旦炮轰武昌,高级中学就将成为发起进攻的场所,所以一切外国人均从那里撤出。
以上都是武昌的事。下面讲讲我们汉口这边的故事,星期二(10月10日)一整天,我们都在听消息,星期二整天和星期三(10月11日)晚上,我们听到了枪声。接着星期四(10月12日)下午,英国领事馆来令,命令我们所有人在五点之前离开教会大院(注:教会大院位于汉口城中武圣庙(Wu Sheng Miao),距英国租界3英里。在那种情况下,汽艇显然是比通常的人力黄包车更安全的交通工具。)。我们大约只有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我的任务很轻松,因为我只有一些周末休闲衣服,所以很快就准备好了行装,然后准备所有人的食物和睡床,并在贝尔(Bell)和诺拉(Norah)送病人回家的时候,为他们做好护理安排。五点整,我们——克莱顿(Clayton)夫妇、布思(Booth)夫妇、修女艾丽斯(Alice)、贝尔、诺拉、明蒂(Minty)夫人与我——开始撤离。一艘汽艇已驶入汉江来接应我们,我们顺江驶往英国租界,尾杆上飘扬着英国国旗。下船后,我们被送入一间大空宅,这是当地一位乡绅慷慨地免费提供给教会使用的。
在这里,我刚刚听说邮政船将要起锚,所以我最好写到此处为止,明天起在下封信中接着再写。别为我们担忧,我们相当安全和健康。如果中国人没有什么麻烦的话,我们将会很高兴。
爱你们的 埃米莉
10月15日,星期日
于汉口英租界
为了节省时间,信封是请贝尔写的。
家书二
亲爱的家人们:
昨日之信匆匆而写,今天续写此信。我想,上一封信已告知我们在汉口租界的情况,一个大宅院借给我们作了免费避难所,院子空空如也,一片狼藉。无论如何,我们确实万分感激,有地方住就很不错了,还能抱怨什么呢。我们借到了几张席子,铺在地板上后,再把床单摊在上面。贝尔和我就在两张长藤椅上过夜。我们的房间里有五个人,大家挤在一起非常高兴。我们集中了所带的各色罐头,匆匆做了一顿晚餐,共有二十多人吃饭。餐后,我们几个未婚女子去帮助那几位太太们铺床,安顿孩子睡觉。最后,大家都落实了铺位,在这样的环境中尽可能地睡一觉。不时有枪声传来,但除此之外,一切平安。
星期五(10月13日)早上,留在武昌的人也过来了。我们雇用了三十二个强壮的仆人。我们的院子很大,人再多也可以住得下。星期五一整天,我和贝尔扎着头巾,清扫墙壁和天花板,并把我们要住的小阁楼打扫干净。修女艾丽斯(Alice)、诺拉·布斯(Norah Booth)、贝尔(Bell)和我四个人住在一起,我和贝尔睡在地板上的马鬃席上。一开始,我们睡在席上感到难受极了,但后来贝尔从医院带回一些东西,我们现在反而感到舒服多了。起初,我们常常会在半夜醒来,发出声声呻吟“哦,我的骨头,哦,我浑身酸痛。”真有趣,我们的房间里没有一点家具,甚至连日常换洗的衣服也没有。
后来,我们的厨师设法去了一趟武昌,给我带回一箱冬衣。这下,我过冬就没问题了。贝尔和诺拉也派厨师去取了些物品。我们不知道何时能继续工作,也许是一、二周以后,也许是二、三月以后,我们不得不做好准备,应付各种紧急情况。中国人都卷入了这场混战之中,那些有钱人已经逃往乡村或是被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上周,租界里每天人满为患,挤满了想要逃往乡下的中国人,他们肩扛手提各色各样的包裹,有的人还把小孩和贵重物品放在竹筐里挑着走,有的人花大钱,让船家把自己带往长江的上游。但他们常常会在半路上遭到抢劫,所有物品被一抢而空。而在空城里,士兵们却竭力维持着治安,对抓获的偷盗之人一律格杀勿论。结果,城里的坏人全都跑到乡下去了,在那里大肆抢劫偷盗财物。
至今,革命党人旗开得胜,占领了武昌、汉口和汉阳。大批人聚集在他们的麾下。他们军纪严明,决不允许偷盗之事发生。
10月17日,星期二
于汉口租界
我写了以上内容后,又有几天过去了,形势发展得很快。上星期三(10月18日),领事馆发布命令:所有英籍妇女儿童必须离开汉口,直接转移到上海去。出发时间定在星期四(10月19日)晚上。我们一边收拾行装,一边抱怨:汉口非常安全,而我们却要丢下手头的工作,匆匆撤离到上海去,真是懦夫之举。然而,我们在这里也无事可做。星期四早上,我们再次整好行装。我们总是随时准备出发,可能是在某个午夜,我们就会带上挎包,登上一艘炮舰离开汉口。
星期四早上,我们奉命必须撤离了。突然,英国领事和英国海军司令温斯洛(Winsloe)副元帅发来命令:留四位英国女士在汉口,随时准备护理受伤的士兵和志愿者,兼做其他工作,一位英国水兵作为这四位女士的警卫,以防出现危险。执行主席克莱顿(Clayton)先生当时并不在汉口,在他回来之前,人员的名单根本定不下来。有三位女士是肯定要留下的,她们是诺拉·布斯、修女艾丽斯(她俩是护士)和贝尔。但第四位人选很难定。大家认为帕特(Pat)太纤弱,而我们许多人都愿意留在汉口。最后,克莱顿先生回来了,他站在平台上,大声地宣布了名单,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布斯小姐,谢克尔顿(Shackleton)小姐(注:即艾丽斯。),威尔金斯(Wilkinson)小姐(注:即贝尔。)和尤因斯小姐将根据副元帅和领事馆的命令留守汉口。我告诉你们,当时我有多兴奋。我愿做任何的事情,我的特殊工作就是在别人做护理工作时,为她们看看家,做些病号饭之类的事情。我有时也帮着做一些护理工作。现在是诺拉在看家,因为租界内未发生任何战事。除非租界遭到炮击或轰炸,欧洲士兵才能还击。但清军和革命党人都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不把战火引向租界。看来双方都能遵守诺言。我们唯一担心的是:其中一方军队战败后,会借道租界撤退,因为租界离汉口城最近。上周,离租界六英里的地方发生了激战,我们能清楚地听到枪炮声,我们还看到了长江上中国战舰群向下游驶去。听到消息之前,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枪炮发出的火光,革命党人赢得了胜利,据说有二、三百人受伤。但真相谁也搞不清,因为到处是各种各样的传言。我们今天得知,在同样的地方还将有一场恶战。克莱顿先生曾想带我们去参观一下防御工事,他听了这个消息后就放弃了,过几天视情况再定。布斯医生(Dr.Booth)的医院里来了许多伤员,伦敦会(注:L.M.S=London MissionarySociety.译注:即伦敦会。1807年入华,总部设在伦敦(16,NewBridge St,London),1904年统计有信徒14748人,其中英国信徒486人。)医院也有不少,人们想组成一个红十字会,但又非常担心敌对双方不会理睬红十字旗帜。中国人看来已经知道红十字旗能保佑他们平安,很多人在房顶和商铺顶上插上了红十字旗。不用说,这样一来事情变得更复杂了!
我们都希望革命党能取胜。如果清军赢了,中国又要陷入混乱之中,新的思想根本不可能得到实现,甚至还会有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如果清军真的赢了,老百姓们希望武昌、汉口和汉阳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许多中国人公开说:他们等待着结果,再决定支持清军或是革命党。不过,他们的内心还是愿意革命党能成功。汉口的轿夫们会抬着想看一看打仗的人前去观战,分文不收。如果你知道以前轿夫们为了几个小钱而计较的情形,就能理解这场战争对他们的重要性。
昨天平静地过去了,我整天都在休息。晚上我们去了伦敦会教堂做了礼拜,这是座珍贵而小巧的建筑物,以接待外国人为主。克莱顿先生布道非常精彩,诺特(Knott)先生也在,还有贝京赛尔(Beckingsale)小姐,以及几位伦敦会的女士。今天我主要是在看书,我们努力搜寻所需的书籍,为以后的考试做准备。贝尔和我已经开始学习,想尽早通过考试。看来我们要呆上一段时间。我忘了告诉你们,我们的仆人中,有一个人渡江去了武昌,把我的衣服都带了回来,一部分整整齐齐地放在箱子里,另外的用一条床单杂乱地裹在一起,像是“红色葬礼上用的物品”。
好了,我不能再写了,不然会误了邮寄的时间。
送上我所有的爱。
爱你们的 埃米莉
10月23日,星期一
于汉口租界
家书三
亲爱的家人们:
这是续写上一封信,因为时间紧迫,不能一一给你们写信。另外,信是否能顺利寄达也难以确定。英国和中国的邮局都关门了,我们只有千方百计地找机会,看是否有去上海的人愿意带走我们的信,沿江而下,在上海把信寄出。因此,我不知道你们何时能看到这封信。
我想尽一切可能,力求按顺序把本周内发生的事告诉你们,当然这有点难,因为事件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它们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我先进一讲星期二(10月24日)这一天,上封信中已经提到星期一可能有一场恶战,那天晚上,我们整夜未眠,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星期二上午,我和贝尔继续学习。下午,我们开始制作红十字袖标和做其他的事。我们这儿是红十字会的一个分支,一旦开战,伤员将会源源不断地送进来。星期二晚上,双方终于在大约离我们七英里的汉水入长江口处开战了。距离如此之近,我还以为就在我们的门外呢。一开始革命党人就占了上风,我们全都很高兴。清军被打得节节败退,不断有伤员被送到各个教会医院,但总数并不多。星期三(10月25日)和星期四(10月26日)的情况差不多。克莱顿先生星期三带我们去看了租界的防御工事,一队队的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英国士兵严守在各自的租界入口处。这次的巡视令人兴奋,守住入口主要是出于一种担心,万一一方战败,士兵会借道租界,途经内城,那他们就会边逃边打枪。星期五(10月27日)早上,传来的消息更令人兴奋,革命党人已经推进到租界的边缘,他们正在修筑工事,要开始另一场恶战。尽管革命党人已经接近了内城,但仗一直打到现在还未停,他们的装备与清军无法相比,清军有机枪和大炮,以及受过德国教官训练的士兵。然而革命党人非常勇敢,他们一次次地发起冲锋。我恨透了机关枪发出的射击声,这个可怕的家伙一分钟能射出三百二十颗子弹,杀革命党人就像割草一样,一会儿就倒下一大片。我现在能体会戴维(David)在写赞美诗时祈求神力降临的心情,我真想用我最强烈的意志调转机枪对着清军扫射。当然受谴责的不应该是清军官兵们,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何打仗。北京政府很明白,假如清军官兵了解真相,他们肯定会投向革命党,所以清政府只告诉他们是平息叛乱,他们到了这里才领到了武器。清政府让所有的满族士兵(大约三千人)带着重武器在后面督阵,任何一个临阵脱逃的官兵都将被立即处死。现在有一些清军官兵也被送进了医院,在这里他们知道了是跟那些要使中国脱离满清统治的同胞们在打仗。真相使他们惊呆了,他们说:早知如此,他们绝不参战,但现在为时已晚。他们的话恰恰表明了清政府在他们的中国士兵中不得人心。
整个上午,战斗一直在延续,枪炮声不断。炮弹呼啸着在我们头上飞过。革命党人被迫撤到了火车站。临近午夜时,枪炮声暂时停了下来,克莱顿先生带着诺拉、修女和我到火车站去。那里挤满了士兵,有些看上去还是小孩。他们在首领的鼓动下,勇敢参战。他们的情况很可怜,浑身上下肮脏不堪,但他们还是准备再投入战斗中去。清军的大炮开始轰击火车站。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幸运地回到了住地。整个下午,战火又起,租界的房子也遭到了炮击。有消息传来说,清军的舰队首脑沙元帅,在星期六(10月28日)的下午要开始炮轰武昌。所以领事馆又下了命令,所有的妇女儿童必须离开此地,登上江上的船只。我们四个人则还是留在这里,还有银行经理的夫人和三位美籍女士。经理夫人说:如果情况紧急,她就躲到银行的地下室去,她决不离开丈夫。美籍女士们忙于照顾伤员。我们也做好准备,接受任何外籍伤员。我们把两个大房间作为病房——至少诺拉和修女做这件事,我和贝尔则卷那些能够拯救生命的绷带纱布。
星期六(10月28日)下午,汉口成了一座空城。所有的船只都开走了,只留下一艘英国炮舰凯杜斯号(Cadmus)停泊在我们房屋的正面。它的对面就是武昌,情况变得十分紧张。假如沙元帅下令轰炸武昌,来自武昌的反击枪炮就会落到租界。我们看到在长江下游三英里处的沙帅舰队。下午一点左右,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我们吃了午饭后,又开始卷绷带。枪炮声再次从后方响起,我们等了三个小时,这期间,我们看到子弹和炮弹飕飕地飞过江去。的确,三点钟时,呼啸的炮弹声又响,我们跑出门去观战。正如谚语所说:射击完美的捕鼠计划有时也会失败(thebest laid schemes of men and mice:gang oft agley sometimes),我们发现沙元帅的舰队受阻于一个临时修筑的江上要塞,革命党人勇敢地把它修筑在下游三英里的地方,正对着清军的十一艘战舰。沙元帅根本无法炸开它,结果也过不了这段江面,它们只能掉头向后开炮,我们看到炮弹爆炸和子弹射出的火光。幸亏有了这个要塞,我们未看到武昌遭到轰炸。三位伦敦会的女士已经登上将要驶向上海的战舰,现在她们又回来了,其中包括诺特(Knott)太太。
克莱顿先生刚进来取信,他说有可能请人代为邮寄,所以我们各自都匆匆写了信。昨天是星期六(10月28日),我们一整天都紧张地卷着绷带。贝尔、克莱顿先生和我把大批的绷带送到美国教会医院。在回来的路上,一发炮弹就落在我们后面几英尺的地方。租界的大批房屋遭到轰炸,我们听到炮弹的嗖嗖声,真的非常害怕。现在战斗延伸到了内城,尽管还能听到炮声,我们却安全多了。
我不能再写了,给你们我所有的爱。
爱你们的 埃米莉
1911年10月29日
于汉口租界
标签:武昌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尤因论文; 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汉口论文; 汉口租界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