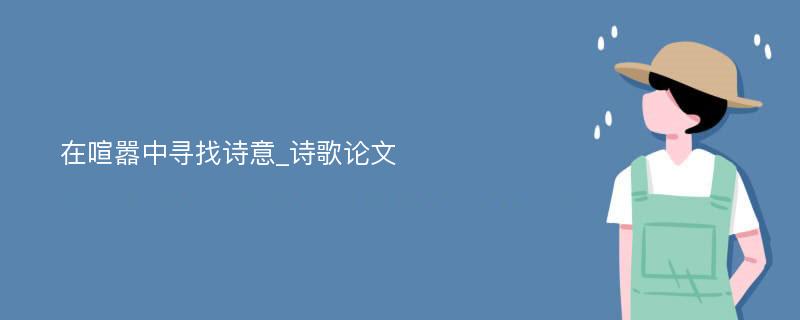
在喧嚣中寻找诗歌的路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标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4)05-0015-04
诗歌是什么?什么样的诗歌才能被称为好诗?诗与非诗、好诗与劣诗的界限在哪里?这是 在讨论诗歌标准时首先面对并值得我们不断追问的问题。用一种掉书袋的语义分析来考 查“标准”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明晰的启示。“标准”指的是衡量事物的准则,这个准则 可以在同类事物之间进行比较。“标”是一种标尺,一种高度,从距离标尺的高低可以 判断所处的位置,所达到的艺术水准,既然是标尺和高度,那么也意味着它不是每个人 都能轻易抵达的标高;“准”指一种准确的“准星”,是一种刻度,代表一种水准,它 可以评判高下优劣的天平,只要评判其离准星的距离远近就可以判断其份量的轻重和质 量的优劣。诗歌标准应该是衡量、区分诗歌好坏优劣的一个基本的艺术准则,也是一个 时代的诗人共同面临、努力抵达的路标,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艺术共同体,凝结着一 个时代在诗歌艺术上的全部艺术创造、智慧、精神境界的最高但又是最普遍的准则。围 绕在标准和路标周围的“风景”应该是关涉诗歌艺术命脉的一些基本质素,如诗歌的创 新与传统,诗歌的境界,诗与人的分裂合一,诗歌语言中口语与书面语的选择,诗学理 念中个人化与时代性、历史感的调谐,当下诗坛中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当然还 有对诗歌准则的追求与艺术个性的坚守等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诗坛是喧嚣善变的,标准是混乱且不断下降的。经过1980年代中 期“第三代诗歌”的全面冲击和1990年代“民间写作”旗帜的高扬,以及“知识分子写 作”与“民间写作”的激烈论争,加上后现代文化在中国诗坛的登陆和洗礼,目前新诗 写作中的“无标准”和“无难度”问题日益显得严重。在加速度的标准下降过程中,诗 歌的艺术品质也被不断稀释,“非诗”、“伪诗”满天飞,“丑诗”、“劣诗”随处见 ,笑傲江湖的是那些“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的无“诗”自通的诗人,而那些为艺术矻矻探求终生困惑于“没有十年写作经历怎么能成为一个大诗人”(此处借用 郑敏语)的诗人却被当成了历史陈迹。
标准是有底线的,底线意味着边界,意味着区分,意味着跨越和不能跨越。如果一定 要给出一个标准,那么给出的其实是一种边界和区分,如好或坏、美或丑、雅或俗、高 深或低下、精深与平易、优秀或糟粕、字字珠玑或胡说八道……也就是说,建构标准并 非是一个程式化、概念化、一成不变的凝固体,并不意味着框囿,建构标准其实是寻找 标准的方向,是我们在喧嚣中寻找一个诗歌的路标。在喧嚣和混乱的诗歌烟云中,如果 我们有了一个大致的艺术准则和路标,那么对诗歌标准的建构和寻找,则可能会得到一 个诗歌艺术前行的趋向和当下的定位,所以对于诗歌标准的思考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
一、谁去谁留:“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归途
要讨论诗歌写作的标准问题,不能不再一次提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 论争及其论争中所暴露出的问题。这场诗歌论争本来可能为一场在诗歌层面上深入探讨 、争论提供一种契机,但事实上它却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场诗人的争斗,而不是诗歌的 争鸣,所以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人事上的斗嘴打架,而不见有谁是“为真理而斗争”,“ 为诗而战”。“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用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境界几乎很 难看到。即使有谁试图向诗学的方向扭转方向盘,也经常被鸡零狗碎的“人斗”所消解 或在喧嚣的笔仗中却步。而另一个事实是:自从“盘峰诗会”之后,诗坛的分化现象似 乎越来越分明,同时关于诗歌标准的问题逐渐被搁置,关于诗歌写作中涉及的重要诗学 问题并没有得到理论的澄清。目前需要继续追问的或许是:当代汉语诗歌究竟向何处去 ?好诗与劣诗的界限在哪里?诗坛是否只能有“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二元对 立或握手言和?诗坛是否必须要有个你死我活的所谓主流与非主流方向的分野?在现在这 个吵吵嚷嚷的年代,他们之间所有的争论是否仅是一种“有意的误读”?
面对自封为“民间写作”的诗人,我所吃惊的是他们中很多人的言论和姿态,至今我 仍惊异于一些人的仇视知识(或许是因为仇视知识分子而恨乌及屋的)、对抗或谩骂文明 。但有时候我也想,与知识分子诗人有意作对的这种对抗,其中一部分只是混水摸鱼似 的嚷嚷,我相信他们只是在言语上对抗和拒斥,实际上他们对物质上的“文明”有着比 知识分子或真正生活在民间的普通人更强烈的欲望和享用。无知的人往往是心虚的,但 表面上很骄傲。所以我的感触是:无知者无畏,无知者无耻。最可笑的是自从“民间” 内部分化出“下半身”写作之后,“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就自然地演 变为“上半身”与“下半身”的论争。据说“下半身”代表身体,或者说性,“上半身 ”被划定为代表“头脑”、“知识”。我不知道民间生活在等同于性之后,民间生活中 的贫穷、苦难和压迫被丢弃在哪里?身处民间的弱势群体的爱憎和血泪被虚置或遗忘在 哪里?当口语变成了口水,积极的文学论争必然变质为消极的口水战,而其中所搀杂的 流氓气、小团伙气、类黑帮式的集团围攻显而易见,当然最恶劣的是论争中频频闪现的 政治术语和政治帽子……在“反知识”、“反文化”、“反理性”的大旗下,我为一些 人惊人的无知和以无知为荣而吃惊。我们这个民族从“反智”中得到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尤其是我研究了文革之后这种感觉犹甚!至今,我们缺乏的恰恰仍是“崇智”、“求 知”的社会氛围和文化抉择。
不过,其中的“智”与“知”不能简单化理解。“有知识”和“知识分子”是两码事 儿,“求知”、“崇智”并不等于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写作身份与文学精神、写作 立场并不具有天然的契合度。知识分子诗人应该反思的是:粗通文墨的人是否知识分子 ?有学院背景的人是否一定是知识分子写作?拿起笔开始写诗是否意味着一下子可以摇身 一变为诗人、变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写作”是否具有启蒙民间的合法性?诗歌中是否 用书面语写作就代表了文学的贵族性,是否就高人一等?同样的追问是:知识分子写作 等同于对知识的写作之后,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贫穷、苦难和血泪,知识的救赎力量在哪 里?面对身处民间的弱势群体,知识分子的爱憎在哪里?诗人在某种角度上的确可以说是 知识分子,既然是知识分子,就应有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批判性,也就是要在精神上有一 种人间的、人道的关怀,就应该把精神往高抬但把眼睛“往下看”。如果没有带有自己 生命体验的思想、情感的投入,没有人间、人道的关怀,那么知识只能变成知识的酱缸 ,失却再生的能力,而知识者也只能变成“长脚的书柜”,诗人也只能在知识化的同时 被“博物馆化”和“图书馆化”,知识的精神意义将正是在知识的传递中被消解殆尽。
据说,“当代汉语诗歌真的出现了看似已经无法弥和的分歧,由第三代诗歌运动发展 而来的口语写作、日常写作已经构成了当下诗歌写作的一支主流”、“面对民间诗人根 本不讲技巧、不讲诗歌精神的写作,只有知识分子写作才能代表着诗歌的前进方向”… …分歧肯定已经出现,但我觉得这样的自我感觉与自我判断多少有点一厢情愿。
日常经验与口语写作的盛行,致使诗歌写作变成了一种不需要任何技巧和任何思想的 平铺直叙,这种状况在“第三AI写作作”中尤为突出。诗歌的简易化倾向带来的是诗人和 诗作的大跃进生产。在“无标准”、“无难度”的口号蛊惑下,很多人认为诗歌是一种 最简便的文学样式,很容易写,不用进行大的结构和复杂的叙事,分行写作,不用长篇 大论地像写小说一样凑字数。过去一向被认为最难写、最难懂的诗歌,现在被很多人认 为最好写、最好懂,这是进步还是退步?但是,无技巧并不等同大巧若拙,那句“最高 的技巧就是无技巧”对于所有初学者来说是一句最有害的名言,“民间写作”、“口语 写作”口号的提出只是给庸人写作者提供了一个美丽的理论借口。因为一切文学艺术都 是一种需要技艺的、抬高的创造,尤其诗歌,作为最高的文学样式,被誉为“文学中的 文学”,它绝对不是可以普及或速成的。这使我想起了叶赛宁的名言:“我生来就是严 格的手艺人”,进而想起长期被遮蔽的诗人多多,他也像一个严格的“手艺人”,他的 诗歌写作就像是在操练一门“手艺”,但是他所修炼的手艺,并不纯粹是技巧的打磨和 推敲,而是包含了对思想的冶炼和提纯。
我们不要把自己真正的“无知”作为“反知识”、“反文化”的顺水推舟,也不要以 为多读了一点中国或外国的书就以为有了一种高人一等可以指点江山的优越感。我的意 思是:诗歌写作是一门需要技艺的手艺,标准、难度永远是大师跳高的超越刻度和诞生 新大师的最终依据。
二、二元对立之后:第N种写作的可能性
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中,对概念和人事的过多纠缠忽略掉的是 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即诸多复杂具体多元的诗歌创作本身和诗歌现象在二元化的对立中 被简单狭隘地遮蔽了,而其间批评话语的介入并未使很多问题有了理论化的澄清,反而 还是一团乱麻,而批评者战战兢兢的站队心理更使诗坛陷入非此即彼的绝境。我所思考 的是: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外,是否有第三种写作?甚至第四、第五 种写作?这第N种写作是否可能?难道我们只能非此即彼,或在此与彼之间亦步亦趋,不 能有一点旁逸斜出的超拔和独异?难道一场论争过后,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失语?
如果说论争仍有积极的一面,那应是边缘化的诗歌突然引人注目起来,诗歌出版突然 “繁荣”,让我们在局部的分化中看到多元写作的可能性,即:由于现在诗集、诗选在 编辑、出版上的圈子化、同人化,我觉得诗歌出版业的实绩为新诗标准的思考提供了具 体的例证。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一系列诗歌丛书,至今已经出版近百部诗集(诗选), 像“20世纪诗歌译丛”,对于一向冷落的诗歌出版来说,可谓盛事。早在1997年,王家 新、西川、孙文波、陈东东等被后来称之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些诗人就出版了一套诗集 “二十世纪末中国诗人自选集”;1998年,张枣、孙文波、黄灿然、张曙光、臧棣、西 渡等人也出版了一套“九十年代中国诗歌”;2000年,多多、宋琳、潞潞、杨克、郁郁 出版了一套“黑皮诗丛”。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以老诗人为主的“诗世界 丛书”(一般叫《××诗选》,包括沙鸥、吕剑、犁青、邹荻帆、蔡其矫、牛汉、绿原 、郑敏等)以及以青年诗人为主的“蓝星诗库”(一般叫《××的诗》,包含食指、舒婷 、顾城、海子、王家新、西川、于坚、昌耀、孙文波、肖开愚等)几乎成了新的“权威 ”诗选本。另外《他们十年精选》、《女子诗报年鉴》、《诗江湖2000》以及各种标注 “90年代”“20世纪”字样的诗集、诗丛不断出版。在这种热闹的诗集出版中,诗歌写 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自娱自乐的“地下写作”,也不再仅仅是标榜边缘性的“民 间写作”,这种诗集(选)的出版也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二元对 立的打破和诗歌写作的多元,也让我们再一次重新思考诗歌的标准问题。
诗歌出版中引起关注的是由韩东主编的一套《年代诗丛》,它主要选取四川的“非非 ”诗群(《非非》派)和南京的“他们”诗群(《他们》派),收录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以 地下民刊和网络为主要阵地的代表性民间诗人的重要作品。我想追问的是:对第三代诗 人而言,《年代诗丛》的出版是否仅仅意味着介入正规话语渠道从而进入文学史,从而 也就意味着有了一个正当圆满的归途?而失去了张扬之气、归入主流正途的第三代诗人 、民间诗人还有没有他们所一贯宣扬的生命力与活力?诗歌编选本身是最能反映诗歌的 审美标准,就像“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导火索最初也是由两本诗歌选 本——即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和杨克的《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引起争端 并扩大化的一样,我们不能一味指责他们在诗集编选中选择的褊狭,在“褊狭”中亦有 可能带来诗歌风格的净化和纯粹。正如程光炜、洪子诚二先生最近编选的《朦胧诗新编 》,把朦胧诗基本定位(几近等同)于北岛、芒克主编的《今天》形成的“今天”诗群, 这里面折射出的也是一个标准的问题。
而我个人所认同的是诗集、诗丛出版所关涉的诗歌作品本身,我以为,阅读优秀的作 品的确比阅读陷于意气之争的论争更为有效有趣,也更有积极意义。谈到标准,中国作 家并不陌生,我们曾经经历过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时代,但不是说今天就可 以翻转过来把个人化标准置于唯一的第一。在多元的时代,文学标准日益多元化,审美 不再是单一的,我们的诗歌标准也不应该是单一或者是排座次式地划定第一、第二一样 。关于多元化与个性化的问题,我赞成郑敏先生的观点:“目前的多元写诗实则带有滥 而不精、失去准则的缺点。‘个性化’本身并不能代替审美原则,因为个性有深有浅, 有雅有俗,岂能单独作为标准?也不是流行的就是好的,因为时尚也有良莠雅俗之分, 不成其为价值标准。”(郑敏:《我看中国新诗》,《思维·文化·诗学》,河南人民 出版社,2004年版)。多元的诗学观和写作风格是第N种写作的前提,基于对二元对立观 念的打破,我们是否应该把思考的重点放在“第N种写作是否可能?”的追问上。
三、极限与局限:在建构标准中寻找路标
客观而言,自1970年代的“地下诗歌”写作至今,当代汉语诗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同时也不断引起持久的诗学本身以及诗学以外的论争。尤其是经过上世纪末的“盘 峰诗会”、“沈韩之争”等等,喧嚣的论争遮蔽了诗歌本身的光芒和人们阅读诗歌的耐 心和清醒,简单的二元对立逻辑似乎仅仅给诗坛划分出了一个简单的流派对阵图,到了 新世纪,诗歌的面目基本上处于一种“既不见树也不见林”的状态。论争过后清点“言 语的碎片”,证明了很多喧嚣浮躁背后隐藏或曰暴露的恰恰是诗歌写作和诗歌认识的一 种极限和一种局限。极限启示的是诗歌在某一个方向上似乎已经走到尽头,现在必须回 头,必须撤退了,如果再走下去必然是局限的重复和面临枯竭的命运。没有标准,没有 难度,这样的写作能够维持多久?陷于论争漩涡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还 能走多远?
标准需要建构,但建构标准必须寻找到一些与诗相关的路标,因为标准不是唯一不变 的,而是带有指示意义的一个个路标。这其中必然牵涉一些基本的诗学问题,比如诗歌 的语言问题,“口语写作”绝不等于“口水写作”,“知识分子”也绝不能和知识本身 划等号,“非诗化”名义下的所谓诗根本就不是诗。诗歌从来都不是方块汉字的随意组 合,也并非是只要会写汉字就能写诗,更不是堆砌典故术语的知识概念轰炸。我以为诗 歌的写好写坏并不是操持什么语言的问题,即根本问题不在于是用口语还是书面语的问 题,而是怎么表达,怎么写的问题,在于诗人内在的精神贴近哪里的问题;也不是能否 引用外国人名地名、能否化用中国古典知识和西方文化因子、吸收中西诗学精神的问题 。
另外,从诗歌写作的创新与继承传统来看,文学创作如果没有标准,是否意味着我们 的审美能力出了问题,说明我们时代在把握新现象时的一种无从下手,我们对“超越” 远远胜过对“继承”的热衷和敏感,由此我们的兴奋点总是集中在“代”的不断更替中 ,批评总是追逐在“新”的话语聒噪中不断追尾,实际上可能仅仅是“搅浑水以显得深 邃”的一种策略。近一个世纪的诗史经验告诉我们,越是极端的作法越是对推进诗歌创 作没有益处,反而贻害无穷。在创新与传统中经常会被提及的是“影响的焦虑”,而“ 影响的焦虑”就是“创造的焦虑”,这种焦虑是每一个有志创新的写作者所共有的心态 ,即在漫长的历史流程中,写作者怎么寻找我自己,确立我自己而不至被湮没?所以“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经常成为一种摆脱影响的创新法宝,而古往今来的诗坛大 家,哪一个不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起飞,是深厚积淀后的超越?从这个角度看,未来出 现的优秀诗人必定是那些有创新精神,但同时又是能承古化古的人。
前段时间和郑敏先生访谈,她一再反问:没有诗人,哪有诗?我觉得这倒是讨论诗歌标 准的一个很好的前提。但面对纠缠于具体个人(甚至个人隐私)与纷杂人事上的诗情消耗 与精神角斗,我再一次想到的是鲁迅在上世纪初确立并疾呼的“立人”思想,而在新世 纪初的现实困境中,我却再一次清醒认知到“立人”思想在中国以及中国当代诗坛的任 重道远甚至遥不可及,所以我的现实立场暂时只能是对诗不对人。另外,我的呼吁是: 从“非诗”回到诗歌本身,从诗之外围回到诗之内核,这种精神和心灵的回归是一种艺 术的回归,但并不是回到所谓的民间或者知识分子,也不是回到诗人。
收稿日期:2004-0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