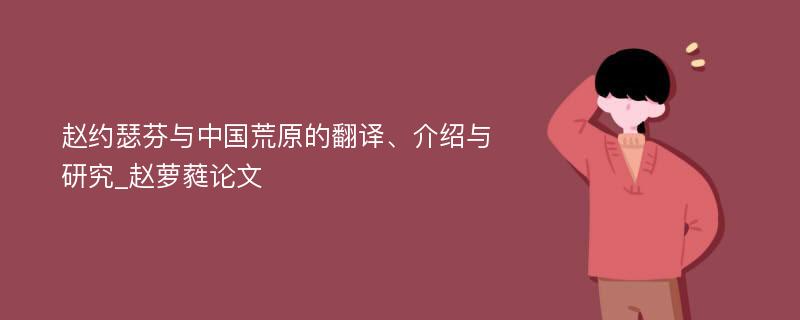
赵萝蕤与《荒原》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荒原论文,中国论文,赵萝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6)04-0111-15
1922年,T.S.艾略特(Thomas S.Eliot,1888-1965)出版了西方现代主义经典诗歌《荒原》(The Waste Land),该诗在西方引起震动,艾略特也因此而在英美现代诗坛获得霸主地位,并成为“世界诗歌漫长历史中一个新阶段的带领人”。《荒原》在中国诗歌界影响巨大,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对中国诗歌形成了自“五四”以来“第一个最大的冲击波”。② 但是,《荒原》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与一位著名学者兼翻译家的辛勤劳动密不可分。她就是已故的北京大学英美文学专家赵萝蕤先生(1912-1998)。不过,学界对赵先生翻译和研究《荒原》似乎重视不够。本文试图系统梳理赵先生译介与研究《荒原》的重要业绩,并以此管窥《荒原》在中国的流传以及中国学界对这部现代主义经典的释读与接受。
赵萝蕤1912年出生在浙江杭州,父亲赵紫宸是位著名学者、神学家。1926年,赵紫宸受聘担任燕京大学教授兼神学院院长,赵家迁居北京。1928年,赵萝蕤考入燕京大学,主修中文,1930年在英语教师的劝说下改修英文。深厚的家学渊源、良好的教育背景以及赵本人对中国古典诗词、英语文学的特别爱好,使得她在大学毕业时已经具备良好的中外文修养。燕京毕业后,赵萝蕤进入清华文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得到叶公超、闻一多及美籍教师温德的教诲。她喜欢写诗,“曾寄过三两首给上海的戴望舒先生,在他编辑的《新诗》上发表”。③ 温德先生对《荒原》的讲解,对赵先生后来翻译这首诗起到了重要作用。赵先生后来留学美国时,曾与艾略特在哈佛大学共进晚餐(1946年9月7日),艾略特带给她两本书:《1909-1935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艾在前者的扉页上写了:“为赵萝蕤而签署,感谢她翻译了我的《荒原》”。艾略特希望赵萝蕤先生接着翻译他的《四个四重奏》。
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艾略特在中国文学界已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中国文学界表现出希望了解艾略特的急切愿望。根据笔者的统计,从1933年到《荒原》汉译出版的1937年,我国期刊共发表评介艾略特的文章达50多篇,其中1934、1935这两年就有30多篇。主要有:1933年3月《新月》第4卷6期的“海外出版界”刊发了荪波介绍著名批评家F.R.利维斯的《英诗的新动向》(1932)一书的主要内容,该书的第三章讨论艾略特,说英国现代诗歌创作偏离浪漫主义“大半由于爱略特的努力。他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开始,树立了新的平衡”;1934年2月《现代》第2卷4期上发表了日本人阿部知二的论文《英美新兴诗派》(高明译),它是中国较早翻译的系统介绍艾略特的文章。文章指出,艾略特“乃是新诗派最重要的巨星”,又说,艾略特有“《荒土》(按:《荒原》)的长诗(四三三行),其流派可不问,从发表的1922年以来一直在英美诗坛保持着中心的兴趣,而至于今日”;1934年《学文》月刊上刊登了卞之琳应叶公超之约翻译的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这是最早在中国译介的艾略特诗学论文;1934年7月12日《北平晨报》刊载了宏告翻译的I.A.瑞恰慈写的《哀略特底诗》;1934年10月《现代》第5卷6期出版的“美国文学专号”刊载薛惠撰写的《现代美国作家小传》(有艾略特传略)、李长之的《现代美国的文艺批评》(提到了艾略特的诗歌观点)以及诗人邵洵美撰写的《现代美国诗坛概观》,邵文对艾略特评价很高,说《荒原》这种诗“是属于这个宇宙的,不是属于一个时代或是一个国家的。我们读着,永远不会觉得它过时,也永远不会觉得它疏远”;1934年《清华周刊》第42卷第6期上发表默棠翻译的R.D.Charques的《论现代诗》,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较全面地评介《荒原》的译文,说:“爱略特君对他同时代人的巨大的影响是不成问题的”;1935年《清华周刊》第43卷9期载有章克椮翻译的威廉姆荪的《T.S.厄了忒的诗论》;1936年《文学季刊》第1卷3期上发表了罗莫辰译的敏斯凯的《T.S.艾略忒与布尔乔亚诗歌之终局》;1936年《师大月刊》第30卷78期刊载了艾略特的《诗的功用与批评的功用》(赵增厚译);1936年10月《新诗》第1卷1期上刊载了周煦良翻译的艾略特的论文《诗与宣传》;等等。
至此,在中国艾略特的“形象”已经被定位为:英语诗歌中“一个新的开始,树立了新的平衡”和“对他同时代人的巨大的影响”。艾略特已经成为这段时间中国译介界的中心,仅艾略特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在短短几年里就重译3次,④ 就是明证。中国新诗人也早就注意到了艾略特,1928年徐志摩创作的《西窗》专门加上一个副标题——“仿T.S.艾略特”,孙大雨1931年发表的《自己的写照》,对艾略特的《荒原》模仿得更是“神形兼备”。诚然,此时中国已有不少评介艾略特文章,但普通读者并没有机会阅读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因而他们对艾略特的了解还只是“雾里看花”。
1937年,赵萝蕤翻译的《荒原》出版,整个中国文学界有机会目睹这位文学巨擘的“庐山真面目”。从接受理论的角度看,赵先生此时翻译《荒原》已经具备了十分适宜的接受语境,前面介绍的中国文学界对他的热情可为证明。但客观地讲,并非赵先生本人适时地抓住了这一时机,而是当时中国现代派诗歌的领军人物戴望舒。戴当时主持上海新诗社,请还是研究生的赵萝蕤翻译《荒原》。中国现代派领袖向西方现代派大师发出邀请,这一历史事实引入深思。赵萝蕤由于温德老师课堂讲授艾略特及其《荒原》,而“对于艾略特的诗歌发生了好奇的兴趣……无意中便试译了《荒原》第一节。这次试译约在1935年5月间。……到1936年底,上海新诗社听说过我译过一节《荒原》,他们很希望译文能够完成,交给他们出版,于是我便在年底这月内将其余的各节也译了出来”。⑤ 很快,《荒原》汉译本交到上海新诗社并顺利出版,这是“翻译界介绍西方现代派方面的一件大事”。⑥“赵译《荒原》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在于它是该诗的第一个汉译本,还在于它是译介到我国的第一部西方现代派力作”。⑦《荒原》汉译出版不久,林语堂主编的《西洋文学》就发表邢光祖的书评,称“赵女士的这册译本是我国翻译界的‘荒原’上的奇葩”。⑧
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艾略特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引进在近半个世纪里几乎没有进展,赵译《荒原》也就成了几十年中国内地唯一的译本。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之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介绍开始“解冻”。赵萝蕤对40多年前翻译的《荒原》进行了重新修订,并在《外国文艺》(1980年第3期)上发表,这是“拨乱反正”后中国发表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首部重要译著。赵先生在译文前写有序言,译文后是曹庸译的艾略特最有名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赵先生在“译序”中指出:“艾略特不仅是在他那一代人中几乎居于首位的诗人,而且也是颇有威望、多有创见的评论家和剧作家”。这位在1937年就翻译出版《荒原》的翻译家,近半个世纪后又首开新时期译介艾略特的先河,真是意味深长。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开始选编一套大型的介绍外国现代派的选读《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4册),历时5年(1980—1985)才出齐。赵萝蕤修订后的《荒原》入选该丛书第一册。
可能是受到赵译《荒原》的影响,很快,中国的艾略特译介就取得可喜成绩。1983年,《外国诗》创办的第1期(外国文学出版社)就用了大量的版面隆重推出艾略特:刊有裘小龙翻译的《荒原》,其翔译的《关于艾略特的评论两篇》,程红译的《艾略特谈他的创作》和赵毅衡撰写的《〈荒原〉解》。1985年,裘小龙在漓江出版社推出的《四个四重奏》更是一个较为全面的艾略特诗歌的汉译本。赵译之后有多位翻译家重新翻译了《荒原》,除已经提到的裘小龙之外,还有赵毅衡(《美国现代诗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查良铮(穆旦)(《英国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叶维廉(《诺贝尔文学全集》,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汤永宽(《情歌、荒原、四重奏》,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等的《荒原》译文先后印行。这些译本都出自名家之手,各具特色,翻译家们都力求从形式到内容再现这一部现代派经典之作。傅浩认为“赵萝蕤的译本流利畅达、不失为佳译;赵毅衡和裘小龙的译本显然受到了赵萝蕤译本的影响,但未能过之。”⑨ 我们想指出的是,80年代初赵修订印行的《荒原》又开风气之先,对在新时期传播《荒原》具有特殊的意义。
1995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当代翻译家自选集,赵萝蕤以“荒原”命名她的“自选集”,由此可知《荒原》一诗在她翻译生涯和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性。
1936年赵萝蕤翻译《荒原》,直接原因是当时的诗坛领袖之一戴望舒的约请。从文学交流与接受角度看,也可以解释为这件事情证明了当时中国文学界对艾略特的认同和需求。因此,一般很容易理解为赵萝蕤的翻译只是被动地迎合了他人的需求。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赵萝蕤作为诗人和英语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她十分清楚中国诗歌的发展,也非常了解艾略特诗歌的特别之处,对自己翻译《荒原》有着明确的目的性。
1940年,赵萝蕤应宗白华先生之邀撰写了《艾略特与〈荒原〉》一文,发表在宗先生主编的《时世新报》(1940年5月14日)。该文清楚地阐明了她翻译《荒原》的目的。她为什么要译这首“冗长艰难而晦涩的怪诗”?她被艾略特那全新的诗歌观念和深刻的精神内容打动了。她看到了艾略特的“最引人逼视的地方”,即诗人的“恳切、透彻、热烈与诚实”。而且,“这些特点不但见诸于内容,亦且表现为形式,因为内容与技巧实在是分不开的,”赵萝蕤深刻理解艾略特所表达的现代人特有的“荒原求水的焦渴”,看到“欧战以后,人类遭受如此大劫之后”,只有艾略特“将其中隐痛深创如此恳切热烈而透彻的一次倾吐”。她说:“因为艾略特的诗和他以前写涛的人不同,而和他接近得最近的前人和若干同时的人尤其不同。他所用的语言的节奏、风格的技巧、所表现的内容都和别人不同。”这些表明,赵萝蕤认为,《荒原》是一首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特殊意义的诗,值得向中国读者介绍。更重要的是,赵认为译介这首诗能切中当时中国诗坛之时弊,她指出:
但是单是不同还不足以使我好奇到肯下工夫,乃是我感觉到这种不同不但有其本身上的重要意义,而且使我大大地感觉到我们中国新诗的过去和将来的境遇和盼望。正如一个垂危的病夫在懊丧、懈怠、皮骨黄瘦、色情秽念趋于灭亡之时,看见了一个健壮英明而坚实的青年一样。——我感到新生的蓬勃,意念意象意境的恳切、透彻和热烈,都是大的兴奋。
赵萝蕤看到了“艾略特的处境和我们近数十年来新诗的处境颇有略同之处。”赵在文章最后说得更为直白:“我翻译《荒原》曾有一种类似的盼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常的大时代里,这其中的喜怒哀乐,失望与盼望,悲观与信仰,能有谁将活的语言来一泻数百年来我们这民族的灵魂里至痛至深的创伤与不变不屈的信心。”由此可见,赵萝蕤翻译《荒原》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或针对性,是她自己经过慎重考虑后做出的选择,而她考虑所依据的理由是《荒原》本身的独特艺术和思想价值及我国诗歌发展与接受者的现实需要。
翻译《荒原》,赵先生不仅目的明确,而且其译介策略与翻译方法也独树一帜,充分展现出她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的具有启示性的思考。她在《我是怎么翻译文学作品的》⑩ 一文中曾论述了自己的文学翻译观,刘树森先生在《赵萝蕤与翻译》一文中对赵萝蕤的翻译成就及翻译方法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我以为,赵译《荒原》有三点极富启示意义,值得我们认真领会:(一)“信”字为先;(二)充分利用“周边文本”(11),降低原作的陌生度;(三)具有灵活性的“直译法”。
“信”就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部忠实于原作,要获得“信”的效果,就必须充分研究、正确理解原作,如赵在《我是怎么翻译文学作品的》中所说:“对作家作品理解得越深越好”,她还认为:“文学翻译应该着重一个‘信’字。”为了获得“信”,赵萝蕤在接受翻译《荒原》任务后,“经过多方比较选择了当时较为理想的版本”,“首先对《荒原》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12) 她在1937年版的《荒原》“译后记”中说,为了更好地传达原作的风格,她对曾采用哪种体裁形式进行翻译设计了几种方案,如采用六朝的骈体、各种文言以及不同时代的文风,试图以体裁和文风的多样性从形式上努力再现《荒原》所包含的各种语言和文体。完成翻译后,她把“平时留记的各种可参考可注释的材料整理了一下,随同艾氏的注释编译在一起”。(13) 这体现出译者为了达到“信”而付出的努力。她一直坚持的“直译法”目的也是为了译文的“信”。“周边文本”指“序言”、“跋”、“注释”等,由于《荒原》典故多,征引复杂,跳跃性大,读来晦涩难懂,赵萝蕤充分利用“周边文本”,降低作品的陌生度。在1937年的译本中,她一方面对艾略特的原注进行增补,另一方面又对中国读者可能理解有难度的地方自己补充了30条注释。1980年,她在修订稿中又增加了15条新的注释,还根据当时中国读者已经长期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绝缘、并且“政治第一”的文学批评观还没有完全冰释的情况下,利用“译序”对《荒原》进行“一分为二”的解读。
赵萝蕤在《我是怎么翻译文学作品的》中说,“直译法”是她“从事文学翻译的唯一方法”,其内涵是:“保持语言的一个单位接着一个单位的顺序,用准确的同义词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译下去”,“单位可以是一个词,一个短句,一个从句,一个句子”。从《荒原》翻译实践来看,赵萝蕤所提倡的“直译法”至少在两个层面体现:一是词序,二是语言风格,即是书面语还是口语体;或者是哪个阶层的人使用的语言,上层人的抑或是普通人的。赵先生在多种文献中谈到文学翻译应该用“直译法”。她强调“直译法”的根据是“内容与形式统一这个原则”。她在同一文章中指出:“形式是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形式为什么重要是因为它能够完备地表达内容。”当然,赵萝蕤所说的“直译法”并不是一味地“硬译”、甚至“死译”,而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特别是要遵循不同语言各自的特点和规律。所以,她说:“若要直译法不沦为对照法全在于译者选择相应单位是否得当,也在于译者的句法是否灵活。”
如果我们把赵萝蕤1936年翻译的《荒原》和1980年的修订本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修订本更彻底地体现了她“直译法”的翻译观。例如《荒原》第一句:"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 ,1937年的译文是:“四月天最是残忍”;1980年的修订译文是:“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刘树森指出:“时隔半个多世纪,赵译仍为该诗流行最广的中译本。”(14) 其奥妙在何处呢?我认为,着重“信”字,透彻理解原作,正确把握原著风格,在尊重汉语特点前提下亦步亦趋的“直译”,充分利用“周边文本”降低原作的陌生度,是她的译文成功的根本原因。
赵萝蕤不仅第一个把《荒原》译成中文,而且她还是中国最早撰写研究《荒原》专文的学者。(15) 她的研究心得不仅体现在前文谈到的《荒原》的翻译及注释中,更体现在她专门撰写的研究论文里。尽管她的论述不多,主要是40年代初写的《艾略特与〈荒原〉》,80年代初为修订本《荒原》写的“序言”和稍后一点的《〈荒原〉浅说》。但这些论述却闪烁着深刻的洞见和独到的见解,反映出中国学者在某个特定时期解读和接受《荒原》的基本思路。
《荒原》汉译本出版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四处掠杀,赵萝蕤与中国众多百姓一样,生活不定,流离失所。直到1940年左右,宗白华问起《荒原》下落,她才寄赠一册与他。“宗先生觉得此诗的作者与本诗,都有加以解释的需要,命我写一篇关于艾略特的文章。”(赵萝蕤《艾略特与〈荒原〉》)这便是赵萝蕤的论文《艾略特与〈荒原〉》的“缘起”。该文是中国学者第一篇有分量的《荒原》研究专论。它“全面评析了艾略特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是国内评论艾略特的先驱文章之一”,(16) 在三四十年代中国《荒原》解读和接受方面具有代表性。
文章先交代了她翻译《荒原》的情况及原因,然后主要讨论《荒原》的艺术特点。赵指出艾略特与“前面走得不远”的诗人们如丁尼生、史文朋、洛维尔(按:洛威尔)、孔敏士(按:卡明斯)等不同,他们的诗歌是“浮滑虚空”的,而艾略特则是“恳切、透彻、热烈与诚实”。紧接着,文章从现代诗歌节奏、繁复的典故运用、对照与讽刺诗艺方面探讨了《荒原》的成就,探讨这首诗的“独到处”。著名文论家R.韦勒克在谈到为什么要研究文学时,以莎士比亚为例说:“我们要寻找的是莎士比亚的独到之处,即莎士比亚之所以成其为莎士比亚的东西,这明显是个性和价值的问题。”(17) 一个作家的“独到之处”就是他的“个性与价值”,一部作品的“独到之处”也同样是它的“个性与价值”。因此,赵文要讨论的正是《荒原》之所以成为《荒原》的独特价值。
《荒原》首先在形式上打破英国诗歌传统的藩篱,采用日常语言和“自由的诗句”(vers libre)的节奏,表现出其现代性特质,正如新近出版的《哥伦比亚英国诗歌史》所言,《荒原》具有“措辞上极端的现代性”(absolute modernity of diction)。(18) 赵文不仅指出了这一点,还大量引用《荒原》中诗行来说明诗歌内“所含的各种情致、境界与内容不同所产生出来的不同节奏”。换句话说,在《荒原》中,情致、境界与内容决定节奏。赵举例说,第一节“死者的葬仪”开头:“四月天最是残忍,它在/荒地上生了丁香,掺合着/回忆和欲望,让春雨/挑拨呆钝的树根。/冬天保我们温暖,大地/给健忘的雪盖着,又叫/干了的老根得一点生命。”赵文分析:“这一节自第一到第四行都是很慢的,和残忍的四月天同一情致。一、二、三行都在一句初开之始断句,更使这四句的节奏迟缓下来,在原诗亦然。可是第五行‘冬天保我们温暖’是一口气说的……是一气呵成的句子,在第一至七行中是一点生命力,有了这一点急促琐屑,六与七行才不至疲弱和嘶哑。但自第八行至节末,节奏完全不同了。”赵还举出了第二节“对弈”中三段诗来展示其“变化更快而紧迫”的节奏。叶公超早在赵译《荒原》的“译序”中就指出:“爱略特感觉一种格式自有一种格式的功用……但是当情绪转变的时候,格式也应当随之而改变;结果是,在一首较长的诗里,如《荒原》,我们应当有许多不同的格式错综在里面。”(19) 赵显然是读过叶文,但赵的论述比叶公超有更具体深入的文本分析。
典故运用显然是《荒原》的重要特色,旁征博引是艾略特的惯用手法。P.帕普落斯基在新出版的《现代主义文学百科全书》中说:“《荒原》实质上就是许多碎片的集合(collection of fragments),有些碎片直接来自于其他文本,艾略特拈来后适当调整构成新的整体。”(20) 赵用大量篇幅讨论艾略特的用典。她还注意到叶公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叶认为艾略特的用典与中国的夺胎换骨有“相似性”(叶公超《再论爱略特的诗》),而赵则认为两者有重要的不同:“即宋人之假借别人的佳句意境,与本诗混而为一,假借得好,几可以假乱真,因为在形式情绪上都已融为一体,辨不出借与未借;而艾略特的用典,乃是把某人某事整个引进,奇峰突起,巉崖果成,而且是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情绪,和夺胎换骨的天衣无缝并不相同。”这体现出赵作为学者的独立品格。依我看,艾略特丰富的学识和独特的传统观使他在创作中广征博引、左右逢源,并能把“向别人借来的东西溶化于独自的感觉中,与它脱胎的原物完全不同”(艾略特语),这确实与夺胎换骨极为近似;但他又常常直接引用英语以外的其他作家的原文,或通过注释,表示出他的用典来源,这确又是他的独特性。
赵文认为,《荒原》由“紧张的对衬而迷到的非常尖锐的讽刺的意义”,这构成了该诗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色,即对照与讽刺。赵文说:“这是一种戏剧家常用的技巧:正在融洩春光,忽然一场暴风雷雨,使天惨地愁,沉郁到更加不可支持的地步”,“这种尖锐的讽刺往往和用典的技巧相得益彰”。她列举《荒原》中描写女打字员与别人淫乱后的情态,“艾氏引入歌德施密斯的一个歌(详见253行注)。这歌本来是咏叹美丽的女人堕落时的哀怨感伤,叹息贞操,歌唱淑德的,而在艾氏的移用下便成为:‘美丽的女人堕落的时候,又/在她自己的屋里来回走,独自/她抚平了自己的头发,又随手/在留声机上放上一张片子’。”美丽的女人堕落了,但没有忏悔与哀叹,而是机械地、漫不经心地在留声机上放一张片子,多么尖锐的对照与讽刺!
文章最后谈到了《荒原》与社会时代的关系,指出:“要给他一个不亢不卑准确的估价,我们必须了解他的时代。”这样,赵文就由《荒原》的技术分析进而深入到了它的社会文化意义。只是结尾显得过于匆忙。
一般认为,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起点是意象派,而意象派主要是从诗歌语言上对传统进行革命,正如诗人罗·邓肯在《H.D.的书》中指出:“意象派诗人摈弃的十九世纪专门的‘诗词语言’,追求普通日常语言的句法和韵律。”(21) 从技术层面看,意象派要求现代诗歌运用日常语言,自然节奏,这正是后来艾略特等英美现代主义诗人所遵循的信条。赵精细剖析《荒原》所运用的语言及节奏,并认为这是《荒原》“技术独特性”的重要表征,这说明中国学者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释读已经比较深入。
众所周知,尽管《荒原》出版后受到庞德、威尔逊、艾肯等大批评家的赞誉,I.A.瑞恰慈在1926年再版其《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Theory)时在“附录”中也写有“T.S.艾略特的诗歌”一节,称赞艾是“寥若晨星的诗人”,说他的诗歌是“观念的音乐”(music of ideas)。(22) 但是,艾略特在西方诗坛确立其权威形象则是F.R.利维斯的《英语诗歌的新方向》(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1932)出版之后。该书第三章“T.S.艾略特”足足40页,而第四章“庞德”则只有18页,艾略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利维斯说艾略特的诗歌“自由地表达了一个完全生活在他同时代人的现代感受、感觉的方式和经验模式”。(23) 艾略特也因此在“他20年代的诗歌里开启了英语诗歌的新纪元”,利维斯特别强调了《荒原》中的“统一性”、“自由节奏”和“讽刺的对照”。(24) 我们无法确认赵萝蕤当时是否读到了这本书,但有《新月》杂志曾刊载过荪波写的书评,而赵与其丈夫陈梦家又常常被划入“新月派”。不过赵拈出《荒原》的语言、节奏、典故及“对衬”与“讽刺”,确是击中了该诗最突出的特点。
新时期,赵萝蕤为修订的《荒原》中译本所写的“译序”(25) 只有短短两千多字,却是一篇意味深长的论文。文章充分肯定艾氏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是在他那一代人中几乎居于首位的诗人”,并对《荒原》这首“划时代的、有极大影响力的诗篇”进行了重点评述:
在《荒原》一诗中,诗体类型很多:有时间的徐疾,诗句的长短,停顿的妥帖安排,各种类型的辞藻的运用,有土语,有十分口语化或十分抒情的片段,有暗藏讽刺的片段等,都真实反映了内容的性质。这些艺术手法对我国的新诗创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赵的“序言”不长,但其评价较为全面中肯,成为我国新时期评价艾略特这位现代派大师的先声。“序言”也提到了艾略特关于自己“在宗教上是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是保皇派,在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的那段著名自白,并说,这“毫不含糊地说明了他在思想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这种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这里,我们多少感受到文化语境对文学释读与研究的某种规约。
几年之后,赵萝蕤发表《〈荒原〉浅说》(26),目的是“试图使读者把这诗的主要内容掌握住”。与她40年代发表的那篇文章不同,该文重点阐释了《荒原》的内容。文章指出,《荒原》影响之深是现代西方诗歌多少年来没有过的,之所以产生“大深”的影响,因为它“集中反映了时代精神,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广大青年对一切理想信仰均已破灭的那种思想境界”。全文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对《荒原》进行“浅说”,分析了复杂的典故、引语、人物、象征,并重点论述了诗歌的思想内涵,所突出的是《荒原》的“认识价值”,这与当时社会历史氛围是紧密关联的。尽管赵萝蕤也提到了艾略特的“局限”,但在语气上、陈述方式上都与上文提到的“译序”不同,这表明艾略特及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在中国已经获得了较宽松的言说空间。
从研究思路和方法来看,赵萝蕤对《荒原》的研究基本属于文本解释型,即“通过分析、释义、评论确定作品的意义,通常侧重于晦涩模糊或者有比喻意义的段落进行阐明”。(27) 因为,《荒原》中充斥着“典型艾略特式的”“英语中从未有过的令人困惑的含混”(28),故而赵的解释从技术层面和思想内涵两方面展开。叶公超在《再论爱略特的诗》中借用艾略特在《但丁》一文中的话说:“一个伟大的诗人在写他自己的时候,就在写他的时代。他(艾略特)认为我们的一切思想都可以从诗里表现,但表现的方式是要用诗的技术的。”叶借此话来表达自己的文学批评观点,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条研究思路:艾略特的诗歌反映时代,同时又有技术的创新。从这点上看,赵萝蕤得了老师真传。40年代赵萝蕤在《艾略特与〈荒原〉》一文中说“我们觉得要了解艾略特,给他一个不卑不亢的估价,我们必须了解他的时代”,并认为“我们感觉到内容的晦涩,其实只是未了解诗人他自己的独特的有个性的技术”。这与赵萝蕤坚持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原则是一致的。她这一认识直接影响了她对翻译方法的选取,即“直译法”,同时,也影响了她对《荒原》的阐释与研究。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赵萝蕤翻译与研究《荒原》都有着明确目的,即帮助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这部伟大的作品。笔者曾有幸两次向赵先生请教《荒原》,她高度评价这首诗并强调外国文学翻译一定要为我国的读者服务,十分令人敬佩。
《荒原》介绍到中国已有近70年的历史,对中国文学尤其是新诗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部经典诗歌也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青睐,已有专论近百篇。毋庸置疑,赵萝蕤先生的翻译和研究对这部经典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她在译介和研究中所表现出的为祖国文化建设服务的自觉意识,在“为研究而研究”、“为翻译而翻译”的当下尤显意味深长,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学习。
注释:
①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转引自裘小龙译《四个四重奏》,漓江出版社1985年,第284页。
②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7页。
③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
④《诗与批评》第39期和第74期分别由曹葆华和灵凤翻译该文(译名为《论诗》),卞之琳译《传统与个人才能》发表在由叶公超主编的《学文》创刊号上。
⑤赵萝蕤:《艾略特与〈荒原〉》,收入《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17页。本文所引此文皆自该书,以下不再注。
⑥袁可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
⑦刘树森:《赵萝蕤与翻译》,载赵萝蕤译《荒原》,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116页。本文所引刘树森文字除特别说明外皆出自该文,以下不再注。
⑧《西洋文学》,上海西洋文学社,1940年第3期。
⑨傅浩:《〈荒原〉六种译本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⑩赵萝蕤:《我是怎么翻译文学作品的》,原载工寿兰编《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后收入《我的读书生涯》,第182-192页,本文所引此文皆自该书,以下不再注。
(11)伊夫·谢夫莱尔在《比较文学概论》中从热奈特处借用来讨论接受问题的术语。孟华在《翻译中的“相异性”与“相似性”之辩》中曾讨论过这个术语。见谢天振主编《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12)刘树森:《赵萝蕤与翻译》,见赵萝蕤译《荒原·序》,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4页。
(13)赵萝蕤:《艾略特与〈荒原〉》,《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17页。
(14)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5)此前,叶公超曾写过两篇总体评价艾略特的论文,参见拙论《叶公超与T.S.艾略持在中国传播与接受》,《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4期。
(16)刘树森:《我的读书生涯》“编后记”,载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17)R.韦勒克等:《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页。
(18)(28)Woodring,Carl.The Columbia History of British Poetry,Columbia UniversityPress,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p.572,p.571.
(19)叶公超:《再论爱略特的诗》,收入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21-125页。本文所引此文皆自该书,以下不再注释。
(20)Poplawski,Paul.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Modernism,London:Greenwood Press,2003,p.91.
(21)转引自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序言》,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第26页。
(22)Richards,I.A..Principles of Literary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26,pp.273-278.
(23)(24)Leavis,F.R..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Middlesex:Penguin Books,1932,p.61,pp.70-87.
(25)赵萝蕤为其所译《荒原》撰写的序言,《外国文艺》1980年第3期,第76-79页。
(26)赵萝蕤:《〈荒原〉浅说》,《国外文学》1986年第4期。收入《我的读书生涯》,第19-28页。
(27)Abrams,M.H..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7[th] ed.Fort Worht:Harcourt Brace,1999,p.127.
标签:赵萝蕤论文; 诗歌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四个四重奏论文; 传统与个人才能论文; 读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艾略特论文; 赵先生论文;
